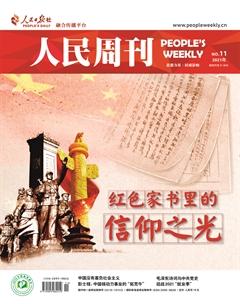古代小说中的谈文论艺
万晴川
古代小说因地位卑下,作者常攀附经史等强势文体以自高,并在小说中谈文论艺,以示博学,提高小说的品位,因此,小说中蕴藏着丰沛的文论资源,值得挖掘和利用。钱锺书先生早就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读拉奥孔》一文中说:“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可惜一直未受到学界重视。谈文论艺所涉及的内容很广泛,诗文曲赋、小说戏曲、书画篆刻等无不应有尽有,或由作者直接介入发表,或借小说中的人物代言,其中不乏精辟之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文艺理论和艺术两个方面。
文艺理论价值
文艺理论价值可从三个方面去认识:其一,发表文学艺术创作观点。如小说的虚实问题,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叙》中有过精彩论述,指出小说中的“事”真假不重要,关键在于“理”是否“真”。吴娥川主人《生花梦》第一回中说:(小说)“然不必尽实,亦不必尽虚。虚而胜实,则流于荒唐;实而胜虚,则失于粘滞。”认为小说创作应该合理把握“虚”与“实”之间的“度”。《海游记》第一回卷首诗云:“说部从来总不真,平空结撰费精神。入情入理般般像,闲是闲非事事新。”明确说“不真”就是小说的本质,只要描写“入情入理”,就自然新颖有趣。这些言论,无疑进一步深化了冯梦龙的小说虚实论。又如《野叟曝言》第十回写文素臣给法雨讲授七律章法云:“诗者,思也;律者,法也。非法无以限思,非思无以妙法。故一诗有一诗之意,无意则浅,有意则深;意显则浅,意藏则深。”阐述了诗歌创作中“思”与“法”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诗意”表达以深婉隐曲为佳。
其二,品评作家、作品。如《谐铎》卷二《隔牗谈诗》写作者某夜与几个已逝世的著名诗人冒辟疆、王渔洋、崔华和陈其年的鬼魂论诗,冒辟疆先是回答了作者关于古诗和近体诗以何为宗的问题,对古体诗和近体诗的发展脉络做了简明扼要的梳理和点评,堪称一篇微型诗史。在接下的对话中,作者嘲笑王渔洋以稗为史,指出崔华的名诗“丹枫江冷人初去,黄叶声多酒不辞”中“丹枫”两字辞义雷同,又不客气地批评陈其年的《梅花百咏》不及庾信的《咏梅花》。这些评论皆切中肯綮。《孽海花》第三十五回对李慈铭、黄遵宪、袁昶等近代诗人进行简评,如认为王子度(黄遵宪)的《入境庐》“纵然气象万千,然辞语太没范围,不免鱼龙曼衍”。《老残游记》第十二回老残点评王闿运的《八代诗选》、沈归愚的《古诗源》、王渔洋的《古诗选》、张翰风的《古诗录》等诗歌选本,其中批评《古诗源》将歌谣与诗混杂一起,也不无道理。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盛行,但千人一腔,千篇一律。《红楼梦》第一回借石头和空空道人的对话,斥责“历来野史”和才子佳人小说内容“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千部共出一套”;又指出“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宣称《石头记》乃“实录其事”。这段对话涉及小说创作、小说批评和小说接受等诸多问题。作者还借贾母之口,剖析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心态:“有一等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了这些书看魔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编了出来取乐。何尝他知道那世宦读书家的道理。”斥责作者缺乏生活体验,胡编乱造,其实是为了获得某种心理补偿。徐述夔《快士传》第一回中则分别指出当时佳人才子、神仙鬼怪等小说有“套语”“虚谈”“太腐”“太俗”“太杂”等缺陷。这些评论都目光犀利,首次揭示才子佳人小说程式化形成的深层原因,有开创之功,为后世学人所取资。有些作者借小说表达对某些文学疑案的看法,如清代流行《西游记》作者“邱长春说”,《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借扶乩驳斥这一说法,断定《西游记》“为名人伪托无疑”,乾嘉学者钱大昕和焦循都有同样的看法。《里乘》卷四《姮儿》中女仙姮儿点评唐诗,批驳《洛神赋》乃曹植感甄妃所作说荒谬不经,“考阿甄与陈思年齿悬殊,况曹文猜忌异常,陈思避嫌不暇,敢赋感甄乎?”“感甄说”唐已十分流传,许奉恩借姮儿之口辩驳,证据有力,对后来有关《洛神赋》的创作动机考察很有启发。
其三,传述创作技巧。如《儿女英雄传》第十六回:“这稗官野史虽说是个顽意儿,其为法则,则与文章家一也;必先分出个正传、附传,主位、宾位,伏笔、应笔,虚写、实写,然后才得有个间架结构。”这乃作者的创作经验之谈。《谐铎》卷二《垂帘论曲》借徐公子宠姬婢女隔帘论曲,细析南北曲之异同。一般认为,南北曲最大的区别,就是南曲有入声。徐婢指出南北曲中平、去两声也有不合者,这在曲论中首次提及。但“且北之别于南者,重在去声”云云一段,则袭自沈起凤的同乡前辈徐大椿的《乐府传声》。又如《儒林外史》中多次论及八股技法,马二先生称“(八股)文章既不可带注疏气,尤不可带词赋气”。从时代背景而言,八股是士子进入仕途的敲门砖,必须全力以赴,无暇顾及其他。再者,八股是一种具有严格规范的智力游戏,士子若沉迷于诗赋创作和学术研究,自然会将诗赋气和注疏气渗入八股,从而造成“破体”,因而《玉娇梨》中杨御史说:“诗词一道,固是文雅,文人所不可少,然最于举业有妨,必功成名就,乃可游心寄兴。”所以,站在当时的角度,马二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顾炎武称明代士子除八股外,“他书一切不观”,北人能诗者“千室之邑几无一二人”。《玉娇梨》第十三回写到山东省“读书的虽不少,但只晓得在举业上做工夫。至于古文词赋,其实没人”。晚清有人试图对八股进行改造,《孽海花》中曹公坊就主张“不拿时文来做时文,拿经史百家的学问,全纳入时文里面”。
艺术价值
作为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谈文论艺描写的艺术功能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有不少描写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成为“学术之汇流,文艺之列肆”。将理论价值与文学功能完美結合,《红楼梦》堪称典范。如第四十八回写香菱学诗,黛玉称自己喜欢山水诗人,主张写诗不必有太多的束缚,立意最为要紧,若“意趣真”,平仄可以不拘,词句不必修饰。她的文学主张与宝玉相似,宝玉创作《芙蓉女儿诔》,“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这些诗论继承明人“意趣”至上的主张,又表现了宝、黛的率真个性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第四十二回写宝钗论画:这园子却是像画儿一般,“你就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这番话不但表现出宝钗博学多识,还凸显了她装愚守拙、富有心机的个性。又如《浮生六记》陈芸论李杜之别,称更喜欢李诗的“落花流水之趣”,司马相如等作家和《西厢记》等戏曲作品也是她的枕头之物。其文学偏好正是她不为礼教束缚的写照。《青楼梦》第六回写挹香推重《石头记》的“情思缠绵”和《西厢记》的“文法词章”,也十分贴合她的个性。
《儒林外史》中蘧太守和鲁编修的文学观念截然相反,蘧太守认为“与其出一个斲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骘的通儒”,他教蘧公孙作诗要“吟咏性情”;而鲁编修则声称“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他从小把女儿当儿子培养,教她做八股,鲁小姐每日涵玩,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它”。这样,就为后来蘧公孙和鲁小姐的婚姻不幸埋下了伏根。明末清初的很多小说都提出诗贵性情,虽是老生常谈,但置于当时的语境中,也具有挑战八股和理学的进步意义。
总之,古代小说中的谈文论艺描写,是古代文艺理论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总体成就虽不能与专论比拟,但其中渗透着作者的创作经验,比一般的学者之论更切合实际,既可丰富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也可借此考察文论的传播和接受状况。而且,一般作为小说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发挥着刻画人物性格等艺术功能,因而值得学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