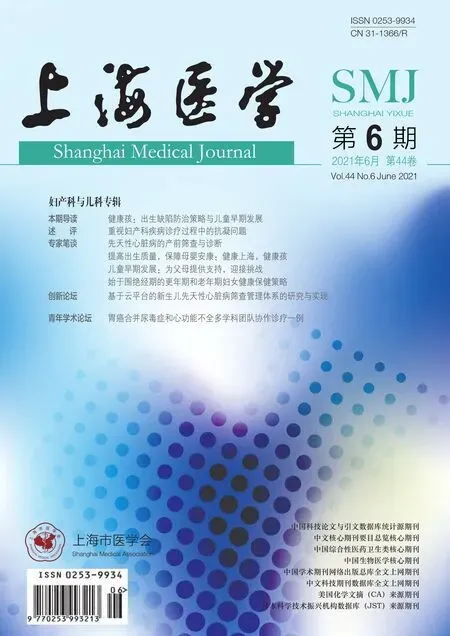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与卵巢癌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郭 浩 辛建海 韦伊芳 余沈桐 刘吴瑕
在免疫系统中,单核巨噬细胞具有异质性。在体内不同环境下,巨噬细胞的异质性体现在其对于不同微环境信号的刺激表现出较强的可塑性[1]。细胞因子和微生物产物极大地影响着单核巨噬细胞的功能,尤其是在不同微环境中,细胞因子能够诱导巨噬细胞分化。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r-associated macrophage,TAM)是存在于肿瘤微环境中,参与调控肿瘤免疫和生物学行为的巨噬细胞群。TAM是抗肿瘤免疫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其能够直接杀伤肿瘤细胞,或者提呈肿瘤相关抗原诱导体内免疫应答,从而发挥清除肿瘤细胞的作用。近年来,在对免疫治疗的研究中,人们逐渐意识到肿瘤实质或间质内存在的巨噬细胞并未完全发挥抗肿瘤作用;相反地,一些TAM参与了肿瘤的生长、免疫抑制、侵袭和转移等过程,这一现象出现在乳腺癌、前列腺癌、肺癌、淋巴瘤和恶性黑色素瘤等肿瘤中[2-4]。因此,深入研究TAM对认知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具有重要作用,TAM有望成为肿瘤治疗的新靶点。
卵巢癌是高度恶性的妇科肿瘤,其发病率居妇科肿瘤的第2位[5],患者5年生存率仅为30%~40%[6]。目前,对卵巢癌发生和发展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其遗传学改变方面,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TAM在卵巢癌的发生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一项meta分析结果显示,CD163阳性TAM浸润与卵巢癌的不良预后相关,肿瘤组织中M1型TAM与M2型TAM比值(M1/M2比值)高则提示预后较好[7]。可见,微环境中的TAM对卵巢癌的进展具有重要影响。以下从TAM的分类和特性、TAM对卵巢癌进展的影响和临床应用3个方面进行综述。
1 TAM的分类和特征
1.1 TAM的分类 根据免疫表型的不同,TAM可分为M1型和M2型两种亚型。“经典激活途径”的M1型TAM由IFN-γ或TNF-α或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诱导分化而形成,能够分泌高水平的促炎症细胞因子,促进辅助性T细胞(Th)1样免疫反应发生,在肿瘤组织中发挥肿瘤杀伤作用;“旁路激活途径”的M2型巨噬细胞由TGF-β或IL-4或IL-10或IL-13诱导分化而形成,具有很强的免疫调节作用,能够促进Th2样免疫反应发生(表1)。总体而言,M2型TAM具有抗炎作用,通过组织重塑和细胞外基质的分泌参与伤口愈合。大量研究[8-10]结果表明,在卵巢癌肿瘤微环境中,TAM以M2型为主(高表达CD206、IL-10),主要发挥免疫抑制作用,促进肿瘤的进展。
1.2 TAM的生物学特性 两种类型的TAM在细胞膜表面受体、分泌的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等方面存在差异(表1)。M1型TAM的膜表面表达多种模式识别受体,如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2和4,表明其在固有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Fc段γ受体(CD16、CD32、CD64),以及CD80、CD86在M1型TAM的细胞膜表面也显著表达,为T细胞的活化提供第二信号。M2型TAM的膜表面显著表达清道夫受体(CD204)、甘露糖受体(CD206)、CD14、CD163,以及Fc段γ受体Ⅱ,其中CD163是识别M2型TAM的重要膜分子,CD204在清除细胞碎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表1 M1和M2型TAM生物学特性
M1型TAM以分泌TNF-α、IL-1、IL-6、IL-12、IL-23和Ⅰ型IFN等促炎症细胞因子为主,M2型TAM以分泌IL-10、IL-1受体拮抗因子(IL-1 receptor antagonist, IL-1ra)等抗炎症细胞因子为主。此外,M1型TAM和M2型TAM也分泌不同的趋化因子(表1)。
M1型与M2型TAM在生物学效应分子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以精氨酸代谢为例,M1型TAM以iNOS和活性氧中间体(reactive oxygen intermediate,ROI)为主要效应分子[11-12];M2型TAM则主要表达Arg 1,以生成鸟氨酸和多胺类物质为特征,促进组织修复和细胞生长[13]。另有研究[14-15]结果表明,M2型TAM能够特征性地分泌表皮细胞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nsulin like growth factor,I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等,促进卵巢癌的进展。
1.3 TAM在卵巢癌中的分布 卵巢癌组织分为实质部分和间质部分,两个部分中均有TAM分布;在不同病理类型的卵巢癌组织中,TAM分布存在差异。在浆液性癌和未分化癌中,TAM主要聚集于肿瘤实质;在黏液性癌中,TAM以间质浸润较为常见;在子宫内膜样癌组织中,TAM浸润相对较少[16]。这种组织分布的差异可能与不同肿瘤组织分泌的黏液类物质和肿瘤性质不同相关[17-18]。除了卵巢组织外,TAM还构成了上皮性卵巢癌癌性腹水中的主要细胞学成分[19]。
1.4 TAM的分子标志物 分辨肿瘤中的TAM类型对于开展TAM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常情况下,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分子标志物对两种类型的TAM进行鉴别和流式细胞学分选。在使用CD68的基础上,加用M1型和M2型TAM的特异性表达分子进行共同标记,如使用CD80、CD86、iNOS、TLR2标记M1型TAM,使用CD163、CD204、CD206或IL-1RⅡ标记M2型TAM[8,16,20]。
2 TAM对卵巢癌进展的影响
研究[21]结果表明,多种效应分子介导了TAM与卵巢癌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生物学过程。Hagemann等[22]的研究结果提示,卵巢癌细胞能够调节TAM的表型。将卵巢癌细胞与TAM共培养后发现,CD204、CD206等M2型TAM相关基因的表达水平升高,表明其向M2型TAM转化[22];在微环境缺氧时,上皮性卵巢癌细胞通过分泌外泌体传递微RNA(microRNA)等诱导巨噬细胞向M2型转化[23-24]。Goossens等[25]提出一种更为新颖的假说,即卵巢癌细胞能够促进TAM细胞膜胆固醇的流出,间接地决定了TAM的表型。
反之,TAM也能够对卵巢癌细胞的生物学行为产生影响,体现在被募集的巨噬细胞通过分泌EGF、IGF和炎症因子等影响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迁移,以及影响化学治疗(简称化疗)药物的耐药性和免疫微环境等促进卵巢癌的进展。
2.1 TAM促进卵巢癌细胞的侵袭和迁移 卵巢癌的转移途径包括腹腔种植性转移、经血液和淋巴途径转移,其中腹腔种植性转移是其主要转移途径。有研究[26]结果显示,高水平的TAM浸润与卵巢癌转移和不良预后密切相关[27],逆转TAM的极化(M2型向M1型转化)可抑制卵巢癌的转移。
然而,TAM介导卵巢癌转移的机制尚未被充分阐明,越来越多可能的分子机制已被提出。Ke等[27]的研究结果显示,当TAM与卵巢癌细胞系SKOV3共培养时,SKOV3细胞中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2、MMP9和MMP10的表达水平显著升高,与TLR信号,以及下游NF-κB p65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通路的活化相关,表明TAM具有促进卵巢癌细胞侵袭和迁移的能力。新近的研究结果表明,M2型TAM通过分泌EGF激活卵巢癌细胞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ERK)通路,抑制长链非编码RNA LIMT的表达,促进上皮性卵巢癌的转移[15];球体形成是卵巢癌腹膜种植性转移的一个重要步骤,M2型TAM分泌的EGF可促进腹腔种植性转移早期肿瘤球体的形成[28]。
2.2 TAM促进卵巢癌脉管形成 脉管形成是肿瘤细胞与微环境细胞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肿瘤发生转移的先决条件。TAM广泛参与脉管形成的过程,如TAM分泌的MMP和组织蛋白酶能够降解基底膜[29],分泌的VEGF、血小板衍生因子(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等促生长因子能够促进血管、淋巴管内皮细胞的增殖等[30]。
研究[31]结果表明,TAM的数量与上皮性卵巢癌组织中淋巴管密度呈正相关,且TAM通过诱导淋巴管内皮细胞增殖、迁移来促进淋巴管形成。在卵巢癌中,腹腔CD68阳性TAM与高表达的血管细胞黏附分子(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VCAM)的CD31阳性内皮细胞紧密接触,提示TAM与内皮细胞之间存在相互作用[32]。以TAM与卵巢癌细胞共培养的上清液处理脐静脉内皮细胞时,内皮细胞形成的小管显著增多,使卵巢癌细胞迁移能力增强[33]。在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中,转录因子GATA结合蛋白-3(GATA3)介导了TAM与卵巢癌上皮细胞间的相互作用,促进血管形成[21]。
2.3 TAM促进卵巢癌细胞对化疗药物的耐药性 晚期卵巢癌的化疗主要采用基于铂类药物的联合化疗方案。研究[34]结果表明,紫杉醇在卵巢癌中的抗肿瘤作用部分依赖于重新激活对肿瘤的免疫反应,引导TAM向M1型抗肿瘤表型转化。然而,耐药性的产生使得卵巢癌患者预后不佳。Dijkgraaf等[35]的研究发现,基于顺铂和卡铂的化疗可诱导肿瘤细胞NF-κB信号通路激活,引起IL-6、前列腺素E2的表达增加,导致单核细胞向M2型转化,使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产生耐药性;若阻断这一过程,能够大大提高卵巢癌细胞对基于铂类药物化疗的敏感性。使用集落刺激因子(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CSF-1)受体抑制剂阻断TAM募集、减少肿瘤灶中TAM浸润,能够抑制化疗药物耐药性的产生,提高铂类和抗VEGF治疗的有效性[36]。
2.4 TAM促进卵巢癌免疫抑制微环境的形成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肿瘤微环境具有免疫抑制特性,这一特性促进肿瘤细胞的免疫豁免和存活。TAM作为卵巢癌实质和间质中重要的细胞成分,参与了抑制性免疫微环境的形成。
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是一种抑制性T细胞群,负责对自身抗原的免疫耐受和免疫系统活性进行调控;卵巢癌中Treg数量的增多与患者高死亡风险和低生存率有关[37]。进一步研究[37]发现,TAM通过分泌趋化因子CCL22介导Treg在肿瘤灶中浸润。除此之外,TAM可通过分泌IL-10激活叉头框p3(forkhead box p3,Foxp3)通路诱导CD4阳性T细胞向Treg分化;通过外泌体传递microRNA,抑制T细胞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STAT)3的表达,并促使免疫细胞Treg与Th17比值增高,从而促进抑制性免疫微环境的形成[38]。另有研究[39]发现,卵巢癌肿瘤间质存在一群TAM细胞簇,其表面表达B7-H4分子,该分子介导TAM与T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抑制T细胞的增殖和细胞因子的分泌;该群巨噬细胞负向调控T细胞免疫,与Treg的浸润和肿瘤预后密切相关。靶向B7-H4分子已成为一种解决Treg介导免疫抑制的免疫治疗新途径[40]。综上,TAM促进卵巢癌免疫抑制微环境的形成,为卵巢癌细胞免疫逃逸提供了必要条件[41]。
3 TAM的临床应用
3.1 TAM作为卵巢癌的治疗靶点 TAM作为极具应用前景的治疗靶点已受到广泛关注。目前,以TAM为靶点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3个方面:①抑制单核细胞的募集;②干预TAM的极化,使M2型TAM向M1型TAM转化;③抑制TAM中免疫信号的转导。
CSF-1和CCL2是募集单核细胞浸润的重要细胞因子。因此,阻断CSF-1、CSF-1受体或CCL2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止单核细胞向肿瘤灶聚集,使其无法发挥促进肿瘤进展的作用[42]。近年来兴起的材料生物学大大促进了生物治疗的发展,以纳米颗粒为载体投送生物分子靶向调控肿瘤细胞活性已成为可能。在近期的一项研究[43]中,研究者以纳米载体携带编码IFN调节因子5及其活化激酶核因子κB抑制因子激酶(inhibitor of nuclear factor kappa B kinase,IKK)β的mRNA治疗卵巢癌、黑色素瘤和胶质瘤,均取得较好的疗效,成功逆转了TAM的极化表型。类似的研究以TAM的叶酸受体2(folate receptor-2,FOLR2)为靶点,携带G5氨甲蝶呤(G5-methotrexate,G5-MTX)的纳米颗粒能有效清除卵巢癌病灶和腹水中的TAM,抑制肿瘤进展[44]。此外,关于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功能受到抑制的问题也有了较好的解决方法,即阻断TAM与T细胞间抑制性信号(如B7-H4信号)的转导,均能够抑制肿瘤的进展[40]。
3.2 TAM作为卵巢癌预后的重要预测因子 M1型TAM与M2型TAM在功能上相互拮抗,协同决定着卵巢癌的预后。有研究[45]结果显示,与高级别卵巢癌相比,低级别卵巢癌中M1与M2型TAM比值更高;卵巢癌转移灶TAM的总量和M2型TAM的数量均增多,表明M2型TAM数量的增多与高级别卵巢癌及其远处转移相关。Zhang等[16]对112例卵巢癌患者的临床数据进行分析后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M1与M2型TAM比值随着肿瘤等级的增高而降低,即该比值越高患者的预后越好。
除了TAM数量外,还有一些与其间接相关的生物学标志物对预测卵巢癌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如黏蛋白(mucin,MUC)2是在卵巢癌细胞中异常表达的黏蛋白分子,能够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转移。有研究[46]结果表明,MUC2与M1与M2型TAM比值呈负相关,可作为卵巢癌患者生存时间的预测指标。其他M2型TAM相关标志物,如血清IL-10、VEGF、CCL2和TGF-β等水平,对预测卵巢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无病生存期和化疗药物敏感性均具有重要意义[47]。
4 总 结
TAM作为一类高度异质性的免疫细胞在不同肿瘤组织中的作用十分复杂,具体的作用机制仍未阐明。作为肿瘤微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肿瘤生物学特性的重要因素,TAM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在卵巢癌中,TAM参与了肿瘤发展的各个阶段,介导了肿瘤的进展,成为极具应用前景的生物学靶点。尽管应用前景广阔,但以TAM为核心的治疗方法在临床应用中仍受限,其主要原因为TAM在不同肿瘤微环境中的复杂性和异质性,以及如何将该治疗方法与其他抗肿瘤方案有机结合。简单的M1、M2分型尚未完全概括TAM的所有功能,下一代测序和全基因组测序的发展必将为了解TAM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为其应用于临床提供更充分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