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写作、回溯视角与个体化叙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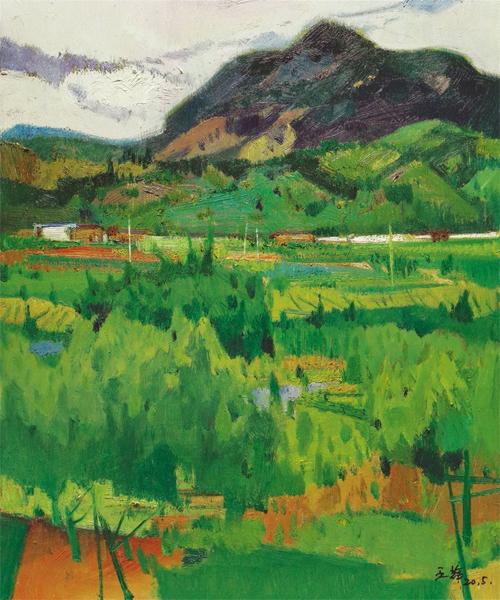
一
讨论新移民作家张惠雯的写作,我想到的第一个词是“中产写作”。与相当多移民作家更多依靠海外传奇景观吸引读者不同,张惠雯的作品并不依赖于“世界”景观的展示而宁愿聚焦人物内心的细微波澜。这应该与她对“世界人”“世界性”的不同理解有关。在与作家林森的一次对话《把爱人放在爱边界之前,那你也是世界人》中,林森说:“如果没有记错,我们第一次见面是2009年,当时我们一块参加《中国作家》在内蒙古乌审旗的一个活动。当时我刚刚到《天涯》不久,转眼十一年就过去了,我几乎都成了《天涯》最老的编辑了;你当时好像在新加坡,现在定居美国了。也就是说,不管是像我一样一直呆在一个岛上,還是像你一样,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世界人,积累一段时间再回看,其实变化都是很惊人的。你能否谈谈这十来年的生活轨迹?我估计国内你的不少读者,对你谜一样的行踪,还是很有兴趣的。”张惠雯谈到了自己对“世界人”的理解:“事实上,不少人周游世界,眼界和心胸也未必开阔到哪儿去。而你待在岛上、待在同一个地方,也并不会阻止你成为‘世界人。世界人和脚没有太大关系,它是一个精神概念。如果你觉得你是人类的一员,你和其他人类有一种同舟共济、相互依存的关系,你把爱人放在爱边界之前,那你也是世界人。”
所以,可以猜测,正是出于对“世界人”的这种理解,使得张惠雯没有把写作的焦点放在如何以人物的海外戏剧性经历吸引读者上,而是选择了另外一种叙述策略。在她看来,所有的人类都要面对同样的一些人生命题,比如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比如幸福的标准、人生的价值等终极问题。并且,在全球化时代,在物质日益繁荣的时代,这些问题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当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们会感觉幸福感问题、价值感问题、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越来越重要了。文学永远是为读者服务的。文学应该为弱势群体、为底层呼吁,这一点都没错,但是当越来越多的读者已经进入中产阶层,关心温饱之外的其他问题,我们的作家也应该更多关注他们新的心灵需求与情感需求。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重视中产读者,必须重视中产写作这个概念了。也因此,张惠雯才会在《在阅读方面,我是一个“杂食主义者”》这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小说是一门艺术,我觉得艺术本就应该风格各异,每一种风格都有它的魅力和光彩,它是千人千面的。所以,在今天的小说界,我们不仅应该重视一直推崇的那种关于时代、关于历史,譬如家族史那一类宏大的叙事,也应该去重视关于私人生活、关于家庭和情感中各种关系的精致的写作。我们不仅应该鼓励小说家去关注社会的底层,也应该鼓励他们把目光放开,看到社会的层层面面,比如也关注到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
同样,今天文学界一直在提倡“城市写作”,也是在提醒我们,我们面对的读者和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乡村经验不再是大部分读者最重要的生存经验,他们日常面对的场景是都市化的生存景观,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基本的温饱问题,而是各种精神压力与伦理困境,是解决了温饱之后的新问题。这是我们讨论张惠雯作品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她的作品特色的重要方面。她的叙述眼光决定了她对小说题材、人物形象和叙述旨趣的选择。
张惠雯的短篇小说因此往往选择身处中产阶层事业有成、但依然有着内在的缺憾与不满足感的人物作为她的小说主人公,在短小的篇幅中为我们展示人物曲折的心路历程与内心的巨大波澜,这种心灵的巨大波澜又与人物外表的平静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引起读者内心的震荡,引发关于人生选择、价值的种种思考。以《涟漪》为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年届五十的学者,当他回到一个多年前经常来的城市时,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他三十八九岁时在这个城市留下的一段婚外情。那是他在一次研讨会上认识了“她”,一个年轻的女诗人,两人逐渐互生情愫。尽管他在文学界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帮她谋取一些额外的利益,但她拒绝了。她不希望他们之间的情感掺杂利益的成分。作者没有用一种世俗的道德批判的眼光来叙述这段婚外情,反而为这段感情尽力渲染唯美的色调。应该说,和妻子相比,或许他和“她”在一起彼此更情投意合、更幸福。但命运展示了它冷酷的一面,当他终于鼓起勇气向她宣布自己即将离婚,也准备和妻子谈判时,妻子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了。于是,他的离婚计划夭折了,他与她的关系也不得不戛然而止。在情感和责任之间,他最终选择了责任。多年后,一切已然风平浪静,但他无法不回想起他们之间曾经的美好,无法不设想要是他们能够走在一起是怎样的人生风景,在他即将步入暮年时他只能接受自己充满遗憾的人生风景。“五十而知天命”。他的人生已经没有太多可能,留给他的只有记忆和遗憾:“我想到,一个人在故地重游时内心那一波波的涟漪、他被一个细微事物突然牵动而产生的痛楚、那种面对苍茫的时间却感到生命空空如也的怀旧和孤独……这一切,对所有别的人别的事物都没有任何影响,都毫无意义。而当我和她都死去,那段情事在世间再也没有任何痕迹,我们的生命踪迹也会一一被时间抹去,即便我们在亲人心中引发的痛苦、怀念,也会像涟漪一样慢慢荡开、消弥、平复。载满了作家、诗人、学者的大巴车堵在路上,偶尔向前,又戛然而止,车身随着后坐力重复着一波波轻微的颠簸。车里是一阵高过一阵的笑闹声浪,充满了插科打诨和有着性暗示意味却无伤大雅的玩笑。我假装疲倦,胳膊肘支在车窗边缘,专注地看着外面熟悉而陌生的景象,渐渐觉出一种喜忧参半的意味:在这里掩藏着一个挂着椭圆形镜子的房间,像是荒芜城市里的一小块绿洲,悬空的牢笼里的一个小天堂。车子终于能比较顺滑地往前行驶了,街边的灯纷纷亮着,灯光和暮色交织成一团半灰半蓝的烟雾,街景是压在这片半灰半蓝的毛玻璃下面的不断切换的相片……像一道一闪而过的光,像某个来自深处的音符,充溢着所有的绝望和希望,契诃夫小说里的那句话突然在我心里响起:米修司,你在哪里?”
显然,张惠雯的小说主人公衣食无忧,但他依然充满烦恼与遗憾。这种烦恼与遗憾与他生而为人遭遇的伦理困境相关。作者并没有为我们或者为小说主人公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她只是展示问题,让我们关注到问题的存在,毕竟,真正的选择权在人物和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二
关注张惠雯小说叙事策略的读者会发现,她的小说大部分采用回溯视角,在过去与现在这两个时空之间穿插,通过今昔对比展示人生可能性的丰盛与萎缩,从而引发我们对于人生终极问题的存在主义哲学式的思考。在这种不同时空的对比中,过去往往是明媚亮丽的,而现在则是黯淡无光的。或者说,每个主人公一开始都是充满成功的种种可能性,笼罩神奇的“灵韵”,但最终却日益走向平庸与贫乏。《梦中的夏天》以第一人称叙述“我”在国外与昔日心目中的梦中女神重逢的情景。“站在路边等待时,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是好几年前的她的样子,是我们一起走在北京的街道上、胡同里,要去某个地方或者只是飯后随便走走的情景。她总是会走在稍微靠前一点儿的地方,像是带领着我。于是,她的样子也总是我从侧面或后面一点的角度看过去的样子,通常是在黄昏里或是夜色里,她在那一小段我们都刻意保持的距离之外,高高的,温柔里隐藏着美人特有的甚至是无意的傲慢……过去,偶尔,在我的记忆里,这些影子会奇怪地重叠起来”。显然,在“我”的记忆里,“她”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她也曾经拥有美貌、青春和幸福生活的无限可能,但现实是残酷的,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她一步步远离人生的高光时刻,陪伴智障丈夫生活在异乡,“我无法不去想她是怎么度过这些年的,和汉森那样的一个人,在这么一个地方,在一个对酷暑和寒冷都无能为力的铁皮匣子里坐着、来回走着、流着汗,日复一日,听着《我梦中的夏天》这样的歌,看着小窗户外面橡树的阴影和快要被荒草吃掉的农场小路……她,连同她的美貌、青春的热力,被囚禁在这贫瘠、劳作和无望之中,像被无情地侵蚀、过早地凋谢了的一朵荒原上的小花……她说得对,如果她过去的生活不是梦,那么现在的生活就是个梦,一个墨绿的、冰冷芜杂的梦”。正如小说中的歌词所唱的:
“在这古老大树的绿荫下
在我梦中的夏天
在高高的青草和野玫瑰旁
绿树在风中舞蹈
光阴那么缓慢地流过,
圣洁的阳光普照
……
我看到我的心上人
站在门廊后等着我
夕阳正徐徐落下
在我梦中的夏天”
每一个人都曾经拥有“梦中的夏天”,但只要稍有偏差或者因缘不足,就可能与“梦中的夏天”失之交臂,丧失享受人生“高光时刻”的机会,只能面对日益黯淡的人生。
《昨天》同样是一次“回望”,“我”回望昔日的初恋女同学,如何从记忆中充满活力的样子,陷入眼前的庸常,从“空荡荡、冷飕飕,她穿着一条白裙子,站在光线阴暗的背景前面。这就像一帧镌刻在我脑海里的旧照片”变为眼前的一个普通中年妇女,“我注意到她只是微笑着看我们争辩。我刚进来时她有点儿激动的情绪平复了。偶尔,她睁大眼睛专注而直率地看着我,往日那种镇定、安详的神情像飞云的阴影般从她脸上掠过。但仅此而已。她的神情里已经没有我过去熟悉的那股仿佛努力克制住的热情和天真了,取代它的是一丝中年的惯常和倦怠。她坐得离我很近,在白色的灯光里,我们彼此看得更清楚。她脸色苍白,微微发灰,眼周和唇边散布着细纹。她像一朵完全干燥了的花,连衣服也过于中规中矩,就是一位疲于奔命的中学老师的样子。我想,生活并没有好好对待她”。
事实上,大部分人都会经历张惠雯小说中人物的人生轨迹,从充满理想、朝气的少年变为日益平庸、乏味的中老年。是什么夺走了我们年少时的梦想和冲闯的勇气?为什么我们会与自己理想中的模样一次次失之交臂?当你获得了足够的温饱与物质的保障后,你还依然葆有曾经的初心吗?你还依然记得什么是生活中最值得珍视的东西吗?这或许是张惠雯借由她的作品想要拷问每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人的问题。
三
写作对于张惠雯而言是对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心灵的感知和触摸,是一次次发自内心的个体化叙述的冲动,不是基于常规的道德判断,也不是基于一时一地的社会热点宣传,“小说家的目光不应该只看到那些大而化之的各种人的分类,而是应该看到每一个‘人的个体,看到这个‘人的生活的层层面面、形形色色的细节。在我的写作中,我有时甚至会刻意避开那些比较社会性或话题性较强的题材,因为我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小说,仅仅是因为它写得好,或者是它能唤起读者某种普遍的情感和感受力,而不是因为它涉及到他们所关心的某个热门话题。我希望我选择的不同途径,能够为众声喧哗的中国小说界带来一个不同的语调”。所以,她一直强调要关注普通个体可能经历的内心隐秘故事,而不是众人瞩目的英雄传奇;认为文学应该关注更为恒久的人性问题而不是某一节点的时代热点,“作为作家我只有一个义务,就是把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写好”。(张惠雯《把爱人放在爱边界之前,那你也是世界人》)
张惠雯的叙述关注的是作为个体的人,作为个体的男性和女性,作为个体的母亲和父亲,可能遭遇的诸多伦理困境。《飞鸟和池鱼》关注的是被亲情、孝文化绑架的年轻人,为了照顾病重的母亲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发展;《雪从南方来》中的父亲为了照顾女儿的感受,离婚后放弃了重新结婚的机会。《二人世界》中年轻的母亲沉浸在和儿子的日夜互动、纠缠中,逐渐抛弃了生活中的其他乐趣。这些问题与困境其实都是普遍性的人性的困境,是所有人都可能面对的,也是张惠雯孜孜不倦乐于叙述的。“对于潜伏在心灵深处的情欲、恶念甚至某些纯真的渴求,我可以尽情猜测,却永远也无法确定”。对于不确定的个体心灵秘密的探求,无疑是张惠雯叙述的最大动力,也是她写作最大的成就感之所在。
本辑责任编辑:练建安 马洪滔
郑润良,厦门大学文学博士,鲁迅文学院文学评论高研班学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编“中国当代中青年作家作品巡展”在场丛书、海南作家实力榜丛书、“锐势力”中国当代作家小说集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