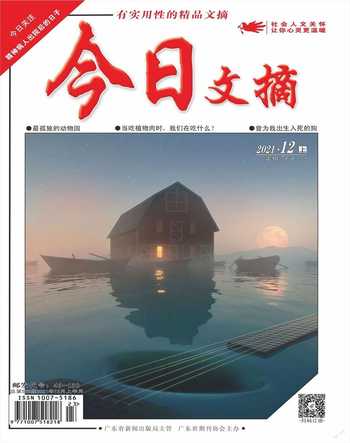精神病人出院后的日子
曾宪雯
很长一段时间,姜瑜都无法接受自己得了精神疾病的事实,“为什么是我呢?”她害怕遭到别人的议论和耻笑,在生病后的前两年,大部分时间都窝在家里睡觉、发呆、刷手机,她无法说服自己走出去,与人交流也仅限于家人和好友。“我会觉得,生病了,跟大家不一样了,我就是个异类。”
姜瑜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病耻感,在精神疾病患者当中十分常见。研究显示,64.5%的精神障碍患者有病耻感体验。她们担心因为精神疾患的身份遭到歧视,不能面对也不敢承认患病的事实,甚至会找出各种原因和证据否认、掩饰病情。而很多已经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就连吃药也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他们害怕被人发现。
“我是精神病人”
2017年秋季学期的一个晚上,正在教室学习的姜瑜,突然对着空气破口大骂,全班同学注视着她,眼神中满是疑惑与害怕。
姜瑜已经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就读于湖北一所私立高中的她,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持续高强度的学习压力让她喘不过气来。就在刚刚过去的暑假,姜瑜喜欢的男孩子跟自己分手了。就连昔日无话不谈的闺蜜,近来也突然不理她。姜瑜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些情绪堆积在一起,闹得她心里极不痛快。
“你去死吧。”姜瑜耳边的谩骂声已经持续了好几天,刚开始,她告诉自己要忍住,直到这天晚上,她再也受不了了。与空气对骂后,她也察觉到了自己的不对劲,主动和班主任说,让妈妈带自己去看病。
之后,医生诊断她为精神分裂症,姜瑜在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封闭治疗了一个月。根据《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规范》,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这六种精神障碍的确诊患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很不幸,姜瑜的病症名列其中。
近期发表在《柳叶刀》精神病学子刊上的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显示,我国精神障碍患病率达9.32%;而据央视新闻报道,截至2020年9月底,全国已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多达620万人。
4年前,精神科护士何敏突然频繁收到好友林宁发来的红包,因为数额不大,她没想太多。林宁表姐也说,她近来老是没有来由地给亲属转账,何敏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她打电话叮嘱林父带林宁去看精神科。“好端端的怎么会是精神病呢?”林父不以为然,在他眼里女儿只是情绪上暂时出现了问题。
接下来的几天,林宁的行为举止越来越怪异,她开始无端辱骂家人,把手机从三楼窗户扔下,不穿衣服在屋里跳舞,甚至觉得自己可以拯救世界。
林宁这才被家人送到精神疾病专科医院,由于症状严重,她必须马上住院接受治疗。经医生诊断,她的病症是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和抑郁交替出现,发作时会极度放大自己的情绪。
亲眼看到林宁发病,何敏吓坏了,她实在想不通,与自己相识十几年的朋友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在此之前还毫无征兆。
“旋转门”
第一次发病,入院治疗一个月后,姜瑜的情况出现好转,情绪逐渐平复,幻听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经医生同意,她出院吃药观察治疗。
新冠疫情暴发不久,或许是长期在家待着太孤单,姜瑜的幻听又出现了。与第一次发病时的谩骂不同,这次的声音是陪伴,“让你出去一个人转一转,会跟你聊天,鼓励你,让你觉得好像自己也不差。”有了第一次发病的经历,姜瑜已经大概能判断病情的严重程度,她自行前往医院,又封闭治疗了一个月。
第二次出院后,幻听并没有在姜瑜的耳朵里彻底消失,那个声音不再激烈,也不再温和,只是持续性存在着。她无法预料自己会听到些什么,也无法预料病情的走向。没过多久,姜瑜便出现严重抑郁情绪,厌食,体重急速下降。
由于精神疾病复发率高,社区的精神康复资源相对缺乏,很多患者出院后,只能呆在家里,无法得到专业帮助,极易复发,他们总在“住院——回家——再次发病入院”这个过程中循环往复。精神科医生常把病人这一过程称为“旋转门”。
从一个病情严重的精神障碍患者,到走出融入社会生活的第一步,姜瑜花了4年。和很多精神疾病患者一样,在这4年间,她过了两次“旋转门”,也曾与死神擦肩而过。如今的她看起来跟大家没什么两样,但她很清楚自己比大多数人脆弱,比大多数人更容易崩溃,也明白没有人能保证她再也不会发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康复中心主治医生王茹工作了十年,她看到太多的病人反反复复住院,作为医生,她感到无奈,“感觉刚刚把他送出去,没几个月就又开始乱跑,情绪不稳定,最后又回来住院。精神疾病目前没有办法查到完全的诱因,大都是综合因素导致的,所以没有治愈一说,没有说彻底治好了,都只能说是好转,就是说你现在稳定了,但也有复发的可能性。”
药的副作用
第一次发病,病情趋于稳定后,姜瑜回到了学校,可她没有办法再坚持高强度的学习,平日严重嗜睡,也很容易疲惫,注意力没法集中。姜瑜最终选择了回家,虽然母亲非常希望她参加高考,看到女儿的状态也只能放弃。
原本以姜瑜平时的学习成绩,她连普通高中都上不了。大概是初三开始努力,中考时她离重点中学竟然只差1分。“觉得自己还挺牛的,然后就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姜瑜说,她的学习积极性一直挺高的,只是这一场没有预料到的疾病,打乱了原有的计划,她不得不放弃学业。
回家后,姜瑜无法忽视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我以前吃药觉得自己变笨了,接受不了。”刚开始时,她没有按照医嘱,擅自停了药,没过多久,病情二次发作。一些患者服药后变胖变丑,停药也导致复发。
王茹见过很多因药物副作用私自停药而复发的病人,她再三强调,一定要按医嘱吃药,严重的精神疾病第一次发病,需要服药三到四年左右,如果复发五次以上,则建议终身服药,很多病人出院后會因为病情好转擅自停药,而一旦停药,复发的可能性极大,“如果副作用很大,可以找医生调整用药。”
精神疾病药物通用的副作用第一个叫过度镇静,就是会让你非常累,非常想睡觉,身上的肉非常松。第二个就是食欲增加。还有一些比较强烈的副作用,比如口渴、便秘、口水减少、震颤、烦躁、失眠。除此之外,血糖偏高或偏低也都是常见反应。治疗精神疾病,使用的药物一定是在正作用和副作用之间取平衡,有的患者严重幻听,药量吃多了副作用一大堆,人变得很僵硬,但到最后只剩下一点幻听,不太影响生活,就可以不用再吃那么多药物。
现实中,医生的治疗和调整用药可以让很多患者的病情和药物副作用之间达到一个平衡,但无法让患者的生活回到原来的轨道。
一名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出院后已居家三年,他不愿意相信医生的诊断,也不肯好好吃药。住院的那段时间,有人问起他去哪儿了,他的家人闪烁其词,告诉对方出远门了。为了不让更多人知道他的病情,一家人四处打点,对知情者千叮咛万嘱咐,害怕走漏一丁点风声。在他们看来,如果被外人知道孩子是精神病人,那以后就再也抬不起头来做人了。
重新融入社会
在精神科做了近三年护士,何敏听过很多家人的抱怨,“他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也有病人曾向她诉苦,“我现在每天都要吃药,好害怕别人问我吃的什么药。也担心哪一天他们发现我吃的是精神科药物。”除了安慰,何敏并不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这一点还是得靠自己,如果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周围环境怎么去接受你呢?”
实际上,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属产生病耻感,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社会环境对他们的排斥,数据显示,55.9%的精神障碍患者都经历过公众的歧视。
2017年2月18日,湖北武昌火车站附近,一名精神二级残疾的病人因口角纠纷,在一面馆门口持菜刀将面馆老板砍死;2019年5月14日,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一名躁狂症患者突然持刀砍向一名陌生女子,对方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近年类似的社会新闻不断,只要一个杀人犯是精神疾病患者,公众对这一群体总投来异样的目光。
很少有人主动和别人说自己是精神疾病患者,姜瑜也一样。她害怕一旦被贴上“精神病”的标签,哪怕做出一些正常人都会有的情绪反应,别人都会在旁边说上一句“因为她是精神病”。她并不否认一些精神疾病患者在发作时会有一定的危险性,“有的真的会伤人,但还是希望大家对这个病能多点了解,少些偏见。”姜瑜精神分裂症曾三次发作,严重时也出现自伤,但她从未伤害过其他人。
“过去把精神疾病妖魔化了,其实它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得高血压,也需要终身服药,精神疾病只是生病的地方不一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康复中心主任李先宾说,大众因为对精神疾病了解不够,才会对患者充满恐惧,他们更常见的状态是怕事、畏缩和自我封闭,而精神疾病患者杀人的极端案例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李先宾认为,正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偏见,才让精神疾患以生病为耻,延误治疗,最终难以融入社会生活。
对于精神疾患而言,急性期住院治疗是短暂的,并不能帮助患者走出家门、回归社会。李先宾希望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人能够更重视出院之后的康复治疗,“我们不太容易改变社会大众对精神疾病的偏见,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它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慢慢变好,但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改变的,而引导病人正确认识疾病、坚持用药和预防复发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目前,针对病情稳定的患者,安定醫院开设了日间康复病房,主要是为了帮助病人正确认识精神疾病,训练他们的社交技能,教会他们坚持用药。
一部分病人发作多次,大脑受损严重,不可能再回归社会生活,康复病房便把他们放在低功能区,康复过程中努力让他们能够自己解决衣食住行。还有一部分病人,出院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意回到社会,针对他们,康复目的则是回到工作岗位。
“现在是我生病以来状态最好的时候。”姜瑜的情绪平和了许多,在刚刚过去的夏天,她在一家私人影院做前台,闲暇之余也在准备大专扩招考试,这是她生病之后第一次真正尝试走出家庭这个单一的环境。
重新融入社会,是姜瑜打心底里高兴的事情,尽管情绪偶尔也有起伏、波动,她会转移注意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在慢慢重新了解自己,接受自己现在的一切。”(文中姜瑜、何敏、林宁均为化名)
(韩泽语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