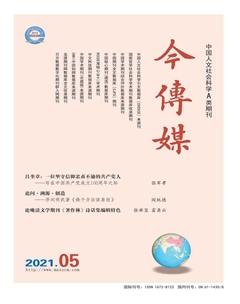“家园” 在中国生态电影中的解读和思考
温馨
摘要:家园议题于电影中的存在总是无形但却有力量。家园以或物质或精神的方式羁绊着每一位受众,但却总被人们忽略。家园应该如何适应现代电影需求出现在观者眼中?生态电影或许可以成为彰显中国家园风格的桥梁,几千年文化传承中的“知黑守白”定律融入“乡土中国”的生态电影中将喷发出一种极具民族、历史气息的火花。
关键词:生态电影;存在家园;精神家园
中图分类号: J9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號:1672-8122(2021)05-0105-03
一、家园的双重解读
把家园的概念放置在电影中,所代表的含义是具体的人物或出场或寻找或迷失的具体地点;是人物关系和故事不断展开的实际位置;是通过具体的空间栩栩如生地表达出导演对于具象家园的思考。实际家园一词从中国早期电影就开始不断地被演艺,《渔光曲》(1934年)、《乌鸦与麻雀》(1949年)等影片都呈现出因为历史问题,导致人们赖以生存的住所遭受外来人的侵占,人们生活的家园遭受大规模破坏,电影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时局下表现的是人们对实际地理位置“家园”“家”的追寻。等到战争结束,人们在废墟中重建家园,但也开始注重经济发展,人为地破坏自然家园,并在工业、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下,离开了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草原、乡村和鱼塘。在生态家园破坏日益严重的今天,人们又重新开始预设地球家园可能出现的问题,反思真实的“家园”存在的意义。
同时,影像中的“家园”议题也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传承中,家园已经深入每个人心里,一种以传统家庭为中心的思维让中国人形成了对家园的依赖。家园不仅是地理位置,更是心中的精神归属。当然,家园不只属于我们,其他民族在表达家园时,他们会将自己的种族描绘成拯救世界的王者,将家园的范围放大到整个宇宙。他们也会通过揭露社会黑暗引发人们改变物欲的生活方式,寻找一种精神层次的超越,探求现代人一直迷离和遗忘的精神空间。因此,影像中“家园”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空间实体,更是人们向前发展的精神支柱。即一切的起点,一切的归属。
二、生态电影中家园的呈现
“生态学”一词是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1869年将两个希腊词Okios(家园或家)与Logos(研究)组合而成的。可见,“生态”的确包含“家园、居住逗留”之意。生态家园是人类最直接的家园呈现,生态电影是指以生态思想为主导的正面表现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反思人类生态现状和社会发展模式,体现对人类生命和整体生态体系的现实关注和终极关怀的电影。中国生态电影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防治沙漠化》《森林和我们》《大西北种草》等带有生态保护含义的科教片让人们明白保卫地球家园的重要性。1989年具有故事性的生态电影《大气层消失》利用动物说话这一手法突破了生态电影“以人类为中心”的叙事视角,将生态电影的表现形式更加贴合当时人们的状态。
如果说之前的中国生态影片只停留在对实际存在家园的追寻,那么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2006年)则打开了人们精神家园的大门。在这最后的原始荒原上藏羚羊在减少,捕杀者在破坏家园,藏羚羊保护站的巡山队员则守护家园。“转山的人的手和脸很脏,但他们的心是很干净的。”巡山队员纯朴、善良、简单,他们仿佛没有金钱的欲望,守卫家园似乎是血脉里留存的法则。当镜头转向荒漠沙地上被秃鹫啄食干净的藏羚羊尸骨时,血淋淋的画面仿佛人类自己躺在那里。在现实的警醒下,现在守护“可可西里”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保护自然家园的标杆。为什么《可可西里》对西部地区的真实描绘能引起人们注意?是中国人自己身上血脉归属的牵引吗?是大趋势人们只注重经济而忽略生态自然的忏悔吗?可能是但不完全是,当影片落幕时,更多人是一种举足无措的无奈,可可西里就像远隔千里的母亲,无法陪伴但心里却明白她终将离去。那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我们不能再回去的家园。
青年导演李睿珺的电影《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4年)讲述了我国甘肃省两个裕固族孩子——哥哥巴特尔、弟弟阿迪克尔在爷爷去世后,暑假结伴寻找“水草丰茂的地方”的家园故事。在七天六夜的行程中,兄弟俩风餐露宿,一路上看到村庄变成了废墟,草原变成了盐碱地。当他们满怀憧憬地找到父亲时,却发现想象中水草丰茂的地方已经建起现代化的大工厂,而放牧的父亲也已成为淘金大军中的一员。就如影片中老喇嘛嘴上念的:“像母亲一样的河流干枯了,像父亲一样的草原枯萎了”。从《可可西里》中还有少部分青壮年抗争、保护家园,到《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青壮年选择逃离家园,只剩下将死的爷爷和老喇嘛与自然家园一起离去,儿童们迷失的表情和被动选择,逃离家园时渐行渐远的背影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人和自然变成了一种同方向的放弃,时间在往前看,越来越少的人还留在原地,“水草丰茂”的地方就消失了。
在高度工业化的后现代,人们不仅在恶化的环境中难以为生,同时还面临精神分裂、内心信仰恶化等危险局面。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精神上的流浪者,社会病态的追求经济发展割裂了凭借社会环境为生的精神依恋。生态电影《可可西里》《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都将这种现实家园被推倒、精神家园也同样迷失的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种自然观念的文化表述,它更多传递的是精神与信念,是生存的方式与可能,是重新思考自身生活方式的机会。生态电影作为人类面临生态危机困境时充满希望和理想精神的艺术尝试,它借助艺术审美将文化与信仰的救赎加以表达,它以艺术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与反叛”[1]。精神家园在生态电影中的追寻符合生态电影本身对“质疑与反叛”的探索,家园也可以作为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的支柱,充实生态电影的叙事。
三、“知白守黑”的生态电影模式
在《论真理本性》中海德格尔引用《老子》的一句话:“知其白,守其黑”。黑白之间的道理都明白,但仍为追寻某种平衡而将白棋保留,将黑棋展示在世人面前。黑棋在表面看起来是绕路,稍显愚笨。但真正将实际存在的东西抛开,放弃占据,放弃追逐,它则是诗意的存在。经济的高速发展把人们引入了光鲜的白棋世界,但“知白守黑”会不会才是最终的结尾?结合当前的电影模式,若现在我国的生态电影不同于其他国家专注未来和对现在家园的书写,放弃这枚显而易见的白棋,而是将古老却真实存在的故事进行描绘,守住纷乱世界的黑棋,或许能找到真正潜移默化地展示中国特色的方法,让世界发现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魅力,通过中国影像真正找到人类的精神依托。
不同于中国生态电影,国外的生态电影深入挖掘生态危机造成的严重后果。故事一般讲述因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而导致的自然灾难,人类迫于生存而选择逃离或者存在真正的勇敢者带领大众战胜危机寻找下一片绿洲。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从对自然的伤害到受到自然惩罚,是一种对家园的再认识。奉俊昊导演的《雪国列车》(2013年)就描述了这一主题。该片讲述了因气温骤降而遭遇嚴寒的地球,在疾驰的列车上穷困人民发动叛乱的故事。自然家园的破坏作为大前提对人们进行警示,当人们解决不了存在的、具象的家园问题时,就要搭上最后的“末班车”。和其相类似的还有电影《后天》(2004年)、《2012年》(2009年)、《哥斯拉》(2014年)等这样具有强烈震撼效果的,涉及温室效应、冰川融化、物种变异、瘟疫等的生态危机大片。将所要展现的内容放大化,家园便不再是个体的,而是世界的。家园面对的问题也不是缓慢的无能为力的服从,而是迫在眉睫的改变。国外生态电影在家园的塑造上,更强调对新家园的寻找,西方人很早形成的“天人相分”思想让其对地球家园的态度是征服自然,是“离家出走”的思维。而中国人对家园的情怀是“天人合一”,这种概念是深到骨子里的家园情结。
从家园的角度出发,保卫家园总要比逃离家园更为舒适,在2019年中国科幻电影之光的影片《流浪地球》中,便将“天人合一”的保卫家园理念运用得惟妙惟肖。拯救地球家园成为一条主要故事线,在电影中把家人的生死放在第一位,营造紧张气氛,是适用于中国观众的。将中国文化融入到电影里,彰显出独到强烈的中国风味。此外,《流浪地球》也将中国科幻与家——家园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体现出当代中国人对于实际存在家园的态度。生活在后现代的人们都将自身放置于地球家园,无论是否存在真正的精神乐园,实际存在时刻都牵绊着人们的感情,影像中的实际家园变成了一种共通的语言,人们达成共识,为的是更长久的与实际存在家园为伴。
四、生态关怀中的理想家园
文艺理论家鲁枢元在采访中说到:“要创造优秀富有生态精神的作品,最关键的还是在于观念的转变。文学艺术作品不一定非得表现污染、公害、环保、节能、救助动物、退耕还林等主题。关键在于对工业文化、现代社会深刻的认识和恰当的评价,从生态系统的立场和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定位出发看世界,重新审视那些被认作无可挑剔的理念,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劳动的价值和‘幸福的意义。有了深切的生态观念和诚挚的生态关怀,那么无论写什么都可以是生态的”[2]。再看“家园”一词,其代表着对固定的居住环境、安定的生活以及和家人和睦的关系,是普通人最基本的情感归属的需求,其甚至可以等同于“劳动的价值”“幸福的意义”。这就说明只局限于实际存在的家园是不够的,应该更多地去探索具有生态关怀的精神家园,尤其是中国人专属的精神家园。
在中国人专属的精神家园中,看不到弱肉强食的人类中心价值观,看不到尔虞我诈的种族排斥,更多的是人与自然的共生。人和自然本质上是相通的,相处模式是一个闭合的环,在不断的配合中“环”才能徐徐向前,人类对自然的思考不能仅是瞬间爆发的生态危机,而应注意滴水穿石般不经意的伤害。但现实中人们却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利益,一意孤行成为更多人的标签,当出现像李睿珺这样的青年导演去关注边缘人物时,会被大众称作“逆行者”。但作为与乡土最亲近的中国人,这才是顺应发展的本色,人们常说自己迷失家园,其实只是不愿承认自己是与土地共生的血脉。
家园本就具有自己的独特魅力,但却不能吸引我们。现在生态电影具有与家园相重合的点——对实际存在家园和理想家园的书写与改变。中国式家园找到它可以宣泄的合理空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中国式精神家园也许并不是我们一直往前走就能找到的,有可能转个身,家园就在那站着,向我们挥手。
参考文献:
[1]孙玮.中国生态电影的创作反思与审美走向[J].电影文学,2018(22):4-9.
[2]乔燕冰.生态关怀:艺术实践的时代精神——访著名文艺理论家鲁枢元[EB/OL].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1121/13/7954487 331000704.shtml.
[3]徐海涛.李睿珺《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的多重主题[J].电影评介,2016(9):35-37.
[4]曾繁仁.生态美学的东方色彩及其与西方环境美学的区别[J].河北学刊,2012,32(6):29-33.
[5]牟方磊.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理论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0.
[责任编辑:武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