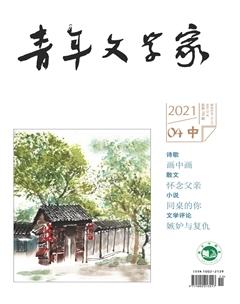林清玄散文中的“小人物”创作
张沁仪
林清玄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其乡土散文融入了他的家国情怀、乡土情怀和宗教情怀,开创了台湾乡土散文的新气象。林清玄同其他乡土派作家一样关注台湾社会中卑微的小人物形象,农民、士兵、小职员、小商贩,乃至三教九流的方外人等,都是他笔下鲜活的主角。但是林清玄并不着意去刻画或批判左右小人物命运的社会力量,也不是从这些小人物身上发掘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因素。他笔下的小人物大致可以分为“时代造就的可怜人”、“社会转型的边缘人”、“顿悟佛理的世俗人”三类。他们大都笼罩着“柔软生刚强、宁静而致远的温情”,共同展现了林清玄精神家园的思想内核。
一、时代造就的“可怜人”
林清玄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意识在他创作的“时代造就的可怜人”这类小人物身上可以体现。林清玄生于台湾,没有在大陆生活的童年经历,但是他从小聆听老一辈人讲述大陆的故事,对老一辈台湾人的乡愁感同身受。因此,他的创作与余光中、琦君等作家有所不同,他对大陆深厚的情感往往是通过其笔下“时代造就的可怜人”这一类小人物形象所展现的。
《月光下的喇叭手》刻画了一位送葬吹喇叭的老人。老人24岁被迫离开家乡,来到台湾参军,退伍后也未能回到故乡,成为了一名喇叭手。林清玄以感伤动人的笔调,讲述了这位饱经沧桑的退伍老兵的故土情怀。贫困和衰老消磨了老人的外在形体,只有烈酒给予他暂时的安慰。老人一开始装模作样,后来“装着,装着,竟也会吹起一些离别伤愁的曲子”,以曲寄情,宣泄他的乡愁。林清玄将月光与乡愁交织在一起,让历史与现实交融在月光下的苍老的喇叭手身上,使乡愁中又蕴含了对时代的感叹。“喇叭手”既象征了无数失落故土的流浪老兵的心灵律动,又隐喻了历史悲剧之后的集体化的乡愁冲动,营造了老一辈台湾人失去故土、失去家园的悲凉感。
林清玄塑造的“时代造就的可怜人”往往体现了离乡、战争、边缘化的三重悲剧。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大批人卷入了战乱,背井离乡来到台湾,最终因为历史因素等原因无法归乡,但又难以融入台湾社会,最终被时代遗忘,成为社会的边缘人。林清玄由这一类小人物展现被历史原因暂时分离的海峡两岸所具有割不断的种族亲情和文化血缘,将乡土情怀植根于家国情怀和民族意识,探寻老一辈台湾人的精神家园。在创作过程中,林清玄还常常会通过月亮等传统意象渲染意境,透露出一种历史的苍凉和悲壮之感,显现出其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深挚情感。因此,虽然林清玄书写的都是所见所闻的故事,但是他所展现的家国情怀却浓烈且厚重。
二、社会转型的“边缘人”
20世纪以后,台湾的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社会进入转型时期。林清玄虽然生长于都市,但是对现代都市文明颇有微词。他称工业社会和后工业时代为“包装的时代”,把台湾社会转型以后,人性的普遍失落造成的精神危机,比之为“洗碗水社会”。在社会的极速转型之下,都市中出现了一群“乡下人”。他们无法适应都市的生活节奏,没能跟上社会转型的步伐而被社会边缘化,成为了社会转型中的边缘人,而他们身上又往往体现了坚韧的品质。林清玄常常以同情的笔调叙写这类小人物的生活境遇。
《阴阳巷》展现了同一栋大楼中都市人和乡下人两类人物的生活境况,刻画了房东、简老先生等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描绘了一幅典型的都市角落图。《阴阳巷》最后用 “黑白”与“彩色”象征了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的生活状态。“黑白页里的人往往向往着彩色,而有了彩色的人又都忘记了他们黑白照片中的一段日子。” 乡下人向往融入现代化社会,而都市人又在现代文明中迷失自我,出现精神危机。林清玄在抒发对“社会转型的边缘人”这类小人物的同情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乡下人与都市人之间的矛盾,即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通过都市中的“乡下人”挣扎搏斗的生存状态的刻画,表达了其对乡村文明的眷恋和对都市文明的抵触。
林清玄对这一类人物的刻画执着于他的乡土情怀。他在乡村长大,对土地和乡村生活怀有深厚而执着的情感。在经历了台湾工业经济的冲击后,林清玄敏锐地发觉了从生态环境到伦理道德与人的审美关系所发生的变化,意识到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生态失衡。因此,他时常在散文中表达出对现代化进程中都市人失去土地和精神家园而产生焦虑、浮躁的生活态度和社会种种争斗、污染的担忧。但林清玄始终怀有对社会和生活的热爱,他深谙社会转型期人性的陷落和精神的挣扎,却少有对社会的着力讽刺与批判,也没有后现代主义荒谬、颓唐的色彩,他始终带着人文关怀去看待那些与生活挣扎搏斗的人,思考现代人生存中的矛盾和问题。
林清玄通过社会转型下的“边缘人”的生活状态反映都市人急功近利、心性浮躁的生活状态,进而关注现代社会中人们精神家园的缺失。他以真实、生动的笔触描绘了20世纪台湾人的精神现状,反映了其对人性与自然的思考。对这一类小人物的刻画反映了林清玄在现代社会中寻找和重建精神家园的思想历程,表达了他对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
三、顿悟佛理的“世俗人”
林清玄笔下“顿悟佛理的世俗人”是他个人的写照。林清玄虽然皈依佛教,却没有远离尘世,他认为“红尘里就有菩提”。他信仰佛学,但没有消极避世,而是积极地从日常生活中感悟佛学智慧。因此,他的散文没有单纯地宣扬佛教思想,而是用自己独特的体验和深刻思索得来的智慧来贴近生活化的佛教哲学,在佛学世界中展现宁静致远的生活态度,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一点在他的散文《木鱼馄饨》中就得到了很好地体现。
《木鱼馄饨》描写了一位常常在深夜敲着木鱼卖馄饨的老人。“木鱼”是佛教徒诵经的法器,“馄饨”是满足口腹之欲的器物。木鱼于馄饨是佛性的象征,高雅的别致,馄饨于木鱼是世俗的事物,陌生的存在,两者毫无关联。因此,林清玄在小街小巷里听到木鱼的声音时有一种神秘感和惊喜感,但是当林清玄发现木鱼仅仅是老人一个简单的信号,是老人劳苦生活的工具时又感到了失望。而在与老人的相处中,林清玄渐渐发现“木鱼”与“馄饨”是可以融为一体的。老人只着一袭布衣,他的馄饨完全是精肉做成,不加一点葱菜。他三十年如一日的深夜敲木鱼,就是让远近都听闻而不至于吵醒熟睡的人们。因此,木鱼不仅是老人的生活工具,还是老人为人处世的象征。餛饨摊子虽然普通,却在静谧的深夜,用一种蕴涵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叫卖”。老人虽然是一介俗人,但他内心简单且干净,生活恬淡而宁静,拥有一套自我生命哲学和生存价值,蕴含佛学智慧。
《木鱼馄饨》中的老人可看作林清玄自己的化身,老人的生活态度也是林清玄的真实写照。在生存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林清玄主张人的佛性的回归。林清玄的人生信条是“快乐即在当下,尽心即是完美”。他认为“禅”就是“表示简单”,要功德圆满,充满禅悦,就要学会“简单”,学会“活在当下”。他始终心怀禅意去观察生活、感悟生命,用出世的眼光看待尘世,他的宗教情怀中常常包含了其对人间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其说林清玄是“虔诚的佛门弟子”,不如称他为“佛教文化的欣赏者”。他的宗教情怀更像是他在传统的生存状态与现代的生活方式之间搭起的桥梁。林清玄注重的并非具体的社会问题的解决,而是个人的自我修炼。他所彰扬的侧重于心灵的澄明、精神的提升、感情的超脱、境界的清净等,更像是他为现代社会中的都市人找到的心灵的慰藉,是对精神家园的重建。
四、结语:
林清玄的散文不会着力叙写人物的大喜大悲,而是将人物情感的外部宣泄转化为了内部的生长,引而不发,使人物形象更具张力。因此,他的散文常常让读者感受到简单又自然的美好。他以细致而真实的笔触勾画出“小人物”的生命际遇和内心世界,一方面寄托了自己对他们生存境遇的同情和忧虑,另一方面也借助于对这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描写,揭示他们平凡人生的审美价值,并上升到佛教意义的生存关怀。正是出于精神上的慈悲仁爱,林清玄带着一种平民的意识和悲悯的情怀看待“小人物”的生命历程,感悟“小人物”在艰难和残忍的生存状态下的坚韧与刚强,透过“小人物”的生活展现其人生的体验、佛学的意趣和生命的价值,塑造他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