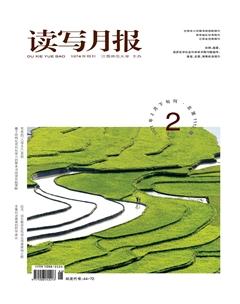略谈叶圣陶语文教材观
李思敏
叶圣陶先生作为语文教育界的大师,其语文教育思想对当今的语文教育改革和实践有着深远的影响。叶老在其长达70余年的教育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在语文教材的性质、功能、编撰、使用等方面得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形成了其鲜明的语文教材观。
一、叶圣陶语文教材观的形成和发展
叶圣陶先生语文教材观的形成、发展与其生平经历息息相关。叶老1899年开始进入私塾学习,读“四书”“五经”,学八股文。这为其熟悉古籍打下了基础,也让叶老了解了“八股精神”,并为其日后反对“八股精神”提供了现实依据。
1907年,叶老进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在这所学校中,叶老体验到了分科教育的优势,学习了系统的现代化科学知识,在学业方面突飞猛进。这所学校对叶老最大的影响就是它借鉴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的“乐育”方式,这对叶老之后形成的“工具论”教材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12年到1923年,叶老进入小学教书。五四运动爆发,很多像杜威的“兒童本位论”的先进西方教育思想传入中国,这对叶老的教材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叶老针对当时小学教育中的各种问题,在1919年与王钟麟合写的《对小学生作文教授之意见》中透露了对教材编制的新看法,即“顺自然之趋势,而适应学生之地位。于读物则力避艰古,求近口说”。所以叶老之后在初小和高小的《开明国语读本》中分别提出“以儿童生活为中心”“随着儿童的生活的进展”“取材从儿童周围开始”等以儿童为中心的观点。在这期间,叶老还提倡白话文,主张小学语文教材要完全用语体文来供学生阅读。1922年,叶老参与了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的编制,明确强调中学阶段的教材宜混选白话文和文言文两种书面语言的文章,并规定了语体文是教材的文体。
1923年到1930年,叶老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24年,他发表了《关于初中国语教科书的陈述》,在该文中论述了关于中学语文教材选取古文、翻译文,以及采取混合教本为教材的观点。
1931年到1937年,叶老任开明书店编辑一职,这也是叶老语文教材编制思想趋于成熟的时期。在这期间,叶老把自己的精力主要放在中小学教材编写上,在语文教材的建设方面取得了丰厚的成果。1932年和1934年,叶老与丰子恺合编了小学初级学生和小学高级学生用的两种版本的《开明国语课本》,该书在解放前共印40余版次,其出版问世体现了叶老对“儿童本位论”理念的重视。1933年,叶老在回应吴鼎弟的文章——《我的答语——关于语文读本》中主张语文教材对于文体的收纳应兼容博采,无论是记状、叙述、解释、议论等基本体式,还是便条、书信、电报、广告、章程、意见书等实用文的体式。1935年,叶老和夏丏尊先生合编了《国文百八课》。这是其语文教材编写思想的一次重要实践,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第一部以文章知识统领单元建构的教材。《国文百八课》编辑大意和《关于<国文百八课>》一文可以说是叶老对语文教材思想和实践的一次总结,也是其语文教材思想成熟的标志。编辑大意强调了“本书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与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1]。首先,其认为,语文教材应当选用不同体裁的文章,包括应用文、科学记述文等,力求多样。其次,教材的编排需要科学,以文章知识统领单元,包括文话、文选、文法和修辞四项,并且四项互为一个整体。这些教材编制的要点都为后来的语文教材编写提供了参考的范式。而在之后的一年,叶老在《谈教科书不是最后的目的》中提到,“语文教科书好比一张旅行的路程单,亲自到那些地方旅行,不是单单记住一张路程单”,这为之后其关于语文教材“凭借说”的功能论奠定了基础。
在1938年到1942年这段动荡的时期里,叶老的语文教育生涯也变得动荡不安。1938年,他应邀去过重庆巴蜀学校教国文,去过重庆中央国立戏剧学校教写作,之后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2年。1941年迁家到成都,1942年任职于教学科学馆国文科。在这期间,虽然叶老的工作、生活动荡不安,但他还是和朱自清先生合著了《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阐释了“语文教材如何阅读”以及“语文教材的性质是什么”等问题,正如《略读指导举隅》前言中谈到,“凭借是什么,就是课本和选文”[2]。
1943年到1948年间,叶老在成都开明书店办事处主持编辑事务。这段时期虽然国内还在发生战争,但叶老的生活相对稳定,所以这也有利于其对语文教育的进一步探索。1943年,叶老在与朱自清先生合作的《国文教学》一书中专门谈到了他对语文教材性质和功能的看法。这篇文章是其关于语文教材性质和功能的具体描述,也是其语文教材观进一步成熟的标志。这篇文章中提到:“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青年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的书中举出来的例子;其意是说你如果能够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阅读同类的书,不至于摸不着头脑。”[3]除此之外,还提到了“语文教本的内容和形式应着眼于背景、头绪、需要、结构、规律等方面”“语文应将白话和文言分开来教”等观点。之后的1946年和1947年,叶老分别与周予同、郭绍虞、覃必陶等人参与出版了六册《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和三册《开明新编国文读本[乙种]》,其中前一版专选白话,后一版专选文言。这种编制就是关于将白话文和文言文分开教学的一次实践。在此基础上,叶老与朱自清、吕叔湘等人在1948年合编了六册《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和六册《开明文言读本》。这套教材是采用白话与文言分编的形式,既满足了学生的生活实际需要,也在每篇文章后面分列“篇题”“音义”“讨论”“练习”四栏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此外,其还强调语文教材的编著要由浅入深,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至此,叶老的语文教材观已经初步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后,叶老长期主持参与全国中小学教材的编审工作,同时也发表了大量关于语文教育的文章。1949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制定了《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其融合了叶老几十年来关于语文教材建设的成熟经验,同时也根据时事提出了新的教材建设观点,从而发展了其语文教材观。比如中学语文教材就精神而言,通过语言文字,培养了学生对劳动的热爱、对祖国的敬爱以及爱护公共财物的集体主义精神。在此之后的十几年间,叶老多次主持参与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订工作。其中,1963年的新编中学语文课本最能体现解放以来语文教材建设的经验。该教材强调:首先,语文教材的选材要文质兼美;其次,文本数量增多,但文本篇幅缩短;最后,要加强基本训练。
1966年到1976年十年动乱时期,叶老不得不停下了语文教材研究的步伐。十年动乱后,叶老又开始了语文教材的研究。虽然年事已高,但他经常开展讲座,回答语文教育界人士的问题,认为语文教材的改革须通过认真研究才能实现。正如叶老1979年3月29日回复来信道:“切实研究,得到训练学生读作能力之纲目与次第,据以编撰教材,此恐是切要之事。”[4]“研究”是叶老语文教材观的精髓,其语文教材观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其一生对语文教育踏实的研究和执着的追求。
总之,在叶老的一生中,其单独编撰、与他人合编以及亲自主持参与编撰工作的语文教材高达129册,发表的关于语文教材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叶老一生不断磨砺,总结经验,逐渐完善、丰富其语文教材观。
二、叶圣陶语文教材观的内涵
(一)语文教材的“凭借说”
叶老曾言:“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青年现在或将来需要读的同类的书中举出来的例子;其意是说你如果能够了解语文教本里的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阅读同类的书,不至于摸不着头脑。”[5]此外,葉老在1948年草拟的《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中提到:“教材的性质同于样品,熟悉了样品,也就可以理解同类的货色”。[6]“例子”和“样品”都是叶老对于语文教材性质和作用的描述。无论是“例子”还是“样品”,都是用来观摩学习的,是让学生作为一种“凭借”来使用的。叶老曾说:“知识不能凭空得到,习惯不能凭空养成,必须有所凭借。那凭借就是国文教本。”[7]“要知道国文选本只是个凭借,有了凭借,历练才有着落。”[8]这里的“知识”是阅读和写作的知识,“习惯”是阅读和写作的习惯。知识的习得和习惯的培养需要历练,历练的结果就是学习语文的目标,语文教材则是达到该目标的“凭借”。一方面,学生凭借语文教材,揣摩选文的结构和表达方式,习得了阅读和写作的知识;另一方面,学生凭借语文教材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和兴趣,提高了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进而产生阅读相关的文章和书籍的愿望,阅读和写作的效率也因此得到提高。换言之,语文教材不是学生学习的最终目的,而是帮助学生学会阅读其他文章、书籍的工具,是引导其养成广泛阅读的习惯和兴趣、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的一种手段。
总之,语文教材是教师和学生进行教学活动的媒介。教师凭借教材引导学生学习,学生凭借教材获得阅读和写作方面的经验。
(二)语文教材的选材追求
1.选材的内容追求
首先,语文教材的每篇文章不宜太长,选的文章要精练,要把语文教材当作一种“凭借”。学生通过琢磨课文中的句法结构、思想感情等等,可以学会自主阅读其他的文章。因此,语文教材须选录篇幅适当且有代表性的文章供学生学习。
其次,语文教材应当贴合学生的实际情况,针对不同学段的学生使用不同内容的教材。就小学生而言,内容要以儿童周边的生活为依据,并且要符合儿童的心理条件。如《开明国文读本》这一教材收录了《新学期》《满天的星》等充满童趣的课文,并强调图画对儿童想象力和美感培养的重要性:“本书图画与文字为有机的配合;图画不但是文字的说明,且可拓展儿童的想象,涵养儿童的美感。”[9]就初中生而言,内容要考虑初中程度青年的认知水平和生活状况。正如初中生用的《国文百八课》中就没有收录论文和文艺理论作品,因为这些“对于初中程度的青年并非必要,甚且足以诱致一知半解的恶果”[10]。叶老在《关于<国文百八课>》中也谈到:“根据青年的需要,从他们生活上取材,分门别类地写出许多文章来,代替选文。”就大学生而言,叶老为了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为《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和《大学国文[文言之部]》两本教材设定了两种不同的目标,前者是培养大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后者则是培养大学生批判地接受文化遗产的能力。
最后,语文教材应当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那些表现消极的精神和价值追求的作品被摒弃,一概不被允许收录进教材之中。而表现为人民服务的、洋溢着健康情感的、反映新民主主义价值追求的文章才会被选入教材之中。正如《国文百八课》收录了《工作与人生》《项脊轩志》等充满积极色彩和人生哲学的文章。除此之外,叶老在1949年参与制定的《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中强调了语文教材要通过语言文字的展示,培养学生忠于祖国、热爱人民、服从集体主义精神的意志和情操。
2.选材的形式追求
叶老认为,在语言文字的学习上,如果只关注内容而忽视形式,最终只能事倍功半。因此,首先,就语言表达形式而言,语文教材应当分成两种:一种是文言文课本;另一种则是白话文课本。其中文言课本用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白话文课本则用于传递当代社会的语用习惯。为了实现白话、文言混教的目标,叶老编制了《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并分成了专选白话文的甲种和专选文言文的乙种两个版本。
其次,就选材的体裁而言,叶老认为各类体裁应兼收并蓄,正如其在一次回信中说道:“学生离校而后须阅读各类各体之文,故教材须兼收各类各体之文。”[11]诸如记叙文、描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多种体裁的文章须被选入语文教材中,用以增加语文教材的多样性。但在不同学段的教材中的占用比例要有所不同,如《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的“一二册记叙文描写文要多些,说明文议论文少些。以后说明文和议论文逐渐增多,五六册中记叙文描写就比较少了”[12]。
总之,选材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方面都要注意,如果只关注其中一个而忽视了另一个,就会出现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的后果。
(三)语文教材的编排要求
1.语文教材编排设计的科学性
叶老强调把语文学科当作一门科学性的学科来看待,语文学科的地位应与其他学科并列,而不是从属的关系。因此,其与夏丏尊先生合编了《国文百八课》,从此开启了中国语文教材科学化的先河。在《国文百八课》之前,语文教学更多地只是停留在讲读课文的层面上。如读书先生一样,只会让学生当堂学会课文的读音、理解文章大意。这是机械的记忆,一堂课后就容易忘记。并且其没有阶段性目标,无法对学生作出适时的评价,容易引发教学混乱的局面。考虑到以上问题,叶老在其参与编著的《国文百八课》中进行了一定的调整。首先,其设置了每小时和每周的教学目标,使语文教学有一个明确的评价参考,提高了教学效率;其次,教材设置了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以及习问四个专题,让学生从理解文本的体裁入手,进而学习文章,理解大意,感受情感,学习语法,最后通过问题来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此外,叶老对文章排列的系统性要求也体现了一定的科学性。《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分册中的文章就是按照由浅入深的顺序进行系统性排列的。一、二册中的记叙文、描写文比议论文和说明文占比要大得多,而五、六册则是后者比前者占比要大得多。在《开明文言读本》的编辑例言中也有明确强调:“排列的次序大体是依照文字的深浅。”[13]
2.语文教材编排人员的科学性
除了语文教材本身的编排设计外,参与编排的人员也体现了科学性。叶老建议参与编排语文教材的人员须是语文学科的从教人员。原因有两点:第一,教师是学生除了家长以外最了解他们的人。学生在校内的学习活动与教师直接挂钩,并且双方有着共同的学习目标。正如叶老在其自传性质的教育小说《倪焕之》中提到:“为了迁就教本,勉强把不愿意交给学生的教给了学生,因而感到欺骗的学生似的苦闷。为什么不自己编撰呢?最懂得学生的莫过于教师。”第二,语文教师自身的教育热情促使其不会像一些书店、出版商那样把语文教材当作商品。这份热情会赋予语文教师强烈的责任感,促使其为了学生选出文质兼美、符合学生实际需求的语文教材。正如叶老在《倪焕之》中评论书店道:“最关心的是自家的营业,余下来的注意力才会轮到文化和教育。”
(四)语文教材的阅读策略
语文教材就算编得再好,最终也要归结到学生如何进行阅读上来。因此,叶老提出了相应的语文阅读策略。
1.精读与略读相结合
叶老说过:“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只是补充;但是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14]语文教材的每一篇文章都需要精读。一方面,学生只有养成精读的习惯,读其他的书籍才不会马虎;另一方面,掌握了精读的条理和步骤,对文章的领悟自然也会更加精进、深刻。
略读是在掌握精读的技巧后,能够应用自如的一种阅读状态,是学生在获得精读的经验后,自行运用这些经验去阅读其他文章的行为。如果说精读是细嚼慢咽,略读就是提纲挈领,二者各有益处,缺一不可。
2.教师指导与学生自主阅读相结合
就精读方面来说,学生阅读语文教材的第一步是以自主通读全文的方式预习,了解文中生字词、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以及文章中作者思想情感发展的脉络等;第二步是教师上课指名用吟诵或朗读的方式通读全文,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之后由教师考问学生教材上的内容;第三步是读完教材上的每一篇文章后再去读相关的课外文章和书籍,从而达到触类旁通的目的。
就略读方面来说,教师要在课内进行略读指导,让学生总结阅读的方法和结果。具体的略读指导应当包括版本指导、序目指导、参考书籍指导、阅读方法指导和问题指导等。学生在获得略读经验、养成良好的略读习惯后,可以选取寒暑假的时间自由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籍。
3.独立阅读和集体阅读相结合
独立阅读语文课文主要是在学生的课前准备阶段,集体阅读指的则是课上学生集体学习课文、提升思维能力。课前独立阅读可以帮助学生获得关于课文的相关知识以及独到见解,课上的集体阅读则能够帮助学生提高阅读的兴趣,通过讨论、提问的方式来使彼此的眼力更加敏锐、思维更加敏捷,从而达到弥补独立阅读的缺陷的目的。
三、叶圣陶语文教材观的启示
(一)语文教材要贴合学生的实际效用
叶圣陶先生在其教育论著中强调学生的实际生活对语文教材编撰的重要性,语文教材要容纳满足学生生活需要的各种题材的文章。要想在最大程度上发挥语文教材对学生的实际效用,在编撰语文教材时就需要着重考虑学生的实际生活,坚持生活本位的原则。《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就强调:“教材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适应学生的认知水平,密切联系学生的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15]随着时间的推移,语文教材在不断地调整、更新,但始终不变的是“学生是教材的受用者”。语文教材只有符合学生的实际发展水平,学生才能真正受用,才会有主动学习的动力,才能达到“不教”的目的。
要想使教材贴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语文教材的编排者就要了解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身体层面,还是心理层面。为此,语文教育者需要积极参与、仔细观察学生的日常生活,做好统计与整理,配合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
(二)要合理地看待语文教材的功能
当前,部分语文教师对教材的态度存在两种极端的表现:一是“照本宣科”,即完全按照语文教材来讲,不放过任何一个知识点;二是“胡讲海讲”,在课堂上天马行空,完全脱离了语文教材。前者会造成课时不够,学生压力过大,失去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后者则会导致语文课失去教学重点,容易造成把语文课上成思想课、道德课的窘境。这两种现象其实是由于一些语文教师错误地看待语文教材的“凭借”功能而导致的。“照本宣科”是因为教师过于重视语文教材的“凭借”功能,所以在课堂上不敢拓展,生怕出现差错;“胡讲海讲”则是因为过于轻视语文教材的“凭借”功能,认为只要按照自己舒服的节奏来上课就行。
显然,这两种行为都是不可取的。语文教师要在明确语文教材“凭借”功能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实施语文教学任务,始终秉持着“既不夸大、也不贬低”的态度在语文教学的道路上前行。
(三)语文教材的编撰要建设健全评价机制
语文教材的编撰往往处于“闭门造车”的窘境,虽然编排者征求了相關专业人士和学校的建议,但是渠道还是相对狭窄,这可能会导致语文教材出现一些问题。社会对这些问题是非常敏感的,更需要认真把关,建立健全语文教材的评价机制。
换言之,既然社会对语文教材的容错率如此之低,我们就更加需要在评价中增加公众评价机制,即在教材编撰后,将文本发布出来,征求公众的意见,而后根据反馈进行适当的修改之后再出版。这种做法既让相关专业人员参与了评价,也让广大的语文教材受众参与了评价,形成了更健全、更科学的语文教材编撰评价机制,从而大大降低了语文教材的错误率。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14]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71页,第19页,第182页,第744页,第182页,第201页,第3页,第214页,第166页,第172页,第735页,第194页,第19页,第19页。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