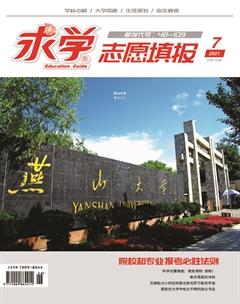不是第一名,也很优秀
黄建昌
高中时期的我,心里充满了狂妄与偏执。有一位老师,她一直默默地鼓励着我,让我慢慢懂得了何为人,如何为人。
她是我高中三年的班主任小方,一个二十来岁,古灵精怪的老师。她曾经也是这所高中的学生,高考考上了一所“985工程”高校。大学毕业几年后,她就遇到了我们,或者说,是我们遇见了她。我记得那是一个温暖的午后,她手里拿着一沓资料,一身白衣潇洒地推开了教室的大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清澈的眼神,一张温柔的笑脸,以及随之而入的阳光。自此,我们与小方结下了三年的缘分。
小方的字很好看。高一的时候,她送了一本崭新的《班级日志》给我们,让我们每天记录下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她在《班级日志》的第一页上写着“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娟秀的字迹流露着她对我们的鼓励。以此为引,同学们在这本日志里勾画出了心情冷暖,心之所向。
高中的物理比初中的物理要难很多,高一不做好过渡就很难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学好物理。小方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她的物理课总是那么地通透,让同学都能轻松理解。课余时间,她也端端正正地坐在讲台上,手里拿着一支黑色水性笔,在草稿纸上勾勒出一个个物理过程模型图,一遍又一遍地为同学们解读着迷惑之处。
我们经常会问她:“老师,你都考上这么好的学校了,为什么还要回来这里任教呢?”她总是微笑着,淡淡地说:“因为我喜欢呀!”
她总是那么地淡然。而我总是偏执地认为,一定要走在最前面才是最优秀的,就像我一定要拿到班级第一一样。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大家都想要取得好成绩,但过度在意“第一”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困扰与苦恼。这个目标,对于初上高中、基础不稳的我来说太过于远大,也很不真实。我常常对着那些不尽如人意的成绩单暗自苦恼,一科又一科地和班级第一名进行比较,假设着这里多拿两分,那里再拿三分。但现实却是,高一高二的两年里,我都没有拿过班级第一,人却已经开始走向了极端。我经常会推掉班里的一切活动,班级篮球赛不参加,也不去观赛;小组活动也不想参加,只是埋头“啃”着那些书,“啃”着那些遗憾与不甘。相反地,那位班级第一名总是在各种活动中都如鱼得水,崭露锋芒。我落寞了,总是一个人看着远处发呆,或是坐在没人的教室里,黯然神伤。
这种情况不会自己变好,只会越来越糟。在一次月考中,考数学时出现失误,我直接从班级前五掉到了二十开外。
小方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长谈。我双手捂着头,支支吾吾地说着自己的苦恼。小方在一旁静静地坐着,温柔似水的眼神鼓励着我说下去。听我说完后,她一脸严肃地对我说:“没有,我就觉得你很优秀,而且班里的每一个同学都是优秀的。一个人是否优秀并不是全由成绩来决定的,这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是否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你这种心态要及时调整了哦,不然会影响高考的。”我有些半知不解,用双手把有些蓬乱的头发理顺,把头抬起来,回之以微笑。
从那以后,我慢慢地不再那么看重结果,而是去关注过程,去欣赏那些我走过的小路,去聆听风吹叶落,去仰望万里晴空。
时光如白驹过隙,在上课铃声与下课铃声交替间,高考已至。有的老师穿上了旗袍,预祝同学们旗开得胜;有的老师举着“高考必胜”的牌子,默默地在一旁为同学们加油打气。小方站在送行的公交车下,举着一朵太阳花,给我们传递着最后的温柔与善意。我慢慢地走到车前,小方用太阳花碰了碰我的肚子,微笑地对我说:“加油。”装载着希望与梦想的公交车在一路颠簸中,缓缓地朝最终的目的地驶去。在这最后的一段路里,不再有阻拦,不再有喧嚣,只有冷静至极的心安与陶醉……
在成绩出来的前一天,我们要到学校領取《高考指南》。我早早地就坐在学校的办公厅前等候。在离正式上班时间还有大概10分钟的时候,小方骑着她的小电驴悠悠地驶来。她远远地就看到了我,和我打了个招呼。第二天,我查到好成绩后第一时间告诉了小方,本来还想说很多感谢的话,小方却说:“早就跟你说过了,你很优秀的,这些都是你努力的结果,祝贺你。”谢谢你,小方!
只要向往优秀的人,都是优秀的人,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