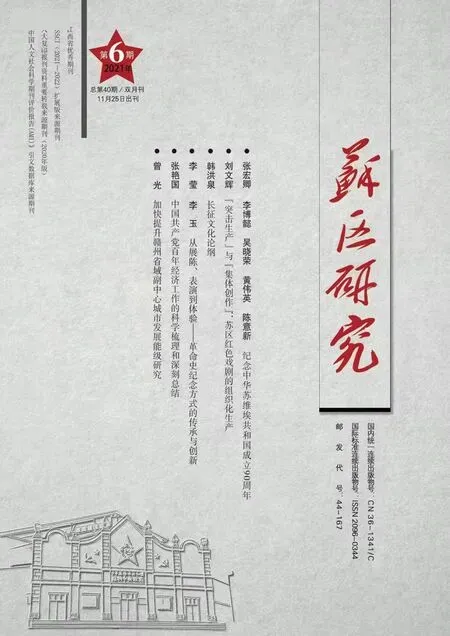“突击生产”与“集体创作”:苏区红色戏剧的组织化生产
刘文辉
提要:革命把戏剧从都市带到乡村,改变了戏剧的生存空间,也改变了戏剧的生产方式,使戏剧生产脱离世俗化的市场轨道,进入革命的组织化流程。革命者通过实施短期突击计划,发展革命竞赛,加强临时突击生产,组织批量复(仿)制等方式不断扩大戏剧生产与再生产,强化革命的突击动员。与此同时,通过组织人员即兴“凑戏”,组建创作小组,公开向工农兵大众征稿等方式积极推动集体创作。突击生产与集体创作构成了苏区红色戏剧最主要的生产方式。红色戏剧的组织化生产既满足了革命动员的现实需求,也契合了革命者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生产的文化想象;既是一种现实的革命动员策略,也是工农大众的集体化生活形式。
苏维埃革命不仅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武装革命,而且是一场激进的社会革命;革命的主旨不仅要促使工农大众实现翻身解放,而且要推进工农大众的“翻心”实践。“激进的理念和形象要转化为有目的和有影响的实际行动,不仅需要有益的外部结构条件,还需要在一部分领导者和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感工作。”(1)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方式》,《中国学术》总第8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8—99页。演剧成为革命者发动工农大众,塑造革命主体的有效媒介。在苏维埃革命的早期阶段,红四军就设有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内设娱乐科。“仅于纪念日或每月举行工农兵联欢会,或红军纪念会,有演说,有新剧,有京广团,有双簧,有女同志跳舞,有魔术,这些多能引起士兵的快乐。”(2)陈毅:《关于红军的宣传工作(节录)》(1929年9月1日),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革命者通过组织演剧来活跃部队生活,宣传革命观念。1931年底,在苏区中央局的支持下,革命者在红军学校俱乐部的基础上组建了苏区第一个专业性的戏剧团体“八一剧团”,领导和组织苏区戏剧演出,推动苏区戏剧运动的开展,提升了苏区戏剧演出的整体水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为进一步扩大革命战争动员和丰富军民文化生活的需要,革命者开始致力于构建苏区群众性文艺组织,在“八一剧团”的基础上,组建了群众性戏剧组织——工农剧社,发展工农大众戏剧演出团体——蓝衫团,自上而下建构起群众性戏剧组织网络。在苏区,“每一‘列宁学校’、小学和农工苏维埃,以及前方各军队,都有它自己的剧团和临时戏院”(3)[美]威尔斯著,陶宜、徐复译:《续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中共制定了《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纲要》《工农剧社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等戏剧政策及法规,推动苏区戏剧生产走向组织化与制度化。苏区没有职业的作家,但几乎人人参与了文艺的生产,很多革命领导者主动参与编戏,甚至登上舞台演戏、唱歌,官兵同台,军民同乐。苏维埃政府还创建了专门的文艺学校——蓝衫团学校(后改为高尔基戏剧学校),先后为地方和军队培养了1000多个戏剧骨干,曾经组织60个戏剧队赴苏区乡村与前线阵地巡演。演戏和看戏是苏区革命亲历者最深刻的文化记忆。“在以前江西中央苏区时代,戏剧运动的发展与活跃,在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因此你在陕北苏区中,如果遇到从江西来的红军战斗员或工作人员,话锋一触及当时的戏剧运动,那末他们立时就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唾沫往往不知不觉地溅在你的脸上。”(4)L.Insun:《陕北的戏剧运动》,汪木兰、邓家琪编:《苏区文艺运动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历史空间里,戏剧运动与革命运动始终相伴相生,取得了不俗的历史实绩。“从那时起,文艺工作就是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必须要有而不是可有可无的的一种部队工作形式和生活形式。从那时起,文艺活动就广泛地表现于广大指战员的各种活动之中。在部队中,往往紧跟着工作任务或战斗任务而来的,就有文艺活动的协同作用。”(5)傅钟:《关于部队的文艺工作》,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第100页。
在苏区,举凡群众集会、战斗动员、胜利庆功、节日庆典等活动,都会组织戏剧演出活动。演戏和看戏是苏区军民最重要的集体生活。(6)据相关的资料统计,仅中央苏区,戏剧名录就有269种之多,其中话剧180种;讽刺剧、滑稽剧、哑剧5种;活报剧34种,戏曲、木偶戏16种;歌剧、舞剧、表演唱29种。参见刘云主编:《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共产党人把戏剧从都市剧院带到乡村广场,使其由都市市民的文化消费品转化为乡村革命动员的现实武器,戏剧演出也因此脱离了都市的市场化轨道而进入革命的组织化程序。在革命历史情境下,戏剧生产已然不是个体化的创造行为,而是集体化的革命实践,被纳入革命一体化政治文化生产体系中,成为革命者推进乡村社会变革,建构新的意义体系的重要路径。对于苏区文艺的组织化生产,既有的研究成果或将重心放置于描述苏区文艺的组织化历史过程;或强调瞿秋白等文艺领导人的贡献。对苏区戏剧组织化生产的具体方式论述不多。(7)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李振:《苏区文艺的组织化过程》,《文史哲》2014年第4期;傅修海:《瞿秋白与中国现代集体写作制度——以苏区戏剧大众化运动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6期。目前关于革命文艺生产方式的研究,关注点多集中于抗战文艺与延安文艺,对于苏区文艺的生产则着墨不多。在苏维埃革命历史空间里,革命者依托独特的“突击生产”与“集体创作”方式,推动了现代戏剧在乡村的大规模生产,使演剧成为革命突击动员的重要方式和军民公共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
一、“突击生产”是苏区戏剧生产的主要形式
突击生产是战争年代戏剧最突出的组织化生产形式。从苏区到延安,“突击是中国共产党在野时期政权内部的一个普遍现象。”它“反映出根据地社会日常生活的军事化特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心态以及普遍的‘突围’心理。”(8)周维东:《“突击文化”与延安文学引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2期。
苏区时期,需要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残酷围剿,中共革命处境更为艰难,军民“突围”心理更为普遍,文化的“突击”特征也更为直接和明显。早期的文艺宣传组织性不强,“对宣传员的训练没有计划”,“宣传队的工作简直随随便便”,“突击”特征也不明显,而“化装宣传完全没有”。(9)《红军宣传工作问题》(1929年12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4—25页。随着苏维埃革命的深入,红军和苏维埃政权逐步建立起较为成熟的“宣传兵”和“俱乐部”制度,“突击”宣传成为革命常态的宣传方式。“在苏区内除了各种纪念节外,必须举行各种宣传鼓动的运动。”为应对紧迫的苏维埃革命动员任务,革命者在发动诸如“查田运动”“扩红运动”“归队运动”“春耕运动”“卫生运动”等革命突击运动的同时,也相应地发动了各种文化突击运动,推进苏维埃文化的突击生产,不间断地制造群众运动高潮,激发群体的革命狂欢。“每一运动时期,各种报纸,各种会议必须尽量提起群众对于这一运动的兴趣,而且自动地参加。到处应该粘贴关于这一运动的口号与标语。”(10)《中共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1931年4月21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42页。突击生产成为实现苏维埃文化突击的最有效路径之一。
随着工农剧社和蓝衫团(苏维埃剧团)的广泛建立,苏区戏剧的突击生产有了更坚强的组织保证。各级苏维埃剧团积极参与突击宣传,“用表演戏剧等的艺术宣传,参加一般的革命斗争,赞助工农红军的革命战争。”(11)《苏维埃剧团组织法》(1934年4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34页。革命者建立起灵活的突击生产方式,有效激活、重组、整合既有的戏剧资源,推动戏剧的生产与再生产,提高戏剧生产效率,扩大戏剧生产规模,增加剧本供应,利用巡演、公演、汇演等等各种戏剧演出组织方式,满足革命动员的现实需要。
(一)实施短期突击计划
革命的突击生产是非常规的军事化生产。超常的速度与效率是突击生产追求的主要目标。为提高革命生产效率,中共不断地制定和发布各种短期突击计划,调配和发掘潜在的革命资源,集聚新的革命能量,限期完成特定革命生产任务,提高革命生产效率,促使革命长久保持活力与动力。
在紧张的革命动员情势下,短期突击成为革命者扩大戏剧生产与再生产的常规路径。这种短期突击方式往往会有一套相对严整的组织化流程。首先是由上级党政机关或群团组织发布限期突击计划、决议、通告或指示信,而后下级党政机关或群团组织根据区域情况制定具体的突击工作实施流程、方法与目标。在计划的组织实施上,注重党、政、军、群团的合力运作以及俱乐部、剧团、剧社等戏剧组织的联动突击,集中生产,短期完成特定戏剧生产目标,激活戏剧生产潜能。最后各部门需提交突击总结报告,交流突击经验,塑造突击典型,为制定下一个短期突击计划提供实践指导。这种短期突击或以“季”为时限。如《少共赣东北省委关于冲锋季工作计划——自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到九月二十三日止》规定,各级团组织须在“冲锋季”中编出歌谣小调1本、戏剧10种、并出版画报每星期1次。(12)《少共赣东北省委关于冲锋季工作计划——自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到九月二十三日止》(1932年6月18日),江西省档案馆、共青团江西省委选编:《江西青年运动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或以“月”为时限,1933年江西省委宣传部发布命令,要求各级俱乐部、工农剧社在扩红突击月(六、七两月)中必须单独举行扩大农业工人师,店员手工艺人师及少共国际师的晚会,并在晚会上组织适合扩红动员的新戏活报的表演;(13)《扩大两个工人师及少共国际师的宣传鼓动工作》,江西苏维埃出版物(1931—1934)(陈诚档案微缩资料),第6卷。闽浙赣省苏维埃教育部制定突击计划,要求各俱乐部扩红突击月(七、八两月)中必须完成演戏4次、晚会4次、活报出刊2次的演出任务。(14)《闽浙赣省苏维埃教育部关于七、八两月文化教育工作的突击计划——第二次县教育部长及直属区教育部长联会决议》(1933年6月24日),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等编:《闽浙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5页。或以“周”为时限,如1932年7月底,瑞金县组织了八一示威运动周。在运动周期间,其15个区中有22乡演了文明戏。县一级机关都组织了化装宣传队出发宣传。(15)《中共瑞金县委七月份工作报告——附“八一”示威运动工作总结》(1932年8月9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32年(一)》,内部发行,1992年版,第422页。从某种意义上讲,戏剧突击是革命军事突击在戏剧舞台上的表现。革命者依靠短期的戏剧突击生产不断制造乡村演剧的高潮,吸引民众参与广场狂欢,强化革命突击动员效果。
(二)发展革命竞赛活动
在紧张的革命动员情势中,革命竞赛是最常见也最有效的突击生产形式。革命竞赛既是战时军事突击的权宜之计,也体现了革命集体主义精神主旨。对于乡村民众来说,革命竞赛还有民间“打擂台”的传统竞赛精神余绪。
以革命竞赛的方式推进突击生产是共产党人自觉的创新实践。学者何友良指出:“将当前强调的重点事务分解为竞赛指标,以县际竞赛来推进工作,以各类数据来衡量成绩,是苏区稳定时期县政运行的重要方式。”(16)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页。革命竞赛贯穿了苏维埃社会大生产整体进程,且形式灵活,不限于县际,扩展到个人、曲、乡及省际之间,“发展生产,以革命竞赛的方式发动个人与个人、乡与乡、区与区、县与县各种生产的竞赛”。(17)《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土地问题决议案》(1932年6月3日),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演剧比赛是苏区革命竞赛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者常常有意识地把戏剧表演和政治训练乃至军事训练结合起来,把戏剧表演竞赛与宣传工作竞赛、文化教育竞赛、游艺大赛、政治文化体育竞赛乃至运动大会等组合在一起,推进戏剧的突击生产和革命的突击动员。苏区的演剧竞赛活动频繁,贯穿苏区戏剧运动始终,现有据可考的大型戏剧竞赛活动就有近10次。(见表1)

表1 苏区大型戏剧竞赛活动
除组织具体的竞赛活动之外,革命者还设计了诸如“比赛周”“竞赛月”等竞赛突击计划,制造革命竞赛高潮。在苏区,每一场革命竞赛就是一次有组织的革命突击生产实践,一般都有周密的组织流程。与前述短期突击计划组织流程相似,一般先是由上级党政机关发布竞赛活动指示或通令,提出竞赛活动内容和方案;而后组织各参赛单位订立竞赛条约,确定竞赛目标。如前述瑞金“八一”宣传鼓动工作竞赛,各区委都签订了竞赛条约,确定了八一期间各乡演剧任务;条约订立后,各参赛单位则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具体竞赛实施方案,调配及集聚资源参与竞赛;在竞赛活动结束后,评定成绩,总结经验,树立典型。革命竞赛激发了军民参与演剧的热情,挖掘了新的戏剧生产潜能,扩大戏剧的再生产。
(三)强化临时突击生产
革命生活是非常态的军事化生活。革命动员也是一种军事化的突击动员,天然地带有临时机变的实践属性。面对复杂多变的战争环境和各种突发的战争事件,中共建立起一套灵活的应急动员机制,突击表演是革命者常用的应急动员手段。特别是在苏维埃革命初期,临时性的突击表演几乎无处不在。“敌人耍什么花样,党采取什么对策,宣传队员们就到大街上化装演讲,苏区军民就能及时了解清楚”。(18)潘振武:《忆红一军团宣传队》,《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512页。举凡部队出征、祝捷或驻扎修整,宣传队常会临时赶排节目或直接组织化装表演进行突击宣传。
随着革命的深入,战争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各种突发事件时有发生,临时突击表演越发频繁,表演形式也更加成熟。据李伯钊回忆,1931年12月宁都起义胜利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马上组织宣传队慰问起义官兵,进行突击动员。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为宣传队拟定宣传主题,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则为宣传队提供具体的演出建议,宣传队根据起义官兵的实际情况制定表演方案,表演戏剧《为谁牺牲》,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为完善苏维埃革命动员体制,革命者有意识把临时突击表演上升为一种戏剧生产制度。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订定的《苏维埃剧团法》规定临时突击表演是中央苏维埃剧团的基本任务。“剧团的工作不应只限于大规模的戏剧,还应当组织最简单的化装宣传队(十几个人或五六个人的)以适应乡村的条件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因为这样可以分成几组出发同时进行几处的宣传,而且行动和供给较为便捷许多”;(19)《苏维埃剧团组织法》(1934年4月),《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36页。要求苏维埃剧团应适时依据当地实际情况,临时创排剧本,开展突击演出。为强化基层突击动员,县级苏维埃剧团设定为临时剧团,其主要职能就是开展临时突击演出,激活基层戏剧生产。从李伯钊关于中央苏维埃剧团春耕巡回演出的报道来看,临时突击已经是中央苏维埃剧团主要的突击动员方式。“除了自己准备好的关于春耕运动必要的表演外,其余都是采集群众生活的实际材料,经过剧团集体创作的研究,依靠我们原有的技术的基础,很快就在舞台上出现了。”(20)戈丽:《苏维埃剧团春耕巡回演出纪事》,《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303页。临时突击表演强化了革命动员的应变功能,使演出紧密追踪革命时事,及时回应民众的现实诉求,扩大了演出的动员效果,也为战争年代戏剧的快速生产提供了最便捷的通道。
(四)组织批量复(仿)制
为应对日益紧张的革命动员,中共积极推动戏剧的扩大再生产,使戏剧蔓延到乡村的一个角落,重构民众的公共文化生活。批量复制成为革命者扩大戏剧再生产的主要路径。学者唐小兵在谈及革命宣传画的复制和印刷时指出:“大量印制和广泛采用并不是一个特殊现象。相反,这一现象是社会主义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此种文化致力于确保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同心同德,因此常常通过各种媒介和传播形式,使反复加工升华过的视觉形象或文学人物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统一的大规模生产过程,其效果与消费主义时代精心策划的广告活动,距离其实并不是很远。”(21)[美]唐小兵著,朱羽译:《试论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中的先锋派概念》,《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戏剧是流动的革命宣传画,乡村苏维埃革命者对于剧本的批量复制与集中供给有着更强烈的现实冲动。革命者初步构建出自上而下的覆盖党、政、军、群的戏剧再生产平台,为剧本的批量复制与集中供给提供了组织保证。
中央宣传部设有编辑委员会和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有计划地编辑一切宣传教育的丛书,小册子等”“负责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22)《中共中央宣传工作决议案》(1932年5月3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16页。中央及各省教育部设有编审出版委员会,负责“编辑普通教育、社会教育的各种材料,审查下级编辑的材料,并以之出版”。(23)《省、县、区、市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1933年4月15日),《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06页。红军各级政治部设有文化运动科(股),专门负责组织革命竞赛、化装演讲,编辑剧本、化装娱乐等工作;1932年5月,鄂豫皖省苏维埃发布通告,强调“编审新剧工作,极为重要”,要求省文化部编委会按照革命实际情形组织剧本编撰;同时集中收集各县文化部及其他革命团体已经编成的剧本审查出版。(24)《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通知(文字第一号)——搜集和捡寄各种报纸审查》(1932年5月3日),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湘鄂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内部发行,1996年版,第195页。战争情境下的剧本复制往往是临时性的和突击性的,复制的数量与速度依据既有条件和现实需要而定,为特定的宣传动员任务服务。1932年,瑞金县为执行七县三个月(即三、四、五月)竞赛条约,组织新编戏剧3种,翻印戏剧1种,分别印制1200份及250份发往各地,意图在竞赛期间掀起演剧运动高潮,扩大革命动员;(25)《瑞金执行七县竞赛条约三个月(三四五月)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6月13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1932年(一)》,第241页。同年春,红军总政治部为推进部队文化工作竞赛,将组织创作完成的10余个剧本批量印发给各基层俱乐部,同时督促各基层俱乐部讲创作完成的剧本交由总政治部审查印发。(26)《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文化运动工作给各级政委的一封信》(1932年3月3日),江西苏维埃出版物(1931—1934)(陈诚档案微缩资料),第8卷。1933年11月,苏区中央局宣传部为纪念广州暴动6周年印发活报《十月革命节》,要求“各县委需翻印,要能够办到每个乡的支部都有两份”。(27)《十月革命节》(活报),江西苏维埃出版物(1931—1934)(陈诚档案微缩资料),第3卷。1934年,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瞿秋白还亲自编辑了中央苏区第一部剧本集《号炮集》,油印300多份发往各地,以应对革命的突击动员。(28)瞿秋白曾设法由交通把此剧集带往上海去,未果。参见赵品三:《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的回忆》,《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500页。
革命者有意通过《红色中华》《青年实话》《苏维埃文化》等报刊推介剧本,拓展戏剧传播通道。《红色中华》“赤焰”副刊公开刊发了《“三八”纪念》《我们自己的事》《揭破鬼脸》《“抗日”喜剧》等剧本;《苏维埃文化》首期就刊发了戏剧《无论如何要胜利》(李伯钊作);《青年实话》曾专门刊发推介的歌剧《扩大红军》的广告,强调此剧为“苏维埃戏剧运动的新贡献,对歌舞有兴趣的同志,应该以先看到为快意,对戏剧有兴趣的同志,尤不可小看,从事剧团剧社,俱乐部,学校教员,更不可不人手一本了”。(29)《青年实话》1934年5月20日,第3卷第23号。
剧本的批量复制加快了苏区戏剧的传播,有效缓解了基层剧团剧本供应不足的困难,使得自上而下的戏剧动员能围绕着相对集中的主题,确保戏剧内容不会溢出既有的意识形态轨道,强化突击动员效果。如兴国蓝衫团所演节目中大多是上级文化宣传部门和中央工农剧社印发的剧本和演唱材料;其次才是自己编写的短小节目,如兴国山歌。(30)《中央苏区工农剧社兴国分社“蓝衫团史”座谈会纪要》,《功崇惟志写春秋——全国十大文艺集成志书江西卷编纂纪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赣东北工农剧团演出剧本除部分自编外,很多来自省文化部供给。(31)钱荣花:《回忆赣东北工农剧团》,《闽浙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161页。很多苏区名剧如《送郎当红军》《扩大红军》《阶级》《旧世界》等通过巡演和翻印等方式广泛传播到基层的宣传队中,成为其演出的常规剧目。(32)如留存下来的《阶级》《新十八扯》《旧世界》等剧本都是基层部队翻印的剧本,参见汪木兰,邓家琪编:《中央苏区戏剧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而红军《宣传队工作日记》就有宣传队多次排演《扩大红军》的记录,参见江西苏维埃出版物(1931—1934)(陈诚档案微缩资料),第5卷。在舞台的循环演出中,剧本内容和结构会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在新的演出情境诱发下,容易衍生出新的剧目,进一步促进戏剧的扩大再生产。以苏区流传最广泛的歌舞剧《送郎当红军》为例,其初始演出形式为男女对唱赣南采茶戏——“十月怀胎调”,一唱一和,“妻子”手舞手巾花,送夫参军,深情款款。到了赣东北苏区,剧词曲调便有了变动,由男女对唱改为女声合唱,唱词加入部队纪律和阶级斗争的新内容,歌唱性增强,表演性减弱。传至彭泽,则又删去了男角,改换了道具,变为独角戏。表演者不甩手绢而耍莲枪,原地踩步,边唱边用莲枪上下击拍手掌,每当唱完一段,则口念“哎呀我的哥我的哥”曲词作为过门,念完之后,又用莲枪做出各种击打动作和舞姿。一段曲词一套枪,左右交替,跳跃活泼,更酷似莲花落风格。(33)《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江西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戏曲志·江西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版,第243页。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化的剧本复制和集中供给本身也契合了社会主义大生产的组织形式,引导民众参与戏剧生产,有力地推动了戏剧大众化在乡村的广泛实施。
“仿制”是革命年代一种动态的戏剧“复制”方式。“仿制”是基层俱乐部、剧团实现演出剧本自给的重要方式。最常见的“仿制”常常直接套用“母本”的情节框架,依托当时情境,稍微改变戏剧时空和角色名称,或者改变一下演员的扮装,然后搬上舞台或广场演出。流行于苏区各地的“打土豪”化装演出流程大体一致:先是诸如地主、土豪、反动军官等压迫者出场,狂妄自大、目空一切、颐指气使、自吹自擂;然后是百姓或士兵等“被压迫者”出场,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生活困顿;再是“压迫者”辱骂、殴打“被压迫者”;最后,正当“压迫者”洋洋得意、作威作福,“被压迫者”求告无门之际,红军、赤卫队等“救世者”出场,救出“被压迫者”,活捉、暴打“压迫者”,让他们游街示众或直接打死。而诸如《打倒萧家璧、罗普权》《打倒钱如命》《打狐狸精》《打倒尹道一》等几乎就是“打土豪”化装演出在不同演出情境下的变体。有时候戏剧“仿制”方式会更复杂一些,甚至会改变情境、台词(唱词)、唱腔。如《送郎当红军》《送夫当红军》《送子当红军》《送哥当红军》《我要当红军》《志愿当红军》等剧呈现的是“妻送夫”“母(父)送子”“女送郎”“妹送兄”等不同戏剧情境,角色配置和情节布局并不相同,或一方同意参军,另一方千方百计阻拦;或一方不愿意或害怕参与,另一方极力规劝;但从整体上看,它们的主体框架非常相似,唱词(台词)也大同小异,俨然也是一个“母体”衍生出来的不同变体。“仿制”降低了戏剧创作的门槛,提高了基层俱乐部、剧团戏剧生产效率,扩大了其戏剧生产规模,推动同一主题戏剧的快速传播,使戏剧演出与革命突击动员保持在同一频率,产生共振效应。
二、“集体创作”是实现戏剧“突击生产”的现实路径
集体创作是革命年代戏剧突击生产最有效的现实路径,也是革命集体主义生活的独特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共产国际倡导的世界无产阶级新的文艺生产方式,集体创作伴随着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进入中国,成为中国左翼文艺群体热衷于推广的创作方式。(34)在20世纪30年代洪深主编的《光明》与《读书生活》杂志中,发表了多篇介绍“集体创作”的文章。参见周维东:《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战略与延安时期的文学生产》,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苏维埃革命者有意识地把集体创作方式引入乡村,旨在充分整合有限的戏剧资源,发掘乡村潜在的红色戏剧主体,推进乡村戏剧主体泛化,激发工农兵大众的创作热情,提升红色戏剧生产能力,建构独特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
在革命的乡村,无产阶级的集体创作方式与乡村民间戏班原始的“凑戏”传统遇合,展现出独特的历史活力,发挥了独特的历史功能。在战争年代,乡村革命者的集体创作首先表现为集体“凑戏”。“没有剧本,自己编。先有个剧情大意,排演时即兴发挥,你一句我一句地就凑起来了。”“要开大会了,需要编个剧,大家就东凑西凑,根据大概什么人物、什么内容,在一起排排,上台后,再自编、自演。”(35)刘毅然:《原战士剧社部分红军老战士座谈侧记》,《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523页。不只绝大多数突击性的化装表演是临时拼凑而成,而且诸如《我——红军》《庐山之雪》《杀上庐山》《为谁牺牲》等苏区名剧都是集体“凑”出来的戏。它显然无助于戏剧审美品格的提升,但有利于满足多变的战时情境下军民对于演剧的需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剧本供应不足的困境,也为演员的即兴发挥预留了许多开放的空间。“那时剧本不像现在这样细,是粗线条的,所以演的人可以充分发挥。”(36)聂荣臻:《红军时期的文化工作》,《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457页。公开资料显示,《庐山之雪》《杀上庐山》《为谁牺牲》等戏的舞台演出多有演员的即兴发挥。即兴表演是最灵活快捷的集体创作方式,也集中凸显出革命表演的群体狂欢色彩。
在紧张的苏维埃革命动员情势下,革命者开始探索性地组建创作小组,整合优势人才资源,推进戏剧集体创作,把集体创作纳入组织化程序之中。在苏维埃革命的早期阶段,创作小组往往是为应对突击任务而由宣教机构临时组建的,成员并不固定,人数也比较灵活,任务结束后就宣告解散。如为庆祝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苏区中央局委托李伯钊、钱壮飞、胡底等组成大会筹备会文娱小组,负责筹备大会庆典演出。文娱小组还承担了创作小组的功能,集体创作了《最后的晚餐》(钱壮飞执笔)、《黑奴吁天录》(李伯钊负责)等剧目。(37)李伯钊:《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演出的剧目》,《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487页。
1931年成立的红军学校俱乐部戏剧管理委员既是苏区最早的专门戏剧管理机构,也是苏区最早的常设集体创作小组,吸纳了李伯钊、危拱之、赵品三、伍修权等知识分子,组织集体创作,定期推出新剧本,丰富戏剧演出活动。为应对日益紧张的革命动员,革命者自觉推动集体创作常态化与组织化。苏区俱乐部中普遍设戏剧组(股),新剧团中设有编审组。新生苏维埃政权积极探索建立模范剧团,集中骨干力量,推进集体创作。“省应物色影剧特长人才创造模范剧组,编辑剧本。”(38)方锡银:《黄石老区教育史》,内部发行,1999年版,第172页。“编纂组的同志聚在一起共同确定主题,分析研究,然后个人分头结构。初步结构完成后,又聚集一起将各人结构谈出来,然后截长补短,将结构确定,推一人执笔。剧本写完后,必须叫当地党委审阅批准,方能正式演出。”(39)刘绶松:《老根据地文艺活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红军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1932年成立的中央工农剧社编审委员会是苏区最具影响的集体创作小组,由沙可夫、韩进、赵品三、李伯钊、胡底等苏区戏剧骨干组成,在1933—1934年间接连推出《战斗的夏天》《沈阳号炮》《松鼠》《改选之前》《假充老婆》等大量产生广泛影响的剧本。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从地方征集的剧本,总量不少于65部。(40)张启安编著:《共和国的摇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8页。尽管其中不乏个人创作,但由于创作者进行创作时所依托的不是个体身份,而是集体身份,以服务于集体革命实践为主旨,只是别一种形式的集体创作。
面向全苏军民公开征稿是中央苏区时期实施集体创作另一重要方式。革命年代的公开征稿常常具有明显的文化突击特征。1933年3月,工农剧社改组,编审委员会正式开展工作,向全苏公开发布征稿启事,不仅面向前后方俱乐部征集现有剧本,而且征集戏剧创作题材。(41)《工农剧社启事》,《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60页。1933年8月31日,《青年实话》编委会发布《征集山歌小调启事》,面向红军战士及工农大众征集流行的山歌、小调,编辑革命山歌小调集。(42)《征求山歌小调启事》,《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79页。4月21日,教育部创办的《苏维埃文化》公开发布征稿启事,向“每个从事文化教育戏剧工作的同志”征集剧本等文艺作品;(43)《〈苏维埃文化〉征稿启事》,《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302—303页。1934年6月20日,为改善对白军士兵的宣传煽动工作,《红星》也面向部队官兵发布征求宣传白军士兵的革命歌谣小调的启事。(44)《征求宣传白军士兵的革命歌曲小调》,《红星》第49期(1934年6月20日),第4版。公开征稿营造出一个开放的集体创作平台,吸引广大的工农大众集体参与戏剧创作,有效地激活苏区潜在的戏剧创作资源,丰富戏剧创作题材,拓展剧本来源,推动苏区戏剧大规模生产。
瞿秋白在推动苏区戏剧集体创作走向深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据赵品三、石联星等人回忆,瞿秋白积极发动工农剧社演员开展集体创作活动。“我们没有作家、戏剧家和作曲家,可我们可以搞集体创作,可以向山歌、民歌学习,把群众中好的东西记录下来……”;(45)石联星:《秋白同志永生》,汪木兰、邓家琪编:《苏区文艺运动资料》,第351页。“集体创作不但能多产生剧本,同时能很快地提高每个同志的写作水平”。他要求工农剧社演员制定创作计划,并由总社综合成总的计划;鼓励他们深入体验工农大众生活,与工农大众做朋友,听取和记录他们的故事,从大众生活中汲取创作资源,接受工农大众指导,吸引大众集体参与戏剧创作。与此同时,瞿秋白积极推进戏剧集体创作制度化,领导工农剧社和蓝衫团(苏维埃剧团)制定剧本审查与预演制度,规定剧本需经过集体讨论、审查、预演之后才能正式演出,在演出中不断完善和成熟。“凡剧本,没有经过预演,是不可以肯定好坏的。剧本的成功,必须经过‘写’和‘预演’两步程序。演一次改一次,才能有好的剧本产生。”(46)赵品三:《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话剧工作的回忆》,《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499—500页。
1934年4月教育人民委员会批准的《工农剧社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等教育法规进一步完善了集体创作制度。《工农剧社简章》设计了一套从支社到总社自下而上,上下联动的集体创作制度,规定工农剧社各支社“平时有系统地研究戏剧理论及剧本,收集当地材料,练习上述各种游艺,并按时将工作情形及所收集材料报告分社。”“工农剧社的县分社及省分社负责指导下级剧社,供给短篇剧本,指示工作方法。”“工农剧社中央总社负责指导省分社编制剧本,并会同高尔基戏剧学校及中央苏维埃剧团编发戏剧运动函授讲义,在理论上及实际上领导全苏区工农剧社”。而《苏维埃剧团组织法》则强调苏维埃剧团应注重在演出中不断推进集体创作。“每次巡回演出后,委员会必须向教育部作出书面的总结报告,并先在团员大会上讨论批判,采纳团员的意见,一并报告教育人民委员会。”(47)《苏维埃剧团组织法》,《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233—236页。
1934年初,中央苏维埃剧团春耕巡回演出期间,采用新的集体创作方式,深入民众生活,引导民众参与戏剧创作,提高了戏剧生产效率,即时表演了《惰二嫂不努力耕田》《小脚妇女积极参加生产》《富农婆压迫与毒打童养媳》《奸商富农破坏苏维埃经济》等反映当地民众革命生活的新编戏剧,深受民众欢迎。“我们在这次巡回演出中,与群众生活打成了一片,我们开始在新的环境中,运用我们新的工作方式,使我们的表演更能深入群众,群众欢迎它,模仿它,工农大众的艺术特征鲜明的标志更显著了。这次我们还在表演过程中,开始培养工农出身的作家,虽然才是开步走,但在集体创作方法中我们已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一个月来剧团研究组创造了八个活报、三个戏。——这当得过去剧社编审委员会数月的产额。”(48)戈丽:《苏维埃剧团春耕巡回演出纪事》,《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第307页。当然,在紧张的苏维埃革命战争中,集体创作的组织化过程往往非常仓促,有着明显的军事突击特征。集体化创作成为苏区军民集体化生活的独特表现形式。
结语
戏剧的组织化生产集聚了革命乡村既有的戏剧资源,扩大了苏区戏剧的生产规模,提高了苏区戏剧的传播效率,推动苏区戏剧在乡村的广泛兴起,既满足了革命动员的现实需求,也契合了革命者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生产的文化想象。对于革命者来说,戏剧的组织化生产既是一种现实的革命动员策略,也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生活形式。革命者通过组织化的演剧重建了乡村大众的公共生活,同时也“将文艺理念通过组织的规范与运作传达并在每个支端末节建立其绝对的权威。”(49)李振:《苏区文艺的组织化过程》,《文史哲》2014年第4期,第30页。革命重建了现代戏剧的艺术精神,使戏剧生产与政治动员及军事突击连结在一起,演剧成为现实的革命突击实践。革命者就地取材,突击生产,创作出大量扩红戏、春耕戏、肃反戏、祝捷戏、出征戏等与革命现实紧密相连的剧目,用身边人演身边事,激发群众的观剧热情,强化宣传的即时效应。在演出形式上,苏区戏剧演出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化装表演、活报以及各种“旧瓶装新酒”的歌舞小戏在苏区十分盛行,话剧形态也变得更加开放,杂糅歌舞、曲艺等多种艺术元素,追求观演一体,尽管艺术形式相对粗糙,但常能取得强烈的戏剧效果,演剧成为革命突击宣传最有效的形式。成型于苏区的戏剧组织化生产在延安时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戏剧制度,规约着中国革命戏剧的大众化历史进程,对中国当代戏剧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