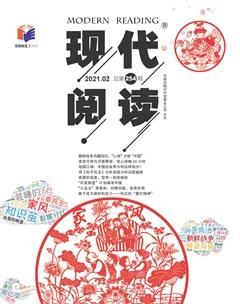与鳝鱼来一场曼妙的相遇
杭州地处长三角南沿,南与绍兴、金华相接,北与湖州、嘉兴两市毗邻。市内,西有丘陵分布,东则地势低平。隋朝大业六年(610),杨素凿通400多千米的运河,从江苏镇江沿吴地越嘉兴而下。后又经唐朝、五代十国、北宋历代变迁,这座钱塘江边曾经的小小村落已然“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逐渐成为江南人口数量最多,商业最繁华的州城。直至宋室南迁至此,随钱塘江水滚滚而来的八方菜系,于这片“水牵卉服,陆控山夷”之地汇聚融合,有绍兴的蓑衣虾球、宁波的冰糖甲鱼、嘉兴的炒虾蟹,更有湖州的五彩鳝丝。
鳝鱼是一种奇特的食材。很多人觉得鳝鱼有一股腥味,难闻得很,不像是什么珍贵的东西。但江浙人、闽南人却很把它当回事,因它一是鲜嫩,二是少刺。鳝鱼整食容易腥腻,但切丝切块倒显得口感柔润。
鳝鱼亦可作药用。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
黄质黑章,体多涎沫,大者长二三尺,夏出冬蛰。
用黄鳝鱼数条打死,香油抹腹,蟠疮上系定,顷则痛不可忍,然后取下看,腹有针眼皆虫也。未尽更作,后以人胫骨灰,油调搽之。
效果有否,皆不可考。但从现代营养学的成分和角度考证,除了鱼类富含的卵磷脂和DHA,鳝鱼中还有鳝鱼素,有调节血糖之效,特别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
现今,鳝鱼多为人工养殖,少有野生捕捉的了。长辈教我挑选鳝鱼时,强调色、触、味,色要灰黄,触觉要硬朗,味则指闻起来要清。
杭帮菜中的五彩鳝丝,因为有了春笋的加入,成了一道热门的时令菜。
杭州人最重视时令,善用时令食材也成了杭帮菜的根本。千百年来,以农业生产为根据,天文观测
为骨骼,中国人自成一套独特的时令与节气论,时令食材本身就是天文、气候及物候文化的集合。鹅肝鱼子再珍贵,也不及时鲜货来得鲜美。
竹笋是山珍海味中的“下八珍”之一,清代文人李笠翁曾誉其为“蔬菜中第一品”。
立春一到,春笋便来了。春雨润泽,山上的泥土里水分充足,是笋生长的最佳时节。破土而出的笋尖,恰如一声响雷,呼唤挖笋人上山,撷取这份春日馈赠。春笋肉质鲜嫩,通体洁白,如玉般透亮,光看卖相已经是极品。于是,古人用它来比喻美人的指尖,比如苏轼的《满庭芳》里曾有:
报道金钗坠也,十指露、春笋纤长。
唐太宗最愛吃春笋,每到春笋上市的时节,总要召集群臣来一场“笋宴”。
但因笋多生于南方,古代的北方人要想吃到点儿春笋简直难上加难,往往到嘴里的时候已经变老,咀嚼起来索然无味。
唐代李商隐曾经说到北方春笋的金贵:
嫩箨香苞初出林,
於陵论价重如金。
白居易的《食笋》中更是慨叹:
久为京洛客,此味常不足。
笋最善吐纳,所以极宜搭配味道冲的食材,与鳝丝同炒,可以冲其腥气,也能入鲜味。
先将鳝鱼破开,也就是剪开脊梁,破开龙骨。鳝鱼头部的肉无甚可取,是整条身上最“柴”的部分,遂弃去。在江南地区,市场上常有烫好划丝的鳝鱼售卖,不需要再回家费事处理。
接下来,便是“五彩”的处理。中国菜讲究色香味俱全,杭帮菜素喜色泽清雅,少旁杂,但也要有趣味。嫩白的春笋,既承担“清雅”,也负责“鲜香”。鲜亮的红椒和青椒,不仅用来提味,颜色更是“小绿间长红,露蕊烟丛”,为菜品增色。
除去鳝丝,食材里和春笋最搭的便是火腿。两者难分主次,互相入味,相辅相成。
杭帮菜的清淡,是以原汁原味为基础,追求一种极耐品咂的细微口感的变化。因此,丝切得越细,便越容易吃出不同的层次与体会。
鳝鱼吃多了,易导致消化不良。因此,一小盘浅尝辄止,便是时令里与这道菜最曼妙的相遇。
(摘自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国宴:至味在西湖》 作者:姜晟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