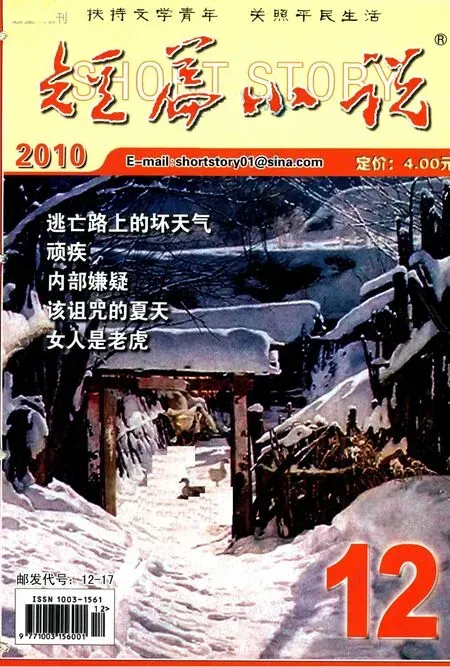内招兵
◎宋秋实
上了火车,程东风和徐卉卉才摘掉了扣在脸上的医用大口罩,解开系在下巴上羊剪绒军帽的系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
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程东风脑袋里忽地冒出电影《地道战》里这句有名的台词,暗想,去当个兵,搞得跟鬼子进村似的。

昨天晚上这个时候,程东风在村里的大队部急急忙忙地接了父亲的一个电话,说外婆病了,让他赶快回家。回到家才发现外婆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程东风想没有大事家里是不会以这样的借口叫他回来的。
事情源于邻居家的徐卉卉。
徐卉卉是程东风青年点的同学,三天前请假回了家,磨着家里人非要去当兵。
当时程东风就奇怪,卉卉好好的怎么就突然回了家。
卉卉的爸爸徐大夫和程东风的爸爸一样都是邻近边陲红城中部队医院的普通医生,在部队里属于干部中垫底的存在,把孩子送去参军,困难不是一般的大。卉卉的爸爸求遍了可求的熟人,还是没给卉卉找到当兵的路子。
卉卉见爸爸没招儿了,便说:“爸,你别费劲了,我自己来,直接去分部找首长,就赖在那儿不走了,看他们收不收。”
卉卉爸是真怕了这疯丫头,这孩子的脾性是说出来就能做出来,大姑娘家家的一个人往外跑还不把人担心死了。
“让你家东风回来和卉卉一起去吧。”卉卉爸和程东风的父亲商量。程东风的父亲和卉卉爸相比人脉更差,也正在为儿子的前程着急,他想了想,心想这事能成更好,成不了也不丢孩子们一块肉,就当让孩子们去闯荡闯荡,便说,“好吧”。
从内心讲程东风是不太想去的,但他理解爸妈的心情,虽然他们没那么大能力把儿子直接送去当兵,但他们不愿放过任何一个能让儿子有个好前程的机会。
可能是夜车的原因,车厢里人不多。程东风向坐在对面的徐卉卉问道,“徐叔叔为什么要我跟你一起去呀?”其实他是明白卉卉爸妈的心思的,有个男孩子跟着毕竟安全些,更主要的是程东风稳重,遇事能帮卉卉定定砣,但他还是想听听卉卉怎么想。
卉卉咯咯笑了,“他们喜欢你啊,你知道,他们打小就喜欢你,你可没少吃我妈包的饺子。换别人他们不放心,把他们的宝贝闺女拐跑了怎么办。”
程东风脸一红,“别瞎说,谁能拐跑你,你不拐跑别人就不错了。”
程东风和徐卉卉同岁,两家人的关系极好,两人的妈妈怀着他们大肚子的时候,两家的大人说笑着约定,若生的分别是男孩和女孩就做亲家。
小时候,卉卉妈妈见到程东风就喊大姑爷,徐家包饺子,吃好东西一定会给程东风送过来一份儿。程东风的爸爸见到卉卉就说,叫老公公。大点儿之后,知道害羞了,两人便很少说话,大人说什么也当笑话听。等到中学快毕业的时候,两人终于可以像正常的男女青年一样地说话了,可程东风发现眨眼间徐卉卉已经变成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
见卉卉面带不悦,程东风赶紧说,“把你的水缸子给我,我去给你打杯开水。”卉卉从军用挎包里掏出来一只绿色的搪瓷缸子递给程东风。
打水回来,卉卉吹着缸上的热气,试着喝了一口。
“卉卉,你说我们这么个去法儿能有多大把握,能成吗?”程东风问。
“就是有一成的把握也要去,爸爸听一个朋友说,现在军委叶帅说了算,有人请示叶帅说,地方的孩子没工作可以接班,部队的孩子没有班接怎么办?叶帅说,可以当兵。叶帅发了话大单位的孩子们连那些不够岁数的一夜之间都要去当兵,就我们这样的小地方、小单位的孩子还在农村在家里待着。这次口子开得大,机会难得,一定得试试。”
听徐卉卉说完,程东风明白了为什么最近青年点一下子走了好几个人去当兵了。邢院长的女儿邢亚红下乡在知青点只待了几天就走了,应该是邢院长自己的神通。首长们的孩子去当兵,是正常的,有首长们说句话就行了。
这种通过特殊关系入伍的兵在部队被称为内招兵,数量不是很大。可最近连续走的李副处长的儿子,聂教导员的女儿,田医生的儿子,都不是首长们的孩子,显然是搭了叶帅的这班大数量内招兵的顺风车,叶帅是替基层干部的子女说的话。
连续有人当兵离开了农村,其他的人便心慌了起来,就像一粒接一粒的石子投进湖里激起的涟漪一样,一波一波地震荡着青年点每一个知青原本平静的心。这当然也包括卉卉和程东风。
列车开动了,昏黄的光线中站台两侧的灯柱和建筑缓缓地向后闪去。
程东风有些忐忑,因为他和徐卉卉是从货场溜进站的,没有买票。离家时母亲在他的上衣兜里塞了二十元钱,这也是他长这么大兜里第一次揣了这么多钱。生产队实行工分制,钱要秋后分红才有。队里一个工分能合五分钱,程东风一天能挣十个工分,从七月下乡到年底能挣个七八十元就不错了。
程东风摸了摸军装的上衣兜,那折成两折的二十元钱静静地躺在里面。这钱要省着花,别兵没当上,反倒没了一个多月的工分。车上不查票最好,查了也要想法赖过去。
一个小时后,列车停在了一个叫元庄的小站。从小站再往前走十里,就是程东风和徐卉卉下乡的村子了。列车再开起时,一个抱孩子的农村妇女坐在了卉卉身边。孩子哭闹起来,女人有些慌乱,忙解开对襟棉袄,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
“大姑娘的奶是金奶,新媳妇的是银奶,生了孩子就是狗奶。”和程东风并排走着拎着一桶白漆的陈玉说。陈玉是大队治保主任的弟弟,和程东风同是七六届毕业生,毕业后在程东风的小队当会计。
程东风顺着陈玉手指的方向看去,见初秋的暖阳下一个岁数不大的女人正敞着怀奶孩子,两个雪白的大乳房,一个露在外边,一个被孩子含在嘴里。“看见那女的没,才十八岁,一生孩子就跟老娘们一样了,啥也不忌。”陈玉的眼睛像钩子一样盯着那喂奶的女人。
程东风就笑陈玉,“你都说人家那啥是狗的了,还瞅个没完。”
陈玉说,“那不是为了配合你看个新鲜吗,这个你在城里看不到吧?”
两人说笑着走到了中街青年点门前。青年点有点像四合院,前后两栋,一栋西厢,东边空着,和大队部的大院相连,一水儿的红砖红瓦,是全村最好的房子。两栋正房的墙上用白粉笔分别写着一行仿宋体的大字,“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字是程东风昨天写的,还没刷上白漆。
陈玉站在墙前端详着墙上的大字说,“挺好看的,你真有才,不过我说你把后院那条团结紧张整完就行了,前院那条就算了,还能省半桶白漆。”
程东风就问,“为什么?”
“我觉得你们这个点当兵的孩子早晚得走,你看那个姓邢的长得挺白挺胖的大眼睛姑娘,才待几天就走了,不写这个省得村里人说你们口不对心。”
见程东风要张嘴说话,陈玉又说,“哎,你也别怪我说得不好听,其实走也没什么,招工,招生,招兵,哪年都不少走,扎根只是号召而已,你们走,不占队里的名额,对我们是好事。”
“哎,想什么呢,前面就是咱们大队啦。”徐卉卉敲了敲桌子。
程东风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说,“走神了。”
徐卉卉看着程东风,程东风能感觉到卉卉有点上翘的凤眼里那缕炽热的火苗。徐卉卉说,“我看出来你走神了,你走神的样子挺有意思的,眼睛里像是什么都没有,又像藏了好多东西。我喜欢这个样子。”
程东风避开了卉卉的目光望向窗外,窗外黑黢黢的一片,远处青年点所在的村庄静卧在夜色之中,只有铁道两侧落满白雪的灌木和路基在车窗透出的灯光中忽隐忽现。
“检票了,检票了!”车厢的一端传来列车员的喊声,车厢里乱了起来。没票的人有的躲进了厕所,有人起身向另一侧走去。程东风和卉卉尽管心里发慌,但坐在座位上没动。
列车长和一个乘务员走过来,对程东风和相邻座位的人说道,“把你们的票拿出来。”
程东风和卉卉站了起来,卉卉朝列车长笑了笑说道:“知青,还没分红呢,没有钱。”
列车长看了看穿着一身军装的程东风和卉卉问:“你们家长是哪个单位的?”
卉卉说:“前进医院的。”
列车长没再说什么,盯了他俩一眼便转身离去。
逃票竟然如此容易。程东风和卉卉都松了一口气。想来应是知青的身份或是这身军装和父母单位的名头起了作用。
“是个好兆头,我们以后都能这么顺就好了。”卉卉说。
“会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程东风学着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瓦西里的台词,顺和着卉卉说。
程东风和卉卉要去的地方是叶寿城郊的齐杖子被服仓库。出发前,卉卉爸爸说,分部的一个新兵连就在那里集训,到了那里,跟在新兵连队伍后面,赖着不离开就行了,这个办法好多单位去当兵的孩子都用过,很灵的。
程东风想,到了齐杖子两人会怎样,会像吴琼花参军一样跟在队尾吗?和演吴琼花的祝希娟比,卉卉更漂亮,程东风的脑子想象着卉卉跟在队尾的样子。
半夜一点多钟两人在叶寿下了车。夜,黑沉沉的,细碎的雪花随风落下,车站昏黄的灯光射向四周没有多远便被无边的夜色吞没。雪花衬着人们的影子在灯光中摇曳,斑斑驳驳,空离而虚幻,给人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如入梦境。程东风掐了掐自己的手和脸,实实在在的痛感传来,不是梦境。
没有住宿介绍信,两人没有旅店可去,只能在车站熬到天亮。候车室的长椅上满是或躺或坐的候车旅客,中间的空地上一个汽油桶做的大炉子烧得正旺,火苗透过炉顶盖子的缝隙在暗黄的白炽灯下不停跳跃着,让刚刚从雪夜中走进候车室的旅客们感到格外的亲切和温暖。
程东风找了一个空位置,让卉卉先坐下。卉卉从背包里掏出一张报纸铺在空位上坐下后,看着一旁站着的程东风说,“我们挤挤坐吧。”
她挤了挤左侧挨着她的中年妇女,又把右侧躺着睡觉的农村大爷的腿蜷了起来给程东风弄出一个刚好够一个人坐的空位,随后又把铺在自己身下那张报纸抽出铺在空位上,用报纸隔开了睡着的农村大爷的脚。
“坐呀,还傻站着干啥。”卉卉说。程东风看着那窄巴巴的座位有点迟疑。
“别磨叽了。”卉卉伸出手拉着程东风坐了下来。
这是程东风第一次和卉卉这般近距离地相邻而坐,即使隔着厚厚的棉衣他也能感受到少女柔软的身躯散发出的温暖。
程东风闭上了眼睛,对卉卉说,“对付睡一会儿吧,明天还要起早去仓库。”卉卉嗯了一声后便不再说什么。
初秋,快要下山的斜阳懒洋洋地照在人们的身上,悄悄地褪去了夏日那种热辣。青年点门前的白菜地里,程东风把从厕所掏来的粪便兑在一只木制水桶的水里,一垅一垅地浇着已经分棵定型的大白菜。
卉卉下工回来,见程东风一个人忙着,便说,“我来帮你吧。”
“别介,怪臭的,你回去歇歇吧,上一天工了。”
卉卉拎起水桶去渠里打水,说,“没事,我陪你一起挨熏好了,正好有点事和你说。”
程东风就问,“什么事啊?”
卉卉压低了音量,“东风,你说那柴保国烦不烦人啊,天天跟在我屁股后边转,惹得别人乱咬舌头,搞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帮我拿个主意呗。”
柴保国和卉卉是一个生产队的,高高的个子,长得挺精神,父亲是行政处的处长。卉卉漂亮,青年点有好几个男生明里暗里追她,这柴保国是追得最紧的一个,大家都在传,说两个人在搞对象,为这事青年点的带队干部贾教导员还分别找两人谈了话。
程东风笑了笑,真不真假不假地说,“柴保国人长得挺精神,家庭条件也好,对你也蛮不错的,你们看起来倒是挺般配。”
卉卉嗔怪地白了程东风一眼,说道:“你瞎说什么呀,那柴保国就是绣花枕头草包一个,中看不中用,我对他真的是一点意思也没有,不过你要是能像柴保国那样对我,没准我还真能寻思寻思。”
卉卉是个直性子的人,想啥就说啥。在卉卉热辣辣的目光下,程东风掩饰着内心的慌乱,认真地对卉卉说:“卉卉,别人乱说,也没什么,柴保国剃头挑子一头热大家心里也清楚,不过你离这些小子远点还是应该的。带队干部一再说不许搞对象,不管是柴保国还是别的什么国追你都不能当真,别为这事影响前途。”
卉卉脑子有些热,程东风不能不理智,知青搞对象的结局好的不多,有些话他也一直想对卉卉说,但没合适的机会。
卉卉似乎有些不高兴,伸出拳头做出要捶打程东风的样式,回应道:“你啥都好,就这死正经劲让人受不了。”
天亮了,鱼白色的晨光从满是霜花的窗子透进候车室。程东风起身在大炉子上翻来覆去地烤着四个从家里带出来的白面馒头。慢慢地馒头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硬壳,空气里溢散着诱人的面香,不时地有人将目光盯向那四个烤馒头。程东风和卉卉就着开水干掉了四个馒头后,起身上路了。
去仓库的路很好找。车站到仓库有一条铁路专线,铁路线旁边是一条沙石路。
天蓝雪白,晨光里,两人急急地走着,军用大头鞋踩得雪地咯吱咯吱直响。
一辆拉着一台柴油机的四挂大马车从身后赶了上来,赶车的是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程东风用当地的方言对赶车的车把式喊道:“掌包的,我们去前面的部队仓库,捎我们一段中不中啊?”掌包的是当地人对赶车的尊称。
车把式看了两人一眼,爽快地应道,“有啥不中的,上来吧!”
上了马车,徐卉卉笑着对车把式说,“谢谢你啊大叔,没你这大马车,这两小时路可是够我们俩走的。”
车把式说,“谢啥哈,顺路的事儿,我们村和部队仓库邻着嘞。”
程东风问:“掌包大叔,那你看到部队里有没有许多和我们一样穿着新军装不带领章帽徽的年轻人?”
车把式应道,“前些晌(日子)好像见到过许多,最近哈没留意。”新兵在新兵连期间是不带领章帽徽的,分配到部队戴上领章帽徽才算真正的军人。仓库里穿军装不戴领章帽徽的人应该就是新兵。
程东风一路上提着的心微微地放了下来,有些兴奋地对徐卉卉说,“徐叔说的是对的,新兵连应该就在这,找到新兵连,事就成了一小半。”卉卉也有些兴奋,挥手对四匹口鼻喷着热气在路上疾驰的马喊道,“驾!”
齐杖子仓库南向坐落在一座高大的褐红色石头山峰的脚下,南东西三面砌着红砖墙,北边靠山,院内有两座小楼和几排平房。
高大的红色山峰越来越近了。走到一个丁字路口的时候,马车停了下来,程东风和徐卉卉谢过车老板,跳下了马车,走向仓库的大门口。仓库院里一些年轻的战士在清扫着地面上的积雪。都是当兵的,没有那些穿军装不戴领章帽徽的人,程东风的心向下沉,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他瞅向徐卉卉,卉卉也在瞅他。
仓库的大门口有一个一人多高木制的绿色小岗楼,岗楼旁立着一块红底白字的牌子,“军事禁区,严禁入内”。岗楼前一个小个子卫兵持枪而立。
小个子卫兵操着四川口音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有啥子事?”
卉卉说:“我们是前进医院的,要找吴主任。”
来之前的晚上,卉卉爸交代说,你到齐杖仓库找吴主任,我给他当过几天管房大夫,大事他管不了,照顾一二还是可能的。
卫兵走进岗楼,操起岗楼里的电话,摇把子摇了一阵后,卫兵说:“值班室吗?有人要找吴主任,是,吴主任开会去了,不在。”
卫兵放下电话对两人说:“吴主任开会去了,不在。”
卉卉问吴主任什么时候回来,卫兵说不知道。
卉卉说:“东风,我们等,一直等到吴主任回来。”
卫兵换了两班岗,都知道这两人在等吴主任。两人脚冻得直痒,只好原地转圈不停地跑,热汗和呼出的热气将羊剪绒军帽的外沿和眉毛染成了白色。
一辆北京吉普从院里开了出来。
徐卉卉和程东风站在路中间张开双臂拦下了吉普车。一个年轻的军官跳下车,厉声问道:“什么事?为什么拦车?”徐卉卉说:“不和你说,我们要见车上的首长。”
一个面色白净,长得有点儿胖的中年军人从车上下来,上下打量了两人一下,“你们有什么事,家长是哪个部队的?”
徐卉卉忙迎上前笑着说:“叔叔,我爸爸是前进医院的徐凯,他叫我们来找吴主任,说新兵连在这,我们要当兵。”
中年军人说:“老吴去分区开会了。新兵连不在这儿,一星期前就走了,你们找老吴也没用。”卉卉接着问:“那新兵连去哪儿了?”中年军人说:“不知道,知道也不能告诉你,部队有保密条例你们该晓得吧。”
中年军人避开了两人失望的目光,转身对卫兵说:“告诉政治处给他们弄点热乎的吃,看看有没有方便的车,把他们捎到叶寿。”
兵答道:“是,魏政委。”
画了一个圈,一切又似乎回到原点。叶寿火车站候车室内,徐卉卉在看去夕阳的火车时刻表。程东风则在犹豫是继续北上夕阳还是南下回老家。能当上兵当然是最好的。自己枪打得准,学校军训打靶,老式的七九步枪,三枪二十九环,赶上战争立个功也是可能的。
实际一点的话,争取先在连里当文书,再到营里当书记,提个干是不成问题的,写写画画是他的特长。可问题是,没了熟人,新兵连找不到,只能硬闯分部,万一兵当不成,又闹出影响来,还怎么在青年点干。
“卉卉,当不成吴琼花,就回去当吴献忠吧。”程东风对转回身刚要开口说话的徐卉卉说。
卉卉一愣,随即明白程东风的意思,声调也比平常高了两分,“要回去,你一个人回去,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问题是到了分部我们连大门都进不去,还能遇到魏政委那样的好心人吗?”程东风问。
“那就在大门口等,说什么也要见到分部首长,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再不行就写血书,绝食,我不怕把事情闹大。”
徐卉卉想法和程东风不一样自有她的道理。程东风是知青里的人尖子,在学校时就是学生干部,全市七六届毕业生上山下乡誓师大会上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过言,是大家公认的才子。
卉卉就不一样了,政治表现平平,想在广阔天地闯出点名堂来也是难。还有些话,徐卉卉也不好对程东风说。大队管青年工作那个长得人模狗样的副书记,找卉卉谈过几次话,夸卉卉长得好看,说卉卉只要肯要求进步,入党,招工啊,都可以考虑的。
卉卉既怕他,又觉得他恶心,在村里,遇见他就躲得远远的。靠自己努力去当兵对卉卉来说也许就是她人生最好的出路。
程东风叹了口气说:“唉,我就是建议一下,你既然坚持要去,我陪你就是。”
卉卉有些赌气地说:“我们买票去夕阳,再买些吃的,把钱花尽,破釜沉舟,断了回家的念想。”
程东风和卉卉在夕阳站下车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了。“解放军同志,麻烦你能告诉我们去分部的路怎么走吗?”程东风向一个肤色白皙文质彬彬的部队干部问路。军人打量了两人一眼。两人年纪不大,穿四个兜的军装,这是部队家庭子女最常见的穿着。
“顺这条路向东走两公里,过了肉联厂向北沿玉山路一直走就到了。”军人回答得很细致。
“有公交吗?”卉卉问。
“公交要一小时一班,还没有走快呢。”
“那我们还是走吧,卉卉。”程东风说。
太阳西沉,收走了它最后一抺余晖。没了阳光的冬日又多了些许阴寒。过了肉联厂转向玉山路后,北风兜面而来,像一把把小刀在脸上刮过。程东风和卉卉不约而同地掏出口罩戴在脸上。
前后没有行人。马路的东边是一条两米多宽的灌渠,落满厚厚的白雪,通向不远处的村庄;西边的大片空地上覆盖着殷红色的冰层,是动物的血液和积雪融合而成。红色的冰野在周围茫茫雪色中分外醒目。
程东风对卉卉说:“我们靠中间些快点儿走吧,争取天全黑前赶到分部。”黑灰色的柏油路只有中间比一辆汽车宽的地方露出本色,两边的人行道尽是板结了的冰雪。黑色的柏油路上两人加快了脚步。
一辆丁字开头的解放CA10军车驶入了玉山路。副司机王三娃瞪大眼睛,打开大灯,踩离合挂上了五挡。还有几分钟的路,马上到家了。早上王三娃和班长接了去矿山拉煤的任务。中午装完煤的时候班长急性阑尾炎发作住进矿务局医院。打电话请示连长,连长命令先把煤拉回来,说连里会派人去矿务局医院看班长。
想到医院里的班长,王三娃有些分神。这会儿班长该做完手术了吧,会穿孔吗?大夫说穿孔会很麻烦的。王三娃脑子里浮现出班长捂着肚子,疼得面目扭曲的样子。
两个向一边躲避的行人的身影出现在车头前的灯光里。回过神来的王三娃惊出了一身冷汗,刹车,打方向,可车轮像抺了油一样,不听使唤,车头奔向行人撞去。
半明半暗的天色,系得紧紧的帽耳,注意力全在赶路上,这一切都降低了程东风和卉卉对身后的感知。当程东风发现身后的灯光,向后转身,拉着卉卉匆匆避向路边时,却见一辆汽车的车头径直向他们撞来。
车头撞来那一刻,程东风用力将卉卉向路边推去,接着,便是自身和卡车蒙皮的撞击声,一切都淹没在巨大的疼痛和无尽的黑暗之中,一切都在瞬间远去,一个念头闪过,完了,被撞死了。
手术室门楣上方的红灯亮着。徐卉卉和王三娃一个坐在手术室门口的长椅上,一个在长椅旁站着。卉卉脸色惨白,红肿的眼睛盯着手术室上方的红灯。王三娃在地上转着圈,眉心揪成一团,两只手不停地搓着。
他们只知道程东风已经输了2000多毫升鲜血,因为这其中有400毫升是卉卉的,卉卉是O型血,王三娃的血型对不上,其他的都是医院的工作人员献的。程东风腹腔内大出血。
万人体育场人声鼎沸,红旗如海。两点多钟的太阳热辣辣地挂在天上,烤得人全身是汗,满脸冒油。程东风站在主席台前面的长桌后,长桌上并排立着三支麦克风。没用稿子,稿子的内容早已印到了脑子中。
“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同学们、战友们,这个火红的岁月为我们的人生搭建了壮美的舞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启程自我们英雄的城市红城,落脚在广阔的农村、草原……”
台下红旗舞动,毕业生们向台上涌来,争抢桌子上的麦克风。桌子被挤倒了,程东风被人们踩在脚下,肚子和全身一阵阵疼痛……
天和地都是白色的,雪不停地下着,落在脸上,又化掉,像是去仓库的路上。
回家了吗,妈妈在哭。想睁开眼睛,眼皮太沉了,睁不开。妈妈说,“都怨你,乌鸦嘴,说什么丢不了孩子一块肉,你看看好好的孩子没了脾,你让他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爸爸的声音,“这孩子也是,他不推卉卉一把也许就没事了。”
自己还活着,没死,爸爸妈妈在身边呢。
程东风醒了。妈妈哭着说:“儿子啊,你可醒了,你都要吓死妈妈啦。”
午后的阳光照进病房,让素白的病房更加明亮。
徐卉卉拎着一个小网兜进了病房,兜里装了几个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的苹果。和程东风的妈妈问了一声好,徐卉卉拉了一把椅子坐在了床边。妈妈说,“我去打壶水。”拎起暖壶走出了病房。
程东风昏迷不醒的时候,徐卉卉几乎天天都来。程东风苏醒的那天,徐卉卉哭着对程东风说:“都是我不好,非得拽着你来当兵。”
旁边的妈妈说,“你输了好多血,其中就有卉卉的。”卉卉廋了,脸上也没了在青年点时红润的血色。程东风望了卉卉一眼,无力地闭上眼睛。
徐卉卉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把精巧的水果刀,又从网兜里拿出一个苹果坐在椅子上不声不响地削着。随着卉卉一只手不停地旋转,一条长长的果皮脱了下来。卉卉变得很安静,没有了以前那种洒脱奔放。
卉卉看着程东风说:“你别难过,你要是愿意,你以后的生活我会照顾。不是你推我一把,我也不知道会是啥样。”病房里静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
程东风有些难过,他觉得徐卉卉看向他的眼神没了那团热辣辣的火焰。程东风说:“你别犯傻了,我能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我不需要人照顾。”
一拨一拨的人来看程东风。王三娃和王三娃的连长,带队干部贾叔叔,大队王书记,还有卉卉的爸爸。人们来看他的时候,程东风的话很少,常常走神,两眼空空的,不知在想什么。
分部的参谋长来病房看望程东风,参谋长瘦高的个子,长得很像南征北战里的高营长。程东风想要起身,参谋长伸出双手向下一压,示意他躺下。
参谋长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参军是不可能了,部里已经通知前进医院替你办理病退回城手续,工作的事嘛再想想办法。你和家里还有什么要求可以和部里提。”
程东风提了两个要求,轻一点处分王三娃,让徐卉卉当兵。参谋长说,“怎么处理王三娃部队里有纪律,徐卉卉的事,我个人说了不算,要集体研究一下再说。”
参谋长出去了。程东风想,兵当不成了,广阔天地回不去了,自己的天地在哪?后悔是没有用了,好在自己脑子没撞坏,手脚好好的,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徐卉卉来和程东风道别,卉卉要当兵走了。据说是参谋长说的话,说是基层干部的子女很不容易。两个人握了握手,徐卉卉先伸的,稍稍地等了那么一小片刻。
天是阴着的,零散的雪花在窗外落下。
程东风站在窗前,盯着楼下的雨搭,看见徐卉卉从那里走了出来,径直向前面的门诊楼走去。徐卉卉没有回头望向程东风的病房,程东风有点失望,目送着徐卉卉的背影消失在门诊楼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