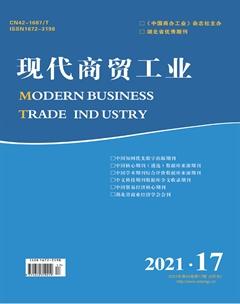失信惩戒的限度问题研究
摘 要:由于缺乏对失信行为明确定义、主管部门权责不清等原因,导致我国各地出现失信惩戒措施适用条件泛化的情形。必须要从失信行为与道德的关系、公民的隐私权等方面出发明确失信惩戒限度的界定方法,健全协同联动的信用修复体系,从而完善我国的信用制度建设。
关键词:失信惩戒限度;信用修复;道德档案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17.066
自国务院于2014年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以来,全国各地开始了探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道路。但是由于缺乏对失信行为明确界定,导致各地出现失信惩戒措施适用条件泛化的情形。并且国务院在2020年12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约束制度构建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也指出应当对失信惩戒的限度应当进行一定的规制,防止不适合的泛用乃至滥用,要确保过惩相当,切实保护信用主体的正当利益。
1 失信惩戒限度现状
1.1 制度的合法性欠缺
由于没有统一的社会信用法的指导,在此情形下,地方立法也仅能依据《立法法》赋予其的权利来进行规定。在联合惩戒的配合下无法避免的是失信行为惩戒呈现泛化的趋势。实践中存在诸如激励少惩戒多、失信行为界定范围扩张等问题。失信惩戒的合法性也就会引起质疑,因为并没有明确的上位法的支撑,面对信用体系的建设,失信惩戒的随意性、任意性会严重引起信用惩戒的权的行使偏离了法治的运行轨道。失信惩戒的合法性是现阶段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国家可以建立起有效统一的管理制度,通过统一的信用立法来完善信用体系的法律保障,避免地方立法对于失信惩戒权的行使过限。
1.2 制度的谦抑性不足
失信惩戒的谦抑性主要是在法律上来看,失信惩戒现采用的联合惩戒的前提就是失信行为基本上已经被相关的法律做出了相应的评价。但是为了防止对于失信行为的重复处罚,在失信惩戒权的行驶过程中如果对于失信行为已经有了其他法律来做出惩罚,那么应当优先适用已有的法律规定,这时失信惩戒措施便应当保证谦抑制性的存在。信用体系的建设是国家在高速发展中的一个产物,社会信用立法也不会是独立于其他法律的部门。它的处罚必然是与其他的违法行为有交叉的部分,如果对于失信惩戒的适用没有明显的界线,那么无论是对于失信行为人的多重惩罚还是对于法律的适用都会产生影响。对于失信惩戒对失信行为人的二次约束是不仅是处于构建诚信社会的紧迫性,还是通过想事前预防模式能够有效弥补事后处罚的不足。但是在适用的过程中对于是失信惩戒权的行使限度还是需要法律来约束的,防止出现对于失信惩戒行为的过度处罚,侵害行为人的基本权利。
1.3 信用激励的界限模糊
2016年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可见建设还需要通过信用激励的手段来进行发展。但是由于近几年来的部分規定混淆了信用激励与公民权利的概念,侵犯了公民权利。比如,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1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发展的通知》,提出了将无偿献血纳入社会征信系统,提高献血者的公共利益。无偿献血是公民的一项权利,其有选择鲜血与不献血的自由,不应当将其作为公民的守信激励来作用。并且失信惩戒措施本身就是一种反向的信用激励,它从对公民信用的严格要求来约束公民的行为,最终形成对信用体系的构建。信用激励作为一种鼓励手段,应当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之余才能继续发挥作用。信用激励不是替代公民权利的可供选择,任何一种激励方式都应当是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由于失信惩戒在没有统一的信用立法的前提下,地方的立法限度出现了泛化的趋势,部分的措施模糊了信用激励和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度。这是地方急于构建社会信用体系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失信惩戒限度的现状表现之一。
2 失信惩戒的适用条件泛化的成因
2.1 失信行为缺乏官方定义
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贯彻于公民内心与实践,是公民的行为准则,它体现的是民族的信仰和公民行为的约束原则。而诚信与信用不同,信用是以诚信为原则的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社会关系。诚信作为法律中的原则性规定是没有具体的内涵所在的,需要人们来进行价值判断,信用则是具体的社会关系与制度。
基于诚信与信用的区分,对于失信行为的界定也需要具体的方法。但是失信行为目前的法律没有具体的规定,而是通过《纲要》中所涵盖的一些区域和规定来解释。这也导致了地方立法的时候对于失信行为的范围把控的不够准确,会出现失信惩戒措施泛化,甚至会对公民的权利进行侵害。部分地方出台的失信行为的范围和惩戒措施就是涉及的范围过于宽广,将有些仅是违反诚信价值观的行为列入了失信惩戒的范围,这是对失信行为的概念没有具体的局势表现。由于目前我国并没有对失信行为定性,并且缺乏统一的社会信用立法,所以产生了失信惩戒的时使用条件泛化现象。
2.2 失信主管部门权责不清
当前,我国的失信惩戒制度主要是全范围的各机关联合运作的失信惩戒。但是失信联合惩戒的机制目前只是已经作为一个简单的概念被主管部门提出和广泛应用,对于具体的失信联合惩戒行为如何界定等诸多相关的问题。因为缺乏权威的认定标准,社会各界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观点和认识也不尽相同,实践中由于缺少相关法律规范,难以作为行政管理中的依据。失信的联合惩戒有利于失信惩戒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但是当失信联合惩戒出现行为认定的错误时,失信惩戒的主管机关该如何负责也是失信联合惩戒制度设计时应当关注的重点。
失信惩戒的相关法律规定和配套制度是形成失信惩戒部门长期有效工作的前提。联合失信惩戒中的主管部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引起了失信主管部门权责不清。当失信惩戒措施的实施过程中产生负面效果或者其他问题时,没有明确的归责原则,使得解决问题的效率低下。实施惩戒的机关容易产生对负面影响的推诿塞责,导致了失信惩戒的适用条件泛化。
2.3 失信惩戒和道德档案混淆适用
《纲要》规定的重点领域失信惩戒仅是对失信惩戒的范围进行规定,但是却没有对失信行为进行明显的界定,这也使失信惩戒的范围泛化。例如北京市交通委将车厢内进食、大声外放视频音乐等规定为可以记入个人信用的不良信息。这对人行为的约束范围已经扩大至日常行为,这让失信惩戒措施出现了滥用的情形。在国家的运行过程中法律的规制应当由明确的立法依据,而法律惩戒的层面应当是与道德由严格区分的,只有严重违背道德且造成法律上的危害后果的行为,方需要进入法律惩戒的范围。目前我国各地的惩戒立法呈现出“道德档案”的趋势,失信行为与失德行为的区分不明。混淆法律与道德的概念会形成失信惩戒措施涵盖范围不断扩大的趋势,比如不同地方立法将公民的本来应当由社会道德规则来规范的行为划入失信惩戒应当规制的限度中。自古以来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就是被学者讨论的话题,在公民的个人行为中应当只有严重违背道德且造成法律上的危害后果的行为,方需要进入法律惩戒的范围。道德与失信行为的范围应是统一的社会信用立法来进行规定。
3 失信惩戒限度的制度构建
失信惩戒由于缺乏统一的社会信用立法,导致了地方立法的适用范围泛化,失信惩戒的界限不清的情形。失信惩戒的具体界定方法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事中、事后的信用修复也是失信惩戒制度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
3.1 明确界定方法
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目前没有明确的国家立法来规定,所以失信惩戒制度应当作为管理性规定来适用。由于信用惩戒措施与其他的法律规范规制的行为具有“重合”性,所以在同一行为触犯到不同的而法律规范时,应当先以其他成文的法律规范来进行规制。失信惩戒措施只能作为一种管理性措施来适用。现在国家信用体系的全覆盖的建设稳步建设中,对于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应当以现有的国家法律为先,防止出现一事双罚的情形。把失信惩戒措施作为管理性规定来适用是对失信行为惩罚较为合适的理解。
现今失信惩戒措施是以行政执法部门联合执法的方式推进,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导致失信惩戒行为被重复处理,或者范围扩大的情形,所以失信惩戒的限度问题是不可忽视的。失信行为应当属于法律的规制范围内,而不能与道德混淆。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线,失信惩戒的限度应当在法律的规制内,切勿上升到道德的约束范围。失信惩戒应当在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失信的联合惩戒过程中会无意间对于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进行公示,但是应当严格明确信息查询使用权限和程序,防止失信被执行人的隐私泄露。
3.2 完善信用修复制度
信用修复理论上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失信惩戒部门对于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判定错误时的信用纠错。另一种是失信被执行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惩戒部门在事中事后通过监管机制使失信主体退出惩戒措施,从而到达信用修复的制度。對于失信惩戒部门判定出错而导致的信用修复主要是源于部分学者认为的信用修复原始的制度意义,而对于第二种的信用修复持有违背制度原意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获得更多的支持。更多的学者认为信用修复应当是第二种的信用修复制度。根据2020年12月7日《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完善信用修复制度,要求失信主体应当按要求纠正失信行为,消除不良影响的,均可以申请信用修复。对于信用的修复也是事后救济失信惩戒限度扩大的重要制度。信用修复也应当是全网覆盖型的制度,信用体系建设的网络覆盖化决定了信用体系的修复工作也应当做到及时、全面。实施失信惩戒的部门应当根据失信被执行人提供的证据后,停止相关的惩戒措施,并且将修复信息及时向社会公示。
信用修复制度也是一种对于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激励和监督,对于整个失信成绩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信用修复工作的有序进行需要失信惩戒部门严格的监督工作,信用修复工作应当伴随着部分惩戒措施的终止行为。在信用的修复过程中,失信被执行人的信息不得被随意的发布,应当修复的具体情况进行公示。应当健全信用修复的配套措施,对于信用修复的证据审查和监督、适用条件以及后续的登记公示等程序也不可忽视。建立协同联动,网络信息全覆盖的信用修复机制,解决信用修复难的老大难问题。建设规范、完备的信用修复制度,形成协调有序,安全稳定的信用修复体系。
参考文献
[1]郭秉贵.失信联合惩戒的正当性及其立法限度[J].征信,2020,38(2):58-63.
[2]李林芳,徐亚文.社会信用体系法治化原理探析[J].学习与实践,2019,(11):29-35.
[3]周海源.失信联合惩戒的泛道德化倾向及其矫正——以法教义学为视角的分析[J].行政法学研究,2020,(03):69-81.
[4]沈毅龙.论失信的行政联合惩戒及其法律控制[J].法学家,2019,(4):120-131+195.
[5]王学辉,邓稀文.“执行难”背后的信用激励机制:从制度到文化[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7(1):71-80.
[6]杨福忠.诚信价值观法律化视野下社会信用立法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57-67.
[7]史玉琼.关于建立失信惩戒机制的研究[J].征信,2019,(9):22-23.
基金项目:2020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失信惩戒的立法限度问题研究”(SJCX20_0902)。
作者简介:蔡双双(1995-),女,汉族,江苏宿迁人,法律硕士,江苏师范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