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论德性即知识
田书峰
[中山大学, 广州 510275]
一、德性的理智主义:德性即知识

苏格拉底并没有将德性即知识的命题视为一种复杂的形而上学的教条来进行阐释,也没有将其当作某种逻辑上的推理来进行论证,相反,他将德性即知识的命题深深地植根于自己的生活经验本身,植根于现实的伦理实践中。所有的正义的、节制的、勇敢的、虔敬的行动最后都可以还原到行动者的伦理知识那里,伦理知识是行动的正确性的保证。但是,当我们问到德性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时,苏格拉底的回答只能是善(the good),那些有德性的人,即勇敢的、节制的、正义的、虔敬的人知道何者是善的和正义的。有关于善的知识使一个人成为有德性的,但是,善在这里也仍然只是被理解为在实践中的行动目的,这仍然是形式上的、普遍的界定,并不能解释有关正义、勇敢等德性的知识究竟是什么。很多现代学者们都看到了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即知识的命题流于形式、过于普遍的问题,比如Zeller就非常犀利地指出,苏格拉底对德性的定义只是普遍的形式意义上的界定,从这样的普遍规定或原则中并不能产生出任何具体而确切的伦理行动。所以,为了能够解释伦理行动,苏格拉底需要另外一种能够引起行动的动机性的因素,那就是有益或有用(Nutzen)。如果某个东西或某个行动对我是有用的或有益的,那么,这就是善的或美的。Zeller认可色诺芬的主张,苏格拉底的伦理学最后是建立在有用性(Nützlichkeit)的动机上。(3)Xenophon,Mem.IV,6,8f..色诺芬在自己的《回忆苏格拉底》中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苏格拉底伦理学最终是落于有用的原则上。比如,他认为,我们应该努力获得节制,因为节制的人比不节制的人活得更快乐;我们应该勇敢,因为勇敢的人更容易抵御危险,为自己赢得荣誉;我们应该保持谦卑,因为傲慢会带来损失和耻辱;我们应该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保持和谐,因为兄弟姐妹对我们是有用的,如若使他们蒙羞,那是愚蠢的;我们应该多交好友,因为一个忠实的朋友是最有用的财富;我们应该不要逃避参与公共事务,因为全体公民的幸福对我们每个个体都是有好处的;我们应该服从法律,因为这对我们和城邦都是有用的;我们应该过有德性的生活,因为德性不论是从神还是从人的方面来说都带来很大的好处。(4)Xenophon,Mem.III 9,4; 12,11; 1,18ff.; I,7; II,3,19; II,4,5f.; II 4,5f.; III 7,9.如果色诺芬的记载是可信的,那么,我们确实可以认为苏格拉底伦理学有不解的悖论之嫌,因为,他一方面认为德性是生活的最后目的,但同时,又通过德性带给我们的好处或有用性来进行辩护,呼吁我们走向德性。但是,Zeller则认为,苏格拉底德性伦理学并不会真的陷入这种矛盾中,因为苏格拉底愿意将伦理生活建基于知识之上,尽管这种知识概念只是形式上的界定,缺乏质料上的确定性,但是,这并不是对伦理内容的缺乏,而是对科学性的系统性的反思的缺乏而已。(5)Zeller,E.,Philosophie der Griechen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zweiter Teil,erste Abteilung.Leipzig 1875.S.130-135.
二、虔敬作为知识(Euthyphro)

苏格拉底一方面忠实于自己的哲学方法,即建基于理性之上的被称为苏格拉底式的“反驳法”,但是,另一方面,他从未质疑过神明的存在,而且对人与神之间的界限和差异了然于心,神在能力和智慧方面都远非人所能相比的。他最终被冠以渎神或不敬神的罪名而被判死刑的事实(Apo.18a-19d)说明,他并没有放弃自己通过哲学的反思和检验而获得的一些有关神和宗教的新的理解。相反,他的言辞和思想表明,他从未觉得自己的宗教热忱与他的哲学方法和理性的诘问之间存在着什么格格不入的矛盾,相反,他坚信自己的哲学使命就在于批判雅典当时的宗教传统,这无疑对当时的宗教权威来说是一种挑战和威胁,他希望自己用哲学批判的方法所获得的新见解和新观点能重新塑造他所处时代的宗教观,建立一种新的哲学。Zeller所言甚为恰当,苏格拉底并没有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神学理论,相反,他之所以谈到神学和宗教乃是基于他对伦理问题的探究或对德性的认识的内在需要。(6)Zeller,Philosophie der Griechen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S.143ff.我认为,要理解苏格拉底在自己的宗教热忱和哲学使命之间的关系,一个最好的选择就是Euphyphro。虽然,这篇对话最终还是未能达到令双方都满意的对敬神的定义,但是,我们通过分析苏格拉底对敬神的不同定义的反驳也能够知晓他所寻求的敬神应该是什么样的,即必然地是某种有关人对于神的义务或责任的知识、关于人与神之间的界限的知识。
苏格拉底所寻求的敬神定义是普遍的、使所有的虔敬行动成为虔敬的形式或原因(6d-e),而不是列举出何种行动是虔敬的。
因此,“虔敬是对所有作恶的人进行控告(5d-6e)”并不是虔敬的真正定义。第二个定义:虔敬是取悦于神的东西,也被反驳(7a-9d),因为Euthyphro所信仰的神明对何谓虔敬的行动并没有统一的看法,苏格拉底所寻求的是一个普遍的、适用于所有的神明、人类的道德统一标准,而非一种双重的道德标准(参:Rep.I 378b)。第三个定义:虔敬是取悦于所有神明的东西(9e-11b),也被苏格拉底加以反驳(10e-11b),因为他认为,Euthyphro只是说出了有关虔敬的一个特性,并没有抓住虔敬的本质。苏格拉底相信,一个行动是虔敬的,并不是因为它悦乐于神,而是,这个行动之所以悦乐于神,是因为它本身是虔敬的。苏格拉底的神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有智慧的、喜爱德性的行动。第四个定义:虔敬是关于人对于神的义务的正义部分,帮助神明在首要的任务中完成最美的作品(12e-14a),但是,Euthyphro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也不知道神究竟需要我们什么帮助。于是,苏格拉底引领Euthyphro尝试给出第五个定义:虔敬就是关于献祭和祈祷的知识(14b-15c)。从苏格拉底对第五个定义的反驳我们可以看出,他拒绝虔敬在于寄望于物质的回报或赏报为目的的传统祈祷和献祭(14c-15c)。(7)关于希腊人的传统宗教观,请参:McPherran,M.L.,The Religion of Socrates,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Mikalson,J.D.,Honor Thy Gods.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Mikalson,J.D.,Ancient Greek Religion.Oxford: Blackwell 2005 and Greek Popular Religion in Greek Philosoph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古希腊人在处理那些关于人与神之间的事务时所要参照的法则并不是内心的信念,而是先祖的传统。(8)Mikalson,Ancient Greek Religion,pp.6-9.毋庸置疑的是,荷马和赫西奥德(Hesiod)的史诗对诸神的描述为希腊人建立了一种关于神明的世界的标准的故事目录,那些悲剧、哀歌和抒情的诗人们从这个标准的故事目录中源源不断地汲取创作素材,并同时赋予传统的神话一种新的功能和意义。(9)Zaidman,L.B.and Pantel,P.S., Religion in the Ancient Greek City.Trans.Paul Cartledg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p.144.但是,无论如何,建立在荷马和赫西奥德的传统之上的宗教观与一神论的宗教观大相径庭,这些神明并非世界的创造者,毋宁说他们本身是受造的,他们在荷马和赫西奥德的笔下往往是通过奸诈和暴力而获得权力,既非全知,亦非全能,但是,他们往往与凡人的生死纠缠不清,卷进人间的事务中,有时为了好的和坏的目的而带给人饥荒、瘟疫和战争。这完全是一种人神同形论(anthropomorphism)的宗教观。而且当时的宗教献祭不只是为了联合,苏格拉底对这种传统的神人同形论和以物质的回报为动机的献祭和祈祷表示不齿,他认为,唯一的善就是德性和幸福,以物质的回报为目的的祈祷和献祭非但不可以促进一个人的幸福和德性,反而会因为错误的滥用而减损一个人的幸福。相反,为了哲学活动或追求真理而投入的时间和其他的善也胜过任何焚烧的献祭(Apo.23b-c,31b-c,37e-38a; Mem.4.3.17-18)。事实上,修昔底德和欧里庇得斯对这种宗教观也表达了不满,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就已经将希腊人的献祭和祈祷视为自己批判的核心。
苏格拉底虽然认为他们对虔敬的定义的探究进展得并不顺利,但是,有一件事他从未怀疑的是,虔敬的本质是某种道德知识,一种关于神的本性和人对于神的义务的知识。在苏格拉底看来,我们人无法达至神所拥有的智慧和知识,也无法对神的事业或杰作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理解,因为神明有完全的智慧、是绝对的善(Apo.23a-b,Hip.Maj.289b),就像一个好人行事正直,那么,神明也是这样,只知行善,不识罪恶(Crito 49c,Rep.I 335a-d,379a-391e)。苏格拉底对神的这种道德性理解与当时的雅典人或希腊人的传统宗教观大相径庭,因为根据自荷马以降的传统宗教观,正义在于回报,以恶报恶,以善报善(lex talionis)。(10)参见:Aeschylus, Cho.306-14,Ag.1560-6; Aristotle,EN 1132b21-1133a6; Hesiod,fr.174; Pindar,Pyth.2.83-5; Plato,Meno71e.甚至,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正义观也充斥在神明的世界里(Il.4.31-69)。但是,苏格拉底则希望通过永不以恶报恶的道德信念来打破这种旧有的宗教观,不只是我们不应该行不义之事,而且也不能以恶还恶(Crito 48b-49d,54c; Grg.468e-474b,Rep.I 335a-d)。如果对于苏格拉底来说,那唯一的善就是德性或智慧(Apo.30a-b,Crito 47e-48b,Grg.512a-b,Euthyd.281d-e),那么,很显然的是,神手中最重要的事业就是德性和智慧,而我们对神的服务就是帮助神在这个世间建立德性或立功立德。苏格拉底对自己和别人的诘问或检验就是在于达成这个目的,提升他们的道德信念的一致性,关心灵魂,转向德性,如此,哲学活动也就是一种十分卓越的敬神或虔敬的活动。所以,苏格拉底可能认为,一种严肃而认真的哲学生活,一种审慎的自我省思才是真正的虔敬的敬神活动,当然,那些并非为了获得物质上的回报或自私的意图为目的的献祭和祈祷并不是毫无价值的,如果它们是以感谢和荣耀神明,或者祈求伦理帮助为目的,就是有价值的,因为人们这样通过祈祷和献祭可以提醒自己应当遵循正义之途,并意识到自己的界限,即人的智慧和能力并不能与神的智慧和能力一比高低,人终究还是人,终究是可死的造物。
苏格拉底通过对虔敬的崭新理解、通过对传统的宗教观的批判而打断了这种以恶报恶的恶性循环,重新对人与神的关系进行定位,这表明,虔敬是一种关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道德知识,是一种关于真正意义上的献祭和祈祷的知识。这是基于苏格拉底内心中从未动摇过的两个基本信念而来:对神和人来说,唯一的真正的善就是德性和智慧,神有真正的德性、智慧,他是善的。正是基于这种对虔敬的知识本质的理解,苏格拉底才敢于对传统的政治和宗教权威发起挑战,因为他相信,他所做的事是神命令他去做的,并且,他坚信神会帮助他完成这项事功(Crito 28e4-29a2),他曾说自己听到过某种声音(Apo.31d)。所以,他之所以能够坚持,是因为他相信,神会帮助那些立功立德之事的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色诺芬就认为苏格拉底接受了神的帮助,因为他对于雅典人所做的就是出于对神的虔敬。(11)Xenophon,Mem.1.1.9,1.1.19,1.3.3,1.4.15-19,4.3.16-17,4.8.11;Symp.47-49.
三、节制作为知识(Charmides)
这篇对话主要讨论节制的定义,Charmides先后给出了三个定义,即节制是某种宁静或稳重、是知耻或自谦、是做自己分内之事或自我约束,苏格拉底一一进行了反驳。Kritias随后也对节制的定义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节制就是做好的行动、就是认识自己。最后苏格拉底和他们达成一个双方都赞同的结果:节制是关于知识和无知以及其他诸种知识的知识(166c)。苏格拉底紧接着马上对这种以自我为对象的知识的可能性和有用性进行了验证,他以感觉活动、即听觉和视觉、欲望、意愿、爱、恐惧和意见等不同类型的活动为例子证明,在这些活动中没有一个活动是以自己和其相反的东西为对象的,比如,他发现并不存在一种不以颜色为对象,而是以自身和其他的视觉能力以及无视觉能力为对象的视觉。尽管如此,苏格拉底并没有否认存在着这种以自身为对象的纯粹形式上的知识,但是,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证明这种知识的存在。如果节制就是一种形式上的自我知识或以知识和无知为对象的知识,那么,它就很难具有什么样的具体用处,因为节制作为这样的知识并不存在于一个人所具体地知道或不知道的知识中(what one knows and not knows),而只是存在于一个人知道还是不知道中(that one knows and not knows)。因此,这样的自我知识显得好似是虚空无物的,医好病人的是有医术的医生,不是以知识和无知为对象的自我知识。因此,这种形式上的自我知识对我们的幸福好似也不能产生什么样的贡献。但是,我认为苏格拉底的用意并不是在于反驳节制的本质定义是知识,而是通过这种反驳法逐步地将节制的真正含义揭示出来,节制作为“知识的知识”便是节制的知识本质的最好表达。

我认为,Kosman从自我意识的视角来阐释节制作为“知识的知识”符合苏格拉底所说的节制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的特性,因为这种知识不像其他技艺性的知识那样,以不同的外在对象为对象,这些技艺性知识的目的就是选择那些能够达到其创制目的的工具或手段,但是,节制并不只是在于知道在一些可能性中选择那些能够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而更是在于知道或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做的事,有自我意识地去行动和生活,并且能够说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或原因。尽管苏格拉底并不完全赞同这种定义,并对这种知识的可能性和有用性提出了质疑,但是如果我们把Charmides和Critias对于节制的定义所给出的所有表述放在一起来看的话,会发现,节制作为一种自我理解或知识是所有这些定义中最苏格拉底式的,完全符合苏格拉底在其他对话中关于自己有知和无知的形象,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苏格拉底对自己的有知和无知都了然于心,知道自己事实上知道的东西,对自己事实上不知道的东西就认为自己不知道,而且也能指出别人的无知和有知。
Critias提出最后的有关节制的定义:节制是关于善恶的知识,但是,这个定义并不只是适用于节制德性,而更可以被视为对普遍的德性的定义。尽管学者们对Charmides的对话主旨争论不已,有的学者认为,Charmides根本不是要探究节制的定义,而是旨在借助当时在民间流行的对节制的理解而进一步地探究或阐释知识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德性的本质。所以,节制的形式原则是知识,而不是稳重、知耻等人表现出来的行动,这种知识不是技艺性的专业知识,而是以人的善和善本身为对象的知识。最后苏格拉底和其对话者发现,节制作为关于善恶的知识也是一般意义上的德性定义,如此,节制的本质定义虽然没有被发现,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节制与其他所有德性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都是关于人的善恶的知识。
四、勇敢作为知识(Laches)
在Laches中,勇敢本质是苏格拉底和其对话者们所要寻求的。直到对话的中间部分,他们才真正开始围绕勇敢的定义来展开讨论。对话的前半部分的目的主要是揭开此次对话的序幕和提出此次对话的场景。雅典的两位长者:Lysimachus和Melesias对他们的儿子的教育问题备感焦虑。他们两位都是名门望族之后,前者是Thucydides的儿子,后者是Aristides的儿子,他们的父亲平时都忙于城邦的事务,或征战沙场,或为民辛劳、鞠躬尽瘁,但是,却对自己的孩子们的教育则并没有那么上心和投入,因此,他们在自己的父亲面前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像他们的父辈们那样出类拔萃、光宗耀祖,不要做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急于找到专家,帮助自己教育孩子。有人建议他们让自己的孩子学习一种新的军事训练,那就是佩戴盔甲作战(fight in armor)。他们邀请了两位当时有名的将军Nicias和Laches来给自己的儿子们传道授业、指点迷津。但是,苏格拉底在其中更关心的问题是勇敢的本质。在对话的后半部分,苏格拉底对Laches与Nicias所给出的关于勇敢的定义进行了检验。我们可以把Laches对话进行如下区分:
I.关于教育的问题 (178A-189C)
A.搏斗在教育中的价值(178A-184D)
1.请求对搏斗给出建议(178A-181D)
2.关于搏斗的矛盾性建议(181E-184D)
B.关于灵魂的教育(184E-189C)
1.建议应该来自一个在灵魂的照顾方面有知识和经验的人(184E-187B)
2.苏格拉底习惯于检验灵魂(187C-189C)
II.勇敢的定义 (189D-201 C)
A.苏格拉底检验Laches (189D-194B)
1.勇敢是坚守自己的阵地,不逃跑(189D-192A),
2.勇敢是“明智的忍耐”(192B-194B)
B.苏格拉底和Laches检验Nicias (194C-201C)
1.勇敢是关于何者应当是可怕的和何者不是可怕的知识(194C-197D)。
2.苏格拉底检验Nicias的定义(197E-201C)。
首先,Laches所给出关于勇敢的三个定义都被苏格拉底否决了:勇敢是坚守自己的阵地,与敌人搏斗(190e),但有时逃逸也是勇敢之举,因为逃逸是一种对策;勇敢是一种坚定坚韧(192b),但愚蠢的坚韧并不是勇敢,因为不是任何一种坚韧都是勇敢,哪怕带有明智的坚韧,比如一个人花钱大手大脚,因为他相信通过花钱,他可以赢得更多的金钱;或一个患有热症的人需要吃喝,但是他坚持不吃也不喝,这就不是坚韧;所以,勇敢是一种伴随着知识的或明智的坚韧(192d),但有时看起来好像那些没有专业知识的人比那些有知识的人在面对危险时或完成一个高贵的目的时表现地更为勇敢。苏格拉底的质疑使Laches陷入一种他貌似接受有关勇敢的互相矛盾的定义的境地,这显示出,Laches实际上对勇敢的本质是一无所知的。这个让人觉得无可奈何的一个两难问题就是:一方面Laches承认明智的或伴随着知识的坚韧是真正的勇敢,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接受不太明智的人或没有专业知识的人要比更明智的或有专业知识的人更加勇敢(193c9-e5),这样的话,愚蠢的坚韧看起来才是勇敢,但这明显不符合Laches对勇敢的定义。Santas试图通过区分出对事实的知识和对价值的知识来解决这个矛盾:(15)The cases that Socrates described for Laches contain information only on the first sort of knowledge,the agent’s estimate of what the situation is and what are his chances of success; we are told nothing about how the agents conceived the values of that for the sake of which they were enduring and the values of the alternatives to enduring.But clearly information on these points will make a difference to our judgment whether the agent’s endurance is wise or foolish.If,say,the man with the lesser or no advantage conceives what he is fighting for (say,the defense of his city) as high enough in value and /or the alternatives to enduring as low enough (say,the enslavement of his city and family),his endurance in fighting on may be anything but foolish.Santas,G.,“Socrates at Work on Virtue and Knowledge in Plato’s Lach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rates: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d.Gregory Vlastos,New York,p.193.
如果我们赞同Santas对知识所做的区分,那么,这种矛盾就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矛盾,因为,这里所涉及的知识只是有关事实或处境的,并非涉及对于这个事实或所处情境的价值判断。所以,不明智的坚韧只能是一种愚蠢或鲁莽,而非勇敢。就像Vlastos所说的,苏格拉底在这里所说的明智或知识实际上是指伦理知识,而非技艺性或技术性的专业知识(文本中提到跳水、经商、医术、军事、骑术、射箭和游泳的例子),这些事物和知识并不能被视为是“关于重要或重大的事物的知识”,苏格拉底所说的明智和知识只是关乎人的伦理的善和应该如何生活才能获得幸福,因为我们并不能通过对生活中的各种技能或技艺的掌握来把握到勇敢的本质,这些技艺并不能保证我们可以做得好,即获得幸福。(16)Vlastos,G.,Socratic Stud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pp.112-115.
接下来,苏格拉底与Nicias就勇敢的定义的讨论对我们理解勇敢的知识本质最为重要。Nicias给出了新的定义:勇敢是对何者应当惧怕和不当惧怕的知识,不管是在战争中或是在任何其他处境中。现在,我们将苏格拉底对他的这种定义的论述或反驳简列于下:
(1) 勇敢是德性中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其他“部分”是节制、正义等德性(198a,cf.190c-d)

(3.1)“可怕的事物”是那些带来恐惧的事物,“给人希望的东西”是那些并不带来什么恐惧的事物(198b5-7)。
(3.2)害怕或恐惧就是“对未至之恶的想到或预见”(198b8-9)。
(3.3)因此,可怕的东西就是未来之恶(198c2-3)
(4)因此,勇敢是对于未来的未至之恶和未至之善的知识(198c6-8)
(5)一种知识与其认识对象是相互对应的,什么样的知识就理解什么样的对象,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比如医术、军事和农业的知识各有其对象(198c9-199a9,尤其199a6-9)。
(6)勇敢不只是对未来的恶和善的知识,也是对现在和过去的任何阶段的善和恶的知识(199a10-c2)。
(7)勇敢是关于在各个阶段的所有善和恶的事物的知识(199c6-d2)
(8)一个有这种知识的人或知道所有的善以及其在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时段中的产品的人不会在德性方面有所缺乏(199d4-7),这样的人不仅是勇敢的,也是正义的、节制和虔敬的(199d4-e1)。
(9)如此,Nicias所描述的勇敢不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所有的德性、德性之整体(199e3-5)
(10)但是,这与(1)所说的勇敢是德性的一“部分”相互矛盾。
(11)结论:“我们未能发现勇敢究竟是什么”( 199e11)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接受(9)和(10),那么,我们就会发现(1)是错误的,即如果勇敢是整体德性的“一部分”,那么,勇敢就不能等同于整个德性,因为德性还包含着其他的德性部分;但是,如果勇敢的定义被证明为是整个德性的定义,那么,勇敢就不是德性的一个部分了。学者们争论更多的问题是,苏格拉底是否接受上述的结论。Santas,Penner和Taylor都支持这种阐释,认为苏格拉底和Nicias都接受(1)是错误的,(17)Santas,G.X.,“Socrates at Work on Virtue and Knowledge in Plato’s Lach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rates: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d.Gregory Vlastos,New York 1971,pp.202-203.Penner,T.,“The Unity of Virtue,” Philosophical Review 82: 60-62.Taylor,C.C.W.,Plato:Protagoras,translated with notes,Oxford 1976.p.107.Irwin,T.,Plato’s Moral Theory: The Early and Middle Dialogues,Oxford 1977.p.302,n.62.但是,Vlastos坚持认为,这种两难的处境使他们苦心孤诣地一路探究下来的努力并没有付之东流,功亏一篑,因为苏格拉底并没有否认一开始就被提出来的有关勇敢是德性的一“部分”的观点(190c8-d8),并认为Laches应写于Protagoras之后,因为在Laches中,苏格拉底清晰地意识到,如果勇敢被定义为“对那些可怕的和给人希望的东西的知识”,那么,这里所说的知识就是指伦理知识,与技艺的专业知识正好相对,而苏格拉底在Protagoras中并没有这种清晰的知识之区分。(18)Vlastos,G., Socratic Studies,Cambridge 1994.pp.121-126.Vlastos认为,实际上苏格拉底并没有拒绝Nicias对勇敢的定义:对可怕的和不可怕的东西的知识。(19)Vlastos,G.,Platonic Studi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pp.266-269.这三个理由是:(1)Nicias认为他所提出的定义是来自于苏格拉底的教导;(2)苏格拉底在Protagoras的论证中同样提出了这个定义360d;(3)柏拉图在Rep.429c-430b仍然保持了这个定义。 Nicias在194c8-9中明认不讳地说这个定义就是苏格拉底的立场。哪怕我们承认苏格拉底事实上接受了Nicias所做出的关于勇敢的定义,这也不会造成与前面所说的勇敢是德性的一个“部分”的命题相冲突,因为Vlastos的判断在这里是十分适宜的,即尽管苏格拉底最终意识到勇敢的这个定义并不能完全把握到勇敢的本质,但是仍然可以被视为是关于勇敢德性的必需的和充足的条件(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20)Vlastos,Socratic Studies,p.125.
我们在Charmides中同样发现节制最后也被定义为是关于善与恶的知识,这确实会引起我们在Protagoras中所遇到的“德性的一体性”问题。如果节制和勇敢都可以被界定为关于所有的善的和恶的东西的知识,那么,我们可以说所有每个具体的德性也就是一回事了,一个勇敢的人必然同时也就是一个正义的、节制的和敬神的人。我们会在后面详细地探究德性的一体性问题,我们在这里关心的问题也不是勇敢的定义与其他有关德性的命题之间如何协调,而更关注勇敢的知识本质,即勇敢必然地与伦理知识密不可分,不管我们将其称为“关于可怕的和给人希望的东西的知识”或“关于所有的善和恶的知识”,勇敢总是与某种伦理知识相关,并不同于技艺性的专业知识,因为只有前者与人如何达至幸福、即做得好和活得好的问题相关,而技艺的专业知识的活动并不保证人们的幸福,也不会告诉人们应当如何生活的伦理问题,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些知识对于人的伦理生活没有什么价值,它们仍然有一种工具价值,它们的运用可以保证对于人的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外在善或条件。勇敢所涉及的伦理知识所要晓谕我们的是,伦理学是不同于一种技艺的专业知识的独立学问,就像苏格拉底经常所说的,伦理的知识在其自身就是善的,因为它保证人对于各种其他的善的正确使用,而只有对这些善的正确使用才对我们有益,否则反而对我们有害(Euthyd.281e),因为只有这种伦理知识或道德洞见才会帮助人始终将人的一生的好生活作为自己的伦理行动的目的,而不是犯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
五、德性即知识(Protagoras)
在这篇对话中,苏格拉底并没有直接就“德性即知识”的命题进行论证和说明,这个问题的出现是他和Protagoras之间的对话的必然结果,“德性即知识”一开始就与德性是否可教和德性是否是一体的联系在一起,Protagoras将德性理解为某种特殊的可以传授于人的技艺性的知识,这使得苏格拉底一定要进一步弄清楚德性的本质,即如果德性是知识,那么,我们就能断定德性是否可教的问题。
德性是否可教在西方哲学史尤其是西方伦理学思想的发展史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不可取代的地位,这一点从以下几点就能得到证明。柏拉图在中期和晚期对话中的伦理学思想之发展就得益于他对早期对话中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的接纳(Rep.435e ff.; Philebus 20c ff.);另外,斯多亚伦理学在对德性的理解上直接越过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克伦理学》中发展出来的德性或伦理观,而是直接回归到苏格拉底伦理学,比如,将德性等同于关于善的智慧或知识,德性是达到好的生活的必然的、充足的条件等,在对德性的一体性、对理性作为统治的部分等方面也与苏格拉底相同。(21)Plato,Protagoras.translated,with notes,by Stanley Lombardo & Karen Bell,introduced by Michael Fred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See: Introduction,pp.1-3.而John Stuart Mill就干脆直接追认Protagoras为自己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发端,而Protagoras本人就是功利主义的先驱人物。但是,学者们对什么是Protagoras的核心主题争论不已,莫衷一是,有不同的意见,比如, Adam认为Protagoras最关注的问题是方法论问题,而Jaeger和Friedlaender则认为这篇对话的最终目的则是教育,(22)Plato,Protagoras.Translated,with notes,by Stanley Lombardo & Karen Bell,introduction,pp.3-10.Taylor 认为是伦理的问题,而Kirk认为是认识论。但是,不管这些学者们的意见有多么不同,但是,他们都承认一个基本看法,Protagoras是苏格拉底对当时的智者或智术师们的攻击或反驳,这是来自于大家一贯的对智者们的敌对态度。Michael Gagarin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他认为,Protagoras与苏格拉底都关心对人和城邦来说都十分重要的两样东西:教育与德性。(23)Gagarin,M.,“The Purpose of the Protagoras”,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Vol.100 (1969),pp.133-164.尽管,苏格拉底在对德性的本质和可教性的问题上走得更远和更深入,但是,我们并不能认为,苏格拉底对Protagoras所提出来的积极的有关德性和教育的观点完全持否定的态度。我认为,无论将Protagoras这篇对话的最终旨趣视为是苏格拉底对智术师的具有敌意的反驳,抑或是怀有好意的共同探究,我们都必须承认,这篇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德性的本质和可教性,苏格拉底对德性即知识的真知灼见在与Protagoras的对话中才慢慢显示出来,而且二者在关于德性的讨论方面有很多相一致的观点。苏格拉底对德性即知识的命题的阐述并不是在对话的一开始提出来的,而是在最后的论证中(348c5-360e5)才提出德性即知识的观点。苏格拉底在之前与Protagoras的对话中已经做了足够的铺垫,而在最后一部分中则直接就德性的知识本质进行论述。
这篇对话的结构是这样的:(1)引言:309a1- 314c2;(2)普罗泰戈拉的长篇讲辞:314c3-328d2;(3)苏格拉底的第一个论证:328d3-334c6;(4)关于方法论的插曲:334c7-338e5;(5)塞蒙尼德的诗歌阐释:338e6-348c4;(6)苏格拉底的最后论证:348c5-360e5;(7)结论:360e6-362a4。首先,Protagoras认为自己所教授于人的不是什么特殊的技能或技艺,而是政治技艺,就是使青年学徒无论在自己的个人事务还是在城邦的公众事务中都能出类拔萃(318e),一言以蔽之,他使人成为好的公民(318)。但是,苏格拉底认为德性不可教,因为那些有智慧的雅典人在各个不同的技艺领域中都会去请教专家,而在公众的事务上,他们会听取任何人的意见,并且最有智慧的和德性的雅典人也没有能把自己的德性传授给下一代(312b-320b)。为了回应苏格拉底,Protagoras发表了自己的长篇讲辞,目的就是为了德性是可教的进行辩护。Kerferd认为Protagoras的长篇讲辞对苏格拉底的回答应该是令人满意的,如果它被完全正确地理解的话。 我认为,Kerferd可能忽略了另外一点,即苏格拉底的真正用意是想要使Protagoras在伦理德性与技艺技能之间做出区分,因为技艺可以由专家而传授给另外一个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宜学习同一门技艺,相反,德性并不局限于某个群体或某个阶级,而是人人都可以获得德性。问题是,德性是如何被传授的呢?苏格拉底并没有否定 Protagoras提出的这些观点,只是认为后者缺少一种概念上的明晰性,所以,苏格拉底慢慢将何谓德性的本质的问题视为关键的问题。
苏格拉底已经将自己对德性即知识的看法放置到了自己对Semonides的诗句的阐释中,虽然苏格拉底对Semonides的诗句的阐释有虚而不实的夸大成分,但是,他最大的用意则是要为德性即知识的看法而进行铺垫。在苏格拉底的最后讲辞中,他提出了德性即知识的观点,但是,他也并没告诉大家德性的知识所涉及的对象是什么,它的性质是什么,苏格拉底倒是给了我们一些有关德性的知识的一些特征,比如,智慧是最德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330a2),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后来他承认智慧和知识是人类中最强有力的东西(352d1-3);再比如,好的东西都是有益的(333d9),Euthydemus的一个核心论点就是知识或智慧是在其自身就是有益的,是无条件的善。同样地,苏格拉底在Protogoras中也只是进一步说明了德性即知识,而并没有进一步论证这种知识是何样的知识,是如何得来的,即并不像亚里士多德在《前后分析篇》中所做的那样对知识理论进行系统的分析。在这里,苏格拉底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阐释德性即知识的论点的:(1)苏格拉底借助勇敢即智慧或知识来说明;(2)快乐论证中的测量技艺。
勇敢是知识:为什么苏格拉底以勇敢为例来说明德性是知识呢?因为在前面的对话中,Protagoras认为,智慧、节制、正义和虔敬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唯独勇敢是不同的,因为我们可以在不具有其他德性的条件下而具有勇敢的德性(349d2-8),所以,接下来,苏格拉底证明勇敢就是智慧或知识(349e-350c),苏格拉底这样做的原因并不只是为了反驳Protagoras所说的勇敢与其他的德性不同,他只是想以勇敢为例来说明德性就是知识这个对他来说坚信不疑的一个道德信念(358d-369e)。他对勇敢是知识的证明如下:
(1)所有勇敢的人都是有胆量的,
(2)勇敢是高贵的,因为它是德性的一部分,
(3)有(专业)知识的人是有胆量的(比如有跳水、搏斗知识的人),
(4)某些无知的人也是有胆量的,
(5)无知者的胆量是愚钝的,
(6)所以,勇敢是智慧。
Protagoras在这里似乎意识到苏格拉底有意将勇敢等同于胆量,这是基于他对苏格拉底的提问而表达出来的,承认了(1)之后,苏格拉底便顺着这个思路一直问下去,直到他最后也同意(5),即无知者的胆量是愚钝的,但是,苏格拉底接下来的反问使Protagoras和听众都误以为他将勇敢等同于胆量:
你是怎么来看勇敢的人呢?,我说到,你难道不认为他们是有胆量的人么?(350b7)
Protagoras回复道:
如果你问我勇敢的人是不是有胆量的,我会同意;但是,你并没有问我有胆量的人是不是勇敢的,如果你这样问了我,我就会回答你了,不是所有的。(35067)
O’Brien坚持苏格拉底在这里使用的定冠词就是用来肯定或否定同一性的,但是,大部分学者都会认为苏格拉底在350b7并没有有意将勇敢等同于胆量,这样的话,他就会是一个十足的傻瓜了。(24)Vlastos,G.(ed.),Plato: Protagoras.Indianapolis 1956,xxxii.Taylor列举出柏拉图在早期对话中的三个实例来说明以下这个用法:F是G可被用来谓述G属于F的系列属性中的一个(Lach.195e1; Prot.342b4-5; Grg.491e2)。(25)Plato,Protagoras,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C.C.W.Taylor.Oxford 2002.Introduction:pp.xi-xx.不管怎样,苏格拉底通过这个提问想要表达的并非勇敢与胆量的等同,而只是想要借助这个问题进一步引入到对勇敢与胆量的原因的探究,只要弄清楚了勇敢和有胆量的背后的不同原因,那么,我们也就对勇敢与有胆量之间的相同和差异自见分晓。
命题(2)和(3)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勇敢作为德性的一部分是高贵的,而勇敢的人是有胆量的,那么,勇敢就是一种高贵的或好的有胆量。那么,是什么使某些“有胆量的”是好的、高贵的呢?Protagoras也承认是知识使然,他承认那些有知识的人要比那些缺乏知识的更有胆量(350a6-7)。但是,这是否与命题(4)相矛盾呢?因为(4)认为某些无知者也是有胆量的?这并不矛盾,因为勇敢的人凭借自己的知识要比那些无知的人凭借自己的无知表现得更有胆量,所以,那些有智慧的人的胆量是好的,而那些无知的人的胆量是不好的,甚至是疯狂的(350b5-6),所以,苏格拉底结论说,那些最有智慧或知识的人是最有胆量的,而那些最有胆量的人也就是最勇敢的人,所以,勇敢是知识(350c2-5)。
Protagoras接下来对苏格拉底的勇敢即知识的命题表示不满(350c-351b),他的反驳是这样的:苏格拉底认为知识是一种好的有胆量的(无知也是一种有胆量),勇敢是一种好的有胆量,苏格拉底就基于以上命题推论出勇敢就是知识。如果这样的推理是有效的,那么,苏格拉底也可以做出力量就是知识的推论。于是,Protagoras用力量作为类比来解释勇敢并不能等同于知识。他认为,力量是一种能力,力量的来源是出自于自然和身体的良好营养,而其他的三种能力的来源可以是知识、疯狂和激情。力量是来自于身体的训练,因为有些人的身体天生适宜于这样的训练,比如拳击手,但是,那些因激情和疯狂而表现出来的力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力量。同样地,勇敢也是来自于对学徒的灵魂的一种训练,因为他的灵魂天生适宜于这样的训练。所以,这样的勇敢不同于来自于知识、疯狂和激情的勇敢。按照Protagoras的看法,勇敢来自于好的自然禀赋和对灵魂的训练与照料,就像力量那样。
快乐论证中的测量技艺:苏格拉底接下来回应了Protagoras对勇敢就是知识的反驳,这就是有名的快乐论证(351b-358d)。学者们对苏格拉底的快乐论证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苏格拉底是否真正持有或接纳了这样的快乐主义命题,抑或仅仅是将其当作反驳Protagoras的一个临时策略而已。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各自秉持一方,相持不下。Adam、Hackforth都坚持认为,苏格拉底确实相信快乐是善的说法,(26)Adam,J.,Platonis Protagoras,Cambridge 1893 p.xxxii (‘the episode in question is intended to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historical Socrates’); Hackforth,R.,“Hedonism in Plato’s Protagoras”, Classical Quarterly 22 (1928):39-42.Vlastos也认为这是目前大部分学者所接受的看法。(27)Vlastos,G., Plato’s Protagoras,Jowett’s translation revised by M.Ostwald (N.Y.I956),in introduction,p.xi.但是,第二种观点认为,苏格拉底在这里提出来的快乐论证只是一个专门的策略而已(ad hominem),目的是为了证明德性即知识的命题。(28)Grube,G.M.A.,“The Structural Unity of the Protagoras”,Classical Quarterly:27(1933)203ff..这种反快乐主义的解释应该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的Marsilio Ficino (1433-1499),See: Grote,G.,Plato and the Other Companions of Sokrates,new edition Vol.II,London,1888.p.314,n.1.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所谓的第三立场,比如Goodell就认为,在Protagoras中,我们就根本找不到快乐主义,因为对于苏格拉底或柏拉图来说,那些伦理上是善的东西就必然地对正常的人性来说都是令人愉悦的。(29)Goodell,T.D.,“Platon s Hedonism”,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42 (1921):25ff.如果我们分析文本就会得知,苏格拉底在这里的意图并不是要论证自己是一个快乐主义者,而是要借此证明,哪怕是在一个以快乐为目的的生活中,知识也是多么的重要,但这并不表明他自身就是一个十足的快乐主义者。我在这里认同第二种观点,(30)Gagarin,Sullivan,Zeyl等都认同第二种立场。Sullivan,J.P.,“The Hedonism in Plato’s Protagoras”,Phronesis,vol.6,1961,pp.10-28;Klosko,G.,“Toward a 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tagoras”,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vol.61,1979,pp.125-142.苏格拉底的快乐论证应当被放置到对话的上下语境和对话目的中来看,既然Protagoras坚持勇敢不是知识,而是来自于天生的根底和后天对灵魂的照料,那么,苏格拉底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去证明所有的那些非理性的能力(快乐、激情、痛苦、爱和怕352b7-8)也都会屈服于知识的力量,使这些能力屈服于理性的并不是靠身体的训练,而是靠知识。苏格拉底虽然在这里将快乐等同于善,将痛苦等同于恶,但是,这种等同只是权宜之计,目的则是要去论证德性就是知识。这一段的论证结构如下:
(1) 未加区分的快乐主义:快乐是好的,痛苦是恶的(351b3-c6);
(2) Protagoras的反驳,因为有些快乐是恶的,有些痛苦是好的(351c7-e8)。
(3) 苏格拉底否定不自制的可能性(352al-353b6);
(4) 苏格拉底为区分后的快乐主义进行辩护:有些快乐之所以是不好的是因为它们最终导致痛苦,阻挡我们享受到其他更大或更多的快乐;而有些痛苦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它们最终以快乐为结果,带来更多或更大的快乐,或减轻和避免更大痛苦。如此,人们将快乐视为善来追求,而将痛苦视为恶来逃避(353cl-354e2)。
(5) 反驳不自制(354e3-355e)。
(6) 选择痛苦和快乐的知识是测量技艺,人选择恶是因为无知(355a-358d)。
苏格拉底在这里使用快乐主义的论证的目的是为了反驳不自制,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证明知识的力量(352c8-d3),知识对德性来说是足够的或者德性就是知识。(31)Cf.Irwin,T.,Plato’s Moral Theory: The Early and Middle Dialogues.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p.83.我们可以将苏格拉底在这里所说的快乐主义称之为认知意义上的快乐主义(epistemological hedonism),有些快乐之所以是不好的是因为它们最终导致痛苦,阻挡我们享受到其他更大或更多的快乐;而有些痛苦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它们最终以快乐为结果,带来更多或更大的快乐,或减轻和避免更大痛苦。如此,人们将快乐视为善来追求,而将痛苦视为恶来逃避(353cl-354e2)。所以,这种知识就在于能够认识到那在整体上更大或更多的快乐。如果大众接受这种认知意义上的快乐主义,那么,不自制的说法就会在自身内包含某种荒谬的结论:如果不自制是因为被快乐所战胜而不能选择自己认为是更好的行动,又如果“快乐”和“痛苦”与“善”和“恶”可以互换,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荒谬的结论,不自制者是因为被某种善所战胜。Irwin这样来表达不自制者内心所具有的这种自相矛盾的信念:
A chooses y over x,knowing that x is better than y overall,because A believes that y is better than x overall.(32)Irwin,Plato’s Moral Theory,p.84.
苏格拉底认为,不自制之所以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大众对不自制的原因解释——“被快乐所战胜”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的错误归咎于快乐,而应归咎于认识或认知上的错误,是因为缺乏正确的知识(357c-d)。如果我们的生活的拯救之道就在于对痛苦和快乐的正确选择,即选择更大或更多的快乐与更小或更少的痛苦,那么,这种正确的选择就需要知识,即衡量或量度技艺。因为事物从近处看,就会显得更大,如果从远处看,就会显得更小,如此,这些表象具有某种魔力似的,使我们感到困惑,使我们对同一事物经常改变我们的想法,对那些显得可大可小的事物的选择而感到后悔不已,但是,这种衡量的技艺可以指出真理之所在,(33)苏格拉底所说的针对表象的衡量技艺似乎含沙射影地指向Protagoras在Thaetetus中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homo-mensura)”,事物就是它向每人所显现的样子。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断定说,苏格拉底完全否定了Protagoras的观点,他在这里想要表明的是一种与Protagoras所教授的“政治技艺”不同的一种“测量技艺”,前者更相信后天的训练和先天的禀赋,而后者更相信理性和知识的力量。德性归根究底只是知识,而其他的非认知意义上的因素并不是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使表象失去魔力,带给我们心灵的平静,拯救我们的生活(356d-e)。由此可见,不自制者的错误在于选择了更少的善,而牺牲了更多的善(355e2-3),原因就在于表象的显现之魔力,眼前的短暂快乐和痛苦会显得更大或更好,因此,有人就会在快乐和痛苦方面做出错误的判断,选择眼前显得较大的快乐,而实际上则是以较小的快乐或痛苦为结果。最后,苏格拉底又回到对勇敢的定义上,勇敢是对于什么是可怕的和不可怕的知识,反之就是无知(359d)。
六、结 论
我们通过对这几篇对话的核心段落的分析对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即知识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Euthyphro中,虔敬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就是一种关于人神关系的道德知识,是一种关于真正意义上的献祭和祈祷的知识,因为对神和人来说,唯一真正的善都是德性和智慧,所以,真正的虔敬就是追求德性和智慧。节制的知识本质在Charmides中也展露无遗,尽管最后苏格拉底对节制的定义并不满意,因为与其说这是对节制的定义,毋宁说是关于所有德性的定义,但是,节制作为一种特殊的“有关知识的知识”所强调的是,有节制的人知道或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做的事,有自我意识地去行动和生活,并且能够说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或原因。在Laches中,勇敢必然地与伦理知识密不可分,不管我们将其称为“关于可怕的和给人希望的东西的知识”或“关于所有的善和恶的知识”。在Protagoras中,苏格拉底通过快乐论证揭示了知识的力量,因为只有智慧或知识(在这里指测量技艺)让我们不受显像的力量之迷惑。
当然,苏格拉底的德性即知识的命题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其实这种批评并不是从现代学者们才开始的,而是早在古代就已经开始了,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发现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即知识所包含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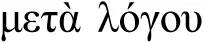

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批评不无道理,但是,他站在自己对德性的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的区分的前提上对知识或理性与伦理德性的关系重新定位,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完全推翻或否定苏格拉底对伦理学的贡献,而是对苏格拉底的德性观进行某种改进或纠正。正因为这种批判,德性即知识反倒成了刻在苏格拉底伦理学上的最深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