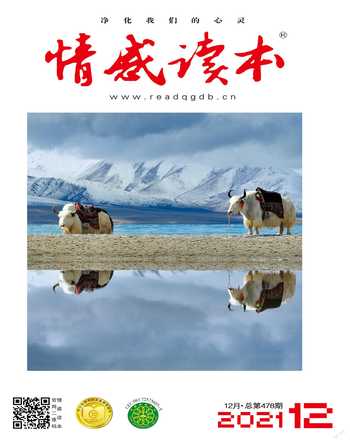与父亲相处的二十天
朱敬宇
一个受了四十年苦的八十岁老人,心态比我还乐观、阳光。写他,只是为了记录下这么个人,这么一个替我们全家受了千重罪,而依然熠熠生辉的一个好人!
爸爸已经七十八岁了,可粗浅了解他,却是近二十天来的事。以前也一起生活过,只不过是旅途中的几天,在他相对健康的时候。爸爸已经截瘫坐轮椅三十八年了,要说健康,是说他除了下肢残疾,没有其他的病症,诸如三高之类。
今天早起,想给爸爸换个口味,其实也是为了自己。天天喝稀饭吃一个味儿的包子,真想换个口味儿,昨晚睡前我就在策划,明早吃个肯德基。一早起来,倒尿洗盆换褥子后,我说爸,我去买早点,就出了门。偌大的铜川只有一家肯德基,就在小河沟口正大超市边上,七八分钟路程。爸一个人在病房,为了节省时间,我一路跑到店里,终于吃上了久违的辣鸡腿汉堡和美式咖啡,心满意足后,给爸爸带了一份不辣的汉堡和豆浆。爸爸没想到早餐变了,可也没说什么,认真用完这份不一样的早餐。也许是天生的好奇心支配着他。到下午了,爸爸看了看尿桶,冷不丁说了一句,敬宇,今天咋尿得这么少?会不会是鸡肉汉堡吸尿哩?咋没尿了?哈哈,这就是我可爱的爸爸,他的奢望简单至极,就是每天能站一会儿,每天不尿床,不拉裤子。
手术过后,爸爸的要求更简单了,敬宇,我能侧身躺半个小时嗎?趴了一天真难受啊。他像小孩一样讨好的笑,让我能记一辈子。二十天来,很累,但特温暖,恍惚之间,又回到了山半坡窑洞里那个温暖的家,电棒(日光灯管)亮着,灯下,我抹了桌上的尘土,写作业,报纸糊的顶篷上,小老鼠打架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
爸爸最高兴的一天,是用纸尿布最少的一天,他连连问我,今天还可以吧,你看今天还可以吧。每个人都有奢望,即使再简单,也需要尊重。
爸爸的奢望就是这样,就是一杯水,如此简单!
小唐叔是爸爸的病友,三十多年前在洛阳治病时结识的,叫唐东洲。他开一辆残疾人代步电瓶车,从铜川最南端的川口,穿过交通拥挤的闹市区,来到医院,直接把电瓶车开到了三层外科病房。车后放着三盒礼品,一盒华县土鸡蛋,一盒核桃花生奶,一盒特仑苏。
爸爸和他都行动不便,已多年不见,没想到他能来,喜出望外,赶紧让倒水。小唐叔把车停在爸床头,问明病情,哈哈一笑,这病没事,伤口外渗黄水太正常了,有一年在洛阳,我的腿上伤口渗黄水,用鸡蛋清用药水擦,咋治也治不好,你知道陈屯一个大夫,姓啥我忘了。爸爸说姓郭。是郭大夫,给我一种面面药,说你就可劲抹,出水就抹,不怕厚,结果过了一阵就结茄了,再过一阵,好了。爸爸说,主要是术后要趴着睡,难受。小唐叔说,这有啥,我趴着睡了二十多年,就是这两年不能趴了,脊椎不行了,老疼,只能侧着睡,趴习惯了,刚开始侧着真睡不着。
小唐叔脸瘦小但有光,剃光头,穿黑色圆领T恤,戴副圆眼镜,可能是因为今天出门会友,光头剃得干净明亮,眼镜也擦得一尘不染,有点像演晚清角色的李连杰。但没说几分钟话,他就痛苦地咬着牙,两只手紧攥着车扶手,埋下头,眼睁睁看着两条皮包骨头的腿在剧烈抽搐,没过十秒,又恢复了正常。爸爸问,还是肌肉神经疼?是,小唐叔说,但现在好多了,不像三十年前,疼得我天天夜里叫,每星期都要打杜冷丁,现在好点儿,一年就打几次,就是有时过不去了,像上螺丝一样,刚上完松了口气,他又接着上一颗,哈哈哈,实在是受不了。可回头说哩,不管咋样,咱已经多活了几十年了,知足!
从爸爸口中知道,小唐叔是一九七八年二十岁时在桃园矿摔伤的,本来伤不重,大便失禁但小便还有知觉,腿也有知觉,他妈和大姐在洛阳白马寺照顾他,后几年又从郊区柳湾北的河间坊山里给他找了个媳妇。都劝他积极康复,但他已心如死灰,就知道和一些消极的病友赌博看电影。有一次他们去洛阳东郊东花坛看电影,电影院的保安嫌他小便流到电影院的水泥地了,他二话没说,轮起三轮车铰把照保安头上猛砸,有人报警把他抓进派出所,他在里面大小便,第二天警察就把他放回来了。后来,媳妇也和他离了婚,回娘家了。
爸爸探问,你妈身体还好?
好着哩,九十六了,我活着她不敢死,不放心!
爸爸又问,小雪在哪儿上班?
在王益区王家河乡政府。
小雪是小唐叔的闺女,大概是1983年生的,是抱来的。当年小唐叔伤后,他大姐担心唐家无后,就托川口矿医院相熟的大夫,给弟弟抱了一个弃婴。大姐抱孩子到洛阳白马寺车站下车的凌晨,陇海线上的这个小车站的房檐下,到处是四下乱飞的蝙蝠,可天上,正飘着洁白的小雪,就给孩子起名叫小雪。多亏了这个闺女,对小唐叔比亲闺女还亲,事事照料精细,从小唐叔的乐观心态和爽朗表情上也能看出来。可善良的大姐却遇上了不幸,有次下班去矿医院看住院的弟弟,出门让车给撞死了。
爸爸又问起小郭叔小赵叔等其他住在休养所病友的情况。小唐叔说,啥都好,就是老鼠防不住。啥,老鼠?父亲问。小唐叔笑着说,那儿的老鼠也聪明,知道住的人是残疾人,没知觉,小郭的几个脚趾头都让老鼠咬掉了,哈哈,也怪他们自己,老不洗脚,不咬他咬谁。
小唐叔就是这样,像二十多岁我刚认识他时一样,元气满满。
这几天夜里,爸爸叫我的次数明显少了。有时早上起来,看我睡眼惺忪,还怯怯地问,我昨晚上没有叫你呀?
我知道,爸爸是心疼我,他虽不说,却默默地在摸索自己顾自己的窍道,比如自己从趴着睡到右侧身睡,从趴着用尿不湿到侧着用自制尿套解小便,研究着如何不用麻烦别人。
我是最怕麻烦别人了,已经下肢没有知觉四十年的爸爸说,啥事都愿意自己干。
过两天我就要走了,离开爸爸去忙其他该忙的事。从刚开始对爸爸偶尔的厌烦,到后来不能回避的无奈,可到了离别的时候,内心却满怀不舍,才越发觉得父亲可爱。回想起来,从当兵那天起,我已经二十八年没有和爸爸朝夕相处这么长时间了。那时青春年少,拼着劲干工作,从没有想过父母会有苍老的一天,更没有想过母亲会只活到五十三岁,那么年轻就永远地走了,二十年过去了,就是现在活着,也才七十三岁。
这两天,爸爸可能也感到离别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脾气特柔和,再没有跟我急一次,批评更是没有,老劝我吃这个吃那个,我让他支几个俯卧撑他就支几个,再不会偷懒说二话。
爸爸说,你放心走吧,都好差不多了,拆线不拆线都无所谓,肯定是好了。
可我还是不放心,因为我知道,我是最合适照顾他的人。我要不在,谁给他处理大便问题呢?谁能把他从床上抱到轮椅上?谁能让他站着锻炼?谁能面对一天尿七八次床的厌烦,有时正在忙着换尿布,他会不知不觉地尿到你的手上?
我是他儿子,我都有厌倦,其他人完全可以理解,又不是他爸爸,礼节到了即可,可礼节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礼节再周到也连大小便问题都解决不了。他趴着睡时间一长会脖子疼,侧着睡时间一长髖骨会压成疮,平着睡正压着伤口,尽管快好了,可一旦尿床,就会污染伤口,引起后患,对他这样的病人,可能会造成致命的伤害。从心底,我说他可以,能行,但是到了跟前,真不想让他再受任何委屈,看其他人脸色。
夜色阑珊,爸爸又打起了舒心的鼾声,对于我,这就是一首最入心的安魂曲,他引领着我,进入美妙的童年时光。
床前侍疾十天有余,终日不离左右,有时悲伤啜泣,有时焦躁懊丧,然而生活也并非暗无天日,随着时间推移,在纷浊当中自有一线澄明。
十一点出发,这是昨天和爸说好的离家时间。
邻居们前前后后来了几个,一个姓张的老太太是弟弟的小学老师,反复地说,和峰峰可像,走路像,说话也像,峰峰像恁妈,你像恁爸。旁边一个邻居说,我不是说哩,恁妈可是个好人,脾气好,能干,事还不多,就是受罪了,没有享上福。你们家的孩子都孝顺,就是离得太远了。多回来,多回来看看恁爸,恁爸可孤单啊。恁每次回来,又一走,恁爸一个人在门楼下坐半天,能难受好几天。闲了可得多回来看看啊。
我应承着说,会经常回来,会经常回来。
爸爸很孤单,我能感觉到。
每次回家要走了,他都要摇着用了快四十年的破旧的老轮椅,轴与轮子发出机械传动的吱呀声,随着我到门口。我看看他,开车门启动,最后摇下车窗,轻轻挥手说走了的那一刻,他端坐在小院的门楼下,一脸平静,偶尔还侧头瞟一眼远处的邻居,不好意思或者想引起他们的注意,告诉他们远方的儿子要回了,回北京去。我转弯走上大路,再回头看看,向他摆摆手,他也就礼节性地挥挥手,还客气地挤出些微笑,好让我放心,可心是颤颤巍巍的,就如端着满满荡荡的一盆水,一不小心就会溅出来,洒落一地。
爸爸是受了罪的人,在这世间,他是被碾压过的受了千重罪的肉身。我说是千重罪,是因为对把自尊看得比命都金贵的他而言,尿湿裤子,被人轻视的训斥,自己翻不了身或者其他力不从心的事,这些敲击他自尊心的事每天都要发生,把他的心生生磨出了老茧。雄鹰瞬间折断了翅膀,可飞天的心却永不会磨灭,即使受着千重罪。他每天大小便后要洗手,一有条件就要洗澡,虽然他常常几个月没有办法洗澡,出门穿衣服,他用心搭配着颜色,在家,每盆花朝那个方向开,他都要调配妥当,错落有致,是个不错的插花师。出去旅游,每到一处景观,他先是顺从大家的心意拍照,观察一会儿,就会选一个自认为最佳的角度说,这儿好这儿好,给我拍一张。
唉,我也不知道怎么写他,我的父亲,写他不是为了宣扬他,宣扬他受的苦和他的强大,他强大吗?我没有觉得,只是比一般人更能忍受、更坚韧、更有爱!一个受了四十年苦的八十岁老人,心态比我还乐观、阳光。写他,只是为了记录下这么个人,这么一个替我们全家受了千重罪,而依然熠熠生辉的一个好人!
丁一摘自《宝安日报》
——以People v. Howard案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