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伦德尔及其学术研究
王安莉
瓦尔特·弗里德伦德尔[Walter Friedländer, 1873—1966]是现代美术史研究领域的一位先驱。他终其一生实践着自己开拓学术的理想,做出了一项又一项的创造性成果。其中,关于16、17世纪艺术的研究尤为突出,特别是他针对手法主义艺术所做的系统性阐释,至今仍然是涉足该领域的研究者们必不可少的指南。在同行眼中,这是一个将学术职责定义为“征服全新领域”1参见Posner, K., et al, “Walter Friedlaender(1873-1966)”, Art Journal, vol.26, no.3,1967, p.258。的人。除了在研究领域做出了诸多贡献之外,他在教学中也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在从德国流亡到美国之后,弗里德伦德尔培养了整整两代美国学者。作为纽约大学美术研究院的荣誉退休教授,他直到九十三岁病逝之前都始终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一 德国时期
1873年3月10日,瓦尔特·弗里德伦德尔在德国格洛高[Glogau](现属波兰)的一个商人家庭出生。2格洛高这座城市自11世纪以来一直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因为长期身处军事要塞而不能充分发展。19世纪时,格洛高决定改变这一身份。1873年(恰好是弗里德伦德尔出生的这一年),城里的防御工事被移到东部,直到1902年才被拆除。二战期间,这座城市被纳粹变作军事要塞,但是,在被苏联红军占领六星期之后,该城市95%遭到了摧毁。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之后,格洛高被划给波兰,德语居民遭到驱逐。直到1967年,这座城市才开始再次重新发展。而这时候,移居美国31年的弗里德伦德尔已经去世一年。年幼失去双亲的他,不得不在路德教会长大,尽管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3父亲西吉斯蒙德·弗里德伦德尔[Sigismund Friedländer]、母亲安娜·约阿希姆斯塔尔(弗里德伦德尔)[Anna Joachimsthal(Friedländer)]。十三岁时,弗里德伦德尔搬到柏林,和姐姐一起生活。在这里,他得到了一个绰号“弗里多林”[Fridolin](他后来的笔名“弗里德里希”[Friedrich]正是由此而来)。之后,弗里德伦德尔进入柏林大学,在阿尔布雷希特·韦伯[Albrecht Weber, 1825—1901]门下学习梵语。他还在瑞士日内瓦跟随现代语言学之父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学习了一个学期的语言学。1898年,年仅二十五岁的弗里德伦德尔获得了柏林大学的梵文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针对《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的部分内容进行翻译和评注,两年后获得出版。在这之后不久,他就借助博士后基金,远赴伦敦大英博物馆进行研究。但是,英国一行使他发展出对艺术史的极大兴趣。伦敦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的宝藏给了他深深的触动,让他立志成为一名艺术史学家。回到柏林之后,弗里德伦德尔便投身到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 1864—1945]门下,开始学习艺术史课程。
弗里德伦德尔以梵文研究开启自己的事业,却在三十岁时毅然转向了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美术史学科。不过,20世纪初的柏林并不承认第二个博士学位。所以,弗里德伦德尔自1904年为报纸杂志撰写艺术评论起,便时常以“瓦尔特·弗里德里希博士”[Dr.Friedrich Walter]的名义进行发表。他真正作为艺术史学家获得认可,要归功于三十九岁时出版的第一本艺术史专著——《庇护四世别墅》[Das Kasino Pius des Vierten](莱比锡,1912年)。这是他在意大利驻留几年之后的成果。在这本建筑主题的著作中,弗里德伦德尔研究了费代里科·巴罗奇[Federico Barocci,约1535—1612]的绘画艺术,尤其是巴罗奇在庇护四世[Pius IV]别墅一楼的第一、第二间房绘制的壁画装饰。梵蒂冈花园中的庇护四世别墅,虽然拥有极其丰富的装饰,但是其中的绘画一直鲜为人知。直到弗里德伦德尔的著作出版,这一局面才有了变化。《庇护四世别墅》首次清晰地展现了画家巴罗奇对于室内设计的贡献。这本开山之作不仅是当时的先锋,在书籍出版之后的六十年里也一直无人超越。直到七十年代,这种状况才算结束——1972年,马尔切洛·法焦洛[Marcello Fagiolo]和玛丽亚·路易莎·马多娜[Maria Luisa Madonna]发表了长篇论文《庇护四世的罗马》[La Roma di Pio IV](见《插图艺术》[Arte Illustrata]杂志);1977年,格拉汉姆·史密斯[Graham Smith]出版了专著《庇护四世别墅》[The Casino of Pius IV](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弗里德伦德尔在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艺术史专著之后,就辗转去了巴黎。经过两年的研究,1914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尼古拉·普桑[Nicolas Poussin]的著作。遗憾的是,这本书在当时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因为,同年出版的奥托·格劳托夫[Otto Grautoff, 1876—1937]的同一主题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他的成就。不过,这一年对于弗里德伦德尔来说,却是人生中极为醒目的一年。他不仅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而且进入了德国布赖斯高地区[Breisgau]的弗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成为这所学校的编外讲师。该校新近成立的艺术史系,是由中世纪研究专家威廉·弗格[Wilhelm Vöge, 1868—1952]领导。他不仅在系里配备了图书馆和照片档案,并且从1908年开始就坚持举办艺术史研讨会。弗格的努力,使他所在的美术史系成为德国最受人看重的科系之一。弗里德伦德尔在此任教了整整二十年,从1914年进校,直到1933年离开。
1914年,弗里德伦德尔进入弗莱堡大学时,用一篇题为〈1520年左右意大利绘画中反古典主义风格的出现〉[Die Entstehung des antiklassischen Stils in der Italienischen Malerei um 1520]的文章作为其就职演讲。该文针对16世纪的手法主义艺术进行了重新评估,这在当时的艺术史领域是一项开先河的研究成果。那时候,就连他的老师沃尔夫林,也仍然把16世纪当作可以忽略的时期。沃尔夫林在一年后出版《美术史的基本原理》[Kunst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1915年,英文版1932年,纽约)时,仍然认为从文艺复兴的古典风格到17世纪的巴洛克风格是一种持续的演进。20世纪20年代前后,欧洲逐渐兴起关于手法主义的研究风潮,弗里德伦德尔堪称其中的先行者。

图1 弗里德伦德尔,《克劳德·洛兰》封面,1921年

图2 弗里德伦德尔,《从大卫到德拉克洛瓦》(1932年)封面,1952年英文版

图3 弗里德伦德尔,1930年
在弗莱堡大学艺术史系,弗里德伦德尔负责讲授从中世纪到19世纪的一系列课程。才华横溢的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也在他第一批学生的行列中。4与弗里德伦德尔一样,帕诺夫斯基也是美国德裔犹太学者,著名艺术史家。他反对沃尔夫林的形式自律原则,以其在图像学领域做出的贡献而闻名。潘诺夫斯基在弗格的指导下,于1914年完成博士论文。遗憾的是,1916年,四十八岁的弗格精神崩溃,不得不从学校退休,从此隐居写作。之后,弗里德伦德尔承担了更多的教学工作。直到1921年,他出版了另一部著作《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继这本书之后,他于1925年、1930年先后发表了两篇论文,这两篇文章在艺术史领域的影响尤其深远。一篇是关于早期手法主义的研究,也即他11年前的就职演讲〈1520年左右意大利绘画中反古典主义风格的出现〉(见《艺术学汇编》[Repertorium für Kunstwissenschaft],1925年,第46 期);另一篇则是关于晚期手法主义的研究〈1590年前后反手法主义风格及其与先验的关系〉[Die Anti-Manieristische Stil um 1590 und sein Verhältnis zum Űbersinnlichen](见《瓦尔堡图书馆学报》[Vorträge der Bibliothek Warburg],1929—1930年,第8 期)。通过这两篇文章,弗里德伦德尔率先为手法主义艺术定义了特征,并划定了它与盛期文艺复兴、早期巴洛克之间的边界。两年后,他出版了针对19世纪初的法国绘画的专题研究《从达维德到德拉克洛瓦》[Von David bis Delacroix](1932年,英文版1952年),并且凭借这本早期现代主义运动的入门书,晋升为临时编外教授(非全职教授)。一年之后(1933年),纳粹执政。当时六十岁的弗里德伦德尔因为其犹太人血统,在临退休之际被解除了大学教授职务。任职于汉堡大学[University of Hamburg]和瓦尔堡图书馆[Warburg Library]的潘诺夫斯基——弗里德伦德尔之前的学生,这一年正在负责出版弗里德伦德尔的纪念文集,也在文集刊印之前因为同样的原因遭到学校开除,当时的他四十一岁(图1、2、3)。
二 美国时期
弗里德伦德尔被解除职务之后,在德国四处周游了两年。1935年,他加入壮观的流亡美国的学者行列。“Friedländer”这个名字在美国被英语化为“Friedlaender”。在潘诺夫斯基的帮助下,弗里德伦德尔获得了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纽约大学新成立的美术研究院里的临时职位。不久后,他得到了纽约大学的长期任用。5与他一起得到纽约大学长期任用的还有另一位德国流亡学者卡尔·莱曼[Karl Lehmann](1894—1960),他年轻许多,同样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一位研究古希腊罗马建筑与雕塑的史学家。于是,从六十三岁起,弗里德伦德尔开始了他在美国的漫长职业生涯。按照哈佛大学教授约翰·库利奇[John Coolidge, 1913—1995]所说:“他的生涯真正开始的时间是大多数人结束的时间,那时他已经超过六十岁了。和其他避难者不同的是,他来这个国家的时候,既没有关于未来的承诺,也没有太多人了解他过去的荣誉。他带着疾病和不适,这些不久后就给他的个人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严重的财务问题。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是弗里德伦德尔忽视它们,并且学会和它们共同生活。他最独特的说法就是:‘我从不干涉自己的事情。’”6参见“Walter Friedlaender”, p.260。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艺术史研究仍然呈现出零星的、守旧的面貌。从德国来的避难者们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学科建设的任务。他们的努力逐渐使这块土地上的艺术史发展跟上了欧洲大陆的步伐。而弗里德伦德尔正是当时这种集体努力中脱颖而出的一位学者。7约翰·库利奇曾经评价说:“他是一个怀疑论者,一个温和的无政府主义者。”参见同前书。他的研究不仅涉足美国艺术史学家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 1865—1959]的鉴定世界以外的领域,对于那些同为移民的同事来说,弗里德伦德尔关于手法主义、拿破仑的御用画家,以及卡拉瓦乔等问题的研究兴趣,也显得与众不同。当然,这些特别的研究兴趣,在他长时间教学的影响下,已经逐渐变成研究主流。他训练了整整两代美国学者,先后有四十多个学生在其指导下获得学位。纽约大学的同事就曾经称赞:“他的确是不可替代的……他拥有一种天赋,在学生身上发现其他人发现不了的学术可能性。他有极大的耐心去帮助学生熟悉图书馆的庞大资源,激励他们热爱思想和艺术,使他们的学术水准发挥到极至。”8参见“Walter Friedlaender”, p.258。事实上,在1935—1942年的七年任职结束之后,以名誉教授退休的弗里德伦德尔又被返聘回校,继续从事教学工作。9退休一年之后,1943年,弗里德伦德尔与妻子艾玛·卡丹[Emma Cardin]离婚。这持续了整整二十四年,一直到他去世。正如当时的纽约大学美术研究院院长克雷格·休·史密斯[Craig Hugh Smyth, 1915—2006]所说,这“打破了我们学校和所有其他学校的规则”。10参见“Walter Friedlaender”, p.2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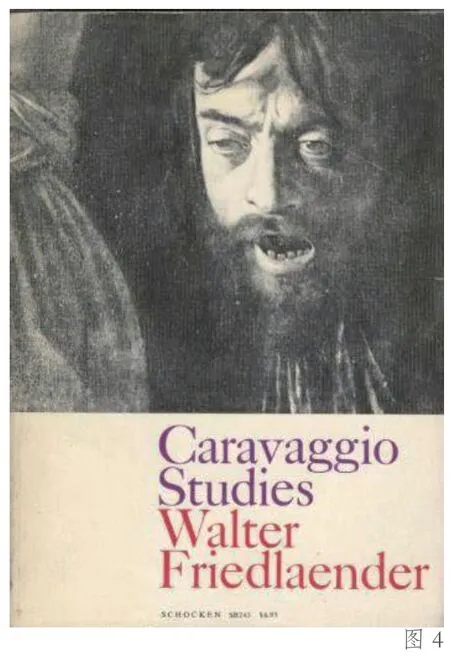
图4 弗里德伦德尔,《卡拉瓦乔研究》封面,1955年

图5 弗里德伦德尔,《意大利绘画中的手法主义与反手法主义》封面,1957年

图6 晚年弗里德伦德尔
在美国期间,弗里德伦德尔继续开展他在德国已经着手的普桑研究。从1939年起,他开始出版关于普桑绘画的整理目录。1940年,美国举办了第一个普桑展。11参见Walter Friedlaender, “America’s First Poussin Show: The Great Classicist Illustrated by his Cisatlantic Works”, Art News, vol.38,no.23, 1940, p.14。《普桑绘画》[The Drawings of Nicolas Poussin](1939—1963)目录总共出版了五卷,从弗里德伦德尔退休前三年开始,直到他退休后持续了二十多年才完成。在伦敦大学瓦尔堡研究院的赞助下,目录陆续出版。12不过,弗里德伦德尔关于普桑绘画的目录遭到了编辑们的大规模改动。鲁道夫·维特科夫尔[Rudolf Wittkower]不赞成他对普桑手稿做出的结论,安东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当时则正在写他自己关于普桑的一本书。1955年,八十二岁的弗里德伦德尔出版了他最后一本著作《卡拉瓦乔研究》[Caravaggio Studies]。这部作品打破了过去人们对于卡拉瓦乔的认识,强调了艺术家的宗教严肃性,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他的名声。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执教期间,弗里德伦德尔热情洋溢的美国学生将他在德国时写的两篇关于手法主义的重要文章主动译成英文,制成油印件,广为传播。按照菲利普·费尔[Philipp Fehl, 1920—2000]的说法:“至少三代美国艺术史学生热衷于学习德语,是因为他们想读这两篇文章。”13Philipp Fehl, “Review”,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Vol.18, no.2,1959, pp.273-274.不过,这两篇学术经典正式结集出版,已经是1957年的事情。书名题为《意大利绘画中的手法主义与反手法主义》[Mannerism and Anti-Mannerism in Italian Painting]。当时,弗里德伦德尔已经是八十四岁高龄的老人,距离他四十一岁就职演说宣读第一篇关于手法主义的文章,足足过去了四十三年。书出版时,当年的译者都已经毕业,有的留在了纽约大学美术研究所,有的去了其他大学和美术馆任职。这本书虽然还不到八万字,但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却使它成为弗里德伦德尔影响最大的艺术史著作(图4、5、6)。
八十多岁的弗里德伦德尔仍然精力旺盛地往来于欧洲和美国之间。1960年,八十七岁的他还到巴黎参加了卢浮宫举办的普桑展。1963年,他过去所在的弗莱堡大学为他授予了荣誉教席,欧洲的旧同事们为了庆祝他九十岁的生日,合力为他出版了纪念文集,他在美国的学生们也为文集提供了文章。两年后的夏天,九十二岁的弗里德伦德尔还奔赴弗莱堡大学进行了演讲。遗憾的是,1966年,他的去世打断了一切。当时他手头上正在准备新的卡拉瓦乔课程的教学计划,同时在写一本关于提香的书。虽然去世时已经九十三岁高龄,但是他的朋友们一致认为他的去世出人意料。约翰·库利奇甚至说:“这是他一生的惊奇之中最后的惊奇。”14参见 “Walter Friedlaender”, p.260。的确,这位学者终其一生都以其活力给人深刻印象。艺术史学家悉尼·弗里德伯格[Sydney Freedberg, 1914—1997]给友人的信中曾经写到:“和其他人一样,我认为(实际上是希望)他可以一直活下去。他给我的生活带来如此多的希望和爱。我发现时不时都要提醒自己,他并没有真的做过我的老师。”15参见 “Walter Friedlaender”, p.258。弗里德伯格直言,弗里德伦德尔带来的影响,就像是“在父亲那里找到了我们工作的起点和冲动”16Ibid.。
不过,谦逊的弗里德伦德尔却常常用深海海龟来比喻自己。尽管他的游离身份从来没有让他归属于任何一个学派或者一个地方,但是,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教师,他都是一个丰富并且慷慨的人。2007年,纽约的利奥·贝克研究所[Leo Baeck Institute]——一个致力于德裔犹太人历史与文化研究的机构,整理了《瓦尔特·弗里德伦德尔全集》[Walter Friedlaender Collection],纪念这位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学生、职业,还有著作的人。五个系列完整地囊括了他的出版物,还有他的相关介绍、通信、日历、笔记,以及1925—1934年纳粹德国时期的剪报。我们暂取潘诺夫斯基1949年11月21日写给弗里德伦德尔的一封信,来略窥一下学者当年的生活(图7)。

图7 潘诺夫斯基1949年11月21日写给弗里德伦德尔的一封信

图8 Gilles, Jean-Antoine Watteau.Gilles.1719.Oil on canves.184cm×149cm.Musée du Louvre

图9 Caravaggio.Supper at Emmaus.1601.Oil and tempera on canvas.141cm×196.2cm.National Gallery, London

图10 Cézanne, Paul.Les Joueurs de cartes.1892-1893.65cm×81cm.Oil on canves.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图11 Cézanne, Paul.Les Joueurs de cartes.1890-1892.134cm×181.5cm.Oil on canves.Barnes Foundation, Merion, Pennsylvania
从信中内容来看,潘诺夫斯基刚从一场可怕的感冒中恢复。他说自己将在12月17日周六这一天到纽约的弗里克收藏中心做一个演讲,想问问弗里德伦德尔是否有空与自己共度周末。言辞间的语气,显露出交往多年的师生之情早已酿成无间友谊。他是这么写的:“我想问问是否可与您共度周六到周日的夜晚。我必须和巴拉共进晚餐,但我们可以一起吃个午饭,在讲座之后碰面,共度一个宁静的下午。当然,还有周日上午的早餐。”潘诺夫斯基询问完约会事宜之后,还谈到了自己同为艺术史学家的妻子多拉的事情。他说,她刚刚完成了讨论画家华托[Jean-Antoine Watteau, 1684—1721]的作品《吉尔》[Gilles](一个哑剧丑角)的文章17《吉尔》为该幅作品的曾用名,现使用更多的是《皮埃罗》[Pierrot]。,最近想到弗里德伦德尔曾经说过,卡拉瓦乔的《以马忤斯的晚餐》[Supper at Emmaus]这幅画被塞尚[Paul Cézanne, 1839—1906]用在他《玩牌的人》[The Card Players]里,很想来与他探讨一下,这个关联到底是众所周知,还是弗里德伦德尔的独特发现。181890—1895年间,塞尚一共画了五幅《玩牌的人》,这些油画可以说是他艺术创作最后阶段的基石。短短的一封信,却足以引发我们关于学者生活和工作的无限想象。可惜的是,潘诺夫斯基远没有弗里德伦德尔高寿,他只活了七十六岁,在老师去世两年之后,随即去世了(图8、9、10、11)。
三 手法主义研究
20世纪中期,关于手法主义风格的定义,一度是学术讨论的主题。虽然学者们最终没有达成共识,但是,这个术语对于用来识别意大利中心地区在盛期文艺复兴到巴洛克之间,也就是1520—1600年之间的艺术风格极有帮助。该术语甚至被更加自由地运用到艺术史之外的学科领域,比如文化史、音乐,以及文学等等。不过,即使在艺术史领域里,手法主义被真正赋予历史重要性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实际上,直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手法主义才逐渐被认为是盛期文艺复兴之后的一种独立风格,从晚期文艺复兴或早期巴洛克的风格中分离出来,并得到确立。艺术史学家弗里德伦德尔正是促成这一共识形成的一位重要学者。1914年,他在弗莱堡大学发表就职演讲,宣读了自己针对手法主义绘画进行研究的第一篇重要文章〈1520年左右意大利绘画中反古典主义风格的出现〉。
实际上,自从吉安·彼得罗·贝洛利[Gian Pietro Bellori,1613—1696]1672年出版《现代画家、雕塑家与建筑师传记》[Le Vite de’ pittori, scultori e architetti moderni],17世纪的写作者就开始使用maniera[手法]一词来形容16世纪晚期的艺术,当时的艺术在人们看来普遍依赖人为的、衍生的再现程式,远离自然的外观。之后,“手法主义”[Mannerism]一词就成为英语世界指称盛期文艺复兴之后那种风格的常用术语。直到20世纪初,人们对于16世纪意大利艺术的认识和欣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在盛期文艺复兴,对于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这类巨人之后的艺术家和艺术的普遍看法,基本上一直没有发生过改变。人们普遍认为,手法主义是盛期文艺复兴之后的一个衰落时期,原因主要在于盛期文艺复兴末到1600年前后的艺术家们缺乏独立性,不加批判地模仿了大师们的手法,尤其模仿了米开朗琪罗那种解剖极为夸张的人物风格。
1910年前后,对于手法主义的年代范围只有模糊的界定。当时人们将手法主义时期的起点定在1530年或1540年前后,终点定在1600年前后。弗里德伦德尔通过对早期手法主义艺术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明确指出了这个时期活跃着的艺术家们有意识地拒绝规范、寻求新的美的理想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比如,压缩空间深度,拉长肢干比例,人物变得格外修长,人物形象被压至扁平等等。在他看来,这些特征都表现出了对古典美学的刻意否定,而不是继续模仿文艺复兴形式的结果。所以,他提出“反古典主义风格”一词,来强调当时艺术的反叛特征。他认为,这种特征正是手法主义初始阶段的关键。经过深入考察,他识别出了“反古典主义”精神在更早时候的表现,从而将手法主义风格的源头精确地定在了1520年前后。唐纳德·波斯纳[Donald Posner]曾经这样评价他的研究说:
罗索[Rosso]、蓬托尔莫[Pontormo]和帕尔米贾尼诺[Parmigianino]这一类艺术家,首次被当作手法主义的创作者专门提出,这促使人们对他们艺术的品质和意义进行一个重要的重新评估。同样,米开朗琪罗在梵蒂冈宫里的西斯廷礼拜堂和保罗礼拜堂绘制的晚期绘画作品,如今也可以被放到更有意义的新语境中来看待。它们不再被视为大师晚年时的怪癖产物,也不再被视为对年轻一代具有腐蚀性影响,它们被看成是那个时代反古典美学的主要宣言。19Donald Posner, “Introduction”, Walter Friedlaender, Mannerism and anti-mannerism in Italian Painti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7, pp.xiii.
弗里德伦德尔看待文艺复兴美术史的新视角具有开先河的意义。当时的研究者基本都把16世纪当作可以忽略的时期,连沃尔夫林在1915年出版的《美术史的基本原理》中也仍然认为,从文艺复兴的古典风格到17世纪的巴洛克风格是一种持续的演进。20弗里德伦德尔批评过的沃尔夫林《古典艺术》[Die klassiche Kunst](1899年),相比之下,沃尔夫林的创造性更多体现在他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方法论上。弗里德伦德尔的视角,显然受到了当时的奥地利艺术史家阿洛伊斯·李格尔[Alois Riegl, 1858—1905]观念的影响。李格尔在20世纪最初十年的研究——《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Die spätrömische Kunstindustrie nach den Funden in Oesterreich-Ungarn](1901年)和《巴洛克艺术的罗马起源》[Die Entstehung der Burockkunst in Rom](1908),都为长期遭受贬低的艺术时期进行了正名。通过重新发掘这些时期的艺术所具有的特征,研究它们的观看方式和感受方式,李格尔明确指出这些时期并非衰弱的时期。他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艺术史研究传统中存在的偏见(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看作风格史研究中的分水岭),年轻一代正是在这样的影响下展开了关于手法主义艺术的解释。事实上,李格尔所属的维也纳美术史学派在当时有一股强大的风气,要为遭受冷落的艺术风格恢复名誉。黑暗的中世纪、怪诞的巴洛克、奴性的手法主义,逐一接受了学者们的重新审视。
20世纪20年代前后,欧洲学者专门针对手法主义艺术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逐渐出现。1919年,维尔纳·魏斯巴赫[Werner Weisbach]发表了〈论手法主义〉[Der Manierismus](见《造型艺术杂志》[Zeitschrift fur bildende Kunst],总第30 期),用否定的方式对手法主义进行了分析,同时强调了手法主义中抽象化、风格化的心态。1920年,奥地利艺术史学家马克斯·德沃夏克[Max Dvořák, 1874—1921]在一次演讲中分析了手法主义艺术中主观的、表现主义的意图,并将手法主义视为16世纪总体“精神危机”的表现。他的演讲手稿〈埃尔·格列柯与手法主义〉[Über Greco und den Manierismus]四年后被收入《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Kunstgechichte als Geistesgeschichte](1924年,慕尼黑),成为他阐释北方艺术的这部代表作的第六章。21《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这本书是维也纳美术史家斯沃博达[Karl Maria Swoboda]和维尔德[Johannes Wilde]在德沃夏克去世之后以他在大学讲座基础上编的一本文集,小册子百十来页,仅由六篇文章组成,但在西方美术史上已经成为经典。而他于1918—1920年间在维也纳大学的课堂上就手法主义所做的详细讨论,也在他去世后收入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史》[Geschichte der italienischen kunst im Zeitalter der Renaissance](1927—1929年,慕尼黑)。
弗里德伦德尔的手法主义研究几乎与魏斯巴赫和德沃夏克同时,甚至更早一点,但他拒绝将手法主义视为衰落风格的理论立场,使其讨论尤显突出。尽管他1914年宣读的〈1520年左右意大利绘画中反古典主义风格的出现〉,直到十一年后才正式发表。五年之后,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1590年前后的反手法主义风格及其与先验的关系〉。在此文中,他和德沃夏克一样,发现了手法主义与其所在时代的精神表达(尤其是德国表现主义)之间的关系。但是,德沃夏克是把手法主义直接定义成一种表达精神性的艺术手段,相比之下,弗里德伦德尔则倾向于分析“1590年风格”与“1520年的反古典主义风格”之间的相似,进而指出手法主义如何走向终结。这像是为前一篇文章划上句号。一篇关于反古典主义(也即早期手法主义)的研究,与一篇关于反手法主义(也即晚期手法主义)的研究,共同为手法主义艺术划定了边界,并定义了特征。两项研究前后耗时十多年,恰如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1924—2014]在他最后那本以“历史分期”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中所说:“人们将时间切割成时期的理由常常来自于某些定义,这些定义强调了人们赋予这些时期的意义与价值……对历史进行分期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充满了主观性和辛勤的努力。”22[法]雅克·勒高夫、杨嘉彦译,《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4页。
弗里德伦德尔关于手法主义的两篇文章完成于德国时期,在他1935年流亡美国之后,执教期间被学生们翻译成英文,广为传播。这两篇学术经典在坊间传阅了二十多年,直到1957年才正式结集出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书名题为《意大利绘画中的手法主义与反手法主义》。20世纪60年代书再版时,纽约大学美术学院的同事唐纳德·波斯纳为其撰写〈导言〉,文中提到:
弗里德伦德尔教授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对手法主义时期本身的第一、第二阶段进行区分。(这一区分在本书中就“反手法主义”风格进行讨论的第二篇文章里有着极为清晰的陈述。)晚期手法主义艺术来自最初的术语Maniera(现代意大利语中表示手法主义的词是il Manierismo),弗里德伦德尔教授认为它是模仿性的,这种“手法化的”手法主义一味夸大,继而破坏了早期手法主义中创造性的反古典主义。将手法主义划分成两个独立阶段,如今差不多已得到普遍接受,尽管现在有人试图将第二阶段的开端定在1530年前后,而不是像弗里德伦德尔教授所提出的1550年前后。但是,近年来,人们主要致力于重估手法主义两个时期的意义和特征。23Donald Posner, “Introduction”, pp.xv.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流亡浪潮之后,欧洲来的移民学者给美国本土的艺术史研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人们将视野投向欧洲大陆,激起巨大的翻译热情。241952年,琳达[Linda]和彼得·默里[Peter Murray]完成了沃尔夫林1899年的《古典艺术》的英文翻译。1953年,哈佛大学的约翰·库利奇将马克斯· 德沃夏克1920年的演讲手稿〈埃尔·格列柯与手法主义〉翻译成英文,发表在《艺术杂志》[Magazine of Art],总第46 期,1953年第1 期。虽然弗里德伦德尔的手法主义研究直到50年代末才以书籍形式正式出版,但从20年代起,“反古典主义风格”的概念就已经在盎格鲁撒克逊学术中扎下坚实的根基。60年代,唐纳德·波斯纳回望人们关于手法主义的认识在时代变迁中的变化时曾说:
弗里德伦德尔教授……似乎没有预见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人们对于手法主义的认识出现了非同寻常的“突变”。在努力将1520年前后到1590年前后的所有欧洲艺术与文化纳入‘手法主义时期’的过程中,诸如彼得·勃鲁盖尔[Peter Bruegel]之类的艺术家最终也被解释成了手法主义者。(例如,参见本内施[O.Benesch],《欧洲北部的文艺复兴艺术》[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in Northern Europe],剑桥,1947年,一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马克斯·德沃夏克的著作。)这种扩张倾向在1955年那场名为“欧洲手法主义的胜利”[The Triumph of European Mannerism]的大型展览中达到了顶点。该展览由欧洲委员会发起,在阿姆斯特丹举行。近来许多通俗、半通俗的书籍都传播了这种极其宽泛的手法主义观念。不过,如今许多学者都在提防这一看法带来的过度简化,他们试图追随弗里德伦德尔教授的引导,集中关注具体场所、具体时期所特有的艺术和文化运动的特征。25Donald Posner, “Introduction”, pp.xv.
弗里德伦德尔的影响,在50年代之后显示出比20年代更加广泛的效应。1963年,第20 届国际艺术史大会召开,配合会议出版的“第20 届国际艺术史大会文献:西方艺术研究”(普林斯顿,1963年)第二卷专题名为《文艺复兴与手法主义》[The Renaissance and Mannerism]。此时,人们对于手法主义的狂热已经回落到相对冷静的状态。作为一种独立风格的手法主义,如今不再是文艺复兴的附庸,但也不像稍早前那样咄咄逼人了。这本书集中呈现了英语世界关于手法主义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约翰·希尔曼[John Shearman]的论文〈作为美学典范的Maniera〉[Manieraas an Aesthetic Ideal](1967年扩展为《手法主义》[Mannerism]一书在英国出版),以及克雷格·休·史密斯的〈手法主义与Maniera〉[Mannerism andManiera](这篇研究详细分析了Maniera风格来自于和先前的托斯卡纳反古典主义风格完全不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径相对立的美学理念)。1965年,悉尼·弗里德伯格发表了〈Maniera绘画研究〉[Observations on the Painting of theManiera](见《艺术公报》[Art Bulletin],第47 期,第187—197页)。1972年,富兰克林·鲁宾逊[Franklin W.Robinson]和斯蒂芬·尼科尔斯[Stephen G.Nichols]在美国出版了《手法主义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annerism],亨利·策纳[Henri Zerner, 1973—2015]的重要论文〈关于手法主义概念的使用考察〉[Observations on the Use of the Concept of Mannerism]也收录在其中。
弗里德伦德尔在为1520年前后的反古典主义和1550年前后的反手法主义这两股浪潮划定边界时,充分利用了关于maniera[手法]一词的分析。他指出,16世纪艺术史家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 1511—1574]在《雕塑》[Scultura]中谈到雕塑家时说:“他们通常把雕像的头发弄得浓密而卷曲,più di maniera che di natura[手法胜于自然]。”26Mannerism and anti-mannerism in Italian Painting, p.48.通过拈出“maniera[手法]——natura[自然]”这一对关系,他追溯了maniera的早期使用,进而展开了关于“反手法主义”风格的诠释,如其在书中所说:
变得“手法化的”恰恰是更老的风格(由于缺少更好的词,我前面称之为“反古典主义的”,但它往往被人从支流逆向追溯,称作“手法主义的”)。也就是说,1520—1550年前后那种高贵、纯粹、理想化的、抽象的风格,在下一个阶段(约1550—1580年)就变成了一种手法;而它变得di maniera[手法化]的途径,一方面是重复、机巧、游戏式的夸张,另一方面则是软弱的让步。一些拥有“健康”意志的明眼人直接指出了当时出现的这一危险。27Ibid.
正是在他的基础之上,后继学者进一步展开了关于maniera概念的讨论,在这个词语的16、17世纪用法与现代诠释之间搭建起桥梁。实际上,瓦萨里使用maniera这个词的时候,主要意味着“手法”或者“风格”。虽然它有积极的含义,但也可以被消极地用来指惯例。比如,瓦萨里提到佩鲁吉诺[Pietro Perugino]的晚期作品时就说过,单调乏味正是来自于他对maniera的过度依赖。而17世纪的理论家贝洛里则把maniera同缺乏合理的创造以及依赖于习惯和惯例联系了起来。对他来说,从盛期文艺复兴之后直到由安尼巴莱·卡拉齐[Annibale Carracci]带来的艺术复兴之间,这一间隔期中的艺术是一种背叛,艺术家背离了自然的模型,反而跟随自己的想象力,误入幻想的歧途。当贝洛里说到艺术家用maniera破坏了艺术时,很容易就让人联想起瓦萨里对佩鲁吉诺的责难。
事实上,弗里德伦德尔借助关于maniera[手法]一词的分析展开“反手法主义”风格的讨论,与他回避“手法主义”这个术语(使用“反古典主义风格”),都是拒绝将手法主义视作衰落风格的体现。虽然他指出,同第一阶段的反古典主义的反叛特征相比,“真正的大敌是第二阶段手法化了的手法主义”28Ibid., p.50.,但他分析16世纪晚期的艺术家如何在“先验”主题的再现作品中清晰表现反手法主义的态度,揭示了手法主义可以被理解成一种主观的、“精神性的”风格。而这种根本的一致性,恰恰体现出一种新的艺术精神。他把“1590年风格”与“1520年的反古典主义风格”这两次运动都看作是对它们之前时期的主流思想反作用的结果,所以,他提出“反手法主义的”一词来描述16世纪最后25年的新风格。他甚至进一步指出,1590—1600年间处于职业鼎盛期的艺术家们的作品,从否定的观点来看,存在着偏离手法主义的转折;但从肯定的观点来看,却存在着朝向真实、规范和理性、人性和内心的改革。他说:“新的精神处理方式需要艺术家在处理人类灵魂中最大的喧嚣时表现得平静而泰然,就像在处理幻像问题时一样。”29Ibid., p.77.
尽管手法主义艺术作为对盛期文艺复兴艺术的反抗,这种积极意义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但在50、60年代,仍然有学者坚持危机说。(理论家将1590年前后的意大利绘画风格中出现的断裂确诊为社会弊病的征兆其实从17世纪就开始了。)比如,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他虽然在1950年出版的《艺术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中断言“帕米贾尼诺和当时那一批力图新颖出奇而不惜牺牲艺术大师所确立的‘自然的’美的艺术家,大概是第一批‘现代派’艺术家”30[英]贡布里希著、范景中译,《艺术发展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201页。,但是,仍然把关于手法主义艺术的阐释列在“艺术的危机(欧洲,十六世纪后期)”这样的章节名称下。之后有学者进一步展开讨论了“危机”中所蕴含的“现代”的意义。比如,60年代中期,美国艺术史学家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 1892—1978]在《手法主义:文艺复兴的危机和近代艺术的起源》[Mannerism: The Crisis of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Origin of Modern Art]这本书中,运用社会学知识将手法主义的概念与当时的文化进行了关联。当然,在对手法主义进行重估的这股潮流之中,仍然存在着将手法主义看作艺术衰落期的例子,比如,60年代末期意大利美术史学家阿尔甘[Giulio Carlo Argan,1909—1992]的《意大利美术史》[Storia dell’arte italiana]一书。
但是,不管怎样,弗里德伦德尔的研究不可回避地使人们聚焦到了“手法主义”艺术上,并因此重新理解了文艺复兴。在他的分析下,作为一种“人为”风格的手法主义,获得了从贬义理解过渡到中性理解的可能性。他用积极的、正面的理解方式,打破了人们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坚持的习惯性认识。“手法”不再被固执地理解成一种空洞的复制,“手法”不只是非原创的,不只是对确定的东西进行重复的,也不只是重复过多之后变得单调乏味的。一些新的认识建立起来,并且越来越清晰。比如,“手法”与“自然”的碰撞,极其主观的变形,日常经验的违背,等等。而且,关于手法主义风格的剖析,帮助他完成了历史分期的工作,充分实现了一种自治风格的建立。在弗里德伦德尔看来,反古典主义风格倾向于回归盛期文艺复兴之前的“哥特式”潮流,与之相似,反手法主义风格反作用于手法主义风格,呈现出对盛期文艺复兴艺术的共鸣。反古典主义和反手法主义都具有否定的、回溯的特征,而这可以解释为新生代反叛“父辈”的法则和教导,倾向于采用“祖父辈”理念的一种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