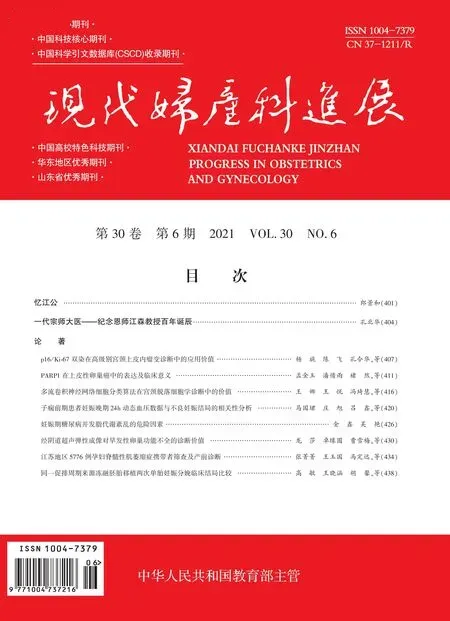忆江公

江森教授离开我们十年了!
时光倏匆,江公音容笑貌就在眼前;往事如烟,宛若昨日。
江公是妇产科学界大师、泰斗,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我们有忘年之交、亲密之情。
2010年9月,正值江公九十大寿之际,我曾写下如下短句,以致敬仰:
泰山之麓,大明湖畔。
斗牛之气,师表非凡。
江河之长,风起源远;
森林之原,范典霄汉。
泰斗江森,大师风范。江公是应该有个熠熠闪闪、厚厚重重的功劳簿的。我在这里,更愿意讲点小故事,觉得真真实实、亲亲切切。
剖宫产术
剖宫产手术及其名称都是舶来品-Cesarean Section,无论叫“剖腹产”或者“剖宫产”,我们从经典的原著中都找不到是“剖腹”还是“剖宫”的概念。在Cesarean(凯撒)一词之后,可以加“birth”、“Delivery”或者“Operation”。显然,肇始于国人翻译或命名,剖腹产就沿袭叫下来了;显然,是剖宫而生,并非仅仅剖腹手术。
江公睿智慧眼,率先指出“剖腹产”称谓之不确,应为“剖宫产”,明确、准确!当时中华医学会有个“科学名词专业委员会”,江公就是主要成员,该意见得到公认、得以公布,江公之功也!
江公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古今皆通、中西合璧。对历史文化更独擅其长,所以,他来“咬文嚼字”是再合适不过了,他曾几次指出“妇产科杂志”的概念就错了,不是“妇产科”的杂志,而是“妇产科学”杂志。
江公还真善于讲“剖宫产”。那年,在南京钟山宾馆开学术会议,江公的题目就是“剖宫产的历史和现状”。江公洋洋洒洒,侃侃而谈,早已超时,主持人张惜阴教授击杯以示提醒,江公自喃自语:“噢,嫌我声音小,那我大点声。”又我行我素地讲下去。后来,他们把我这个会议主席叫去,问“该怎么办?”我听江公讲的真好,便说:“请他讲下去,我讲课的时间都给他了。”
以后,学生们开始“控制”他了,什么薄膜、幻灯、PPT,他得跟上,嘴里会叨咕着“太快了!”也没有办法……
跟江公在一起工作很开心,长知识、有乐趣。
手术大师
江公是手术大师,老道稳健,无所不能;胆大心细,所向披靡。各种疑难复杂的手术,各种罕见创新的操作,都在江公胸前“趟过”,在江公手下“开路”。
更重要的,最难能可贵的是江公大师风范、菩萨心肠,有求必应、手到病除。
那次,我们在温州召开学术会议,温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有位宫颈癌的病人,要请江公手术。江公当然满口答应,欣然前往。
到了中午吃饭时辰,江公还没下台。病变晚期,手术困难。江公认真细微,务求切净,还在艰苦地进行着,我们只好等晚上慰劳江公。可是到了傍晚,江公仍在台上,在解决出血等麻烦问题。宋鸿钊大夫等都坐不住了,全部出动去医院,这“亲友团”可是够壮观了!在手术室,大家反复讨论,认为当下以填塞压迫止血,尽早结束手术为宜,以防DIC发生。江公当然从善如流,也真是劳苦甚矣。我们都表示慰问、敬佩之意,江公却依然精神抖擞,毫无倦怠,竟然风趣地说:我怎么觉得手术刚刚开始,怎么就下来了……
直到晚年,江公依然坚持上台手术,直到关键步骤完成,江公依然坚持做完手术,得让北华教授等连哄带劝地请下台,才得罢休。
我们深知,向江公学习,作为好外科医生,就像一个战士,永远站在手术第一线。要有一种渴望、一片热忱,去解除患者的病痛,去解决同道们的问题。
因此,我们始终都感觉江公永远不老,永远永在!
江公吐哺
江公一生辛劳,教书育人,桃李天下。我与江公接触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一位好老师:谦和而严谨,庄重而耐心,文雅而诙谐。使人愿意亲近、倾心聆教。
参加江公学生答辩是我等求之不得的荣幸。1988年,江公的硕士生郭丰、王冠华、胡国丽三位毕业,题目都很趣,前卫而实用。我见过江公对论文的审批,密密麻麻,甚至有些潦草,那是江公的书写风格,我却可以看得懂。
后来江公的博士年年如“孵鸡破壳”、“窝窝而出”,跳跃飞腾,现今均已成专家名士,如汤春生、杨延林、宋磊、孔北华、王波、张贵宇、张师前……
蒙江公厚抬,我都能应邀参加他们的毕业论文答辩,收益颇多。及至,这些博士们的博士又一批一批的培养出来,我又被邀来评审。情景可是壮观了:江公那会儿每次也就一、二位,二、三位,而今可达十位,二十位——江公后继有人矣!
我想起,给林巧稚大夫八十华诞祝寿诗:
您悉心培养的学生,桃李满天下,
他们又有了学生,天下满桃李。
这到处结实的硕果,浓郁的芳菲,
不正是您用毕生心血
撰写的巨著鸿篇。
我也想起,曹操的《短歌行》: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把它们献给江公,也非常适合。
学术推广
江公对妇产科学术推广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限于山东,也不限于学术会议,《现代妇产科进展》杂志的创刊和发展,就可圈可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妇产科学专业杂志尚少,特别是关于基础研究的论文和发展动态报道显得局促。在这种情势下,江公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和解法,他决心创立、弥补这一缺憾的杂志。
他和殷立基教授,联合温州医学院的俞德祺教授到国家教育部、卫生部请命周旋,赤诚之至、辛苦之极,终于于1989年得批建刊。《现代妇产科进展》定位明确,重点发表研究成果和相关论文,内容广泛深入,已形成品牌,突出特点。在妇产科学界即是雪里送炭,又如锦上添花,受到研究生师生的青睐和广大妇产科医生的欢迎。后来成为国内核心期刊、省区优秀期刊,由双月刊变为月刊,发行量、被引率逐年上升,成为和“中华”、“实用”并驾互补的兄弟期刊。
江公自建刊始即任主编,呕心沥血可想而知。直到仙去,“现代”成为他的遗志珍物,由北华教授接手前行。
在办《现代》中,有一条经验也值得借鉴。调用优秀的妇产科大夫轮流到编辑部“挂职”工作,对文字写作、临床研究以及两者的沟通、协作等都是很好的锻炼,像马玉燕教授都是做的很好的多面手,连我都想去试一试。
《现代妇产科进展》是饱含江公等心血的,爱屋及乌,让人深怀情愫。
苏江二公
一直以来,我们都把苏应宽、江森二位教授尊称苏江二公,不只是山东,更是全国的。他们都学识渊博、医德高尚,他们都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们都是谦谦君子,款款大家。
苏公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之同乡也;江公江西婺源人,胜地名人辈出。苏公比江公长5岁,让人钦佩的是,他们同行、同省市、同一所大学,却总是彼此感情诚笃,友爱和谐;相互尊让,不论伯仲。是楷模,是旗帜!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其实,苏江二公性格差异很大:苏公谦和稳健,看去大智若愚;江公乖巧洒脱,言行时显波谲云诡。可两人在一起却融洽舒润,如天合地作一般。
他们一起掌控山东齐鲁妇产科航船,一起编撰优秀的妇产科学书籍,一起培养学生后辈,我们甚至分不清谁先谁后,孰长孰幼。苏公对江公谦让得多,江公对苏公恭敬得多……这在当下浮躁日盛、功利不让,物欲横流、人心不古之时,尤为难能可贵,当为神明。
我们向老一辈学习,除了他们的学识和技术,更有精神与品格。我们也油然想起林巧稚和王淑贞两位先人,“北林南王”,南北泰斗,但并无分庭抗礼,彼此对峙,而是友好友爱、相敬相亲。王大夫比林大夫长2岁,但林在北京,社会地位高、各种活动多,王大夫总是甘当副手,心心相印。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大学的妇产科学统编教材就是王淑贞主编,特注林巧稚评阅。而林大夫对王大夫及其领导的上海红房子医院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关注。1981年,在苏州召开“文革”后第一次全国妇产科学术大会,王淑贞、严仁英主持,林大夫已在病中,未能亲往,郑重地写了贺信,并特意让我和宋大夫看望王淑贞大夫并转达她的致意和问候。
这便是大家、大师们的榜样。学术非江湖,学问无恩怨。科技队伍和谐团结、精诚一致,方可进步。大家不小气、小气非大家。我们向老师们要学习的太多。
童心未泯
我认识江公时,他已是60有余,应算是老人,但给我的印象却孩童般可爱:走路有些跳跃着,说话不顿挫,思想更活泼,做事有时近乎天真。
他和吴葆桢大夫都酷爱武侠小说,俩人定期交换。坐在一起,一只烟、一杯茶或一盅酒,侃侃而谈的是金庸。所以,江公的作派颇有义士之举、侠气之风,有时你会感觉他像是在仰天长啸、师心自用或捋鬚吟唱、纵横今古。我们有时可以形成一个小型“诗词会”,做个令、接个龙,十分有趣。如若答不出,可是要罚酒的,江公此时可不逊让。
有次选举会,有些不公。江公义愤,竟要闯会讨个说法,真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慨,好不容易才将其劝阻。
有年入冬,江公罹小疾入院手术,术前问学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能复还否?”当然,一切顺利。晚上,却假装输液反应,“骗得”医生给打镇静剂,而后却无不得意的跟护士说:“你看我装得像不像?他们都没有看出来。哈哈!”江公啊,真可爱矣。
一位哲人说:阅读童话,会发现成人倒是幼稚、可笑和低下的。成人若有童心,则会变得纯真、清扬起来。
阅读江公,像是面对思想的铜镜,我们应该有心灵的拷问……
佐佐木(Sasaki)教授是著名的日本妇产科专家,常有中日交流彼此来往。佐佐木还是位汉学家,有中国文化功底。那年在济南开会,会间佐佐木兴致来了,想舞文弄墨一番。展纸研墨,佐佐木写出很不错的三个汉字“不动心”,有点偈语味道。江公找我说,“咱们得接上。”是啊,虽不针锋相对,也要合仄押韵,意不低筹呀。于是,我写下“要认真”三个字,与之呼应。
不知条幅安在否?江公已去,思念还在。“不动心”,“要认真”——也许这正是我们的禅意偈语,就是我们怀念江森大夫的心结。
郎景和
202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