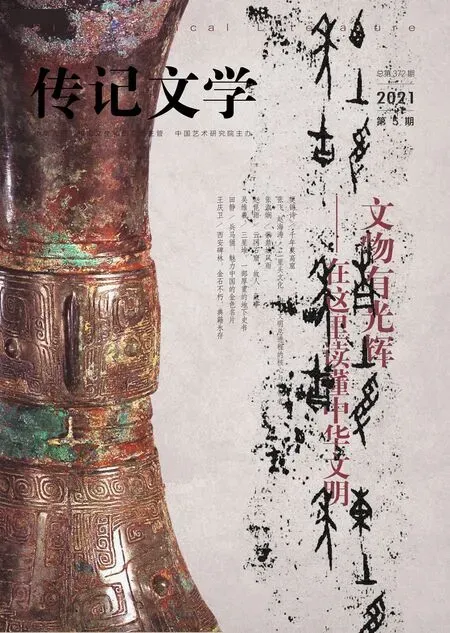饱满而有意义的人生
——我的艺术之路
张祖英 口述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
凌 晨 整理 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编辑部

张祖英,1940年生,上海人。1963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同年到中国戏曲研究院和文化部艺术研究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前身)工作,长期从事油画艺术创作及研究。1981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高级油画研修班。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美术报》副社长、副主编,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国家画院油画院副院长。2004年被欧洲人文艺术科学院授予客座院士称号。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油画学会副主席。
张祖英先生既是一位油画家,也是一位理论家,又是一位中国油画事业发展的推动者。他将研究与创作互通互补,作品呈现出中国油画的大气象。他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与中国油画学会的早期组织者,油画界的众多重要会议与展览都是他组织的,不同时期的油画创作导向的产生,也都与他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他还承担着诸多当代油画创作与研究工作。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著名美术史论家水天中先生认为他在中国油画被中国公众广泛接受为一个民族画种方面所作的历史性贡献,可以与刘海粟、徐悲鸿先生的历史贡献相提并论。与张祖英先生对话,会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张祖英先生是一位“宁静致远”的人,“宁静”是他的潜质,“致远”是他的追求。在对话的过程中,总会被他对油画艺术深邃的洞察理解所折服,也总会被他为中国油画事业倾心投入的奉献精神而感动。现今已届老年的张祖英先生仍然坚持创作与研究,并一直关注着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2021年春暖花开之际,笔者来到张祖英先生的寓所,倾听这位长者讲述他饱满而有意义的人生。
少年时的梦想
我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茶商家庭,父亲曾是中国茶叶同业公会的理事长。受到家庭的熏陶,我自幼对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梦想将来当个大画家。因此,在儿时,画画是最让我高兴和不知疲倦的事情。三国、水浒的人物绣像和欧洲小说的书籍插图是我最早的“教材”,在其他儿童忙于玩弹子和踢球的时候,我却只钟情于画画。只要手中有纸和笔,幼时的我就会一个人埋头涂上半天。我会用两三个小时专注地用粉笔随心所欲地把心里想的故事画出来,从弄堂的这头画到那头。虽然时常因画画弄脏了地方或误了吃饭而受到训斥,但家人对我的兴趣却极为支持,自初中起即送我到当时上海颇有名气的“现代画室”学习。老师是同济大学建筑系的陈盛铎教授,他的素描教学深入浅出,富有启发性,一些难以表现的技法从他的口中讲出,都能让我很快地理解。那时,我每周有三个晚上都去画室,风雨无阻。
高中开始,又在父亲和姐姐的安排下,跟着刘海粟先生学习。刘海粟先生与我家是世交,我的姐姐与他的女儿又是同班同学。经我姐姐传话,刘海粟先生让我带着画去给他看,看过后大为喜悦,随即同意收我做他的学生。他家的书房中存有丰富的古今中外藏书,还有从欧洲带回的与原作等大的大卫石膏头像。特别是从欧洲带回的大量画册和上百张大幅欧洲古典和印象画派的仿真印刷油画,使我极为震撼。正是这些充满生命力的作品,开启了我对油画艺术认知的天地。刘海粟先生学识渊博,中西皆通,他虽不是手把手地教我基本练习,但连续多年每周一次的评阅习作和中外画事谈论,使我浸润其中,开始真正想要探寻绘画的真谛;也使我在逐渐学习绘画基本功的同时,为寻求绘画所表达的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做好了充分准备。刘海粟先生常说:“艺术是一门学问,是学问就要不断探索。”又说:“绘画是愉快的,但也是件苦差事,不努力就会一事无成。”并告诫我要不断学习各种文化知识,提升作为艺术家所需要的综合修养,等等。这些话语我在后来的艺术创作和研究中更是深有体会。

1984年,张祖英与刘海粟先生合影
1959年,我19 岁,正面临高考,那一年也成为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作为一名从小就梦想当画家的年轻学子,我最想去的是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但当时由于各艺术院校都是分别招生,于是我先报考了浙江美术学院,同时作为后备,又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电影学院,结果我被这3 所院校先后录取。那一年,由于上海有5 名考生(我是其中之一)与我同样,两地高校招生委员会协商,决定把我们上海的这5 名考生都留到上戏。这期间家人与我曾多次努力争取,但由于招生体制的原因,我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去自己最想去的浙江美院。那时,年轻的我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现实。后来当知道我的一位画友只考上浙江美术学院而没有考上上海戏剧学院,却反倒顺利进入了浙江美术学院学习,我心中真是百味杂陈,难以言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命运就是这样,当你经历过挫折或苦难之后,好的运气可能正在向你走来。在上戏几年的学习,虽专业的美术技法课少于美术学院,但我接触到了中外造型艺术史、中外建筑史、中外服装史、古典诗词、古典文学等课程,听了无数上海著名文艺专家的精彩艺术讲座,这些综合的文化课程在美术学院是很难学到的。更为幸运的是,我们四年后毕业的时候,正值国家提倡现代戏研究和京剧改革,中宣部、文化部要成立一个艺术创作机构,意图从各高校选调从事文学、音乐、美术的优秀青年人才充实到创作机构中。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部把我调到了北京,进入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前身——中国戏曲研究院和文化部艺术研究机构。现在回想,当初我若去了浙江美院,哪里会有到北京——这一全国文化之都工作的机会呢?
幸运的事还不止于此。1967年我到北京不久,便在两天时间内认识了两位我仰慕已久的知名画家——詹建俊先生和靳尚谊先生。一切都是巧合,就像老天爷安排好了似的。那时,北京建地铁一号线,从木樨地到石景山。我接到为地铁石景山站画《毛主席视察首钢》作品的任务。项目结束前,市领导组织一批专家前来审稿,负责美术方面审稿的就有詹建俊先生。他审完作品离开时悄声对我说,中央美院有一位老师也画了一张类似题材的作品,你们可以相互交流一下。我问是哪位老师?他说是靳尚谊。于是心急的我第二天骑了两个半小时的自行车,到北京南郊的北京木材厂找靳尚谊先生。当时中央美院正在那里开门办学,搞创作。初见靳尚谊先生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天正遇周六,厂里工人都已下班,我走进高大的、空无一人的车间里,在透过天窗的斜阳的映照下,他正在弯腰改画,对画中毛主席的形象进行精心加工。我们见面并商定,两天后,靳尚谊先生到东四八条我的工作室。靳尚谊先生看了看我正在创作的作品,并提了一些具体建议。就是从那时起,我和两位先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在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与他们在油画领域共同探讨和工作。
为实现理想而奋斗
在北京工作的这些年,我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委会与中国油画学会的早期组织者之一,为中国油画的发展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有很多人说我为国家的油画事业付出的个人时间和精力太多了。其实,我的思路是很明确的,作为一名油画艺术家,能把个人的油画作品完成好固然重要,但是为了油画艺术不断有新的发展与开拓,能与师友一起根据艺术发展规律,创造良好的艺术氛围,把业内同仁的力量凝聚起来,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这种付出是值得的。我感悟到在事业发展中,人才固然重要,但只有组织起来的人才才能产生巨大的力量,才能做出大事。“大池有水小池满”,总体环境好了,自己才能有所提高,就像金字塔那样,底子宽了,塔尖才能高。如果只顾个人闭门拔高,最终也高不到哪儿去。人要在一个精英团队里相互熏陶,这对提高个人的综合修养很有帮助,如果没有宽松的学术氛围,个人也很难发展。组织和参与艺术活动,能促使我从宏观角度思考中国油画的发展;在这个优秀的学术团队里,师友间的倾心的互动,使我有很多感悟,也创作了不少好的作品。多年来,为促进中国油画事业的发展而努力也成为了我的使命。
我从事油画艺术工作的始因是第六届全国美展后的一个学术研讨会。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在沈阳举办,同时召开了创作研讨会,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派我和陶咏白同去参加。整个讨论会的个人发言都是预先准备好稿子,会上照本宣科,缺乏生气。但与会者会后回到宿舍里,气氛就完全不同,你一言我一语,经常围绕展览中的学术问题讨论到深夜,观点也很新颖直接,表达他们的真实心声。我当时感觉,既然会上那么沉闷,会后交流却是那样活跃和热烈,那么是否可以专门组织一个会议,让艺术家们有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巧合的是和我住同一个房间的鲍加先生是安徽省美协主席,他也正在思考如何把安徽美术搞上去。鲍加听到我的设想十分兴奋,表示如北京发起这个会议可到安徽来举办,经费问题安徽可以想想办法。周围一些画家听到这样的设想也都表示赞同。话虽到此,一切仍处在酝酿中。第二天上午,在去省展览馆看画的途中,我向同所的陶咏白介绍了昨晚和鲍加交流的情况,讨论我们美研所能否参与发起这样一个会议。陶咏白说这个事情想法很好,回去想办法向所里争取。这就是最初提出会议创意的起因。回到美研所后,我把此情况向所领导作了汇报。“文革”后,美研所同仁们工作热情都很高,几位领导积极支持,所长张明坦让我先准备一个方案。那时我只是个青年研究人员,因为大家知道我对油画事业有热情,看问题又有主见,所以都支持我负责操办这件事。
怎么才能开好这个会呢?当时我考虑到,对油画专业来说,美研所当时的重点是搞史论研究,在油画界影响不大,推动油画的创作和研究,光靠美研所肯定不行。而中央美院是油画界的大本营,我首先想到了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靳尚谊先生,我连夜到他家介绍了举办活动的构想。他听后认为让创作者和研究者共同研讨这个想法很好,并表示美院一定积极参与。当时北京画院也比较活跃,迎春画展后又成立了北京油画研究会,在业内有一定影响力。于是我到画院找闫振铎介绍了组织讨论会的设想,我们是多年的朋友,闫振铎也非常赞同我们的想法,所以北京画院也就参与进来了。就这样,场地由安徽美协主席鲍加落实,美研所的所刊《美术史论》杂志也给予大力支持,大的方面基本上有了着落。为了营造舆论氛围,我又访问并请教了很多在北京的权威艺术家,像吴作人、刘海粟、艾中信、吴冠中、罗工柳、刘迅等,并综合他们的个人观点编写了第一期通讯。那时油画界同仁虽有创作和研究热情,但苦于无从下手。这个消息传开,业内人士都很兴奋,全国各地甚至包括海外的一些艺术家,像陈逸飞、陈丹青、孔伯基等都主动来电联系,要求出席。编第二期通讯时,几个筹备单位的相关人员也都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集中开会,一起落实会议的宗旨和议题,并确定了组织架构和组织委员会成员,我作为筹备委员,被任命为秘书长,负责具体操办实施。这就是当年美术界非常著名的“黄山会议”。会议时间是1985年4月21日到4月26日。开幕式很隆重,当时的安徽省委副书记袁振,安徽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陈登科和老一辈艺术家吴作人,以及罗工柳、艾中信、吴冠中等都亲临会场,向与会同志谈了创作的实践经验和主张。艺术家们皆畅所欲言,会议的气氛热烈。每天白天讨论,晚上9时各组的代表进行汇总,连夜编写简报,会议虽然只开了几天,却出了12 期简报,会后还出版了会议纪要和论文集《油画的春天》。这次会议的精神在全国各地传开后影响很大,开启了国内由学术机构自己组织召开全国性学术会议的先例。

1985年5月,张祖英参加黄山会议时留影
“黄山会议”之后,业内人士感到专家在艺术领域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会后5月上旬,在山东济南召开的中国美协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美术各专业委员会,由各专业的专家来具体引导学术发展。同年11月,美协首先成立了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4 个艺术委员会。油画艺委会设一个主任,两个副主任,18 位委员;詹建俊先生担任主任,闻立鹏、何孔德为副主任,聘任我为秘书长。就这样,在之后几十年时间里,我全力投入到推动油画艺术发展的工作中。
油画艺委会成立后,第二年在北京首次举办了全国油画专业大型讨论会,我具体组织了三个报告:由水天中作中国油画发展史介绍;由朱青生作外国当代艺术情况介绍;由高铭潞作中国青年油画群体情况的报告(这一篇报告成就了后来的“八五美术”运动热潮)。在会议结束时的总结报告中,詹建俊先生代表油画艺委会提出了中国油画发展的宗旨——为创立具有时代精神、中国特色和个性特征的“中国油画”而奋斗。这是中国自有油画以来树立起的最为明确和鲜明的目标和旗帜,这个定位对之后中国油画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1994年,根据油画艺术在全国蓬勃发展的状况,原有的组织机构已不能适应全国油画蓬勃发展的需要。我和詹建俊、靳尚谊、闻立鹏、朱乃正、水天中、钟涵、闫振铎、刘骁纯等诸位先生感到,中国油画如果想做更多的事情,就要有专门的学术组织。1994年8月8日在廊坊召开的油画工作会议上,大家一致决定成立中国油画学会,并委托我准备申请材料并具体操办。经过近一年的努力,1995年11月8日,中国油画学会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会议厅正式宣告成立。学会定性为国家一级民间学术团体,成员以油画艺委会成员为基础,之后在全国各地成立省级油画学会。在之后的岁月中,在师友们的共同努力下,举办了一系列全国性重要学术性展览,中国油画学会声名鹊起,成为了中国油画界的著名品牌,共同推进油画艺术的蓬勃发展。
抓学术是根本
我在多年工作中感悟到,一个机构、团体或个人的成功,应立足于国家文化布局整体发展所需,体现民族精神。学术团体和个人必须具有三个方面的素质,即判断力(也就是定位)、坚持力(也就是不畏艰辛地全身心投入)、执行力(也就是能力和实力),学术团体的主旨应该以抓学术为根本,提高国民的精神素质和品格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我所参与的中国油画学会举办的展览,都有明确的学术目的,项目的选题提出先经主席团成员充分讨论,再根据需要召开专家扩大会议,可以说属于集体策展。会议要求每次展览精心组织筹划,找准学术突破点,力求达到全国最高水平。正是由于展览符合专业发展的需要,而在业内产生共鸣,才能具有学术引领作用,从而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1993年,张祖英(左四)参加第二届中国油画年展时与组委会成员在中国美术馆前留影
1986年,中国美协油画艺委会成立后,需要有一个体现中国油画总体面貌的亮相展。于是我们决定在1987年举办中国自有油画以来的首届“中国油画展”。经过努力,得到了上海美协、上海《文汇报》的全力支持,在上海展览馆成功展出,盛况空前,观众达23 万人次,反响很大,影响深远。这次展览第一次打出了“中国油画”的字样,改变了过去俗称的西洋画或油画字样,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中国油画学会之后进行的众多学术性展览,主要分两类:一类属梳理性展览;另一类展览属针对油画发展中倾向性问题的集中攻关。首次展览后,我们认识到肖像画创作是油画艺术中最重要和难度最大的,就于1987年举办了“20世纪中国油画肖像画展”。通过这个展览及学术研讨会,我们对中国肖像油画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梳理,明确了此领域的代表作品和代表性艺术家。面向新时期,油画的未来发展靠青年,据此,我们又举办了“首届中国青年油画展”,以发现青年才俊。刘小东、闫平、喻红、任传文、忻东旺等青年艺术家在参展中崭露头角。这次展览还选出了20 个获奖青年画家,每件获奖作品都有单独评介,并向作者颁发奖金。现今他们都成了油画界的中坚力量。之后,1998年,正值文化部举办国际美术年之际,我们针对风景画的精神文化内蕴需要重视的契机,又策划了“中国山水画与油画风景中外比较艺术展”,与中国画的重要学术团体积极合作,共同探讨东西方对于自然的不同理念和观察角度,同时召开了盛大的“绘画中的自然”学术研讨会。
再如在油画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受社会风气影响,有段时间油画领域超大之风越来越盛,而其中一些作品画面却空泛、简单、缺少艺术依托,影响了油画艺术的深入发展。而我们研究发现,在油画史上有些欧洲的绘画小而精致,同样具有很好艺术效果和水平,并且有利于油画艺术进入千家万户,应该鼓励和提倡画家往小而精上努力。由此,我们先后策划了两届“研究与超越——中国小幅油画作品大展”予以倡导。此外,有一时期,受商品经济影响,也有不少艺术家热衷于使用照片、图像,在画室中闭门制作,替代写生和深入生活,凭空臆造,忽视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感受,这直接影响了艺术语言的拓展,影响了对色彩、造型生命活力的敏感度。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举办了“首届中国油画写生作品汇展”,促进了之后近十年、遍及全国上千位画家参与的写生热潮的形成,以及不少充满激情、生动、鲜活的优秀作品的产生。
特别要提出的是,我们重点策划了“精神与品格——中国写实油画研究展”,为此召开了三次论证会,讨论绘画艺术,包括写实油画,在商品经济影响下如何避免庸俗、商品化、浅层化的倾向,提倡创作中要注重精神性和艺术品格。另外,随着新世纪到来,在国外艺术思潮的影响下,油画艺术发展涉及到当代性思考,而绘画的当代属性怎么体现呢?由于历史上中国油画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缺少现代性的环节,从古典写实主义一下子到当代了,很多艺术家一下子难以适应。为此,2008年我们在北戴河召开了一个由200 位左右的画家、理论家参加的大型讨论会,并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拓展与融合——中国现代油画研究展”,后续还开展了其他一些展览,来促进当代与传统的融合、拓展,努力使油画艺术沿着健康道路发展。就这样,我们有步骤和计划,认真地一步步、一项一项脚踏实地把中国油画引向高处。
我在油画学会工作近20年,在国家没有一分钱拨款的情况下,共举办了三十余个重要展览和学术研讨活动,有力推动了中国油画艺术的进步。当然,举办展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还涉及许多综合性因素,如项目策划、经费筹集、作品征集、运输、保险、安全、宣传、研究、推广等,这期间我也曾遇到过很多困难。比如,在“20世纪油画展”开幕式前一个月,突然得知一年前谈妥的赞助公司破产,原先谈好的150万元一分钱也无法提供,那时候的这些钱相当于现在的千万元。而那时,展览场地已排定,各地的参展作品都已经在来京运输途中了,而有关此事学会中只有我和詹建俊、朱乃正3 人知道。由于展览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实情根本不敢对外公布,否则会出大问题。作为画展的执行者,我们商量决定:就是砸锅卖铁、个人出钱、借贷款也要把展览办好。当时焦急之心可想而知,一向睡眠良好的我,急得一个星期没有睡好觉,多了不少白发。皇天不负有心人,最后通过不懈的努力,经过半个月积极奔走、多方筹集,终于重新落实了大部分办展的经费。又因为展览的高品质,所缺的钱与美术馆协商靠单独卖门票分成补足,展览终于如期举行。在展览的开幕式上,我站在观众后边,眼看隆重仪式一项项顺利完成,展览受到了业内公众齐声赞扬时,不经意间,热泪盈满了我的眼眶,心中说:“多险呀!”局外人看似风平浪静、近乎完美,但内部经历了惊涛骇浪。又如,为保证展出质量,展场的第一、二幅作品是艺术前辈李铁夫的画,但收藏单位提出每张作品的保险费要100 万元,在当时这是天价。为借作品,我三次去广州,最后顶着风险在保费合同上签字。当然我们也采取了严密的人保措施,安排专人坐软卧包厢把两张作品接来、送回,从而保障了展览的质量。总之,这类艰辛困难不胜枚举,如果没有担当的精神,有些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正是我们精诚努力,使中国的油画艺术取得了长足进步,油画作为引进的外来艺术之一,在改革开放旗帜下成为生气蓬勃、团结共进、发展最为迅速的艺术门类不是偶然的。
2010年中国油画学会换届,由于民政部对学会领导的年龄有要求,我和詹先生退出具体工作。根据文化部的要求,国家画院要组建中国油画院,当时杨晓阳担任国家画院院长,邀请詹先生和我第三次白手起家,一起参与创业,组建和开展油画院的工作。那几年,我们主要着力把中国油画已取得的成绩向全世界推广,扩大国际交流,促进中国油画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
中国油画从百年引进、发展成长到“走出去”的确是中国油画家多年的心愿。我们学习油画这个外来画种,在吸收融汇的过程中融入了我们的理想,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通过吸收与融合,反过来再和西方艺术界进行平等交流。2016年、2018年,我们先后在法国和意大利举办了大型中国油画艺术展,反响非常好,为期一个月的展期都闭幕了,公众还不断要求延期。过去欧洲公众不了解中国油画,当看到中国油画作品良好状态与水平后,感到很新鲜,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欧洲油画是从科学、理性、真实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绘画更多地还是着重中国文化精神和其所体现的画外之意、天人合一、境界、诗性表达的情感等。它强调艺术不只是写真而是写心,是以心写境,以境为画,而境由心造,更注重意境的表达,这些对于西方人来说是新鲜的。当时我们选择到国外展出的作品,宗旨就两点:经典性和创造性。所谓经典性,就是在油画艺术语言表达水平上的到位;而创造性,就是要充分体现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境界和文化精神。如果刻意去模仿和跟风,外国人反而会轻看我们。回想某些在国外举办的展览,以为迎合外国人就会受欢迎,外国人想看什么,就拿什么去,这样反而受人鄙视。正因为我们展示的是中国艺术家特有的艺术面貌,才会受到他们的尊敬与欢迎。
我在油画界工作的近30年中,对中国油画发展有一个总体设想。除组织学术展览之外,我还先后参与编辑了三十几种画册和图书,并帮助北京出版社编了一套《20世纪中国油画》。这是一部共三卷六册大型画集,由闻立鹏任主编,我任常务副主编,水天中和尚扬也参与了编辑工作。我们花了一年时间编这套书,基本上进行了对所有20世纪中国重要油画家的研究。
除此之外,我自己写了一些史论文章,形成了系统性思考。我能够弄清楚很多理论问题,也得益于我的创作经验以及在美研所的研究工作。如果不是身处油画发展的宏观视野中进行大量创作,我就感觉不到中国油画的问题所在;而通过论文梳理,能让我更清楚地思考中国油画发展之所需,从自发到自觉,感悟艺术精华所在。一个艺术家的文化素养决定着他艺术水平和品位的高低。有人评价我的作品能随时代脉搏体现精神内蕴,有对作品内在精神的独特思考,这主要得益于我这么多年对油画从感性到理性的思考更深一些,感悟更多一些,这也是我的油画理论与油画实践互为作用的结果。
纵观中西油画发展历程,从行业发展的轨迹中看,欧洲大都是依靠画廊制度的传承,而中国则是依靠国家体制下的艺术机构展现其独特面貌。回顾新时期中国油画的发展,着重于两个方面:除国家对油画艺术的重视之外,一方面,得益于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十六届高研班,把全国青年艺术家及高校青年老师精心培训了一遍;另一方面,是依靠中国油画学会等这些负责任的学术团体的使命感,通过高质量的展览和研究项目,打造了一个高水平的平台,推出艺术家的创造成果。我们为此贡献了微薄之力,并为我们所产生的作用而感到欣慰。

张祖英创作《创业艰难百战多》

张祖英《创业艰难百战多》160cmx150cm 1976年
我的艺术生命才刚刚开始
我的初心还是期望能在促进中国油画事业发展的同时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画出更好的作品,成为优秀的艺术家。我认为艺术家的作品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艺术家精神境界的载体,也是艺术家个人心智和才情的诗性表达,独特性和唯一性是应该追求的目标,从而体现艺术家创造的存在价值,在这方面我有自己的思路和行事方式。

张祖英《卓玛的世界》160cmx130cm 2007年

张祖英《铁匠阿米尔》128cmx102cm 2006年
肖像画是我努力的方向之一。从幼时起,我就对人物的精神、个性特征的追寻有着无尽的兴趣。而在后来的创作过程中,我常常不自觉地会将精神集中到人物肖像表达中去。如我1977年创作的处女作《创业艰难百战多》,这一表现陈毅元帅的肖像作品就是这样产生的。肖像画是油画艺术的高度和难点,我内心希望在肖像画的创作中攀登高峰,攻克难关。为了做好此事,我下功夫研究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肖像艺术大师的经验。另外,我也会仔细分析研究中国几位与我朝同方向努力的艺术家的长短,并力图与他们拉开距离,这样才能展现我的特点。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作品被称为“肖像画”,其中不少其实只能称为人像画。画作不揭示人物的心灵,而只是表象的罗列,不能被称为肖像画作品。此外,我还牢记在上戏学习时的感悟——创作人物作品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经典作品告诉我们,要有取舍,要突出人物精神世界和时代特性,力求使作品达到单纯、凝练、概括、大方的整体效果,尽可能以最简练的手法,展现人物丰富的精神内涵,不能雷同化和概念化。如我在创作《自画像》时,考虑到过去画家自画像大都是正在作画或手拿画板直视观众的,我便根据自己的经验设计了眼望拟作画的画布,手中擦拭画刀,凝神思考的情景,以体现面对画布前的思考。我还力图在背景和全画里力求凝练和总体概括,使作品具有独特意味。如作品《卓玛的世界》取材于青海格尔木一处市场,我在那里震惊地看到一位大爷带着小卓玛的情景,小卓玛明亮动人的眼睛和略带着害羞的神情吸引了我。于是我在画中打开市场遮天的幔帐,把卓玛的形象辅以碧蓝天空和晶莹透亮的雪山,将它们组合成一个圣洁而美好的境界,而形成“卓玛的世界”的就是圣洁世界的美好感情和诗性的表达。又如《铁匠阿米尔》这幅画中的人物,是我在新疆喀什街道铁匠铺的真实所见:年轻的维吾尔族铁匠在繁重打铁间歇小憩,前景人物塔式端坐,注目前视;后景熊熊炉火及铁墩三位一体,组成了一幅表现少数民族铁匠的辛劳的作品,体现出了人性的真实,它是一首劳动者的颂歌。詹建俊先生认为:“这幅作品是我国少数民族题材肖像画当中十分重要的作品,在艺术上是成功的。”

张祖英《岁月》145cmx135cm 1986年

张祖英《流浪艺人》130cmx160cm 2007年
之前我还创作过一系列肖像画作品,如《青年胡适在北大》《祖母》《红衣老人》《今日文小姐·丁玲肖像》《祈福》《锡林格勒乌兰牧骑女员》《啊!蒙古、蒙古》《来自中国的声音——宋美龄1943年在美国众议院演说》《春》等。今后除了继续发现和表现生活中鲜活、生动的人物外,我还计划为中国社会、科技与文化发展中作出贡献的优秀历史人物进行肖像画创作,使他们光辉业绩和高大形象永远留在我们心中,让历史永远记住他们。
我的油画作品另一大类是风景画创作。常言道:“诗言志”,古人评述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其实画境就是诗情,是寓于绘画语言的诗性表达,但在生活和创作中,真正能体味和实际做到却非易事。绘画中的风景不是大自然的重复,这是艺术家触景生情的产物,所以油画风景画通过对自然的表达,体现作者的心声。我喜欢绵延万里的长城和巍巍山岳,喜欢它们孕育着的凝重诗情。在某种意义上讲,山水的精神就是人生应该追求的精神。我在作品中努力寻求诗性的表达,通俗说来就是希望创作如诗的绘画,为此我先后以“古道”“山”“水乡”“梯田恋歌”为主题创作了众多作品。在绘画手法上,我仍然习惯于用写实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但不受客观事物的局限,着力表达精神内蕴。当我不把他们的外在形态作为创作终点而作为起点时,便取得了某种心灵的自由,展现一个现代人对故土的独特情感,从而超越具象视觉的经验并从中提炼出抽象意味,表达出某种现代哲理,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我早年创作的以长城为题材的作品《岁月》,就是这种思维的良好例证。在巍巍山冈上,屹立着坚实的白色城楼;残缺的明月,映照着斜向的城墙。简洁的构图、强烈的黑白对比,营造出深遂的意境,突显出沧桑历史中屹立着的城楼——这一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呈现出强烈的现代意味。这些年来,我的风景画作品还有《血色长城》《夕》《通往林区的小路》《远山的呼唤》《群山之歌》《山之魂》《晨》《朱家角远眺》《阳光下的寺院》《山那一边》《经塔》《暮色中的伊宁街道》《下弦月》《群山初醒》《落日辉煌》《江南春早》等数十幅。

2021年,张祖英与采访者凌晨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自己的创作宣传不多,因为在我周围师友中名家林立,而我对自己又有所要求。2015年年底,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从艺以来的第一次个展,展出了140 幅作品,用了圆厅和后面两个厅,很多人看完以后极为惊讶,问我说:“张老师,你举办了那么多的国家级展览,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你哪来那么多画?而且每张画都那么深入,件件是尽心之作。”其实这些画都是我起早摸黑,挤时间画出来的。在负责油画艺术社会工作的那些年里,我给自己定下了规矩,清晨早早起床,一直画到11 点,下午处理各种事情,法定假日和休息日都是我创作的时间。我比别人更加刻苦用心,因为我很明白,个人专业水平不上去,从事艺术组织工作就无影响力。必须要有好作品才有发言权,不深入绘画的堂奥,就难探寻前进的方向,所以我对每一张创作都悉心深研。虽然社会工作多,创作时间少,但我努力画一张是一张。质量是水平的标志,同样具有价值。以前周旋于创作、研究和学术推广三者之间而不能专注于我所钟爱的艺术创作,我深感遗憾。而今,我终于卸下了许多工作担子,可以“不忘初心”地全力以赴创作自己想画的作品。
回顾以往,我一边从事油画创作,一边从事油画理论研究,同时还利用大量时间从事油画学术团体工作。创作、研究、艺术推广三位一体,互相融汇,互为因果,互为促进,形成了我一生艺术轨迹与众不同的特性。如今我的人生已走过了大半,我觉得我的艺术生命是丰富多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