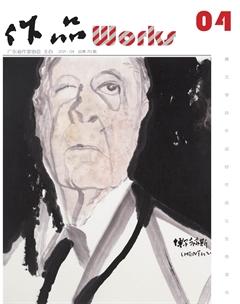只是朱颜改(短篇小说)
葛芳
歐阳点了一支烟,一支口感清凉的金陵十二钗。
不知道谁昨晚塞在他包里。他烟瘾犯了,胡乱一掏,就逮着抽了。
孩子们排着队像一群鸭子在老师带领下嘎嘎嘎欢叫着走出校门。他穿过校园香樟树林,肩上披着的棕色风衣扬起来,给他一种错觉——永远是上海滩的许文强。孩子们经过他的时候,把手举得高高行了个队礼,“欧阳校长好!”他露出黄渍渍的牙齿,微笑点头。校门口停满了车,家长们探头探脑,都是老面孔了,他一一挥手示意,细长的烟杆咬在嘴角。
这校园太他妈熟悉了!镇上唯一一所中学。他爬过河边的老榆树,掏过鸟蛋,也骑在树杈间复习功课。上大学后他又回到这所学校教书,从团委书记到副校长,亦步亦趋跟在校长后面。后来,中学搬到了新址,这儿变成镇上的中心小学,他接到教育局调令,成为中心小学的校长。
早上,他在卫生间待了很久,便秘。
拉不出,实在是件痛苦的事。要命的是他还犯痔疮,一不小心,滴滴答答内裤上沾满了红色的血迹。便秘和痔疮是相辅相成的,医生说,最重要的根源是长期饮酒。但要他戒酒等于要了他的命。孰轻孰重?他总结道,没有酒的人生是苍白灰暗的,就像生活中没有女人。
他来到校园花圃,这里挤挤挨挨长满了虞美人。
负责花圃的老赵不知道溜达到哪去了,水壶闲置在栅栏口。
他又抽了根金陵十二钗,细长的烟夹在手指尖感觉有些怪怪的,女士烟,昨晚饭桌上有几个做生意的女老板,装文气,当然烟也不算贵。他俯下身子,虞美人的单瓣花娇羞可爱,挺直了腰杆在风中摇摆。自从当一把手后他让老赵把所有花全部改种成虞美人。红的,紫的,粉的,黄的,一朵朵,在风里娇柔盼望。
改种虞美人的原因很简单,他喜欢李煜的词。李煜作为南唐后主,非常喜爱各种奇花异香。他看过一段史料:“庐山僧舍有麝囊花一藂。色正紫,类丁香。号紫风流。江南后主诏取数十根植于移风殿,赐名蓬莱紫。”
因为李煜的《虞美人》,他开始效仿,他不可能种丁香类的紫风流,而是让花农撒下很多粒虞美人的花籽。一到春天,蓬蓬勃勃开得校园里特别有生机。教育局长莅临检查学校工作时,连连夸奖校园美化做得有特色。
新来的女教师们眼神明亮,仿佛阳光下透明的黄色虞美人,一个个欢蹦着过来。基本上都是他以前教过的学生。在这个校园里,他好像就是一个老人,背着手踱步,看着学生一茬茬毕业,新教师一个个上岗,见证着岁月变迁。
当然他并不算老,才五十三岁,身体健硕,雄性激素分泌旺盛,若不是痔疮在提醒他生活中偶有不顺,他觉得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镇上的领导昨天下午和他正式谈过话了,七月份整个乔平城教育系统要重新调整干部,他可能要升职到局里。
小镇在夜晚最沸腾。
学校门口空地上聚集了广场舞爱好者。“澎擦擦”“澎擦擦”,音乐声怀着激荡与美好震耳欲聋,要持续整整三个小时。周围的居民实在忍受不了,去政府大院举报。作为校长,欧阳没提反对意见,与民同乐嘛!你看浩浩荡荡的队伍在聚拢,又分散,男男女女一对一对,多开心。他摇下车窗,和欢欢喜喜的男人女人挥手示意。
有人约好了麻将,三缺一。对了,麻将、酒、女人,三样是他挺喜欢的,不分排名。搓麻将他也不搭架子,普通教师喊他随叫随到。一屁股坐下来,就有香烟递上,一战会战到深夜十二点。好,不超过十二点半,这也是他的原则,明天还要上班,赶紧各回各家,洗洗睡了!
今晚是周末,已经六点了,他仍旧在学校花圃旁转悠,他有些心神不宁。到局里做领导意味着他可能会调任教育局副局长,那是副处级干部,管辖范围也不仅仅是一个镇,而是乔平城七个乡镇。
手机铃声响了,是多年的赤卵兄弟邀约喝大酒。那人承包了镇上整个医院,踌躇满志。当今社会,医疗、教育是民生最关注也是最赚钱的。
果然一桌子男人黑压压的,十个弟兄,交往深的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前,穿开裆裤时候就玩在一起要不怎么称赤卵兄弟呢?“欧阳!欧阳!”他喝了多少白酒?早已混沌不清。晕晕乎乎间,开始转换场地了,叫了代驾,急速飞驶,一直开到乔平城最昂贵的娱乐场所摩巴萨夜总会。
他已沉醉。他喜欢这种云雾里缥缈的感觉,或者是醒来后啥也记不起,断片了,仿佛他置身事外,什么也没有参与,只是沉沉睡了一觉而已。人生很多况味就在这里,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似快活非快活,似痛苦非痛苦,没有定论。他眼皮沉沉耷拉着,从缝隙中他好像看到有一片虞美人在风中摇摆,红的,黄的,粉的,紫的,怯怯的,全都娇羞可爱……
“要来片西瓜吗?”一个小女生低弱、温柔地问他。
他大概意识到他是趴在她腿上,她的裙摆低得根本遮不住大腿,她的大腿根部发散着虞美人种植在泥土里的气味。他好像看到一副纸牌,一朵压在书页之间的虞美人,一个钥匙环,一张有红头文件的公函,一个男孩万花筒中的对称玫瑰……灯光逐渐在黯淡,渡轮在发出呜咽似的鸣叫,今夜喝的酒好像不是太纯正。上头。晕!晕得比便秘还要糟糕。他看见了红色,白色被单上的红色,是他的痔疮又犯了!犯了就犯了,他也无暇顾及。
门开了,冲进来一拨人,耀武扬威的。去去去!他捏住女孩瘦弱的肩胛骨,校园里花圃旁的秋千在晃荡……
他醒来,探照灯刺眼,直射他脸上。
两只飞蛾盘旋着向上飞舞,他不晓得时间。手机也不见了,厚厚的镜片夹在鼻梁上,歪了。他迷迷瞪瞪,不清楚身居何处,旁边是两个穿警服的人员,他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候他醒来。
他是醒来了。他压根儿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真是断片,醉得一塌糊涂,悚然间他被惊吓到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警员三十多岁,圆乎乎的脸蛋,应该曾经也是他的学生,只要是本地人,绝对是在他国旗下讲话稿中熏陶长大的。警员咽了下口水,怀着坏笑,说,“欧阳校长,你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茫然,有种秩序被打乱以后的恐慌。
“——嫖娼,而且你的性質最严重,你,嫖的是,一个十七岁的未成年人!”
“靠!”一股热血直冲头顶,欧阳前后摇晃了几下。便秘的感觉又来了,他的脸形扭曲得夸张,一副吃了屎的样子。他隐隐约约记起女孩瘦弱的肩胛骨、低弱温柔的声音,她的裙子太短,她的呼吸太细……他是摸了,亲嘴了,但好像没有真正开始做事。他拼命摇头,喉咙处干涩,他需要一粒青梅来润一下,一种深色、小巧、椭圆的梅子来清凉滋润下。他提了这个要求,圆脸警员傻乎乎地盯着他的欧阳校长许久,然后告诉他:“没有,没有青梅!”
他自己都觉得荒唐。环视了一周,发现派出所的墙上有只蜘蛛在耐心织网——他渐渐恢复了意识,他咳了一声说:“你们殷所长呢?我要找他!”
“不好意思,”圆脸警员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所长不在,这次行动是上面统一部署的,抓你的也是其他镇调配过来的民警。你的名字已经报到市公安局,所以,你找所长也没有用。”
蜘蛛的一只脚垂下来,它大概有八只脚吧,以前他代替其他老师上科学课时,有学生很顶真地向他请教。他嗯了半天,吞吞吐吐地说道:“八只吧!”幸亏没有误人子弟。
他有些愕然,怎么是上面行动,上面怎么晓得那时他恰好在娱乐场所呢?
接下来就是冗长的审讯、笔录阶段。
要命的没完没了的时间段。他的意识在一点一点收回,在聚拢。最后,他哭丧着脸强调:“我没有,……我没有碰她,……这是关键,我没有伤害到她……”
“可是,欧阳校长,被单上有血迹……”圆脸警员学会了狡黠。
“那是,我的血,痔疮犯了!要不脱下我的内裤你瞧瞧……”他颜面丢尽,这小家伙哪一届的?竟敢如此揶揄作弄他。
“可是,她说,你做了!欧阳校长!”小警员极力还原事实真相,带着求证数学题的快感,带着少许的幸灾乐祸。
他在拘留所待了五天。
这五天度日如年。不晓得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深夜,窸窸窣窣下起了雨,空气很闷,他想去摸烟,可是对不起,囚禁的人一无所有,只能眼神空洞地盯着天花板。已经发生了无法想象的事情,那就硬着头皮顶上去,船到桥头自然直,这是他的生活哲学,总有解决的办法,只要出去,离开这鬼地方,他就能联系到一些重要人物——
雨下得更大了,“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背些词吧,他中文系出身,词在脑海里可以随时拿出来一首首温习。不知道那十七岁的小丫头何时冒出来的?仿佛孙猴子无中生有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个小姐,不是他点的,肯定不是他点的,他喜欢丰腴的成熟女人。——十七岁,这么小,不好好读书,为什么出来做这种?这世道是乱了。他躺倒在拘留所简陋的床上。想哭了。他做的糊涂事。他和李煜一样沦为阶下囚,没有自由,没有语言的申辩权利。他闭上眼睛,想象正在洗一副牌,“东东东东南南南南西西西西北北北北中中”,四副风牌都来到他的麾下,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了。他想,会时来运转的。
为什么要喝到断片?
他妈的市公安局怎么会有指示?他想破了脑瓜也没有答案。是他得罪了谁故意要整他?还是太过张扬,遭人羡慕嫉妒恨——于是有人举报,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前不久一个孩子拿着偷来的吹风机,包了糖渍橘片的蜂蜜面包,在镇上的巷子里拼命奔跑。他问那孩子:“为什么偷?为什么跑?”孩子舔着手指上残留的糖傻呵呵的就是不说话。
没有原因,就是没有原因啊。
他没有碰那女孩,他们为什么不相信?他都可以当她爷爷,这点羞耻心他还是有的。可能若干年前,她系着红领巾从校门口向他行队礼,他打了个哈欠回应。她像千万朵虞美人扬起小脸蛋在校门口嘁嘁喳喳喊“欧阳校长”,他振作精神,挥手,他最喜欢挥手了,简洁无声。他想他们真的弄错了,这一点他务必要申明。他伸展四肢,有气无力,床板太硬,他看见那只蜘蛛,仍锲而不舍劳作着。他摸摸自己心脏,跳得时缓时急,窦性心律不齐,最近几年体检一直是这个老毛病,他问过医生,没什么,不会有大碍。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吃早饭,身上有隐隐作痛的感觉,是他睡姿不对,腿怎么搁怎么难受。圆脸警员呼喝他:“欧阳,过来签字!”他尽量让自己平静,不要紧,他对自己说,所有的秩序会恢复原样。
圆脸警员说:“叫家属也来签字,交罚金!”
他迟疑了下,央求着:“能不能让朋友来签字?”
圆脸警员念在当年老校长的分上,答应了。他拨了约他喝大酒的人电话,无人接听,拨一桌子赤卵兄弟的号码,都没有人回应。都人间蒸发了吗?为什么他被逮到局子里,他们却毫发无损?这不对呀——难道说多年兄弟还会给他下套?
——这不可能,完全不符合逻辑。
他没有办法,拨打老婆电话。圆脸警员凑上去把事情原委说了一番。老婆含糊地嗯了几声,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挂了。半个小时以后来了一个陌生女人,走路哆哆嗦嗦,说是欧阳的老婆委托她来签字交罚金的。
这事还有委托?警员乐了,办完事以后他朝欧阳手一挥:“走吧!”
阳光蜇人眼睛,他努力迎接,大踏步走,他想他应该先回学校。
他的棕色风衣揉得皱巴巴的,而且胡子拉碴,很不体面。他转念想,要先回家拾掇拾掇,五天没洗澡,他都嫌弃自己身上的馊味了。他打邀约他喝大酒的人电话,不通。再打其他人手机,忙音。没有车,问题不大,从镇上步行到家里也就十五分钟。路上没碰到什么熟人,这个点,大家都在单位上班了。路边香樟树飒飒作响,风一吹,树叶哗啦啦掉在他蓬乱的头发上。
他想,没有什么,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
小区的保安懒洋洋地在打盹。狗也在打盹,三四条,漫不经心躺在路边。他绕过花坛选了一条捷径走到家门口。心跳莫名其妙快起来,他努力控制好。钥匙插进孔里,“咔嗒”一下时,他肛门坠胀,可恶的便秘感又来了。他不知道家里是否有人,径直冲到厕所,坐到马桶上正想用力时,却又空空如也。哎,他深沉地沮丧着,面对精疲力尽的自己无可奈何。
他提着裤子出来,阳台上芍药花开得很粉,他不晓得老婆去哪里了,对呀,她应该也在上班。她是社区里专门负责后勤的,腰里别着一串钥匙,大小物件都要经她手置办,单位是离不开她的。她今天来不了派出所是有原因的。
他嘘了一口气,拍了下后脑勺,和衣在柔软的床上小憩了十分钟。是他太敏感,一切,应该还是按部就班的,那件事,仅是个误会,对,他会澄清。他要神清气爽出现在众人面前,穿着风衣,对,换一件褐色风衣,欧阳校长,还是欧阳校长,没有任何变化,而且过几天,可能要改口,称呼他欧阳局长。
洗完澡,他拨电话给办公室主任,想了解下学校动态。
无人接听,估计在上课。拨副校长手机,忙音。再拨另一个副校长,也是忙音。“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结结实实的嘟音让他听得脑子也发胀,他艰难地咽了下口水,好像都人间蒸发一样,或者说他们达成了某种协议?粉色芍药在花盘中微微点头,不知从哪里飞来一只鴿子在阳台上盘旋片刻后,“噗”轻松拉了坨鸟屎转身而去。
天不会塌下来的。他嘀咕了一句,很像在自我安慰。
保安醒了。狗也醒了,竖起耳朵看着他,很警觉的样子,他尴尬地递上一个笑容。保安没笑,但也没有特别的表情,春天总是这样,让人慵懒,让人麻木。
他劝自己别胡思乱想了,努力克制自己无限蔓延的不切实际的念头。那女生散发着虞美人种植在泥土里的气息,千朵万朵的虞美人在等待欧阳校长归校,他要放轻松。六一节快到了,孩子们要在镇政府的剧院里汇报演出。读唐诗,读宋词,现在是全民朗读,《虞美人》这首词意境甚美,彩排效果相当不错。他懂一些风雅情调,因此也能恰到好处推一些别致的活动。到了教育局,他想,会更加如鱼得水,他要从提高全民素质入手,着力培养孩子们的人文气息。
快到学校门口时,他却折步而返了。
他的手机是开通着的,却没一个人打电话给他。
这种安静让他窒息,他想,不是别人蒸发了,而是他被世界屏蔽了。他不晓得是不是所有员工都知道他们领导去嫖了一个未成年少女,照理说,这是个人隐私,派出所无权通报单位的。他已经被罚了一万元,被拘留了五天,相应的惩罚他都认了,还要让他怎样?
走得急,脑瓜子上全是汗。心跳得忽慢忽急,仿佛有不着边际的恐慌感。攥着手机的手心也全是汗。风衣里衬衫也湿湿的一层。他晓得,是冷汗,一阵眩晕突袭而来,他只能在路边香樟树下坐下来。
迎面走来一个神经病。他认得他,他叫振兴。振兴穿着一身黄军装,左手拿一把油布伞,伞骨很结实,撑起来可以遮盖住一辆小三轮车。振兴走起来虎虎生风,那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很像阅兵场上接受首长检阅。
痴振兴双手摇摆幅度很大,他一只手紧握拳头放在胸口。痴振兴原来也是高才生,高中毕业去老山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立过功,没想到,复员两年后,就神经病发作。
欧阳讪讪地,想给他一根烟。没想到振兴挥手拒绝了,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六十岁的老人,嘴巴里喷出一股血脉鲜活的气息,他喘着气,像牛在反刍,叽叽咕咕,是嘴巴里发出的声音,还是胃里发出的声音?
他向欧阳敬礼,腰杆挺得笔直。欧阳晓得他发疯的原因,为了一个女人呗。他原有的对象在他当兵期间,陈仓暗度,和别人谈起了恋爱,生了孩子——破坏军婚是犯法的,他立在空阔的街道上,远远地喊叫:
“都是坏人。”
“全是胡椒也辣不死人!”
欧阳挤出一丝笑容,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笑了,他敬重这位老人,他真的一点不见衰老的迹象。他的神经病也是间歇性发作。他不发作的时候,抿着嘴唇,脸部轮廓硬朗,英挺,帅气。可是一到上午十点钟,他就控制不住他的脚步和嘴巴,他抓上黑油布伞,咚咚咚咚出发了,犹如一枚上膛的子弹,直抵政府大院目的地。他嘴巴里冒出来的话也像机关枪里射出来的,“嗒嗒嗒嗒”,可是前言不搭后语,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些什么:他妈的——东娘亲——海里的松鹰——卡子门立——
“欧阳首长好!”振兴今天的状态非常好,声音洪亮。
“好,好!”欧阳忽然有种热泪盈眶的冲动,他把振兴老人的手紧紧握着,他想,够了,这样足够了。
他在寂静的午后恍恍惚惚睡了一觉。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他结结实实睡在自家床上,可终究睡不踏实。
终于,下午三点,他接到了镇办公室的电话,要求到镇政府参加紧急会议。“紧急”两字,如快速旋转的警示灯,不由催人慌乱。他火急火燎赶到政府大院时,天色暗沉,刮起了大风,天气很坏、很坏。他似乎在梦游,走过传达室、长廊、楼梯,到达二楼的会议室,满满一屋子人等着,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在等他。主席台上坐着区教育局领导,镇上四套班子,该来的都来了。他脑袋轰轰作响,杯盖掉到了地板上,发出“哐啷”清脆响声,话筒里传出的官方语言沉闷严肃但有不可违逆的压迫性。可恶的便秘感再次袭来,他的脸憋得青紫,摇摇晃晃,他半屈膝猫着腰挪到卫生间,厕所里很不洁净,他想,卫生工作都没做好,还搞什么接待?
阴霾天气,他透过玻璃窗户长长地叹了口气。提好裤子回到会议室时,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身上,如千万只马蜂攒聚过来,张牙舞爪,要对着他皮肤狠狠蜇一口。他可怜的腿在无助地颤抖,没用,它们还在飞过来,一波又一波,要把他蜇得全身浮肿、面目全非。小时候顽皮的他真被马蜂蜇过一次,而且蜇在小鸡鸡上,整个夏天他光着屁股躺在藤竹椅上。“自作孽,不可活!”母亲摇着扇子嗔怒拍打他身旁的蚊蝇。他想,如果母亲还活着来给他挡掉这些要人命的马蜂该多好啊!他的心脏“怦怦怦”地跳得也够激烈了,他的胸腔显然不够容纳了,他的身体快要失去平衡了,但他必须牢牢稳住,在众人推墙的瞬间,他必须要稳住。
好了,会议终于结束了,简而言之,宣布了一条内容,那就是他被开除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又到放学时候,孩子们排着队像一群鸭子在老师带领下嘎嘎嘎欢叫着走出校门。
风很大。欧阳的风衣被风吹得飘起来。风暖融融的,其间也裹挟着一股股寒气,吹到嘴里已经有了雪的味道。有只猫时不时停住步子,转动着脑袋,窥探着他这个黑乎乎的身影。是只流浪猫。欧阳不晓得该嘀咕什么了。他脑子很乱。他想睡觉。当然,他妈的纯粹意义的睡觉。他完全走乱了方向,走了多久,他不晓得。
还是没有人电话他。
老婆,儿子,都没有一个电话。
儿子在镇上农业银行工作——是他欧阳花了二十万给谋到的肥缺。
——出差了吗?小镇屁大的地方,这个时辰估计谁都晓得小学欧阳校长的丑闻了。儿子天生是个胆小鬼,一碰到事情就把头藏在沙漠里的鸵鸟,只等着老头子擦屁股。现在老头子屙屎了——满屁股都是,没人来料理。
他的风衣上沾满了树叶的野味。他一脚东一脚西穿过了一片墓地。安息堂。他晓得,他的父亲长眠在那里。若干年前,父亲送他到市里读师范学校,裤脚管都是泥巴,父亲不嫌丢人,晓得儿子跳出農门一辈子可以吃皇粮了。父亲死于胃癌,掏了钱也治不好的绝症,父亲摇摇手不要他花这样的冤枉钱,说:“你带我去趟北京毛主席纪念堂看看毛主席我就心满意足了。”他真这样办了。
光秃秃的平原上是一片孤零零的矮树林,投出一个巨大的阴影。他想,走吧,回家吧,可能什么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他在胡思乱想,压根没有什么十七岁的小婊子——没有,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审判——既然是错误的,一切还都会翻案。
月亮正在落下。空气里有一种焦煳味,像是电线老化后自燃的味道。但这是在野外。是他内脏器官自燃的气味吗?胡扯了。他听到了水的沸腾声。老婆放在客厅里的自鸣水壶不知叫多久了。她捂在沙发里睡得死死的。这是个心宽体胖的女人,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豁达——她不会嫌弃嘲笑他的,不仅如此,而且会为他据理力争,他还是欧阳校长,一辈子的校长。欧阳用自己的后脑勺感受着黑夜中的空气,后脑勺变成了地球仪的顶端。北极、南极?无所谓。他的身体感觉到冰、水、山峰、土地的几重界限。
他于幽暗中好不容易摸索到家。
他瞅见院子里七零八落丢满他的衣服、裤子。一件他最爱的褐色风衣,从德国买的,飘在石榴树枝丫间,像一块充满油渍污垢被丢弃的灶台布。
第二天半夜,欧阳想从自家阳台上跳下来。
左脚抬到栏杆上时,他忍不住号啕大哭。结果,左邻右舍纷纷亮起了灯。他被强压着回了房间。现在他成了寄生虫,既不能自食其力,还尽给家人丢丑,他希望自己变成卡夫卡笔下的那只大甲虫,慢慢地慢慢地,身体各器官病变腐烂然后悄无声息死掉最好。
夜,漫长,漆黑。他确定自己没做那丑事,但已经摊上了,就永远绕不过去了——不晓得他的褐色风衣是否已经风刮走,如果没有,他需要它覆盖在自己逐渐冷却的身体上一起推进焚尸炉。
第三天傍晚,他打开门,关上,右转,又折回。打开门,走进房间,翻抽屉,抽屉里有他许多的荣誉证书。他一本一本取出,然后掏出打火机。化为灰烬后,他又打开门,左转,飘飘忽忽走了十里路。他什么也没想,像发了高烧在梦境里游走的人。撞了树不管。他瞥见了一个女孩的脸,清秀,头发染成黄绿色,怪里怪气的颜色。他用微小到不能再微小的动作,朝女孩傻笑了下。继续游走,梦境越来越诡异,天空中布满了火烧云,马呀,猪呀,土鸭子呀,乌龟呀,都上了。他一不留神摔倒了,闻到了泥土的气息,虞美人的气息——他嘤嘤嘤地哭。女孩又在他不远处闪现,他知道自己丢人现丑了——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不能丢的呢?他定定地,女孩的脸似曾相识,以前的学生?极有可能。他想,随她看吧——人,走到最后,颜面丢尽,生不如死。他甚至故意将一把泥土往嘴巴里塞——苦涩得说不出味道溢满全身。那女孩仓皇失措地奔跑开去,瘦弱的肩胛骨像富有冲击力的铁掌直击他的视网膜。
第四天上午九点。
他接收到了一条莫名其妙的短信:新来的领导说了,明天把校园花圃里的虞美人全部铲掉,换种一些普通的月季、美人蕉。
他原本想死了算了的人,接到陌生短信后,热泪纵横。他没有去追问谁发来的短信,重要的是这条信息十分关乎他内心——那上千棵虞美人明天要被连根拔起。他坐在窗前想了很久。上午的光线很玄妙,射进来,反弹在衣橱的镜子中,照出一个颓废的垂着两鬓发白脑袋的男人。
他想,他不能这样坐等上千棵虞美人被戕害,这是他种下的,要不,依旧是他去收走它们的身体和灵魂?这似乎最合理。
他想得血管都快爆裂了。嗯,他洗了个澡。他觉得他一个人干不过来的,这么多活,学校最起码有三十个小花坛,有六个大花圃,他得找一个帮手——很快他想到了最佳人选痴振兴,他没有他电话,但不要紧,每天上午十点,痴振兴会雄赳赳气昂昂带上黑油布伞,咚咚咚咚出发,犹如一枚上膛的子弹,直抵政府大院目的地。
离十点还有二十分钟,欧阳立马收拾好上路。春日的阳光不强,热乎乎的,这个无关紧要的光源跟随他快到区政府门口时,他堵住了痴振兴。
“欧阳首长好!”
他招手把痴振兴约到树底下。树叶纷纷落在他们俩头发上,像鸟儿停泊在黑乎乎的沼泽水滩里。他们一拍即合,几乎不需要思考或犹豫的时间。说好后各自分散,如同两个地下党员会晤后立即装作不认识的样子。这个效果很不错,有戏剧色彩,欧阳瞬时乐了,回去的路上和一只流浪猫逗了很久。它在灌木丛里弓着背,浑身毛发奓起。
夜晚,学校门卫在看电视,欧阳和痴振兴轻轻松松潜入校园。他们准备把所有虞美人拔起来后放入蛇皮袋。这上千棵虞美人攒聚在一起后,他要给它们弄一个冢,也就是坟墓,他比画给痴振兴看,一定会很高,像农村那时候将收割的稻子一捆捆摞起来。美人冢,有香味的美人冢。振兴点头,竖起大拇指。
花圃中的成片的虞美人楚楚可怜,挺直了腰杆在等待欧阳,等待他的救赎。
月光在自然奔涌着,银色的光芒洒落在各种颜色的虞美人花枝上,恬静空旷。欧阳不着急,点了一根金陵十二钗,不知怎的,就喜欢上了这口感,特地去超市买的。他感觉是在梦中,在金色原野上,他不孤单,也忽然没有了前几天面对无可更改的世界终结时的恐慌。风在呼呼作响,仿佛在不断变换着方向的空寂。
振兴在催他了,说:“首长,动手吧!不然敌人要追上来了。”
“嗯,不然敌人要追上来了。”
他回应了声。
于是,撅起屁股,拿出年轻时干农活的蛮劲,三下五除二,发了疯似的一声不吭劳动起来。有两只鸟儿飞过,啁啾了几声。这声音带着可怕的诱惑力,使得他的动作愈加生猛。伴随着一种急促而刺激的快感与战栗,他发现他的痔疮开始发作。血顺着他的裤脚管,如同蚯蚓一路蜿蜒而下。他管不了这么多。他想,他要把这个美妙的眩晕感还给这个世界,让他们晓得——他是一个慈祥、爱着孩子、爱着学校的好校长。
强劲的风来了,开始还是小的,怎么说大就大了。
他不管。
他用两只手,揪起一把又一把的虞美人,连根拔起后直接塞进蛇皮袋。他的手掌心满是植物的清香和泥土的味道,还有一种说不清的混杂的腥味。该死的,他的脑海里晃过了十七岁女孩的面孔,瘦削的尖脸蛋,至于眼睛鼻子他压根也想不起是怎样的。他的脸怎么就蹭着她了?但是他肯定没有碰她,他摸着良心保证!她就是他孙女辈的,那么柔弱。——她在暗处跟着他吗?昨天傍晚时分,在树后闪现过的脸就是她吗?她为什么要仓皇奔跑,像只土鸭子?
树叶在风里打着转转,落在花瓣上。流浪猫爬到树上,胡子翘得老高,它生气了。它生气什么?发毛奓起。他差点把它抱回家。可是它凶得离谱。
他已经整了十个花坛了,双腿酸疼,肛门处肿胀得无法忍受,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奋力脱离他的身体。无所谓啦,人就是这样衰老的,一个又一个器官开始病变,他完全泰然处之了。他听到远处隐隐约约的音乐,手风琴的声音,幻觉吗?不是的。读中师的时候,他是拉手风琴的高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乐曲悠扬沉醉——“长夜快过去天色蒙蒙亮,衷心祝福你好姑娘,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
音乐越来越近,撼动着他的心脏,他听见振兴在声嘶力竭大叫:
“首长,快跑啊,敌人追上来了!”
他晃了晃肿胀的肛门。他一点也跑不了。几十把手电筒里射出的雪亮光线齐聚在他身上,仿佛无数把尖刀要把他就地刺死。他晃了晃肿胀的脑袋,终于看清,是镇上联防队的年轻人们。一二三四五,他眯缝着眼,一路数过去,啊,都是从他手上领过毕业证的娃啊!当然还有那圆脸警员。
他回过头,对着振兴,一板一眼说:“敌人上来了,不能跑,要迎头抗击。”
“都是坏人!”
“全是胡椒也辣不死人!”
振兴大吼了两声,操起随身带的黑布伞伞柄,直击圆脸警员,幸亏圆脸警员躲得快才逃过一劫。
欧阳没有想到,万万没想到,痴振兴的力量和速度如此迅猛——岁月根本没有从他身上夺走过什么——而他自己,朽木一截,那蹲在花坛上的双腿麻木得完全不属于他了。
他听见“咕咚”一声。
什么东西,像一个冬瓜,栽倒在了花坛里。啊,那些多姿的虞美人,严严实实覆盖住了他的鼻子和嘴巴。只剩眼睛依稀还能看见,那花秆轻盈地摇动着花朵,在银色月光帘幕的包覆之中,向远方伸展。
那个门卫,四十岁的门卫,当年欧阳亲自招聘过来的保安走过来,结结实实踹了欧阳一脚,他說:“他妈妈的——竟在老子的眼皮底下溜过!”
痴振兴一个恼怒,又爆发出口头禅,他已被几个联防队员牢牢擒住。
“都是坏人——全是胡椒也辣不死人!”
“都是坏人——全是胡椒也辣不死人!”
欧阳被门卫踹了一脚之后,因便秘而长久以来的憋屁竟在那一刻畅通无阻放了出来。
在柔软花瓣的抚摸下他渐渐沉静下来,仰面望着树梢上的天空,他忽然想通透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所有的一切,都是个屁!
他的思维又开始游走,晚风凉爽,他像是躺在童年的树底竹凉席上,父亲养的鸽子停在旁边,它的羽毛摸起来有点滑湿。他抱起它,紧贴胸口。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