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菌、基因与文明——传染病如何影响人类社会》
[英]戴维?P. 克拉克 著
邓峰 张博 李虎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0.10
[英]戴维·P. 克拉克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博士,曾先后在耶鲁大学与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81年进入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现为该校微生物学系教授。他不仅关注微生物学和公共健康方面的研究,更注重从长期角度考察微生物对人类个体和人类历史的塑造。主要作品包括《通俗分子生物学读本》《生物技术》《病菌、基因与文明——传染病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等。
本书着重探讨了两个主题,一个是传染病对人类基因的自然选择,每一场传染病的暴发都会导致人口减少,同时,疾病对人类基因的选择也在发生;另一个是传染病是如何塑造与改变人类历史的,罗马帝国的兴亡、基督教的兴衰、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与清教运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背后都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由病菌导致的传染病流行。
5世纪初,阿提拉麾下的匈人横扫欧洲,他们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世间曾经最伟大的文明,罗马帝国,此时风雨飘摇。再狠狠来上一下子,它就要分崩离析了。但诡异的是,就在即将摧毁罗马之际,阿提拉撤退了。这是怎么回事?
许多个世纪里,官方解释都说是上帝在冥冥之中保护了教廷所在地、上帝之城罗马。直到近现代,这类超自然的答案失去了魅力,这个问题才再度浮现出来。有人说,是罗马的神圣震慑了阿提拉。那么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异教徒统帅要敬畏一个基督教中心?阿提拉不是什么无知的野蛮人。他曾邀请罗马和希腊的工程师前往匈人领地安装盥洗设施。他对罗马文明的尊重显然是基于现实主义而非宗教的。另一个理论是,阿提拉害怕无人照管自己位于现今匈牙利境内的新国土。那他为什么要大老远跑到罗马去,晃悠了好一阵子才返回?无论怎样,所有解释都基于同一点,那就是阿提拉确实应该是抱着征服罗马的念头出兵的,只是最后半途而废。
越来越多的现代证据表明,阿提拉是折戟于一场严重的流行痢疾,或是类似的疾病。他的多数将士病得无法骑马,还有大批士兵死亡。一句话,救了罗马的是细菌。古人不知道有细菌这种东西存在,所以多数古代文明相信,流行病是天神们表达自己不悦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圣经》中,瘟疫通常是对恶行的惩罚,被罚的对象既有违逆上帝指示的以色列人自己,也有外来的侵略者。例如,一场流行病把圣城耶路撒冷从亚述入侵者手中拯救了下来——这仿佛是阿提拉罗马城下退兵的预演。于是,上帝拯救罗马这种早先的解释被现代科学重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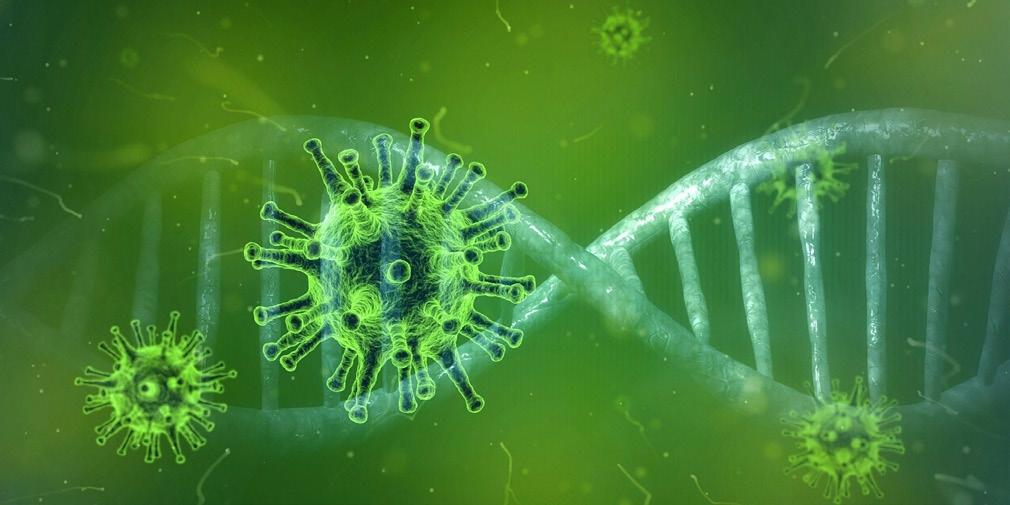
在急于把细菌登记成罗马的荣誉公民之前,我们还要考虑事情的另一面。阿提拉能进军罗马,一个主要原因便是早先发生的瘟疫让罗马败落到了这步田地。在匈人冲进欧洲之前,罗马就已经历过数次灾难性的流行病。所以,这些微生物到底站在哪一边呢?
今天这个时代,洪水、地震、火山爆发都被视为“天灾”——至少保险公司是这么想的。这种说法暗含的一个意思是,无论是受害者,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需要为灾难负责。这其实是不诚实的说法,执意要把家安在洪泛区或是地震带的人,至少是有部分责任的。类似的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流行病不会随时随地、平白无故地落到某群人头上。无论是席卷罗马的瘟疫,还是战胜阿提拉匈人大军的病灾,都不是随机暴发的。更重要的是,两者的来源是有关联的。
在阿提拉之前,罗马也曾侥幸逃过蛮族部落的劫掠。有那么几次,看起来罗马人已经穷途末路了,但他们总能逃过一劫。这里自然有罗马人自己的功劳,他们有非比寻常的坚定意志,不会轻易投降。不过,悄无声息、无影无踪的微生物军团的功劳也不应被忽视。今天的我们不难理解一个过度拥挤、缺少卫生设施的古代城市为什么会持续暴发瘟疫。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疾病会如此频繁地插手战事,在一次又一次的蛮族进攻中保护同一座城市。

我们不妨想象一个正走在城市化之路上的古代社会,比如巴比伦、雅典或者罗马,这种扩张中的城市会有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规模远远大于周边的群落。就传染病的传播而言,通常传播效率在拥挤的城市要比在人口稀疏的村庄和偏远地区更高,所以城市出现瘟疫只是早晚的事情。届时这座城市的人口会大幅减少,而且在一段时间里它会易受攻击。但如果这座城市能恢复元气,它的大部分人口就对同样的瘟疫有了抵抗力。换言之,率先对当地某种传染病形成抵抗力的是更为密集的人群。等战乱再次爆发的时候,调拨的军队和迁徙的难民就会在战区四周散播传染病。和城邦相比,乡村或小城的人群抵抗力较差,所以瘟疫总是站在大城市那一边。
一旦某座大型城市遥遥领先于其竞争对手,瘟疫就会使其固若金汤。古罗马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在罗马早期,一连串人们至今也搞不清名字的流行病让当地哀鸿遍野。后来,但凡蛮族部落逼近,这些侵略者就会被大流行病击垮,而同样的疾病对罗马人影响轻微。假如匈人保留游牧生活方式,他们受流行病的影响会很小。即便偶有劫掠者在拥挤的定居点患上传染病,瘟疫也很难在分散的、规模不大的游牧群落中传播。可一旦匈人集結成军,处于集中领导之下,那么形势就会发生巨变。一方面,先前没接触过瘟疫的匈人缺少抵抗力;另一方面,他们现在又聚集在一处,给微生物扩散搭建了温床。从某种程度说,介于游牧与城市化两者之间的脆弱处境,才是阿提拉悲剧的根源。
凭借早先感染而形成抵抗力的社会,会得到瘟疫的优待。这是一条对人类历史有着广泛影响的原则。它不仅在旧大陆上导演着帝国的生死存亡,还在欧洲入侵者占领美洲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