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人类的地理学视角下丽江古城旅游地的营建与消费
尹铎 高权 卢薇 朱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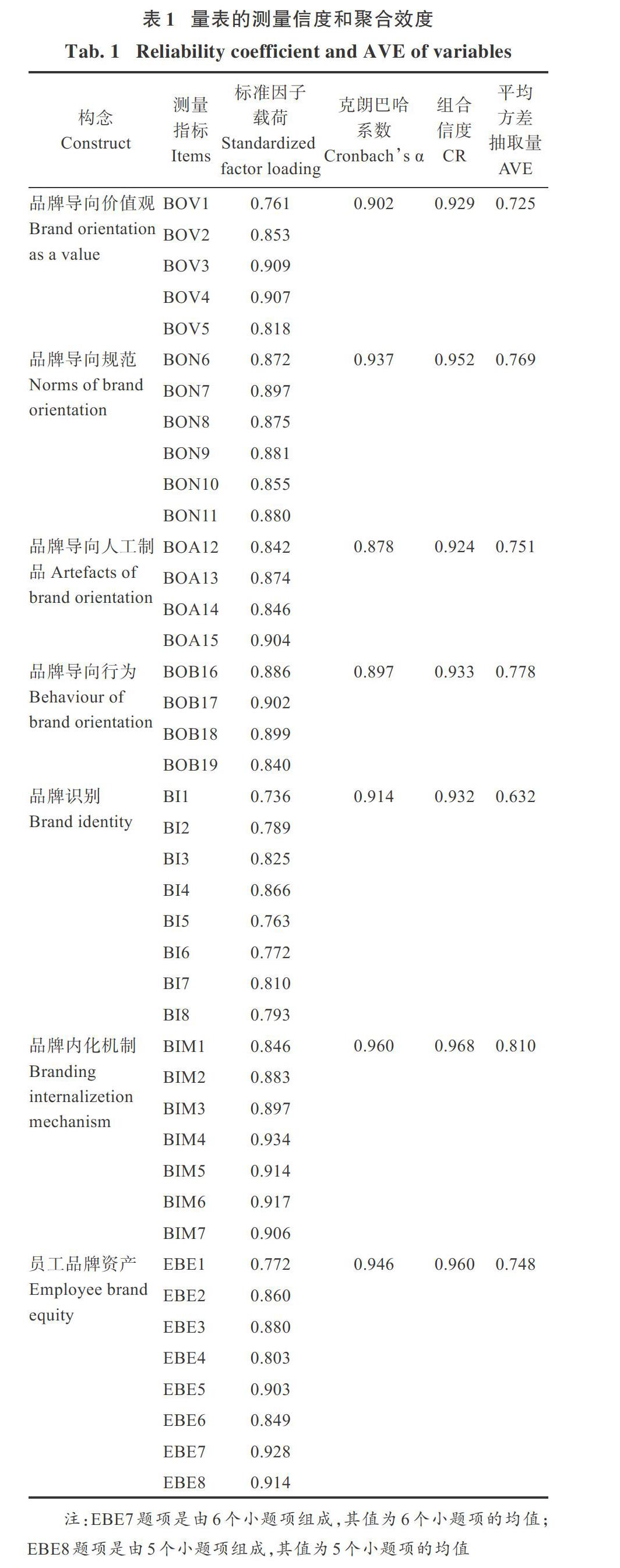
[摘 要]文章以超越人类的地理学为切入点,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以及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宠物狗为研究对象,分析丽江古城旅游地中宠物与人类行动者关系的营建与消费,以此探索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塑造的地方。研究发现:(1)丽江古城的地方意义全然镶嵌在人与非人类的完整行动者网络之中,而不应简单地理解为“社会关系”的表征和建构。宠物狗可以联结不同的行动者并营造丽江古城“家”的地方意义。(2)宠物狗参与构建丽江古城地方意义的过程与旅游消费情境紧密结合,这种消费并非是单向的,而是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行动者互动的双向过程。(3)在浪漫化的丽江古城地方意义之下,对于人与宠物狗关系的营建与消费表象实则在展演着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研究旨在为旅游地社会文化现象分析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解构提供新的视角。同时,在实践层面上,研究对丽江古城作为旅游地“人-地”关系的演化与有效治理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地方营建;宠物狗;旅游移民;旅游消费;超越人类的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4-0096-10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4.011
引言
旅游地的建构与消费(the constr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ourism place)一直是旅游地理与社会文化地理的研究热点之一[1]。旅游不仅推动着外来的旅游者与经营者进驻、消费与体验着地方,也作为一股强大的动力在营建、重塑并改造着地方。旅游驱动下的地方营建与消费是一个同时进行的双向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多元行动者都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2]。学者们对于这一过程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与实践之中。例如,Becker研究了在导游这一重要群体的带动下,旅游作为一种地方营造的活动,使得柏林的一座清真寺成为公众参与的典范,维持了在德国生活的土耳其移民世代相传的宗教实践[3]。Everett探讨了随着英国食品旅游的日益普及,传统食品生产商开始向游客敞开大门,促成食品生产场所向旅游体验空间的转变,并在其业务运营和发展新的消费领域之间达成平衡[4]。这类只关注社会行动者的人类中心主义研究视角,近年来开始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反思。例如,Gran?s发现,地方意义建构的过程中,非人类(nonhuman)会与人类行动者联合与互动,使得旅游地转型充满复杂的政治与生态纠葛[5]。但总体而言,对于人类与其他非人行动者的互动在旅游地建构与消费中的复杂作用与关系网络的建立机制,尚缺乏深入探讨。
近年来,伴随着超越人类的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的兴起,欧美旅游地理与文化地理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人与非人类关系的重要性[6]。它重在强调人类与其周边非人类(non-human)物质实体间的互嵌关系,并质疑基于人与非人类二元对立而建立的政治与伦理立场[7]。超越人类的地理学强调采用关联的能动性(relational agency)视角分析人类与非人类共同构建的世界,关注非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及其在构建完整的行动者网络中的意义[8]。其中,动物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非人类行动者之一,它们具有丰富多彩的生物特征以及与人类相生相伴的悠久历史[9]。因此,从超越人类的地理学视角出发,动物本身并不是因为自身的功用(utility)而被动卷入人类社会之中,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构建社会文化网络的一个内在维度。
丽江古城是国内外知名且发展成熟的文化遗产旅游地,其中尤以大研古城与束河古城最为著名[10]。针对丽江古城旅游地已有许多学者从其空间形态的发展演变,以及内部社会文化变迁进行了卓越扎实的研究。已有研究发现,伴随着旅游发展的逐渐深入,古城原住纳西族居民逐渐搬出,大量旅游移民进驻,原本的民居住宅变成了客栈、餐厅、旅游纪念品店等供旅游者消费的商业空间[11]。不同旅游移民与旅游者的来与走、去与留,构筑了丽江古城日常生活与旅游活动相交织杂糅的多元社会文化图景。然而,鲜有学者关注的是,号称“高原姑苏”“东方威尼斯”的丽江古城旅游地,同时也被称为“狗的天堂”。丽江古城中的宠物狗品种多样,难以计数。在古城各类空间均可看到它们的踪影。宠物狗在塑造丽江浪漫化的旅游地意象的同时,也为丽江古城旅游地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问题与挑战。由于旅游移民与旅游者高度的流动性,大量宠物狗被遗弃而成为古城流浪狗,并由此带来了极大的卫生与安全隐患。宠物狗作为非人类的行动者,逐渐成为古城难以忽视的存在。丽江古城旅游地的人与宠物狗的复杂关系引出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作为非人类行动者的宠物狗是如何参与到旅游地的建构与消费之中?它们与旅游地的人类行动者又是如何进行互动的?本文试图借鉴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研究视角,着重分析丽江古城旅游地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如何共同塑造旅游地的社会网络与浪漫化的地方意义,并揭示在浪漫化的丽江地方意义之中,人与宠物狗关系营建与消费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希冀研究可以脱离传统旅游地演化冲突治理路径探讨的窠臼,力图为这种管治与协商提供一种旅游地人地关系的反思。
1 超越人类的地理学视角下的人与宠物关系
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研究指出,“社会”与“日常生活”并非纯粹的人类领域,动物与人类一样具有能动性(agency)和生活经验,并能够与人类一起进行地方营建(place making)[12-13]。所謂动物的能动性是指,动物作为非人类主体影响他者或被他者影响的能力[14]。正如Dempsey所述:“能动性不是某物或某人的固有属性; 它不是来源于人的自主性、目的或价值观,而是来自更广义尺度中不同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由于互动实践而产生的协商、联盟与冲突[15]”。
为了展示动物的能动性,超越人类的地理学者们开始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生物哲学以及非表征理论[16],探讨具象化的空间情境中人与动物的互相影响与作用。除了批判性地参考目前为止人类所建构的动物话语外,学者们更倡导通过参与式观察、追踪等多元研究方法刻画动物的生活世界,展演动物的空间活动与主体性,尽量让动物为自己发声[17-19]。例如,Bear利用参与式观察及饲养员深度访谈的方法,跟踪调研了水族馆中一只名叫Angelica的章鱼,发现Angelica通过或安静或狂躁的肢体动作,对其觅食需求、探索生活空间的休闲需求等主体性进行展演,进而影响饲养员与游客的投食及观览时间,最终实现其个体能动性发挥[20]。Hinchliffe等则在英国伯明翰(Birmingham)与黑区(The Black Country)的溪水畔与湿地中,训练并利用研究者的具身性体验去感知动物的日常生活。他们通过观测并追踪水田鼠的足迹大小、深浅以及粪便的气味及组份,来判断其空间活动轨迹、觅食来源与聚居空间等,从而展示动物作为被忽略的非人行动者所组建的城市景观[21]。
除了备受关注的野生动物外,宠物作为伴侣动物的能动性,亦是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研究最为重要的话题之一。人与宠物的互动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塑造着不同空间尺度的地方意义[22]。然而,这种关系并非人对动物的单向支配,而是“人性”(human nature)与“动物性”(beastly nature)的互动协商[23]。一方面,基于动物的功用(如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情感价值),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西方哲学界在人与动物关系上长期争论的话题之一就是人类如何能够将“动物性”纳入人类“文明”的话语体系之中[24]。例如,Blouin认为宠物不同于家畜等其他动物,其价值不在于使用功能,而在于其对人类的情感支持[25]。许多宠物不仅被允许进入住宅生活,甚至还在家中拥有原本只供家人使用的专属房间与家具[26]。
另一方面,“动物性”往往是动物本身的一种能动性,能够影响人类的行为和情感认知。宠物不仅仅是由人类饲养的、可提供玩乐或服务的被动客体,也是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能动主体。实际上,宠物狗的品种不同,甚至同一品种的个体不同,都会具有迥异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它们难以掩盖的气味、脱落的毛发和不受控制的吠叫,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为了重塑宠物狗的主体性,使其作为动物的自然本性更加契合人类之“家”安全、整洁与秩序井然的特征[27],主人会安排每日固定的遛狗时间、对狗随地便溺等越界行为进行惩罚,或在客人到来时将狗区隔到固定的活动空间等。这种人与宠物的互动,不仅塑造着私密住宅空间的意义,也在塑造着公共空间,甚至整个城市的地方意义。例如,在城市中的日常遛狗活动不仅是一种人与狗在住宅之外培养感情的日常互动,也是对一个城市开放与包容程度的塑造与展演[28]。
基于先前研究对人与宠物关系的探讨,本研究旨在将研究情境放置于现代社会高度流动性背景下,更深入地探讨宠物如何与人类发生复杂互动,以及如何在此过程中发挥其主体性与能动性。当今社会,人们为了追寻自我价值实现(individual fulfillment),会在更广域的空间尺度中以流动性的方式进行工作、休闲与旅游[23],而宠物往往也参与其中。作为家庭成员,宠物可以帮助人们减少对于迁出地的留恋,更快速适应迁入地的生活,并逐步建立对迁入地的地方认同[9]。Riggs通过对移民至澳大利亚的儿童难民的研究发现,通过在定居地的宠物饲养,借助与宠物“对话”“爱抚”等活动,可以抚慰儿童流亡的心理伤痛并重建安全感与地方依恋[29]。Fox等通过对赴迪拜工作的英国精英移民研究发现,例如长途飞机的运输过程、宠物入关隔离检疫的安全性以及东道国对于移民签证到期后的离境政策等具体问题,都会影响着移民是否与宠物一起迁移以及在离开迁入地时是否继续带走宠物[30]。在流动性背景下,移民、宠物与地方营建不仅仅是移民家庭在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去与留的简单选择,更是一个关乎具体地方社会文化背景、动物伦理与区域资本及劳动力流动的综合性问题。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虽然探讨了流动性情境下宠物与饲养者的关系,以及人类的流动选择对宠物的影响,但关注的人类与宠物关系所涉及的行动者仍然较为单一,且对于宠物狗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刻画与追索亦较为单薄。
丽江古城旅游地在旅游资本介入后,成为融合日常生活、休闲与旅游消费的复杂地方。关于丽江古城的话语既有超脱现代性压力,犹如乌托邦一般避世、慢活的安定与浪漫,亦有金钱包裹之下纷繁复杂、包罗万象的流动与世俗[31]。在这里,空间的私密性与公共性变得模糊,主人与客人、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分界亦不再明显。本文选择大研古城与束河古城这两处特殊而又典型的丽江古城旅游地,以古城旅游地中具有显著数量优势以及在公共空间中更加显见的宠物狗为非人类行动者代表,期冀能够更加生动地展现高度流动性情境中,多元复杂的人类与非人类关系以及超越人类的行动者如何进行主体性发挥和能动性展演。
2 研究方法
超越人类的地理学主张结合参与观察的民族志方法和动物行为学等方法来理解动物的生活世界,提倡运用动物行为学中对动物的直接观察捕获那些超越文本与意义之上的,关乎动物自身的实践、技能、情感和习惯[18-19]。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对非人类行动者能动性与主体性的展示并不意味着对于文本和话语的彻底抛弃,而是应该选择那些与动物密切接触的、休戚相关的人类行动者,利用他们关于动物的亲密知识(intimate knowledge)[32]或权威认知(epistemic authority)[33]来全面展示动物日常生活中的微观细节。
因此,本文主要运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以及文本分析的方法,于2015—2019年在丽江大研古城与束河古城进行了5次实地调研。首先,选择客栈、餐厅与旅游纪念品等不同类型的典型商业空间以及宠物狗活动频繁的古城街道等公共空间,观察旅游移民、游客与宠物狗的互动,以及宠物狗之間的互动(包括被遗弃的流浪狗)。对典型活动场景进行民族志式的记录,并在征得宠物狗主人同意后,对典型的互动方式与场景进行照片拍摄(图1)。
其次,为了获得更加深入的信息,研究者依据所观察到的情况,以宠物狗类型与数量的差异性以及旅游移民类型(如劳工移民、旅游移民企业主等)的多元化为考量依据,结合宠物狗饲养年限与成长经历,对古城的9间商铺的旅游移民(全部为宠物狗的日常饲养者)以及15位进店消费的游客进行了深度访谈。旅游移民与旅游者受访者根据访谈的时间顺序,分别编码M1,M2……M9与T1,T2……T15。访谈时间在40分钟至3小时之间。访谈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进行。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后进行了录音或笔记记录,并在后期进行了转录整理。同时,与主要受访者添加微信好友,保持密切联系,通过对方朋友圈所展示的文字与图片,持续追踪旅游者的旅游体验以及旅游移民在古城的店面经营情况与宠物狗的日常生活。
此外,研究还采用了文本分析的方法,在携程、马蜂窝等旅游网站搜集与宠物狗相关的丽江古城旅游体验与评价。同时在百度新闻中检索关于丽江宠物狗的新闻报道,力求对丽江古城中人与宠物狗的互动及其矛盾进行深入分析,尽可能地全面理解人与宠物狗共构的丽江古城旅游地。
3 浪漫化的丽江: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建的地方意义
丽江古城通常被大众媒体、旅游者和各种旅游组织建构和想象为一种浪漫化的、自然的或是具有异域风情的(exotic)的地方[34-35]。先前研究大多基于建构主义的研究视角,认为来到丽江的旅游移民与旅游者,大多是为了短暂逃离城市现代性的生活,把丽江古城作为与压抑的城市生活相对的精神圣土,通过日常生活与旅游体验对丽江进行营建与消费。然而,本文需要指出的是,丽江的地方意义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关系”的表征和建构(不同人类行动者所组建的社会关系),而是镶嵌在人类与非人类组建的完整行动者网络之中。其中,宠物狗就是丽江地方营造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
3.1 旅游移民、狗与古城生活方式的营建
首先,旅游移民与宠物狗的互动与实践聚合了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的联系,帮助旅游移民更加快速地适应与融入丽江古城的日常生活。M4先生与太太在丽江相识相知并于2011年结婚,在束河古城定居,创建了一家12间客房的客栈。在丽江定居后,他们将原本在北京与上海饲养的两只宠物狗可卡犬(16岁)与贵宾犬(8岁)都带来了丽江。这两只宠物狗对主人极度依恋,可卡犬因为年老体衰又患有白内障而被饲养在M4的卧室细心看护,而贵宾犬则是形影不离地跟在M4的太太身边。由于宠物狗与主人同吃同住的日常生活,使得M4一家在丽江成功地延续了与原本在北京、上海时的生活理念与模式。狗对于他们而言早已成为家庭成员,照顾它们已经成为家庭生活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在丽江古城的新家中复刻与宠物狗共同相处的日常生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旅游移民在空间置换和流动中能够更加稳定地在丽江古城扎根与生活。
除了个体家庭的营建外,宠物狗促使原本陌生的旅游移民之间建立起了属于群体内部的社会网络。宠物狗的主体性发挥为旅游移民之间提供了社交的机会,增强了移民的群体认同。例如,M2在其所饲养的泰迪犬(名叫Gucci,母犬)出现爬跨、举尾、拱背等求偶行为后,就立即与同在大研古城做生意并饲养泰迪犬的好友联系,准备“结亲”以保证“毛孩子”的血统纯正。他们会在日常品茶闲谈时滔滔不绝地交流饲养经验,亦会在狗不慎丢失时在朋友圈请求帮助,并一呼百应地得到全古城养狗好友的应援。除了整体的认同感外,旅游移民之间还会因为与狗的日常互动差异区分彼此不同的群体与认同。例如M9在谈到遛狗牵绳与捡拾狗粪便的态度时表示:“那前面有一家开客栈的养着一只藏獒、一只比特,这可都是大型猛犬,从来不见拴绳、戴嘴套,那么大的狗自己遛自己,狗屎到处拉。这种人,除了破坏环境、败坏我们养狗人的名声,啥也不是。(我们)跟他们不是一类人。”因此,宠物狗一定程度上让地方的体验突破了私人空间而进入公共空间,从家庭内部认同延伸至群体认同,同时也生产着丽江古城新的地方意义。
其次,旅游移民通过与宠物狗在丽江的互动与实践,营建并塑造着他们所追求的、认为在丽江定居理应享受到的简单而纯粹的慢生活,从而营造出一种浪漫化的旅游地地方意义。为了体验想象中天然纯净的自然环境以及古城简单纯粹的日常生活,M1在大学毕业后就只身一人从深圳来到丽江,作为餐厅服务人员已经在束河古城生活了7年。她所在的餐廳饲养了4条宠物狗,分别是属于老板的一只萨摩耶犬(名叫春天,母犬)和一只混血杜宾犬(名叫阿里,公犬),以及属于她的一只萨摩耶犬(名叫刀刀,母犬,春天的后代)和同事所饲养的西伯利亚犬(名叫可乐,公犬)。在过去的7年里,为了解决宠物狗的排便问题,每天清晨M1都会和另一位养狗的同事在10点餐厅营业之前,在从宿舍去餐厅的路上遛狗。在10—12点客人来吃中午饭前以狗粮作为正餐喂狗。下午再以客人们消费剩余的三文鱼作为零食当作它们听话的奖励。为了让宠物狗保持健康的身体与愉悦的心情,在傍晚客人少或者淡季的时候,M1会带着狗去雪山脚下的草地跑步,呼吸着新鲜空气,看着它们在草地上雪山下尽情地打滚撒欢。狗已经成为了她在丽江简单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移民与狗的日常互动共同构筑了外界所追求与想象的、逃避世俗与放松的丽江。
再次,丽江古城之于绝大多数的旅游移民而言,最终也只能是短暂停留的地方,当他们不得不面对是否应该离开丽江的选择时,狗的情感依赖与健康问题会成为他们选择去与留的牵绊因素之一。资本以时间消弭空间的历史计划,正在逐步将丽江纳入资本积累的体系中来。外界所想象的、纯粹而游离于现代性之外的丽江,其实恰恰是正在经历高度现代化的地方[37]。在现代性社会背景下,“家”本身就是高度流动与不稳定的,就像一个又一个的月台,人们总是在一个月台上短暂停留而后又踏上旅途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下一站[38]。对于何时离开丽江,M1说:“就是它一直把我绊在这儿吧,没有办法那么坚决地说要走啊。丽江这里非常适合它的生存,夏天没有那么热,冬天干燥又冷,对长毛狗来说就很舒适。再一个就是老板的因素,老板对我们很好,就像家人一样,待遇也不错。所以一直也没有想说要走啊什么的。”
旅游移民在丽江古城的去与留,并非只是单纯地面临着或需要面对工作与家庭等压力,或需要去寻找下一个更加“纯粹”的地方的选择,非人类行动者与其构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情感,亦成为其地方体验与个人生活抉择的重要维度。
3.2 旅游者、狗与古城中的旅游消费
宠物狗作为构建丽江古城地方意义的一个非人类维度,也紧密地镶嵌在旅游消费的情境之中。除了旅游移民外,旅游者与宠物狗的互动亦是消费丽江地方意义的重要内容。旅游者在丽江古城的旅游消费活动,主要集中于摄影、购物以及休闲方面[34]。他们对丽江的想象,结合在实际消费时的具身性体验,共同形成了他们感知中的丽江。值得指出的是,从超越人类的地理学视角出发,这种对旅游地地方意义和符号的消费不是简单的一种单向“凝视”过程,而是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互动的双向过程[38]。
首先,被当作文化符号消费的宠物狗,是影响旅游者与潜在旅游者到访古城后的旅游行为与体验的因素之一。旅游者会选择性地凝视和拍摄一些特定的景观,并投注自身的情感,再通过微信朋友圈、短视频与旅游博客等虚拟社群进行分享。古城中随处可见的在太阳下发呆的宠物狗,无疑迎合了他们对丽江放松、文艺与友好氛围的想象。在这个层面上,宠物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被消费。旅游者Yong挑选了51张照片,来记录从初到丽江至离开丽江完整的旅游体验,其中有17张就是专门对古城中不同空间的宠物猫、狗进行记录与拍摄。在游记文本中,她这样描述这些猫狗,“古城猫狗儿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会享受生活的动物了。不选地方、不分时间,也像到这里旅行的游客一样,伴着巷道中流淌着音乐肆无忌惮地‘发呆‘晒太阳,丝毫不畏惧陌生人。”1在游记下,评论的游客也纷纷留言并点赞,并表示也想去丽江,去住这些有萌宠的客栈。可见,在游客间对照片“晒”与“赞”的强化中,丽江古城的旅游地意象得以建构,拥有宠物的旅游商业空间得以营销,同时也影响着潜在旅游者在出游前对丽江意象的感知与认同。游客T1表示,“我来之前就在网上看到过照片,古老的街道与木楼搭配起来这些狗,觉得真心文艺,来了以后自然猛地拍它们(晒太阳)的懒样子,感觉很羡慕,我也想这样无忧无虑。” 因此,旅游者对古城作为旅游地的凝视,并非只是对宠物狗的单向消费过程,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因为宠物狗而来,他们的旅游消费选择受到宠物狗的影响,亦是宠物狗主体性与能动性发挥的显著体现。
其次,宠物狗能够成为打破主客对立的中介,使得旅游者更加融入旅游移民构建的旅游商业空间。这主要体现在狗作为动物所具有的主体性的展演,会成为旅游商业空间的吸引力。在大研古城与束河古城的许多客栈和餐厅,宠物狗都是散放饲养,旅游者前来消费就可以有机会随意地与宠物狗进行互动。在笔者们对M8所在的手工鲜花饼店持续的观察中,店铺所饲养的萨摩耶犬在营业的绝大多数时间都被栓在店铺门口发呆或睡觉。而只要游客注意到它并靠近,萨摩耶犬就会顺势躺下并露出肚皮撒娇示好。此时,绝大多数游客都会跟着狗一起蹲下并开始爱抚狗的头、背及肚皮等身体部位。许多游客还会顺便进店购买甜品,并与萨摩耶犬一起分享并拍照留念。这表明了宠物所引导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人性”中对亲密感的需求,进而促进了旅游消费并产生积极的旅游体验。
除了摄影与购物消费外,对于为了追求慢生活来到丽江休闲度假的旅游者而言,客栈是一个隔绝嘈杂古城街道与商铺的“世外桃源”。在他们熟知的客栈中,白天在躺椅上晒太阳,晚上在院落的秋千上数星星,与相识多年的老板聊天品普洱茶,是充满意义并满足对古城“真实性”与“传统”生活想象的事情。而与宠物狗相处的典型时空场景,对于他们而言,也会成为难忘回忆或找回对古城曾经熟知的旅游体验的载体。在M7客栈中品茶聊天的游客T2说道:“我很多年没有来丽江了,我以前来(丽江)的那个晚上,也是杨大姐(客栈固定合作的司机)来接的我。一进门这个小鬼(M7饲养的古牧犬)就扑大姐身上去了,当时以为它咬人,吓我一跳,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我住的这几天,每天趴我身上让我摸,我后来买的一个银戒指有豁口还勾掉它一撮毛。哈哈哈。多少年过去了啊,虽然他们换了店面,但是看到它,熟悉的感觉还是没有变。”而对于另一些旅游者,在客栈中乖巧的宠物狗摇尾等示好的亲密行为,则勾起了他们对逝去日常生活情境的重现。旅游者T9对M3家饲养的金毛犬爱不释手,在客栈住宿的4天里,每天从丽江其他旅游景区回到客栈都会在院子里陪狗玩耍,她说道:“我们家巴迪也是金毛,跟了我11年,前年肾衰竭死了。那之后,我再也没碰过狗。来之前我也没想到这儿的客栈有这么多狗。那天刚一进门,它(金毛)就在我腿上蹭,头往我脚上趴。摸着它,我想我家巴迪了,可能它也想我了吧。”
与宠物狗的互动实践承载着旅游者对过去熟悉的旅游地的温情回忆,使旅游者在丽江的旅游消费活动紧密地嵌入在追求别样的异域体验与找寻熟知的地方意义的二元张力之中。在这一复杂纠结而又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丽江成为传统与现代、熟悉与陌生交织的旅游地,不断地吸引着不同的行动者的来与走、去与留。
4 吸纳与排斥:營建与消费面纱下人与宠物狗的权力展演
在浪漫化的丽江地方意义之下,对于人与宠物狗关系的营建与消费表象实则在展演着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一方面,人类主导的文明话语体系,在城市管治和交通管理等方面建立起一套对动物的吸纳与排斥的机制。这种权力关系的运作主要体现在宠物狗的空间可进入性与人的流动性两个维度。另一方面,宠物狗并不是处于一种绝对的被支配关系,其自身难以被人类控制的“动物性”[18,39-40](如攻击性、繁殖能力等主体性)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在古城泛滥的流浪狗“景观”。
狗的“动物性”作为动物的内在属性,一定程度上必然与丽江浪漫的地方想象相悖。当狗的主体性展现妨碍了旅游者的消费活动或影响了旅游商业空间的正常运营,它们的主体性就会被建构为不被允许的“兽性”(beastly),进而成为应该被约束与规训的理由[27]。大部分的宠物狗只有经过训练以后才能够以“听话”的模样出现在旅游商业空间。而凶猛如杜高犬等品种的猛犬则会被较为严格地限制在旅游移民私人居住空间,不得出现在旅游者的活动范围内。在客人消费时,如果遇到令宠物狗兴奋或愤怒的事,比如遇到了路过的其他宠物狗或者有穿着怪异的人出现,狗的天性会驱使它狂吠或失控,这时为了不影响旅游者消费,主人会使用棍棒等利器进行教训与呵斥,并在适当时候限制它们在商业空间内部的活动范围。游客T4对于为何没有进去大研古城的一家饰品店购物,解释道:“我本来想进去看看(饰品)的,你看这么大个狗(阿拉斯加犬)躺在门口,虽然可能不会咬人,但还是小心为妙,开开心心出来玩别被咬一口,不划算。干脆就不进去,不去惹它。”
而对于如何管制自家餐厅的狗不影响客人消费,笔者观察到古城中许多餐厅的应对策略是:在餐厅的后院中放置狗笼,只要有客人怕狗或对狗表示厌恶,就会将狗集体关在狗笼中,待顾客离开后再重新将狗放出。在丽江,虽然旅游者与宠物狗的互动与情感不同于其他大城市,具有在消费空间严格的人与“非人”的界限(宠物禁止入内)。但这种表面上看似轻松、和谐的人与宠物关系的展演,实际却也建立在对宠物狗主体性的规训之中,以达到更好地为旅游经济增长服务的目的。
另一方面,人们会根据宠物狗的物种形态来对其主体性(动物性)进行话语建构,从而在地方管治方面占据主导地位。首先,人根据宠物狗的品种、外貌等生物特性定义了何为“凶猛”与“驯顺”,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对可以饲养何种宠物狗进行限制与规定[41]。例如,作为中国城市文明建设的典范,北京市严格规定只得饲养成年体高35厘米以下的小型玩赏犬,而除此之外的犬种都被建构为严禁饲养的“猛犬”,违反者将由公安机关处以罚款并没收犬只。对于为何要饲养罗威纳犬,从北京移居来束河开客栈的M5解释道:“泰迪、京巴儿这样的(狗)不适合我,我喜欢大的(狗),北京管太严不让养,但这儿可是束河,跟北京不一样,不必什么都拘着。”在人们对宠物狗“动物性”的建构下,丽江古城旅游地成为与其他城市不同的、自由包容的浪漫地方。仅古城区而言,在2013年摸底排查所统计的两万只宠物狗中,就有三千只为北京所定义的烈性猛犬1。这种自由与包容是人们来丽江饲养宠物狗的理由,却也成为丽江街头产生大量流浪狗的重要原因。一旦饲养宠物狗的旅游移民或旅游者要离开丽江,由于不同城市宠物饲养政策的差异,加之中国铁路、航空运输繁琐的审批手续与主人本身的厌弃,许多宠物狗最终并不会随着主人一起迁居流动,而是被遗留在丽江古城旅游地。
虽然还在同样的地方,但当宠物狗被迫脱离了原本由人类主导所营建的“家”空间[22],原本被赋予的“家人”的意义就将被剥夺,宠物狗也将转而变成所谓的“流浪”狗或“野”狗,成为“凶猛”“肮脏”的象征。这一话语体系的转变也使得人类对流浪狗的管控合理化,例如,丽江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会采取措施对流浪狗进行绝育、扑杀或捕捉以等待被再次收养。
但是,人类对流浪狗行使的管治權力往往也会受到动物能动性的制约。例如,流浪狗的行为模式与对空间的利用方式不同于宠物狗,它们会以古城中固定的垃圾箱和休息地为中心,三五成群划定各自的领地与活动范围,且不允许其他狗随意地越界。它们在古镇中日常的游荡、为争夺交配权的吠叫和撕咬,经常使得途径之处游客纷纷避让。因此,丽江古城旅游地泛滥的流浪狗成为具有负面旅游地意象的景观,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对动物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忽视,也反映了我们需要将动物纳入政治与伦理共同体之中,并深刻反思我们过去制定与实践政治和伦理的方式[42-43]。
此外,从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研究视角出发,丽江古城旅游地人与宠物狗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关联的、相互作用的权力关系中。人类可以通过话语对动物的主体性进行建构,对宠物狗或接受或排斥,这一过程看似是人始终在对宠物狗行使权力。但事实上,宠物狗的能动性也在影响并制约着人类,即人类需要围绕着宠物狗来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换言之,权力总是在不同实体之间波动,行使权力的主体、被施加权力的客体以及权力所要达成的目的需要在具体情境中具体分析[44]。但需要指出的是,人与宠物狗的权力关系深深地偏向于人类的偏好与利益,动物能动性发挥的有效性取决于它们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以及所涉及的人类行动者。丽江人与宠物狗关系所展演的权力运作过程是镶嵌在旅游移民与旅游者的日常生活与旅游活动中的,人与宠物狗的互动过程中充满复杂的矛盾与张力。这些看似不能兼容的或浪漫化、或冲突与矛盾的意义、话语与实践,共同组构了充满张力的丽江古城旅游地行动者网络,展演了复杂、动态而又互相关联的人地关系(图2)。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超越人类的地理学为研究视角,以人与宠物狗关系为例,解析了丽江古城旅游地的营建与消费及其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研究并非意在强调并凸显狗在丽江古城的重要性,亦并非意图证明宠物狗已经成为丽江古城旅游消费的主要对象或吸引力。而是通过关注在丽江古城高度流动性的旅游情境下人与宠物狗的关系,展现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非人类的角色与价值,及其与人类行动者共同组建的丽江古城。
本文为旅游地的地方意义营建与消费研究,引入了一个“超越人类”的研究视角。发生在旅游地的流动性、生活方式打造与旅游消费是复杂且系统的动态过程,不应简单地理解为“社会关系”的表征与建构,非人类行动者也是呈现地方意义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研究选择以丽江古城旅游地中较为典型的宠物狗为例,发现在饲养宠物狗的家庭中,旅游移民与宠物狗互动的日常生活实践使得旅游移民能够更加快速且容易地将原本迁出地熟知的日常生活紧密地嵌入丽江古城的文化情境中,并帮助旅游移民形成群体之间的社会网络,建立群体身份认同。人与宠物狗的关系展演能够满足并再现外界将丽江作为精神圣土的地方想象,能够助力丽江成为旅游移民心中与原本压抑的快节奏现代城市生活相对的“世外桃源”[11]。同时,宠物狗作为具有生命的行动者,会成为旅游移民在高度流动性的社会中选择未来生活方式与目的地的重要抉择依据之一。
其次,研究不同于以往对于野生动物旅游的关注[45],为彰显旅游消费研究中的非人类行动者在旅游地中的角色与作用,提供了“宠物”作为非人类的探讨视角。研究发现,旅游地地方意义和符号的消费是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互动的双向过程。在旅游商业空间中,人与宠物狗关系的展演,可以显著地影响旅游体验并促进消费为旅游经济增长服务。在与宠物狗的互动中,旅游者在丽江的旅游消费活动紧密地嵌入在追求别样的异域体验与找寻熟知的地方意义的二元张力之中[36]。
最后,研究批判式的反思了人与动物在旅游地互动中的权力运作过程,发现人对宠物主体性的建构会间接影响地方意义的形成。而人在不同意义的地方流动,宠物的命运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但宠物主体性的展演同样会对人类的行为造成影响或制约。丽江古城旅游地人与宠物狗的权力运作过程始终处于动态关联、相互作用之中。因此,权力的运作主体并非总是人类,而是要在具体情境中具体分析。
本文展现了动物所具有的关联的能动性与主体性,响应了旅游研究对于分析人类与非人类共同构建的社会文化世界的号召。将地方的政治经济结构、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放置到关联动态的网络中,审视特定主体(特别是与资本积累有关的主体)的权力差异,为分析旅游地社会文化现象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尝试。同时,在实践层面上,本文探讨了宠物狗如何参与丽江旅游地意象的构建,以及如何对丽江旅游景观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启示着人类在与动物的互动实践过程中应反思对动物具有的伦理责任,充分考虑动物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研究对于丽江古城作为旅游地的演化与管理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作为微观的个案研究,未能细致地区分、展示与对比在丽江古城旅游地中不养狗甚至不喜欢狗的旅游移民、旅游者,会因为宠物狗与流浪狗景观对于旅游地营建与消费产生怎样的影响。期待未来研究能够继续关注人类与非人类关系建构中更为宏观复杂的运行机制。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HULTMAN J, HALL C M. Tourism place-making: Governance of locality in Swede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9(2): 547-570
[2] RAKIC T, CHAMBERS D. Rethinking the consumption of plac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9(3): 1612-1633.
[3] BECKER E. Tour-guiding as a pious place-making practice: The case of the Sehitlik Mosque, Berlin[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8: 81-90.
[4] EVERETT S. Production places or consumption spaces? The place-making agency of food tourism in Ireland and Scotland[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2, 14(4): 535-554.
[5] GRANAS B. Destinizing finnmark: Place making through dogsledding[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8: 48-57.
[6] PANELLI R. More-than-human social geographies: Posthuman and other possibilitie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0, 34(1): 79-87.
[7] WHATMORE S. Materialist returns: Practising cultural geography in and for a more-than-human world[J]. Cultural Geographies, 2006, 13(4): 600-609.
[8] ANDERSON B, MCFARLANE C. Assemblage and geography[J]. Area, 2011, 43(2): 124-127.
[9] BULLER H. Animal geographies I[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4, 38(2): 308-318.
[10] SU X, TEO P.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Tourism in China: A View from Lijiang[M]. Abingdon: Routledge, 2009.
[11] SU X. Moving to peripheral China: Home, play and the politics of built heritage[J]. The China Journal, 2013 (70): 148-162.
[12] CRESSWELL T. Geographic Though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M].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2013: 239-259.
[13] LAUREN E, PATTER V, HOVORKA A. ‘Of place or ‘of people: Exploring the animal spaces and beastly places of feral cats in southern Ontario[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8, 19(2): 1-21.
[14] GREENHOUGH B. 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M] // LEE R, CASTREE N, KITCHIN R, et al. The SAGE Handbook of Human Geography. UK: SAGE Publications, 2014: 94-119.
[15] DEMPSEY J. Tracking grizzly bears in British Columbias environmental politics[J] .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0, 42, 1138-1156.
[16] WHATMORE S. Hybrid Geographies: Natures, Cultures, Spaces[M]. London: Thousand Oaks, 2002: 1-7.
[17] BULLER H. Animal geographies Ⅱ: Method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5, 39(3): 374-384.
[18] LORIMER J, SRINIVASAN K. Animal geographies[M]//JOHNSON N, SCHEIN R, WINDERS J. The Wiley-Blackwell Companion to Cultural Geography.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3: 332-342.
[19] HODGETTS T, LORIMER J. Methodologies for animals geographies: cultures, communication and genomics[J]. Cultural Geographies, 2015, 22(2): 285-295.
[20] BEAR C. Being Angelica? Exploring individual animal geographies[J]. Area, 2011, 43(3): 297-304.
[21] HINCHLIFFE S, KEARNES M, DEGEN M, et al. Urban wild things: A cosmopolitical experiment[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05, 23: 643-658.
[22] FOX R. Animal behaviours, post-human lives: Everyday negotiations of the animal-human divide in pet-keeping[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06, 7 (4): 525-537.
[23] NAST J H. Critical pet studies? [J]. Antipode, 2006, 38(5): 894-906.
[24] REGAN T. Animal Rights, Human Wrongs: An Introduction to Moral Philosophy[M].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1-10.
[25] BLOUIN D D. Understanding rela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their pets[J]. Sociology Compass, 2012, 6(11): 856-869.
[26] FRANKLIN A. “Be [a] ware of the Dog”: A post‐humanist approach to housing[J]. Housing, Theory and Society, 2006, 23(3): 137-156.
[27] POWER E. Furry families: Making a human-dog family through home[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08, 9(5): 535-555.
[28] FLECTCHER T, PLATT L. (Just) a walk with the dog? Animal geographies and negotiating walking spaces[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8, 19(2): 211-229.
[29] RIGGS D W, DUE C, TAYLOR N. ‘I want to bring him from the aeroplane to here: The meaning of animals to children of refugee or migrant backgrounds resettled in Australia[J]. Children & Society, 2017, 31(3): 219-230.
[30] FOX R, WAISH K. Furry belongings: Pets, migration and home[M] // BULL J. Animal Movements, Moving Animals: Essays on Direction, Velocity and Agency in Humanimal Encounters. Uppsala: Upsala University, 2011: 97-118.
[31] 蘇晓波.反思旅游空间正义[J]. 旅游学刊, 2017, 32(3): 7-8. [SU Xiaobo. Reflection on tourism space justice[J]. Tourism Tribune, 2017, 32(3):7-8.]
[32] COSTALL A. Lloyd Morgan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animal psychology[J]. Society and Animals, 1998, 6: 13-29.
[33] COX G, ASHFORD T. Riddle me this: The craft and concept of animal mind[J].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 1998, 23: 425-438.
[34] SU X. The imagination of place and tourism consumption: A case study of Lijiang Ancient Town, China[J]. Tourism Geographies, 2010, 12(3): 412-434.
[35] 白凯, 胡宪洋, 吕洋洋, 等. 丽江古城慢活地方性的呈现与形成[J]. 地理学报, 2017, 72(6): 1104-1117. [BAI Kai, HU Xianyang, LVU Yangyang, et al. Study on the identity with placeness of slow living in Lijiang[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6): 1104-1117.]
[36] SU X. Tourism, modernity and the consumption of home in China[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4, 39(1): 50-61.
[37] SU X, CAI X, LIU M. Prostitution, variegated homes, and the practice of unhomely life in China[J].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9, 20(3): 407-426.
[38] BARUA M. Nonhuman labour, encounter value, spectacular accumulation: The geographies of a lively commodity[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7, 42: 274-288.
[39] PHILO C, WILBERT C. Animal Spaces, Beastly Places: New Geographies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M]. London: Routledge, 2000.
[40] HODGETTS T, LORIMER J. Methodologies for animals geographies: Cultures, communication and genomics[J]. Cultural Geographies, 2015, 22(2): 285-295.
[41] SRINIVASANL K. Conservation biopolitics and the sustainability epistem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17, 49(7): 1458-1476.
[42] CARTER J, PALMER J. Dilemmas of transgression: Ethical responses in a more-than-human world[J]. Cultural Geographies, 2017, 24(2): 213-229.
[43] KIERNAN M, INSTONE L. From pest to partner: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White Ibis in the more-than-human city[J]. Cultural Geographies, 2016, 23(3): 475-494.
[44] SRINIVASANL K. The biopolitics of animal being and welfare: Dog control and care in the UK and India[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3, 38(1): 106-119.
[45] 尹铎, 高权, 朱竑. 广州鳄鱼公园野生动物旅游中的生命权力运作[J].地理学报, 2017,72(10):1872-1885. [YIN Duo, GAO Quan, ZHU Hong. The excise of biopower in wildlife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Crocodile Park, Guangzhou[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72(10):1872-1885.]
Place Constr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Lijiang Ancient Tow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
YIN Duo1,2, GAO Quan3, LU Wei4, ZHU Hong1,2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Center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Southern China,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3.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81Victoria Street 188065, Singapore;
4.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grounded examination of more-than-human geography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 in the context of tourism. Based on qualitative methods including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 this article analyses how the human agents and pet dogs collectively shape the meanings of place in Lijiang ancient town, Yunnan, China. In particular, we explore the way in which pet dogs as non-human actor assemblage the network of tourism place and human-animal power relations. First, the meaning of tourism place in Lijiang is not merely the represen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but rather a complex and hybrid process that embeds into the fabrics of both human and non-human. Specifically, the pet dogs serve as an agent connecting the inter-subjective relationships and simultaneously, anchoring a sense of home among tourist migrants. Pet dogs also help tourist immigrants to form a social network of lifestyle migrants and establish group identity.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that facilitates immigrants to choose future lifestyles and destinations in a highly mobile society. Second, the interaction of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situated conditions of tourism consumption. Pet dogs were utilised as a cultural symbol that represents the romantic, authentic and exotic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of Lijiang. Yet, pet dogs are not negative recipients of tourism economy, but rather capable of affecting the mobility of human actors with their agency. Therefore, the consumption of place meaning and symbol in tourist destinations is a two-way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non-human actors and humans. Third, pet dogs are subject to a model of inclusion/exclusion premised on the order and discourse of human civility. Despite this, pet dogs cannot be unlimitedly controlled and manipulated by human beings because of their “beastly nature”. Instead, pet dogs in turn shape human agents behaviors and tourism space. In other words, biopower does not always operates through human beings but also through the dynamic and relational processes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 (pet dogs in this paper).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relational agency and subjectivity of nonhuman animals, and responds to the call of tourism research to analysing the more-than-human world constructed by both humans and non-humans. This research has made contributions in three aspects by bringing human-animal relationship into consideration. First,it provides useful insights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a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by placing the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 into loc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Second, by exploring how non-human animals participate the process of place-making, it provides a new typical case for the literatur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tudies of tourism place. Also, we seek to provide policy references for the tourism management and animal protection in Lijiang Ancient Town.
Keywords: place making;pet dogs;tourism migrants;tourism consumption;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
[責任编辑:刘 鲁;责任校对:王 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