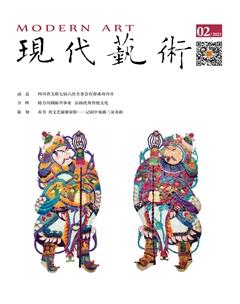不断重返魂灵的镜前
“从高处往下看
二郎滩渡口
酷似一个酒壶
赤水河流经二郎滩
再倒出去
都是美酒”
“给我一株红高梁
加上一株小麦
加上一瓢赤水河水
加上想象我们可以
创造一个市值万亿的企业”
某年某月苏东坡与兄弟夜游赤壁叹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生的飘忽与宇宙的永恒,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心里的隐痛。在倏忽万变的时代,令白驹过隙一样短暂的人生更显局促。其中有些人天赋使命,从自己出发,走过漫长的道路,站在事业人生的高峰,却依然像一个赤子,羞怯地面对所有的成功。反而对事业的缘起或本宗,保持谦逊的敬畏,他们像圣者一样自律,像使者一样勤勉,又像诗人一样深情;他们的事业往往有某种艺术性,而艺术又有经济属性。比如,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先生,他把科技与人文完美结合,让产品显现出艺术家的气质。
在我熟悉的企业界的朋友里,一个是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一个是郎酒的高管李明政,他们身在企业,却依然保持一颗诗心。据明政说,江南春酒量很好,可见他们俩是有交际的。李明政先生在郎酒工作近三十年,酒界不说,他在媒体圈、广告界也广为人知,但他似乎更醉心于自己的创作。他鲜于谈论自己的诗歌创作,即便几十年来,他的作品常被《诗刊》《星星》等国内一线刊物采用,多次入选各种年度选本。例如《两棵树》入选《诗刊》六十年诗选,《一张结满霜花的脸》甚至在中央电视台由周涛朗诵播出。他参加和组织过多次国际国内诗歌活动,在主流媒体中,他的诗歌作品实际影响已经比较广泛。
在李明政丰富的内心世界里:一方面,个人存在需要宁静的空间,需要足以与天地宇宙产生信息和能量的互动,无限抵达现实生活的诗歌语言和语言后面的精神,都需要孤独地参悟;另一方面,企业的商业运营需要与俗世生活勾连、交叉、渗入、迂回、妥协和让步,它赋陈在群体、团队、组织的持续运维,在极尽人世之喧嚣繁华和疲惫抽离。这种出世和人世的一体二元对立的矛盾,是如何分裂挣扎、又如何找到出路,在他的重要诗篇里,我们似乎可以读懂一点点。
最能体现作者内心世界冲突的诗作,当属作品《两棵黄桷树》,同在春天,一颗树的死亡黑影和另一棵树的蓬勃生机,形成了惊骇无比的反差:
一棵在我熟悉的城市
它站着死了
高楼大厦旁
一团巨大的黑影
在阳光下寂静成空虚
一棵在赤水河绝壁
它用网状的裸根
包裹一块巨石
把石头吃成水
吃成泥土
白生生的石头上
结满青翠的枝叶
这两棵命运迥然的黄桷树,是这个巨变时代人们心灵的两个世界的绝妙象征。一个是从中国农耕文明遗传下来的,根植于黄天厚土,甚至是绝壁石缝的坚毅随缘的中国人精神世界,经过几千年历史积累,极易生根发芽,开花散枝,把根系插进石缝,笑傲于陡坡岩石之上。这样的坚韧而乐观的精神能把石头和泥土当食物,给世界一个青翠的春天;也能带着祖先的记忆,越过白令海峡,从美洲最北到达最南,几千年后面对华夏民族的后人,可“眼里有石头一样的安静”(《甩石头打天的人》),是后农业文明的精神风貌。这么强悍的大树,其生命力是一群人的力量。
另一棵树是这片土地上一一二十年就走过西方国家两百年变革之路的背景下,脱离故土,人为矫造的代表,与绝壁石缝的树不同,这高楼大厦旁的树,吃的是钢筋喝的是水泥,沐浴的是闪烁的霓虹灯。钢筋是铁矿石的死亡,水泥是卵石的的粉碎,而霓虹是阳光的假象。死亡后再生、粉碎后重组、假象遮蔽真实,这是某种前工业化的逻辑或者技巧,于这样失魂落魄的生存环境,人们常常感到自我世界的伤逝和属灵的空乏,这一棵树,也就代表着一个失魂落魄的世界。
似乎,人类对地球的进攻历史,就是走出森林,不断让森林退化、土地沙化、河流干涸的过程。难怪他感叹“我开始憎恨人类,他们在天空砌满砖头,在泥土播种水泥”。人类对树的记忆,就是集体无意识对森林的记忆,已经深入人类基因干细胞。现代康复学有一个治疗认知障碍的方式,就是把人放置在水流、森林、草原等环境,唤醒基因中的远古记忆用以恢复认知功能,这种记忆的深刻和喜悦,在作者的另一诗作《白桦树》里,如此表达:
我是说白桦树……
我看到了白桦树,在出租车的灯光下
发亮。我有些睁不开眼睛,多么让人心动
我想说,让我,再看看白桦树
无论是黄桷树还是白桦树,无不是人类早期家园的寄托,在十分偶然的瞬间,作者的这种潜意识都会被唤醒,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是,无论我们如何眷恋农业文明的田园牧歌,历史也会不可逆转地把我们扔进城市文明的大潮,这种身心的分裂,是否有某种调和的出路呢?
从大米和鸡蛋,站到母爱的镜前
作者流传甚广的作品《从米出发》,书写了在飘忽的城市车流里,一个人像离开了水的鱼一样,游走于各种数据和合成的秀场的现代生活画面:CDP数据、KPI数据、财富数据、成功学数据,这些虚无而令人疯狂的数字,跟我们作为一个有灵魂的人毫无关系。那些没有思想的建筑物或商品,只是财富分配的介质。建筑物堆砌的城市总是扮演一个他乡的角色。在心里深处,妈妈所在的地方才是故乡,那里有母親双手劳作生产的一碗碗大米饭,这些米饭曾是我们的天,也是热乎乎可感知的爱。作者用“从米出发”这样陌生化的造句,把我们拉回我们出发的地方+照见母爱的样子:
坐下来
坐下来
你常说几天都没有沾一颗米了
母亲听了很困惑
所以你先坐下来
好好吃两碗饭
然后从米出发
——《从米出发》
如果说《从米出发》把我们从城市生活的恍兮惚兮中,拉回故乡母亲的温暖慈爱的生活空间里,另一首《鸡蛋》则表达了这份慈爱,有多么的绵长:
整个晚上母亲
蜷缩在厨房的角落
她右手拿电筒
左手将鸡蛋举在眼前
一个一个的晃
一个一个的照
多少年我一直这样
带着母亲照过的鸡蛋
离家
母亲的目光
照耀着我岁月里的每一个日子
我想说的是50年来
母亲给予我的每一天
是那样的好
鸡蛋之于中国孩子,在古老的乡村实在是有多种特殊意义,满月要吃红鸡蛋,红鸡蛋祝福的是吉祥、智慧和繁衍不息;由此沿袭的贫苦人家过生,妈妈要给过生日的人煮一个完整的鸡蛋吃下去,祝福新岁的平安健康。诗文里,母亲一个个用手电透光检验过的鸡蛋,自然富含了圆满、智慧、祈福、助力、财富等多种吉祥意义,一个母亲能够给孩子的所有祝福,都演绎在整晚窸窸窣窣检查鸡蛋的细小行为里,对一个孩子的爱,也从来不会像一个过期的鸡蛋,因“寡了”而变质。明政对我说过,他曾想把“鸡蛋”一诗的标题改为“母亲给予的爱从未寡过”。
作者在名利场的搏杀之后,总有这么一些幸运的瞬间,重返人生来处一一母爱镜前,发现自己某种不竭的动力源泉,照见自己的所想依恋的幸福模样。
从鹅卵石返回故园的宏大圣殿
2005发表于《诗刊》的组诗一一《赤水河》,最能表达作者身心是如何安放的。
有一次与诗人探讨这一组作品时,我把这组诗的诗眼浓缩到一个物件一一鹅卵石,诗人立即朗诵出泰戈尔的诗句“不是锤的打击,而是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这瞬间的联想,验证了赤水河的鹅卵石在诗人笔下具有多重要的意义。
在《大鸟:》里,作者认为,赤水河这一只时间的大鸟,这一只“雄美的大鸟”,在无限空间飞翔的大鸟,它
拍打着两岸的峭壁
用了亿万年或者一秒钟
赤水河将褶皱岩层的石块
孵化成羽翼下的卵石
——《大鸟》
庄子在《逍遥遂》里,把小鱼“鲲”,通过造化之手,化身为“鹏”,鹏之大也,大如时空运行的宇宙,赤水河这一只时间的飞鸿,对于个人来说,也只是生命的惊鸿一瞥,而无数生命的积累,像石头一样坚固久远,静躺在赤水河谷:
所谓沧海桑田
卵石看来不值一提
卵石指着身上的珊瑚斑说
这是180000000年的水做成的
(卵石说
我教你读这种大数字
一亿八千万年)
——《赤水河卵石如是说》
这些养育在赤水河里的石头,是娇媚的,又是矜贵的,他的娇媚是只能在水中开放,他的矜贵令他离开水面就死亡:
我……
看见细浪在寻找它
沙粒在寻找它
苔藓在寻找它
而那个卵石
在寻找自己的灵魂
——《踩死赤水河的一个卵石》
“他”就是灵魂,一个有万亿年历史的灵魂,一个只在河水里开花的灵魂,一个漂浮在尘世就会死去的灵魂,一个神灵可以依止的灵魂。万亿光阴的卵石、怍为大树食物的卵石、妩媚的卵石、矜贵的卵石、灵魄的卵石,诗人通过对赤水河谷鹅卵石的体悟,到达这条河的神殿,享受他们的指引,回到祖祖辈辈灵魂寄养的圣殿。
甩石头打天,返回无极,止于至善
基督徒练就圣洁的灵魂献给上帝;佛徒剔除心灵的灰尘,回归生命的空性,不再有生死疲劳;赤水河的儿子从大米和鸡蛋里看见母爱,从骨头骨灰里发现使命,在河水卵石里绽放灵魂。诗人到底要把自己的身心,透明而薄如蝉翼的一颗诗心,安置在何方?
……
她的祖先跨过白令海峡
乘独木舟漂洋过海而来
我是信的
甚至你说他们
是候乌叼了炎黄子孙的骨头
丢在美洲大陆上长出来的
我信
……
她的眼里
有石头一样的安静
有亿萬年的光阴
石头里有不屈的坚守
我去大娄山高山访贫问苦
在一家农户的灶房
也是一个40多岁的妇人
她的眼里
有石头一样的安静
有亿万年的光阴
谁人说的
我们是一堆呼啸而过的钢铁
他们是一群甩石头打天的人
神把一切看在眼里
只是神一直缄默无声
——《甩石头打天的人》
这些眼睛里有亿万年光阴的人,他们有精卫填海的宏愿、愚公移山的意志和夸父逐日的精进,在我们难以稽考的某个时代,或漂洋过海一一跨过白令海峡,乘独木舟而来;或越陌度阡——去大娄山高山访贫问苦。在地球遥远的角落,繁衍生息,哪怕是异国他乡,哪怕是极尽苦寒,他们的眼神,也像石头一样安静,有亿万年光阴。
在四川的民俗俚语里,甩石头打天,是形容无知无助的人,找不到人生困境时的出路,甩石头打天,希望打出一份新境界,给眼前的困境找到意外的解决方案,但这是非常浅层的意义。
在诗文里,这些华夏的子民,多少年来隐忍刚毅,靠自己不懈地耕耘和天人合一的相处哲学,即使生活在各种复杂的环境里,也保持清欢、安静、绵绵无绝,这是一种击破天的精神,给民族铸就了特殊的气质。
郎酒从赤水到中国,从中国到世界的生发过程,像极了“太极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
那么,这个“一”是什么呢?对于甩石头打天的人,愤怒可能是他的“一”,对于诗人,文字的不朽或身心安宁的原始渴望,可能是他的“一”;对于一瓶酱香酒,制造工艺中的“季节为令、山河同酿”的天道,可能是酒神的“一”。
出走半生,归来还是少年,在如此巨大冲撞力的社会洪流里,能够保持这份初心者少之又少,大多是人走到半途,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从李明政的诗篇里,我们看到他不断的返回故乡,如饥似渴的吮吸故乡的乳汁。他笔下那些赤水河风物之间性灵息息相关的隐秘逻辑——万物互灵。当这种互感的灵性,被现代物欲不断打岔、遮盖、变异之后,一个是否还能通过某种媒介接通身心的故国,能否找回故乡的乳汁,往往决定他能够到达的境界,幸运的是,他通过文字,在远方的家园之间,建立起多维度不断重返的体系,这或许是一种少有的幸运。
狄金森诗曰:给我一株三叶草,加上一只蜜蜂,加上想象,我可以创造一个草原。狄金森的三个一和李明政对郎酒的热爱,启发诗人写出题记上的文字,李明政的草原,就是这生花的文字,和遍布世界中国郎的豪情。
读李明政的诗歌,感知一个安静的智者,他如那一只“老鹳”,在城市与故乡的感情、意义、行为、画面的不断冲突里,他通过对母亲、父亲、故乡风物,赤水河的石头等途径,不断在文字里返回自己的故园明镜的前面,在镜中反复观察自己,审视现代社会,守望更深的自己。一面向前远行,另一面频频回首,提醒自己为何出发;在向前奔跑与初心不失之间,找到了某种调和或者出路,这个调和如果非要用一个形象来描述,那就是一个或者一群一一甩石头打天的人。
夏吉林XIA JILIN
独立诗评人,著名作家格非、宋琳等人的高足,上世纪80代末师承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历史哲学系的诸多名师。诗评风格往往超越文字具象直指人性、历史、造化与文化的魂魄,体系缜密视角新颖,颇得诗人们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