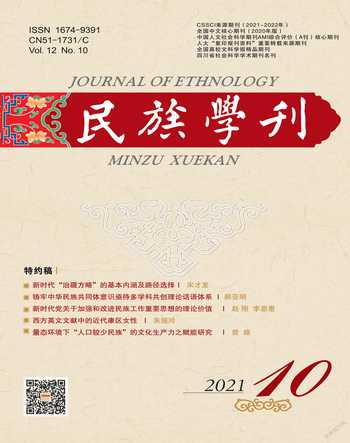清末民初来华西方学者民间文学译介中的文学观与民俗观
[摘要]清末民初,来华西方学者整理并翻译了大量中国民间文学,包括谚语俗语、歌谣民曲、民间故事等不同类型。在介绍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之时,西方学者通过序言、注释、图像,以及穿插其中的阐述,呈现出对民间文学生活属性、审美价值、中西差异的认识,而其中承载的民俗文化,具有收录方式多样、涉及主题广博、地域特征凸显等特征。藉由对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的考察,相关译介呈现出西人眼中的中国语言、文学与文化状态。同时,西方学者尝试探察中华民族国民性格、分析中西民俗异同,显现出模糊的民俗学学科意识。但与此同时,因缺乏明确的术语界定和系统的分类方法,概念不清、分类不明、内容杂陈等问题也较为突出,表明其民间文学观念和民俗意识尚处于初始的萌芽状态。总之,清末民初来华西方学者搜集、整理和翻译的中国民间文学著述,既是追溯国内外民俗学学科滥觞的重要史料,亦是其民间文学观念和民俗意识的直接映射。
[关键词]清末民初;西方学者;民间文学;文学观;民俗观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21)10-0039-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译事奏谕与翻译政策研究”(19BZS05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朱灵慧(1975-),女,土家族,湖北利川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史。湖北武汉 430073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集体口头创作,是集体记忆、民众心理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我国民间文学历史悠久,形态多样,内容广博。但直至“五四”之后,才引起学界的集中与广泛关注,开始展开系统搜集和研究。而在此之前,即清末民初,来华西方学者对我国民间文学表现出浓厚兴趣,将民间谚语、歌谣、故事等各种题材收集成书,译介西传,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我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的勃兴。
清末民初中国民间文学的译者群体,以来华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官为主,为学习汉语之需,或为方便传教布道,译介目的不同,视域各异。相关著述已然引发学界尤其民俗学界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洪长泰[1]、董晓萍[2]、张志娟[3]32-41等在论及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兴起的外来影响和外来思潮时,对这一时期部分译介有所阐述。亦有学者从国别的角度,勾勒美国学者[4]113-122和法国学者[5]43-56的中国民间文学翻译,将此一阶段相关译介纳入其中。除此之外,不乏对韦大列、卢公明等代表性译者,或具体译作展开的大量个案研究。笔者对清末民初来华西人中国民间文学译介的主要类型、选译篇目等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介绍[6]278-289。在上述研究基础之上,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大多译作附有前言后语,阐述材料来源、选材动机、翻译目的,或增加注解,补充阐发背景信息。换言之,序跋、注释、引言、图像等各类译作副文本,呈现了对民间文学传统与样式、各地民俗与风貌、民众生活与性格等的介绍或评论,引领读者了解中国语言表达、文学形态和文化传统,成为探查国内外民俗学学科发轫与发展的重要史料,亦成为其时西方学者民间文学观念和民俗意识的直接映射。
一、概览:来华西方学者民间文学译介
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宗教、信仰、伦理、民俗等等留有先民的心理痕迹和经验残余的语言符号”[7]10,涵盖内容广博,涉及题材多样。清末民初,英、美、德等各国来华西方学者,对中国民间文学表现出较高热忱,大量搜集整理,翻译介绍,涵盖谚语俗语、歌谣俗曲、故事传说等各种不同类型,掀起一股“中学西传”的浪潮。
来华西方学者首先便关注到中国民间谚语俗语。谚语语言凝练,内容丰富,是人们对长期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总结,蕴含了“民众在美感、道德、科學等方面的价值观”[1]164。相关译著收录数量多、涉及范围广。法国传教士童文献(Paul Hubert Perny)整理编译的《中国俗语》(Proverbes chinois,re cueillis et mi sen ordre,1869)收录谚语俗语441条;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编撰的《英华萃林韵府》(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2)含谚语700余条;英国传教士沙修道(William Scarborough )编译的《谚语丛话》(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1875)收译谚语2720条;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编译的《汉语谚语俗语集》(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1902)收集约8000多条中国谚语俗语。不仅收录数量多,著述中对汉语谚语俗语的形成、特性,价值以及翻译困难也做了深入细致的阐述。
其次是对歌谣的整理和翻译,对我国五四“歌谣运动”产生了直接且广泛的影响。司登德(George Carter Stent)搜集并编译了《二十四颗玉珠串》(The Jade Chaplet in Twenty-Four Beads,1874)和《活埋》(Entombed Alive,1878)两部民曲、意大利外交官韦大列(Guido Amedeo Vitale)收集整理了《北京歌谣》(Chinese Folklore:Pekinese Rhymes,1896)、荷兰籍美国传教士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编译了《孺子歌图》(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1900)、英国汉学家文仁亭(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er)整理翻译了《中国民间小调》(Chinese Ditties,1922)等等。其中,韦大列、何德兰的歌谣整理和翻译为学界广为关注,不仅当代学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研究,胡适、常惠、周作人等五四知识分子在随后著述中也多有论及。
谚语和歌谣短小易记,故常见原文、译文逐行对照翻译的方法。因其中富含传统文化、地方风俗、民间语汇,译者通常补充背景信息,对原文本进行“深度翻译”(thick translation,也有学者译为“厚翻译”),即“通过各种注释和评注,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8]84-85,从而使源语文化的特征得以保留。如明恩溥在翻译中增加评注,介绍历史人物、民俗文化等内容,“虽然部分有错,但仍不失为详细的注释”[1]164。韦大列在《北京歌谣》中,介绍了每首歌谣传唱时的场景和方式,再现出北京的生活情状和民俗风貌。文字副文本之外,插图、照片等图像副文本也在相关译作中频繁使用,如何德兰的《孺子歌图》,每首歌谣均附黑白照片,生动直观,带给读者画面感和既视感。
相较于谚语和歌谣,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民间故事的译介数量更为丰厚。民间故事“以散文形式叙事,有人物、情节,有一定的传奇或幻想成分”[9]44,既充满对现实世界的刻画,亦饱含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美国女传教士斐姑娘(Adele Marion Fielde)的《中国夜谭》(Chinese Nights Entertainment:Forty Stories Told by Almond-eyed Folk Actors in the Romance of the Strayed Arrow,1893),被视为“第一本以现代田野作业方式采辑的中国民间故事集”[3]35;美国学者戴维斯(Mary Hayes Davis)与周龙合作编译了《中国寓言和民间故事》(Chinese Fables and Folk Stories,1908);皮特曼( Norman Hinsdale Pitman)编译了《中国童话故事》(Chinese Fairy Stories,1910)和《中国奇书》(A Chinese Wonder Book,1919)。其它还有如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编撰的《中国童话》(Chinese Fairy Tales,1911)、意大利汉学家韦大利编写的《中国笑话集》(Chinese Merry Tales,1909)(由我国赴洋留学生吴仰曾译为英语)、法国耶稣会士戴遂良(Léon Wieger)编译了《近代中国民间故事集》(Folklore Chinois Moderne,1909),以及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搜集并译为德语版的《中国民间故事》(Chinesische Volksmarchen,1914),随后由马顿斯(Frederick H.Martens)又译为英语于1921年在纽约出版。西方学者的民间故事译介涵盖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生活故事、笑话、寓言、童话等多种类型。
以上所收民间故事既有选自经典文献的神话和传说,也有来源于活性形态的口头采录。由于篇幅略长,口耳相传中难以完全保持原本,故形成同一母题下各具特色的异文。翻译时大多采用译述之法,即不严格按照原文逐行翻译,“而对原作的内容进行概括和提炼”[8]123。译者根据听到或读到的中国民间故事,用其它语言复述。部分著述论及这一过程时,措辞分别为“用英语讲述”(told in English)、“阐译”(translated and illustrated)、“译述”(translated or paraphrased)等不同方式。民间文学在流传过程中,因时空变化具有流动变异性,[9]10而在以英语、法语等其它语言传播时,无疑表现更为突出。抛开为传教目的的主观阐发不论,这一过程本身难免造成原本内容的变形和歪曲。“艾伯华曾批评这种故事记录是不成功的”,认为经过西方人转述的中国故事已经变味,但其故事资料中的母题大致没变,因此“这批资料依然可用”。[2]99
总之,西方学者译介的民间文学,类型多样,涵盖面广,记录了北京、福州、汕头、上海、天津等各地语汇与习俗,并以英语、法语、德语等多种语言,再现出中华民族的群体记忆。尽管“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关注,大多是其宗教和社会活动的副产品”,初衷“仅仅是认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手段”,[4]114但客观上,一定程度促进了我国民间文学的整理和传播,亦促发了近代民俗学的兴起。相关著述大量使用各种类型副文本,包括译作序言、注释、评述、插图、照片等,是对中国民间文学、民间习俗、民众风貌的注解,也是其时西方学者民间文学观念和民俗文化意识的直接映射。
二、民间文学观:生活属性与审美价值
来华西方学者以民间文学为媒介,通过收集整理和翻译介绍,旨在学习中国语言,探察民族心理,洞悉思想观念,以了解中国境况和国民性格,为传教等其它活动服务。在收集整理和翻译中国民间文学时,有意无意间,在长篇论述或只言片语中,常论及中国民间文学的来源、题材、内容和形式,阐发对其生活属性、审美价值,以及中西差异的认知,显现出民间文学观念的早期态势。
民间文学“是民众宣讲故事、抒发情感、记忆过去、阐述观念的一种方式”[10]42。西方学者相关著述序言导语中常见对民间文学生活属性的阐述。如谚语是“中国人思维模式的呈现”(as exhibitions of Chinese modes of thought),是“以最凝练的语言,对人们长期生活经验的总结”。[11]11掌握谚语,对了解中国民众,尤其对传教布道,不无裨益。[12]1又如民曲是人们自然思想的表达,意义深邃,流传广远(of the deepest and most wide-spread tendencies of natural thought)。[13]4另外,故事和歌谣有助于了解人类社会历史,保留(keep alive)习俗和信仰,显现相同条件下人类思维的基本特性。比如民间小调是人们辛苦劳作之时的放松方式(as a recreation from more laborious work),这一轻快的中国文学令人产生愉悦之感,为中华民族带来的乐趣超乎想象。[14]1-3无论是将民间文学视为生活的总结、思想的表达、习俗信仰的传承,亦或劳作之余的放松,西方學者已然认识到民间文学的社会特性,即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融为一体,故以此切入,意欲了解和洞察中国社会。
他们同样也认识到中国民间文学独有的审美价值。如韦大列指出,歌谣除可以帮助读者“掌握部分不常见到的词和短语”,“了解中国日常生活的景象和细节”之外,还可“认识到真正的诗蕴藏于中国流行歌谣中”。部分歌谣短小凝练,却感人至深,就是诗句(simple and touching and may be “poetry”)。他提醒读者关注歌谣中的韵律,并称创作歌谣的人目不识丁,对书面语言一无所知,却在其中展现出与欧洲,尤其是意大利诗歌相似的韵律。这些歌谣和民众的真情实感,或将催生出一种新的民族诗歌(a new national poetry),即“原生态的诗歌”(uncultivated poetry)。[15]7-10对于古代中国的童话和传说,马顿斯称,与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一样,宝石、黄金和五彩丝绸都散发着东方特有的光芒,其中拥有大量东方独有的奇幻和超自然的表现方式(an oriental wealth of fantastic and supernatural action),但又各自具有特色(an exotic note distinct in itself),有的富含诗意(exquisitely poetic),有的将读者带回中国骑士时代(to the Chinese age of chivary),有的作品如《孙悟空》则是奇幻的巅峰(the summits of fantasy),还有怪异的妖术(weird sorceries)等等,[16]5-6概述了中国童话和传说的多样性表现方式。
这一时期对汉语谚语俗语的讨论尤为深入细致,涉及特性、分类、价值,以及形式等各个方面,呈现出西方学者对中国谚语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较为深刻的认识。就文学性而言,童文献认为,谚语和俗语是一个民族的直接反映。汉语俗语大多句式优美,内容深刻,其简洁(mesure)、韵律(cadence)、和谐(harmonie),尤其对仗(antithesis),在平淡而单调的欧洲语言中难以再现。[17]沙修道指出,亚洲被公认为谚语的沃土(the soil in which it grows to most perfection),而中國尤其如此。沙修道称,西方对“proverb”一词的定义,无一能准确或较为准确地描述汉语“俗话”的内涵。其表述简洁(brevity)、语义凝练(terseness)、琅琅上口(beauty)、结构对称(symmetry),为英语和其它语言难以企及(inimitable),并进而指出,对子、联句、押韵等方式构成的对句是汉语谚语主要表现方式。[18]iv明恩溥则尤其强调汉语谚语的谐音(homophony)、凝练(compactness and force)、对句(couplet)等独有形式造成的理解和翻译困难。[11]11-28显然,汉语谚语短小精悍,长短不拘,上下对偶,句尾押韵,与其它语言迥然有异,具有独特的表述手法和文学价值。
此外,在论及中国民间文学的社会性和文学性特征之时,还不时展开中西异同的对比。既认识到中西方民间文学存在或多或少的共性,同时也指出其中显著的差异性。如将中国童话与日本童话作为“姊妹篇”呈现,但二者尽管一样离奇有趣(equally quaint and delightful),却反映出截然不同的民族精神。[19]通过对比,突显出中国民间文学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伴随着民族历史与民众生活,承载了民族性格和历史传承,从内容到形式都独具特色。但与此同时,其中同样蕴含了民间文学的世界性特征,即人类普遍的思想情感和相似经历,故内容主题和体裁样式均不乏相通之处。
三、民俗意识:多样收录与广泛涵盖
民俗“即民间风俗,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20]1。谚语俗语、歌谣民曲、传说故事等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既是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明末清初来华西方学者的民间文学译介中,相关篇目或条目的选录本身便透射出对中国民间习俗的观察和理解,其中对各种民俗事象的记录方法、评注和补充叙述,则进一步显现出其时西方学者模糊的民俗观念和意识。
首先,记录民俗是民俗学研究的前提[21]6。清末民初的中国民间文学译介中,出现多种民俗记录的方式。其一,实现在不同语言中的文字记录。尽管书面记录必然丢失民间文学原来味道,但书面形式记录民间文学依然必要。[22]1-2由于材料来源不同,文字化的具体过程略有差异。一类是根据民间口头讲述,以不同语言转述,并实现文字化,如生活故事、民间传说大多如此;一类是根据民间口头讲述,以同一语言文字记录,同时还翻译成另一语言的文本,如谚语俗语、歌谣等,相关收录含汉语原本记录和其它语言的译本;另一类因直接选自《聊斋志异》《笑林广记》等各种已有文字文本,故仅为不同语言的文本转换。其二,增加注音。在前文所列谚语俗语收录中,童文献、沙修道、卢公明均以威妥玛拼音的方式,为汉语文本每个字标注了读音,明恩溥则对部分字词予以标注。“‘发音的呈现方式是民间文学与其它文学的根本区别,民间文学的魅力和多样性都取决于发音”[7]44,因此,读音注音既是对民间文学“口头性”特征的尽力再现,亦尽可能保留了民俗的地域性表征,显现出使书面记录接近于口头传统的意识和努力。其三,补充注释。“一个符合当地口头传统的记录文本,必须要有注释”[7]9,可见注释对保留口头传统的重要意义。明恩溥以评注解释谚语含义,司登德增加注释介绍标题和曲目背景信息,文仁亭对小调哼唱的地域、方式、情状阐发说明。其四,插入图像。清末民初中国民间文学译介中,主要涉及两类图像文本。一是随着19世纪摄影技术的逐渐使用,西方学者开始运用镜头记录,如何德兰《孺子歌图》中,每首歌谣均附与内容相关的黑白照片,直观再现了北京民俗文化,成为不可多得的民俗视觉文本。二是插图的使用,具体则指斐姑娘在《中国夜谭》,皮特曼在《中国童话故事》和《中国奇书》中,均有多幅配图,且由当地艺术家所作(illustrated by Chinese artists)。以《中国夜谭》为例,题名“射箭”(Archery Practice)、“八仙图”(Eight Genii)、“鞋铺”(A Shoe Shop)等的插图作品,成为中国文化民俗的生动刻画和影像叙事。
由上可见,清末民初西方学者在译介中国民间文学之时,至少采用了文本、注音、注释、图像等多重方式呈现中国民俗,共同构成立体的活态记录,对保留民俗的本真性,提供“全息”文化志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换言之,民间文学的搜录和翻译并非语言文字和内容梗概的简单保留和转换,其中的说唱方式、地域特色、文化传承均成为不可分割的重要构件。因此,吸纳文字文本、影像文本、声学文本等多模态样式,通过相互映射和叠加,有助于还原中国民俗文化的深厚语境,促进“译本民俗叙事的建构”[23]99-108。尽管上述民俗收录方式尚不完备,并且注释和图像均不可避免包含主观阐释和画面选择,但依然初现出清末民初传教士和汉学家的民俗意识。
其次,来华西方学者的民俗意识还体现于多样性涵盖,记录的民俗来源广博,内容多样。广义的民俗“不仅指涉如赛会社戏那般乡间风俗活动,也指涉了在传统观念指引下的日常生活习俗习惯,后者尤其会带有某种规范性、训诫性的价值观念”[24]98。民间文学作品本身便是语言民俗之一,承载了民族知行观念,描述了日常生活景象,其具体内容则涉及民俗活动、礼仪、信仰等不同方面,显现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传承的喜好、风尚、习俗、禁忌等多样性主题。在译介民间文学的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类型各异的民间习俗。以《北京歌谣》为例,译文注释中含出嫁女儿“回娘家”、初一十五“烧香”等风俗,婆媳、夫妻、姑嫂等传统家庭关系,白塔寺、玉兔等共同文化想象,向西方读者描绘了中国民间传统和惯习。在歌谣“拉大锯”注释中,详细介绍了“搭大棚”“唱大戏”的文化背景,即中国传统房屋房间不大,遇婚丧嫁娶等重要日子宴请客人,则在院子里“搭大棚”,有钱人家还请戏班子前来“唱大戏”。[15]1-2又如“小五儿”的注释中,介绍了中国家庭为孩子取的“奶名”(亦称小名,乳名),即根据排序被依次取为“一子”“二哥”“三儿”“四儿”等,韦大列称这些乳名仅依排序而来,类似西方Charles,John等教名。[15]42-43再如“两枝蜡”的注释介绍了老北京祭灶习俗,腊月二十三祭灶王爷,为防止向玉帝说坏话,专门送上关东糖黏在灶王嘴上。[15]135-137这一习俗在明恩溥的谚语收录译介中也有论述,称“中国祭灶王爷的习俗产生了很多相关俗语”,如“灶王爷下锅台,离了板了”“灶王升天,黏着嘴咧”“灶王爷回家,一褡儿新”等等。[11]202-204这一时期,不同著述、不同题材的民间文学形成互文,共同勾勒出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各类传统习俗风尚。在关注我国形式各异的民俗时,不时将故事母题或民俗习惯与西方国家相互比较,如韦大列在介绍玩泥巴、打花巴掌等多种孩童游戏时均指出,外国孩童有类似玩耍活动和方式。
西方学者对中国民俗多样性的认识还体现于对地域性的强调。沙修道在翻译中尽力保持汉口方言中的韵律[18]ii,“斐姑娘”记录了潮汕民间故事,韦大列、何德兰保留了北京方言,译者大多意识到各地语言和民俗的地域性和差异性。《中国民间小调》收录了湖北、江西、黑龙江、安徽等各地民间口头传承的小调,译文后注释多以“该小调流传于……”(This song is current in...)开头,介绍其起源和流传地,凸显出较强的地域意识。同一母题的故事,或相似内容的谚语、歌谣,在各地存在表现手法的差异性。明恩溥在“汉语谚语的异文”(variations in Chinese proverbs)部分,指出“各地表现形式差异”(the forms in which they are heard in different localities,may vary widely)[11]28-32,并在第六章从地理位置、各地历史、特殊习俗等角度,专门讨论了地域性谚语的特点。我国民俗学者李家瑞曾撰文论述“三宗宝”谚语,称“中国各地方常常把自己地方上所特有的事件,或是所特产的物品”联合起来作为本地的“三宗宝”。[25]4-5而这一“三宝”法在明恩溥的著述中便已有所论及,称各地常将三样地方特色编为一组(a little bundle of three),称为宝,模仿佛教“三宝”法( in imitation of the Three Precious Ones of the Buddhists),如“北京城,三种宝,马不蹄,狗不咬,十七八的闺女满街跑”“保定府,三种宝,铁球,列瓜,春不老”等等。[11]130-131可以看出,西方学者对地域民俗已有较为深入的观察和了解。
不仅如此,西方学者透过对民俗文化的收录和译介,阐述了中华民族在思想观念、国民性格、历史传承等方面的特性。清末民初“涌入中国的西方人大多数都带着种族偏见和文明傲慢”[26]24,有对中国形象的扭曲丑化,但也不乏正面评价。如斐姑娘指出,性格决定命运,对个人或民族都是如此。书中故事,为中国民众原创,蕴含其对生活的憧憬。斐姑娘尤其提到,与其它国家人民相比,中国人具有目光长远(far-sighted)、勤俭节约(waste less)、乐于奉献(extreme self-sacrifice)、善于学习(ability to learn)、吃苦耐劳(to endure)等诸多优点。同时还指出,中华民族坚韧不拔(a persistent nation),拥有这些特性,未来如何,对其它民族将产生何种影响,值得深思。[27]7-9戴维斯用“沉思、温和和抽象”(contemplative,gentle and metaphysical)描述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并称中国人以独有的方式,深刻反映并解開了世界的谜团。中国人的思想在经年累月中日益发展成熟,随着对其思想之广博(richness)、深邃(depth)与美妙(beauty)的了解,增强了对其价值观念的认识。而要捕捉东方思维的神秘魅力(the secret of its mysterious charm),必须要有开放的思想和强烈的共鸣(an open mind and the wisdom of great sympathy)。[28]5-6总之,以传教士为主的上述西方学者,选择以译介民间文学为路径,了解中国语言文化等传统习俗,正是基于对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这一本质特性的认知。
民间文学的译介,不可避免地关涉民俗文化收录方式、多样主题和地域、民众性格和心理,自然呈现出对民俗类别、地方特色、表现形式和社会功能的态度与认识。确如文仁亭所言,“民俗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蕴含丰厚信息,人们正在开始尝试发掘其全部意义”[14]1。可以说,清末民初的西方学者掀起了一股关注中国民间文学,考察中国民俗文化的浪潮。
四、结语
相关译介呈现出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文学样式,也映射出西人眼中的中国语言、文学与文化。来华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审美价值,而其中承载的民俗文化,具有收录方式多样,主题内容广博,地域特性凸显的多重特征。西方学者藉由对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的考察,尝试探察我国民族心理特征、找寻中西民俗异同,显现出模糊的民俗学学科意识。但与此同时,因缺乏明确的术语界定和系统的分类方法,概念不清、分类不明、内容杂陈等问题也较为突出。总体而言,其民间文学观念和民俗意识尚处于初始的萌芽状态。
这一时期,西方民俗学刚刚兴起,中国民俗学正处发轫之际,对相关著述展开文本细读和系统爬梳,理性分辨,宏微并行,有助于厘清中西民俗学在发生与发展之中的相互作用与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上述民间文学的译者大多带有传教目的,故不乏“以自命高尚的救赎者的身份审视着中国和中国的文化”[29]17,扭曲甚而丑化中国形象。如“在热心传播神话、传说以及相关民间信仰、宗教习俗的同时,也散布并强化了对中国人、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神话的诸多肤浅、武断的偏见”[30]155-160,因此务必警惕相关认识中的功利性和狭隘性。从收录的角度来看,其中所含大量对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客观公正的介绍与注解,以及留存的文本、注音、图像和注释等资料,数量可观,可资借鉴,是追溯国内外民俗学学科滥觞的重要史料,亦为当今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走出去”留下启迪,借此探讨以何种翻译方法,讲好中国民俗故事。
参考文献:
[1][美]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新译本) [M].董晓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董晓萍.现代民间文艺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张志娟.西方现代中国民俗研究史论纲(1872-1949)[J].民俗研究,2017(2).
[4]张多.美国学者搜集整理、翻译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史和方法论[J].文化遗产,2019(2).
[5]卢梦雅.早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民俗的辑录和研究[J].民俗研究.2014(3).
[6]朱灵慧.由民间到海外:清末民初来华西人之中国民间文学译介[J].华中学术,2021(第36辑).
[7]万建中.民间文学的再认识[J].民俗研究,2004(3).
[8]方梦之.翻译学词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9]段宝林.中国民间文学概要(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10]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Smith,A.H.Proverbs and Common Sayings from the Chinese[M].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2.
[12]Scarborough,W.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M].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5.
[13]Stent,G.C.The Jade Chaplet in Twenty-Four Beads:A Collection of Songs,Ballads,etc.,from the Chinese[M].London:Trübner & Co.,1874.
[14]Werner,E.T.C.Chinese Ditties[M].Tientsin:The Tientsin Press,1922.
[15]Vitale,G.A.Pekinese Rhymes[M].Peking:Pei-tang Press,1896.
[16]Wilhelm,R.The Chinese Fairy Book[M].Translated by Frederick H.Martens.New York:Frederick A.Stokes Company,1921.
[17]Perny,P.H.Proverbes Chinois[M].Paris:Firmin Didot fre?res,Fils et Cie,1869.
[18]Scarborough,W.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M].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5.
[19]Giles,H.A.Chinese Fairy Tales[M].London:Gowans & Gray,Ltd.,1911.
[20]鐘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1]张举文.民俗影视记录与数字时代的民俗学研究[J].民间文化论坛,2021(3).
[22]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载[J].歌谣,1922(2).
[23]刘翔.伊维德说唱文学英译副文本德民俗叙事建构[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9(6):99-108.
[24]张春茂.鲁迅民俗观论析[J].民俗研究,2017(6).
[25]李家瑞.三宗宝[J].歌谣周刊,1936(11).
[26]吴友富.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7]Fielde,A.M.Chinese Fairy Tales:Forty Stories Told by Almond-Eyed Folk[M].New York and London:G.P.Putnams Sons,1912.
[28]Davis,M.H.,Chow,L.Chinese Fables and Folk Stories[M].New York:American Book Co.,1908.
[29]李娅菲.镜头定格的“真实幻像”——跨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形象”构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0]杨利慧.一个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神话——倭纳及其《中国的神话与传说》[J].湖南社会科学,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