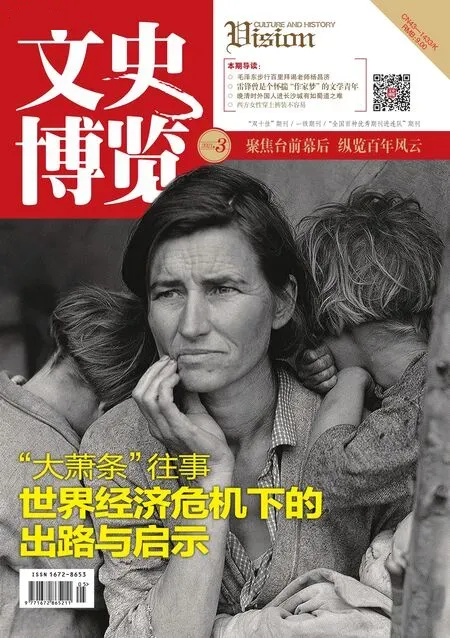忆战火中的父母爱情

1946 年沙飞、王辉夫妇合影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一首《松花江上》的歌曲迅速传遍中国大江南北。广东省汕头市电报局职员沙飞(原名司徒传)和王辉(原名王秀荔)热血沸腾,他们思考着如何报效祖国。在他们的推动下,电台成立了一个救国会,他们都被选为常委。救国会的工作主要是捐款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出版刊物《醒来吧》。1932 年“一·二八事变”后,他们的募捐工作更加紧锣密鼓,全台的人都很热心。他们还增加通报时间,专门收集上海第十九路军抗战的消息,然后为汕头市民报道。
在共同的抗日救亡中,1933 年3 月,沙飞和王辉结婚了,他们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不久,我的大哥司徒飞和大姐司徒鹰相继出生,家中充满了欢乐。
为摄影,父亲“抛妻弃子”
如果不搞摄影,父亲沙飞应该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兄长、好儿子,整个家庭很温馨。但为蜜月旅行买的照相机使父亲对摄影产生了兴趣,他逐渐迷上这小黑匣子。当时他是电台的特级电报员,每月有150 块大洋的优厚工资收入,给祖父母寄钱后,留下的钱几乎全用在了摄影上。
那时的汕头,日本军舰常耀武扬威地游弋于港口,水兵上岸大摇大摆盛气凌人。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积极寻求救国出路。父亲认为摄影应该、也一定可以为抗日救亡服务,因此努力钻研摄影技术。
1936 年初,父亲拿来一本外国画报给母亲看。里面有几幅照片,是1914 年6 月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青年枪杀的场景。这几张照片,从此改变了父亲的人生。他激动地说,我要当摄影记者,我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
1936 年6 月,父亲背着照相机,乘着小木船,颠簸几个小时,来到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广东南澳岛。他以自己特有的敏锐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对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南澳岛率先并多次作了摄影报道。
1936 年10 月,父亲又因为拍摄并发表鲁迅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及其葬礼的摄影作品,引起社会广泛震动。
1937 年1 月初,父亲到达抗战文化名城广西省府桂林,踌躇满志地准备在这里举办个人影展。但母亲一直认为摄影不是职业。父亲为了摄影离开家,四方奔波,没有固定工作、固定收入,只挣点稿费,这样下去,这个家还要不要?再加上母亲当时也参加了一些抗日运动,照顾两个孩子已是力不从心,所以考虑再三后,她给在桂林的丈夫写了一封信:希望你能尽快回到汕头,否则提出离婚。

沙飞镜头里的鲁迅(1936 年)
这封信如晴天霹雳,几乎使父亲疯狂、崩溃。他曾写道:“……痛哭过甚至企图自杀过”,但他终于“以衫袖揩干了热泪,执起笔来,写下八个字‘誓不屈服,牺牲到底’,然后大笑起来,回了妻子一封同意离婚的信”。
母亲本来认为毕竟是恩爱夫妻,又有两个孩子,父亲收到信后一定会立即回家,决不可能同意离婚。但她万没想到,父亲竟然会弃家搞摄影。她了解他一旦决定就决不会回头的脾性,只得无奈地吞下了自己酿的一杯苦酒。
桂林影展闭幕后的第10 天,卢沟桥事变发生。8 月15 日《广西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沙飞的文章《摄影与救亡》:“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工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
这是父亲参加抗战的宣言书。随后,他带着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豪情满怀地奔向沙场,成为一名战地摄影记者。他要见证历史、记录历史,实现他报效祖国的理想。
为抗日,母子分离近两年
其实1936 年冬,母亲已经背着丈夫参加了“潮汕抗日义勇军”,搞读书会、新文字运动,1937年9 月即已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8 月“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正式宣告成立,母亲是发起人之一,任理事。她在青抗会用的名字是王玉珠,1940 年到重庆后改名为王辉。
母亲在广东汕头、梅县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随时可能被捕、牺牲,所以她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恰逢组织上安排她去找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联络到南洋华侨中募捐,买武器、弹药,在潮汕地区搞抗日武装斗争,趁这个机会,她就把两个孩子送到了香港战时儿童保育院。从此,汕头市一个温馨浪漫的小康之家彻底破碎,父母亲各自走向抗日前线,一双儿女流落为难童,一家四口天各一方。
1940 年9 月,母亲离开广东到了桂林,在李克农领导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其间,母亲一直牵挂着两个孩子。后来香港战事吃紧,她便向李克农提出,可否请廖承志撤离香港时将自己的两个孩子带出来。李克农说,现在香港十分混乱,廖承志工作很忙,自顾不暇,没有办法。年底,母亲收到香港朋友吴伟机来信,说香港保育院已撤退到贵阳。
1940 年12 月,母亲奉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她乘八路军军车经过贵阳休息时,有意识地翻阅当地报纸,在一张报纸的下角果然看到一则香港保育院一批儿童到贵阳的消息。她赶紧联系,在贵阳八路军交通站负责人袁超俊的陪同下,终于在一座被日本飞机轰炸过的破楼里,找到了两个孩子——7 岁的司徒飞和5 岁的司徒鹰。兄妹两人经过长期逃难生活,骨瘦如柴、眼睛发炎、皮肤溃烂,和街头小叫花子没有两样。当时已是寒冷的冬天,他们还没穿棉衣,晚上睡觉没有棉被。他们望着跟前面熟而又陌生的女人发呆,母亲一把将两个孩子拉过来,紧紧搂抱着,亲吻着,叫着他们的乳名,他们才慢慢地胆怯地喊出了“妈妈!”母子三人悲喜交加,抱头痛哭。
袁超俊将两个孩子从保育院接到住所,帮他们洗身上溃烂的疥疮,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办事处给他们发了棉被和新灰布棉衣,医务室的医生治愈了他们的眼病和身上的疥疮,那段苦难的生活终于结束了。
随后,李克农命令身上带有绝密账本的母亲与办事处人员按规定时间离开贵阳。眼看要再一次与孩子分离,母亲于是请示李克农,希望组织将两个孩子送往延安。李克农要袁超俊电话请示在重庆的周恩来。12 月底,母亲抵达重庆。在周恩来安排下,不久,两个孩子也随贵阳交通站全体人员一起撤离到重庆,回到母亲身边。
1941 年1 月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决定部分人员及家属撤到延安。为此,大哥改名为王大力(即王达理),大姐改名为王小力(即王笑利)。到延安后,大哥大姐到延安保小读书。
而母亲仍留在重庆工作。此时母亲担任中共南方局会计兼出纳。周恩来、董必武等用钱都在母亲那里支取,给她收条。她用最薄的纸做账页。每月终,她把账结清,然后交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审核,之后把单据销毁,在账页上签名做绝密件保存。有几次周恩来叫她到办公室,将捐款现金交给她,让她当场清点。周恩来再三嘱咐母亲,钱来之不易,要绝对保密,如果暴露,就会追查迫害捐款人,将造成极大的损失。
因为工作原因,母亲和周恩来、邓颖超交往甚密。她后来还跟我们讲过一些周恩来的事——
当时党中央为照顾周恩来,发给他180 元保健费,母亲把钱拿给周恩来。但周恩来说,我身体很好,不需要,小超当参议员有津贴,够我们两人用。母亲说,这是中央决定发的,你不要,我不好处理。说完把钱放在他办公桌上就出去了。后来知道,周恩来把这笔钱给了有实际困难的同志。
周恩来当时在公开场合穿的一身西装,是他在苏联休养时做的,裤子早就磨破了。邓颖超找母亲要一块布补这条破裤子,母亲觉得周恩来穿得太寒酸说不过去,便从周恩来的警卫员那里要了那条裤子做样,买了料子,送到裁缝店做了条新裤子,做好后不敢送去,就交给了邓颖超。为此周恩来还把母亲批评了一顿。
战火中破镜重圆

沙飞拍摄的白求恩在山西五台松岩口村模范医院给伤员动手术的场景(1938 年)
1942 年下半年,母亲患了肺结核病。病中的她看到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抗战中的八路军》及沙飞主编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终于懂了父亲:他在用照相机记录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壮丽画卷,为抗战服务。当初那么坚决地反对他搞摄影,真的错了。他现在个人生活怎么样了?想我和孩子吗?还恨我吗?坚强的母亲掉下了眼泪。
邓颖超看到她情绪低落,主动跟她聊天,讲自己在长征途中患了肺病,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坚持走到陕北的往事,鼓励她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母亲跟邓颖超大姐谈了自己与沙飞的关系。邓颖超说,既然你们俩现在都参加了革命,如果他现在还没成家,就应恢复关系。谈话后母亲似乎看到希望,心情轻松了很多。经过一段时间休养,她终于病愈,恢复正常工作。
1944 年3 月,母亲被调往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其间,她向从晋察冀边区来的同学打听沙飞的情况,得知沙飞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且还没有结婚,一向冷静沉着的母亲沉不住气了。邓颖超了解到情况,建议我的父母恢复关系。于是母亲马上写了封信给父亲,告诉他自己在延安学习,两个孩子也在延安上学。母亲原来从不跟孩子提及他们的父亲,现在可以高兴地告诉他们:爸爸叫沙飞,在华北前线晋察冀军区搞摄影,是画报社主任。孩子们也高兴极了。

沙飞作品《战斗在古长城》(1942 年)
有一天,未满12 岁的大哥带着妹妹及项英的儿子项阿毛等几个孩子去杨家岭周恩来那里玩。在院子里,邓颖超拿出《晋察冀画报》给孩子们看。大哥一边翻着画报,数沙飞拍了多少张照片,一边很自豪地对小朋友讲这是自己爸爸的作品。阿毛告诉他,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现在就在周恩来办公室。大哥找到聂荣臻问:聂司令员,您认识沙飞吗?聂荣臻一边回答认识,一边打量眼前这个穿灰布制服的少年,发现他长得挺像沙飞,马上问,你是沙飞的弟弟?当听到“我是沙飞的儿子”时,他愣了:“什么?沙飞有这么大的儿子?”大哥于是又拉着笑利说,这是我妹妹。聂荣臻既惊讶又高兴,叫大哥给父亲写信。
聂荣臻马上发了一封电报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政治部主任朱良才接到电报后,当天通知了父亲。父亲看到电报,愣了很久才回过神来。朱良才征求他本人对复婚的意见,父亲毫不犹豫地立马明确表态,我愿意与她复婚!并立即亲自回复电报。父亲的电报是:信收到,即带飞儿来此。
母亲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
1945 年6 月,母亲奉命调往晋察冀军区。在那个抗战即将胜利的7 月,父母亲终于团圆!
他们愉快地度过了“第二个蜜月”。那些天,他俩晚饭后手拉手在村外河边散步,那么亲密、幸福、美满。父亲的脸上经常挂着笑容,精神振奋、情绪高涨。大家都受到了感染,为他们高兴。
一个月后,日本投降了。神州大地举国欢腾。年底,两个孩子从延安到河北张家口与父母亲团聚。那天画报社办公室坐满了人,大人们叫俩孩子辨认父亲。有的人出来说,我是你爸爸,搞得大姐不知所措,还是大哥凭感觉认出了父亲。父亲一下子把两个孩子拥进怀里,久久地亲吻着,妈妈则任由幸福的热泪默默地流淌。
在以后的4 年里,他们又有3 个孩子陆续出生。抗战前的四口之家,变成七口之家,这是我们家难得的一段安宁幸福的日子。
一场劫难,天人永隔
没想到,命运再一次使这个家庭遭到重创。
父亲是南方人,身体本来就不好,还有肺结核病,到北方以后,战争太残酷,战友的牺牲让他深受打击,加上长期积劳成疾,久之精神出现了一些异常。1949 年12 月,父亲在石家庄和平医院枪杀了为其治病的日本医生。1950 年3 月,他被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处以死刑,终年38 岁。
父亲出事时,母亲刚调到北京10 多天。决定处决父亲的通知下达时,母亲正出差到天津,处决完了才通知母亲,父亲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知道消息后,母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星期没有出来,眼泪全哭干了。
那段时间,她把很多事情想透想通了,带着5个孩子,她必须面对现实。此后几十年,为了家庭和孩子,她默默承受着重担,从来没有说过我父亲一个不字。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别人搞了个爆炸性新闻,说父亲是被共产党枪毙的。当天母亲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家。旁边一个人说,看着你们母亲,不要让她自杀。然而她很坚强地说,我不会自杀,做人清白,什么都不怕。这么多年的苦难煎熬,她已经练就了一颗强大的内心。后来她还说,不应该怪那些批斗她的人。
1985 年6 月8 日,北京市精神病医学鉴定小组的医学鉴定书正式签署,临床诊断沙飞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枪杀日籍医生津泽胜时正处于疾病期,属于辨认障碍,应判定无责任能力。1986年5 月19 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做出新的判决: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1950 年2 月24 日法字第九号判决,恢复沙飞军籍。1986 年6 月11日,中共北京军区纪检会做出决定,恢复沙飞党籍。
2005 年5 月,母亲安详地走了。这些年来父亲平反了,父亲的作品也被公之于众,她可以没有遗憾地去跟父亲团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