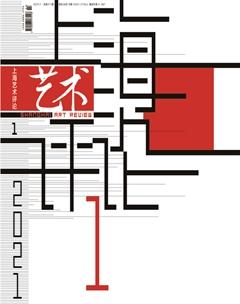现实题材戏剧如何获得超越性
张之薇
作为戏曲现代戏创作重要省份的河南,在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优秀剧作家还是优秀导演均以群体形式出场。2000年河南的《香魂女》在戏曲界一炮而红,随后2004年的《常香玉》,2014年的《焦裕禄》,2015年的《风雨故园》,2016年的《秦豫情》,1随着这些打着河南创作人标签的戏曲现代戏作品一一亮相,也让编剧姚金成、陈涌泉、杨林,以及导演李利宏、张平、张俊杰等创作者渐入全国视野。笔者以为,河南戏曲现代戏的崛起得益于话剧人向戏曲创作的渗透,同时也离不开创作者们对现代戏现代精神的把握,以及现代戏样态的重新思考。
在这些创作者中,剧作家杨林是笔者始终关注的一位。细数杨林的作品,从京剧《霸王别姬》(2004)到豫剧《常香玉》(2005),从话剧《红旗渠》(2011)到吕剧《百姓书记》(2013),从豫剧《河南担》2(2016)到沪剧《敦煌女儿》(2018)、淮剧《浦东人家》(2018),如果再加上一些未上演,或即将上演的剧目,3将近二十年的光景,他的作品仅有十部左右,这在当今众多剧作家中实在算不上高产。但是,令人惊叹的是,就是在这些屈指可数的剧作中,京剧现代戏《霸王别姬》和话剧《红旗渠》2006年与2012年两度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豫剧《常香玉》在2007年第八届中国艺术节上获文华剧作奖,而话剧《红旗渠》和吕剧《百姓书记》在2013年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上又同时斩获文华大奖。
如果打破话剧和戏曲的壁垒,可以发现杨林将近二十年的戏剧创作重心都聚焦在一个题材类型上,那就是“现实题材”。而今“现实题材”越来越成为国家对艺术创作的政策导向,对于戏剧界来说研究杨林的作品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如何将“现实题材”戏剧作品初始的宣传初衷转换成艺术作品应有的审美价值,笔者认为杨林是有自己思考的。
让“现实”融入史诗
首先,突破“现实题材”中对“现实”一词的窄化认知,是杨林在创作“现实题材”作品时的重要思考。那么,怎么样才能突破“现实题材”中“现实”窄化的问题呢?杨林的方法是无论书写时代新人,还是书写时代精神,都将其放置在一个历史的大格局中。当笔下的真人真事有了时间的肌理和厚度时,时事剧顿时会被赋予了史诗剧的光泽。
因此,在他笔端无论是常香玉、樊锦诗这些具有璀璨光环的人;还是如杨贵、王百祥(原型王伯祥)这些时代的弄潮儿;抑或是谢廷信(原型刘廷信)这样被生活压弯了腰的普通人,杨林都是把他们放在时间的长河之中去回看,努力去探寻他们被社会的光环或生活的琐碎所遮蔽的“人”的定位。他剧作里的常香玉似乎与以往社会让我们看到的那个强者常香玉不尽相同,这是一个更为私人化的心灵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是一名弥留之际的老人去回望她的一生,作者以史剧的格局为那个现实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常香玉一点点“祛魅”,让她变成一个真实的人。她既是万人追捧、崭露头角的豫剧名伶,也是以一己之力捐出飞机的爱国艺人,更是在舞台上成就自己、活出自己的角儿,但她还是那个自幼因为学戏被乡族抛弃的张妙龄,是与地方恶霸周旋的底层戏子,也是那个“文革”中被学生侮辱抬不起头的“牛鬼蛇神”。
史剧,是杨林书写“现实题材”的切入口,而诗格则是他想让史剧抵达的更高境界。无论是书写红旗渠、新疆建设兵团这样的宏大事件,还是书写樊锦诗、杨贵、王百祥这样的时代新人,杨林都在尽力探寻人物的历史沧桑感,而且他并不回避20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动荡和各种“运动”的纷扰,只为能够渲染出大历史下苦行者的渺小。于是,创造“意象”常常是杨林书写“现实题材”时营造诗格的一种方法,而“意象”最终的指向则是情感。在杨林的剧作中,《红旗渠》中的胭脂盒,成为那片干涸土地上最动人的亮色,它既是吱吱这一人物的灵魂写照,也是所有林县人对水的渴望的情感投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霸王别姬》中那个沉默的水神爷,永远守护着他怀中的那壶水,他无疑寓意着戏曲人心底对那个小小舞台图腾般的守护。《敦煌女儿》中那个多次出现的“九层楼”更是象征着敦煌人的敬畏之心,杨林通过“九层楼”上的“铁马”和佛灯的意象寄托了樊锦诗对敦煌无限的深情。这种将情感投射到物象之上的意象化处理,无疑为史剧化的“现实题材”平添了一份浓浓的诗意。
寻找角色和自我情感的连接点
生活永远是杨林心中的第一角色,将自己的生活体验渗透于创作中,是杨林创作“现实题材”的另一种自觉。“现实题材”常常以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身边的事为创作对象,但是从生活到舞台其实远非想象得那么简单,因为戏剧并不是生活本身。如何把平凡、琐碎的生活本身升华为真正具有审美力量的戏剧艺术作品,这就需要创作者从技术到观念意识的加持。
英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说:“最伟大的艺术力量要得以恰如其分地显示,就需要有艺术力量相当的第一流的技巧。”4
杨林,是一位会写戏的剧作者,这首先来自于他对编剧技巧娴熟地运用。他从不满足于把听来的“生活”简单而平铺直叙地复制到舞台上,而是擅于制造戏剧性将人物推向情感顶点。豫剧现代戏《秦豫情》中小勤和张大的初遇就是很好的例子。二人相遇的戏剧行动因一车撞碎的瓷器而起,二人一个跑、一个追;一个藏,一个闯,在推进过程中,算命先生马虎和下层妓女吕嫂相继登场掩护小勤,在与张大的周旋中,原本并不可爱的马虎和吕嫂却显露出了各自善良的本色。杨林在这场戏中通过矛盾冲突、人物关系、戏剧情境各种因素的变化,对戏剧场面进行了精彩开掘,整场戏让小勤和张大从两厢敌对滑向暗生情愫,可谓把戏充分做足,也为下一场的转换做好准备。可见,杨林深谙讲故事是需要技巧的。
实际上,如何运用技巧也是剧作者讲述生活、进而思考生活的方式,而将外在于作者的客观生活充分内在化,不仅需要作者的生活沉淀,更需要作者強大的主体意识,也就是说,任何好的作品都暗藏作者自己。对于杨林来说,每一次创作他都在努力寻找这个题材和题材中的人与自己个体生命情感的连接点,从自己的情感记忆出发去触摸笔下的人物。他的处女作京剧现代戏《霸王别姬》之所以获得“曹禺剧本文学奖”,大概即得益于此。《霸王别姬》讲述的是当代某城市,当凋敝的戏曲剧团迎来一个千载难逢排戏机会后梨园人的众生相,这里面既有圈内的坚守者虞姬,也有出圈的戏曲人霸王;既有被舞台抛弃的梨园守护人水神爷,也有捍卫梨园精神的师父;更有年轻一代的佼佼者青衣。剧中,每一个人物的名字,既是戏曲舞台上角色的名字,又是对人物性格的隐喻。杨林用自己从13岁起就在剧团中摸爬滚打的人生经历,将转型时代下戏曲人内心的冲突和碰撞展示出来,让我们看到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也是戏曲人最隐秘的世界:他们对戏的执着是那么令人动容,但是他们对舞台的占有欲又是那么强烈,当然最终戏与舞台的魅力让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渴望、守护与信仰跨越了一切,这才是这些戏曲人的主流精神。杨林通过剧团这个小世界放大的是人的本性、私欲与人的崇高理想之间的矛盾。杨林曾经说过:“《霸王别姬》里有我对生活的感悟,有我对人生的看法。在很多人物身上,有我的影子;许多人物的语言,就是我想说的话。”“这是我完全、主动、最纯粹的一次创作经历。创作动机,是我生活安定之后,想对自己的十年人生做一个总结。”5
其实,这种将自己的生活感悟内化之后的艺术创造体现在他所有创作中。《常香玉》中,小张妙龄被迫离家前父亲的“三问”就是杨林从小学戏放弃学业,父亲与他“三问”的人生写照;6《红旗渠》的创作中更是熔铸了自己父辈人的深厚情感。7他曾经说过:“生活历练了我,戏剧造就了我”,8生活和戏剧实际上是成就杨林不可或缺的两面,而戏剧更像是他对自我的找寻和救赎。
让英雄成为真正的人
对人性的深刻思考,是杨林让他的作品抵达观众内心的密钥,这主要体现在“现实题材”中,他如何处理正面人物或英雄人物。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先生说:“对于作家来说,真正的英雄式的观念,是不屈服自己心灵之外的各种压力,敢于面对人,面对人的真实的复杂的世界,把人按照人的特点表现出来,把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些价值表现出来。”9
在杨林的作品中,英雄或时代的弄潮儿,这些国家话语体系下被歌颂的人常常是他的主角,但杨贵、常香玉、樊錦诗、王百祥等这些被讴歌者却绝不止步于干瘪的符号,这首先得益于杨林所持的“英雄也是人”的观念。比如:在话剧《红旗渠》中,以当代历史上河南林县修建红旗渠的事迹为背景,杨林写出了在20世纪60年代修建这一“人工天河”工程的核心人物杨贵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杨林显然没有沿袭之前同一题材创作者的固有思路,而是深刻思考那个战山斗地,人定胜天的特殊年代,同时也是冒进盲从的特殊年代中英雄杨贵的所作所为。劈开太行山,引彰入林,这是一个在当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杨贵义无反顾,毫不退却,他既是林县老百姓的父母官,也是那个年代的狂想者,还是引领众生走向光明的大无畏的巨人。但是另一方面,在金钱、技术、设备均不充足的情况下,他所有的无畏似乎都与无知、盲目纠缠在一起。他拒绝听从反对意见,他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他甚至为了让红旗渠顺利完成,“发配”反对者黄继昌至山西平顺。显然,杨林并不满足于简单地书写一位我们惯常看到的完美无瑕的英雄形象,而是想通过挖掘杨贵高光背后的阴影,来让这个人物接近更真实的人。
必须明确的是,在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创作中并不意味着要排斥艺术虚构,相反通过合理的艺术想象进行创造是尤其必要的,在《红旗渠》中杨林虚构了黄继昌这一人物,虽然仅仅四场戏,但却举足轻重。他是作为杨贵的对立面出场的,在修建红旗渠这一行动上,黄继昌表现出的科学、务实、严谨与杨贵的豪情、冲动、冒险必然导致矛盾冲突,但这是性格的冲突,而不是立场的冲突。因此,在二人一次次的冲撞中,行动推进着他们内心渐渐靠近。实际上,杨贵和黄继昌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只是方式不同,当两个男人以男人的方式大打出手,其实预示着他们的和解。狄德罗曾言:“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这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10《红旗渠》中的杨贵和黄继昌无疑是真正的人的样子,他们其实都是那个年代的英雄,但英雄也是多层次的,如果说杨贵是“光明与盲目”的集合物,那么黄继昌就是“伟大与渺小”的复合体,正是杨林对剧中角色的人性开掘才使得《红旗渠》在一众同题材作品中显得卓尔不群。
人性的深度开掘还表现在对人情感多面性的开掘上。在杨林的剧作作品中,人物的私我情感从来不曾缺席。《红旗渠》中杨贵对死去的少女吱吱和自己年迈父母的情感透露出这个强者的柔情;《敦煌女儿》中的一心扑在事业上的樊锦诗,杨林也写出了她作为孩子的母亲,作为丈夫的妻子,与自己敦煌事业相冲突时的情感矛盾;而《百姓书记》中,杨林既写出了时代潮头的改革者王百祥,也写出了他与老父母的舐犊情深;还有《秦豫情》中的下层妓女吕嫂、算命先生马虎、甚至张大的母亲,每一个人物都不是扁平的,而是让人物多层次的情感成为其灵魂撕扯的张力。可见,让人之所以成为人,关键是让人物不同层面的情感紧紧绞缠在一起,形成内心的碰撞。
用发现的眼光深入生活
对于“现实题材”创作者来说,无论是对人性的挖掘,还是对历史“真实性”的挖掘都应该是一种使命,而如何去“伪”,如何求“真”,以及如何寻求旧题材的新视角同样是杨林的创作自觉。他从不满足于在既定题材、既定框架下去沿袭既定的故事套路,相反,他懂得唯有突破“既定”才是一条重生之路。除了“红旗渠”这类被人们一写再写的题材,还有《百姓书记》《秦豫情》《浦东人家》等,均是杨林在前人写就的基础上重新动笔,从别人的终点重新出发,然后又打开一个新局面。
新疆建设兵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军人在戈壁滩上建造的奇迹,之前无论是话剧还是戏曲都有作品。尽管如此,杨林的话剧《兵团》11从其对兵团题材新视角挖掘上看还是令人惊艳。在他的笔下,曾经那片广袤荒凉的土地上那些原本姓名不存、顶天立地的“兵马俑”们,成为了一个个活生生的、有着七情六欲的人,这是一次属于杨林的艺术发现。他找到了这片土地上的兄弟情—二年、大年这一对人物。孩子兵二年由于对上战场内心惧怕,于是,为了兑现母亲的承诺,大年代弟从军,却不曾想归来时发现二年还是离去了。于是,大年与二年的枣骝马在戈壁滩相伴终老,只为等待着魂归的二年一起回家。这对兄弟情代表了时代号令下无数佝偻的个体,但却又用信念支撑起自己的那些生命强者。杨林还找到了这片土地上的夫妻情—黄三水和岳玲玲这一对人物。寻着理想而来,自愿报名赴疆的岳玲玲,当真正来到的时候遭遇的却是仓促无感的婚姻,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然而现实迫使她接受眼前的一切,当岁月老去时,有梦的女人与粗粝的老红军已经无法分割。燕窝儿与王赵成这一对则是杨林找到的恋人情。两个无助的年轻人在孤岛般的戈壁滩上,彼此信任、彼此取暖,让无处安放的灵魂找到了栖息地。其实,时间才是《兵团》这个作品隐藏的主角,生命的沧桑感才是这个作品真正的主旨。没有任何口号和概念,也没有主题先行的宏大叙事,戈壁滩的豪情是时代赋予的,个体的人则逃不开青春被岁月消磨,爱被现实操控,理想被生活击打,以及唯有迎接与承受的生活本质。杨林力图寻找那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以及这些不同的人在那个时代下多棱的情感,使得这一题材进入到一个新的审美空间。
新的发现往往是对现实更深处的探入,随着近来“悬浮剧”一词越来越成为人们对“现实题材”作品的揶揄,剧作者是否深入生活的问题愈发引人重视。杨林是从真正的生活中走出来的剧作者,他也意识到作品中每一位个体的灵魂都是浸泡在时代中,并从时代中生长出来的,所以,在他的剧作中首先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在淮剧《浦东人家》中,杨林大量选取具有时代特征的环境、电视剧、人物语言、人物典型行动来凸显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代印记;京剧《霸王别姬》中,杨林通过下海、歌舞厅献唱等形形色色的典型动作来展现市场经济大潮下剧团和社会的“浮世繪”;《敦煌女儿》12中杨林用不同时代的典型氛围来塑造敦煌人对敦煌的眷恋,他尤其没有回避特殊时代的错乱与癫狂,也没有回避经济大潮对敦煌人的冲击,正是因为他对不同时代的白描,反而为人物的“真”添加了养分,让樊锦诗、常书鸿、段文杰等这些敦煌人的精神与动荡起伏的年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以“现代性”品格寻求超越
2021年,“现实题材”戏剧作品即将迎来创作的高潮期,如何运用艺术的法则、从而突破速朽性无疑是很重要的,杨林的“现实题材”作品或许有一定借鉴和示范的意义。
可以说,无论是20世纪初的戏曲改良运动下产生的现代戏,还是1949年之后的现代戏,抑或是如今的“现实题材”皆以正面表现时代和时代中的人为主要目的,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迈过“时代性”“即时性”抵达“现代性”,始终对于剧作者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挑战。也正是因为此种艰难,现代戏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后所剩无几,正如著名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先生所言:“世纪之初许多戏曲现代戏的出现,就同当时的政治密切联系,这是对国家和民族命运关心的表现。但是,单凭政治热情不能保证艺术创造的成功,大量现代戏都由于艺术上的幼稚而失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反而要求更高。人民的现实生活、时代精神通过现代戏可以更有力地体现,但真理往前一步便成谬误。过分要求现代戏(其实不止现代戏)直接为政治服务,必然会形成以政治代替艺术,政治家代替艺术家的局面。”13其实,现代戏的问题与当下的“现实题材”的问题是异曲同工的。
进入21世纪以来,戏曲理论界对戏曲现代戏的思考进入另一个层面,即对其是否具有“现代性”表现出极大关注,这不仅是由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古装历史剧方面出现了如《曹操与杨修》《董生与李氏》《金龙与蜉蝣》等极具“现代性”品格的佳作,也与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知识界对“现代性”层出不穷的讨论脱不开干系。其实,相较于知识界对“现代性”的多义性探讨,以及对“现代性”不同程度的反思,14戏曲理论界对“现代性”的诉求则越来越达成一致,那就是“现代性”品格对现代戏曲的必要性。而笔者也认为,“现代性”正是“现实题材”作品、戏曲现代戏获得超越的唯一路径。
那么何谓“现代性”品格?笔者以为,恰如美学理论家周宪先生关于“现代性”的核心概括:“反思乃是现代性概念的核心所在”。15但是同时,“现代性”一定是与转型这一契机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社会领域的转型,还是文化领域的转型,对“现代性”问题的争论和探讨都会促使人们对过去和未来进行思考。而关乎戏剧中的“现代性”品格,即表现在审美的“现代性”这一问题上,反思性当然也是一把不可丢开的标尺。恰如《曹操与杨修》反思了文人与威权的关系;而《董生与李氏》则是反思了女人与男人的关系,《金龙与蜉蝣》则反思了人在前行的过程中失去与获得的关系,话剧《狗儿爷涅槃》则反思了1949年之后土地与农民的关系。这些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被公认为是具有“现代性”品格的作品,皆离不开它们的反思性。
杨林的剧作或许称之为经典还为时尚早,但从他作品中表现出的对现实、对人性、对英雄的思考,以及对“现实题材”创作视角的新把握,则是让他的作品可以走得更远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