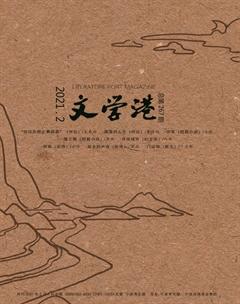江南寻隐
玉兰儿
方先生的稽山瑞草
张岱《陶庵梦忆》写兰雪茶:“日铸者,越王铸剑地也。茶味棱棱,有金石之气。欧阳永叔曰:‘两浙之茶,日铸第一。王龟龄曰:‘龙山瑞草,日铸雪芽。”
方先生的稽山茶园,就坐落在日铸岭即绍兴平水会稽山山脉。在稽东镇沿车竹线右转入横路岗,青山翠薇,蓝天高悬,山路弯多而陡峭。映山红照眼,紫藤树袅娜,山路风景怡人,原始得很,可谓云深不知处。约700米海拔左右,在人迹罕至的日铸岭所在会稽山最深处,见几座泥墙房子,矮矮的,很朴素。原来,这就是方先生的稽山茶坊。
茶坊很简朴,几屋几室几台机器和制茶必备的竹制工具,但极干净。方先生说制茶前一天上山清洁工具,平时忙其他事务。
见面寒暄,方先生说喝茶。
拿出新制绿茶和红茶各一罐,茶名写着稽山瑞草,方先生说茶名都是其妻用钢笔写的。很有章法和韵味,清而简。
汲羊角湾的一泓清泉,烧山泉,我们先试新茶。方先生拿出一只盖碗,很家常地说这碗是民国的普通茶具。碗另一侧有凤凰牡丹图案,碗盖是缠枝花纹。方先生用一个当代高仿大明成化年制的鸡缸杯给我作茶盏。茶未喝,看着这些茶器分明已经微醺了。有道是新火试新茶,眼前分明是旧器试新茶,别具穿越感。陆羽《茶经》中说:“碗:越州上……越瓷类玉,类冰,越瓷青而茶色绿,越州瓷、丘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红白之色。”不知道方先生的白瓷杯子是否是越瓷。但有些类玉类冰。
一起喝茶的还有一位方先生道教朋友余先生,余先生懂医术,对养生术颇有研究。看上去和方先生一样书生气,清秀。余先生笑着说:方先生日常器皿,在外人眼中皆是宝物,但他用平常心待之,爱之,用之。
绿茶在淪水中,慢慢醒过来醒过来,开始两泡清淡,第三泡第四泡茶叶复活了,散发茶叶的芳香和茶味,清冽,甘润,沾百花清香。
茶毕,看方先生和他的朋友制茶。
朱先生在收农妇们采来的青叶,过秤,分类。将青叶拿到阳光下摊青。竹筛早已经排队恭候新茶佳人的到来,我走过去和朱先生的夫人张女士(营养学教授)一起摊茶叶。茶叶需要不停地翻转,目的是让青叶走水均匀。摊青时把一些采摘遗漏的枯叶和杂物去掉。方先生的红茶都挑老茶新芽制作。
萎凋时,我看到人间奇景。
我想我是在稽东山上,看到了一幅莫奈的睡莲图。真实得几近虚幻,虚幻得几近真实。圆圆的竹筛,青青的茶叶,在阳光下,当我用镜头拍摄的瞬间,我惊呆了,我眼前分明看到的是一幅幅的画,如水波荡漾着的睡莲。从来佳茗似佳人,信然。
方先生说,我们一起去山上看茶树吧。
出门,即可见到茶树,茶叶其实才探出一点点新芽。绿竹挺拔,成群结队。山路逶迤,山泉叮咚,山花烂漫。方先生说,我们泡茶用的水就是山泉接下来的。
路上遇几个农妇采茶,见到方先生,个个笑脸招呼方先生,似乎很尊敬他,而方先生和他们的对话很亲切平和。
“你们明天还收茶吗?”农妇问。
“今天收,明天下山了,今晚通宵做茶。”方先生答。
“你这些茶叶准备自己家里做吗?不要放蜡啊,纯手工好。这是绍兴茶的传统啊。”方先生见到一个自制茶叶的老妪,语重心长地叮咛一遍。
“老茶树真是没收益啊,你看,才这么点新芽。我想割了种香榧。”一农夫说。
“老茶好呀,这百年老茶树是你家的宝物啊,千万别铲掉。过不了几年,这片茶树一定会给你带来好收成的。”方先生还是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沿着岩石路继续上山。岩石沟壑两边,都是一片片老茶树,有一人多高。山泉唱得很欢乐,山花发出迷人的香味,一旁一株百年红豆杉像老道一样,如如不动。这晨霭雾岚的日夜浸淫,茶叶多么出尘。我和德玛忍不住摘了几片青叶咀嚼起来,全然没有普通茶叶之涩味,似木兰沾露,清香而味甘。
方老师指着一棵茶树说:“你看,这个茶桩,台刈过的。这个就没台刈,所以长得很野。”
方先生也会突然很动情地说:“你看,这岩石缝里的茶树,也许只是一只青鸟衔来的种子,古茶树都是茶籽播种而生的。长得很顽强。都差不多百年了呢。”
这一片茶树,可谓秉天地至清之气,自由而狂野地生长在这叫做稽东山脉的最高处。得天独厚。
“方老师,你当初为何选择在这里做茶?”我好奇地问。
方老师说了下面一些话——
说来也是好玩的。
数年前,京城的一场古籍拍场,突然杀进一匹黑马,上手即以高价抢得一件唐末雕版印刷的佛教经卷。此人就是后来成为我好朋友的窦兄。窦兄是个当代奇人,学外文,通经史,好茶而仗义。生在京畿,定居上海,访茶武夷。
你知道,陆羽在写作《茶经》的过程中,曾多次来到越州,在会稽、剡溪各处深入农家,采茶觅泉评茶品水,也诵经吟诗、观赏山水,优游林下。他在山阴、会稽、诸暨、上虞、余姚、剡溪一带的考察和监制茶的活动是很多的,在“八之出”,叙述各州产茶情况和品评各地茶之优劣中,他盛赞越州茶。当时他考察了山南、淮南、浙西、剑直、浙东等道共31州的茶,认为浙东茶区“以越州上”。
张岱也写到绍兴的禊泉和兰雪茶。可见历代茶之名家都认可越州茶。
我在农业系统工作,和从事茶学者为同事,自己有对绍兴地方文化和传统物产的探究爱好,并从收藏资料典籍的角度,有意识地开始留意收集绍兴茶和绍兴酒的文献史料(都很少见),由此对越地茶的辉煌历史由逐渐认识到变得自傲。
而真正改变我喝茶习惯的,是窦兄。自认识起,印象中他随时都自带茶具茶叶,只要是友朋相聚,必泡茶荐茶,由此引导我们改变原来的单一粗放的喝绿茶习惯,真正诱发出对茶的兴趣。
他让我在绍兴找老茶树,从唐宋贡茶,到清代以降的全国最大出口茶平水珠茶,都是混合老茶品种。恰好我一个朋友外婆家在竹田头,经过多次探访,此山真有嘉木——老茶樹。
窦兄看到如此壮观的连片茶园,仅单一地采制一点早期绿茶,觉得可惜,建议我们试制红茶并请来在武夷山做红茶的师傅。于是我们四个朋友决定一起合作玩茶。制作放心茶给自己吃也把好茶分享给一些朋友。刚才在收茶的朱先生也是其中的投资者。
不觉已经过去了三四年。这三四年,积累了一些制作经验。朱先生现在已经是经验丰富的手工红茶大师傅。其实做茶很辛苦,这期间几乎是没日没夜的,因为红茶制作过程中不能停歇,碳焙的过程还要控制火候与时间。
我们制作的茶,口感不一定是最好的,但相信一定是最干净的,茶叶是原始的。我觉得应该是地道的越州茶味。
其实方先生是几年前我和我们浣纱读书会成员一起慕名拜访认识的,方先生也是咱诸暨人,大学毕业分配在绍兴工作。在平水若耶溪边,一座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陈列着他的宝贝,绍兴地方文献古籍和六朝会稽文字砖。当时叹为观止。方先生在古籍收藏界,是颇有些名望的。
今天,领着我们钻入深山丛林中的方先生,俨然已一位茶人。
我们爬到蓝殿头,过西岙,横穿竹林,至杨沟湾,顺着山路,回到茶坊。
此刻,朱先生在揉茶,揉好一个批次,即送入发酵房。
方先生立即加入制茶工作。认真而虔诚。方先生说,“萎凋到要求的程度,即转入揉捻,揉捻后即入发酵房发酵,发酵适度,即可烘焙,烘焙干了,即是毛茶。毛茶存储一段时间,还需复焙,并捡剔黄片和碎末,遂为成品。”
只见碳焙间的砖砌炉灶有好几个。竹制焙笼也已清洁干净,就地待命。
我和德玛贪茶,又来到茶室喝茶。这次我们喝红茶。
许是刚爬山出汗口渴之故,这泡茶喝下去,通体舒畅,鸡缸杯内的汤色滋润,突然想起我喜欢的《老残游记》中喝茶的一次描述:“咽下喉去,觉得一直清到胃脘里,那舌根左右,津液汩汩价翻上来,又香又甜,连喝两口,似乎那香气又从口中反窜到鼻子上去,说不出来的好受。”
我记得喝台湾东方美人茶时,感觉到清凉芬芳;喝牛栏坑肉桂时,满身的霸气;而今日所喝之稽山瑞草,五泡六泡后汤色依然醇厚,口感香甜,似有桂圆香味,真是难得。
晚上回家,在月色下,和武夷山刚访茶归来的先生一起品方先生的红茶,开始他并不怎么夸此瑞草,待到茶至第五第六泡,见汤色依然醇厚,香味芬芳,先生说,这茶味厚,制作当是行家,已脱金石气,有太和之气了,不虚稽山瑞草之名啊。
舜老师和他的青梅草堂
去青梅草堂的必经之路,便是斯宅的斯民小学。校舍古朴,徽派建筑,门台上康有为题字“汉斯孝子祠”;校训“公诚勤恒”,乃刘江所题。校园内古树掩映,古意荡漾。斯民小学乃诸暨一所人才辈出,学有蕴藉的百年老校。而其不远处的千柱屋更是充满了传奇和文化的积淀。
斯民小学的地理位置很讲究风水,面水靠山,据说以前河流之水可以撑竹排,水上运输风行。千柱屋的砖瓦估计也是水上运输而来。当年张爱玲寻找躲在千柱屋附近小洋楼中的胡兰成,记录的倒是陆路。风尘而颠簸,艰辛无比。而斯宅向来尚文习武之风蔚然,斯民小学走出去的名人很多,科学家斯行健,教育家斯霞,救过周总理的斯烈斯励兄弟,以及国民党五虎将之一蒋鼎文等。当地人颇以此为豪。
从斯民小学退休的舜老师,便是土生土长的斯宅人。舜老师本姓斯,因当地斯老师多,其名第一个字是舜,便被学生们称呼为舜老师。尧舜在我们心目中毕竟是英明君主,舜帝更是和我们绍兴有了关联,他传位的虞安葬在绍兴,大禹治水的故事深入人心,舜老师的称呼无端就高大上。
见到舜老师时,我好像看到了金庸先生笔下的一个江湖人物。半长头发,都梳向脑后,露出宽阔的脑门。因彼此并不熟悉,不便开玩笑。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和舜老师说过。游舜老师梅园时,好像沾了一点笑傲江湖的味道。
舜老师的青梅草堂就坐落在斯民小学的后山。上山的路并不陡峭,也不宽大。舜老师荷着一把锄头,走在前面。他说这条路原先是一条泥泞的田塍路,为了上山种梅,他省吃俭用,自己挖路挑泥,慢慢铺路慢慢建起来,已经习惯上山下山背个工具,方便随时修路。历时几十年,如今还在修建中。路边是原始的乡村风貌,有序堆放了村民劈得齐整的柴爿,别有原始风情。见一碑,是刘江先生所书“梅魂”二字。梅园就在眼前了。
抬头,只见满山的梅树,此刻,初冬的季节尚不见梅消息,只有看上去横冲直撞的枝枝桠桠,树皮棕褐色,充满野性。
但茶梅开得正好,梅园房前屋后的红豆杉,缀满了红色的果子,红绿夹影,分外动人。
舜老师领我参观了碑林。只见一池边上,竖立了好多绿字碑。有斯舜威先生用行书所写的“梅苑小记”,行云流水般记录了梅园成形史;还有很多中国知名书法家比如金鉴才先生的墨宝,骆恒光先生的自作诗和书法。我喜欢其中“傲雪”二字,似乎和梅花一样有一份铮铮铁骨的硬气。平时舜老师习字处,恰好临窗对池,真是好地方。
舜老师说:每年梅花開时,他就会把这些书画家的作品展示出来,和梅花相映成趣,互为唱和。真是“莫道山居无远志,世间万物是芳邻”。
我还在欣赏梅园的画作时,舜老师飞步到一小山坡,摘了几朵腊梅花,汲一边的梅井之水烧开泡制,腊梅香裹挟着茶香,喝一口,真是色香味俱全了。梅园的一只黄白相间的猫很温柔地依偎在我们身旁,眨巴着温柔的眼睛。
舜老师,是什么让你发心建造这座梅园?有阻力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如今你又收获了什么?
我好奇,几口茶水下去,忍不住发问。舜老师抿了口茶,缓缓而道——
我自小就对花草有很浓厚的兴趣。小时候,门口有个小花坛,是祖辈留下来的。我看上谁家的花,总是向他们要,种花的主人见我这么喜欢花,就很愿意送我并教我怎么种,怎么浇水,怎么施肥。当时我在长长的一个花坛里种了梅花,紫荆,牡丹,菊花,月季,黄精,玉竹,泽兰,红花,等等。一年四季,花香整个台门。但最喜欢的一直是梅花。
沿山路蜿蜒向上,不一会儿又见一庙,那庙简直是镶嵌在巨石中似的,翠竹掩映,奇石环绕,蓝天中白云悠然荡来飘去,好像有些人的人生,不长根,一生漂浮。这岐石山上石头形状各异,踞了几个庙,更让人觉得此处非人间,有世外佳境之感。
庙横幅道长学生用隶书写“护国佑民”四字,对联是道长徒弟用甲骨文所书“雷声若鼓云中响,泉石同盤山野弘”。非常难认,以至于请教了好几个书法老师都破译不了,最后只得请教卢道长。庙内供奉道教的几个长老,还有文武判官。和伽蓝殿一样,只见山风不见人的庙内,红烛高照,香火很旺。
这个地方更适合打坐和呼吸吐纳。卢道长说,他会带他的学生来此处,沐浴山风,打坐静心。他自己也会选择在这个处所打坐。山风习习,隐者的内心和自然化而为一。庙前道长种植了一排篱笆树,我这个所谓的植物学家,也没细究是什么植物,我個人更建议种植梅花,梅花的梅格适宜槛外之所。
下山,来到卢道长的“龙溪书院”。所谓书院,不过一桌几凳,几排书架和坐拥书房感觉的一张床。“鸟衔花落壁岩前”,挂在书桌墙面上,另写着“道法自然”四个字。在这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地方,充盈了一种和面积不相匹配的智慧和力量。我好像能听到童子琅琅的念书声,和少年道法自然的修习模样。
道长,你怎么想到在这样一个深山峭壁上创建书院呢?我好奇心萌发。
道长说:
我目前推动管理两个书院。天台龙溪书院(南宋天台四家著名的书院,黄水叶氏叶亨孙创建)和磐安杏坛书院(婺州南宗孔子后裔五十代孙孔挺创建)。都有非常感人的故事和历史背景。
之前我在安徽合肥推动过秋浦书院的筹建。就特别注重和关心民间书院的恢复和保护。
通过集体学习的方式,让孩子重温历史、关心社会、激励自我。让孩子们亲近自然,熟悉家乡的市井生活,也要孩子们看看科幻片,听听有趣的笑话,听听喜欢的音乐。如今很多家长慕名送孩子来这里,我会教孩子们农耕劳作,手工刺绣,教孩子们自己动手做菜洗衣,当然也学四书五经,习字,爬山,打坐,茶道。
我觉得道长的教育方式在承袭孔子式的教育模式。有意思的是道长每天教孩子们听当日的新闻。
出世和入世,本来就是如此相辅相成。他说《论语》这本书就是孔子用儒家的思想解读当时最贴近社会的生活的课堂记录。他说能陪伴孩子们慢慢成长,真心不愿看到孩子们被应试教育禁锢住自己的天性和灵魂,希望给孩子心灵留下记忆里最美的回忆,记得家乡的山水,还有自己拔过草的书院,这些孩子长大后内心是温润的。
说到温润,卢道长的茶室布置是温润的。菖蒲茁壮,苔藓深厚,杯垫用石头磨平而成,水汲自山泉,院子里的走廊上写满了廿四节气称谓,一方一方贴在窗格上,下面种植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菊花。茶室后墙都是卢师兄自己所写的隶书,燕尾横很足的感觉,写满了各种隶书碑帖的名字,我猜测卢道长是临“礼器碑”为主的,既有沧桑感又有点笔势的妩媚。但我很喜欢他笔墨间开合有度的俊朗和雍容有度。这个布景不禁让我想起魏晋风度,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茶是德玛带去的大红袍,山泉泡制,别有清冽的甘味。贴在茶几边上那句话很有意思:茶淡了要不要加一点?我想加一点什么呢?人生淡了也要加一点味道吗?修行的路上总是百般滋味,酸甜苦辣。道长说,希望来书院修习过的孩子,让身心可以自由些,从孩子开始,少些功利心,多些快乐的体验,认真而深情地拥抱这个时代。
德玛因之前关注卢道长的微信,所以对卢道长去外地讲学有所了解,席间讲到卢道长去南京老崔茶馆讲学的经过,描述中秋节在太湖边举行的一次拜月祭月的仪式,他说用宋代仪式,缓慢而唯美地呈现拜月的仪轨和过程,人和月亮,人和自然,人和古人都有了一个最自然和美好的链接,那样的美好,是需要我们好好去创造和珍惜的。我脑海中翻出千江母亲祭月的场景,她们祭月形式传统迷信而喜感,充满了民间的乐趣和愿景。更多的是祈福和祝愿。
这样的描述,让我和德玛神往之极。德玛力邀道长来甘棠茶馆讲课,因为甘棠也在举办一月一期的读书会活动,道长欣然应允。他说,自己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手艺有着近乎执着的挚爱。他会给我们带来关于竹制品的前世今生的一堂课。
因我们还想去国清寺赏隋梅,只能起身依依告别。
出书院,来到车旁,只见清澈如洗的蓝天上,挂着半轮明月。青宇而澹邈。道长笑言,若赶到国清寺时万一关门了(寺庙4点关门),你们就和师父说,是隋梅托梦给你们,才赶来赏梅的。一定能见到。
道长说话机锋有趣,胶原蛋白丰富的脸上,露出真诚而迷人的月牙式笑容。恍若天上那轮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