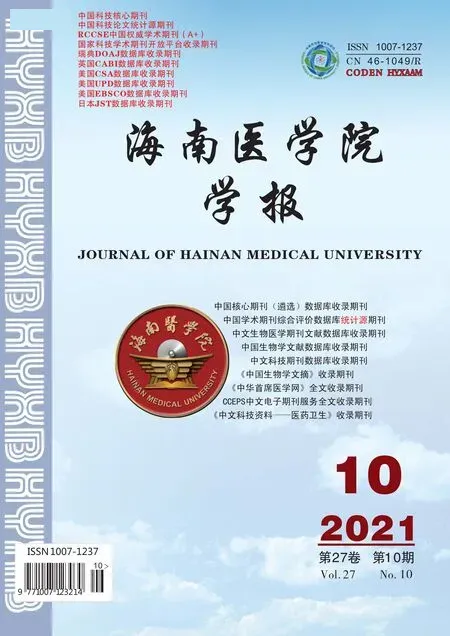单核细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在心血管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桑婉玥,李红建
(1.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01;2.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高血压科,新疆乌鲁木齐830001)
单核细胞参与的炎症和氧化应激是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斑块破裂和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CVD)的发生基础。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HDL)可通过抑制巨噬细胞的迁移、低密度脂蛋白氧化以及促进血管中的胆固醇转运出细胞等途径中和单核细胞的促炎、促氧化作用,从而表现出抗AS的作用。已有大量研究证实,单核细胞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monocyte to HDL cholesterol ratio,MHR)可作为CVD的实用、经济、高预测性、反映动态炎症趋势的标志物[1]。
1 单核细胞与高密度脂蛋白在慢性炎症中的作用
AS的基本病理过程包括内皮损伤、脂质沉积、氧化应激与血管慢性低度炎症。慢性炎症不仅是局部反应,也是一个全身性、系统性过程,随着炎症的发展,炎症介质(例如急性期反应蛋白、细胞因子和粘附分子)会随之逐渐升高,单核细胞是促炎物质在AS形成期间的主要来源,而HDL则直接参与多项AS的抑制进程。
单核细胞密切参与AS斑块的形成、发展和破裂等连续事件。长期血脂异常等危险因素使动脉内膜功能紊乱,低密度脂蛋白进入内膜并氧化修饰使内膜受损,大量单核细胞与受损血管内皮上表达的黏附分子结合并迁移到内皮下后,成熟为巨噬细胞,氧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并诱导促炎和促氧化细胞因子释放于炎症部位,吸引其他单核细胞和T淋巴细胞进一步促进脂质斑块的形成。此外,在多种与AS相关的可溶性因子(例如免疫刺激剂、生长因子、血小板等)影响的循环衍生活化产物和类花生酸蛋白质等的影响下,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可进一步导致CVD及其并发症的的发生[2]。
HDL是一种抗AS因子,具有包括胆固醇的逆向转运、抗氧化、抗炎等多种生物活性,低水平或受损的HDL介导的胆固醇外流会导致造血干细胞增殖,尤其是单核细胞增多,从而促进AS斑块的进展[3]。HDL可通过阻止激活p38c和磷酸肌醇-3激酶来抑制单核细胞中组织因子的表达[4];还可通过降低F-肌动蛋白的含量来防止单核细胞聚集并黏附于血管内皮,控制其活化及单核祖细胞的增殖分化[5],从而有效抑制氧化应激及炎症反应的进展。由于单核细胞和HDL在AS过程中分别具有明显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将这两个指标按比例计算得出的结果(MHR)较单一指标评价疾病发展更有优势。
2 MHR与原发性高血压及靶器官损害的关系
高血压病是导致动脉弹性受损、左心室肥厚等靶器官损害最主要的疾病之一,包括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等在内的细胞成分在高血压病的发生和发展中都起着核心作用。研究表明,与健康受试者相比,MHR在新诊断且未经治疗的高血压病患者中明显增高[6];MHR水平与主动脉僵硬度指数呈正相关(r=0.294),与主动脉扩张性呈负相关(r=-0.281),尽管此研究规模较小,相关性不强,但MHR可能是高血压病患者主动脉僵硬度和主动脉扩张性的独立预测因子。高血压病及其靶器官损害均与血管内皮组织的损伤相关,当损伤程度不足以引起相关组织功能障碍时,称为无症状靶器官损害。Aydin等[7]对比了272名已诊断为高血压病的患者及91名健康志愿者的靶器官损害指标,结果显示:患高血压组的平均MHR高于对照组(4.9±1.7)vs(12.6±5.4),该组的尿白蛋白水平、左室质量指数(left ventricular mass index,LVMI)、颈动脉中层内膜厚度(carotid intima media thickness,CIMT)均 与MHR呈 正 相 关,(r=0.482、0.396、0.486)。且MHR是尿蛋白、LVMI、CIMT及无症状靶器官损害严重程度的独立预测因子,MHR是CIMT、LVMI、尿蛋白水平和尿白蛋白水平增长的独立危险因素。若MHR高于9.06,其对于预测无症状靶器官损害的灵敏度为94.2%,特异性为100%,因此MHR对于无症状靶器官损害具有很高的预测及辨别能力。
3 MHR与冠状动脉疾病的关系
3.1 MHR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CAD)是AS持续进展累及冠状动脉,使冠脉管腔狭窄或闭塞的结果,是AS所致器质性病变中最常见的类型,其发生基础也是血管内的慢性炎症反应。将MHR与反映机体慢性炎症的金标准C-反应蛋白以及SYNTAX评分结合,可评估MHR预测CAD进展以及动态反应炎症趋势的效能。SYNTAX评分是一项基于患者个体CAD病情特点的个性化评分标准,评分越高提示病情可能越严重。一项对1 229例CAD患者的横断面研究发现,MHR与CAD的负担独立相关,其中MHR与SYNTAX评分(r=0.371)和C-反应蛋白水平(r=0.336)显著相关,MHR每升高1 U,SX评分增高的风险增加8.3%[8],提示MHR可能为SYNTAX评分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且可作为全身性炎症的强大生物标志物。
此外,MHR对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急 性期的斑块进展有重要预测作用。研究表明,MHR是STEMI患者院内死亡率(HR=3.74,95%CI:1.31~5.95)、5年 死 亡 率(HR=2.048,95%CI:1.225~4.091)、院内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s,MACE)(HR=1.50、95%CI:1.02~1.99)以 及5年MACE(HR=1.285,95%CI:1.064~1.552)的独立预测因子[5]。MHR还可作为STEMI患者随访期间QRS评分的独立预测因子(OR=0.390,95%CI:0.252~0.605)[9],该评分对估计心肌梗死面积以及预测STEMI有预后价值,因此MHR不仅可有效反映炎症趋势,而且是评估CAD严重程度及预测CAD进展的有效指标,对于CAD患者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研究结果来看,MHR尚无法精确提示具体不良结果的发生,仍需进一步临床研究加以佐证。
3.2 MHR与PCI术后支架再狭窄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目前是STEMI患者最常见的治疗方式,但PCI术后因血管内皮对支架产生超敏反应、斑块破裂等所引起的炎症反应可导致内膜过度增生,出现支架再狭窄。尽管支架再狭窄的病理生理是多因素的,但炎症是该过程的基石。Ilhan等[10]根据PCI术后是否发生支架内再狭窄,将患者分为两组并分别观察两组中MHR的变化,发现支架再狭窄组的MHR更高(1.67vs1.47),证明裸金属支架治疗后的STEMI患者发生支架再狭窄风险与MHR水平升高相关,MHR最高的患者发生支架再狭窄风险值是MHR最低患者的1.65倍。两篇早期不同研究的数据同样支持该结论,在成功植入裸金属支架的心绞痛患者中,术前MHR最高者的再狭窄率(OR=1.45,95%CI:1.06~1.88)[11]高于MHR最低者(OR=1.29,95%CI:1.15~1.49)[12]。因此,术前MHR可作为支架再狭窄的独立预测因子,但目前尚无相关文献介绍MHR与STEMI患者药物洗脱支架植入术后支架再狭窄的相关性,且尚无研究说明需要临床早期干预的MHR阈值,无法在临床上作具体参考。
3.3 MHR与冠脉慢血流/狭窄/扩张
冠脉慢血流即在冠状动脉造影时没有发现冠脉存在明显病变,但在其远端发生血流灌注延迟的现象,其确切病因尚不清楚,但其氧化应激、炎症、内皮功能障碍在冠脉慢血流发病机理中的作用已得到充分证实。已有研究证明,冠状动脉造影前MHR升高与冠脉慢血流的存在显着且独立相关(OR=1.24,95%CI:1.230~1.451)[13],血流动力学显着病变的患者(分数流量储备值≤0.80的患者)MHR较高,提示MHR在血管造影术中是冠状动脉狭窄的重要独立预测因子[14]。此外,与阻塞性CAD和冠状动脉造影正常的患者相比,孤立的冠状动脉扩张症患者MHR显著增高,且冠状动脉扩张症越严重,MHR越高,患者死亡风险越大[15],因此较高的MHR水平可能对冠状动脉血流具有促炎和促氧化作用。
3.4 MHR与心脏X综合征
心脏X综合征通常是指患者出现心绞痛或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在运动平板实验或应激性心肌灌注显像术中可发现心肌局部缺血。但在冠状动脉造影中无异常表现的类似心绞痛胸痛,病因尚不明确,考虑其可能与内皮功能受损和微血管功能障碍相关。有报道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心脏X综合征患者的MHR显著升高[16],提示较高的MHR(OR=1.09,95%CI:1.03~1.16)也可能与心脏X综合征的发生相关,但目前相关性研究较少,需更多临床研究验证。
4 MHR与心房颤动
心房颤动由心房电生理紊乱、心肌收缩和结构重塑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引发,它的本质依然是炎症部位的促氧化因子聚集。在冷冻球囊导管消融术后房颤复发的受试者较未复发者MHR更高(HR=1.20,95%CI:1.15~1.25),且MHR的增高与房颤复发率增加相关,故MHR可作为房颤复发的独立预测因子[17]。此外,铃木等报告称单核细胞与HDL的比率升高也与房颤的发生有关(OR=2.057,95%CI:1.301~3.251),但与房颤患者的其他临床参数(例如房颤持续时间、超声心动图参数和左房容量)没有发现显著相关性[18]。然而,另一项研究称,MHR与左心房直径和心房颤动病史持续时间显著相关,可作为预测心房重构严重程度的新型标志物[19]。因此,MHR可作为房颤复发的独立预测因子,但与房颤持续时间、左心房直径等房颤患者其他临床参数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5 MHR与感染性心内膜炎
感染性心内膜炎为心内膜表面的微生物感染,其主要机制为病原微生物侵犯心室壁内膜、心脏瓣膜及邻近大动脉内膜从而诱发慢性炎症反应,死亡率相对较高,因此找到早期精准而易得的炎症标志物用于筛查高风险患者,在治疗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时是必要且迫切的。研究表明,在左心室射血分数正常的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中,高MHR与高CRP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r=0.396),反映出MHR在预测全身性炎症中的价值,且当MHR>21.3时,MHR可 作 为 院 内(OR=3.98,95%CI:1.91~8.30)和远期死亡(HR=2.29,95%CI:1.44~3.64)的独立预测因子,对预测院内死亡的敏感性为74.4%,特异性为57.6%[20]。因此,由于MHR具有经济、易得等特性,较传统的单一炎症指标具有更强的预测性,可作为早期感染性心内膜炎诊断及预测预后的重要参考。
6 MHR与代谢综合征
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etS)是一种以肥胖、血压升高、葡萄糖代谢受损和脂质代谢异常为特征的疾病,尽管其病因尚未完全明确,但这些代谢参数的改变和相互作用均可导致氧化应激、内皮功能障碍和慢性全身性炎症等,如:内脏脂肪过多和脂肪细胞肥大会刺激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从而导致慢性全身性轻度炎症,这种病理生理状态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影响胰岛素信号传导和β细胞功能以及CV事件,从而导致AS以及由于AS进展所引起的心血管疾病。因此,患有MetS的人群较普通人群患CVD的风险更高,且全因死亡率较正常人群增加1.5倍。研究显示,较健康对照组,MetS患 者 的MHR显 著 增 高(13.15±6.07)vs(9.74±5.24),且MHR不仅是MetS的独立预测因子(95%CI:0.721-0.945),且与MetS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r=429,P<0.000 1)[21]。
7 展望
目前MHR被认为是反映炎症状态的一种新型标志物,其与全身性炎症和内皮功能障碍有关,被认为是可以预测CVD发展及预后的标志物。MHR不仅具有实用、高预测性、非侵入方式获取等特点,且具有经济优势,这对于不同人群CVD等的早期预防,降低人群CVD患病率及死亡率均有益处。MHR水平升高不仅与不良预后相关,并且预示着更严重的疾病。但该指标缺乏疾病特异性,且尚无研究说明其在各类CVD中需要早期临床干预的具体阈值,因此仅可作为筛查指标在临床中使用。综上,在临床中可将MHR作为参考,用于评估CVD的预后并对可能发生的不良心血管事件进行早期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