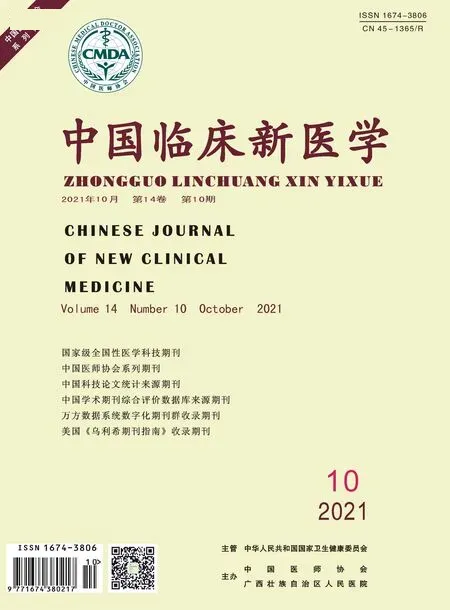鼻咽癌微环境中外泌体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钟宇萧(综述), 蒿艳蓉(审校)
鼻咽癌(nasopharyngeal carcinoma,NPC)是一种常见的头颈部恶性肿瘤,来源于鼻咽部的上皮细胞,和其他上皮性头颈部肿瘤起源于相似的细胞或组织谱系,易发生局部浸润和颈部淋巴结转移且恶性程度高。NPC发生与EB病毒(epstein-barrvirus,EBV)感染、肿瘤抑制因子失活、癌基因激活和环境等因素有关[1-2],在我国广东、广西、福建,以及东南亚、北非地区高发,多见于男性华人,男女发病率约为2.5∶1,年发病率近千分之三,具有家族聚集性特点,高发的家族移居后发病率也会高于当地居民。而且NPC具有双峰年龄分布特点:一是在50~60岁左右,二是小高峰为青少年和年轻人[3]。根据目前世界卫生组织的病理分类,NPC分为角化鳞状细胞癌和非角化癌。后者进一步细分为非角化分化癌和非角化未分化癌。随着影像学技术的进步,虽然同步调强放疗加化疗、手术以及其他辅助性治疗,使得患者局部症状的控制率有所提高,尤其是新型放射技术或设备的改进,局部控制率可达到90%左右,但是在针对远处转移和局部复发治疗的效果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机制上讲,NPC发展过程中,肿瘤细胞不断向周围环境释放外泌体,外泌体浓度越高,代谢和生理活动越活跃,恶性程度越高。本文对外泌体主要通过调节细胞过程在细胞-细胞通信中发挥重要作用进行综述。
1 NPC微环境外泌体的形成
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由肿瘤基质、周围血管和肿瘤细胞本身组成,包括周围的免疫细胞、血管、细胞外基质、成纤维细胞、淋巴细胞、骨髓源性炎症细胞和信号分子[4]。NPC微环境中细胞间的通讯,通过直接的细胞-细胞接触或通过转移分泌的细胞因子介导,是维持多细胞生物细胞功能和组织稳态所必需的因素。细胞相互作用的破坏会导致正常细胞-细胞通讯的中断,从而促进NPC的发生[5-6]。通常细胞会释放各种类型的囊泡来维持正常的功能,如来自内小体和质膜的外小体和微囊泡[7]。外小体是直径约40~150 nm由质膜直接向外出芽形成的水泡结构,它包含转录因子、细胞表面受体、胞浆和核蛋白、miRNA和mRNA。质膜的内吞导致细胞内形成内吞小泡,进而相互融合形成内小体,随着内小体的生长和成熟,形成多囊体。多囊体可经内溶酶体降解回收,也可被外溶酶体释放到细胞表面。当多囊体与质膜融合时其腔内囊泡释放到细胞外,从而形成外泌体[8]。NPC微环境外泌体不仅包括EBV相关外泌体、NPC衍生外泌体、间充质干细胞-衍生外泌体和人类EBV转化淋巴母细胞衍生外泌体,它还含有许多来自树突状细胞和骨髓祖细胞的外泌体等[9],这些外泌体携带的大量功能性蛋白质、mRNA、miRNA、DNA片段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
2 NPC微环境外泌体的迁移、侵袭、凋亡作用
上皮细胞-间充质转换(epithelial-to-mesenchymal trasition,EMT)是促进细胞运动和启动转移的关键。Guo等[10]发现间充质干细胞来源p53激活C-C基序趋化因子配体2(CCL2)的转录,CCL2水平升高后通过chemokine receptor 2(CCR2)促进转移和EMT。同样,NPC衍生外泌体潜伏膜蛋白2(latent membrane protein 2,LMP2)通过诱导PI3K/AKT/mTOR通路促进NPC中的EMT磷酸化为4EBP1,激活的4EBP1-eIF4E轴可以上调表达转移的肿瘤抗原1(metastatic tumor antigen 1,MTA1),并且通过Wnt1途径和激活β-catenin来促进EMT[9,11],还可以通过ERK1/2通路促进转录因子Fra-1的产生,LMP2A上调鞘氨醇激酶1(sphingosine kinase 1,SPHK1),可产生鞘氨醇-1磷酸(S1P)激活AKT,从而促进EBV相关的NPC细胞迁移[9,11]。Wasil等[12]证明LMP1可上调局灶性黏附(FA)复合物的形成,促进上皮细胞迁移。LMP1还可以下调肿瘤抑制因子miR-204,从而增强Cdc42介导细胞侵袭特性的活性,如焦点复合物的形成、整合素的定位和MMP的表达[13]。此外,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related fibroblasts,CAFs)对癌症的发生、进展和转移至关重要。Zhu等[14]证实了环氧合酶-2(cyclooxygenase 2,COX-2)在原发性NPC组织中的低表达,但在CAFs转移部位高表达,COX-2在成纤维细胞中的高表达通过COX-2-PGE2-TNF-α轴增强NPC的迁移特性。Wu等[15]研究发现EBV感染的NPC微环境中EBV相关外泌体LMP1通过NF-κB/p65信号通路激活正常成纤维细胞(normal fibroblasts,NFs)成为CAFs,而LMP1已被证明通过依赖ERK-MAPK通路的机制在上皮细胞中诱导EMT,但抑制TGF-β信号对逆转EMT表型没有影响[16]。我们可以推测LMP1可以通过上皮细胞中的ERK-MAPK信号直接驱动EMT,或者间接通过CAFs的招募和激活,刺激它们释放的TGF-β以旁分泌的方式作用于TME中的NPC细胞,或者二者是协同作用。可见,NPC微环境的外泌体通过不同的信号通路诱导EMT或CAFs,对调控TME发挥了重要作用。CAFs是预后较差的一个突出特征,因此,外泌体在CAFs中的作用,在将来有望帮助肿瘤的诊断分期、治疗效果评估以及成为监测肿瘤进展的标志物。
3 NPC微环境外泌体的促血管生成
肿瘤的发生、发展、复发和扩散取决于新生的血管,这些血管为维持肿瘤生长提供了所需的营养、生长因子和氧气。肿瘤在进展的不同阶段,肿瘤血管生成涉及复杂的内皮细胞活动的编排,包括增殖、迁移、入侵、黏附和分化[17]。Lu等[18]用迁移法、管形成法和基质凝胶塞法分别评价了内皮细胞相关外泌体miR-9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系(human umbilical vein endothelial cell line,HUVECs)在体内和体外细胞迁移和管形成关系,研究数据表明了外泌体miR-9通过靶向介导MDK和调节PDK1/AKT通路抑制内皮细胞生成,从而抑制血管形成,然而miR-9过表达则通过AMPK信号通路促进成骨细胞分化和血管生成。结果揭示miR-9可以通过多条信号通路介导内皮细胞的生成,进而影响血管形成。Bao等[19]发现内皮细胞和高血管化组织中富集的miR-23a-27a-24-2簇成员通过抑制miR-23/27靶向诱导Sprouty 2和Sema 6A蛋白来抑制发芽血管生成。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发现上调miR-23a可促进细胞生长、迁移和内皮细胞的管形成。我们可以进一步猜测,是否外泌体miR-23a以旁分泌的机制,从NPC细胞转运到内皮细胞后通过直接靶向睾丸特异性基因抗原(testis-specific gene antigen,TSGA10)加速邻近肿瘤内膜的血管生成。BMP和激活素受体膜结合抑制剂(BAMBI),作为TGF-β typeⅠ受体家族成员的竞争伪受体,在肿瘤的发生和血管生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Duan等[20]的研究表明,来自NPC细胞的外泌体miR-17-5p通过靶向作用于BAMBI和调节AKT/VEGF-A信号促进血管生成。此外,TME外泌体还通过VEGF、EGFR和STAT3介导的途径,以多种方式调节细胞生长、迁移和血管生成[17,21]。综上所述,NPC微环境外泌体在介导血管生成中起着重要作用。
4 NPC微环境外泌体参与免疫作用
NPC微环境中存在许多免疫抑制因子,通过募集免疫抑制细胞抑制局部免疫反应,使得原本起保护作用的免疫反应抑制肿瘤生长失败,甚至导致癌基因的产生。然而,外泌体通过免疫细胞和癌细胞之间的通讯,参与微环境的免疫机制,对免疫监测、免疫抑制和免疫逃逸起着关键性作用[22]。一方面,NPC细胞分泌的外泌体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可能参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等免疫介质的调节,通过调节细胞内通讯抑制微环境中免疫反应[5,23]。活化基质、抗炎M2巨噬细胞等是免疫衰竭的特征,可激活WNT/TGF-β信号通路,促进TGF-β在衰竭亚型中显著富集,从而抑制宿主的免疫应答[24]。研究[25]表示PD1/PD-L1过表达,通过转化生长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TGF-β1)去掉DNA甲基转移酶1(DNMT 1),以启动子的去甲基化或以依赖TNF-α的方式激活IKKE/NF-κB信号通路,从而促进TME中的免疫逃逸。另一方面NPC衍生外泌体和间充质干细胞衍生外泌体(IEXs)已被证明通过转移抗原来激活CD4T细胞和CD8T细胞,从而增强抗肿瘤反应并抑制肿瘤进展[23]。同样,微环境中EB病毒核抗原-1(EBV encoded nuclear antigen 1,EBNA-1)蛋白,通过产生IgA抗体来增强对EBNA-1的体液免疫反应[26]。NOPC来源的外泌体白介素-18(interleukin-18,IL-18)和CXC趋化因子配体10(CXCL10)可能诱导趋化因子受体3(CXCR3)阳性T细胞产生γ干扰素(interleukin-γ,IFN-γ),IFN-γ能形成积极的调节回路促进恶性上皮细胞产生CXCL10,导致炎症反应和白细胞浸润。此外,LMP1还可上调IL-18,这导致IL-18、IL-6和血清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进入TME增多,从而抑制TME中的免疫监测[11]。由此可见,微环境的免疫调节关系错综复杂,提示了仅靠单一靶点很难掌握免疫调节机制,要不断发掘新的靶点及代偿通路,微环境中有更多外泌体有望成为免疫治疗的新靶点。
5 NPC缺氧微环境中的外泌体
肿瘤细胞的增殖使局部基底膜受损,TME遭受缺氧和破坏。TME缺氧是触发肿瘤血管生成并激活缺氧诱导因子-1(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HIF-1)表达的主要力量[17]。HIF-1是一种转录因子,参与细胞代谢和生理过程的各个方面,包括癌症的发生、发展。由于骨髓祖细胞来源外泌体HIF-1a mRNA的表达整合多种病毒致癌的生物途径,使大多数致癌病毒能够稳定或增强血管生成因子HIF-1的转录活性。缺氧微环境中,随着HIF-1a的积累,激活许多缺氧条件下的靶基因,如促血管生成因子和促生长因子、葡萄糖转运蛋白以及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由于HIF-1a在诱导机制中的重要性,使得MMP-13过度表达,从而诱导NPCEMT和肿瘤侵袭[27]。Li等[28]用Hre2构建了4个质粒,证明了NPC衍生外泌体葡萄糖调节蛋白-78(glucose-regulated protein 78,GRP78)嵌合启动子调控融合基因TK/VP3,表达的TK和VP3,在葡萄糖缺乏或缺氧条件下能显著抑制NPC细胞的增殖,促进NPC细胞的凋亡。同时证实了miR-519可以直接结合HIF-1a,并显著抑制其表达,若HIF-1a过强可反馈性抑制miR-519进而抑制NPC细胞进展。此外,LMP1在这些细胞成为低氧甚至缺氧微环境下的高级肿瘤细胞之前,激活具有肿瘤干细胞或祖细胞样特性的细胞的低氧信号通路,这有助于维持肿瘤干细胞在NPC早期阶段的发育[29]。综上所述,缺氧是TME重要的组成因素,癌细胞可以通过多种细胞机制适应所处的缺氧环境,同时TME外泌体在通过不同的信号通路促进或抑制肿瘤细胞的适应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6 NPC微环境外泌体在临床中的应用
在NPC的进展中,肿瘤细胞不断向周围环境释放外泌体。外泌体可以将生物信号从肿瘤传递到远处的组织和器官,甚至进入血液循环中遍布全身。因此,外泌体可以作为靶向给药载体,在供体细胞和受体细胞之间的细胞货物的载体中起内源性作用,以及在激发生物反应中起作用。外泌体在治疗中的使用包括抗肿瘤药物的药物传递、免疫调节、去除体液中肿瘤来源的外泌体、调节外泌体含量以防止肿瘤的发生和转移[5,30]。外泌体中嵌有不同类型的病毒成分,如LMP1、LMP2A、BAMHI-a向右结构1(Bam-HIA rightward frame 1,BARF1)和EBV核酸(DNA、mRNA和miRNA),这些EBV相关外泌体靶点可以作为NPC诊断和预后指标,也可以作为不同类型EBV相关癌和疾病的治疗靶点[31-32]。而且研究[33]发现,环亲素A(cyclophilin A,CYPA)不仅可以被排入外周血,还可以被输送并富集在血清外泌体中,外泌体CYPA和EBV-VCA-IgA的结合可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尤其是当EBV-VCA-IgA为阴性的时候。该研究提示,循环外泌体CYPA是一种新的提示NPC不良预后的生物标志物。而且还有研究[9]提示,NPC微环境中外泌体EBV-BART1-miRNAs在肿瘤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作为无创生物标志物用于NPC患者的早期检测、诊断和治疗监测。此外,RAB27A通过调节外泌体介导的侵袭性,从而刺激癌细胞侵袭和转移,表明RAB27A是发病机制的重要调节因子,因此它既是几种类型癌症的关键预后指标,也是治疗靶点[34]。综上所述,虽然微环境中外泌体在肿瘤的治疗、诊断及预后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NPC极易复发和转移,使得其在临床方面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微环境中外泌体有着巨大研究潜力和意义。
7 结语
我们探索了NPC微环境的外泌体通过多种途径参与NPC细胞的转移、侵袭和凋亡,外泌体有望成为评估肿瘤进展的一项重要的生物学指标。外泌体通过不同信号通路调节血管生成,例如外泌体miR-9通过靶向诱导MDK和调节PDK1介导的AKT通路进而抑制内皮细胞,从而抑制血管形成,使我们有望找到调控血管生成起主要作用的关键突变,有可能找到抗肿瘤血管生成的新的治疗靶点。此外,通过外泌体在TME中的免疫检测、免疫调节及免疫逃逸等机制,有可能为肿瘤的免疫治疗提供新的治疗思路。尽管现在外泌体的研究进展较大,但总体理解和认识仍不够全面。在TME中如何识别不同活性细胞来源的外泌体,以及如何通过外泌体所携带的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如蛋白质、miRNA、DNA等,进一步发现、验证、提取出更多重要的外泌体是不小的挑战。目前,关于NPC微环境中的外泌体在临床的诊断工作中运用研究并不是很多,外泌体在NPC诊断中的潜力还没有被挖掘出来。我们要挖掘更多的外泌体,并进一步阐明它们的功能作用和临床意义,探讨其在NPC患者的治疗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