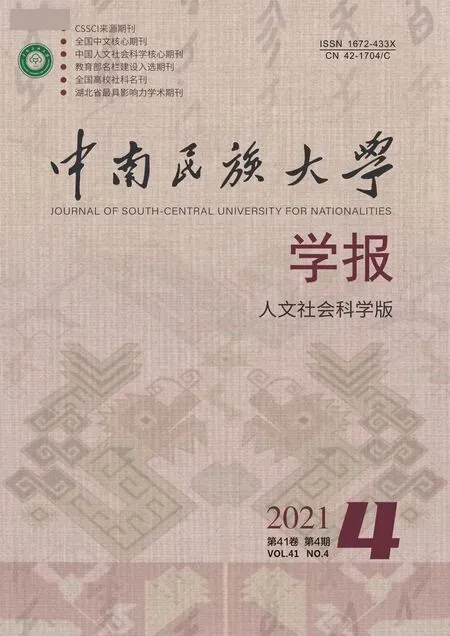成为保加利亚人:民族国家构建与地方社会转型
——以保加利亚波马克人的民族化进程为例
魏 剑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等概念众说纷纭。英国民族和民族主义研究权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至今尚无一致通论或标准规则,可作民族区分的标准。民族根本不可能具有恒久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1]。民族的多义性使得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国家构建等概念也不易界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不同时间、地域的经验显现出的民族、国家的特征无法完全与民族、国家等概念吻合。现代国家是以民族-国家样式出现的,这种国家样式自然比传统国家(比如帝国)有更清晰的地理边界,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私人的、封建的、地方的依附关系,更强有力地推行公共的且同质化的文教、司法,将个人整齐划一为国民并以此增强国家的凝聚力。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产生于18世纪,比如英国、法国和美国。
列宁在1914年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在西欧大陆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所包括的是一段相当确定的时期,大致是从1789年到1871年。这个时代恰恰是民族运动以及建立民族国家的时代。这个时代结束后,西欧便形成了资产阶级国家体系,这些国家通常都是单一民族国家。”[2]225列宁所说的1789年到1871年,即从法国大革命到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但列宁并没有忽略东欧和亚洲。“在东欧和亚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是在1905年才开始的。俄国、波斯、土耳其和中国的革命,巴尔干战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东方’所发生的一连串有世界意义的事变。只有瞎子才不能从这一连串事变中看出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的兴起,看出建立民族独立和单一民族的国家的趋向。”[2]234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成立,更像是一个过渡阶段,它在继承、反思西方启蒙运动以来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同时,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的、理性的市民社会意义上民族国家,又在反启蒙运动价值影响下开创了族裔文化民族主义之先河,且为这种变形了的民族主义向中东欧传播作了示范[3]。这就是由汉斯·科恩区分且被后世研究者继承了的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文化民族主义类型。值得一提的是,不能忽视族裔文化民族主义对公民民族主义的解构力量。
列宁意义上的“民族”也就是斯大林在1913年《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对民族的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4]。但马克斯·韦伯对“民族”的界定与此大不一样。在韦伯看来,“民族”首先与“国民”并不一致。韦伯认为,“民族”是这样一个概念,无论如何,不能根据属于它的人的经验的、共同的品质来界定。必须要求某些人的群体面对其他人的群体时有一种特殊的团结一致感,因此属于价值的范围。民族的属性并非必然建立在现实的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即人类学类型上的共同性并不足以说明是一个“民族”。同样地,共同语言的群体,也未必是同一民族[5]。“民族的”——如果说有什么统一的东西的话——就是一种特殊的激情[6]。韦伯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实质上是“族群”[7]。
19世纪中期民族主义的变形,为后世不同流派、范式在认识论上的竞争提供了思想资源。对于“民族是什么”的不同认识并非源于斯大林和韦伯,分歧也不仅仅存在于他们之间,众所周知,第二国际内部就有“民族自决权”与“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张,但斯大林和韦伯都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与韦伯的“族群”观以及那个时代的民族、民族国家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作为认识论范式的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原生论与建构论之争。这一方面,使得当代民族问题有了更多可以借助的思考资源,同时,也使得当代的民族问题异常复杂难解。简言之,诸神之争依然继续,不同观念、主张甚至势同水火,因而需要从不同视角历史地、经验地研究民族问题,世界民族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族”是什么。
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尔干期间,波马克人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宗教少数人群体,保加利亚民族国家构建带给这一群体的是一个新的保加利亚族身份。民族国家构建深刻影响了保加利亚波马克人的民族化进程和地方社会转型,也为我们认识民族、民族国家构建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试验场地。
二、谁是波马克人
谁是波马克人?这或许与定义“民族是什么”同样困难。学者们往往以波马克人的语言或宗教界定其族裔身份,认为波马克人是将保加利亚语作为母语的斯拉夫保加利亚人,但他们的宗教和和文化习俗则是伊斯兰化的。
从地域上来看,波马克人是聚居在从保加利亚东罗多彼山脉到阿尔巴尼亚北部山脉之间狭长地带的山地居民,巴尔干半岛的五个国家,保加利亚、土耳其、希腊、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都有波马克人居住。由于民族主义的影响,波马克人的族源一直都是巴尔干各国学者争论的重要问题。保加利亚学者认为,波马克人是在16-18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被强制伊斯兰化的保加利亚人(族)[8]。希腊学者表示,波马克人原是古色雷斯部落,后来经历了希腊化、斯拉夫化和伊斯兰化。土耳其学者指出,波马克人是在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半岛之前流亡到该地的突厥语部族,诸如佩切涅格人、阿瓦尔人、库曼人的后裔[9]。这种争论往往以单一语言或宗教来追溯其族源,而忽视了民族是个历史范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保加利亚学者以语言为基础,认为波马克人是被强制伊斯兰化的,而土耳其学者认为波马克人在与斯拉夫人共同生活中失去了土耳其语。
2011年最新的保加利亚人口调查没有将波马克人列为单独统计条目,而是将其置于保加利亚族名目之下,因此,没有确切的波马克人人口统计数据。据学者们估计,保加利亚波马克人数量大约有20万,其中90%以上的波马克人分布在南部罗多彼山区[10]。笔者的田野调查地点主要是罗多彼山区斯莫梁市的苏诺村、库拉村(1)为保护访谈人隐私,本文的地名和人名均为化名。。库拉村是穆斯林村庄,全村约有300人,苏诺村是穆斯林波马克人和东正教保加利亚人共居村庄(苏诺村的穆斯林是社会主义时期由周边村庄迁入的),全村约有200人,其中波马克人占一半左右。奥斯曼帝国时期,波马克人村庄库拉村是周边几个村庄的中心,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将罗多彼山区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中解放出来,改变了当地中心村庄的分布格局,苏诺村开始取代库拉村的中心地位。1979年,设立苏诺市,苏诺村(市政府所在地)成为周边10个村庄的中心,周边穆斯林村庄的波马克人大量流入苏诺村。保加利亚转型后,村庄人口不断外出,苏诺村又重新回到村级单位。
田野现场带来的是“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世界有着不同于知识精英建构的历史话语。在“谁是波马克人”问题上就是如此,未必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穆斯林称自己是波马克人。尤利娅是一位嫁到苏诺村的穆斯林,她认为不能将穆斯林直接等同于波马克人。
并不是所有的保加利亚穆斯林都是波马克人,我自己是生活在罗多彼山区的穆斯林,但我不是波马克人。苏诺村的穆斯林不是波马克人,库拉村的穆斯林是波马克人(2)2019年4月,资料来源于访谈对象苏诺村波马克人尤利娅。当笔者问到尤利娅,你婆婆不是从库拉村(目前居住在苏诺村)迁来的吗,她则说,不是所有穆斯林都是波马克人。也就是说,她虽然说库拉村的穆斯林是波马克人,但同时不承认其婆婆是波马克人。。
戴芬娜,一位63岁的苏诺村波马克人,笔者的报道人之一。戴芬娜认为一个人既可以是穆斯林又可以是基督徒,她本人就有两个宗教信仰,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见到基督教的小教堂(3)Параклис一般指建在野外的小教堂,往往就是一间屋子,屋内摆设一张案几,供人们点灼蜡烛祭拜之用。这种小教堂不同于城市或乡村中的църква(有专职人员负责看护管理且功能设施齐全的教堂)。(параклис)就进去点上蜡烛。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既是基督徒又是穆斯林?似乎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但在田野调查中有些人表明自己拥有双重宗教身份,既是穆斯林,也是基督徒。
2019年6月15日,苏诺村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波马克人共同参加庆祝罗多彼从奥斯曼帝国解放107周年(巴尔干战争之后,罗多彼归属保加利亚)纪念活动。在庆祝仪式上,东正教牧师同样为穆斯林波马克人施圣水礼祈福。因此,只有置身于地方,从日常生活世界才能更全面地理解“民族”是什么,本文也是从这种意义上理解民族国家构建的。
三、民族国家构建与地方社会转型
现代保加利亚国家独立初期,承袭奥斯曼帝国时期“米勒特”制度以宗教区分“我者”与“他者”的标准,且保障不同宗教社区一定程度的自治权。波马克人和“土耳其裔”属于穆斯林“米勒特”社区成员(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人”大致等同于穆斯林,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称谓,东正教保加利亚人甚至称波马克人为“土耳其人”),在宗教、文化教育等方面有很大自主权。在1880、1885、1888年的人口调查中,保加利亚语穆斯林(波马克人)被置于“土耳其裔”名下,直到1905年才有“波马克人”单独条目[11]。保加利亚政府在人口调查中将波马克人与土耳其裔分置不同的条目,实质上是有意分化波马克人与土耳其裔,即打破马克人和土耳其裔的宗教共同体意识。这种分类思想始终存在于保加利亚现代国家的基因里,由于波马克人的语言和宗教特性,才有了“我者”波马克人与“他者”土耳其裔的划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保加利亚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的波马克人的基督教化运动以及恢复波马克人的保加利亚族意识。
(一)波马克人的基督教化
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之前,保加利亚波马克人聚居区罗多彼山区、瓦尔达尔马其顿(巴尔干战争之后并入塞尔维亚,即今日的北马其顿地区)、爱琴马其顿(希腊北部)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巴尔干战争以后,保加利亚现代民族国家的版图才逐渐浮现。巴尔干战争期间,保加利亚在新占领的罗多彼地区发动波马克人基督教化运动,而后开启了漫长的波马克人改造运动。波马克人的基督教化首先打破的就是奥斯曼帝国的遗产“米勒特”制度,将波马克人从“米勒特”社区解放出来。
保加利亚军队和东正教牧师在新占领的罗多彼、西色雷斯以及马其顿地区强制推行将当地穆斯林基督教化的大规模改宗运动,涉及20万人,覆盖西色雷斯、马其顿和罗多彼山区的数百个村庄。随军牧师将波马克人的名字由原来的土耳其-阿拉伯名字改成了基督教名字,以及将土耳其传统服饰如“菲斯”(фес,传统土耳其人帽)、头巾(фередже) 改成了保加利亚帽子和头巾[12]。由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失败以及国内政治因素诸如议会选举的需要,保加利亚瓦西尔·拉多斯拉夫政府决定从1913年秋季开始,允许所有波马克人恢复其伊斯兰教信仰及其土耳其-阿拉伯名字[13]。
巴尔干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化是保加利亚政府整合波马克人的第一步,但宗教信仰的改变并不能解决民族认同问题,恢复波马克人的保加利亚族意识成了那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二)波马克人的保加利亚族身份构建
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构建浪潮率先出现在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非穆斯林群体中,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的民族建国运动。但土耳其民族主义(凯末尔主义)及其民族国家构建对土耳其民族的锻造又反过来影响着巴尔干半岛的穆斯林居民。虽然在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前,现代意义上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建国思想已经浮现,但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却是一个标志性阶段的开始。现代保加利亚是巴尔干半岛土耳其裔少数民族最多的国家,保加利亚政府对凯末尔主义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从这种意义上说,保加利亚面临着国族主义国家构建与土耳其裔族裔民族主义的张力,而波马克人恰恰是徘徊在东正教保加利亚主体民族与土耳其裔少数民族之间的“摇摆”群体。
波马克人的第二次改名运动与“罗地纳”(Родина,意思是“祖国”)组织密切相关,“罗地纳”是在保加利亚政府支持下于南部斯莫梁地区成立的一个穆斯林文化、教育组织。1937年,“罗地纳”成立,其目的是致力于恢复波马克人的保加利亚族意识。“罗地纳”通过一些活动,譬如,翻译保加利亚语古兰经、废除割礼、抛弃传统服饰等以改革波马克人的日常生活。1938年,“罗地纳”组织开展了反“菲斯”运动。在一个穆斯林古尔邦节(Курбан-байрам)上,“罗地纳”成员向斯莫梁及其周边地区的波马克人发放传单并声称,波马克人在民族上是保加利亚人,应该丢弃你们的红色的有外国人(土耳其和土耳其人)象征的“菲斯”帽,这会亵渎我们的穆斯林宗教心灵。宗教信仰与衣服和帽子没有什么关系[14]。更为重要的是,1942年“罗地纳”组织发动了将波马克人的土耳其-阿拉伯名字改为保加利亚名字的运动[15]。从宗教与民族两端看,第二次改名运动与第一次有着根本区别,波马克人第一次得到的是基督教名字,而第二次是保加利亚民族传统名字。正如亚历山大·卡拉曼朱柯夫指出的那样,“罗地纳”的成员们对信仰与民族有明确区分,他们的目的不是将波马克人基督教化,而依据民族纽带整合波马克人对他们来说更重要[16]。在“罗地纳”组织看来,宗教信仰与民族归属并不矛盾,两者是统一的,波马克人可以信仰伊斯兰教,同样可以是保加利亚族,即作为保加利亚族的穆斯林。与巴尔干战争期间的基督教化波马克人运动不同,“罗地纳”组织更重视“民族”而轻“宗教”,这与奥斯曼帝国时期重“宗教”轻“民族”恰恰相反。因此,有学者指出,“罗地纳”的宗旨是恢复保加利亚的民族意识,在该组织领导者的意识中,成为保加利亚人(族)也可以是一个好的穆斯林[17]。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保加利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保加利亚党和政府同样需要将少数民族整合进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来。社会主义初期,保加利亚政府在民族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谴责了民族主义组织“罗地纳”的活动,且允许波马克人恢复他们的土耳其-阿拉伯名字。但自从5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波马克人、罗姆人、鞑靼人等穆斯林群体开始冒充或自称土耳其裔[18]。1950年代后期,保加利亚政府因担心波马克人土耳其裔化,开始采取措施进一步“恢复”波马克人的保加利亚人(族)民族意识,大保加利亚民族主义思想再次抬头。
1962年夏,保加利亚共产党斯莫梁地区委员会给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提到,要将罗多彼地区脱离奥斯曼统治50周年的庆祝与保加利亚语穆斯林(波马克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教育联系起来[19]72。巧合的是,2019年6月15日,笔者有幸参加苏诺村举行的纪念罗多彼解放107周年的活动。村民们载歌载舞庆祝罗多彼山区从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解放,这无疑是在诉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对穆斯林波马克人和基督徒保加利亚人同样都是至暗时刻。
1970年7月17日,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恢复“伊斯兰教信仰的保加利亚人的民族意识”的决议。1970年8月3日,保加利亚共产党斯莫梁地区委员实施提高伊斯兰教信仰的保加利亚人的“民族意识”(националното осъзнаване)和“爱国主义教育”(патриотичното възпитаване)的中央决议[19]74。保加利亚政府更改波马克人的土耳其-阿拉伯名字为保加利亚名字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由此,保加利亚波马克人的民族“复兴运动”拉开序幕。
1972年,我们这个地方的穆斯林改了名字,我改名之前的土耳其-阿拉伯名字叫泽基,我有两个儿子,一个住在村子里,另一个在省城斯莫梁市工作,儿子们都已经结婚,我已经有了四个孙子。我们村曾经历过三次改名运动。第一次是在1912年,巴尔干战争的时候。第二次是在1940年左右“罗地纳”时期。第三次是在1972年,也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改名发生在1972年的秋季,大概是10-11月份左右,改名运动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如果不改名的话,就会面临失去工作的风险(4)2019年3月20日,资料来源于访谈对象波马克人德尔科。。
我今年63岁,1956年出生在巴尼泰,在小阿拉达村上学,因为父母没有钱,我只上到10年级就辍学了,我以前的名字叫阿萨白(Асабай),但是在16岁那年改成了戴芬娜(Дафинка),现在一直用戴芬娜这个名字。那时候我的年龄还小,父母的名字都改了,我也就跟着父母改了,亲戚和朋友们的名字也都改了。我和我的丈夫都不是本村人,我们来自巴尼泰,后来在保加利亚北部城市鲁塞生活过一段时间,我们一家1979年迁到苏诺村,到目前为止已经整整四十年了(5)2019年6月10日,资料来源于访谈对象波马克人戴芬娜。。
(三)乡村经济、文化发展促进民族融合
保加利亚社会主义时期不同于资产阶级政体的地方在于,保加利亚党和政府致力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发展,并通过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整合,这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地区治理传统。历史上,罗多彼山区的生计方式主要是山林伐木、畜牧,部分地区种植烟草。社会主义时期,通过边疆开发以及推行计划经济,传统的生计方式逐渐消失。
1969年11月11日,保加利亚共产党政治局第500号决议通过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有关进一步提高斯莫梁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草案。1969年11月15日,部长会议第43号法令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斯莫梁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1970年5月5日,经济协调委员会134号决议明确提高各部委和商业协会在斯莫梁地区建设新企业和出口该地区工业产品的力度[19]63。在保加利亚党和政府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刺激下,罗多彼山区涌现出很多乡村集体企业。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诺村建立制衣厂、奶酪厂等集体企业。
社会主义时期,苏诺村是周围几个村庄的中心。1974年,苏诺村成立了制衣厂。1979年,苏诺村周边村庄的穆斯林大量来到制衣厂工作,部分从此定居在这里,目前生活在苏诺村的波马克人就是周边村庄穆斯林移民的后代。我的父母于1979年迁到苏诺村,母亲曾经在制衣厂工作过。苏诺村制衣厂的经营时间是在1974年至1994年的二十年间,工人最多的时候达到100人左右。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村里的波马克人和基督徒已经很深地融入到一体了。九十年代以后,苏诺村的工厂就关闭了(6)2019年6月2日,资料来源于访谈对象波马克人罗森。。
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苏诺村新建了制衣厂、牛奶和奶酪加工厂,也有奶牛场,每家每户基本上也都养有奶牛,经济作物有种植烟草和土豆等,附近的村民都来苏诺村工作。社会主义时期,保加利亚与苏联的关系很密切,苏诺村不但有些工农业产品可以出口到苏联,而且也有很多人员往来交流机会,村里很多人尤其是老年人几乎都会说俄语。我也会说俄语,大学时曾经去过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留学(7)2019年3月13日,资料来源于访谈对象波马克人西卡。。
保加利亚社会主义时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走苏联工业化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系统内同其他国家发展贸易[20]。乡村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过去的经济结构,农村地区遍布轻工业,比如,纺织加工、制衣、制鞋厂,山区畜牧业、牛奶、奶酪加工等,基本形成工作处处有、人人有工作的局面。保加利亚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尤其是乡村经济发展得到极大改善。
社会主义时期,罗多彼山区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小学,适龄儿童可以在本村接受小学教育,核心村庄甚至有可以覆盖到周边村庄的寄宿制初、高中。农村几乎没有文盲,每个人都得接受八年制义务教育。70年代,苏诺村在原有小学基础上建立了一所寄宿制学校,开设从小学到高中(1-12年级)的课程,许多教师从索非亚、普罗夫迪夫等大城市分配到苏诺村,目前有些未“返城”的教师仍然居住在苏诺村。
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行八年制义务教育,村民至少得上到八年级,社会主义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没有人不识字的,即使八九十岁的老人也识字,老年人大多都会说俄语,有些人对俄罗斯文学作品很熟悉,有时候我们图书馆(Читалищте,乡村社区文化中心)会组织村民去斯莫梁剧院观看演出。上一次看契科夫的舞台剧《海鸥》,有不少老人都会参加,她们的欣赏水平很高。但现在有些年轻人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就辍学了。社会主义时期是必须接受至少八年制的义务教育,整个村庄都没有文盲。在社会主义时期,索非亚、普罗夫迪夫的教师前来罗多彼地区支教,学校配置了教工宿舍,而且专门建造房子供外来教师居住(8)2019年5月16日,资料来源于访谈对象达妮。。
另外,乡村学校有医疗室,负责学生常见疾病的诊治,镇上有更高一级的卫生院。尽管乡村学校医生的诊治水平参差不齐,但至少能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且基本上是免费的。
如前文所述,在社会主义时期之前,苏诺村是没有波马克人居住的,因此村庄的墓地里安葬的都是基督徒。社会主义时期,苏诺村建立了一些集体企业,周边村庄波马克人移民的到来改变了这一现状。苏诺村的波马克人依然保持着一定的穆斯林习俗,尤其是在出生、死亡等有关事项上,波马克人去世后安葬在本村墓地。宗教在这里表现出很大的宽容,没有非此即彼,上帝没有讲究差异原则。笔者田野调查期间多次探访墓地,村民们给笔者讲述墓地的历史,介绍墓碑上的人物,哪些人是基督徒,哪些又是穆斯林。从墓地勘探到的情况得知以下信息:苏诺村墓地已有两百年历史,目前现存最早的墓碑立于1950年代,直到1984年波马克人才安葬在这里,而后的几十年不断有穆斯林在此墓地安葬,而且波马克人墓碑上的名字是保加利亚人名字。
(四)东欧剧变后的波马克人生活变革
罗多彼山区居民不停地向笔者抱怨他们没有钱、没有工作,甚至会咬牙切齿地控诉保加利亚政府的腐败。保加利亚转型以来,政府将大量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私有化甚至转让给西方资本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大量社会主义时期的乡村企业纷纷关闭,转型的连环效应给罗多彼山区居民带来了私人生活的变革。苏诺村的企业也没有逃过这一命运,奶酪加工厂、制衣厂相继关闭,其他乡村集体企业也不复存在,当地村民失去工作,但又无法回到社会主义之前山区畜牧型生计方式。农村集体经济曾经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工厂关闭之后,平原地区的农村居民尚可以耕地为生,但对山区居民则意味着灾难。由于山区没有大块耕地从事种植业,大量劳动力只能选择背井离乡,年轻人大量外流到索非亚、普罗夫迪夫等大城市谋生,致使乡村萧条进一步加剧。2007年,保加利亚加入欧盟,保加利亚人大量走向海外发达国家诸如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寻找工作机会,山区农民也不例外,这是当地居民的另一项收入来源。国外工作的工期并不固定,一般而言都是两三个月的短期工或者季节性劳工,工作项目结束就回到村里。
劳动力外流致使当地适龄教育儿童严重减少,先是各村庄小学关闭,学生分流到更大的村庄,而后初、高中也关闭。2008年,苏诺村寄宿制学校关闭,目前,苏诺村及其周边村庄的学生都去几十公里外的1000人以上的大型村庄就读,每天都有校车专门接送学生。教育资源的地域分布不均再一次使得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家长们不愿意孩子奔波于家与学校之间。乡村各级学校的关闭使得大量教师失业,很多人不得不靠打零工为生。
我年轻的时候做过三份工作。在保加利亚转型之交的那些年里,我在本村小学做了28年的教师,教的学生是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但在二十一世纪初,很多人离开了村子移居到其他地方,像索非亚、普罗夫迪夫等大城市,学校里没有学生了,我也就失业了(9)2019年3月20日,资料来源于访谈对象波马克人德尔科。。
罗多彼山区无法提供工作,但当地居民又深深地融入现代经济生活中来,无法回到社会主义之前山林放牧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因此,留守农村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这也是笔者田野调查期间只参加过村民的葬礼而从未参加过婚礼的原因。农村不再有年轻人,尤其是未婚女青年,为数不多的男青年也因此找不到对象。现实的窘境,使得村民对社会主义时期充满了回忆,社会主义是他们难以忘记的“乡愁”。
在日夫科夫社会主义时期,村里有很多工作,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工作。库拉村的村民来苏诺村工作,早上来,晚上回去,每天有一趟公交车,但有两个来回。但现在村里没有工作,无论年轻人还是年纪大的人都找不到工作。很多年轻人不得不去国外打工,去德国、西班牙、英国等国家(10)2019年6月11日,资料来源于访谈对象波马克人卢思卡。。
笔者田野调查期间,正值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到访保加利亚,电视上都是他在索非亚的画面。在演讲中,他将东西冷战意义上的“铁幕”改为“冰幕”,指出东欧转型30年,欧洲再次陷入一场新的分裂,即东西欧之间的贫富差距致使大量移民从东欧贫穷国家来到西欧富裕国家。这与社会主义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保加利亚转型后,苏诺村的全部、库拉村的大部分穆斯林没有改回原来的穆斯林名字,而是一直沿用1972年改名之后的保加利亚名字,年轻人全部采用保加利亚名字。苏诺村的丹尼尔和米莱娜夫妇告诉我说,“我们就是保加利亚人,是保加利亚族”,不禁让笔者想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
结语
保加利亚民族国家构建和波马克人的民族化进程表明,保加利亚在发明“民族”方面并不是那么成功,恢复波马克人的保加利亚族意识的实践往往倒向大保加利亚民族主义。事实上,自从脱离奥斯曼帝国以来,保加利亚政府的波马克人问题行动逻辑及其目的都很明显,即恢复波马克人的保加利亚族意识,成为保加利亚人,融入到保加利亚社会生活中来。这种现代国家的迷思伴随着保加利亚近现代史,整个巴尔干半岛大体上也是如此。“民族”的发明背后实质是巴尔干各民族国家对领土的要求,以至于“欧洲火药桶”成了巴尔干半岛的标签。因此,只有打通奥斯曼历史遗产、西方民族国家经验以及巴尔干本土传统,在文明、文化交流互鉴中进行多民族国家建设,巴尔干才能摆脱“欧洲火药桶”的魔咒,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