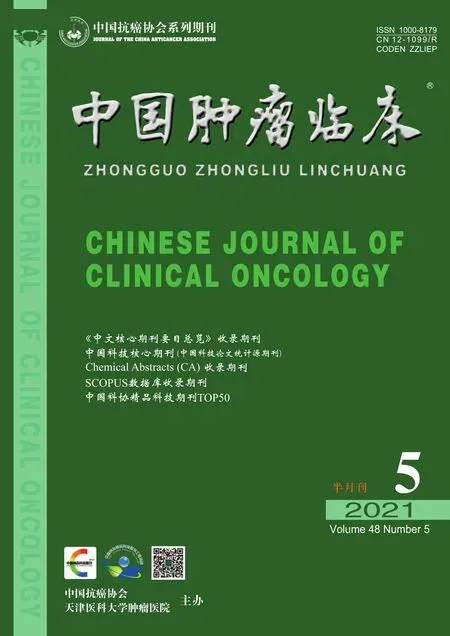类器官在肿瘤中的研究现状及应用前景*
高婷 郭瑢 黄胜 陈德滇
恶性肿瘤一直以来都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备受关注。目前,用于研究恶性肿瘤的临床前模型主要是细胞系和患者源性的肿瘤异种移植。尽管其为肿瘤的研究做出贡献,但仍有缺陷。近年来,一个新兴起的领域—类器官,为肿瘤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类器官能够在体外高度重现体内肿瘤的原始特征,在药物研究、预测患者对治疗的反应以及为患者提供个性化医疗方案方面,拥有广阔的前景。目前,已经成功培养出如胃肠[1]、肝[2]、前列腺[3]和乳腺[4]等多种类器官。类器官的出现,无疑给肿瘤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本文将对类器官的研究现状及其在肿瘤研究中的应用前景进行综述。
1 现有的肿瘤研究模型
人类肿瘤较为复杂,不同的肿瘤患者对相同的临床治疗反应可能存在很大差异。目前,肿瘤进展的机制以及药物疗效和耐药的产生机制仍不明确[5]。大量通过Ⅰ期药物安全性测试的抗癌药物在Ⅱ、Ⅲ期的疗效测试中被淘汰[6]。因此,需要优化临床前疗效模型来改进对临床治疗反应的预测,降低临床试验的失败率。目前,正在使用的几种人类临床前模型包括细胞系(cell lines)、患者源性的肿瘤异种移植(patient-derived tumor xenografts,PDTX)和患者源性的肿瘤类器官(patientderived tumor organoid,PDTO)[5]。
1.1 细胞系
细胞系可能是这些技术中最常见和最完善的。与大多数其他体外模型相比,细胞系操作起来更容易,成本更低,且易于进行基因修饰。细胞系还能够在短时间内对多种药物和化合物进行高通量筛选[7]。但细胞系通常来源于单个细胞,而肿瘤通常由多种不同的细胞类型组成,可能具有不同的治疗敏感性,因此细胞系不能完整的概括肿瘤多样性[8]。传统的细胞系模型缺乏许多关键的信号转导因子,这些因子对细胞的增殖、分化和存活起重要作用。因此,利用传统的细胞系模型在体外条件下预测患者对治疗的体内反应,可能不够准确[7]。此外,细胞系培养的细胞是单一的,不能模拟体内肿瘤细胞与其他细胞(如基质细胞、免疫细胞和神经细胞)的相互作用[9]。
1.2 PDTX
PDTX 是将癌细胞或组织移植到免疫缺陷的小鼠体内建成的临床前模型[7]。目前,多种癌症类型已经建立了PDTX 模型,包括结直肠癌[10]、胰腺癌[11]和胃癌[12]。PDTX 模型允许移植细胞或组织在具有脉管系统的肿瘤结构和环境中生长[13]。有研究利用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的PDTX模型与供体组织相比较,发现供体组织中检测到的突变总数,仅43%突变出现在相应的PDTX 模型中,4 个原发肿瘤中不存在的突变出现在PDTX 模型的早期传代中[14]。由此可见,PDTX 模型无法完全还原原始肿瘤的基因特性。此外,其还具有诸如耗资耗力、培养周期长、效率低和难以开展高通量药物筛选工作等局限性[9]。
1.3 PDTO
类器官,来源于组织特异性干细胞的三维体外细胞结构,具有自我组织形成类似于原始组织的“微型器官”的能力,可以弥补传统的培养技术在治疗反应预测方面的不足。有研究从乳腺癌患者切除的肿瘤中获得肿瘤组织,通过机械破坏和酶解结合的方式去除正常组织并分离出乳腺癌细胞,在体外三维培养条件下,成功的建成了可长期培养的乳腺癌类器官[4]。与细胞系相比,PDTO 模型在细胞形态和空间结构方面,能更好地显示与原始肿瘤的相似性。与PDTX 相比,类器官更容易进行基因修饰[15],也更适合高通量药物和治疗测试。尽管PDTO 是一项相对较新的技术,但正常组织干细胞来源的类器官和癌症干细胞来源的类器官已经在癌症生物学和个性化医学领域做出巨大的贡献[7]。来源于正常组织的类器官更加接近正常的生理状态,可用来研究人体的生理过程,药物研究时可用来测试药物的内脏毒性,期待未来可以建成用于器官移植的健康类器官。来源于肿瘤组织的类器官因其能够高度还原原始肿瘤特性的特点,在为患者提供个性化医疗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同时也为肿瘤进展、侵袭和药物反应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然而,由于缺乏神经支配、血管和免疫细胞,类器官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9]。
2 类器官的应用
类器官的应用汇总,见图1。

图1 类器官的应用
2.1 药物研究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从传统的细胞系筛选而来的抗癌药物在临床研究中均失败。对于大多数细胞毒性药物,在肿瘤细胞系中观察到广泛的活性,但对患者的临床疗效却是有限的。有研究[16]曾评估体外细胞系在预测临床疗效方面是否可靠。应用细胞系来预测针对乳腺癌、非小细胞肺癌、卵巢癌和结肠癌的细胞毒性抗癌药物的药物活性。结果表明,体外细胞系模型对结肠癌无预测作用,对其他3种癌具有预测作用。由于肿瘤类器官是接近生理的结构,保留了母瘤的特定功能,并能准确地再现药物反应。因此,类器官技术填补了基于传统细胞系的药物筛选与临床试验之间的空白。研究表明,类器官可以作为评价癌症患者特异性反应的良好模型[17-18]。此外,还可用来探索耐药性背后的详细因果和遗传改变。目前,一些癌症的类器官生物库已经建立,用于识别和测试新药物,而健康组织的类器官可以用于测试药物毒理学[19]。
2.1.1 药物筛选 PDTO 在高通量药物筛选,为患者选择合适有效的治疗方案方面具有很大潜力。目前,已经有研究将类器官应用于药物筛选[20]。有研究[21]通过对20例结直肠癌患者的肿瘤类器官进行药物测试,证实肿瘤类器官适用于高通量药物筛选,并可以检测基因-药物关联性。Pauli 等[22]提到在药物库中筛选ER+乳腺癌患者源性病例和BRAF 突变黑色素瘤患者源性病例,发现他莫昔芬、BRAF 和MEK抑制剂为最佳推荐药物,表明高通量筛选可以确定临床已验证的靶向药物。该研究还认为仅基因组学信息不能够为大多数晚期癌症患者确定治疗方案,因此使用PDTO进行高通量药物筛选,以发现有效的治疗方案。并通过分析2 例子宫恶性肿瘤和2 例结肠癌来源的肿瘤细胞,确定有效的药物组合,并使用3-D 培养模型和PDTX 模型对其进行验证。上述研究均表明,利用肿瘤类器官可进行高通量药物筛选,检测基因—药物关联性,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2.1.2 药代动力学研究 类器官技术可以应用于药代动力学测试,这是药物开发的关键[19]。有研究发现[23],由人类诱导多能干细胞生成的肠类器官,具有药代动力学功能。并发现在一些小分子化合物的作用下,类器官中可检测到药物转运蛋白、通过AB⁃CB1/MDR1 的外排转运活性以及核受体配体对药物代谢酶CYP3A4的诱导作用。由此可看出,运用类器官技术,可以进行药代动力学研究。
2.1.3 药物毒理学研究 在药物开发中,类器官技术的另一个主要优势是可以生成和利用正常的类器官来筛选仅针对肿瘤细胞而不伤害健康细胞的药物[19]。在临床试验中,不可耐受不良反应是导致药物失败的主要原因,包括肝脏毒性、心脏毒性和肾脏毒性[19]。肝类器官可以用于测试药物的肝毒性[24]。药物相关的肝毒性主要是通过细胞色素P450酶介导的,肝类器官能够接近生理水平观察到细胞色素P450酶的作用[25]。心脏毒性反应如心律失常和心功能降低也可以在类器官中测试[26]。此外,肾类器官也被用于药物毒理学研究[27]。将类器官技术应用于药物临床前的毒理学研究,有助于降低药物临床试验的失败率,减少药物临床试验阶段不良事件的发生(图2)。

图2 用类器官进行药物筛选
2.2 肿瘤发生发展机制的研究
类器官通常可以从正常的人类上皮细胞中获取,可在体外对所有阶段的恶性肿瘤进行突变建模。有研究提示[28],在体外培养各种类型的癌前结肠瘤具有可行性。基因突变是肿瘤发生发展的基础。为此,多个研究团队通过对类器官进行基因修饰,来研究肿瘤的发生发展机制。有研究认为[29],Kras突变或p53缺失的小鼠胰腺和胃类器官,会导致其发育异常和过度增生,将这些类器官移植到小鼠体内后可形成肿瘤。有研究利用CRISPR-Cas9技术将4种通常在结直肠癌中发生突变的基因(KRAS、TP53、SMAD4 和APC)引入到人类肠道组织干细胞中[30-31]。Drost 等[31]通过从培养基中去除单个生长因子来选择突变体,并将其移植到小鼠体内,可生长为具有浸润性癌特征的肿瘤。Matano 等[30]在四突变体的基础上引入另外一个突变—PIK3CA,并将此五突变体移植到小鼠的肾囊中,同样可以形成肿瘤。随后,Drost 等[32]又利用CRISPR-Cas9 技术敲除人类结肠类器官中关键的DNA 修复基因,并对其进行全基因组测序。该研究还发现,错配修复基因MLH1缺失的类器官可以准确地模拟错配修复缺失的结直肠癌中观察到的突变谱。有学者通过胰腺类器官研究证实KRAS突变可诱导巨噬细胞成瘤表型,从而促进肿瘤生长[33]。上述研究均阐明了类器官的能力,可用于揭示癌症基因组的复杂性以及基因突变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有助于癌症精准治疗的药物靶点的发现。
2.3 临床治疗的研究
2.3.1 个性化医疗 个性化医疗,也称为精准医疗,旨在通过在分子和药物基因组学水平上更好地描述疾病特征,为每个患者制定有效的治疗策略[19]。类器官在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上具有巨大的潜力。如测量来自囊性纤维化患者的直肠类器官中囊性纤维化跨膜电导调节器的功能,可以确定哪些人将受益于囊性纤维化跨膜电导调节器矫正治疗[34]。为了证实原发肿瘤的遗传基因组学特征能否在类器官中被保留下来,有研究[35]对来自14 例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的类器官的1 977 个癌症相关基因进行了基因分析。结果表明,90%的体细胞突变在来自同一患者的类器官和活检标本中是相同的,并且类器官和相应的原始肿瘤的DNA拷贝数图谱的相关系数为0.89。表明类器官可以很好的捕获原始肿瘤的遗传特性,为类器官在个性化医疗中的应用提供有力的证据。尽管目前类器官技术在个性化医疗中还处于不成熟阶段,但更深入的研究将完善该模型,拓宽个性化医疗的视野,替代传统的“一刀切”治疗方式[19]。
2.3.2 预测患者对治疗的反应 预测患者对治疗的反应是类器官技术的另一潜在应用。可以通过在体外对患者源性类器官进行一些治疗操作,以此类器官对治疗的反应来预测提供活检组织的患者对治疗的反应,以便为患者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案。Hubre⁃cht 类器官技术基金会进行了一项关于转移性乳腺癌、结肠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的大型多中心队列研究[36]。在该项研究中,来源于转移病灶活检的肿瘤类器官的药物反应与患者的临床反应呈正相关。但患者实际治疗方案与体外药物筛选方案中药物剂量的差异,是需要进一步去探索的难题。目前,已有学者用转移性胃肠癌的类器官来预测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并比较了类器官和基于患者源性类器官的原位小鼠肿瘤异种移植模型对抗癌药物的体外反应和临床试验中患者的反应,阳性预测值(预测某一特定药物有效)为88%,阴性预测值(预测某一特定药物无效)为100%[17]。提示患者来源的类器官能够在体外条件下预测患者对治疗的反应,为个性化医疗提供指导。
2.3.3 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是一种新颖而有前景的肿瘤治疗策略,利用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杀死肿瘤细胞。免疫治疗的先决条件是恶性细胞表现出足够的免疫原性来触发足够的免疫反应。癌细胞的突变状态,有助于新抗原的产生,激活免疫反应。然而,由癌细胞新抗原引起的免疫反应强度不足,可以通过在体外激活和扩增免疫细胞,应用于患者体内来解决[19]。多项研究为类器官技术在免疫治疗中的应用带来新的希望。如上皮内淋巴细胞在含有白介素-2、白介素-7 和白介素-15 的培养液中,与小鼠肠道类器官共培养,可维持增殖状态[37];有研究成功的进行T淋巴细胞与人原代乳腺上皮类器官的共培养,发现这些T 淋巴细胞可以有效地清除三阴性乳腺癌的癌细胞[38]。这表明,来自健康献血者的T淋巴细胞可以被类器官在体外扩大和激活,之后用于体内治疗患者,且可使健康献血者来源的T细胞对患者来源的类肿瘤细胞的细胞毒性效应在体外测试成为可能[19]。将类器官与免疫细胞进行体外共培养,可以扩增免疫细胞,增强免疫反应,为后续的免疫治疗提供强而有力的保障。此外,研究肿瘤微环境也离不开类器官与免疫细胞及其他细胞的共培养技术。
2.4 肿瘤微环境
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在肿瘤的发生发展及治疗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的肿瘤类器官模型普遍缺乏完整的微环境。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类器官与TME细胞的共培养为研究TME 的某些特征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如胰腺星状细胞与胰腺癌类器官共培养产生了典型的胰腺癌间质纤维增生,并直接导致了胰腺癌的癌相关成纤维细胞(cancer associated fibroblast,CAF)亚型的发现,其中包括分泌白介素-6 以支持类器官增殖的亚型[28]。另一关于PDTO-CAF 共培养的研究揭示了两种不同CAF 亚型的生化途径,以及在胰腺导管腺癌微环境中建立不同成纤维细胞群的机制,并阐明了选择靶向支持肿瘤生长的CAF的方法[39]。尽管如此,这些共培养系统仍在开发中,目前尚未达到的目标是确定这种PDTO-CAF 共培养是否会对传统和正在研究的药物产生耐药性,以及其是否可以用于优化体内外治疗反应[28]。为了在体外模拟糖尿病血管病变,最近的一项研究报道了从多能干细胞形成人血管类器官,这些多能干细胞自我组织成毛细血管网络,包括内皮细胞和外膜细胞,并被基底膜包围[40]。该研究将这些类器官移植到小鼠体内后,形成了一个稳定灌注的血管树,包括动脉、小动脉和小静脉。人体血管类器官的建成,为研究TME 提供了新的可能。不仅可以采用PDTO与CAF、免疫细胞共培养,还可以实现PDTO 与血管类器官的共培养,来模拟更多的TME成分。
3 结语
综上所述,来源于人体不同组织的类器官,可用于药物的研究,有利于药物的筛选和新药的研发;也可对其进行基因编辑,来研究肿瘤的发生发展机制;还可在体外预测患者对临床治疗的反应,有利于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医疗方案。虽然类器官模型具有诸多优势但下述问题仍亟需解决:1)提高生成效率,缩短类器官模型的培养周期,降低培养成本[28];2)目前的类器官主要来源于上皮细胞,需要进一步研究非上皮类器官的培养方式[19];3)目前暂无一个具有类器官的最优培养条件的标准化方案[9];4)继续完善除免疫细胞和成纤维细胞之外的TME成分与类器官的共培养[28]。肿瘤是个复杂的疾病,无论发病机制、转移机制,还是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和耐药机制,均有很多尚未明确的问题亟需探索。未来的研究需要不断完善对TME 的模拟,以创造更为接近原始肿瘤特性的肿瘤类器官模型,从而更为全面地了解恶性肿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