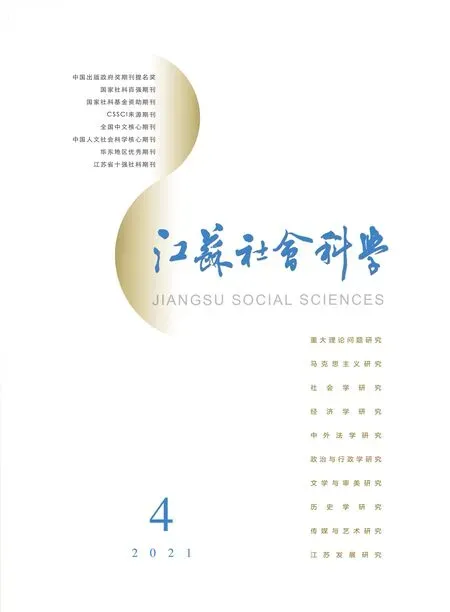西渡诗歌的修辞想象和历史想象
苗 霞
内容提要 本文从形式出发对西渡诗歌进行修辞学批评,以探求其文本的意义建构而不是意义表现。叙述,对于西渡来说不唯是一种写作技巧,更是一种结构形态。西渡诗歌叙述的结构形态传统温和、平缓舒展,其意义诉求和价值目标在于用叙述带入节奏,试图借助略带叙事性的格局把文本的疏密度和时间速度转换成一种诗歌的节奏。同时,思辨在叙述的节奏内鼓荡奔突,给文本注入沉重尖锐的价值观和命运感,表征出诗人对历史丰沛的想象力。对西渡诗歌的个案批评可以阐释当代诗歌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语言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探析出诗学和社会学、修辞想象和历史想象间张力营建的枢机所在。
引 言
在人类文化史上,诗歌曾受到数次批判,其中最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古希腊柏拉图把诗人从他的理想国驱逐出去,其中缘由:一、诗歌不直接反映真理本身,而是反映真理的影子的影子;二、诗歌摧残理性,逢迎人性中低劣的情欲,不利于培育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1]〔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30页。。另一次是阿多诺对诗的“审美之罪”的判定:“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2]〔美〕马丁·杰:《阿多诺》,翟铁鹏、张赛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两者都是立足于现实的理由对诗歌进行指控。前者指控诗歌诱惑了现实,后者控诉诗歌遗忘了现实。由此可以看出,诗学和社会学的关系是从古至今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当前诗歌在现代性、后现代的状态下,“语言作为主题、作为现象已成为诗歌写作的一个基本动机”[3]耿占春:《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见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在“改变语言”的梦想中诗歌语言越来越个人化,甚至成为隐秘的无任何外界通道的私人话语。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是文学“改变世界”的一翼真的丧失殆尽了吗?对语言道德和诗歌精神的追求从来就不会被人真正忘记。因为对意义的追寻,是人性固有的不竭热情。如同昌耀在《意义的探索》中铿锵有力地写道:“疏离意义者,必被意义无情地疏离。/嘲讽崇高者,敢情是匹夫之勇再加猥琐之心。”[1]昌耀:《意义的探索》,《人民文学》1996年第6期。
今天再次重审这个话题,绝非为了回到所谓文学的传统“外部研究”——那种侧重文学与时代、社会、历史的关系研究,而是研究“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语言与现实世界的联系”[2]韩作荣:《2000年的中国新诗》,《诗探索》2001年Z1期。。这是20 世纪以来哲学“从认识论到阐释学”转变下批评学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语言哲学理念下的批评性阅读强调从形式出发。“现代批评已经证明,只谈内容就根本不是谈艺术,而是谈经验;只有当我们谈完成了的内容,即形式,即作为艺术品的艺术品时,我们才是作为批评家在说话。”[3]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43页。形式不仅是批评的出发点,更是批评的对象。形式不是有助于意义,它本身就具有时代的、精神的、文化的、社会的意义。形式与内容的互为辩证,早已成为现代文学理论中的定见。这样,形式批评的方法论中自然导入价值论和意义阐释,同时也实现了修辞批评、美学批评和社会学批评的统一,既从感觉、感知和感受状态的审美角度介入诗歌,又从真理和历史的角度把握诗歌,将诗歌形式所指涉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带入问题讨论中来。
接下来,笔者试图通过对西渡诗歌的阐释探析出诗学和社会学、修辞想象和历史想象间张力营建的枢机所在。从形式技巧上看,西渡作品工拙相半,大巧若拙,因朴生文,因拙生巧。在修辞方面,透明、纯粹和高贵,整个诗歌意态呈现出一副宁静的外貌,显得平和安然,有一种古典性的静穆纯粹的气韵。但在平淡、温和的表面之下,隐藏着某种尖锐之物,潜伏着某种不安和绝望。这种尖锐之物是一种对存在、死亡、命运、历史的激情思辨,它的机锋、锐利和沉重的压迫性力量深深戳痛着读者的心灵。可以说,西渡诗歌生动演绎着“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4]耿占春:《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见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挖掘出西渡诗歌文本中深潜着的形式技巧,并在此基础上探析出简约的言说方式与错杂的言说内容、语言的平缓与内涵的尖锐之间的矛盾,就成了笔者的努力向度。
一、用叙述建立节奏
自《寄自拉萨的信》始,叙事性的因素进入西渡诗歌创作;但叙事性作为一种明确的诗歌意识,则是从1997年的《阜成门的春天》自印诗集开始的[5]王东东编:《诗歌中的声音:西渡研究集》,华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257页。。在二十多年的诗歌创作中,西渡的叙述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诸如《一个钟表匠的记忆》《在黑暗中》《公共时代的菜园》《屠龙术》《但丁:1290,在大雪中(之一)》《但丁:1290,在大雪中(之二)》,都具有一种由叙述语调所支撑的整体感,隐含事件的某些基本要素,虽然叙述并不完整。其中《一个钟表匠的记忆》是西渡诗学中叙事性的一次集中而精彩的呈现,已被臧棣精辟地阐释[6]臧棣:《记忆的诗歌叙事学——细读西渡的〈一个钟表匠的记忆〉》,《诗探索》2002年Z1期。。钟表匠的记忆中铭刻着“她”一生的个人史,这种个人史又镶嵌在时代史之中。“她”,从特殊年代的政治热情勃发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狂热,乃至最后的加速度死亡。几十年间,诗人摄取多帧重要的生活图景镶嵌在一起:
第一帧——“我们在放学路上玩着跳房子游戏”;
第二帧——“那年冬天我看见她/侧身坐在小学教师的自行车后座上/回来时她戴着大红袖章,在昂扬的/旋律中爬上重型卡车,告别童贞”;
第三帧——“当锣鼓喧闹把我的玩伴分批/送往乡下,街头只剩下沉寂的阳光/仿佛在谋杀的现场,血腥的气味/多年后仍难以消除”;
第四帧——“几年中她回来过数次,黄昏时/悄悄踅进后门,清晨我刚刚醒来时/匆匆离去”;
第五帧——“在我的顾客中忽然加入了一些熟悉/的脸庞,而她是最后出现的:憔悴、衰老”;
第六帧——“之后我只从记者的镜头里看到她/作为投资人为某座商厦剪彩,出席/颁奖仪式。真如我盗窃的机谋得逞/她在人群中楚楚动人”;
第七帧——“随后是我探出舌头/突然在报上看到她死在旅馆的寝床上”。
七帧画面,每一帧都有各自充足的时代感,虽然它们只是横断面的叙述,但组合在一起又构成了纵向的线性结构,在散碎的经验碎片中造就一种整体的历史时间体验,一种体验中的历史时间整体,形成一个富有文本意义的历史故事。
西渡的叙事性有时还体现在一连串的动词上,持续性的动作行为组合在一起就会变成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事件。如:《在黑暗中(致臧棣)》一诗,慢慢陈列出一系列的空间性动作:“压在”“串起来”“一扽”“拉直”“引出”“缝缀”“跃起”“弹起来”“转身走到”“俯视”“伸出手”“捧出”“说”“贡献”。围绕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两个描述性的句子“……像……”,加大了该动作行为在叙述时间中的长度,也加大了它在读者阅读时间中的长度。表面看来,装饰性语句“……像……”是一种手段,可在这里它更是一种目的,其功能和意涵被导向了复杂化。这正是文学上的转喻或换喻现象,喻体成为主角突出在前台,喻本却退隐其后。这里的叙述其实已分化为讲述和描述,讲述与描述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同流并峙的格局,二者除了在功能上的互补性之外,还有结构上的互渗性。这样的叙述从容不迫,松弛和散漫之中含有某种即兴的诗味,实现了西渡“用一种讲述真实事件的口吻来呈现一个心理事件”的目标诉求。有时,西渡干脆抛弃讲述,而把叙述渐渐变成一种纯粹的描述,一种精彩的现象学描述。在《对风的一种修辞学观察》中,对风的描述修辞是这样的:“风行的路线/上可牵挽云的纤手,下可/安抚浪的细腰,调皮的时候/可以像一截牧羊鞭抽打/浪的肥臀。憋足一股风气/可以和遗老的山较劲儿/心软了,可以把自己变做/雨的轿子、花的枕巾/用最细的吸管、最多情的嘴/吸干草叶上的露水。也是/最风流的浪子,压倒一排排草/剥下她们的细腰裤,让她们/大吃一惊,来不及捂住惊鸿一瞥的/风情。”[1]西渡:《西渡诗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19页。
如果说《一个钟表匠的记忆》讲述一场现实事件,那么《对风的一种修辞学观察》就是用语言自我编织、自我繁殖的描述方式制造一场语言事件。《一个钟表匠的记忆》中的叙述是故事情节的推移,《对风的一种修辞学观察》中的叙述是修辞的大量自我衍生,但它们无疑都是一种力学反应(现实反应和心理反应)。这些叙述方法,对于西渡来说,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写作技巧,更是一种结构方式。这种叙事性的结构方式不仅形态上独异,而且其旨意也是大为殊异。这种差异也存在于西渡和别的诗人之间。为了廓清这一不同,需要把目光回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诗坛。当时一批诗人如张曙光、肖开愚、孙文波、翟永明、陈东东、欧阳江河、西川等纷纷在诗歌创作中引入叙事性手法。这种现象最初是出于诗歌观念的巨大改变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性行为——为了摆脱80年代诗歌绝对夸饰情感的浪漫主义写法。因为只有叙事性,才能把日常生活经验引入诗歌里面去,使诗更有生活的鼻息和心音,具有真切的、可以还原的当下感,使诗歌的话语保持硬度并使之在生命经验中深深扎根,有助于诗歌维系住生存情境中固有的含混与多重可能[2]陈超:《求真意志: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见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但到后来,对很多诗人来说,策略性就变成了技术性之一种。从策略性到技术性,就是从自为到自在,由此他们的叙事性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在张曙光那里,日常生活是一种碎片化的呈现,而叙事性就是一种碎片化的呈现形式,这种叙事技巧强有力地保证诗歌智慧“主脑”的运行,能够达至对反思的反思,一种批判的再批判[1]见拙文:《思想的自由和风景的迷离——张曙光诗歌艺术新变论》,《中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肖开愚90年代的创作对“叙事的条件”有着自觉的追求:叙事不仅关涉“陈述句”的表达问题,更关涉诗歌“综合的写作才能”(尤其是诗歌的“戏剧性”)[2]贾鉴:《身体地理学与“间歇”的诗意——肖开愚90年代诗歌论》,《新诗评论》2016年总第20辑。。西川的“叙事性”是和重新考虑一种“在质地上得以与生活相对称、相较量”的语言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它在现实性上是一种“能够承担反讽的表现形式”,可以充分接纳“经验、悖论、噩梦”,其可能的指向则是“把诗歌的叙事性、歌唱性、戏剧性熔于一炉”的“综合创造”[3]唐晓渡:《九十年代先锋诗的几个问题》,见唐晓渡主编:《辩难与沉默:当代诗论三重奏》,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87—88页,第88页。。在翟永明那里,“叙事性”和“戏剧性”的重要在于可以借以打破那种“来自经验底层”,并逐步凝定为一套“固定词汇”的力量对写作的控制,由此发展出一种具有“细微的张力、宁静的语言、不拘一格的形式和题材”的更见成熟的个人风格[4]唐晓渡:《九十年代先锋诗的几个问题》,见唐晓渡主编:《辩难与沉默:当代诗论三重奏》,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第87—88页,第88页。。
和他们相比,西渡的叙述形态较为传统温和,没有他们的峭急峻刻,而是一派从容舒缓。而且,西渡诗歌叙事性的意义目标诉求与他们也截然不同,他不像张曙光、西川、翟永明那样为引入日常生活和现实景观而叙事。西渡诗歌深受海子、骆一禾、戈麦的影响,诗歌审美有追求崇高理想、圣洁人格、神圣信念、唯为天道的一面,只不过没有后者那么绝对化。即使是写日常生活,西渡也是选择其中能把主体带入巨大的日常满足和巨大痛苦的体验之中的一瞬间、一片刻:“衣服一件件脱去,暴露出苍白/的肌肤:那些日常的仇恨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多么丑陋的印记/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教训那些留在/室内的人们吧,我要在自己身上唤醒/另一种饥饿,划向日益明亮的天际。”[5]西渡:《西渡诗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34页。西渡关注的是“日常奇迹”,一场生活中的雨带给诗人的是一种精神的新生,沐浴了诗人整个的内心世界,“湿重新把/我们生下”。这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观照日常生活经验的方式——“自上而下”的方式。“诗人主要还是从自我诗性思维的类型和先在的诗歌趣味出发,不忽视日常生活中具有意味和‘寓言性的’部分,选择性地体验和关注日常生活中和前者相适应的部分。”[6]程波:《先锋及其语境: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这样的现实被诗人称之为“日常奇迹”,自动自觉远离着、屏蔽着世俗的柴米油盐和一地鸡毛。
显然,西渡叙述形态的意义诉求和价值目标不在现实的日常性,西渡叙述更重要的意义是:用叙述带入节奏,试图借助略带叙事性的格局,把文本的疏密度和时间速度转换成一种诗歌的节奏。叙述是通过词语的连续性关系显示出存在的时间维度,时间维度又转化为一种诗的节奏。
与古典诗不同,现代自由诗的节奏,“与其说是音乐性的,不如说是语义性的。自由诗节奏捕捉的是意义的运动。意义聚集在节奏上,就像鳗鱼的自由一样有力,就像秋之行进”[7]赵毅衡:《断无不可解之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70页。。西渡的诗歌,要么借助叙述事件的动态发展,要么借助叙述行为的动态发展,形成一种诗的节奏,前有《一个钟表匠的记忆》《屠龙术》等,后有《在黑暗中》《俄耳甫斯》《大海不断升高》等。在《屠龙术》中,“他”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我们”和“他”的故事可能是同一个故事,也可能不是同一个故事。两个故事的分分合合,时而并列时而交叉,蜿蜒而过留下的辙印正是诗歌的节奏。故事的同中异、异中同引发搅动着诗人的思辨——无用的本领、秘密的技艺,因为无用武之地,我们为之悲伤。但最后诗思攀升高峰——“浪费也许就是俭省,但故事/也可能不是同一个故事。我们发明的/重新发明我。我们曾为此私下忏悔/却常常有一种傲慢的脱离大地的感觉”[1]西渡:《西渡诗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48页。。这些看似矛盾悖反的生命感悟使该诗的节奏如同一首乐曲,前面有着充分的回旋,沉郁舒缓,婉转曲折,但到最后,一段尖锐而绚丽的诗思拔地而起,把整首诗篇带向高潮,并在此戛然而止,诗情、诗思、诗感结束在最强音上。
二、蕴蓄于叙述中的历史思辨
西渡的叙述或速或缓地弹出大大小小的字符,建立起诗歌的节奏;沿着节奏婆娑起舞的,是思辨。一条思辨的河流在叙述内流淌,给叙述注入价值观和命运感。这一切根源于叙述声音的内在性——心灵内在的深刻思索和细致思辨。叙述,在诗歌文本中成为思辨力跳跃的浮桥。如果说叙述是文本展面的话,那思辨就是诗的“刺点”,也即“诗眼”。无论古典诗还是现代诗,都必须有“诗眼”,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古典诗的“诗眼”可以从文本中摘引出来,剥离出来仍然是一个生机充沛的“有机活体”;而现代诗的“诗眼”,它的活力只存在于文本中。其原因在于,古典诗的语法结构灵活自由,而现代诗的语言逻辑缜密严实。现代语言结构的逻辑性和整体性使诗歌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读者面前,词或句子只能在诗的整体结构中去呈现诗意,一旦离开整体,就失去了在诗歌中的意义。西渡诗的“刺点”正是生长于展面之中、之上,无展面,就无“刺点”,唯有在展面上的聚合脉冲才能形成“刺点”。其叙述展面营造的是诗的宽度和广度,思辨性“刺点”提升的是诗的深度和高度。唯有二者相互支撑,诗的张力空间才能营构。此空间,也是诗人尽情“游于艺”的地方。
西渡最有力的思辨是历史性思辨——体现在历史观的深度和广度、道德意识形态的想象力和政治哲学的领悟力以及心理的敏感程度上。这种历史性思辨时而在历史语境中生发出来,时而植入现实语境之中。历史语境又有两类,并且二者之间大为殊异。一类如《一个钟表匠的记忆》《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刻》《公共时代的菜园》等。个人历史是其叙写中的一个强烈的时间背景,一种确切的个体记忆和生活经验。一类是以古人古事为抒写对象的《中国人物》《中国情史》《返魂香》等组诗,写陶渊明、谢灵运、杜甫、李商隐、苏轼、郑和、杜十娘、苏小小等,西渡现代性的宽广视域和精微深邃的目光、同情的敏锐直觉给历史人物、事件注入了活的灵魂。但在我看来,体现叙事和思辨结合之巧妙、思辨之精微悠远的,是前者。前文述及的《一个钟表匠的记忆》,其历史性首先系在一条“从前到现在”的连续性历史时间之链上。“过去的历史”变为被当前叙述行为分别唤起的一个个瞬间,在回忆中把时光在几何层面上推演,并且叙事人以自身的叙述来自由穿梭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哪里是红色的童年,哪里又是/苍白的归宿?下午五点钟,在幼稚园/孩子们急速地奔向他们的父母,带着/童贞的快乐和全部的向往:从起点到终点。”
立足于当下,同时又瞻前顾后,由此一来,时间与时间的缠结扩张出一种个体命运的历史张力。历史,在时间中才具有历史性。诗人,在时间中思索时间,思索关于或快或慢的时间速度。《一个钟表匠的记忆》中的“她”,作为时代的先锋,时间在其人生中一直处于“加速度”的状态。“她”在从“梳羊角辫的童年”时,就被“红色激素”所过早催发,后来“经济激素”又成为“她”自我陶醉的催情剂。“她”一路被时间催逼,最后不可避免地呈加速度向黑暗的死亡深渊里坠落。时间既可以在推迟中延伸因而膨胀,也可以在加速中缩短。加速度的人生其实是把人生意义极大简化了的。简化就是泛化、虚无化。其实,在这首诗里,简化人生意义的不只是加速度(追求快),还有崇尚“宏大”的虚幻性。把自己献祭于某种意识形态(政治神话和经济神话)的庞然大物,那种献祭的热情会把人的主体性掏空。与其说“她”所献身的革命是以主体的建立为目的,倒不如说它恰好背道而驰,实际效果反把主体性消融净尽。无论是加速度人生,还是宏大的意识形态化人生,对人性都是一种删繁就简。去除了血肉、感性、细节,人性就成了一种概念式的简化和推演式的概括,一种抽象的符号。而这些,笔者认为是诗人对现代性的一种批评。现代性在追逐“新”和“大”的路上疯狂驱驰,使人越来越失去脚下的土地,产生一种华而不实的悬浮感和漂移心理。
所以诗人倡导“诗歌是一种慢”,在这个主题上,诗人不止一次地思辨过。在《晨跑者之歌》中,在时代快速发展的列车上,“我”作为一名乘客,在向前跑的惯性中又如何保持住自己的“慢”?这实在是一个悖论,诗人的解决办法是:“而我不像你/我干脆在火车上侧身躺下去,拒绝和邻座/玩撞大运的游戏。但你的脚怎么伸进了我的梦里?!/在梦里,我似乎也不由自主地像一匹木马/机械地奔跑起来。那是你在我的身体里奔跑!/噢,但愿我一觉醒来,火车已经停靠/一个上世纪的火车站,站台上上世纪的人物/人来人往:四周围着一圈穿白大褂的医生/正研究我的嗜睡症:而你仍没有停止奔跑。”
即使是抒写现实的存在,西渡诗歌的背后也有一种被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充满着历史性张力。比如《饥饿艺术家》《为蟑螂而写的一首诗》《实验课》等,诗人富有历史感地将历史性的当下作为透视人生复杂体验的瞬间。这是因为诗人的思维方式有一种宏大的历史感和宇宙哲学做基础。寄寓着天地变化和历史盛衰的宇宙哲学和历史哲学,来自于西渡深厚的古典学养,发散出去,自然也洇染着古典性的神韵。《鸥鹭》的最后几句“潮起潮落,公子的白发长了,/美人的镜子瘦了。//一队队白袍的僧侣朝向日出。/一群群黑色的鲸鱼涌向日落”,在天地浩瀚、历史更迭不可胜极之方面,直追唐诗《春江花月夜》和“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抚千年于一瞬、挥万载于弹指的神韵!
因为具有包举大端的宇宙哲学和历史哲学,西渡的眼睛能领悟包蕴在永恒的现实中的过去和将来的一切,他更多的是用历史的长度、高远的视野,用历史中的感受者,用感受者的心灵去体验这个时代。《为蟑螂而写的一首诗》在寓言的意义上具体地呈现出完整的时代真实图景,但其中又无不震颤着历史的经验想象方式。“蟑螂”,一个被人类权力结构命名为“卑贱者”的异类。这里所谓的权力,不独存在于政治领域,只要充满着差异关系的领域,权力必定存在,并且“在社会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在边缘,在角落,在晦暗或者明亮的地带,权力在调动、出没、施展、发挥其特长和技术,实践其诡计和意图”[1]汪民安:《现代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生为另类,在权力社会其生存法则是在鞋底和蝇拍下苟且的。社会总体性的施暴结构已深深植入了人的无意识深处。当这种活命的生存法则成为一种艺术,它同时也在“我”的身上获得永恒。“我”即便是“越江而北,抵达红色的首都”,依然会去寻找属于“我”的角落和缝隙,羞怯而安分奔流在“我”的血液里,侧身隐入缝隙是“我”的宿命。但作者在历史的战栗中也怀揣着历史的救赎愿望:希望“在患躁狂症的年代隆隆过去后/我们将留下来,守住大地的居所”。
针对现代社会无限泛滥的物欲和肉欲,《饥饿艺术家》倡导一种精神的高远、清洁。为了得到,必须失去;为了丰盈,必须饥饿。市场经济把个人的欲望当作合理的原初动力,“以普遍的个体占有为形式的贪欲正在变成时代的秩序、统治的意识形态和主导的社会实践……在这个社会制度里,积累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新的积累,让人感到欲望的无限性”[2]〔英〕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页。。但事物往往是物极必反。享用的过满过足、物质的过度刺激、感情的过剩会导致一种人性的嫌恶症,像一个饕餮者面对满桌的珍馐美味却打起了饱嗝,也即诗中所说的:“而饕餮者很快发现/再没有什么可吃的/更严重的危险在于/他们从未拥有适当的品味。”而饥饿的艺术家“除了担心想象力/他用不着担心别的”。诗人再一次以诗歌的形式重新阐释了里尔克的那句“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警句。艺术与现实的永不消除的矛盾,正是艺术得以存在的根本理由。
无论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西渡诗歌都具有强烈而执着的历史关怀和人文视角。在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变化带来了以非价值化和意义丧失为标志的时代环境中,当诗歌自身的社会与文化功能日益衰落时,出于知识分子良知和角色的自我确证以及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承诺,西渡的诗表现出了历史的真实和生命的逻辑,始终保持着诗的良知,在一种真正的独立性中表达对于历史经验、现实价值的深切注意和关怀。
三、叙述与思辨:一种矛盾性张力
至此,可以说对于“以什么样的方式建立语言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这个问题,西渡做出了他自己的回答——一条缓缓的叙述河流承载着生存之重的巨轮。这是一种举重若轻的艺术法则。艺术的诀窍不是避重就轻,而是举重若轻。轻重之辨在西渡那里就是简约透明的言说方式与错杂繁多的言说内容、语言的舒缓与内涵的尖锐之间的矛盾张力。如果说“社会学的内容必须对位恰当的诗学形式,而这一诗学形式,又和社会学的内容必须保持某种内在的一致性”[1]杨庆祥:《一份社会学与诗学的双重文本》,《作家》2019年第6期。,这诚然不错,但我认为这是一种传统的诗歌美学观念。不和谐的张力才是整个现代艺术的审美原则之一。诗歌更是如此。它总是尽力避免单一性的内涵传达,更乐意成为一种表意与多层理解含义富丽的复合体,包含了一种永远不能综合的内在歧异。具体表现为神秘玄隐的引语与敏锐灵慧的智识、简约透明的言说方式与错杂繁复的言说内容、语言的浑融圆满与内涵的空缺悬疑、极为微小的主题范围与最为激烈的风格转换、稳固的主题与一种不安定的风格铺展、语言表达内涵的确定性与外延的不确定性[2]〔德〕胡戈·弗里德里希:《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之间的矛盾张力。只有在种种矛盾性的张力中,诗歌的修辞、形式和主题、内容才能双峰并峙,实现欧阳江河所说的“词与物的异质性”。它针对两种时弊:一是语言修辞、形式表达归顺服务于主题、内容,终至湮灭无痕,也即传统诗话中的得意忘言,用现代批评术语来说就是“词”被“物”所替代;二是主题、内容被修辞、形式所虚无化,在没有社会功能的虚幻的修辞自主性中陶醉,达致马拉美意义上的“纯诗”的极端追求——“诗定然要脱离具体的现实,脱离诗人个性的表达,脱离任何感情的词采,变成一个说明虚无的符号”[3]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0页。,“词”成为脱离“物”独自飞翔神游于太虚幻境。
所以,在笔者看来,诗学和社会学、修辞想象和历史想象最好的构成结构应是张力所撑举起来的相爱相杀的双峰并峙,达致这一结构状态的路径是各不相同的,而西渡,也只是给出了最适合他自己的答案——把叙述不仅作为一种写作技巧,更作为一种结构形态。叙述形态传统温和、平缓舒展,其意义诉求和价值目标在于用叙述带入节奏,试图借助略带叙事性的格局把文本的疏密度和时间速度转换成一种诗歌的节奏。同时,思辨在叙述的节奏内奔突鼓荡,给叙述注入沉重尖锐的价值观和命运感。由此形成简约透明的言说方式与错杂繁多的言说内容、语言的舒缓与内涵的尖锐之间的矛盾张力,在矛盾性张力中实现“词与物的异质性”,带动文本内现实与文本外泛化现实的广博的相互指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