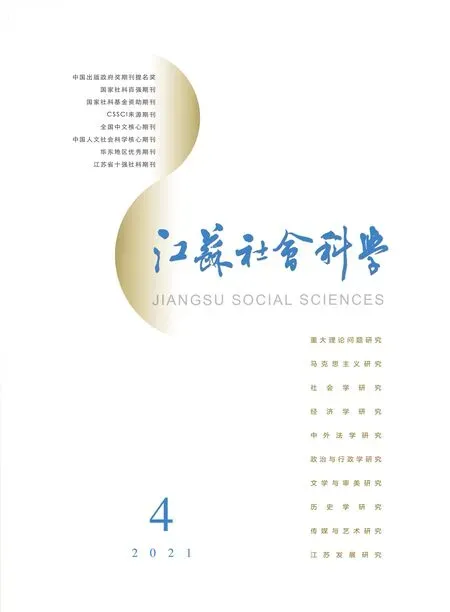中国早期电影中新女性形象的类型和成因
陈吉德 陈 悦
内容提要 新女性自立自强,特立独行,敢于对父权文化和男权主义说“不”。她们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早期电影中,新女性的形象大体分为情欲型、知识型、革命型三种。新女性的出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都市消费文化、政体体制的变化不无关系。中国早期电影对新女性形象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公式化、口号化的弊端,但毕竟改变了人们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丰富了电影的人物画廊,更主要的是给电影注入了现代化的气息,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早期电影中出现了大量的新女性形象。五四之后,“新女性”一词颇为时尚。1925 年冬,章锡琛在上海创办了名为《新女性》的刊物。1935 年2 月,蔡楚生导演的电影名为《新女性》。1935年5月,上海民立女子中学学生自治会编辑出版的刊物名为《新女性》。与“新女性”词义相近的还有“新妇女”“觉悟的女子”“现代女子”“女杰”“摩登女性”等等。但是到底何为“新女性”?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1918年9月,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做题为《美国的妇人》时使用的是“新妇女”一词,并指出其特点是“衣饰古怪,披着头发……言论非常激烈,行为往往趋于极端,不信宗教,不依礼法,却又思想极高,道德极高”[1]胡适:《美国的妇人》,《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3号。。1926年,辑人在《新女性》上撰文,用“三无四有”来概括新女性的特质,即“无贵族气,无虚荣心,无依赖性;有科学家的头脑,有艺术家的情绪,有体育家的体格,有军事家的勇敢”[2]辑人:《第一次征文当选我所认为新女子者》,《新女性》1926年第1卷第11期。。1927 年,乔治在《妇女杂志》上提出新女性的六个基本条件:一是精神解放;二是实事论事,有务实的态度;三是确定求学宗旨,学习实用的科学知识;四是牺牲精神,为解放其他妇女贡献自己的力量;五是无高傲态度,高傲态度不利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六是经济独立[1]乔治:《新女子应具备的条件》,《妇女杂志》1927年第13卷第2期。。到了1930年代以后,“新女性”一词更为流行。1932年,左企在《玲珑》杂志上提出新女性要“尊重你自己的人格,勿为虚荣心所惑,勿为利欲引诱……培养相当的职业技能,务必达到经济独立的目的”[2]左企:《怎样才是新女性》,《玲珑》1932年第2卷第58期。。
纵观人们对“新女性”一词的理解,虽然言人人殊,歧义丛生,但大体相同点还是有的。新女性大都勇敢地与家庭决裂,把“贤妻良母”视为陈腐的旧迹,把“三从四德”当作成长的羁绊。她们自立自强,特立独行,敢于对父权文化和男权主义说“不”。她们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新女性形象与千百年来的传统女性形象大异其趣。在20世纪的中国早期电影中,就存在着大量的新女性形象。这些新女性形象大体可分为情欲型、知识型和革命型三种类型。
一、情欲型女性:都市中的“雀之灵”或“恶之花”
情欲者,七情六欲也。情属于心理层面,欲属于生理层面,二者应该融为一体。情欲是每个人都无法抹去的本性。王夫之曾言:“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3]王夫之:《诗广传》,《船山全书》(第3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375页。。但在谈性色变的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情欲的言说大都遮遮掩掩、欲说还休。到了中国早期电影中,情欲型女性浮出地表,成为都市天地中一道特殊的风景,受人关注。情欲型女性天生丽质,将神性和魔性融于一身,有的是美丽的“雀之灵”,把人带向诗意的佳境;有的是可怕的“恶之花”,将人引向无底的深渊。她们浑身飘溢着荷尔蒙气息,与月份牌上的摩登女郎形成互文,共同承载着人们对新女性的无边幻想。
情欲型女性大都生活放荡、肉灵分离,注重肉体的快乐和物质的享受。《三个摩登女性》中的虞玉本是一位清纯的南国姑娘,后来到了香港,成为富婆。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她回到上海,经常找张榆寻欢作乐。《女儿经》中的高华非常虚伪。她表面上整日积极鼓吹“妇女运动”,其实是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现代一女性》中的地产公司女职员蒋葡萄为了填补心灵的空虚,疯狂地追求爱情刺激。她与已婚的新闻记者余冷有染,与公司史经理也不干净,最后以偷窃罪被捕入狱。
情欲型女性中,交际花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她们才貌双全,杨柳含烟,风情万种,锦衣玉食,经常置身于霓虹灯闪烁的舞池或者富丽堂皇的高档酒店,尽情渲染着都市的绚烂与奢华,如《渔光曲》中的薛绮云、《女儿经》中的徐莉、《粉红色的梦》中的李蕙兰、《少奶奶的扇子》中的黎女士、《乱世风光》中的柳如眉、《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王丽珍。关于交际花的特点,有人总结道:“她多少有一点自行处理其友谊与爱情的经验,有着相当的美丽妩媚,当她们越懂得多时就越变得富有诱惑性。她们当然聪明、伶俐、机智的。总之,她们在天赋上似乎和一般的平凡的女孩子颇有一点不同。你可以说那是好的;但也未尝不可以说那是坏的。”[4]蒋嘉:《交际花型的女孩子》,《中美周报》1948年第314期。但是在大部分人的意识里,交际花是一种负面的存在,成为伤风败俗的代名词。当时《玲珑》杂志发表的关于交际花的文章多持谴责的态度,仅从文章标题即可看出,如《交际花受骗失身》[5]《玲珑》1933年第3卷第9期。、《交际花略诱男子》[6]《玲珑》1935年第3卷第10期。、《交际花做不得》[7]《玲珑》1936年第6卷第33期。等等。《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交际花王丽珍年轻美丽,时装、汽车、豪华公寓、夜生活成为她的标配。她就像歌德《浮士德》中的魔鬼摩菲斯特,一步一步地将爱国热血青年张忠良引向无底的深渊,成为民族的败类。当时有人是这样评价她的:“王丽珍是一位泼辣精明的交际花。她惯于应用一切所谓‘女人的便利’而获得一些利润。她凭娇媚妖娆的迷人态度,而让那长袖善舞的大兴贸易公司董事长庞浩公做干爹,再迷惑颠倒了这位落难薄弱的张忠良作她的俘虏。这种在上海这地方也实在是不乏人的……她对张忠良没有一分爱情,她底占有他仅为了满足她自己。她会用一切最毒辣的手段来表现她自私的本性。”[1]容戈:《〈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几个女性》,《妇女》1947年第2卷第8期。《粉红色的梦》中的交际花李蕙兰被指责为“中国都市里有闲阶级的尚未发展而早崩溃了的道德的女性”[2]鲁思:《何时梦醒?》,《晨报》1932年9月6日。的代表。总之,她们都代表着都市中的邪恶、诱惑、堕落等负面因素。
情欲型女性中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类型,这就是妓女。妓女与交际花并非是一个概念,因为有的交际花并不卖身,有的妓女并没有机会出入高档社交场合。毫无疑问,妓女的主要生存策略是以自己的身体做资本,以情欲做依托,与男性进行交易而获得钱物。她们主动或被动放逐传统的伦理道德,身处边缘,大都属于葛兰西所谓的“属下阶层”(subaltern),如《上海一妇人》中的爱宝、《火山情血》中的柳花、《天明》中的菱菱、《神女》中的贫困母亲、《船家女》中的阿玲、《马路天使》中的小云、《人海遗珠》中的珠儿、《前程万里》中的小凤、《夜店》中的林黛玉、《丽人行》中的金妹等等。
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看来,妓女无论在什么时候就是一个“迷恋物”。是的,在这个“迷恋物”的诱惑下,古今中外的无数文人墨客献出了名篇佳作,他们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展现妓女的身体及其承载着的情欲。到了电影艺术当中,在形象化的视听语言的作用下,妓女的身体及其情欲就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真真切切,时时散发着荷尔蒙气息。
妓女既然是一个“迷恋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被凝视的功能。《火山情血》中黎莉莉饰演的柳花性感十足。在柳林酒店里,柳花吸烟、画眉、涂粉,衣着非常时髦:羽毛装饰的白色短袖大衣,脖子上挂着项链,里面是黑色背心和白色的草裙。她的习惯性动作是大腿翘在高处,颇具诱惑力。更具诱惑力的是她脱去大衣,露出雪白的肌肤,在众多男人的注视下站在桌子上,脱掉高跟鞋,光脚跳性感的夏威夷草裙舞。影片不时呈现出她微笑的面部和扭动的大腿的特写,以及男人们色眯眯的反应镜头。然后,一个粗壮的男人将柳花从桌子上扛了下来,男人们立刻围了过去,近距离地欣赏她迷人的身体。看与被看,劳拉·穆尔维所谓的“视觉快感”在此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妓女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她们通过出卖肉体与社会秩序发生关联,这其中必然或隐或显地呈现出性别色彩。《神女》是左翼电影中影响深远的一部作品。主人公神女过着一种极为分裂的生活,这正如影片字幕所言:“在夜之街头,她是一个低贱的神女,当她怀抱起她的孩子,她是一位圣洁的母亲。”当她安放好孩子,走向夜色中的街头时,影片极力展现她情欲化身体的魔力:身材高挑,黑白相间的旗袍,皮肤白皙,胸部隆起,搔首弄姿,不时地抽烟并吐出烟雾。富有象征意味的是,神女的画面深处是一个巨大的“当”字。如果说人们通常“当”出的是物品,那么神女“当”出的则是身体。手段不同,目的相同,都是获取金钱。接着,以一名壮汉为首的几个男人经过神女的眼前。巧合的是,神女后来被警察追赶时,躲进的恰恰是该壮汉的房间,从此该壮汉就成了神女身体的霸占者和无偿消费者。当影片结束时,神女绝望地杀死该壮汉,被投进了监狱。这旨在表明,女性情欲化的身体只是男性的消费品,他们对男性反抗的结果必然是自身的毁灭。
美籍华裔学者李欧梵认为,上海1930年代时尚女性的身体展示“已成了和日常现代性相关的一种新的公众话语”。借助于报刊、杂志、月份牌、广告、电影等多种传媒手段,女性身体逐渐变成上海城市形象消费的一种重要体现[3]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显然,妓女的身体就是一种时尚的身体。她们的身体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出售,都是在展现女性身体的商品化属性。当身体具有可赢利的交换价值时,就必然呈现出现代性。《船家女》中有两个场景很有意思:一是阿玲为了医治被恶棍打伤的父亲,被迫给一个阔少做绘画模特:画面是阔少把钱给帮忙的恶棍唐大胖子。下一个画面是阔少给阿玲抹口红,然后阿玲听从阔少的指使,摆出各种造型。身体的交换价值在此被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二是阿玲被迫卖入妓院后,虽然着装华丽性感,但愁容满面。当铁哥找到她时,她哭倒在铁哥的怀里说:“我已经不中用了。”铁哥安慰她说:“玲妹,这不是你的错。”所谓的“不中用”,意指自己失去贞洁,不配做他的妻子。阿玲的悲剧无疑是缘于自己身体所潜伏的交换价值。
情欲型女性经常与汽车、豪华公寓、酒店、咖啡馆、夜总会、舞厅、霓虹灯、时装、秀发、高跟鞋、口红、香烟等叙事元素交织在一起。她们或者是都市中的“雀之灵”,或者是都市中的“恶之花”,共同营造出都市生活集既时尚前卫又藏污纳垢,既催人奋进又诱人堕落的复杂面貌。
二、知识型女性:命运的主宰与抗争
在中国早期电影中,有一部分女性接受了知识的熏陶。按理说,知识能够改变命运,但这些知识型女性并没有因为知识而走向辉煌的人生,相反,她们大都命运多舛,以悲剧收场。
《桃李劫》的主人公黎丽琳与陶建平是青梅竹马,都是新式建工学校的毕业生,在当时算是地道的精英阶层。在校园里,她和陶建平拿到毕业文凭时是快乐的。他们在湖边携手奔跑,在垂柳下依依相偎,情意绵绵,幸福无边。她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秘书工作,但却经常受到公司经理的骚扰,无奈辞职。分娩后无人照料,处境艰难,雪上加霜的是自己提水上楼时又摔成重伤,最后因无钱治疗而魂归西天。通过黎丽琳的悲剧,“该片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黑暗,揭露了普通民众的生存困境”[1]毛亚蓉:《电影〈桃李劫〉说明书》,《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12年刊。。在20世纪的20—30年代,像黎丽琳这样的知识分子理应能够过上比较幸福的生活,但冷酷的现实生活无情地撕破了她的梦想,并吞噬了她的生命。
与黎丽琳有着同样悲剧命运的还有《新女性》中的韦明。她接受过高等教育,是个地道的知识型“新女性”。她相信婚姻自由,也找到了自己所爱的人,并生有一女,但不久即被抛弃。她只身到了上海,靠自己的知识在私立乐育女子中学谋得了音乐教师的职位,并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影片开场时,她身着时髦的旗袍,从市民报馆领稿费坐公交车归来,这说明她的文学创作小有成就。但此时她已经不相信爱情和婚姻,认为所谓“终身的伴侣”不过是“终身的奴隶”。所以,她尽管爱上了出版公司的编辑余海涛,但仍然不愿走进婚姻的殿堂。影片中几次出现名为“不倒的女性”的玩具形象,这个玩具旨在表明:韦明希望自己坚强勇敢,永远不倒。可影片结尾她还是“倒下”了,其因有三:一是亲情的打击。女儿患了肺炎,日益加重,亟需治疗而她又身无分文。二是工作的打击。校董王博士对她垂涎三尺,欲得而不能后,将其辞退。尔后,韦明为了给女儿治病,不得已做了“一夜的奴隶”,孰料嫖客竟然是王博士。她发出了愤怒的呐喊:“你们这班狗,设下了种种的方法,叫我们女子不能不在各方面出卖给你们……你们这天罗地网,你当永远是天经地义吗?”三是大众传媒的恶语中伤。韦明卧床后,本有治愈的希望,她创作的小说《恋爱的坟墓》也出版发行,但小报却捕风捉影,接连刊出她“生前秘史大暴露”“女性终为弱者”等小道消息。她看到这种不实报道后彻底失去了活着的勇气,对朋友这样说道:“姐姐,我实在不能再活下去了,这社会我们又没有力量去改造它……”韦明是一位出走后的现代版“娜拉”。她会写作,爱音乐,懂教学,被人爱慕和追求。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五四时期倡扬的‘独立’‘自由’‘平等’的新女性精神,是五四时期‘自由女性观’的代表者。而韦明经过奋斗最终自认失败,是时代发展的必然”[2]刘海玲:《从〈新女性〉看中国现代“新女性观”的演变》,《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这也是鲁迅《伤逝》小说所探讨的主题:如果整个社会不解放,单靠女性自身去反抗,大都是无效的。
知识型女性因为受到知识的启蒙,个体意识开始觉醒,觉醒后的最大目标就是抵制封建思想,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冲破家庭的束缚。《自由神》中的陈行素就是这样一位“我行我素”的“自由神”。影片的叙境是1920年代,彼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荡神州大地,“自由”“民主”“科学”的口号洗涤着人们的陈旧观念。作为女中学校的学生,陈行素时刻思考着自己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她努力进取,成为学生会的代表,积极领导学生运动。她不但视家庭为牢笼,鄙视封建闺阁小姐的身份,而且强烈反对学校的陈规陋习。有三件事非常能够说明她的性格特征。一是与同学林之彬相爱。陈行素与林之彬情投意合,感情真挚,但却遭到父母的阻挠,她是这样表达自己立场的:“为了争取我全身的自由,我是不怕这种吃人的礼教的。什么父母之命啊,我现在是个有主张的啦。”后来,她大胆地与林之彬私奔到上海。二是出演《终身大事》的女主角田亚梅。胡适的《终身大事》明显受到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表现的是女子与家庭决裂的主题。在影片中,没有人敢演田亚梅。陈行素却独异于众,登上舞台。她最欣赏田亚梅的一句台词是:“不!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和别人没有关系。我是一个人,一个堂堂的人!”显然,与其说陈行素是在演田亚梅,不如说是在演自己。“一个堂堂的人!”这句台词在影片中出现多达8次。这显然是创作者对陈行素个性的有意指认和强化。三是与青年军官周范决裂。陈行素参加北伐战争,与周范邂逅,产生爱情的火花。但当她到上海后,发觉周范早有家室,遂与之绝交。这也是陈行素作为“一个堂堂的人”不愿苟且活着的表现。所以当时有人这样评价她:“在多样的‘中国娜拉’里面,《自由神》中的陈行素(王莹饰)也许是最坚韧的一个,为着要做‘一个堂堂的人’,她注定了走着荆棘的道路,可是她始终带着胜利的笑的,‘五四’时代不肯乖乖地‘从’父,五卅之后不肯安逸地‘从’夫,现在,上海‘一·二八’战争又幻灭了她下意识的‘从’子的梦了。”[1]方岩:《〈自由神〉二题》,冯沛龄编:《电通半月画报——老上海电影期刊经典1935年5月—1935年11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不可否认,在中国早期电影中,也有部分创作者对知识型女性持排斥态度。在他们的眼中,女子永远要为家庭而活,做家庭的奉献者。《摩登女性》中的云珍是一名大学生,虽然成家,但又不愿为家庭所束缚。她对丈夫志华说:“志华,我希望你不要把我看得跟别的女人一样,结了婚就拿贤妻良母的大帽子来压着我,让我情情愿愿地在家里给你做一辈子奴隶。我告诉你,我一向认为,一个女子情情愿愿地在家里做管家婆,那是最没有出息的女人干的事情。”由此导致了家庭的破裂。后来,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又和志华破镜重圆。为此,影片还设置了玉英这个人物作对比。玉英也是大学生,她却知书达理,做事周全,既有事业又有家庭。她经常开导云珍,希望她跟自己一样做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不难看出,影片埋伏着可怕的男权中心主义色彩。创作者在骨子里认为,女子即便有知识,依然应该是男人的傀儡和家庭的附庸。
三、革命型女性:走向赤色的广阔天地
在中国早期电影中有一种新女性,她们勇敢地冲破狭小的个人空间,走向广阔的社会公共空间,在赤色的天地中找到自身的价值定位,在各种形式的革命献祭中完成神圣的精神救赎。这种革命型女性抹去了女性形象常见的阴柔与婉约品质,显得激进、粗犷甚至悲壮。
革命型女性在外形上大都呈现出这样一种特征:着装朴素,少饰物,拒绝长发,动作干脆利落。《三个摩登女性》中阮玲玉饰演的周淑贞出场时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乌黑长辫,脸庞秀丽;到了上海谋生,考取接线员之后,形象大变。田汉的剧本是这样描写她的:“淑贞穿一件干净、朴素的蓝布旗袍,脸上不施脂粉,在绮罗锦绣的来客中,她自然显得与众不同了。”[1]田汉:《三个摩登女性》,《田汉全集》(第10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所谓的“与众不同”,主要是与虞玉等人所形成的对比。《新女性》中的李阿英总是梳着齐耳短发,身穿短袖粗布上衣、宽松的长裤和常见的平底鞋,走起路来像一阵风,说话快言快语,眼睛炯炯有神,看上去十分精明能干。《遥远的爱》中的余珍更有意思。她做佣人时留着长长的辫子,身着旗袍,后来参加了革命,就变成了短发,而且穿起了军装,动作敏捷。上述电影通过服装、发型等外形的塑造,淡化或遮蔽女性的性别特征,这种性别符码显然被纳入到宏大的革命话语体系之中。
毫无疑问,革命型女性的最本质特征主要不在于外形,而在于内在的思想。她们不是反对爱情,只是反对卿卿我我、风花雪月般的爱情;她们不是鄙视所有的家庭,只是鄙视变质为牢笼和枷锁似的家庭。质言之,是因为她们不同程度地具备了革命的思想,能够站在更广阔的赤色天地中要求自己、审视自己。《三个摩登女性》中的周淑贞当听到别人说国难是小事时,义正严辞地反驳道:“请问,我们大片的东北土地沦丧于铁蹄之下,关外三千万同胞,整天过着亡国奴的日子,这是小事吗?可以不管吗?我们的兄弟姐妹,在被敌人任意屠杀,许多人死在敌人的刺刀之下,这是小事吗?也可以不管吗?”张榆听后感慨万分地说:“淑贞,今天我才知道,只有真正自食其力,最理智、最勇敢、最关心大众利益的,才是当代最摩登的女性!”周淑贞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高度,才会参加护士队救护战士,才会参加电话局的工人大罢工。影片最后打出这样的字幕:“苦难将给我们创造民族的女战士、时代的新丽人。”是的,周淑贞就是这样一位“民族的女战士、时代的新丽人”。《新女性》中的李阿英是一位具有阶级意识和民族解放意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女性。她努力与工人阶级并肩作战,将个人的“小我”锻炼成革命洪流中的“大我”。她把流行的黄色小调改编成了反映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歌曲《黄浦江》,并且灵活运用于日常教学。《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江玲玉是上海某大学剧社的著名演员,具有满腔的革命热血。当音乐家高礼彬在街头演讲、疾呼抗日救国时,她怦然心动,冲破重重阻力,在《义勇军进行曲》雄壮激昂的旋律中,毅然推开家门,参加了抗日演剧队。在苏州,她和高礼彬倾情演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形式活泼,让观众感动不已。在南京,她所在的演剧队被日军包围,虽然接到指令要求立即撤退,但她还是坚持演出结束后再撤。演出时高唱的《大刀进行曲》令全场热血沸腾,士气大振。在长沙,虽然生活异常艰难,但她还是和队员患难与共,保持着高昂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继续演出,揭露买办资产阶级卖国求荣、唯利是图的丑恶嘴脸。最后回到上海,她和高礼彬虽然身处低矮昏暗的小阁楼,但依然对生活充满着坚定的信念,喜欢在柔美的小提琴曲中感受生活的诗意。但是尽管她这样正义善良,最后还是昏倒在街头,生命垂危。这不得不让我们对当时的社会有所反思,所以影片最后出现这样的字幕:“这位文化战士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前途是死是活,请诸位贤明的观众自己去想。假如她的前途是死的,那么请反省一下——我们是否有责任?”
当然,革命型女性的成长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总要经历各种磨砺和考验。《遥远的爱》中的余珍就从传统的女性最终成长为殉道者似的革命战士。她出身卑微,只读过两年书,为躲避财主的纳妾之祸,从东北逃到上海。受到流氓车夫侮辱后,她坚决反抗。在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萧元熙家做佣人是余珍成长道路上的重要阶段。她与萧元熙的关系渐次由被雇佣与雇佣的关系慢慢演变成被改造者与改造者或者说被启蒙与启蒙者的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雕琢”,余珍果然摆脱了封建思想和旧习惯的束缚,从内在的思想境界到外在的言谈举止都达到了“摩登小姐”“现代的女性”“理想的新人”(萧元熙语)的水准。萧元熙对自己的“杰作”非常满意,于是与她结为夫妻。其实,这与其说是结为夫妻,不如说是给余珍戴上“父权”的枷锁,放进“家庭”的牢笼,所以,萧元熙的启蒙不可能是彻底的。于是影片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萧元熙之外设置了工农出身的革命知识分子李连群这一正面形象。与萧元熙启蒙立足点截然不同的是,李连群特别强调民族解放和国家安危。这种革命话语对余珍特别有吸引力,于是她越来越鄙视萧元熙精神导师的身份,继而矛盾不断,离家出走,投身到抗日运动的洪流,最终成为身着戎装的革命战士。这时余珍与萧元熙的关系悄然逆转:由被启蒙者与启蒙者的关系变成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关系。余珍以至高无上的民族自由解放立场对生活困顿、精神颓废的萧元熙告诫道:“你的爱是自私的,不关心别人的生活,所以你会感觉到寂寞孤独。”片名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副标题,叫《一个时代的悲喜剧》:“悲”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萧元熙黯然离场,“喜”的是余珍终于成长为成熟的革命女性;无论“悲”“喜”,都与那个“时代”密切相关。
中国早期电影在构建革命型女性形象时,通常将私人的婚姻家庭空间与社会公共空间相结合,将个体的恩怨与时代的血与火相结合,最终的趋向是对民族解放和国家情怀的强有力认同。所以,革命型女性大都不是卿卿我我的“小我”,而是风风火火的“大我”。她们虽然在性别特征上有时被弱化,但都喜欢在赤色的广阔天地中跳起铿锵的舞蹈,呈现出女性的阳刚之美。
四、出现原因:一个复杂的社会命题
以上,我们论述了情欲型、知识型、革命型三种新女性形象,当然,这三种形象也不可能穷尽新女性的所有类型,而且这三者之间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而论之,只是出于行文的方便。但凡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原因。新女性的出现也有其复杂的社会因素。
中国早期电影中新女性形象的出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竭力弘扬自由、平等的先进思想。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其本质就是“人的发现”,就是鲁迅所说的“立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人的发现”对于女性来说就是女性解放,就是对几千年来有碍女性身心健康发展的封建纲常礼教的否定和批判。陈独秀可谓是为女性解放而呐喊的勇士。他在《新青年》1915年第1卷第1期刊登了自己翻译的《妇人观》一文。译文明确肯定女性追求爱情的权利,指出,“不见爱于所爱之人,大不幸也。然爱汝者为汝不爱之人,其不幸尤甚”。随后又在1915年第1卷第3期上发表《欧洲七女侠》一文,号召女性向居里夫人、罗兰夫人、贞德等七人学习。之后,《新青年》又陆续刊登了《女性与科学》《青年与性欲》《妇子问题》《女子问题》《结婚与恋爱》《结婚论》《社会妇女解放问题》等文章,讨论女性解放的有关话题。在中国早期电影中,我们不难发现“女性解放”的影子。电影《新女性》的主题歌是这样写的:“新的女性,是生产的女性大众;新的女性,是社会的劳工;新的女性,是建设新社会的先锋;新的女性,要和男子们一齐翻卷起时代的暴风!暴风!我们要将它唤醒民族的迷梦!我们要将它造成女性的光荣!不做奴隶,天下为公!无分男女,世界大同!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击;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2]孙师毅:《新女性》,《五四以来中国电影剧本选集》(上册),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第278—279页。歌词中明显包含着五四先驱者所倡导的劳工神圣、男女平等等观念。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新青年》1918年第4卷第6期的“易卜生专号”。专号刊登了易卜生的《娜拉》《国民之敌》《小爱友人》等作品。开篇是胡适所写的《易卜生主义》,文章指出了易卜生剧作所写家庭的四大恶德:自私自利、奴隶性、装腔作势、怯弱胆小,分析了三种大的社会势力:法律、宗教、道德,从而理清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易卜生专号”的影响下,女性独立自强的观点日渐深入人心,娜拉所说的“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成为20世纪中国女性的人生格言,娜拉与家庭决裂的“出走”行为成为女性寻求自身解放的理想范式,由此也深刻影响着戏剧、小说、电影等文艺作品的叙事态势。《现代一女性》《自由神》《八千里路云和月》《遥远的爱》《丽人行》《关不住的春光》《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等中国早期电影都隐含着娜拉“出走”模式。
与易卜生主义同样有影响的还有爱伦凯的“新性道德论”。爱伦凯是瑞典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教育家。她的思想经《妇女杂志》《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周刊》《良友画报》《晦鸣周刊》《出版周刊》《玲珑》等早期报刊介绍到中国后,影响广泛。爱伦凯的“新性道德论”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恋爱自由。恋爱自由的核心是灵肉合一,只有灵肉合一,才会产生蓬勃的生命力。爱伦凯称之为“大恋爱”:“大恋爱给一对人的东西,就是只有完全的发达所能给人类全体的东西,即官觉与精神的合一,欲望和义务的合一,自保和自爱的合一,个人和民族的合一,现在和将来的合一。”[1]〔瑞典〕爱伦凯:《恋爱与结婚》,朱舜琴译,光明书局1933年版,第78页。二是结婚自由。双方只要灵肉合一,有结合的欲望,不一定要履行合法的程序。这就是爱伦凯所主张的“有爱没有结婚比结婚没有爱好”[2]〔瑞典〕爱伦凯:《妇女运动》,林苑文译,光明书局1936年版,第4页。。三是离婚自由。爱伦凯认为,只要夫妻一方有意离婚,即可满足离婚的条件,这不仅减轻了对女性的奴役和压迫,还减少了卖淫、嫖娼等社会负面问题的产生。在中国早期电影中,不难发现爱伦凯理论的影子。《野草闲花》中富家少爷与街头卖花女冲破重重阻力终于走到一起;《现代一女性》中的蒋葡萄最后挣脱恋爱的束缚,昂首走向新生之路;《天明》中的渔村姑娘菱菱真心爱着表哥,虽死无怨;《太太万岁》中的陈思珍自感不妙时,果断提出与唐志远离婚。
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讨论的妇女问题的本质,有人这么说,“其实就是妇女的人格独立、人身自由、人权平等的问题,就是‘人的发现’推广应用于妇女身上,发现了‘妇女也是人’,妇女发现了‘我也是人’,由此而生的种种问题。”[3]舒芜:《女性的发现——知堂妇女论类抄》,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这种讨论对中国早期电影中新女性形象构建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都市消费文化也是中国早期电影中新女性出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早期电影的重镇在上海,作为国际大都会的上海一直有“东方巴黎”的称誉。在这个沿海开放城市,趋新崇洋成为时尚。自开埠以来,异域的各种娱乐方式不断涌入。电影院、咖啡厅、洋行、音乐厅、歌舞厅、游乐场、跑马场、赛狗场、百货商场、高尔夫球场、游泳馆等休闲场所的出现,共同营造出颇具诱惑力的消费文化。这种商业化、国际化、殖民化、现代化的都市消费文化对女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外在形象上说,她们变得更加洋气,更加摩登。披肩卷发、高跟鞋、旗袍,俨然成为女性的标配。张爱玲就回忆说:“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4]张爱玲:《童言无忌》,《张爱玲集·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从思想观念上说,她们越加鄙视封建传统礼教,变得激进前卫现代,比如积极参加公共事务,介入社会活动,在性的观念上比较开放。当然,这种影响也有消极的一面,有些女性沉湎于感官刺激,迷恋于奢华生活,成为没有灵魂的空壳。
另外,政治体制的变革也影响着中国早期电影中新女性的构建。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体彻底瓦解。以父权、夫权为中心的传统家庭关系失去了法律保障,一夫一妻制、父子平等、男女平等的观念渐入人心。正因为如此,《遥远的爱》中的余珍才会对萧元熙说出这样响亮的话:“我要我独立的人格!”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早期电影中新女性身上的“新”并非都是一新到底,有时可能是由旧到新,由新到旧,或者新旧杂糅,这也许是一种新生事物出现时的常态。虽然从艺术手法上讲,中国早期电影对新女性形象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公式化、口号化的弊端,但毕竟改变了人们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丰富了电影的人物画廊,更主要的是给电影注入了现代化的气息,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