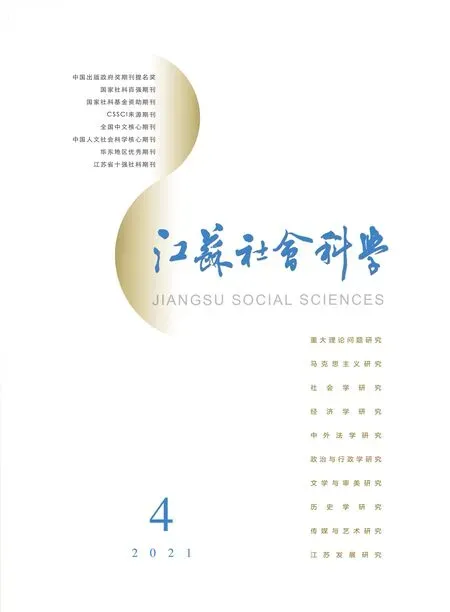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研究
——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比较及启示
吴林海 陈宇环 陈秀娟
内容提要 本文从政府治理公共社会事务政策工具产生与演化轨迹的视角,重点剖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进程中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各不相同,但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轨迹却基本一致,皆经历了从强制型工具为主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相结合,并最终趋向于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相互融合的动态演化过程。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发展的共同特征,其本质体现了一个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而差异性主要由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所处阶段与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不同而产生。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完善既要科学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要从本土的实际出发,促进并努力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均衡与匹配。
一、引言
食品安全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公共社会问题[1]Michiel P. M., Krom de, "Understanding Consumer Rationalities: Consumer Involvement in European Food Safety Governance of Avian Influenza", Sociologia Ruralis, 2009, 49(1),pp.1-19.,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无法独善其身。据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长期监测所得的数据估算,美国平均每年爆发食源性疾病4800 万起,导致12.7万人次发病和3000人死亡。食品是商品,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同时又具有社会公共品的相关属性。然而,市场失灵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严重影响了食品安全这一公共社会事务的治理效能[1]胡颖廉:《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食品安全:起点、体系和任务》,《宏观质量研究》2020年第2期。。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信息不对称。在食品供应链体系中,作为市场主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垄断了信息来源,消费者不易获得完整的食品质量信息,无法在交易过程中掌握主动权[2]Zecca F.,Rastorgueva N.,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of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Consumers and Italian Traditional Food Producers", Recent Patents on Food Nutrition & Agriculture, 2016, 8(1), pp.19-24.,由此导致市场失灵,产生了严重的“柠檬市场”现象。虽然全球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制度不尽相同,食品安全风险的治理体系也千差万别,但为确保食品安全,诸多国家的政府努力从食品作为公共品的这一基本属性出发,探索既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又能确保政府在食品安全这一公共领域发挥更加有为的作用,同时又不失时机地积极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而政府的政策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谓政策工具主要是指政府治理包括食品安全风险在内的公共社会问题的手段和方式[3]汪丞:《教师定期交流的政策困境与对策——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教师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不同的政策工具具有不同的特征、作用边界,选择和使用合适的政策工具对于政府顺利实现公共社会事务的管理目标、增进社会福利具有重要意义。学者们虽然对政府使用积极有为的政策工具来干预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中的市场失灵等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但具体到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这一特殊领域的研究却甚少。故本文系统梳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府政策工具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的演化历程,比较研究其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共性与差异性,以期为中国政府完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政策工具体系提供参考。
二、公共社会事务领域政策工具的产生与演化轨迹
政策工具的出现源自对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纠偏。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市场近乎是万能的。然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出现,使得人们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进行了质疑,产生了市场失灵理论。该理论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体系下的“理性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将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信息不对称、市场垄断以及公共物品市场供给的低效等。而主张政府应该利用货币、财政和税收等政策工具积极干预市场的凯恩斯主义为解决市场失灵提供了理论基础。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3年执政后在美国使用了一系列组合性的政策干预工具,对促进美国摆脱经济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理论提供了实践范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对西方国家缓解经济危机、减少失业、刺激经济增长等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更大范围内为市场化国家的政府所采用。由此,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政策工具在西方国家逐步成为政府干预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福利国家政府的“超级保姆”的角色定位导致这些国家普遍产生公共职能扩张、运行机构臃肿、管理效率低下、公共财政恶化的积弊,在环境保护、市场垄断、食品安全等问题的治理上日益显得力不从心,并由此掀起了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浪潮,政府对政策工具的应用逐渐从市场经济领域延伸至公共管理领域。从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脉络来看,政府利用政策工具干预公共社会事务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传统公共管理占主导的时期。政府被认为是解决社会事务的最重要的责任者,有义务提高社会管理效率,但政府管控手段单一,主要依靠强制型工具。随后,政府管理社会事务效率的低下,迫使传统公共管理模式逐步变迁。
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公共选择学派的兴起与发展。这一时期英国撒切尔政府采纳了新公共管理理论,逐步改革原有的公共行政模式,开始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相对均衡的社会治理体系,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优势互补。在原有强制型工具的基础上,政策工具增加了发挥市场机制功能的引导型工具,而且政府逐步推进强制型工具与市场化手段相结合,要求公共部门强调顾客至上、竞争、绩效评估等理念,通过使用一系列组合性政策工具以提高政府社会治理的效率[1]周峰、陈静:《新公共管理的政策工具:PPP的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1期。。
第三阶段是二十一世纪初建立、至今不断发展的新公共治理改革期。在新公共治理下,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主体趋向多组织、多元化,政府、市场、社会等相关利益主体间加强合作,更加紧密与坚定地构造多元网络空间治理结构。其中,政府更多扮演服务性的角色,主要为市场与社会公众参与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提供服务。随着新公共治理理念的兴起,政府在治理社会公共问题时可使用的政策工具也愈加多样化,在政府强制型工具与市场化手段组合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包括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的引导型工具、激发社会公众自发参与的自愿型工具等在内的政策工具。
由此可见,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结构的不断演化,政府依据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间关系的变迁,在公共管理模式的更迭与优化过程中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由最初的主要依靠强制型工具治理逐步演化为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自愿型工具的组合治理,最终形成了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三类工具既能充分发挥各自治理功能,又能弥补单个工具的缺陷,实现相互组合治理的政策工具体系,以矫正市场失灵避免社会福利损失,力求社会更加公平合理。
三、公共社会事务领域政策工具的主要分类
政策工具又称治理工具,是学者们对政府就干预市场失灵与完善社会公共治理所采用的治理工具的高度概括[2]Schneider A., Ingram H., "Behavioral Assumptions of Policy Tools", Journal of Politics, 1990, 52(2), pp.510-529.,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政策工具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与分类。Hood从作用对象的角度将政策工具描述为:政府利用信息、财政、权威和组织等四种可用资源来监督社会并改变其行为的方式[3]Hood C. C.,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Brain Behav Evol, 1983, 1(1), pp.170-175.。Vedung 基于活动过程的视角,将政策工具定义为关注对社会过程的影响和治理的政策活动的集合[4]Vedung E., "Policy Instruments: Typologies and Theories", Policy Instruments & Their Evaluation, 1998, 10(1),pp.17-21.。Salamon等基于系统论的视角,将政策工具视为政府通过某种方式调节自身行为的机制[5]Salamon L. M., Elliott O. V.,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Action: A Guide to the New Gover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p.47-49.。而国内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的研究普遍都认为政策工具是政府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具体结果的路径、手段和方式。
在界定政策工具概念的同时,学者们探讨了政策工具的分类,以明晰各类政策工具在不同经济社会活动中的具体效用。Kirschen可能是最早研究政策工具分类的学者之一,其提出了64种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未系统化地阐述不同政策工具的分类方法[6]Kirschen E. S., Economic Policy in Our Time, ULB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1964, pp.101-108.。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学者们持续研究政策工具的分类,并基于不同的角度形成了不同的分类方法。目前,较为成熟的分类方法主要有四类:一是按照作用方式的不同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等三种类型[7]Rothwell R., Zegveld W., Reindusd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Logman Group Limited,1985, pp.42-50.。其中,供给型政策工具是政府通过加强转移支付、资源配置、教育培训、信息化建设等措施,从供给面作用于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环境型政策工具是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政策宣传作用于社会公共领域外部环境的改善,服务于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需求型政策工具是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价值标签等激励类手段,从需求面作用于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二是根据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干预程度的不同,将政策工具分类为强制型、引导型和自愿型等三种类型[1]Howlett M., Ramesh M., "Studying Public Policy: Policy Cycles and Policy Subsystem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95,91(2), pp.548-580.。其中,强制型政策工具是政府通过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来干预社会公共问题;自愿型政策工具是主要依靠市场与社会力量共同治理社会公共问题;引导型政策工具是政府实施一定程度的干预措施,通过制度安排引导社会积极参与。三是基于工具类型对政策目标影响程度的不同,将政策工具分为命令工具、激励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系统性工具和劝告劝诱工具等五类型[2]Mcdonnell L. M., Elmore R. F., "Getting the Job Done: Alternative Policy Instruments", Educational Evaluation &Policy Analysis,1987,9(2), pp.133-152.。其中,命令工具是政府通过颁布法令以约束社会行为;激励工具是政府通过给予物质或精神奖励等手段,以改变与引导市场主体与社会公众的行为;能力建设工具是政府使用教育培训、技术研发、信息化建设等工具帮助目标实现而采取特定行为的能力;系统性工具是政府注重整个体制机制的变革,重新分配权力责任;劝告劝诱工具则是政府利用政策宣传、思想教育等工具引导社会公众改变自身偏好与行为习惯。四是依据政府在治理社会公共问题时采用的不同干预方式,将政策工具分类为检查工具、惩治工具和信息工具等三种类型[3]Rouviere E.,Caswell J.A., "From Punishment to Prevention: A French Case Stud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o-Regulation in Enforcing Food Safety", Food Policy,2012,37(3), pp.246-254.,其中,检查工具是政府定期与不定期地对监管对象实施交叉检查以实现监督目标的手段;惩治工具是政府通过惩罚检查不符合法定标准的监管对象以改变监管对象行为的手段;信息工具是政府将依法收集的信息公开化以实施透明化监管。由于研究视角与研究背景的差异,学者们对政策工具的分类不尽相同,但不同的分类标准为政府在不同领域为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有效匹配、组合和优化不同的政策工具奠定了基础。
四、西方与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发展
食品安全是重要的社会公共事务,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产生、演化与发展本质上体现着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动态演变。世界各国治理食品安全风险具有共同的规律性,基于此,系统梳理中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治理食品安全风险中蕴含的政策工具的演化逻辑,对于中国政府完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政策工具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西方国家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历程。西方国家的政府利用政策工具治理食品安全风险大致经过了如下三个发展阶段:
1. 公共行政时期。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食品工业不断发展,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促进了食品市场的逐步繁荣,但食品安全问题开始显现,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制型工具干预市场,以弥补市场与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相对不足。如Turner指出,十九世纪初伦敦牛奶市场掺假现象严重,英国政府通过实施食品安全法规这一政策工具,弥补了食品安全立法的缺失,对减少伦敦牛奶市场的掺假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4]Turner A., "Viewpoint: The Story So Far: An Overview of Developments in UK Food Regulation and Associated Advisory Committees", British Food Journal,1999,101(4), pp.274-283.。同样地,二十世纪初的美国食品造假问题也相当严重,特别是一些企业使用廉价原料生产劣质食品,致使依法经营的企业在价格竞争中深受其害。为打击严重的食品造假问题,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组合性的政策工具,美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理食品造假的联邦法案《联邦食品与药品法案》也由此产生[1]Hutt P. B., Hutt P.B.I., "History of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Adulteration and Misbranding of Food", Food Drug Cosmetic Law Journal,1984,39(1),pp.2-73.。二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一时期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食品造假事件数量大幅增加,西方国家的政府愈加重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为西方国家的政府进一步干预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政府不仅增加了强制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数量,而且其类型也日益丰富。然而,《联邦食品与药品法案》并没有对食品标准做出具体规定,由于存在这一法律漏洞,低劣食品充斥当时的美国市场,威胁消费者健康。在此背景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国会制定了《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规定的政策工具的种类更多、作用范围更广、有效程度更高,扩大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监管职能,奠定了美国现代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基础,促进美国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食品监管法律体系[2]宋怡林:《美国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的经验》,《世界农业》2014年第5期。。总体来说,公共行政时期,西方国家的政府对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手段大多为强制型政策工具,政府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2. 新公共管理时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伴随着食品品种多样性、生产工艺复杂性的显著增加,产生了更具不确定性的食品安全问题,然而,政府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效率低下,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绝。尤其是食品生产的日益规模化与食品添加剂的大量使用,更加剧了食品污染与造假事件的发生,并且产生了与传统风险不同的新型食品安全风险。例如,食品问题使美国产生了较为普遍的儿童肥胖症这一社会问题,不仅影响儿童的身体健康,而且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由此滋生出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3]胡颖廉:《美国如何突破食品安全立法困境》,《公共管理研究》2017年第2期。,政府迫切需要改善治理机制与提升治理效能。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政府不断优化治理工具,在延续使用传统强制型工具的基础上,开始尝试将融入市场化治理手段的引导型工具引入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之中,大幅提高了食品安全风险的治理效能。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于瑞典的社区支持模式实际上就是政府推行的通过协议方式保障农产品质量、体现市场手段的强制型治理工具。农业生产者与消费者达成供求协议,生产者直接将农产品送货上门,政府确保协议的有效性,并监督生产者履行协议的状况。这一新型工具在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提升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从源头降低了农产品安全风险,引导了农业生产者自觉遵守食品安全规定。总的来说,新公共管理时期,政府与市场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组合使用强制型、引导型等多种政策工具,提高了食品安全风险的治理效能。
3. 新公共治理时期。二十世纪后期,西方福利国家的政府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效率低下,食品安全事件源源不断,公众对此强烈不满。在此背景下,强调多元分散主体构建的多边互动的合作网络的社会治理理论开始在西方国家持续兴起,逐渐形成内涵丰富的社会治理理论,开启了丰富多样的社会共治实践,非政府组织的不断发展与公民群体等力量的持续崛起弥补了政府和市场的治理缺陷,对有效治理食品安全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自二十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国家在继续有机结合强制型工具与市场化手段以高效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同时,不断引导私人机构、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发展引导型、自愿型治理工具,并积极探索能从根本上打破信息壁垒的信息化工具,包括信息和劝诫、内部市场、税收和使用费、补贴与完善可追溯体系、召回机制等。如Rouviere 等对法国佩皮尼昂市场的研究发现,政府开始由事后惩治为主的政府监管向以事前预防为主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使用了一系列包括激励与教育的引导型政策工具,改善了法国进口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水平[4]Rouviere E., Caswell J. A., "From Punishment to Prevention: A French Case Stud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o-Regulation in Enforcing Food Safety", Food Policy,2012,37(3), pp.246-254.。美国逐步建立了国家、地方、产业、企业和个人等五个不同层级的信息采集平台,通过信息公开促进社会力量广泛协同参与食品造假的治理。在新公共治理阶段,西方国家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逐步构建起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优势互补、相对均衡的多元治理体系。
(二)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政府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政策工具从无到有,发展到现阶段基本形成了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相结合的政策工具体系。总体而言,中国政府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演化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1. 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年)。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食品安全的主要工作是保障粮食等农产品与食品的数量供应,当时的政策工具主要是思想与道德教育、技能培训、劳动竞赛和行政处罚等传统指令型工具,目的是增加农产品与食品产量。这一时期的食品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食物中毒方面,且主要是由于农产品与食品极度匮乏,再加上人们普遍缺乏食品卫生科学知识,人们无意间食用有毒有害食物所致。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食物间的交叉污染、放置时间过长与变质等原因,上海市徐汇区就发生了众多的食物中毒事件。计划经济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食物中毒事件,每年因中毒导致死亡的人数估计数以万计[1]陆娇、吴林海:《中国食源性疾病的风险特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66页。。为此,政府开始探索并尝试施行法律法规这一政策工具。1953 年,当时的卫生部颁布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食品卫生法规——《清凉饮食物管理暂行办法》,较好地扭转了当时因饮食不卫生而引起的食物中毒问题。
在计划经济阶段,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将食品工业作为公共物品,直接掌控食品生产与市场。这一时期虽然有少量的造假等食品安全风险,但在1956 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私营食品企业和个体食品摊贩基本不复存在,食品造假现象也随之基本消失。当然,这一历史时期也发生了因环境污染而导致的少量重金属中毒等市场风险问题。由于认识的局限性,对于这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并不十分明显的食品安全风险,政府并没有采用相关工具来治理[2]张蓓等:《新中国成立70 周年食品安全演进、特征与愿景》,《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2. 经济体制转轨时期(1979—1992年)。这一阶段是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转轨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经济政策的不断改革,虽然农产品、食品与相关的产业部门发展较快,产量大幅增加,但食品安全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对食品的基本需求同相对紧张的农产品、食品供给之间的矛盾[3]闫志刚:《制定国家食品安全战略应关注的三个问题》,《中国食物与营养》2018年第2期。,人们关注的重点依然是食品数量安全。但此阶段以食物中毒为典型特征的食品安全问题继续大量出现,尤其是由环境污染导致的食物中毒问题进一步凸显。比如,1982年浙江全省就发生了273起食物中毒事件,中毒人数达到3946人,病死率为0.71%,分别比1979年发生的132起食物中毒事件、3464人的中毒人数、0.49%的病死率有了较大的增长[4]丛黎明、蒋贤根、张法明:《浙江省1979—1988年食物中毒情况分析》,《浙江预防医学》1990年第1期。。这一时期与计划经济时期最大的不同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食品市场主体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开始进行食品造假。如1989年浙江绍兴查获的制售万瓶假茅台和董酒大案,涉及78个国营与集体企业(单位),涉事人员多达151人[5]诸永东、张雪林:《假冒伪劣商品违法活动的特点及整治对策》,《商业经济与管理》1989年第6期。。
为了有效治理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食品安全风险,政府不断探索政策工具,主要是实施《食品卫生法(试行)》等法律法规、逐步实行企业登记管理、推行行政处罚制度、探索刑事处罚制度等。但由于制度体系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这一时期政策工具仍然以强制型的惩治工具为主,但也逐步融入了相对简单的市场化手段,如激励性合同、收益分享、组合税收、污染权交易等引导型工具[1]曾蓓、崔焕金:《食品安全规制政策与阶段性特征:1978—2011》,《改革》2012年第4期。。与此同时,政府逐步引入了食品技术标准、市场奖惩、司法裁判等治理方式。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政策工具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混合的色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成为这一时期政府职能改革的核心问题。
3.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1993—2012年)。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农产品生产与食品工业步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然而,粗放式发展中长期积累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日益凸显,特别是长期使用农药、化肥等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影响了农产品与食品原材料的质量安全。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由市场竞争引起的食品安全风险加剧,食品造假成为食品安全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峻[2]吴林海等:《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考察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第84页。。
在2006—2015年的十年间,全国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达245862起。以2011年为拐点,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数量开始下降。在2006—2015年间全国所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中,72.33%的事件是由人为的违法失信行为所导致[3]吴林海等:《中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考察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第84页。,主要是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造假、使用过期原料或出售过期产品等,食品安全领域的主要问题已由食品数量供应、食物中毒等全面升级为食品质量安全。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政府引导食品市场有序运行的能力和经验取得快速提升,这为政府完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强制型工具、实施引导型工具并开启使用自愿型工具创造了条件。在这一时期内,不仅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经历了1993年、1998年和2003年三次全国性的重大改革,全面实现了由食品卫生向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历史性转变,而且初步形成了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强制型工具日趋完善且彰显了较强的威慑力量。与此同时,体现市场机制的新型强制型工具开始出现,逐步建立起以“证”为核心的食品市场准入制度、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制度、信用监管机制等,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规范食品市场秩序的治理工具,以及多种治理工具并用的信用监管体系。在这一时期,引导型工具相继出现。例如,1993 年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对保护消费者食品安全消费权益、维护食品市场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成立了食品行业协会、食品工业协会、饮料行业协会等全国性的第三方社会化组织,其在参与食品行业规制、标准制定、技术咨询等方面开始逐步发挥作用[4]曾蓓、崔焕金:《食品安全规制政策与阶段性特征:1978—2011》,《改革》2012年第4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中政府、市场、社会失衡的格局开始逐步得到扭转,市场与社会主体开始参与到食品安全风险社会共治中。
4.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2013年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食品安全领域的主要矛盾开始转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食品安全供给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食品安全日益成为影响民众幸福感的重要因素[5]文晓巍等:《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关注重点变迁及内在逻辑》,《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10期。。全面深化改革以来,农产品与食品工业开始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开启以高质量发展为主要导向的新发展阶段。经过多年的努力,食品安全事件数量已在倒U型的高点向下滑行,食品安全总体风险处于相对稳定与可控阶段,总体上已初步实现食品安全稳定向好的格局。
然而,自2013年全面深化改革以来,虽然困扰食品安全的一些重大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但以食品造假为主的食品安全风险仍然大量存在,为此政策工具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强制型工具更为有力,实施与完善行刑衔接、检法协调、警企合作等治理机制,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趋于完善;实行“最严厉的处罚”,进一步提高食品犯罪成本等。强制型工具与引导型工具组合更为有效,实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公开食品安全信息,引导食品市场消费,完善声誉机制。自愿型工具更为多样,完善投诉举报平台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公众举报奖励制度,建立消费追偿机制;食品安全信用机制覆盖面更广,着重发展行业组织,推动行业自律,试点食品安全责任保险机制等,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共治体系初步形成[1]吴林海等:《舌尖上的安全——从农田到餐桌的风险治理》,中国农业出版社2019年版,第87页。。总之,自全面深化改革以来,政府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政策工具日趋完备,传统工具与新型工具相融合,事前预防与事后惩治相结合,形成了由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工具相互贯通、相得益彰的现代化治理工具体系,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共治格局初步形成。
五、中国与西方国家演化历程的比较与主要启示
本文基于文献研究,在系统梳理西方公共社会事务领域政策工具的产生与演化轨迹、主要分类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时所采用的政策工具的演化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与西方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的治理政策工具演化历程既具有明显的共性特征,也有不同的个性特征。
(一)中国与西方国家政策工具的共性特征。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演化的历史逻辑而变迁是中西方国家政策工具演化的共性特征。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政策工具主要是以法治、技术标准为主要手段的强制型工具,引导型工具与自愿型工具并不多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政府效率低下的特征日益显现,食品安全问题愈发严重,公众对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公共社会服务供给质量强烈不满。为此,西方发达国家推行新公共管理改革,改进食品安全风险的治理方式,政府在开始运用激励机制以提高政府部门治理效率的同时,为有效治理市场主体由逐利动机引发的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市场化手段开始大幅出现并逐渐与强制型工具相组合。然而,在经过长达近20年时间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后,仍然没能较好地解决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并存的根本性问题。1996年在英国爆发并波及全球的疯牛病与其他后续发生的一系列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严重打击了公众对政府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信心。于是,西方国家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又掀起了被称为“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第二次改革浪潮,政府开始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积极发展医疗保健组织、社会服务机构、倡议性团体、基金会、自助团体等社会组织,增加公众参与风险治理的力度。由此,自愿型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并不断完善,帮助政府更好地履行服务型政府的职责,自愿型工具的使用对推动食品安全风险的公私合作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通过组织化和群体化的示威、抗议、宣传、联合抵制等社会活动有效制约了生产者的机会主义,迫使政府改正不当行为,既弥补了风险治理中的“政府失灵”又补救了“市场失灵”,促进了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领域中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间的平衡。
与西方国家类似,中国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变革也是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三者间关系的变化而逐步演化,演化的逻辑反映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角色和定位的转变。在计划经济时期几乎没有市场,社会结构简单,高度集中的体制决定了以解决温饱为主要目的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工具必然是强制型工具,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主要依靠政府单一的行政力量来推进,引导型与自愿型工具处于真空状态。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商品经济开始出现,但仍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机制在调节食品供应上作用有限,而且社会结构较计划经济时期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虽然这一时期已出现了较多的食品造假现象,但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政策工具仍然以强制型工具为主,引导型与自愿型工具极为有限,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间的关系处于严重的不匹配不平衡状态;传统的行政命令、群众运动等带有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政策工具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非政府主体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引导型、自愿型工具开始出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职能持续改革,强制型政策工具随着政府职能的改革而不断完善,行政、经济与司法工具开始有机组合;市场主体之间尤其是上下游企业之间基于契约的自律机制与食品市场准入体系逐步形成,以激励为主的引导型工具大量出现,市场机制在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然而,在此阶段,由于社会力量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制度供给不足,社会力量能力有限,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关系的仍处于相对不匹配不平衡的状态。自2013年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到了重大调整,市场逐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实施两次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并通过“放管服”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标准,保障市场力量的发挥。与此同时,发挥社会力量,致力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社会力量得以进一步激活,自愿型工具发展迅速。以投诉举报为例,截至2019 年底,除西藏外,已有30 个省市自治区颁布实施了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建立了覆盖全国城乡的公众食品安全举报平台。举报平台成为政府监管部门打击重大食品违法犯罪的主要渠道,明显改善了政府、社会和市场三者不匹配不平衡的状态,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社会共治体系初步形成。
(二)中国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中国与西方国家政策工具变迁的差异性本质上是由国情的不同而产生的。虽然食品安全风险具有动态演化的内在逻辑与基本规律,但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以美国为例,在十九世纪早期,美国人口较少且农业生产水平不高,真正的食品安全风险和隐患极少出现。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飞速发展,掺假、掺毒、假冒的食品在市场上泛滥成灾,劣质食品成为当时美国最主要的食品安全风险。到二十世纪中叶,伴随着美国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促使人们对食品产量以及口味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在农产品生产和食品加工过程中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和食品添加剂,食品的化学性风险与危害大为增加。二十世纪末至今,新原料、新工艺、新方法大量应用给美国带来了新型风险,多种风险叠加成为现阶段美国食品安全的主要风险。由于美国是世界上较为成熟的法制化、市场化国家,其治理风险政策工具一开始就是以法治为主要手段的强制型工具,美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理食品造假的联邦法案《联邦食品与药品法案》就是较为典型的案例。随着食品化学性风险的日趋增加,美国继续发展与丰富引导型与自愿型工具,通过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来治理化学污染。与此同时,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新媒体技术极大地缩短了美国公民和食品安全风险治理间的距离,公民的政治参与空间不再受到严格的限制,加速了美国公民社会的持续、有效运转,大力推动了自愿型政策工具的发展。美国大力完善以《食品安全现代化法》为核心的现代化法律体系,建设社会共治制度,发挥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群体的力量,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等依法有序、边界清晰、运作规范的治理工具。
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政策工具的演化有其自身的特征。在1949—1978年间的计划经济时期,致力于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是当时党和国家最基本的任务。在此阶段主要依托政治优势,采用计划经济手段等强制型的政策工具,辅以思想教育、劳动竞赛与少量的立法等方式,以提升农产品与食品数量供应以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并通过爱国卫生运动等方式化解食物中毒这一最主要的食品安全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由补充性、基础性作用最终发展为决定性作用,食品生产与经营的微观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加剧了由市场竞争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使得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的造假逐步成为食品安全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政府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政策工具日益丰富:一是构建完善的强制型工具,推行警告、罚款、停业整顿甚至吊销卫生许可证等行政处罚;针对食品造假等违法犯罪,探索相应的刑事惩罚制度,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密集出台与实施并融入市场化手段的强制型、引导型工具,最典型的就是实施以证照为核心的市场准入制度,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食品商贩,必须先取得卫生许可证方可进入市场。三是发展自愿型工具以规范食品市场行为,尤其是探索公众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制度。1999年3月15日,央视设立了专门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的专用电话,开启了运用自愿型工具治理食品安全风险之先河。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以来,虽然以食品造假为主要特征的食品安全风险有所改善,但仍然大量存在,完善强制型工具、丰富引导型工具、强化自愿型工具成为现阶段政策工具发展的主要特征。最具典型性的政策工具的使用就是通过完善法律法规,融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于一体,实施“互联网+食品安全”的治理方式,治理从农田到餐桌供应链全程体系的食品安全风险。
(三)主要启示。梳理中西方国家的历史可以发现,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演化史实际上就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变迁史,三者之间的关系随着这个国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动态变化。虽然不同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风险的起点不同,但政策治理工具体系的走向与终点必定是围绕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合作治理而呈现出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各类工具相互融合、共同作用的格局,由此构成与本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状况相适应的政策工具体系。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的内在历史逻辑。从中西方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演化的历史进程来分析,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工具依次先后出现,各类工具由最初的相对独立逐渐走向相互融合,而作为强制型工具重要组成部分的立法与执法工具始终贯穿其中。
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演化的历史逻辑来看,中国正在基于自身的食品安全风险状况构建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工具,这一模式既把握全球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的普遍性,又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来构建完善,体现了“全球视野”与“本土特质”的高度融合。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的历史轨迹表明,中国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已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政策工具既分别发挥政府、市场、社会治理主体各自的治理功能,又努力改变传统的政府单一中心治理模式,在更有力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更加有效有序地释放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重要作用,体现治理主体间的有机统一;既明确确定强制型、引导型、自愿型工具各自的职能与边界,又系统回答政策工具治理什么、怎么治理的基本问题,体现了政策工具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内在统一;既科学设计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工具,实行自上而下的“统一性”,又鼓励不同区域灵活性地探索具有特色的政策工具,体现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机统一。然而,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政策工具仍然面临着强制型工具繁杂、引导型工具靶向性不强、自愿型工具偏少且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促进政府、市场、社会主体间治理食品安全风险政策工具的平衡与匹配,是今后完善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