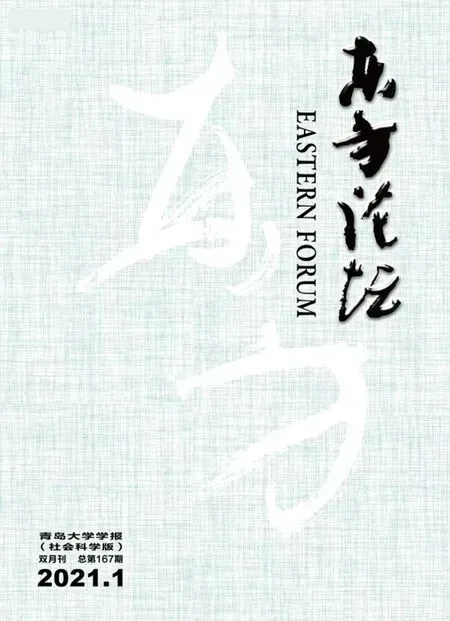论孔颖达的《丧服》制度礼文诠释
邓声国
井冈山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在唐初众多儒家经师鸿儒当中,孔颖达因为奉诏主持编纂《五经正义》而享誉当时。唐初统治者为适应国家科举取士和维护全国社会统一的需要,尽快结束南北朝以来儒学内部宗派纷争,解决经学文献典籍散佚、文理乖错、章句杂乱、师说多门的现状,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受诏撰《五经》义训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云”①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44页。,最终完成《五经正义》这一部集大成的经学义疏结集著作。在孔颖达毕生的治经实践当中,他除了编撰《礼记正义》等著作外,还“与朝贤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谘决之”②刘昫等:《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02页。。贞观十一年(637),孔颖达修成《大唐仪礼》(又名《大唐新礼》)一书,凡一百卷。该书乃是孔颖达与房玄龄、魏征、颜师古等人奉唐太宗敕参与纂修之作,亦即历史上颇为著名的唐“贞观礼”。据此可见,孔颖达对于礼经之学颇为精通娴熟。在礼经之学当中,《丧服》制度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孔颖达虽然没有为《仪礼·丧服》进行专门的著述,但是他对《礼记》49篇当中与“丧服”制度密切相关的篇目,如《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丧大记》《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等篇的礼文诠释中,都贯注了他于“丧服”制度的诠释见解和创见。这些见解且贯穿于《礼记正义》诸篇礼文的诠释当中。为充分发覆孔颖达的诠释成就,本文拟就其关于《丧服》篇礼文弘旨之认知状况,疏解《曾子问》诸篇礼文之诠释焦点,疏解礼文及郑《注》之诠释方法及诠释特色等内容,逐一董理分析如下。
一、《丧服》篇礼文弘旨之认知
孔颖达关于《丧服》篇礼文弘旨之认知,散见于《礼记正义》诸篇礼文的诠释话语当中。今抽绎整理为如下数方面:
其一,关于“五服”服制原则及其“服术”的诠释。对于《丧服》礼文及其具体服制的诠释,必然要涉及到对于其中蕴含的服制原则及其“服术”的阐释剖析。如《礼记·大传》:“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孔氏《疏》云:“上主尊敬,故云‘尊尊’,下主恩爱,故云‘亲亲’。”①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06页。又同篇“服术有六,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郑《注》:“亲亲,父母为首;尊尊,君为首;名,世母叔母之属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长幼,成人及殇也;从服,若夫为妻之父母,妻为夫之党服。”孔氏《疏》云:
此经明服术之制也。“一曰亲亲”者,父母为首,次以妻、子、伯、叔。“二曰尊尊”者,君为首,次以公卿、大夫。“三曰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妇并弟妇兄嫂之属也。“四曰出入”者,若女子子在室为入,適人为出,及出继为人后者也。“五曰长幼”者,长谓成人,幼谓诸殇。“六曰从服”者,即下“从服”有六等是也。②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四,第1507页。
相比较郑玄关于制服原则“亲亲,父母为首;尊尊,君为首”的解释,孔颖达《正义》的疏解更加具体直观。另外,孔颖达还对“从服”做过一次详细的剖析:
“从服”者,按服术有六。其一是“徒从”者。徒,空也,与彼非亲属,空从此而服彼。徒中有四:一是妾为女君之党,二是子从母服于母之君母,三是妾子为君母之党,四是臣从君而服君之党。就此四徒之中,而一徒所从虽亡,则犹服。如女君虽没,妾犹服女君之党,其余三徒,则所从亡而已,谓君母死,则妾子不复服君母之党,及母亡,则子不复服母之君母;又君亡,则臣不复服君党亲也。其中又有妾摄女君,为女君党,各有义故也。③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二,第1496页。
凡此种种,通过列举法进行阐释,皆呈现更为具象化的特点。
其二,关于“五服”义例的认知。“五服”义例,是《丧服》篇及其《曾子问》《丧服小记》所反映的丧服制度的核心理论内容,孔颖达《正义》对此也颇有发覆,不过,在其《曾子问》诸篇的礼文阐释当中,并没有出现“五服”义例的概念,而更多是对服制条文的正、降、义例情况,从情、义、理等角度进行具体的阐释。例如《丧服小记》:“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为妻也,与大夫之適子同。”孔氏《正义》解释说:“《丧服》若举世子为妻,嫌大夫以下有降,《丧服》若举士子为妻,其士既职卑,本无降理,大夫是尊降之首,恐其为適妇而降,故特显之。”①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二,第1496页。孔氏结合《丧服》的降服情况,对《丧服小记》的相类似服制情况进行补充说明。
其三,提出了“礼是郑学”的学术论断。在《礼记正义》当中,孔颖达多次提出了“礼是郑学”的学术论断,如孔氏言:“《礼》是郑学,故具言之耳,贤者裁焉”②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十四,第1352页。“礼既是郑学,故具详焉”③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一,第1488页。“礼是郑学,今申郑义”④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十,第1550页。等等。事实上,在对《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等篇礼文的诠释当中,也是以申解疏通郑氏《注》文为主导诠释,或者是据本书前后文郑《注》文相互发明补充,或者是据《仪礼》一书《注》文诠释《曾子问》《丧服小记》诸篇,等等。孔颖达提出的“礼是郑学”论断,得到了后世诸多学者的认同,如清人陈澧就曾深入发覆说:“郑君尽注《三礼》,发挥旁通,遂使《三礼》之书,合为一家之学,故直断之曰‘礼是郑学’也。……然则郑君礼学,非但注解,可为朝廷定制也。……然则郑君礼学,非但注解,实能履而行之也。”⑤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70页。可谓是对孔氏“礼是郑学”学术论断的进一步申说。
二、疏解《曾子问》诸篇礼文之诠释焦点
孔颖达对《曾子问》《丧服小记》诸篇当中与丧服制度密切关联礼文的疏解串讲,大致与《礼记》其他篇目的训释一致,但也有其独特视角,其中更多的诠释焦点集中在以下诸方面:
其一,重视《曾子问》《丧服小记》等篇目的解题。从《正义》相关卷册情况来看,孔颖达对《曾子问》《丧服小记》等篇目的解题,大都是通过援引郑玄的《三礼目录》来进行诠释的,仅有少数几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援据他人之见加以补充解说。例如《丧大记》篇,孔氏《正义》解释说:“案郑《目录》云:‘名曰《丧大记》者,以其记人君以下始死、小敛、大敛、殡葬之事,此于《别录》属“丧服”。’《丧大记》者,刘元云‘记谓之大者,言其委曲、详备、繁多,故云大’。”⑥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十四,第1571页。又如《丧服四制》篇,孔氏《正义》解释说:“案郑《目录》云:‘名曰《丧服四制》者,以其记丧服之制,取于仁、义、礼、知也。此于《别录》旧说属“丧服”。’郑云‘旧说’,案《别录》无‘丧服四制’之文,唯旧说称此丧服之篇属‘丧服’。然以上诸篇,每篇言‘义’,此不云‘丧义’,而云‘丧服四制’者,但以上诸篇皆记《仪礼》当篇之义,故每篇言‘义’也。此则记者别记丧服之四制,非记《仪礼·丧服》之篇,故不云‘丧服之义’也。”⑦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六十三,第1694页。这则训释例,孔氏在援引郑氏《目录》之文外,还进一步考证分析了《丧服四制》不称《丧服义》之由。
其二,强调通过分章段的方式为《曾子问》《丧服小记》等礼文进行宏观诠释。仍以《丧服四制》篇《正义》的诠释为例,孔氏《疏》文先后云:“此一篇总论丧之大体,有四种之制。初明恩制,次明理制,次明节制,次明权制。既明四制事毕,又明三年丧自古而行之,故引高宗之事。又明斩衰以下,节制之差,结成仁义之事,各随文解之。”“此一节覆说前文礼‘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之事。”“此一经明四制之中恩制也。以父最深恩,故特举父而言之。其实门内诸亲为之著服,皆是恩制也。”“此一经明门外之治,四制之中义制也。”“此一节明四制之中节制也。”①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六十三,第1695页。凡此种种,对于明了各个章段之大旨及其全篇之要旨,起到了很好的诠释效果。
其三,注重从制服原则角度阐释古代丧服规制的深层内涵。例如《间传》:“齐衰之丧,既虞、卒哭,遭大功之丧,麻、葛兼服之。”郑《注》:“兼,犹两也。不言‘包’‘特’而两言者,‘包’‘特’著其义,‘兼’者,明有绖有带耳。”郑玄仅仅只是说明不言“包”“特”而言“兼”者的服制情况,而孔颖达则从服制背后的义理角度,进一步展开阐释说明:“以卑者可包尊,须特著其尊卑之义,故于斩衰重服言之。‘兼’者不取其义,直云绖带麻、葛兼有,故于齐衰轻服言之。于男子而论,其实同也。”②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七,第1662页。又如《三年问》:“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故曰‘无易之道’也。创钜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斩衰苴杖,居倚庐,食粥,寝苫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断之者,岂不送死有已、复生有节也哉!”郑《注》并没有从义理角度解释,孔氏则从义理角度深入剖析:“记者欲释三年之义,故假设其问,云三年丧者,意有何义理?谓称人之情而立礼之节文。”“‘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者,既痛甚差迟,故称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表是至痛极者也。”“‘哀痛未尽,思慕未忘’者,言贤人君子于此二十五月之时,悲哀摧痛,犹未能尽,忧思哀慕,犹未能忘,故心之哀慕于时未尽,而外貌丧服以是断割者。”③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八,第1663页。这为统治者及士族阶层制定礼俗层面的丧服制度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礼记正义》当中,有如是一段关于礼经《丧服》服制的推衍行文,孔氏从“亲亲”的服制原则入手,通过“上杀”“下杀”“旁杀”的方式,对于了解古代丧服服制建构情况具有极大的帮助:
“上杀”者,据己上服父祖而减杀,故服父三年,服祖减杀至期,以次减之,应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俱齐衰三月者,但父祖及于己,是同体之亲,故依次减杀。曾祖、高祖非己同体,其恩已疏,故略从齐衰三月。……“下杀”者,谓下于子孙而减杀。子服父三年,父亦宜报服,而父子首足,不宜等衰,故父服子期也。若正適传重,便得遂情,故《丧服》云“不敢降”是也。父服子期,孙卑,理不得祖报,故为九月。若传重者,亦服期也。为孙既大功,则曾孙宜五月,但曾孙服曾祖正三月,故曾祖报亦一时也。而曾祖是正尊,自加齐衰服,而曾孙正卑,故正服缌麻。曾孙既缌麻三月,玄孙理不容异。且曾孙非己同体,故服不依次,减杀略同三月。……“旁杀”者,世叔之属是也。父是至尊,故以三年。若据祖期年,则世叔宜九月,而世叔是父一体,故加至期也;从世叔既疏,加所不及,据期而杀,是以五月;族世叔又疏一等,故宜缌麻;此外无服也。此是发父而旁渐至轻也。又祖是父一体,故加至期,而祖之兄弟非己一体,故加亦不及,据于期之断杀,便正五月;族祖又疏一等,故宜缌麻;此外无服。是发祖而旁渐杀也。又曾祖据期本应五月,曾祖之兄弟谓族曾祖,既疏一等,故宜三月也。自此以外,及高祖之兄弟悉无服矣。①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二,第1495页。
这样一来,礼经《丧服》篇具体服制条文的逻辑关系就在在得以彰显明晰。
不过,有的时候,孔颖达《正义》对丧服制服原则的解释却有不甚周到之处。例如《丧服小记》:“从服者,所从亡则已。”孔氏《正义》:“‘从服’者,按服术有六,其一是‘徒从’者,徒,空也,与彼非亲属,空从此而服彼。徒中有四:一是妾为女君之党,二是子从母服于母之君母,三是妾子为君母之党,四是臣从君而服君之党。就此四徒之中,而一徒所从虽亡,则犹服。如女君虽没,妾犹服女君之党,其余三徒,则所从亡而已,谓君母死,则妾子不复服君母之党,及母亡,则子不复服母之君母;又君亡,则臣不复服君党亲也。其中又有妾摄女君,为女君党,各有义故也。”又解释说:“‘属从’者,所从虽没也,服此,明属从也。属者骨血连续,以为亲也,亦有三:一是子从母服母之党,二是妻从夫服夫之党,三是夫从妻服妻之党。此三从,虽没犹从之,服其亲也。”②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二,第1496页。另如《礼记·大传》篇:“从服有六,有属从,有徒从,有从有服而无服,有从无服而有服,有从重而轻,有从轻而重。”孔氏《正义》又有解释说:“属,谓亲属,以其亲属为其友党,郑云‘子为母之党’是也。郑举一条耳,妻从夫、夫从妻并是也。……徒,空也。与彼无亲,空服彼之支党,郑云‘臣为君之党’。郑亦略举一条,妻为夫之君、妾为女君之党、庶子为君母之亲、子为母之君母并是也。”③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四,第1507—1508页。
笔者按:“从服”本是“丧服”的制服原则之一,汉唐时期并未作为丧服义例的一种。考上述孔氏《正义》的解释,“属从”之服属于服丧者和服丧对象具有间接亲属关系的从服,《丧服小记》《大传》篇孔氏均将其分为子从母服母之党、妻从夫服夫之党、夫从妻服妻之党“三从”,并无不同。“徒从”之服则属于服丧者和服丧对象并不具备任何亲属关系的从服,《丧服小记》篇孔氏将其分为妾为女君之党、子从母服于母之君母、妾子为君母之党、臣从君而服君之党四者,而《大传》篇孔氏将其分为臣为君之党、妻为夫之君、妾为女君之党、庶子为君母之亲、子为母之君母五者,前后的服制分类范畴颇有差异。另外,《大传》篇六“从服”当中,如果说“属从”之服与“徒从”之服在逻辑关系上处于并列层次的话,那么后四者“有从有服而无服,有从无服而有服,有从重而轻,有从轻而重”则与此二者并不在同一层面上,而且服丧者和服丧对象都存在间接亲属关系。清人孙希旦的说法是:“从服有六,实不外乎属从、徒从而已,其下四者皆属从之别者也。”④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13页。换言之,后四者只不过是“属从”的四种分支类型而已。对此,孔颖达的诠释失于考证。
其四,强调《曾子问》诸篇相关“丧服变除”之发覆。服丧时由成服到释服的过程和仪节,亦即“丧服变除”情况的发覆,是孔颖达诠释《曾子问》诸篇的又一重点。例如《间传》:“斩衰之葛,与齐衰之麻同;齐衰之葛,与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与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与缌之麻同。麻同则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则易轻者也。”郑《注》:“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带,妇人反其故葛绖,其上服除,则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孔氏《正义》:“云‘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带,妇人反其故葛绖’者,此明遭后服初丧,男子妇人虽易前服之轻,至后服既葬之后,还须反服其前丧,故云‘男子反服其故葛带,妇人反服其故葛绖’。但经文据其后丧初死,得易前丧之轻,《注》意明也。后既易以满,还反服前丧轻服,故文、《注》稍异也。”①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七,第1662页。又如《曾子问》:“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内次,然后即位而哭。”关于男女亲迎途中遭遇丧事改服丧服的具体情况,《丧服》篇没有记载,郑《注》亦仅云:“不闻丧即改服者,昏礼重于齐衰以下。”孔氏《正义》则曰:“女既未至,闻婿家有齐衰大功之丧,则废其昏礼,男女变服就位哭。男谓婿也,不入大门,改其亲迎之服,服深衣于门外之次。女谓妇也,入大门,改其嫁服,亦深衣于门内之次。男女俱改服毕,然后就丧位而哭,谓于婿家为位也。”②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十八,第1392页。
其五,强调与《仪礼·丧服》篇服制的异同比较。例如《丧服小记》:“庶子不为长子斩,不继祖与祢故也。”孔氏《正义》:“此亦尊宗之义也。然此所明,与《丧服》中义同而语异也。《丧服》明父是適,为长子斩,此明父是庶子,不得为长子服斩者也,是互相明也。”③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二,第1495页。按:同样是父亲为长子服丧服,由于“父”在家族中身份差异而呈现出服制异同,如《丧服》篇云“父为长子”服斩衰三年,父亲属于“適长子”身份,需要“继祖与祢”;而此篇中,父亲属于“庶子”身份,不能够“继祖与祢”。故父亲为长子服丧存在服制的鲜明差异,孔颖达为此而特意进行二者经文的异同,要皆属于“尊宗之义”的结果。
其六,重视广泛征引前贤训释成说并合理加以取舍和是非论证。根据焦桂美统计,孔颖达撰写《正义》时,合理参考和吸收了此前学者训释成果;其中有明确姓氏称谓的撰者及著作,主要包括庾蔚之《礼记略解》、何胤《礼记隐义》、贺瑒《礼记新义疏》、皇侃《礼记义疏》、熊安生《礼记义疏》等。④焦桂美:《南北朝经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99页。此外,“《正义》中频繁出现‘师说’‘先师’‘先儒’‘旧说’‘释者’‘南师’等,这些名词有着不同的含义。这些词语的使用,可以反映出《正义》大量吸收、利用了前人的成果,包括南北朝时期的义疏”⑤刘金鑫:《〈礼记正义〉解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第75页。。这些征引语段中,不少条目涉及到《曾子问》《丧服小记》等9篇丧服制度的诠释内容。例如《丧服小记》:“久而不葬者,唯主丧者不除。其余以麻终月数者,除丧则已。”孔氏《正义》解释“除丧则已”说:“谓月足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则反服之也,故下云‘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是也。然虽缌亦藏服,以其未经葬故也。”不仅如此,孔氏《正义》还广泛征引各家诠释成说:
卢曰:“其下子孙皆不除也,以主丧为正耳,余亲者以麻,各终其月数除矣。”庾云:“谓昔主,《要记》按《服问》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妇’,故谓此在不除之例,定更思详,以尊主卑,不得同以卑主尊,无缘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长服衰绖也。且前儒说‘主丧不除,无为下流’之义,是知主丧不除,唯于承重之身为其祖曾。若子之为父,臣之为君,妻之为夫,此之不除也,不俟言而明矣。’卢植云:‘下子孙皆不除。’萧望之又云:‘独谓子。’皆未善也,谓庾言为是。”①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三,第1501页。
这一段《疏》文,孔氏先后征引了卢植、庾蔚之、萧望之以及“前儒”等诸家之说,既保留了较为珍贵的众家之说,又据此作出了客观评判,是非臧否,一任读者体悟取舍。
其七,注重从行文义例角度阐释礼篇丧服规制的相关情况。例如《丧服小记》:“礼,不王不禘。”孔氏《正义》申解说:“此经上下皆论服制,记者乱录不禘之事厕在其间,无义例也。以承上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知谓郊天也,非祭昊天之禘也。”②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二,第1496页。按:孔颖达考查发现,此条礼文与《丧服小记》篇上下行文“皆论服制”不类,推测其为记事者“乱录不禘之事厕在其间”,其间并没有行文“义例”的存在,故对此进行发覆。事实上,《大传》篇开头同样有一句“礼,不王不禘”之文,孔《疏》云“此‘禘’谓郊祭天也,然郊天之祭,唯王者得行,故云‘不王不禘’也”③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四,第1506页。,与此段《疏》文从行文义例角度的阐释颇具对比性。
三、疏解《曾子问》诸篇及郑《注》之诠释方法
孔颖达疏解《曾子问》诸篇礼文,无论是对各篇经文所涉及的丧服制度及其丧服变除情况的诠释,还是对郑玄《注》有关丧服制度训释语的申解发覆,其间无不蕴含着孔氏等人特有的诠释方法。这些诠释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后世学者的《丧服》经传记文的诠释与研究。在孔氏《正义》众多方法当中,最为显著的诠释方法当属于文献互证法,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据《仪礼·丧服》篇经《传》之文诠释《曾子问》《丧服小记》等篇经文及郑《注》释语。例如《丧服小记》:“庶子不为长子斩,不继祖与祢故也。”孔氏《正义》:“此亦尊宗之义也。然此所明,与《丧服》中义同而语异也。《丧服》明父是適,为长子斩,此明父是庶子,不得为长子服斩者也,是互相明也。”④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二,第1495页。又如《杂记上》:“未服麻而奔丧,及主人之未成绖也,疏者与主人皆成之,亲者终其麻带绖之日数。”郑《注》:“疏者,谓小功以下也。”孔氏《正义》:“知‘疏者,谓小功以下’者,《丧服传》云大功以上,同居为同财,故知‘疏者’谓小功以下。”⑤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十一,第1554页。按:以上二例,前例将《丧服小记》和《丧服》经文对比,考察二者异同以申解经义;后例通过连通《丧服传》以比对申解说明郑《注》之所以然。
二是据《礼记》各篇礼文来诠释互证《曾子问》《丧服小记》等篇经文及其郑《注》释语。例如《杂记上》:“有父母之丧,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殇,则练冠附于殇,称‘阳童某甫’,不名,神也。”郑《注》:“阳童,谓庶殇也。宗子则曰阴童。童,未成人之称也。某甫,且字也。”孔氏《正义》:“云‘阳童谓庶殇也,宗子则曰阴童,童,未成人之称也’者,《曾子问》:‘庶子之殇,祭于室白,故曰阳童。宗子殇死,祭于室奥,则曰阴童。’云‘某甫,且字也’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时曰某甫,是且字,言且为之立字。”①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十一,第1553—1554页。又同篇“子冯之踊,夫人东面坐冯之,兴踊”,孔氏《正义》:“此一经是《丧大记》君丧之节,于此重记之。但《大记》云‘夫人东面亦如之’,此云‘夫人东面坐冯,兴踊’,惟此四字别,义皆同也。”②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十一,第1558页。按:以上二例,前一例是孔氏《正义》据《曾子问》与《檀弓》之文来诠释申解郑《注》之意,后一例是孔氏《正义》据《丧大记》来诠释说明《杂记上》礼文之意。凡此种种,要皆《正义》强调通过引证与诠释话语关联性较强的材料,达成对礼文及其郑《注》释语的疏解。
孔颖达《正义》运用文献引证法,除了上述两种情况外,还有其他情况,如借助其他儒家典籍和各种先秦两汉文献佐证礼制,借助本经其他位次的郑《注》及其他经典文献的郑《注》诠释语来证成《曾子问》等篇经文服制及郑《注》释语。凡此种种,在此前部分的论述当中已有不少例证,此不重复举证说明。
除了文献互证法之外,孔颖达还特别重视依据服制“尊尊”“亲亲”原则来推理申解诠释《曾子问》《丧服小记》等篇经文及其郑《注》释语的服制规定,这是对汉魏南北朝学者治礼方法的延续。例如《丧服小记》:“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对于这一服制规定,郑《注》解释说:“不敢以己私废父所传重之祭祀。”虽然涉及到“尊尊”的制服原则,但其诠释仍有不足,如从“亲亲”的角度而言,又将如何呢?或者说,父在与父没又有何差别之处?凡此种种,《注》文并不清晰,故孔氏《正义》申解说:“出母,谓母犯七出,为父所遣。而母子至亲,义不可绝。父若犹在,子皆为出母期。若父没后,则適子一人不复为母服,所以然者,己系嗣烝尝,不敢以私亲废先祖之祀,故无服。”③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二,第1495页。较之郑《注》释语,孔颖达的解释更趋完整,更为兼顾了“尊尊”“亲亲”两重制服原则。
四、疏解《曾子问》诸篇及郑《注》之诠释特色
如前所述,在《礼记正义》当中,孔颖达多次提出了“礼是郑学”的学术论断,所谓“《礼》是郑学,故具言之耳,贤者裁焉”④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十四,第1352页。“礼既是郑学,故具详焉”⑤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一,第1488页。,等等。既然“礼是郑学”,那么孔氏撰述《礼记正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申解郑《注》之意义。和其他各篇一样,孔颖达对《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诸篇礼文的诠释,基本上是以申解疏通郑氏《注》文为诠释主导。透过这些申解郑《注》的诠释话语,大致可以发见,孔氏疏解《曾子问》诸篇郑《注》,呈现出如下几方面的诠释特色。
其一,尽管孔氏《正义》大量征引此前诠释成说,但大多根据郑玄《注》文批驳各家之说。有学者称:“孔疏于唐前《礼记》学成果,几乎皆有所征引,然诸说凡有不同于郑注、而又无明文可据者,多以郑《注》为解经标准,或以诸说为非、或不取诸说。”⑥陶广学:《孔颖达〈礼记正义〉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3年,第290页。从《曾子问》诸篇《疏》文的诠释来看,大都如此。例如《杂记上》“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士为其父母兄弟之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郑《注》曰:“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孔氏《正义》则云:
以经唯云父母兄弟,士与大夫之异,不云大功以下有殊,是大功以下与大夫同。所以然者,以重服情深,故使士有抑屈,使之勉励。大功以下,轻服情杀,故上下俱申也。按《圣证论》王肃云:“丧礼自天子以下无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齐斩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达。’且大国之卿与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晋士起大国上卿,当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为大夫,谓诸侯之卿,当天子之大夫,非谦辞也。春秋之时,尊者尚轻简,丧服礼制遂坏,群卿专政,晏子恶之,故服粗衰枕草,于当时为重。是以平仲云:‘唯卿为大夫。’逊辞以辟害也。又《孟子》云:‘诸侯之礼,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又此《记》云:‘端衰丧车皆无等。’又《家语》云:‘孔子曰:平仲可为能远于害矣。不以己之是駮人之非,逊辞以辟咎也。’ ”王肃谓大夫与士异者,大夫以上,在丧敛时弁绖,士冠素委貌。马昭答王肃曰:“《杂记》云:‘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是大夫与士丧服不同者。而肃云无等,则是背经说也。”郑与言礼,张融评云:“士与大夫异者,皆是乱世尚轻凉,非王者之达礼。小功轻重,不达于礼。郑言谦者,不异于远害。”融意以王肃与郑其义略同。如融之说,是周公制礼之时,则上下同,当丧制无等。至后世以来,士与大夫有异,故记者载之,郑因而解之。礼是郑学,今申郑义。云“端衰丧车无等”者,端,正也,正为衰之制度上下无等,其服精粗卿与大夫有异也。又,曾子云“齐斩之情”,据其情为一等,无妨服有殊异耳。若王肃之意,大夫以上弁绖,士唯素冠,此亦得施于父母。此经云为昆弟,岂亦弁绖素冠之异乎?此是肃之不通也。杜元凯注《左传》,说与王肃同。服虔注《左传》,与端衰丧车无等,其老之问,晏子之答,皆为非礼,并与郑违,今所不用也。①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十,第1550页。
以上一段诠释话语中,孔颖达先后援引了王肃、马昭、杜预、服虔等人的观点,且皆与郑玄的解释不同;而孔氏则依据郑氏的解释来批驳他们的观点,并且指出他们的说法“皆为非礼,并与郑违,今所不用”,彰显郑学极其鲜明。
另外还要指出,倘若郑玄《注》文有阙漏之处,孔氏则折衷于此前其他学者成说,选择较为合理的说法,借以补充完善郑氏《注》文。例如《杂记上》:“有三年之练冠,则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屦不易。”为什么要“大功之麻易之”,郑玄《注》文并没有任何说明,故孔氏《正义》为之诠释说:
先师解此,凡有三义。按《圣证论》云:“范宣子之意,以母丧既练,遭降服大功则易衰。以母之既练,衰八升,降服大功,衰七升,故得易之,其余则否。贺玚之意,以三等大功,皆得易三年练衰。其三等大功,衰虽七升、八升、九升之布,有细于三年之练衰,以其新丧之重,故皆易之。”皇氏云:“或不易。”庾氏之说,唯谓“降服大功,衰得易三年之练,其余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则不得易三年之练”。今依庾说。此大功者,时据降服大功也。故下文云“而祔兄弟之殇”,虽论小功之兄弟,而云降服,则知此大功之麻易,据殇也。①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十一,第1553页。
按:孔颖达根据自身目力所及,指出此前学者对此礼文有三种不同的诠释意见,认为当依庾氏之说较为可信,并据此进一步申解经文“以大功之麻易之”之意。这种诠释之法,实际上也是补足郑《注》训义的一种方式。
其二,注重对郑玄《注》文训释疏略处作进一步训释。倘若郑氏的《注》文不能完全阐发经文之意,或者郑氏的《注》文虽然已经包含有某种意思,但并未明确说出,孔氏《正义》往往作进一步疏解,将郑氏隐含之意挖掘出来,从而使得读者更好地理解经文及郑《注》之意。例如《杂记下》:“有殡,闻外丧,哭之他室。”郑《注》:“明所哭者异也,哭之为位。”孔氏《正义》:“有殡谓父母丧未葬,丧柩在殡宫者也。外丧谓兄弟丧在远者也。他室,别室也。若闻外丧,犹哭于殡宫,然则嫌是哭殡,则于别室哭之,明所哭者为新丧也。”②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十二,第1560页。按:郑玄的释文并未对礼文中“有殡”“外丧”“他室”等词语及其整句话加以解释串讲,故孔颖达《疏》为此另加诠释。再如,《曾子问》:“士则朋友奠。不足则取于大功以下者,不足则反之。”郑《注》:“服齐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谓殷奠时。”孔氏《正义》:“殷奠,谓月朔之奠,以其有牲牢黍稷,用人多也。殷,盛也,以月朔之奠,盛于常奠,非月半之殷奠也,以士月半不暇殷奠故也。”③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十八,第1391页。郑玄《注》语云“谓殷奠时”,“殷奠”一词意义不甚明晰,故孔氏为之申解诠释,并进一步辨明“月朔之奠”与“月半之殷奠”二者之差异所在。
其三,注重对郑玄《注》文援引文句出处及征引目的进行分析。例如《大传》:“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郑《注》:“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盖特尊焉。《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泛配五帝也。”孔氏《正义》曰:
云“苍则灵威仰”至“汁光纪”者,《春秋纬·文耀钩》文。云“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者,案《易纬·乾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云“盖特尊焉”者,就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是特尊焉。《注》引《孝经》云“郊祀后稷以配天”者,证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引“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者,证文王不特配感生之帝,而泛配五帝矣。④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四,第1506页。
按:此则孔氏《疏》文,不仅指出了二则隐性引语的出处,同时也分析说明了二则显性引语的援引目的,申解郑《注》的效果极佳。
其四,重视征引各类先秦两汉典籍来证成郑《注》的诠释。众所周知,郑玄注释各类儒家经典的一个重要做法,便是征引各类文献典籍之语料来引证自己的诠释说法。孔颖达疏解郑《注》,同样强调通过广泛征引各类文献典籍之语料,据此证明郑玄训释之有所据,而不是空为之言。例如《曾子问》:“诸侯相诔,非礼也。”郑《注》:“礼当请诔于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史赐之谥。”孔氏《正义》:
按《白虎通》云:“君薨请谥,世子赴告于天子。天子唯遣大夫会葬而谥之。”又《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大夫当请诔于君,则诸侯理当言诔于天子。云“天子乃使大史赐之谥”者,按《大史职》云:“小丧,赐谥。”郑云:“小丧,卿大夫也。”卿大夫言“赐之谥”明谥,明诸侯之丧亦然。①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十九,第1398页。
按:孔颖达《正义》通过征引《白虎通》及《礼记·檀弓》之文,比例而类推之,说明“诸侯理当言诔于天子”。同样地,孔氏又通过征引《周礼·大史职》之文比例类推,说明“天子乃使大史赐之谥”之理。
其五,注重对郑《注》诠释依据进行发覆分析与说明。郑玄诠释《曾子问》诸篇经文,并不说明自身训释的依据所在,故孔颖达作《正义》时,十分重视对郑玄诠释结论的依据进行申述说明。例如《曾子问》:“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郑《注》:“此指谓国君之子也。”孔氏《正义》:“郑知经指国君之子者,以经云‘君命所使教子’,故知谓国君之子也。”②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十八,第1393页。郑玄《注》谓“君命所使教子”的“子” 指国君之子,而不言依据所在,故孔氏指出可据上下文而得知也。有时候,孔颖达也指出郑玄根据其他相关材料(诸如文献材料、世俗风尚等)作出训释,例如《丧大记》:“既祥,黝垩。祥而外无哭者,禫而内无哭者,乐作矣故也。”郑《注》:“地谓之黝,墙谓之垩。外无哭者,于门外不哭也。内无哭者,入门不哭也。祥逾月而可作乐,作无哭者。”孔氏《正义》:“云‘地谓之黝,墙谓之垩’者,《释宫》文。云‘祥逾月而可作乐’者,《檀弓》云‘鲁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孔子曰‘逾月则其善也’,是祥逾月而可作乐也。”③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四十五,第1581页。此则疏文,指出郑玄的诠释先后来自于《尔雅·释宫》和《礼记·檀弓》等,充分佐证并提升了郑玄《注》诠释结论的可信度。
其六,注意对郑《注》诠释语中相关语词的意义发覆。郑玄《礼记注》中的注释语言,到了唐代孔氏生活年代,有些语词已经不太通行,颇有晦涩之嫌,需要后人对这些疑难词语加以诠释。孔颖达作《礼记正义》时,亦不例外。例如《丧服小记》:“君虽未知丧,臣服已。”郑《注》:“从服者,所从虽在外,自若服也。”孔氏《正义》云:“若,如也,谓自如寻常,依限著服也。凡从服者,悉然也。”④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二,第1497页。郑氏注语称“自若服”不易明了,故孔氏《正义》为之训释称“若,如也,谓自如寻常,依限著服也”,后人方可了然郑氏之义。又如《丧服小记》:“养有疾者不丧服,遂以主其丧。非养者入主人之丧,则不易己之丧服。”郑《注》:“其为主之服,如素无丧服。……谓养者无亲于死者,不得为主,其有亲来为主者,素有丧服而来为主,与素无服者异。”郑《注》中的“素无丧服”“素有丧服”到底何意,易于引起歧义,故孔氏《正义》为之申解诠释说:“云‘素有丧服而来为主’者,素,犹本也,本有丧,谓有前丧之服也,已服前丧之服而来主之,不易服也。云‘与素无服者异’者,本无服,谓若来为丧主者,身本吉,无丧服。既来为主,则为此死者服始死之服。”①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三,第1501—1502页。“素”字的意义本颇多,不易理解,通过孔氏《正义》的解释“素,犹本也”,郑氏的训释意义大明,“素无丧服”亦即“本无丧服”,“素有丧服”亦即“本有丧服”。
其七,注重通过不同典籍不同位次郑《注》的训释进行相互参证融通与是非辨别。郑玄注释群经有先有后,“故以著述而言,先注《周官》,次《礼记》,次《礼经》,次《古文尚书》,次《论语》,次《毛诗》,最后乃注《易》”②张舜徽:《郑氏校雠学发微》“注述旧典下”条,《郑学丛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页。。显然,诠释《礼记》诸篇要比诠释《仪礼·丧服》经文更早,其中容有相同相异之处,故孔颖达撰《正义》时,往往从融贯群经郑《注》的高度进行综合体认与解读。例如《大传》:“谓弟之妻‘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郑《注》:“复谓嫂为母,则令昭穆不明,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为服,不成其亲也。男女无亲,则远于相见。”孔氏《正义》:“云‘复谓嫂为母,则令昭穆不明’者,既以子妻之名名弟妻为妇,若又以诸父之妻名名兄妻为母,则上下全乱,昭穆不明,故不可也。郑注《丧服》亦云:‘弟之妻为妇者,卑远之,故谓之妇。嫂者,尊严之,是嫂亦可谓之母乎?’言其不可也。故言‘乎’以疑之,是弟妻可借妇名,是兄妻不可借母名,与此《注》正合,无相违也。”③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四,第1507页。孔氏云“与此《注》正合,无相违也”,显见《正义》此例训释,基本上属于将二处《注》文相互参证为训的情况。
其八,和疏解《曾子问》诸篇礼文一样,孔氏申解郑《注》时,同样征引不少汉代以来前贤的训释成说,借以疏通郑氏之意。例如《丧服小记》:“为慈母后者,为庶母可也,为祖庶母可也。”郑《注》:“谓父命之为子母者也,即庶子为后,此皆子也,传重而已。不先命之与適妻,使为母子也,缘为慈母后之义。父之妾无子者,亦可命己庶子为后。”孔氏《正义》:
“谓父命之为子母”者也,皇氏云:“此郑《注》总解经‘慈母’‘庶母’‘祖庶母’三条也,皆是庶子父命之使事妾母也,故云‘父命为子母’也。”云“即庶子为后,此皆子也,传重而已。不先命之与適妻,使为母子也”者,庾氏云:“郑注此一经,明庶子为適母后者,故云即庶子为后,谓为適母后。此皆子者,此庶子皆適母之子。今命之为后,但命之传重而已。母道旧定,不须假父命之与適妻使为母子也。”④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三,第1500页。
按:这一段诠释话语当中,孔氏先后征引了前人皇侃《礼记义疏》和庾蔚之《礼记略解》的训释成说。这种诠释举措,不仅为后世学者保留下来了大量可靠的汉魏南北朝礼经诠释旧说,同时也打破了汉代以来说经的师法家法窠臼,完全以各家说解是否有经文及郑注之根据来作为取舍评判的标准,使得《正义》的疏解更加广博宏通。当然,孔氏《礼记正义》遵循“疏不破注”的诠释原则,并不是一味完全依从郑玄训释《曾子问》《丧服小记》等篇经文的诠释见解,有时也对郑玄的某些不当诠释提出质疑。孔氏《正义》疑郑《注》与驳郑《注》的相关情况,陶广学先生颇有说明⑤陶广学:《孔颖达〈礼记正义〉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12年,第97页。,此不重述申解。
综上可见,从孔颖达关于《丧服》篇礼文弘旨之认知情况到《礼记正义》疏解《曾子问》诸篇礼文之诠释焦点、诠释特色乃至孔颖达疏解《曾子问》诸篇郑《注》之诠释方法与诠释特色等情况的发覆中,可以看出,《礼记正义》虽然是在南北朝各类旧疏基础上增删损益而成,孔颖达等人在尊崇经典、宗主郑《注》大原则和审慎摘录态度之下,面对此前纷繁的各种诠释成说,采取了兼收并蓄、诸说并存方式,举凡可信者援据以疏解经、注,其不可信者则保存之;并通过“今删定”“师说”或者“先师”“先儒”之说等一类言辞,表明自身的谨慎选择态度。换言之,孔颖达《礼记正义》关于《丧服》制度礼文的诠释,是一种集成式文献诠释,和当时儒学研究整体风貌基本一致,颇具超越前代、重构新局的宏大气概。因而,黄侃先生评价孔氏《礼记正义》说:“孔《疏》虽依傍皇《疏》,然亦时用弹正,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故清世诸经悉有新疏,独《礼记》阙如者,亦以襄驾其上之难也。”①黄侃:《礼学略说》,《黄侃论学杂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50页。即便是单就《曾子问》诸篇丧服规制诠释情况而言,此亦可谓颇为允当,诚属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