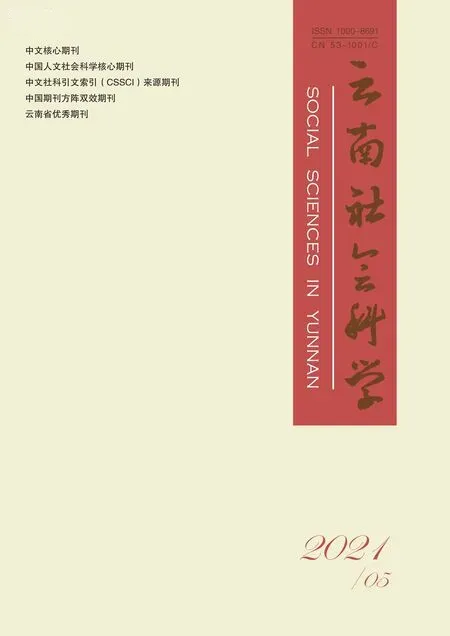中国脱贫攻坚对人类反贫困理论的贡献
郑宝华 宋 媛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大事。围绕贫困和反贫困的理论研究因此成为国内外学者的重要研究领域,并且有不少学者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国外的贫困和反贫困理论主要区分为西方学者和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研究,国内学者则主要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贫困及反贫困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研究。中国的脱贫攻坚不仅使中华民族告别了困扰几千年的绝对贫困,而且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既对西方的贫困和反贫困理论做出了历史贡献,又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贫困及反贫困理论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更是对中国反贫困实践的理论升华。
一、西方反贫困理论及中国脱贫攻坚的贡献
最早涉及贫困问题的西方学者是让·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他于1755年发表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在阐述人类社会的不平等问题时分析了贫困问题。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R.malthus,1766—1834)则于1798 年在《人口论》中最早提出贫困理论。较早对贫困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本杰明·朗特里(Benjamin S.Rowntree,1871—1954)于1901 年 出版了《贫困:城镇生活研究》一书,书中首次给出了贫困的定义:“总收入水平不足以获得仅仅维持身体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生活必需品。”①转引自吴理财:《“贫困”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分析的贫困》,《经济评论》2001年第4期。随后,贫困问题吸引着众多西方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并得到了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口学家甚至文化人类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且取得了丰富成果。因此,在回答中国的脱贫攻坚对西方贫困及反贫困理论所做的贡献之前,有必要对西方除卡尔·马克思(Karl H.marx,1818—188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V.Engels,1820—1895)以外学者的贫困及反贫困理论本身及其不足进行简要回顾。
(一)西方反贫困理论的基本观点
贫困是一个经济问题,但不完全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学首先对贫困及反贫困理论进行了诸多研究,但来自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以及人口学的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有必要从上述学科分别对西方的贫困及反贫困理论进行简要回顾和总结。
1.经济贫困及其脱困之路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围绕贫困的原因及如何摆脱贫困这两个基本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罗格纳·纳克斯(R.Nurkse,1907—1959)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阿瑟·刘易斯(A.Lewis,1915—1991)的“二元经济模型”理论、冈纳·缪尔达尔(G.myrdal,1898—1987)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1915— )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威廉·舒尔茨(W.Schultz,1902—1998)的“人力资本”理论、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1933— )的“能力贫困学说”等。
纳克斯1953年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资本供给(储蓄)和产品需求(消费)都不足,这就进一步限制了资本形成,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之中。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必须大规模增加储蓄,扩大投资,形成各行业的相互需求,从而使恶性循环转为良性循环。1954 年,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世界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呈现二元结构特征,即在面积广大的农村地区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而在城市地区则现代工业占主导地位,这种城乡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性矛盾,使得农村地区越来越贫困,而城市地区则越来越富裕,农村地区想要摆脱贫困,就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途径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1957 年,缪尔达尔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认为,某国家或某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最先起步并慢慢积累起领跑优势的往往都是那些拥有资源、环境、交通等各种先天禀赋优势的地区。这些地区通过循环累积效应,逐渐积攒起强势发展动能并不断扩大与落后地区的差距,最终使落后地区深陷贫困的累积循环泥潭。为此,滞后地区和不发达国家需要在权力、土地、教育等方面进行体制改革,努力改善收入不平衡所依赖的资源、权力和机会的不平等,并最终缩小贫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1958 年,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强调经济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平衡增长是不可能的,需要采取不平衡增长理论。发达区域经济增长可能会对欠发达区域产生有利的涓滴效应,也可能产生不利的极化效应。①[美]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潘照东、曹征海译,潘光威校,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169—172 页。随后,“涓滴效应”被用来解释经济发展对缓解贫困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能缓解贫困。但很少有学者对极化效应进行跟踪研究。1960 年,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概念,并于1964年出版著名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提出了“贫困且有效率”命题。他认为,贫困者之所以贫困,是由于缺乏知识、技术与高质量的投资。只要增加贫困农户的知识、推广先进技术,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并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就可以让他们摆脱贫困,贫困人群的出路就是要提高人力资本投资。1999 年,阿玛蒂亚·森提出的“能力贫困”理论认为,贫困应被视为贫困者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出路就是提高个人的可行发展能力。
2.政治学的权利剥夺和赋权理论
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政治制度揭示贫困的本质以外,西方政治学家也从权利视角来审视贫困问题。印度籍美国学者塞德希尔·穆来纳森(S.mullainathan)和埃尔德·莎菲尔(E.Shafir)的研究发现,长期的“贫困”不仅很容易导致个体专注于“贫困”本身,进而降低其“带宽”容量(即心智容量,包括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能力),致使他们缺乏洞察力和前瞻性,而且会减弱他们的执行控制力,即所谓的贫困可能导致“愚昧”。②[美]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埃尔德·莎菲尔:《稀缺:我们是如何陷入贫穷与忙碌的》,魏薇、龙志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15 页。而阿玛蒂亚·森在强调能力贫困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贫困的实质源于权利的贫困,据此提出了赋权反贫困理论。1981 年,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强调指出,“一个人支配粮食的能力或者他支配任何一种他希望获得或拥有东西的能力,都取决于他在社会中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关系”,这就是源于权利缺乏而导致的贫困,因此要从制度上进行变革,以努力实现贫困人口享有基本政治与公民自由,保障其能顺利获得基本生活、教育、医疗等权利。①[印]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削》,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40 页。
3.社会学的社会剥夺理论
社会学家们围绕贫困进行了许多研究,形成了诸如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1914—1970)的“贫困文化理论”、约瑟夫(K.Joseph)的“剥夺循环论”、郝伯特·甘斯(Herbert J.gans,1927— )的“贫困功能论”、米尔顿·费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的“个体主义贫困观”、瓦伦丁(C.Verlinden)的“贫困处境论”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易斯1959 年提出的“贫困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贫困既是过去的一种结果又是产生新贫困的动因,即贫困的代际传递。刘易斯在对墨西哥和波多黎各贫民窟居民进行一系列调查研究后发现了“贫困文化”的存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因为无法获得成功,所以形成了一套与贫困者社会地位相适应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这种“亚文化”一旦形成,不仅会影响他们改变贫困的状况,而且会代代相传使贫困维持下去。由此,要消灭贫困就必须提高穷人的个人素质,包括文化价值观。②Oscar Lewis:Five Families: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Basic Books,1996,p215.
另外,贫困文化理论还延伸出贫困代际传递论,如美国学者劳伦斯·米德(Lawrencem.mead)认为,福利不足不仅导致贫困,而且会产生代际传递。③Lawrencem.mead:The New Politics of Poverty:The Nonworking Poor in America, New York,Basic Books,1992.马歇尔·哈瑞顿(Michael Harrington)更精辟地指出: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穷人有穷人的语言、心理和世界观”的文化④Michael Harrington:The Other American: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62,p23.,但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种族歧视所形成的社会排斥⑤Michael Harrington:The New American Poverty,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on of Canada limited,1984,p140.。
4.人口学的人口过快增长理论
人口过快增长导致人均福利水平的降低,是最具代表性的解释贫困的人口学观点。早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便将贫困作为特定的社会现象进行规范的理论分析。他认为,“社会人口按几何数列增加,而生活资料因土地有限只能按算术数列增加,因人口增长速度快于食物供应的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最后因食物不足导致人口过剩,必然导致贫困、恶习等出现”。马氏由此将贫困的根源归结为人口的过快增长,并得出了著名的“人口剩余致贫论”。对此,他认为出路就是调控人口增长速度,并使之与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相适应,手段就是采用诸如节育、晚婚等“道德抑制”手段,甚至必要的战争、饥荒、疾病等“积极抑制”手段。⑥[英]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6 页。
由此可见,上述理论从不同角度对贫困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消除贫困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诸多可以借鉴的观点,如阿瑟·刘易斯的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冈纳·缪尔达尔的国家改革,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提升等。实际上,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借鉴过这些理论,并采取过相关的反贫困举措,但大多收效甚微。这就需要正视西方贫困和反贫困理论本身的不足。
(二)西方反贫困理论的主要不足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具有一定的时代使命。而正是这种时代使命,使西方学者关于贫困和反贫困的研究“囿于功利主义和平等主义两类观念,进而形成了个人主义反贫困与结构主义反贫困两种路径。个人主义反贫困理论强调激发‘贫困者’个人的主体性,主要依靠个人努力来摆脱贫困”⑦高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统筹衔接:形势任务与战略转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 年第6 期。,国家因此只需要在资源再分配等方面有限介入即可,不需要进行强力外部干预,而需要把更多精力用于维护市场秩序与保护私有产权,最典型的是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和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提升。但问题是,对于穷人来讲,当他们面临吃了上顿无下顿的生活境遇时,既缺乏人力资本及能力提升投资的现实经济基础和能力,又缺乏进行此项投资的内在动力。反过来,后者还被有些学者解释为贫困文化,如劳伦斯·米德和马歇尔·哈瑞顿。而从经济学上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就是赫希曼的涓滴效应理论。
结构主义反贫困理论强调国家干预、政府动员与再分配,尤其是资源和资产的再分配,提倡实施有利于抑制社会分化的普遍性社会政策。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理论都认为,贫困在没有外力推动下会保持一种高度稳定的均衡状态,不论是单个生产要素的一般状态,还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都会保持较高的稳定性,甚至呈现出低水平的循环,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就是其中的代表。而随后的新制度经济学则更“强调制度是决定经济绩效的核心因素,要求以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主线全面推进制度变革”①高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统筹衔接:形势任务与战略转型》。。
西方贫困和反贫困理论除了以上两大对立观点本身存在的不足外,还有两个涉及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问题。首先,对贫困的理解过于抽象化和个人化。贫困是人的贫困,但贫困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就绝对贫困来讲,贫困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集中性,并突出表现为民族性。集中性也就要求采用除针对贫困者家庭和个人的一些手段外,还需要有一些集中性和集体性的手段,尤其是贫困者家庭和个人无法克服的一些难题,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必要的私人物品如住房、安全饮用水的提供等。民族性则更多强调的是民族之间发展机遇、发展权利的不平等导致的发展差距,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整族贫困问题。这两个问题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主要问题,但并没有引起强调平等主义的西方贫困和反贫困学者的高度重视。
其次,尽管西方学者强调国家干预对反贫困的重要性,但如何干预、干预到什么程度、干预手段、干预时点等都被抽象化了。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尽管经济很发达,但政府干预的手段却很少,除了税收优惠和社会救助外,似乎没有太多有效手段,尤其是在如何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经济等方面。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许多国家不仅经济基础脆弱,而且政治动荡、民族分裂、社会冲突不断,国家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文化基础以及政治基础(包括决策者的政治意愿)都不是很牢固,这也使得政府干预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纸上谈兵。这两者都使西方贫困和反贫困理论失去了其可以发挥作用的制度和社会土壤,久而久之被实践乃至被理论本身所抛弃,最后也就只有回到“循环论”(循环累积、恶性循环以及剥夺循环)以及“处境论”中去自娱自乐了。
(三)中国脱贫攻坚实践对西方反贫困理论的主要贡献
中国的脱贫攻坚走出了一条“理论—实践—理论”的有效发展道路,不仅为人类反贫困事业做出了贡献,而且为包括西方贫困和反贫困理论在内的贫困治理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1.重视贫困者的社会属性
贫困及反贫困理论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就是“谁是穷人?”对此,中国在三十多年扶贫开发的基础上,通过“建档立卡”“回头看”和“动态管理”等措施,把真正需要帮扶的贫困对象界定出来。这是人类反贫困史上规模最大的贫困人口识别活动。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既注意到了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还注意到了贫困村和贫困县以及集中连片区域。中国不仅以“两不愁三保障”作为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的识别标准和帮扶目标,还对贫困村、贫困县和连片特困区域有明确的标准。这一点,对于西方贫困和反贫困理论是一个重要贡献,不仅能够提高贫困识别的精度,而且能够把针对个人和家庭的反贫困措施与针对区域的措施有机结合起来,对于强化反贫困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都具有重要意义。云南省还针对“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推动了整族识别和整族帮扶,这都是创举。
2.把握政府介入的度
贫困是嵌入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特殊社会经济现象,反贫困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本身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既要求充分发挥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主体作用,又要求国家将其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工作来审慎对待。这就既要科学对待西方反贫困理论中的个人主义,又要充分发挥其所强调的结构主义,并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最重要的是把握好结合的度,用科斯的话说,这个度的最优点就是“交易费用最小”。当然,这个度最终还要从制度选择本身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文化基础和政治基础综合考虑。中国在这样的历史节点选择脱贫攻坚的制度设计,是这几个基础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经济基础来讲,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能力把更多资源用于脱贫攻坚;从社会基础来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民孜孜追求的目标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从文化基础来讲,中国人民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伟大民族,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最重要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重要奋斗目标。
3.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从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作为具体的人来说,贫困的原因千差万别,即所谓的“贫有百样,困有千种”,但从抽象的角度讲,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生存发展条件差是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政府在推动脱贫攻坚过程中,把改善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生存发展条件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以“五个一批”为主要抓手,着力改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条件;着力发展壮大贫困人口的经济基础,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着力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提高他们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同时,通过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着力提高他们的内生发展能力,摆脱精神贫困状态;着力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在提高贫困劳动者自身人力资本含量的同时,提高他们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水平,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这既是对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和阿玛蒂亚·森可行发展能力理论的有益补充和显著贡献,更是打破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缪尔达尔贫困“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约瑟夫“剥夺循环论”以及刘易斯“贫困文化理论”的有效途径。
二、马恩列反贫困理论及中国脱贫攻坚的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贫困及反贫困理论的核心,是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贫困问题进行深刻阐释,并把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反贫困理论主要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所处时代和所关注问题的重心,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与贫困的内在联系上。他们虽然没有就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措施进行分析,但却认为共产主义制度能够从制度源头上消除贫困。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贫困和反贫困思想,并将之应用到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以便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生长的土壤。
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困及反贫困理论
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三种可能的社会生活状态①即社会财富衰落状态、社会财富增长状态、社会财富最富裕状态,详见欧阳德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贵州师范大学,2019 年12 月,第28 页。下工人阶级的地位后得出结论:“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增长的状态中,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完满的状态中,贫困持续不变。”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230 页。之所以如此,表面上是资本积累导致了在财富积累的同时,积累了贫困、奴役和劳动折磨,导致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两级分化越来越大,进而使贫者越来越贫、富者越来越富,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增殖的秘密在于资本家通过购买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不仅可以收回购买该商品时所支付的价值,而且能够通过劳动力的使用取得剩余价值。其实质是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劳动力生产的剩余价值,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而劳动者则只能获得其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基本生活资料。这种占有贯穿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整个过程,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到资产阶级手中,而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无产阶级则日益贫困。③胡联、王娜、汪三贵:《精准扶贫的理论创新——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财贸研究》2017 年第7 期。
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没有就此止步,他们进一步分析发现,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马克思称之为占有人和剥削人的制度。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使得资本家阶级占有资本和技术,而工人阶级只占有自己的劳动力,造成了资本与劳动力的分离,形成了劳动与劳动对象、劳动与劳动结果以及劳动本身的异化和分离。而正是这种异化和分离,不仅使剩余价值的生成和积累有了可能,进而富裕了资产阶级,而且使只拥有劳动力本身的工人阶级不断走向贫困化,并且这种贫困化是“无法再回避的、无法再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62 页。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要摆脱这种贫困,就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度,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2.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公有制下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除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贫困的根本症结外,还论述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公有制以后,社会能够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所创造的条件,并提出了防止贫困的基础工作,那就是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104 页。。那是因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③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39 页。。意思就是,要使所有人都富裕起来,并过上全面发展的美好生活,根本途径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同时,让每个人都富裕起来,并实现全面发展。马克思强调指出,在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组织中,“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311 页。。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会组织不仅可以让每个人获得自由发展,而且能够保证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因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273 页。。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认为共产主义公有制能够为劳动者创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基础,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程度。在这种制度基础上,通过公有制的建立,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能够实现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社会财富的真正直接占有,进而最终获得真正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而且能够让每个劳动者都在自由而身心愉悦的状态下工作,可以进一步加快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步伐。换句话说,共产主义公有制,不仅能够让“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使之“不仅成为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成为“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530 页。,更重要的是可以“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⑦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489 页。。
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讨论具有重要历史指导意义,因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既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⑧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130 页。。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当前尽管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公有制的建立已经为这样一种经济形态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都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要务,这就要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实践中,去探索发展生产力的具体有效途径,去寻找贫困治理的有效答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中国的脱贫攻坚是对马克思主义贫困及反贫困理论的原创性和独特性贡献。
3.列宁基于俄国社会主义现实的贫困和反贫困理论
尽管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也是帝国主义国家,但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要落后得多,且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造成了严重破坏,国家千疮百孔,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在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尽管“面包、自由、和平、土地”等口号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为新生的社会主义俄国提供了坚实的人民基础,但列宁(Лнин,1870—1924)也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俄国作为一个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国家,无产阶级力量“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①列宁:《列宁全集》(第4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156 页。。基于对俄国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准确判断,列宁认为,尽管共产主义是奋斗目标,但有一个过程。为此,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②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4 页。,并认为社会主义的俄国不仅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而且全国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面对这样的国情,为了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列宁认为,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生产力。首先着手解决的就是他认为“能使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得到安慰和满足的”③列宁:《列宁全集》(第3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17 页。土地问题,基本途径就是实行土地国有基础上的集体农庄经营制度。列宁认为:“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有的、集体的、共耕的、劳动组合的耕作的优越性,只有用共耕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了农民,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才能真正可靠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④列宁:《列宁全集》(第3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360 页。在此基础上,还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强调要利用科学技术力量“把最落后的农业生产纳入新的轨道,对它进行改造,把它从按照旧的方式盲目经营的农业变成建立在新的科学和技术成就基础上的农业”⑤列宁:《列宁全集》(第3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354 页。。
由此可见,列宁所主张的反贫困举措,就是要不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贫穷的俄国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而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让共耕的、劳动组合的耕作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其基本逻辑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现劳动力与土地和资本的有效结合,从而使生产力水平尽快提高,让每个人都能通过这种耕作方式获得应有的劳动报酬。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不断提高科学技术对提高生产力水平的积极促进作用。
(二)基于马克思反贫困理论脱贫攻坚实践作出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中国的农村贫困从性质上来讲不是无产阶级的贫困,更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夺造成的贫困,其根本原因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基于此,中国的农村反贫困理论除了不断提高贫困家庭的劳动力水平外,还需要不断改善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贫困群体的劳动技能、受教育水平及身体素质。这些都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理论的原创性贡献,是对列宁贫困和反贫困理论的继承性发展。
1.非无产阶级贫困是中国贫困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资本主义贫困本质上是无产阶级贫困,即贫困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其他生产要素;列宁描述的贫困尽管不是无产阶级的贫困,但也是占有其他生产要素很不平衡且生产力整体水平很低的贫困。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既从根本上解决了马克思高度关注的“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109 页。这个基本问题,又使中国的农村贫困在一定程度上是贫困劳动者与土地等其他生产要素实现了结合的贫困,其根本原因是劳动力水平低。
2.中国贫困人口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劳动力水平低
这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论述,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其中对于一些少数民族贫困人口而言,素质(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等)是关键原因,呈现出典型的能力贫困特征。也就是说,中国的贫困是劳动力与资本等生产资料实现了结合,但结合水平很低,最终导致生产力水平较低形成的贫困。这也是当年俄国贫困的明显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都强调把提高生产力水平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手段,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中国开发式扶贫的核心要义也在于此。
3.产业和就业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没有很具体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提高生产力,特别是针对贫困人口的生产力。中国的脱贫攻坚把发展产业和有效就业作为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手段,无疑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反贫困理论的重要贡献。这就是“五个一批”的第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这个手段的核心是如何提高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资料的配置效率,核心是通过产业的转型升级,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高质量配置,进而提高劳动生产力;而转移就业则直接是让贫困家庭的劳动力与其不直接拥有的生产资料实现有效结合,进而提高劳动生产力。除此以外,“五个一批”的第二个一批,即“易地搬迁脱贫一批”,核心是针对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地方,通过生态移民等手段,让贫困家庭的劳动力实现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有效结合,通俗地讲就是“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换穷业本质上就是发展和提高生产力。
4.把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作为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条件
提高生产力是反贫困的根本出路。除了通过发展生产和易地搬迁来提高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水平和效率外,中国的脱贫攻坚还围绕改善贫困者的生产生活条件做了大量工作,目标直指“三保障”,措施就是“五个一批”的其他三个一批。“三保障”为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有效结合和高效配置奠定基础。“义务教育有保障”的最终目标是提高贫困家庭新生代的劳动力素质,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基本医疗有保障”除了缓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外,目标也直指提高贫困者的健康素质和劳动力素质,从而使之与其他生产要素实现有效配置;“住房安全有保障”表面上是改善贫困家庭的生活条件,但“安居乐业”已经说明其对提高劳动力的重要作用。而作为后三个一批,不论是“生态补偿脱贫一批”,还是“发展教育脱贫一批”,都是为了提高贫困家庭劳动力的素质及其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有效结合水平,也都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任何一个执政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中国政府做到了应保尽保、应兜尽兜。这不能不说也是中国反贫困的一个独特贡献。
三、脱贫攻坚对70 年来反贫困实践的理论升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为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奠定了制度基础。而“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又使中国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富差距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反贫困实践,不仅为脱贫攻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理论支撑。而脱贫攻坚基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所形成的精准脱贫理论,则是对新中国、尤其是1986 年以来的反贫困理论的不断丰富、发展和升华。
(一)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反贫困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的状况可谓一穷二白、满目疮痍和百废待兴。贫困不仅是广大农村居民的残酷生活现实,就连刚刚获得解放的部分城市居民也基本上是一贫如洗。在这种特殊条件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消除贫困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通过公有制的建立,让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实现直接结合,为消除贫困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而“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和人民公社制度的实施,更使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而且共同成为劳动成果的主人,在一定意义上为反贫困做出了贡献。
1.公有制为消除贫困奠定了制度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基于“三座大山”是制约近代中华民族独立自强和广大人民群众大面积、持续性处于严重贫困状态的根本制度障碍的认识,在充分吸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与否是消除贫困的重要前提的科学论断,并通过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措施,实现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劳动力与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基本问题。早在1927年2月16日,毛泽东同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两个,即资本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立即实行的问题。”①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 年,第466 页。
1947 年2 月,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主张。1947 年7—9 月全国土地工作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并提出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1208 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共同纲领中明确把中国走向“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作为基本内容。②吴齐:《毛泽东土地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7 年,第55 页。这从思想上和制度上奠定了土地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作用。而在让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之后,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重要的政策就是土地的共同经营,具体措施就是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的公社化运动。
2.实现“共同富裕”是重要奋斗目标
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消除贫困奠定了制度基础,但需要通过具体措施来实现,这就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毛泽东主席1955 年7月31 日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首次提出的。毛泽东主席指出:“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③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见张秋锦主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三农”问题的部分论述》,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年,第217—218 页。1957 年6 月19 日,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强调:“共同富裕”即在几年内“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④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见张锦秋主编:《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344 页。。由此可见,“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农民与贫困做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不仅具有实践指导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就是合作化及现代化。
3.现代化是提高生产力、消除贫困的根本道路
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并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迫切需要提高社会生产力,具体道路就是实现现代化。1954 年9 月15 日,毛泽东主席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时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9 月23 日,周恩来总理在这次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从“摆脱落后和贫困”必须具备的条件出发,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1959 年末至1960 年初,毛泽东主席提议加上国防现代化。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⑤《历史上的今天:1949—2019》,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124165。1965 年1 月4 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正式把“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目标。
(二)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实践的理论创新与不足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开发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大规模减贫的主要推动力量是提高生产力带动的经济增长,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贫困家庭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这除了坚持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外,还得益于因地制宜所推动的开发式扶贫。对此,许多学者做了较为深入的概括和总结,如汪三贵和曾小溪的研究发现,“通过实施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在帮助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助于缓解日益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和缩小贫困地区与一般地区的发展差距,使原本不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过程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益贫的性质”⑥汪三贵、曾小溪:《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改革开放40 年中国扶贫政策的演进及脱贫攻坚的难点和对策》,《农业经济问题》2018 年第8 期。。换句话说,中国过去长时期的区域减贫战略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减贫战略,区域瞄准也因此成为扶贫资源到达穷人的一个“利器”①M.Lipton,M.Ravallion:Poverty and policy.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5.,对于贫困地区农户的收入增长有较大带动作用②A.Park,S.Wang,G.Wu:Regional Poverty Targeting in 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2,86(1).。这是因为开发式扶贫为所有农户特别是那些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贫困农户,提供了依靠自己的主动响应来增加收入的机会。③贺雪峰:《中国农村反贫困战略中的扶贫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18 年第3 期。
从理论上讲,这种扶贫方式也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有益补充。因为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制度选择的首要准则就是制度成本较低,或者说交易费用为零。可以想象,如果要对2011 年中国农村的12238万贫困人口进行建档立卡,且不说其精准性如何,仅就其操作成本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仅2014 年,全国就组织了80 万人深入农村开展贫困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而当年全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大概是7017 万人;2015—2016 年,全国又动员了近200 万人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工作④黄承伟:《深刻领会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http://dangjian.people.com.cn/nl/2017/0823/c412885—29489835.html。,而2015 年全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了5575 万人。但当贫困人口越来越少时,贫困地区扶贫资源外溢到非贫困户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而非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又会被排斥在扶贫资源受益对象之外,最终导致扶贫效率降低。这个时候,以贫困程度深的村为单位进行扶持就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这是因为,中国的村庄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社区,是中国行政区划体系中最基层的一级,有相对完整的组织结构。在村一级实施扶贫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既有利于改善贫困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也有利于村民的直接参与⑤汪三贵、曾小溪:《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改革开放40 年中国扶贫政策的演进及脱贫攻坚的难点和对策》,《农业经济问题》2018 年第8 期。,因此能够提升扶贫效果。
然而,不论是以贫困县为瞄准单元,还是以贫困村为瞄准单元,都不是针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家庭的扶贫机制。而随着贫困人口的持续减少,尤其是将消除绝对贫困人口作为既定目标的时候,也会发现过去以贫困县和贫困村为单元的贫困瞄准机制存在不少问题,一是这种瞄准机制很难让贫困者现身,导致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问有多少贫困户,还可以回答个大概齐;要问谁是贫困户,则大多是说不准。”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年,第61 页。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保证扶贫资源的精准投放或者说靶心瞄准,从而使扶贫项目充斥着“大水漫灌”的问题,真正贫困的群众没有得到帮扶的现象屡见不鲜⑦王世恒、朱家玮、杨茹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习近平脱贫攻坚思想研究》,《三峡学院学报》2018 年第5 期。,最终使扶贫目标难以实现。二是扶贫资源容易渗漏到非贫困人群,尤其是村庄里的一些精英人物身上,导致所谓的“精英捕获”⑧谢治菊、谢颖:《谁更愿意当贫困户》,《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21 年第1 期。,结果是富人受益更多、穷人受益有限,扶贫开发在缩小区域间差距的同时,也加剧了贫困地区内部的机会和收入不平等,并产生“逆向激励”作用⑨李小云:《我国农村扶贫战略实施的治理问题》,《贵州社会科学》2013 年第7 期。,最终甚至会使村庄的社会资本被侵蚀,导致好心办不了实事和好事。三是容易导致帮扶工作出现盲点、甚至盲区,进而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党的形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区域开发转向精准扶贫,瞄准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不仅是完成脱贫攻坚目标的必然选择,而且是完善贫困治理机制和治理理论的必然选择。
(三)脱贫攻坚对中国反贫困理论的升华
脱贫攻坚作为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关键一役,以坚持党的领导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根本保障,以“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为主要目标,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以多方协同攻坚的大扶贫和发挥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为基本着力点,以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和贫困地区的社会生产力为总体要求,促使贫困人口与贫困地区的发展要素与外部输入要素有机结合,在使贫困家庭和贫困地区发展条件得以持续改善的同时,实现了贫困家庭和贫困地区生产力水平的快速健康提升,最终使脱贫攻坚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在这背后,也标志着中国贫困及反贫困理论的升华。
1.与时俱进选准帮扶单元
绝对贫困具有集中性、相对性和原生性①叶敬忠:《中国贫困治理的路径转向——从绝对贫困消除的政府主导到相对贫困治理的社会政策》,《社会发展研究》2020 年第3 期。等特点,其评价标准和扶持标准既有绝对性,也有相对性。当贫困面较大,或者对于贫困面较大的地区,一开始就把对象锁定在贫困家庭上既不必要也不科学,只针对贫困家庭的反贫困措施也很难奏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甚至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贫困状况就属于前者;而到了国家正式开始项目扶贫时,情况就属于后者。这是中国采取开发式扶贫的原因之一。而从扶贫工作单元上讲,为什么要把贫困县、贫困村与贫困人口一起作为对象,也与开发式扶贫的要求相衔接。但当绝对贫困问题面临扫尾之时,就必须进一步缩小帮扶工作单元,帮扶方式也不能再以开发式扶贫为主,而必须以攻坚式扶贫为主。这是脱贫攻坚对中国反贫困理论的一大贡献,即当帮扶工作重心转向完成消除绝对贫困人口这一既定目标后,必须把工作单元锁定为贫困户,把帮扶对象的重点转移到贫困人口上。从这个角度讲,足见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把握扶贫工作全局的敏锐洞察力。
2.毫不动摇彰显制度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为中国取得脱贫攻坚战历史性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和制胜密码。最核心的是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不仅把扶贫工作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的首要政治任务来抓,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贫的格局,而且形成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协同共振的大扶贫格局。脱贫攻坚战已经成为全党全国的第一民生工程,是真正意义上的举全国之力。在这背后,脱贫攻坚与过去近30 年的扶贫开发最显著的变化是,不仅扶贫资源投入力度空前,而且扶贫力量集中空前,更重要的是重视程度空前。而其所带来的变化,不仅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而且使贫困家庭的生产生活条件和贫困地区的发展条件得到显著改善。更重要的是,探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道路和治理理论,还为未来的“三农”工作培养了一批能征善战和敢打能打胜仗的队伍,并明显改善了党群干群关系。这是中国毫不动摇地彰显制度优势的结果。
3.持之以恒提高生产力水平
扶贫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发展问题,它不仅是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而且是全国整体上的发展问题。反贫困因此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工作重点。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要求,也是西方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中国的反贫困始终把提高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作为重中之重,使脱贫攻坚找到了最有效的手段,那就是“五个一批”。这五个一批,既有直接提高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生产力水平的,如“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和“易地搬迁脱贫一批”,也有为提高生产力水平奠定基础的,如“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和“发展教育脱贫一批”,还有为提高生产力水平托底的,如“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这“五个一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仅能够为贫困家庭找到有效的发展道路,而且能够帮助贫困农户和贫困地区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而提升整体社会生产力水平。近年来贫困地区与非贫困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得以遏制就是最好的说明。
4.因地制宜强化内外合力
反贫困需要内力和外力的同频共振、协同发力并形成合力。中国脱贫攻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合力,其中关键之关键是找到了抓手,这就是“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和“四个问题”。这个“六五四”工作法不仅准确界定了帮扶对象和帮扶主体,而且明确了帮扶内容和帮扶措施,且有行之有效的监测评价和执纪问责作为保证,这一方面启动了帮扶对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毕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另一方面压实了帮扶主体的责任。动力与压力的有效结合,在很多情况下就形成了向心力和合力。而为了达至脱贫目标,各级党委政府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提高帮扶对象的发展动力和可行发展能力,而得到的回报就是“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出路”。这又为高扬内生动力、形成更强合力注入了新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