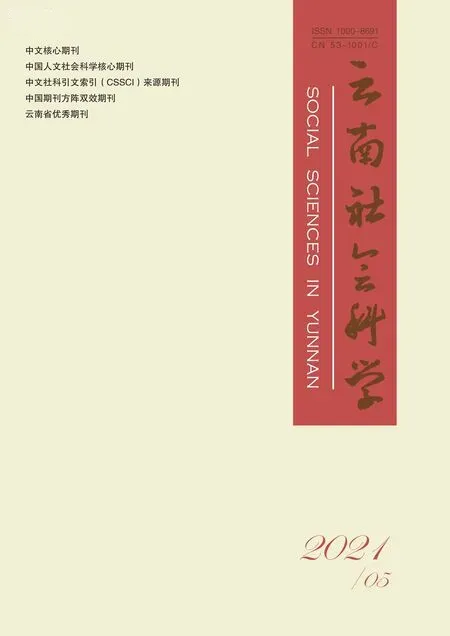人工智能就是认识论
肖 峰
人工智能具有学科上多重性或“多面孔”的特征,它是科学(计算科学的一个分支,一门为了模拟人的智能而研究心灵如何工作的科学),也是技术(在计算机上实现智能模拟的技术,智能机器、机器人等是其作为人工物的技术,算力、算法、数据挖掘等是其核心技术),因此它具有科学与技术一体化的特征,“它指的是计算机科学和机器人技术的一个共同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研究目标是开发能够执行需要人工智能才能完成的任务的系统。”①Flasinski,m.,Introduction to Artifcial Intelligence,Switzerland: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6,p.236.不仅如此,人工智能具有工程的特征,它是不断走向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工程,是日益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并取得经济效益的社会工程;同时人工智能也具有哲学的属性,尤其具有哲学认识论的特征,以至于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工智能就是认识论,从而认识论也是它的“多面孔”之一。人工智能的这些综合特性中,其认识论特征通常被关注较少,而把握这一特征对于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人工智能的意蕴可提供新的启示。
一、在什么意义上人工智能就是认识论?
可以从学科相关性、对象相关性、根基相关性以及终极追寻的相关性等维度上来理解人工智能就是认识论。
从学科上看,人工智能和哲学(尤其是认识论)都可以与认知科学相关。认知科学作为“理解大脑行为”和“揭示心灵奥秘”的研究领域,由六大学科(哲学、心理学、人工智能、语言学、人类学和神经科学)交叉而成,这些学科集合成为认知科学时,就具有了力求把握人的思维认识活动内在机制的共同使命和学术指向。当人工智能最初被纳入认知科学时,那些早期的人工智能理论家也就被归为认知科学家,具有广义认知能力的机器人被称为“认知机器人”,这样的认知机器人力求被设计为能够学习并应对复杂的情况从而在没有人的直接帮助下完成开放式任务,由此就有了“cognitive science AI”即“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的说法。②Uddin,m.N.,“Cognitive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Cognitive Computation and Systems,Vol.1,No.4,2019,pp.113-116.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不是一件东西,而是某些系统的一种属性,就像移动机器人的移动性是允许它们移动的一种属性一样。第二种意义上的人工智能是一门名为认知科学的学科的研究主题,而不是计算机科学或机器人技术。”①Flasinski,m.,Introduction to Artifcial Intelligence,p.236.更进一步看,如果狭义地理解“认知”,即从“信息处理”或“计算—表征”的意义上理解它,所形成的“第一代认知科学”和符号主义范式的人工智能就具有直接同一性,这就是认知哲学家豪格兰德(John Haugeland)所说的:“关于认知科学的一种思考方法是狭义地理解‘认知’一词,并将人工智能作为其本质,那就是物理符号系统的假设,或者我所说的‘好的老式人工智能’。其基本方法是研究如何通过合理地操纵符号表示来实现智力成就,这是根据这种狭义概念进行认知的本质。”②Haugeland J.,“Farewell togOFAI?”in Baumgartner,P.and Payr,S .eds.,Speakingmind:Interviews with Twenty Eminent Cognitive Scientis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101.
在人工智能与认知科学具有某种同一性的基础上,还可以看到认知科学与认识论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同一性,即认知科学一定意义上就是认识论。这主要表现为:第一,现代意义上的认知科学出现以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哲学家是唯一的认知科学家”③Churchland,P.m.,“Neural Networks and Commonsense,”in Baumgartner,P.andPayr,S.,Speakingmind:Interviews with Twenty Eminent Cognitive Scientis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33.,认知科学(包括心理学)所研究的内容都是由哲学认识论来承担的。第二,在现代意义上的认知科学出现后,认识论研究领域中随之也出现了用认知科学取代认识论的自然主义趋向。“试图通过把哲学问题与科学发现联系起来来回答基本问题,这种方法被称为自然主义。”④Thagard,P.,The Brain and themeaning of Lif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5.当然不能赞同用认知科学取代认识论的极端化的看法,但其中所揭示的两者之间具有紧密关联这一事实则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第三,“认知”和“认识”本身就是含义交叉甚至高度重叠的,认知既要研究动态的认识,也要研究静态的知识,而认识论同样如此,它甚至就被界定为“知识论”。总之,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和认识论都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同一性这种特殊关系,使得人工智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认识论这一论题具有了学科意义上的理据。
概而言之,从学科的视角看,人工智能和认识论都可以统摄于认知科学这个共同的领域之下,它们都是“心智研究”这个大家族的成员,无非是研究的方式或手段有所不同:认识论是以哲学的方式研究心智,而人工智能则以计算机科学的方式研究心智,并将这种研究的结果再用于模拟和延展人的心智。
从学科上,还可以从“人工智能就是哲学”的意义上来理解人工智能就是认识论。意大利机器人专家斯查冯拿地(Viola Schiaffonati)认为“人工智能和哲学被认为有很多共同之处”⑤Schiaffonati,V.,“Framework fo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Artifcial Intelligence”,minds andmachines,Vol.13,No.5.2003,pp.537-552.,心智哲学家丹尼特(Daniel Dennett)则更明确地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人工智能就是哲学。它经常直接涉及到那些一眼就能认出来的问题:心灵是什么?意义是什么?什么是推理和理性?在知觉中识别物体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如何做出和证明决策?”⑥Dennett,D.C.,Brainchildren.Essays on designingminds,Cambridge:ThemIT Press,1998,pp.265-266.美国哲学家格莱默尔(Clarkglymour)在一篇标题为“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Philosophy”的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人工智能就是转化为计算机程序的哲学解释。从历史上看,我们所视为的人工智能兴起于将哲学家所提供的解释所进行的可计算化的延展与应用。”⑦Glymour 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Philosophy,”in Fetzer J.H.,ed.,Asp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Springer,Dordrecht,1988,p.195.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必然与哲学相逢,与哲学问题相交织,而人工智能所涉及的哲学问题大量的是认识论问题,与人工智能的研究直接相关的哲学问题则主要是认识论问题,以至于“人工智能和哲学通过认识论相联系”⑧董军、潘云鹤:《人工智能的认识论问题》,《科学》2002 年第4 期。。所以当人们说人工智能就是哲学时,无疑也是在一定意义上主张人工智能就是认识论。
上述相关性也可以说源自于两者在研究对象上的相关性。认识论以人的认识(心智)为对象,而人工智能所模拟的就是人的认识(包括行为,它属于广义的认识,即知和行的一体化存在),所以人工智能是在人工技术装置上呈现出来的人的认识现象。研究对象的相关使得两者也具有共同的旨趣,人工智能所追求的主题正是哲学认识论千百年以来不断追求的目标,两者所做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同一性,就是要搞清楚心灵是如何工作的,即人脑认识活动及智能活动的本质和机理,然后由AI接着进一步在计算机上通过技术手段去实现它。人工智能也被称为“知识工程”,涉及知识的获取、学习、表达等问题,这些也完全与作为知识论的认识论相吻合,只不过前者是使用了另一套术语(形式化语言)来表达的认识论。所以人工智能包含大量的知识论问题:知识的获取问题(通过输入程序来获取,还是通过机器学习来获取)、知识的表示问题(通过符号来表示还是通过联结机制来表示,技能知识如何表示)、知识发现问题(数据挖掘中的知识发现,以及人工智能是否具有发现新知识的能力)、人工智能如何具备常识问题或背景知识、专家的知识如何在AI系统中得到有效应用等问题。这些知识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过程,也就是人工智能对人的智能(认识现象)现象加以研究和模仿进而创建机器智能的过程,所以它无疑具有以人的认识(智能)为研究对象的特征,从而具有认识论研究的特征,只不过它的路径和方法不同于哲学认识论。可以说两者的起点相同而终点不同:人工智能以理解人的认识为起点(与哲学认识论相同),以科学技术的方式建造出人工认识现象为终点(与哲学认识论不同)。由此也表明,说人工智能就是认识论,并不意味着要将人工智能完全归并到哲学认识论中,而是指出两者之间具有交叉重叠但又各有独特性的关系。
这种对象上的相关,使得人工智能和认识论之间具有部分相似的工作原理,或在符号加工上,或在结构涌现上,或在感知—行为上,形成人脑的认识过程和人工智能中的信息处理过程具有局部相似的运作机制,这些局部相似性如果最终通过通用人工智能融汇为整体相似的工作机理,就使得人工智能不断趋向与人脑认识机制的全面相似,从而在人工智能中就越来越完整地呈现出认识论所刻画的人的认识样貌。人工智能和认识论的共同目标,也使得人工智能成为认识论问题探究或解决的一种方式:人工智能专家即使没有使用认识论的术语或引用哲学家的文献,也在直接或间接地为解决某些认识论问题做出贡献。
这种机制上的相关,也可通达“根基”意义上的相关。为了获得对认识机制的理解,人工智能要建立在一定的认识论根基上。人工智能在派别或技术路线上的分野,从基底上就在于它们所秉持的认识论立场不同。如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人工智能就分别秉持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具身认知等不同的认识论立场。这表明人们如何理解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从哲学认识论上理解自己的认知、智能、心灵等。如果将其理解为理性的推理,就会有表征—计算的认知观和人工智能的符号主义进路;如果将其理解为归纳和学习,就会有对人工智能的联结主义阐释;如果将其理解为对环境的灵活应对,就会有具身的认知观和对人工智能的行为主义开发。可见人工的智能范式之分归根到底就是认识论上的流派之别,体现着哲学上不同的认识本质理论,其背后反映着不同的哲学认识论对人工智能走向的影响甚至引导。不同人工智能范式的开发者,就是不同的认识论或认知观的秉持者,他们虽然不是直接用哲学语言来表述其认识论思想,但因其背后总是主张了某种认识论立场,或支持了验证了某种认识论理论,而成为特定认识论的“代言人”或“推广者”,犹如用数字化语言讲述了不同的认识论故事。所以从根基上,人工智能与认识论是紧密相关的。这一点也可以从“前提”的意义上来理解:人工智能是以认识论为前提的学科,因为它要模拟人的认识和智能,前提是要知道认识和智能的本质是什么;人工智能要技术性地实现人类智能,就先要理解智能,从而就要触及认识论的主题,从认识论中获得启示。这样,不同的人工智能范式,无论是自觉地还是自发地、有意地还是无意地都要受某种认识论原则的支配。否则,人工智能就不知道自己要模拟什么,进而也不会知道如何去模拟。
当然,人工智能在发展中也不断扩展着自己的体系,如在学科上也演进出不同的层次,以至于今天有了理论人工智能,实验人工智能和应用人工智能之分。①David E.,“Rumelhart,From Searching to Seeing,”in Baumgartner,P.and Payr,S .,eds.,Speakingmind:Interviews with Twenty Eminent Cognitive Scientis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197.如果承认这样的层次划分,那么至少其中的理论人工智能无疑更具认识论的属性。理论人工智能是整个人工智能的基础,而认识论则是基础的基础。不包含任何认识论理念的人工智能是不可能存在的。人工智能在基础研究中所涉及的概念和问题基本上都是认识论的概念和问题,或具有高度的交叉性,如同荷兰哲学家穆勒(Vincent C.müller)所说:“人工智能中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工程学科,它引起了关于计算、感知、推理、学习、语言、行动、互动、意识、人类、生活等性质的非常基本的问题,同时对于回答这些问题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事实上,它有时被视为一种实证研究)。”②Müller,V.C.,“Introduction:Philosophy and Theory of Artifcial Intelligence”,Minds &machines,Vol.22,2012,pp.67-69.这里列举的概念显然与认识论所使用的概念高度重合,对这些概念加以人工智能视角的理解和意义拓展,显然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深化或拓展认识论的基础研究。所以,从认识论是人工智能的基础这一关系上,人工智能在根基的意义上具有认识论的性质。
这种根基上的相关还可进一步引申为“极致”(终极)意义上的相关。技术的极致是科学,科学的极致是哲学,人工智能的极致就是认识论,这一点尤其表现为人工智能的终极难题就是认识论难题。一些关于人工智能限度的争论,也是既有认识论问题的翻版,如计算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为什么计算机能做一些事情而不能做另一些事情,实际是关于认识和意识的本质、认识的能力和限度等问题的延续。如同人工智能的创始人之一麦卡锡(JohnmcCarthy)所说:人工智能有它的认识论部分,所研究的是世界的哪类事实可提供给哪些特定的观察者,研究这些事实如何在计算机上表达出来,研究可以据此合理地得出哪些哲学结论。③Mccarthy J,“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JCAI'77: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Vol.2,August 1977,pp.1038–1044.一旦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认识”功能或智能模拟的本质有了透彻的理解,则对认识论的传统问题也就有了新的视域和新的理解。可以说,人工智能的一些核心理论问题,就是延展了的认识论问题,如人工智能是否有意识,是否可称为自主的主体,是否有自由意志,凡此种种,表明了人工智能的理论研究终究要通向认识论问题,其中的一些认识论问题可称为人工智能的终极问题,这样的问题也是所谓的形而上学问题。可以说认识论就是人工智能的形而上学,它是关于智能现象的最普遍的哲学学说。它一面可以从人工智能中提升而来,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到人工智能中去,这样的“环路”关系也构建了人工智能就是认识论的一种专门语境,它使人可以实现将人工智能作为科学技术来看待到作为认识论来看待的智力提升,后者导向了从终极性上去阐释人工智能的意蕴。
当然,同中有异,人工智能与认识论并非全然等同。丹尼特认为“这两个领域之间唯一明显的区别是AI 工作者将(认识论研究者的——引者加)扶手椅拉到了控制台边”④Daniel,C.D.,Brainstorms:Philosophical Essays onmind and Psychology,Cambridge:ThemIT Press,2017,p.120.,从而需要在计算机上通过编程活动等去具体地实践某种认识论构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认识论就是一种简单的工作,在丹尼特看来,人工智能对认知的研究要精心地进行算法和程序系统的设计,哲学家则是对普遍性的问题进行探究,后者往往更为棘手。⑤Daniel,C.D.,Brainstorms:Philosophical Essays onmind and Psychology,p.122.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认为人工智能是被嵌入了特定的建模范式从而具备特定的认知功能的人工认知系统,所以它是物化的认识论,是人的认识功能的部分移植,它至少具有局部性地遵循认识规律的特点。从这些“限定”中也可以看到人工智能与传统认识论在同一性中的差异性:“认识论和人工智能是相辅相成的学科。这两个领域都研究了认知关系,但是人工智能从理解旨在建模某种认知关系,或从模型的框架形式和计算特性的角度来研究该主题,而传统的认识论从理解术语的认识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该主题。”⑥Gregory,R.W.,Pereira,L.m.,“Epistem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ournal of Applied Logic,Vol.2,No.4,2004,pp.469-493.因此可以说它们是以不同的方式从事着前后相继的认识论事业:搞清智能的奥秘,然后在机器上模拟它、人工地实现它,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人工智能比哲学认识论走得更远。
二、人工智能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认识论
人工智能作为认识论,具有使认识论研究科学化、实验化、技术化、工程化的特征,从而呈现出科学认识论、实验认识论、技术认识论和工程认识论的特征。
(一)人工智能作为科学认识论或认识论的科学化
人工智能作为科学化的认识论可以从多种维度来理解。
一是从它本身作为一门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如麦肯锡所言:“正如天文学继开普勒发现了天体运行规律之后取代了星相学一样,对机器的智能过程的经验论方面的探索所发现的众多原理将最终导致一门科学”①Minsky,m.L.,Papert,S.,Artificial intelligence,Oregon State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distributor:Distribution Center,University of Oregon,1973,p.25.,这门科学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科学的属性决定了它在作为一种认识论时,必然将科学的特征(如实证性、可观察性以及后面所说的实验性等)、规范和要求带入到认识论研究之中,使得人工智能在作为认识论时,也不是以传统方式表现的认识论,而是结合了计算机科学的认识论,从而是一种特殊的科学认识论。在这种认识论中,通过人工智能的科学原理来揭示认识的机制,所借助的是科学手段,使用的也是符合科学规范的陈述,形成的是关于认识研究的“科学成果”,这和采用人文手段研究人的认识所形成的“人文认识论”或“生活认识论”等具有区别,由此具有了科学化的特征。
二是它的特定学派还以一种特定的科学视角来看待认识的本质,这就是符号主义人工智能从计算—表征的视角看待认识的本质,并形成了计算主义或认知主义的认知科学。这种认知科学也通过如前所述的“自然主义”进路而成为“科学化”了的认识论,更贴切地说是一种认知科学化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中,认识的语言变得符号化、表征化,认识的过程变得逻辑化、形式化、程序化,成为清晰可分析的对象,从而成为可算法化然后由机器去执行即运算。在这种框架中,人工智能对认识论的显现不是采用哲学表达的方式,而是基于数字化语言的科学表达或计算机语言的精确描述,所以在“认识论表示”上两者是不同的。
三是从人工智能所模拟的主要是科学认识的角度去理解。人类的文化可区分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作为文化现象的人类认识也可以大致区分为科学认识和人文认识。作为认识论的人工智能,目前更偏向于对人类科学认识的模拟,还拙于对人文认识的仿真。人工智能作为科学认识论的这种表现或特征既是认识论研究的一种进步,即对认识的本质和机制融入了更多的科学成分和根据;同时也是其局限,就是在强于对那些规则的、理性的、精确的认识加以理解和模拟时,还弱于对日常生活中那些模糊的、非逻辑的、容错的认识的理解和模拟。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对人工智能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对符号人工智能的这种只具“科学能力”而不具“人文能力”之局限的不满。所以人工智能要成为一种全面的认识论,还需要在具身、情景、主客体互动、理解人的情感等人文或生活维度上不断拓展。
(二)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实验认识论或认识论的实验化
从学科性质上,人工智能虽有基础理论研究,但总体上不是空而论道的纯理论,不是扶手椅上的学问,而是“干中学、干中试”的技术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动手去做”的实验性和实践性,要有通过实验而形成的产品以及实际有效的应用作为其存在和成功的标志,因此它具有学科属性上的实践性,从而在作为认识论时也就具有“实践认识论”或“实验认识论”的性质。
人工智能作为实验化的认识论与认识论的科学化相关。首先它是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成果通过算法和程序而形成的结晶,编程就是在进行将智力创新的成果转化为机器可理解可执行的知识形态的一种特殊实验。当人们说人工智能的实质之一就是“有多人工,就有多智能”时,就蕴含了它是特定人工系统中人类智能的集合,而智能程序的运行,犹如凝结于其中的认识能力被纳入到技术性的实验过程之中。尤其是处于研发阶段的人工智能的新设计、新构想、新算法,就更是被置于人工装置上不断加以实验和改进的知识产品。哲学认识论还探究人的潜在的无限的认识能力,而人工智能则在机器上不断扩展人的现实认识能力,使得哲学追求的无限认识能力可以通过AI 作为实验室去逐步加以趋近,使得人类的“认识论理想”得到实在的展现。犹如“虚拟实在是形而上学的实验室”①[美]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仑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86 页。,人工智能堪称认识论的实验室。
人工智能在推进认识论研究时还具有作为认识结果之检验平台的功能。进入到实验运行过程之中的人工智能方案和构想,作为认识的成果,其是否成功和有效,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使用得以检验。这实际上也是将人工智能构想背后的各种认识论主张通过人工智能的实践或实验来进行“试运行”,通过相关的算法能解决什么问题和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实际结果,来考察其中贯穿的认识论理论是否有效。认知哲学家萨迦德(Paul Thagard)认为科学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计算方式得到解决;在德雷福斯看来,计算机使认知主义传统成为研究程序成为可能,就像连接主义使经验主义、联想主义传统成为可能一样,从休谟到行为主义,都可以成为研究程序。②Dreyfus,H.L.,“Cognitivism Abandoned,”in Baumgartner,P.and Payr,S .,Speakingmind:Interviews with Twenty Eminent Cognitive Scientis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73.总之,通过程序的运行可以检验出一些认识论观点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还可以通过设计新的计算原理或新的计算结构来实现关于认识机制的设想,并通过成功还是失败的模拟来检验这种关于认识机理的设想是否正确,如此等等。由此一来,认识论也可以得到人工智能的某种“改造”,它不再仅仅具有思辨的无法检验的性质,而是成为可以依托人工智能的手段加以验证的可检验理论。正是借助各种范式的人工智能,看到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具身认知在何种场合下是有效的,以及在超出了何种场合时又是失效的,这就是对不同的认识论学说的适用范围起到了验证的作用。
丹内特将人工智能程序看作是由计算机进行假体调节的思想实验,他认为一些AI 人士将自己的学科描述为“实验认识论”还不确切,而应更确切地称人工智能为“思想实验认识论”,通过AI 的思想实验所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关于人们是否可以从某些设计中获得识别、推理或进行各种控制的认识能力。③Daniel,C.D.,Brainstorms: Philosophical Essays onmind and Psychology,pp.127-128.人工智能所具有的“思想实验”的特征,还通过“图灵测试”和“塞尔的中文屋”等,将更为基本和深层的认识论问题(如智能究竟是什么)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引发了迄今仍在持续的争论和探寻,形成了无数的试探性阐释,成为当代认识论不断扩展的新维度。
人工智能具有的实验认识论的特性,对认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包括可以借助这一特性来使认识论研究的方法走向多元化。神经哲学的开创者丘奇兰德(Paul Churchland)指出,哲学认识论研究者一直以来都是以一种非经验主义的方式追求他们的兴趣,很难说明认识活动的大脑机制。而有了计算机后,人就可以在人工系统中比在自然系统中更容易地试验和探索神经网络的特性。人工智能所重新创造和理解的生物的认知能力,驱动人们不断接受认识论的新理论,包括关于感知的新理论、心灵本质的新理论等。④Churchland,P.m.,“Neural Networks and Commonsense,”in Baumgartner,P.and Payr,S .,Speakingmind:Interviews with Twenty Eminent Cognitive Scientis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33-39.
(三)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认识论或认识的技术化
“技术认识论”的含义有多重,如技术作为一种人工物的发明和设计活动,其中包含大量的认识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也包含有“发明认识论”“设计认识论”的意蕴。这里笔者重点探讨的是另一重意蕴:人工智能在机器上技术性地实现了人的某些认识过程,当作为技术的人工智能模拟了人的认识之后,就带来新的认识论问题,这就是以人工智能为载体的认识与人的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更广义地说就是技术化智能与生物智能的关系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性地再现”了人的部分智能,它作为人造物上的认识论现象,是人的某种认识能力的技术化再现,如符号人工智能再现人的推算能力,联结主义范式的人工智能再现人的学习和识别能力,智能机器人再现人的感知—行动能力,等等。总之,人工智能就是“用电脑做一些人们用心智能够做的事情”①Dreyfus,H.L.“Cognitivism Abandoned”.,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旨在通过计算机来逼近人类认知的技术,它是人的认识(广义的还包括行为)的人工化、技术化后的产物。探讨人工智能的认识论问题,必须看到这是一种以人工的技术为平台而展开的认识论,电子化、数字化、网络化、程序化、形式化等技术特征贯穿于其中。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当人的一些认识过程或能力可以依托人工智能这一技术得以再现或模拟时,可否认为智能现象也能在技术载体中涌现出来,犹如人的智能从人的身体(尤其是人脑)中涌现出来一样?后者被称为“认知的具身性”或“具身认知”(当然也就包含“具身智能”),那么前者是否可称为“认知的具技性”或“具技认知”及“具技智能”?显然弱人工智能还难以称为具技智能;换句话说,目前的机器认识论还是无心认识论,因此留下了机器认识如何走向“用心思考”的难题与前景。未来的强人工智能(尤其是当人工智能有自我意识和意向性等属性后)中,当它们的技术载体从功能上具有生成智能的条件后,当这样的技术可以相当甚至超越人的身体时,“具技智能”或“具技认知”(以机器为认识主体、机器也可以“用心”思考)就成为不能被忽视的认识论现象,此时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认识论不仅对认识论研究具有辅助的价值,甚至具有主导的意义,这也是人类认识日趋技术化的一种必然走向。②参见肖峰:《认识论:从自然化到技术化》,《哲学动态》2018 年第1 期。当然,具身认知和具技认知的融合,也是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认识论的未来走向。
此外,即使在当今的弱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技术化的信息处理过程也具有认识论的“镜像”意义。可以说人工智能一开始就具有认识论的技术化镜像之功能,它使人的认识活动机制在一种人工技术系统中得以投射,具体说就是使认识过程通过计算程序表达出来,使认识的方法通过算法得以展现出来,使人脑工作的模式或原理通过人工智能的范式或模型实施开来,从而将人的认识加以对象化或客观化,使得认识论研究基于传统手段的许多不可能变为可能。如人脑作为认知的器官就不能作为活体被打开来研究其中的“活生生”的认知活动机理,而借助电脑这个镜像则可以使不能被直接观察的人脑内在认识过程及其机理以一种技术运作的方式成为可以直接观察的外在过程。再如,人们对自己的大脑如何加工处理信息的机制理解甚少,但是对电脑如何下棋的学习的机制则理解得非常深入,由此可以通过电脑的机制(作为技术镜像)来启发和帮助人们理解人脑工作的机制。人工智能这个技术镜像目前虽然还不能全面反映人的心智,但对各种模型、算法、范式的综合与拓新所形成的人工智能迭代演进,可以逐步趋向对人的认知或心智活动的整体性把握。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人工智能的机制,就是在通过镜像去理解人的认识的机制,就是在进入和解决一系列认识论问题。
(四)人工智能是一种工程认识论或认识论的工程化
“工程”是“技术”的规模化、实用化,也包括这个过程中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人工智能是一种蕴含价值追求的认识论追求,和其他技术一样,人工智能只有通过规模化的应用(由技术转化为工程和产业)才能兑现其“价值红利”。所以在从技术走向工程的过程中,人工智能也展现出从技术认识论延展到工程认识论的重要特征。
作为工程认识论,人工智能重在技术的社会实现,关注一种新理念、新构想、新设计的产品化、实用化、效益化,也就是体现出对“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过程中“认识回到实践”或“认识的目的是实践”这一原则的落地。人工智能研发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将其新设计的新算法、新软件等开发为可以为社会工程化使用的技术。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处于从技术爆发到深度应用的阶段,也体现出它的当前主题是使AI 技术化的认识成果进一步转化为工程化的认识成果。可见,人工智能作为技术认识论的延伸,还具有工程认识论的性质。
人工智能作为工程认识论的特征还表现在它作为人类开启的一项重大的智能模拟事业,所要攻克的难关、解决的难题十分巨大,必须动员和组织相当规模的人力和物力才能展开,所以它在许多国家都是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并以重大的国家工程加以启动和管理的,其中的智力协作、联合攻关、有序和谐等就是具有大工程性质的科技研究事业所必须贯穿的认识论原则。
人工智能作为工程化的认识论,也存在于将部分形式化的认识过程在机器上加以机械化、自动化,从而实现规模化和效益化,借助这种工程化的推进,可以使一部分脑力劳动的效率大大提升,完成过去仅以人的智力所无法完成的认知任务,并获取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所以麦卡锡将专家系统的构建直接称呼为“认识论工程”,有的专家还将其界限为“与‘机器智能’建设有关的一个工程分支”①Baumgartner,P.and Payr,S.,Speakingmind:Interviews with Twenty Eminent Cognitive Scientis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11.,在中国的新学科建设中还将它归为“新工科”。这些称谓表明,人工智能可以使人的认识活动被工程化,以工程的方式解决认识(信息处理)问题,由此构成智能时代人类的知识发现和信息生产能力得到巨大提升的生动图景。
机器智能作为一种社会工程,它通过广泛且深入地介入世界而产生实在的巨大的社会效果,使得人工智能作为工程认识论,也是社会认识论。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辅助甚至替代人的智力工作是以工程化的方式大规模展开的,在未来的这种替代甚至构成为席卷一切领域和行业的“社会工程”;人工智能所具有的“像人一样思考”和“像人一样行为”的功能,以及对这些功能的集约化提升所形成的“超人”般的认知和行动能力,无疑会对人自身的工作和生活形成巨大的冲击。所以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具有工程性质的认识论事业,对人类的影响是重大而深刻的,它和社会认识论所追求的对社会问题的合理认识与有效解决的目标是一致的。
上述关于人工智能作为科学化、实验化、技术化、工程化认识论多重视角,其整合可以拓展和加深人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从这种“跨界认识论”的属性进一步看到它作为一门学科的综合性和交叉性,而哲学无疑是它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领域。
三、人工智能拓展认识论新视界
“人工智能就是认识论”还揭示了人工智能与认识论之间具有协同前行、相互拓展的关系。
一方面,这种关系表现为人工智能需要经受认识论分析,如人工智能也有认识来源、认识对象、认识过程、认识本质等问题,只不过是以机器为载体来展现这些问题的。就认识过程来看,机器可以学习、可以识别、可以感知、可以推算,还可以决策和行动,这些环节构成了从起点到终点的一系列阶段和过程,即使还没有实现用通用人工智能来连贯性地在一台机器上实现所有这些环节,但不同(专用)智能机器的联合作业目前可以至少整合出所有这些环节的实现,对这一现象无疑可以进行深入的认识论分析,这样的分析可以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若干启示,所以人工智能先驱明斯基认为关注认识论在人工智能的研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仅是建构一个知识基础,就成为智能研究的重大问题……在这一领域中,我们需要花力气做严格的认识论研究”②Minsky,m.,“A Framework for Representing Knowledge”,in Winston P.H.ed.,The psychology of computer vision,New York:mcGraw-Hill Book,1975,p.193.。
另一方面,认识论研究也需要接受人工智能的洗礼,才能得到不断的拓新。如借助人工智能的推动可以加深对既有认识论问题的了解。不同的人工智能在模拟和延展人的不同认识能力的过程中,也导致了人对相关认识能力的再度反思和理解。如符号主义人工智能促使人们对推算认识的理解,联结主义人工促使人们对学习和感知过程的了解,行为主义人工智能则促使人们对行为中蕴含的认识如何与环境互动的了解。
又如,通过人工智能可以将一些新的概念和问题导入认识论研究的视野。人工智能激活了一些认识论的传统问题,也提出了一些不曾提出过的认识论新问题,如机器是否有意识和目的、人工智能是否有创造性等,就是认识论性质的问题。当然,新旧认识论问题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如上面提到的新问题就与究竟如何界定“智能”的经典问题关联与纠缠在一起。为了说清楚“智能”,还要进一步界定“意识”“意向性”“目的”“自主性”“主体”“知道”“理解”“知识”“自知”“自我意识”等传统认识论概念,这些概念的哲学含义不搞清楚,就会成为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的“概念羁绊”或“认识论障碍”。具体地说,认识论需要有对认识本质的更为全面和透彻的揭示,使其更具包容性和深刻性,才能为AI 的算法融合甚至人机融合提供更为有效的启示和引导。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智能”水平之不满,从最根本的层面上还在于人对自己认识过程中作为认识论对象的“智能”还未真正弄清楚,以及对相关的“信息”“表征”“理解”“适应性”等也缺乏透彻意义上的共识,从而对人是如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机制还缺乏认识论上的精辟入微的解析。可见,人工智能“倒逼”认识论不断拓展和深化自己的研究视野,进而有可能形成认识论问题创新的“突破口”。
再如,人工智能通过对认识论新旧问题的探析,还可能从问题扩展到框架,导向认识论框架或理论体系的创新,以容纳在这个过程中提出的新范畴、新的认识机理等。AI 范式的融合就有可能倒逼认识论流派的互鉴互融:符号人工智能属于传统数理科学的范式,与机器学习范式的人工智能相结合,可以使不同流派认识论的优势得以集合。还有,随着人机融合的认识主体的研究和实现,随着脑机接口使得延展实践被泛在化,随着人工智能使得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获得新的增强和质的提升,对相关的认识论机制的解析和阐释就提上日程,以便为认识活动的新演进、新规律提供新的理论模型,这些新的突破甚至可以汇聚为一场新的“认识论革命”。
总之,认识论借助人工智能可以获得更强大的推动力,从而视界可以变得更加开阔、内容更加丰富、阐释更加精彩,认识论的功能也在人工智能的平台上焕发出新的活力。“人工智能就是认识论”的命题也使人们看到,认识论比人们想象的要“有用”得多,人工智能的新发展、新突破,有待于认识论的革命和突破。或者说,只有看到了人工智能的认识论属性并从认识论基础上提供创新的支持,人工智能才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