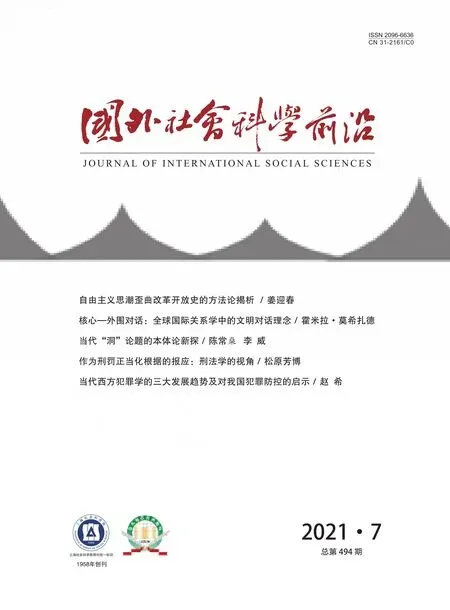当代西方犯罪学的三大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犯罪防控的启示*
赵 希
一、当代西方犯罪学的三大发展趋势
(一)从宏观犯罪学到微观犯罪学
从思考犯罪发生发展机制视野的宏大或微观的区别出发,犯罪学理论可以划分为宏观犯罪学与微观犯罪学两大阵营。宏观犯罪学成为二战后犯罪学的主流理论,其中涉及的各种理论角度各异,这些学说将犯罪产生的根本原因归为社会结构、社会分配、社会文化发展失衡等多种因素,总体来说这些理论看待犯罪现象多从宏观角度出发,其中较为典型的理论是紧张理论、标签理论、冲突理论等。
罗伯特•K.默顿(Robert K.Merton)的紧张理论认为,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性因素会对个体施加压力,从而导致越轨和犯罪行为。在对文化目标(culture goals)和制度化手段(institutionalized means)二者的关系处理当中,人们的行为模式存在遵从(conformity)、创新(innovation)、仪式主义(ritualism)、逃避主义(retreatism)以及反叛(rebellion)。其中创新、反叛这样的行为模式有可能会通过非法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而产生犯罪倾向。1Robert K.Merton, 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3, no.5, 1938, pp.672-682.标签理论的先驱者埃德温•雷伯特(Edwin Lemert)认为,制度在“创造”异常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控制导致了异常行为。2Richard H.Ward, The Labeling Theory: A Critical Analysis, Criminology, vol.9, no.2, 1971, p.269.标签理论具有两个一般性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社会控制机构如警察、法院等通过种族、行为举止、衣着等不同标准对个体进行分类,通过这样的“类型化”过程对个体赋予不同属性。社会控制机构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经常武断地给他们认为是罪犯的人贴上“标签”。第二个假设是,上述控制机构的类型化会促生犯罪行为。3Richard H.Ward, The Labeling Theory: A Critical Analysis, Criminology, vol.9, no.2, 1971, pp.281-282.而冲突理论认为,犯罪是社会冲突的产物,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的阶级冲突观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是引发犯罪的重要原因。在之后的发展中,冲突理论认为权力分配不均衡、文化和社会差异冲突都是产生犯罪的原因。冲突理论关心的主要问题集中于如下几点:政府在犯罪性环境的产生中所起的作用,个人或者群体的权力与制定和适用刑法之间的关系,偏见在刑事司法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犯罪率之间的关系等。4参见吴宗宪:《西方犯罪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405~417页。由这几个代表性理论出发,宏观犯罪学将犯罪问题定位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因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所产生的社会疾病,这为犯罪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地基,但这种宏观思考路径也因此而存在不足,突出表现为与犯罪预防的具体情境较为疏离。
相比而言,微观犯罪学并不否认宏观犯罪学的学术贡献,但认为特定的、具体的情境下犯罪的发生发展机制更值得探讨,以此制定的犯罪预防措施也更为实用。其代表性理论是日常行为理论(Routine Activity Theory)和情境行为理论(Situational Action Theory),前者多为美国学者所倡导,已成为目前美国犯罪学理论中的有力观点;后者则属于目前欧洲犯罪学热议的前沿理论。
日常行为理论起源于劳伦斯•科恩(Lawrence E.Cohen)和马库斯•费尔森(Marcus Felson)1979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发表的一篇研究文章。科恩和费尔森明确地将其理论设定为一种微观层面的设想(micro-level assumption),为微观犯罪学开创了新的理论篇章。1Lawrence E.Cohen and Marcus Felson, Social Change and Crime Rate Trends: 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44, no.4, 1979, pp.588-608.受人类生态学理论的启示,日常行为理论的基本设想是,日常活动模式的结构性变化会影响犯罪率。具体来说,犯罪的发生需要三个因素同时具备:有动机的犯罪人、合适的犯罪目标以及有效监管缺失。上述三个因素中任一因素的阻断,都可以有效预防犯罪。科恩和费尔森认为,这种微观犯罪学模式在两个主要方面突破了传统的犯罪学分析范式:其一,既有理论过于关注犯罪发生机制中的犯罪人层面,而忽视了合适的犯罪目标以及有效监管缺失这两个因素,新模式填补了这种不足,更为周延、具象地解释犯罪发生的先决条件。其二,有助于发现美国自1960年以来在犯罪防控方面宏观政策失效的内在原因。一些改善生活质量的社会变革不仅起不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作用,反而可能会对犯罪推波助澜。例如,汽车在为普通市民提供方便的同时,也给罪犯提供了行动自由。受教育程度提高、城市化发展和科技水平提升为人们提供了逃离家庭束缚的各种机会,同时也增加了犯罪的风险。
日常行为理论是目前美国犯罪原因论中的热门理论,不约而同的是,近年来欧洲犯罪学研究者们解释犯罪成因时也侧重微观情境视角。由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佩尔-奥洛夫•维克斯特罗姆(Per-Olof Wikström)提出的情境行为理论成为当前被引用最多的理论之一。该理论的核心论点是,具有某种犯罪倾向的个体与某种促进犯罪发生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触发了感知选择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了犯罪行为。2Helmut Hirtenlehner and Jost Reinecke,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with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Selfcontrol in Situational Action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15, no.1, 2018, p.3.根据这一观点,情境行为理论的出发点,是将犯罪行为作为“破坏规则”(rule-breaking)行为加以分析,强调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情境”是当个体置身于某个设定环境时个体对行为选择的特殊认知。因此,“情境”并不是指环境因素,而是“对环境选择的认知”,它发生在个体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当中。人们的犯罪倾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与法律相关的个人道德(内化的行为准则以及羞愧、内疚等道德情感)以及自我控制能力。也就是说,一个环境是否容易导致犯罪的产生,受制于个体所感知的道德规范等因素。3Per-Olof H Wikström et al., Young People’s Differential Vulnerability to Criminogenic Exposure: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oriented Approaches in the Study of Crime Caus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vol.15, no.1, 2018, pp.10-31.当具有犯罪倾向的人面对一个强有力的犯罪动机(诱惑或挑衅)做出反应时,犯罪行为最有可能发生。相比于日常行为理论侧重于犯罪机会生成的微观环境,情境行为理论更关注刺激犯罪产生的微观环境中犯罪者本人的道德和自我控制水平。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这两种理论都舍弃了宏观思考路径,进入了犯罪发生发展机制的微观层面。
与微观犯罪学对比,宏观犯罪学理论的特点在于,将犯罪问题的根源建构在整体的社会结构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社会文化歧视等因素上;主张减少犯罪的途径在于社会大环境的改善,例如教育资源、收入分配、文化环境,等等。宏观犯罪学对于犯罪现象的原因解读集中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宏观因素的诠释,例如贫穷、受教育程度低、受歧视可能会导致犯罪,但这些因素是驱动犯罪行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它无法合理说明犯罪发生的“具体”机制,即为何犯罪会发生在此时此地?宏观犯罪学主张政府应致力于消除经济发展、受教育程度等的不平衡,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犯罪,这些宏观目标的达成不仅是刑事政策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目标,是需要耗费长期时间乃至累积世代的发展变迁也较难以完成的人类的“终极理想”,对于紧迫的犯罪预防实践而言缺乏及时性、有效性、针对性。微观犯罪学正是基于此应运而生,它并不是完全推翻宏观犯罪学取得的学术成果,但主张预防犯罪不仅需要长效机制,也需要情境性即时机制。微观机制的目的是从更现实、更急迫的角度解决犯罪问题,通过给犯罪人制造情境障碍阻止其犯罪动机,更好地保护潜在被害人。微观理论认为,相比于变革社会这样的“慢性药”来说,社区层面微观环境的治理对于犯罪防控来说收效更快,也更为实际。
(二)从静态犯罪学到发展犯罪学
从犯罪学理论适用的时空限定性与否出发,犯罪学理论可以分为静态犯罪学与发展犯罪学。静态犯罪学着力于研究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认为所探寻的犯罪发生机制因素是超越时空限制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很多经典犯罪学理论都奉行这一学术主旨,其发展的巅峰之一是“犯罪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crime)。发展犯罪学则认为犯罪的生成机制具有时空的局限,以生命历程作为发展的重要背景来看,不同生命历程中经历的外在环境与内在素质的交织,会对犯罪行为的发生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代表性理论是桑普森和劳布的“逐级年龄非正式控制理论”(age-graded theory of informal social control)以及墨菲特的“犯罪人发展分类法”(a developmental taxonomy)。
顾名思义,戈特弗里德森和赫希的“犯罪的一般理论”是对各种犯罪现象都具有诠释力量的理论。其核心主张是犯罪性的实质是自我控制水平低,基于此,他们又将这一理论称之为“自我控制理论”(self-control theory)。1[美]迈克尔•戈特弗里德森、[美]特拉维斯•赫希:《犯罪的一般理论》,吴宗宪、苏明月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页。自我控制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低水平的自我控制会导致犯罪的发生。这一理论提出了七大假设:(1)年龄与犯罪的关系恒定不变;(2)区分犯罪与犯罪性是很重要的;(3)实施犯罪的倾向方面的个别差异可能在于个体自我控制水平的差异;(4)自我控制差异不仅可以解释所有类型的犯罪行为,而且可以解释不构成犯罪的类似行为,如抽烟、喝酒、赌博;(5)自我控制的差异,源自童年时期的养育活动;(6)犯罪和越轨行为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变化;(7)犯罪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1转引自[美]迈克尔•戈特弗里德森、[美]特拉维斯•赫希:《犯罪的一般理论》,吴宗宪、苏明月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9页。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的(6)与(7)似乎存在矛盾,实际上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按照犯罪的一般理论,“犯罪与越轨行为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变化”主要是指人们的犯罪倾向恒定不变,而“犯罪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少”主要是指成年期之后控制犯罪的力量逐渐增大,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会逐渐减少。由此可以看出,促生犯罪倾向的因素主要源于无效的儿童养育,这从儿童时期就形成并固定下来,此后的人生经历对此影响不大或可以忽略不计。从犯罪学研究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探寻儿童时期自我控制的形成机制。
发展犯罪学理论以一种动态、发展的视角看待犯罪现象,认为年龄代表着生命历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对犯罪的诱因和阻遏机制存在阶段性差异。发展犯罪学以发展心理学作为理论基础,后者将犯罪视为人生历程中的社会事件。根据发展心理学,人的发展可以分为生理发展、认知发展和心理社会发展,在人的一生中,这些发展的不同范畴相互联系,任何一个层面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层面的发展。2参见[美]黛安娜•帕帕拉等著:《发展心理学——从生命早期到青春期》(原书第10版上册),李西营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第11~14页。如果说生命每个阶段的发展需求和发展任务不同,那么,不同阶段的犯罪发生发展机制以及遏制犯罪的方法也会有所区分。根据我国学者的总结,发展犯罪学主要关注三个重点问题:其一,反社会行为以及犯罪行为随个体年龄发展会产生哪些变化?其二,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存在哪些影响个体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的风险因素?其三,个体发展中的重要阶段、重要事件对个体反社会行为和犯罪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3参见张新立、吴晶:《发展犯罪学对青少年犯罪成因的探讨》,《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发展犯罪学的奠基人谢尔登•格鲁克(Sheldon Glueck)和埃莉诺•格鲁克(Eleanor Glueck)提出,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和持续程度与年龄密切相关,在儿童早期发生偏差行为的,很可能会将这种行为模式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成年之后。4转引自张婧:《犯罪发展理论对我国青少年再犯防控的启示》,《犯罪与改造研究》2019年第9期,第2~3页。同样是从发展犯罪学的角度出发,墨菲特教授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年龄—犯罪曲线可能隐含两种不同的犯罪人群体,一类人从童年开始出现反社会行为,并且在之后的整个生命历程中持续从事反社会行为;而另一类人可能只是在年龄—犯罪曲线的高峰时间段从事反社会行为,并在此后逐步停止。这既可以解释年龄—犯罪曲线“倒U”高峰产生的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何一部分人在高峰过后继续从事犯罪活动。1Terrie E.Moffitt, Adolescence-Limited and Life-Course-Persistent Antisocial Behavior: A Developmental Taxonomy,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100, no.4, 1993, pp.675-676.同样立足于发展犯罪学立场,生命历程观点(life-course perspective)有两大关键词:一个是“轨迹”(trajectory),是指生活过程中工作、婚姻、自我认知、犯罪行为等方面发展变化的路径;另一个是“转变”(transition),是上述轨迹中相对突然发生的标志性生活事件,例如第一份工作或初婚。二者的结合可能会促生“转折点”(turning points),修正既有的生活轨迹,从而影响实施犯罪或终止犯罪的决定。2Robert J.Sampson and John H.Laub, Crime In the Making: Pathways and Turning Points Through Lif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7-8.
静态犯罪学以一个核心理论模型为出发点,用以解释所有的犯罪现象,试图构建一定的普适性,便于对犯罪现象进行跨语境、跨国别的比较研究。与此同时,这种进路对于犯罪现象的观察滤镜是稳定不变的,并不考虑犯罪发生的语境性和动态性。与静态犯罪学相比,发展犯罪学最大的特点在于把犯罪置于个体的整个生命历程中来考量,不仅研究个体间犯罪行为的差异,也研究个体内部犯罪行为的稳定性与变化性。3参见崔海英:《生命历程理论对未成年人犯罪危险防控的启示》,《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7年第1期。
(三)从社会犯罪学到生物社会犯罪学
社会犯罪学的基本特征是将犯罪问题视为社会问题,这种学术思路深深根植于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以来的学术传统,即社会行为必须在社会层面进行解读。4C.R.Jeffery, Criminology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Behavioral Science, Criminology, vol.16, no.2, 1978, p.149.涂尔干认为,解读人类行为时必须从“社会事实”出发,“社会事实”是一种外部的压力,它独立于个体意志的存在并约束和引导着个体行为。例如,货币系统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我们要想在社会中生存下去,就不得不使用它,并且服从它的规则。5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英菲利普•萨顿著:《社会学》(第七版),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1页。在此思想体系下秉持着“社会建构主义”的基本立场,认为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包括各种经验、行为和事实,都是社会建构性质的,受到社会权力、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等若干因素的控制,因此反对还原论、决定论和本质主义。6Anthony Walsh and John Paul Wright, Biosocial Criminology and Its Discontents: A Critical Realist Philosophical Analysis, Criminal Justice Studies, vol.28, no.1, 2015, pp.125-126.以埃德温•萨瑟兰(Edwin Sutherland)和特拉维斯•赫希(Travis Hirschi)为代表的主流犯罪学家将上述社会学观点引入到犯罪学当中,与其他学者一起开创了社会犯罪学的盛世。此后犯罪学理论发展纷繁多样,但其中蕴含的共通之处在于主张社会因素促生了人们的犯罪行为,环境因素决定个体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倾向,因此预防犯罪应当从根本上致力于修复和加强有利于建构人们合法行为的社会联系。前文提到的多数犯罪学理论如紧张理论、标签理论、冲突理论、控制理论等均属于社会犯罪学理论阵营,上文已论及其基本观点,在此不再赘述。
相比而言,生物社会犯罪学(biosocial criminology)并不是一门具体的犯罪研究派别,而是一种犯罪研究的整体范式(paradigm)。1John Paul Wright and Francis T.Cullen, The Future of Biosocial Criminology: Beyond Scholars’ Professional Ideolo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riminal Justice, vol.28, no.3, 2012, p.238.它主张通过探索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来解释犯罪和反社会行为,强调将诸如遗传学、神经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等领域的知识引入到犯罪现象的解读和分析中来。在犯罪学诞生之初,生物犯罪学是犯罪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以意大利犯罪学家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的“天生犯罪人”理论为代表,生物犯罪学成为全国性的思想流派并对整个欧洲和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参见吴宗宪:《切萨雷•龙勃罗梭及其犯罪学研究述评》,《刑法论丛》(第11卷),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567~568页。然而,20世纪生物犯罪学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不幸关联,使得这一学派在战后被驱逐出犯罪学研究的领域。随着生物技术的巨变和突破,国外生物犯罪学已在龙勃罗梭式生物犯罪学基础上演化为“生物社会犯罪学”,取得了一系列前沿性研究成果,在当代西方犯罪学领域引领了犯罪学研究的范式革命。
生物社会犯罪学倡导将犯罪问题视为“科学”问题,以实证方法加以验证和解决,其内部大体上可以分为进化论犯罪学(evolutionary criminology)、生物犯罪学(biological criminology)、神经犯罪学(neurocriminology)以及行为遗传学(behavior genetics)四个研究方向。第一,进化论犯罪学认为每个得以不断延续的人类行为都有其进化论基础。以攻击行为为例,在远古时代,迫于与大自然灾害和凶猛野兽斗争的需要,具有更高行为攻击性基因型的人类祖先更有可能生存或繁殖。通过这种方式,攻击性行为可能通过代际遗传代代相传。3Rebecca Eichelberger and J.C.Barnes, Biosocial Criminology, in Wesley G.Jennings (ed.), The Encyclopedia of Crime and Punishment (1st Edition), UK: John Wiley Sons, Inc., 2016, pp.1-2.进化论犯罪学并不是为这类行为辩护,而是找寻行为进化论的“根源”或因果机制。第二,生物犯罪学关注人体生理性指标与越轨和犯罪行为之间的关联性,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特定激素水平、心率高低与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例如,体内的睾酮素含量过高——特别是在胎儿期的过度接触,会增加个体的行为侵略性、冒险性和冲动性,会影响自我控制能力和共情能力,从而与攻击等犯罪行为产生关联。4Travis C.Pratt et al., Revisiting the Crimin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Exposure to Fetal Testosterone: A Meta-analysis of the 2D:4A Gigit Ratio, Criminology, vol.54, no.4, 2016, pp.589-591.第三,神经犯罪学主要关注大脑功能异常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将大脑中若干功能区的受损和功能紊乱与暴力等反社会行为关联起来。例如,前额叶皮层与反社会行为存在密切联系,前额叶皮层功能的减弱可能是一个人走向暴力行为的前奏。因为前额皮层受损会在认知、性格、行为、情感等方面影响个体,使人的智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降、失去自控能力、更易愤怒和暴躁并会导致违规逾矩、敢冒风险等多种不当行为。5参见[英]阿德里安•雷恩著:《暴力解剖:犯罪的生物学根源》,钟鹰翔译,重庆出版社,2016年,第67~68页。第四,行为遗传学犯罪学探讨越轨、犯罪等反社会行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受益于遗传学的不断发展,遗传犯罪学分支从最初的双胞胎行为遗传性研究,到以基因研究为主的分子遗传学,再发展到最新的表观遗传学研究。鉴于遗传犯罪学与当今最先进生物科技相互结合,可以说,它代表了生物社会犯罪学范式的前沿指标。一个重要的表观遗传机制是DNA的甲基化。DNA甲基化贯穿于人类的整个发展过程,能够在不改变DNA序列的前提下影响遗传表现,从而控制基因的表达,甲基化的过程对于环境的影响异常敏感。1Douglas S.Massey, Brave New World of Biosocial Science, Criminology, vol.53, no.1, 2015, pp.128-129.个体的攻击性、暴力倾向、冒险性、精神状态都可能受到DNA甲基化的影响,如有研究认为,催产素受体基因的甲基化与被认为冷酷无情的行为有关。当个体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面临高风险时,为了适应环境,生物系统会重新“塑造”基因的表达方式,进行“适应性编程”,这种适应性反应也会增加个体的侵略性和反社会行为的可能性。2Callie H.Burt and Ronald L.Simons, Pulling Back the Curtain on Heritability Studies: Biosocial Criminology in The Postgenomic Era, Criminology, vol.52, no.2, 2014, pp.248-249.
社会犯罪学奉行“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对国家刑罚的作用持怀疑态度,认为刑罚的威慑作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因此,应当将非政府机构如家庭、学校、邻里社区作为减少犯罪的核心单元,通过社会变革、家庭和学校教育方式的改良来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从社会政策的完善角度解决犯罪问题。这对于社会环境的改善和犯罪的预防,无疑提出了重要而有价值的洞见。但这种思维方式只关注犯罪发生发展的背景和舞台,却偏偏忽视了处于“舞台中心”的犯罪人。在犯罪治理实践中,在犯罪的惩戒、预防等各个环节实行普遍化、一般化的处遇措施,缺乏个体化、个别化考量,只强调犯罪的“社会病因”的治理,而不重视犯罪的“生物病因”的治理和预防。生物社会犯罪学提醒我们,犯罪动机和犯罪倾向至关重要,这与人的生物因素密不可分,在犯罪学研究中不容忽视。而且需要注意的是,生物社会犯罪学的四个主要研究方向都反对龙勃罗梭学说的生物因素决定论,而主张犯罪行为是生物因素与环境因素有机互动的结果。
二、西方犯罪治理模式转型:多元防控、预防主义与实用犯罪学
20世纪最后30年,在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出现了后现代性(late modernity),带来了一系列有损社会控制的危险与不确定性问题,这些问题在制定对犯罪的防控对策时扮演了核心角色。这意味着以福利国家为导向的刑罚时代已经终结,新的刑罚政策更加侧重对犯罪风险进行“控制”。3Davi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reface.工业革命与现代科技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创造了更多技术性风险、政治社会风险与经济风险。风险涉及的范围极广,覆盖社会生活与个体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风险社会中风险来源的人为化趋势增强,系统化、制度化风险逐渐凸显,风险影响的后果更为严重,也更为持续。1参见劳东燕著:《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27页。这给犯罪学研究提出了新挑战和新的学术增长点,使得新的犯罪防控理论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
西方犯罪学的三大发展应新的犯罪防控难题而生:由宏观到微观体现了犯罪情境预防中的精细化,静态到发展是为了满足犯罪预防中阶段性精准预防的需要,社会学到生物社会学则是用更为理性、科学的手段来弥补传统思辨性路径欠缺实用性、科学性的不足。
(一)犯罪控制体系:从国家垄断到多元防控
经典犯罪学理论对于减少犯罪的对策,主要诉诸刑事司法体系对犯罪人的复归矫正项目,以及消除贫困、增强教育、转变不良亚文化等国家主导下的应对犯罪问题的社会政策,犯罪控制在本质上归结于国家变革社会的垄断性力量。但在新的犯罪防控图景下,被犯罪伤害的风险已成为一种人们必须面对的“日常风险”, 而不再被视为异常或罕见的。受此影响,犯罪控制不再完全依赖于国家主导的刑事司法体系以及宏观社会经济变革,一种预防危险和防卫社会的微观机制逐渐成长起来。
根据微观犯罪学的基本思想,犯罪防控的重点应当是减少情境性促生因素以及增加对越轨行为的实际监控力量。这就要求纳入更多的犯罪防控主体和监控措施,以密织犯罪防控网格。根据发展犯罪学,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犯罪生成机制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犯罪防控不可能由单一的国家主导完成,必须融入不同生命历程所需要的多元外在控制力量。
新的发展趋势意味着国家在犯罪防控中的垄断性地位有所松动,转而提倡一种多元防控体系。犯罪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逐渐达成共识:仅凭政府机构本身无法成功控制犯罪。2Davi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Crime and Social Orde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p.105-109.这表现为:犯罪防控的主体增多,政府不再独担大任,而是成为惩治违法犯罪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多元主体中的一员。民间力量、私人力量加入到防控体系当中,预防犯罪的责任落到普通公民以及商界、学校、医院、规划者等主体的肩上。此外,在犯罪防控的空间维度方面,犯罪治理与犯罪预防从宏观的经济社会制度变革转为更强调情境性因素的社区下沉式犯罪防控,其中包括犯罪预防组织、政府与私人合作、社区监管计划,等等。相对于司法机构对违法犯罪行为施加直接打击这种“正式的犯罪控制”模式,以社区犯罪情境式预防为核心的“非正式犯罪控制”模式逐渐兴起,在犯罪预防和控制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犯罪防控思想:从复归主义到预防主义
经典犯罪学理论认为,犯罪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弊病,重视对促生犯罪环境的社会改造以及对犯罪人的教育和复归。社会复归政策采取有利于犯罪人改造的各项刑罚执行措施,同时致力于帮助社会大环境改善。这对犯罪控制来说无疑具有特殊价值,但对于控制滋生犯罪的多重、复杂的风险来源的实际需求来说欠缺实效。复归主义为此遭到了批评,罗贝尔•马丁森(Rober Martinson)教授在1974年发表报告《什么有效?关于监狱改革的问与答》,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现行所有的矫正方法对减少再犯没有任何明显的效果。心理学家雷•辛普森(Ray Simpson)也提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矫治的方法对罪犯的行为与性格倾向有效果,监狱迄今为止的改革都是愚蠢而不适当的。1转引自刘崇亮、严励:《对中国“罪犯改造无(有)效论”的实证分析》,《政法论丛》2018年第5期。
微观犯罪学、发展犯罪学、生物社会犯罪学逐层深入,与预防主义犯罪治理策略、行为人刑法之间的距离不断缩短。微观犯罪学基本上仍然将促生犯罪的外在环境因素作为研究的重点,但这种外在环境已不同于经典犯罪学宏观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外在环境,更侧重对微观环境中可能导致犯罪的情境性因素的预防。发展犯罪学将犯罪的导火线置于生命历程当中,以犯罪人本身作为研究的重点,特别关注生命历程中的重要阶段和转折事件,强调对犯罪的阶段性预防,这也与预防主义犯罪治理策略存在内在勾连。相比于上述二者,生物社会犯罪学则走得更远,最贴合预防主义犯罪控制策略。它虽然并不否认犯罪的病因有社会因素,但认为更需要重视的是生物体自身的因素,犯罪不是社会的弊病,而是人得了“病”进而被不利的社会环境因素所催化的结果。对犯罪人不应当惩罚而应当进行心理治疗和生物治疗,犯罪治理应当重视生物性预防,并结合最先进的生物科技开展早期风险筛查和治疗。
在犯罪学理论逐渐走向更具实效性的预防主义的同时,预防性警务、预防性刑法也开始成为研究的重点问题。例如,很多西方国家犯罪研究中热议的拦截搜查(stop and search)原本仅适用于警方基于合理怀疑对可能进行犯罪活动的个体进行搜查,但这一治安手段转变为一种犯罪预防的策略,越来越多的法案得以出台,允许警察可以不基于合理怀疑,对恐怖主义嫌疑人和危害公共秩序的嫌疑人进行拦截搜查。动用拦截搜查权的法律正当性和适当性问题,让位于维护公共安全、预防风险的需要。2参见赵希、龚红卫、刘志松编著:《国际犯罪学前沿问题综述(2017—2018)》,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63~165页,第322~323页。
在新的犯罪治理策略导向下,犯罪控制横向维度中的国家垄断权力似乎有所松动,多元主体加入犯罪控制体系当中,但新的预防主义犯罪控制哲学则在纵向维度方面使得国家刑罚权进一步扩张,国家介入犯罪预防的时点进一步提前,风险干预时点的空间性、时间性都有所提前,对个体自由的干预程度进一步加强。
(三)对犯罪现象的诠释:从思辨性到实用性
在预防主义犯罪控制模式下,为了达到预防目的,对犯罪现象的诠释必然会倾向于实用性。国外犯罪学家直言:“好的理论是实用的理论。”1[美]乔治•B.沃尔德、托马斯•J.伯纳德、杰弗里•B.斯奈普斯:《理论犯罪学》(原书第5版),方鹏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97页。为了更好地解决犯罪问题,犯罪学研究的政策化、工具化趋势都得到增强。这主要表现为对建构主义研究传统的反思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蓬勃发展。
建构主义论者认为,社会问题不能用自然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和解决,客观事实本身的社会意义有限,社会事实是人们建构出来的。建构主义更关注国家和民众群体如何定义犯罪。2参见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3期。社会学导向的犯罪学在研究当中尤为偏好建构主义,“社会控制”“社会解组”“父权制”“紧张”“标签”等用来解释犯罪的概念都属于一种理性论基础上对社会现象的某种拟制。例如,冲突犯罪学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是引发犯罪的重要原因。建构主义因其理论模型和思考路径的抽象性、思辨性,而与预防主义的犯罪控制需要存在一定的隔阂和距离。对建构主义的反思和批评颠覆了研究传统对“应然性”的偏好,转而探究犯罪预防控制的“实然”机制,通过统计和量化来研究犯罪现象,各种可以精确测量、评估和解码的风险评估手段被加以运用。
以此为契机,犯罪研究中多学科的智识不断汇聚,打破了传统的思辨式研究模型独大的局面。以解决问题的思路为导向,犯罪治理中参与学科日趋多元化。大卫•唐恩(David Downes)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关于犯罪学的论断,他将犯罪学描述成一个“学科集结点”:这一领域以一个社会问题为中心展开,不同基础学科领域(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科学)的研究人员围绕这一中心交换意见,而且不断从外界引入新的观点和理念使其保持生机与活力。3[英]伊恩•罗德等:《犯罪学与刑事法制改革:以英国为例》,《法学家》2012年第4期。
不可忽视的是,建构主义的反思性、批判性哲学倾向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人权保护,而犯罪学研究和犯罪政策的实用主义倾向容易忽视价值维度,即为了解决犯罪问题而采取过于工具化的方式,容易导向对人权的侵犯。缺乏价值判断的学说立场就很容易被操纵,不加批判地看待科技的作用会掩盖其中蕴藏的复杂的社会力量,而正是这些社会力量塑造着社会的构成、人们的行为预期和对犯罪的管控策略。4Julien Larregue and Oliver Rollins, Biosocial Criminology and the Mismeasure of Race,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42, no.12, 2019, p.1992.
总的来说,当代西方犯罪学发展趋势能够反映出国外犯罪控制思路的转变。为了应对风险社会中犯罪风险来源的复杂性和多元性,犯罪防控中横向维度得以延展,纵向维度也不断加深。犯罪防控的参与主体增多,时空范围增厚,犯罪学研究更为繁荣,多学科共同参与。但与此同时,国家刑罚权有增无减,对个体自由的干预程度进一步加深,实用主义理念使得实际的犯罪防控政策存在进一步工具化的趋势,可能会因为过度防控而有损其他社会价值的实现。
三、对我国犯罪防控的启示
通过对当代西方犯罪学的发展趋势和利弊得失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可资借鉴之处:
(一)倡导开展“预防性犯罪学”研究
国外犯罪学的预防性转向与其所处的风险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相比而言,我国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矛盾与西方社会存在一定差异性,尤其是西方所面临的种族问题、移民问题所引发的特殊社会矛盾在我国并不是主要社会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所面临的风险防控形势与西方社会当今犯罪防控形势具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剧烈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等层出不穷,我国所面临的风险防控形势呈现出复杂、多元性格局。国内风险与国外风险叠加、传统风险与现代风险叠加的趋势已经逐步显现。1参见宫志刚:《历史交汇期社会风险防控与警务战略转型》,《公安学研究》2018年第1期。在此背景下,可以预见,犯罪防控的内在思维会更倾向于工具主义与实用主义。
目前这种思维倾向已经在刑法领域有所表现,以扩大犯罪圈、刑罚威慑的手段应对风险的策略已经变成现实,机能主义刑法、积极刑法观、预防主义刑法都是近年以来的热议话题。我国当下犯罪圈的基本走向是刑罚更加积极地介入社会生活的适度犯罪化趋势。2参见付立庆:《论积极主义刑法观》,《政法论坛》2019年第1期。预防性刑法观以“刑罚有效性”为基准,通过刑事立法来实现积极预防风险的社会控制任务。3参见高铭暄、孙道萃:《预防性刑法观及其教义学思考》,《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在应对犯罪问题上,“预防性刑法学”大展拳脚,“预防性犯罪学”却一直默默无闻。
然而,预防主义刑事政策不应仅仅依靠刑法的扩张,因为这只是犯罪防控的“后端”。刑法毕竟是犯罪发生之后的惩罚机制,“预防主义”刑法通过创设更多预防型犯罪,试图以刑罚的威慑力量来遏制犯罪,这种模式是否可信或有效,还缺乏实证根据。4参见姜敏:《刑法预防性立法对犯罪学之影响:困境与出路》,《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1期。刑法归根结底是从犯罪化、犯罪圈出发的,其思考问题的基底是刑法典所划定的犯罪圈。但犯罪的发生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系列有害于安全的诸多因素的汇聚和流变过程,从危险的火苗发生发展到触发刑事法网的熊熊烈火时,所谓“预防性刑法”的登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更需要在犯罪风险防控的各个“前端”进行布阵。换言之,在发展预防性刑法的同时,也需要发展预防性犯罪学,以此汇聚成预防性刑事政策的合力。
犯罪学基于对人类共同体安全需求的深切关注,一切与安全相悖的因素和隐患都是犯罪学所思考的范围,1参见赵希、龚红卫、刘志松编著:《国际犯罪学前沿问题综述(2017—2018)》,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3~5页。犯罪学的研究视域更为广泛,研究的场域兼具微观和宏观层面,对于减少犯罪的社会体系性控制来说更具基础性和实效性。因此,风险社会的犯罪防控必须要求犯罪学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预防性犯罪学是以安全为导向的多重犯罪预防手段的运用,国外相关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二)探寻多维度织密犯罪防控网格的具体机制
国外微观犯罪学、发展犯罪学和生物社会犯罪学的新发展趋势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从不同维度织密犯罪防控体系。微观犯罪学侧重预防的情境性,发展犯罪学强调预防的阶段性,生物社会犯罪学则主张预防的个别性,三者分别从空间、时间、犯罪人维度补足了过去犯罪学理论的预防性漏洞。因此,我国预防性犯罪学的发展可以围绕这三个方面进行建构。
第一,对于犯罪预防的空间层次,社区、校园、城市热点区域这些微观环境下的犯罪预防,可以吸收日常行为理论、情境行为理论等微观犯罪学的学术观点。例如,加强社区防控的监控手段,包括人力监控和技术监控手段,实行邻里互助和邻里守望计划,填补社区防控漏洞,建设校园警务等。建构具有“集体效能”的犯罪防控微观网格,这些网格中的社会成员具有防控犯罪的内在动力,彼此间具有高度的人际信任,居民之间具有干预越轨、犯罪行为的共同意愿。2参见赵希、龚红卫、刘志松编著:《国际犯罪学前沿问题综述(2017—2018)》,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7页。
第二,对于犯罪预防的时间层次,应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犯罪促生的异质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犯罪预防对策。例如,根据婴幼儿期、童年期、青少年期、成人初显期(emerging adulthood)3“成人初显期”是指18~25岁左右以身份探索、不稳定性、自我关注等为主要特征的由青春期到成年之间的新成长阶段,它是在青年人推迟婚姻、就业,受教育年限延长等社会背景变迁下衍生出来的,目前在我国青年群体中已经有所显现。参见赵希:《解读“成人初显期”:理论创见性与本土适用性》,《青年探索》2020年第6期。以及成年期不同的生理发展因素,结合发展心理学等知识进行针对性预防。例如,儿童早期行为障碍、反社会行为如果不加干预,可能会与不良社会环境因素结合在一起,逐步衍生出“问题儿童”,这需要进行不良行为评估和纠正,调整教养方式;青春期不良朋辈的效应较大,青少年越轨中帮伙的比例很高,对此需要遏制不良朋辈效应;“成人初显期”时伴随自我意识和探索性质的增强,应重点注意性犯罪、毒品犯罪的预防;对于成年期来说,加强婚姻、就业、社团等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有利于遏制犯罪和预防再犯。
第三,对于犯罪人研究方面,根据生物社会犯罪学的观点,生理异常是犯罪的重要原因,当生理异常作用于人的理智和情绪时,会直接影响个体对自己行为的认知、决策和行动。尤其对于严重暴力犯罪而言,生物社会犯罪学的成果具有引入的必要性,因为相比于其他犯罪现象,持续的严重暴力犯罪人具有更高的生物异常可能性,探寻并切断其生理病因能够从根本上遏制其犯罪冲动。此外,在刑罚的判处与刑罚的执行过程中,可以考虑对生理异常行为人进行医学介入和干预。例如,对罪犯生理指标进行全面测量,针对其行为和心理障碍进行个别化矫治,针对不同程度的生理异常,有激素治疗、基因治疗、脑损伤治疗等不同的针对性措施。
(三)警惕犯罪防控过度工具化产生的弊端
预防性犯罪学是以追求安全价值为核心建构犯罪防控体系的,由于侧重在实害结果发生之前就予以干预,预防性犯罪学可能会因过度追求安全而牺牲其他社会价值。犯罪防控措施的过度使用可能会造成人人自危的焦虑心理和对被害的过度恐惧,从而影响个体生活。当防控措施常态化、日常化时,社会可能会变为“警察社会”,防控措施可能促生社会信任危机,陌生人之间彼此警惕,防控措施会造成额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预防性犯罪学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容易将越轨者视为某种需要解决的“目标”而被工具化,忽视人道精神,对轻微越轨者、偶然越轨者的不当管控容易使之偏离正常社会轨道,产生标签效应。
我们对预防性犯罪学所蕴含的上述风险应当有所警惕。工具主义一旦打破法治边界,就会造成一系列不幸的后果。对此,应警惕犯罪防控过度工具化产生的上述弊端,增加对犯罪防控手段的正当性追问和合法性省思。预防性犯罪防控观念下国家权力的过度启用可能导致挤压公民权利的空间,因此,应当寻求刑罚权运用的比例原则。1参见高铭暄、孙道萃:《预防性刑法观及其教义学思考》,《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预防性犯罪学的安全防卫手段也应当在具体防控措施的“手段—目的—效能—后果”等一系列环节的科学评估、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予以比例性适用。同时,制定相关的不良后果矫正机制,以及时调整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鉴于警察、法院、监狱等正式犯罪防控机构对越轨个体复归社会所产生的各种标签化的不利影响,犯罪防控体系应当适度松动国家主导的既有思路,发挥非正式社会组织的效用,实行综合治理。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下,社会风险防控是整个社会的任务,需要其他政府部门和各类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和协同治理。2参见宫志刚:《历史交汇期社会风险防控与警务战略转型》,《公安学研究》2018年第1期。
四、结 语
当代西方犯罪学的三大发展趋势不应被简单理解为新犯罪学理论对经典理论的继替。新的理论是应新的犯罪防控难题而生,而经典理论并未丧失其理论意义,其所涉及的社会问题仍然长期存在,这就意味着新旧犯罪防控任务将长期并行,新旧犯罪学理论也将长期存续。
随着风险来源的复杂性、多元性,新的防控思路倾向于一种预防性犯罪学,即围绕个体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等方面,建构对越轨和犯罪的防卫性风险探测和干预体系,从时空维度和个体维度逐步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预防性犯罪学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由于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研究方法势必需要多学科汇聚方法的运用。跨学科研究有助于学术创造力的激发和更具科学性、诠释力的学术思想的产生。学科交叉对犯罪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和新的要求,但这种研究方法是犯罪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未来的犯罪学研究可以考虑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并探寻专门人才的培养机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预防性犯罪学可以有效应对风险社会中各种危险因素的滋生,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动摇其他社会价值,这是值得警惕的。
——许春金先生
——张荆先生
——张荆先生
——张黎群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