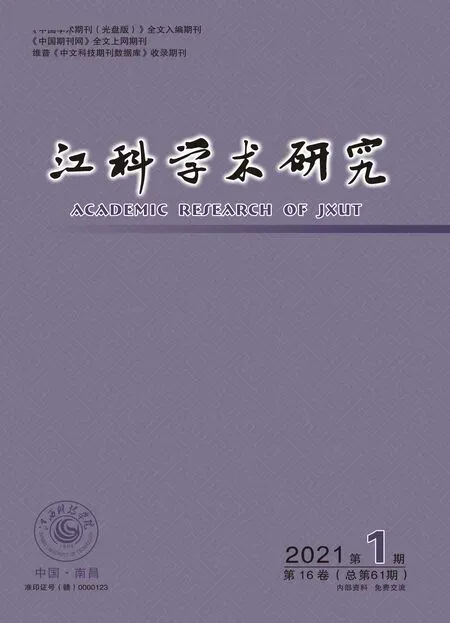董启章“V城系列”小说的时空观
王诺贤
“V城系列”小说的作者董启章是香港文坛的一位当代名家。从1997年开始,他建构出“V城系列”包括《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繁胜录》《梦华录》《博物志》,从此开始大量的以“V城”为话语主体的城市书写,彼时的香港文坛活跃着“城市学”的研究热潮,比如黄碧云所写的以移民回流为主题的小说,而把城市书写追溯到更早的源头便有20世纪60年代刘以鬯展现香港都是生活的生活吗面貌的《酒徒》,70年代又有也斯创作的《我城》来展现时人对于这片在“借来的土地上”的仅有的一点归依感,黄碧云在《失城》中以“此地是他乡”说明回归期限下港人心中的落寂,黄宗仪认为香港这个城市是一座“浮城”、文化是“消失的空间”。西西创作的《浮城》所表现的是香港人飘零无依的浮萍感。相对于其他作家,董启章从《地图集》的创作开始,他“瞻前顾后”既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既承认香港的回归是历史的必然,又在小说的想象空间中重塑过去、投射未来,作者把未来当作已然发生的事实,把过去当作可以扭曲、建构的可能,在这种不定向的时间规制下所构建出来的世界成为了容纳无数可能性的空间,无不寄托着他对香港的感情。
本文研究范围以“V城系列”四部书(《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繁胜录》《梦华录》《博物志》)为主,以深受“V城系列”影响的“自然三部曲”(《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物种起源·贝贝重生之学习时代》)为辅,来探究董启章城市书写的时空观。
一、可塑的空间
《地图集》全书分为四个部分。“理论篇”根据地图的要素,用对应、取代、与界限等地图理论和地图要素的组合构成空间感来探讨香港的前世与今生,香港没有确定的标记点,只有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利益冲突之下被放在不同的地点上的地图命运。“城市篇”以历史、神话、寓言的方法回顾了殖民时期的香港。“街道篇”则是对维多利亚城的旧街道故事、人文、历史、发展的详尽叙述。“符号篇”偏向于对香港未来和当下的想象。整本《地图集》表现的是“文学想象的极致”,全书展现创作的瞻前顾后与把未来当作一个开放的实现过程。
《地图集》较典型地体现了董启章的空间观。《海市》《蜃楼》两篇,命名来看是从海底和空中解读城市。在《海市》里有:传说中的维多利亚城,就像维纳斯一样,诞生于碧海波涛之中……此岛曾出现于陈伦炯所著之《海国闻见录》(1774年)……等文献的地图中,名字皆为“红香炉”。但是在……等地图中却完全没有“红香炉”一名及其地标的记载……在数百年间,红香炉时隐时现……,作者以多种可能性和“空间观双向循环性”的角度理解城市变化。《蜃楼》展现了香港华丽浪漫的城市氛围,空中的“雾气”、“船舰”的层次、“楼房”的高低冒升、“临海邸宅”的时隐时现,构成具有层次感的城市面貌。《蜃楼》描写的是向上生长的城市,《海市》则是沉落于海底的废墟之城,一上一下拉大了空间感,同时空间还富有多种塑造可能。《众坊街》描述了一个四方形的循环的空间广场,街道没有起始和终结,四边长度均等,与其他的街道完全对称,居民面貌也难以区分,四方街就是这样一个易于计算的几何世界。这便是循环无止尽的四四方方的空间,身处街道中的人无法停歇,“复制性的”人们一直循环于空间之中。
对于空间的塑造还可见于《博物志》中的《海星》一篇,这篇在天和地的倒转的前提下,对“怪物”海星进行引出。天和地是倒转了,天在下而地在上。我怎么知道呢?我依然在地上行走,我的脚无疑是站在地面上的,而天空在我的头顶……我低头仰视地而抬头俯视天……高楼继续建设,只是感觉上是向下铺盖而已……,天地进行了180度翻转,原本向上的增加高度变成成了向下的深度延伸。《地图集》中图例、比例尺、虚线、实线等地图要素均可以移动、转变,比如填海造陆工程在地图中的展现,城市边界的消失和移动等,这种大胆的空间想象构成了他的空间书写特点。
二、循环的时间
董启章对时间的敏感几乎贯穿了他所有作品,早期创作多是线性的时间描写。到了“V城系列”,时间去除了单向性的运动,而是双向甚至多向的迂回和循环,从而使“过去”“现在”“未来”这三种时式都富有运动与想象的余地。在《维多利亚之虚构一八九九》中,用刺点构成的虚线为主题切入,引出了香港的“填海造陆”工程,虚线既代表了未来城市的发展动向,也是永恒现在式的宣示。作者引出时式(tense)与时间(time)的差异,时间作为一个标量没有方向性,但时式的包容性更大。在这种时间观的指导下,董启章说:维多利亚城也可以说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城市。它是不断地于地图上用虚线勾画出来的,永远结合这现在式、未来时式和过去时间的城市。《时间之轨迹》这篇假定了时间的凝固,而描绘了在某一时刻下的状况和面貌,在罗湖站“往九龙”的地铁路线中构建了39 分钟的循环时间,时光回归构想的极限是39分钟,朝反方向与时间竞赛,力求延迟现在的到临。时间失去了永动的特征,从现在可以回到过去的某一时刻,这里的39 分钟不是一段时间限制,而是一种可循坏的闭合圆圈。
《繁胜录》是“V城系列”的云顶之作。它有三种时间角度,即俩条叙述时间线和一个称为“大回归五十年”的未来时间回望点,这意味着从小说开头就带入了循环时间、并行时间的概念。序言中中出现了俩个时间点,一是“V城大回归时期”即1997年前后,二是“大回归时期新时代”即2047年前后,一个过去式一个未来式,俩个时间线共同构成了历史空间的想象。永恒的时间观不止体现在“39分钟”的时间块中,《通道之城》说明了V城无本初发源,亦无终极依归,于是亦无成长,无发展,无历史的特点,他把V城当作通道本身,无出发点、没有继承是一种点状随散的时间动态,以“点”构线式就可以作为迂回时间线的完成前提。对V城居民的描述更直接此特点,“通道之城非历史的历史,造就了它的居民既非目的论又非本质论的思维模式”这是由于香港尴尬的割裂性所造成的,在此引入董启章《香港史的断裂性》,在香港被殖民的156年中,香港人普遍没有归属感,自身命运、城市命运一切处于未知的、迷茫的状态。时间的不确定性、循环点状性与香港人的思维意识、认知模式息息相关,董启章先生如此的行文特点更符合香港文化。
在“自然史三部曲”之一的《时间繁史·哑瓷之光》董启章的循环时间观运用的更加成熟。维真尼亚是一位永远17岁的女孩,年复一年只能过着重复的生活,因为时间的循环带来了生活的重复循环。她要为自己胸前的机械钟上弹簧,从而进行循环的生活。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中,栩栩也是一位永远17岁的少女,她是“我”在文字的想象工厂里创造的人物。栩栩被创造出来就已经17岁了,这是一种永恒的存在。
三、“时空观”的书写方式
《梦华录》由99个小故事构成,小故事都是以当前流行消费品作主题的。有电子产品、流行日剧……如《Hello kitty》《Sony DV》……。V城无可质疑代表的是香港,但以“V城”代之,正是建构一层虚构的距离[2](P5),使得在小说创作中有实有虚,可想象,可发挥,可留白,但又不至于偏激到极致。《梦华录》所取流行消费品大部分为1998年-1999年之间的大众喜爱的物品,从“未来的考古学”这一角度看,董启章站在未来的时间点写过去的流行物品,文章中有实际依据的同时,因为时间的间隔落差,会创造出新的想象距离与空间,因此故事的情节、开头、结尾、人物关系倾向荒诞的笔法,大多故事的结尾都没有固定的结局、人物命运也是多变无定式的,留下一种开放式的补充空间。广东方言和英语穿插在物品描写之中,也更生动的再现V城之貌,从文字到语音,董启章以不同的形式来留住对香港的记忆。
(一)以点带事
1.物品的线性影响。流行消费品多充当线索,或者关键转折点。Cuite是当时流行的一个衣服品牌,Cuite 穿插了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在小髀的不同成长阶段Cuite 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小髀的人生轨迹中执行了不一样的功用,使她从一个迷恋流行物的女孩成为一个不受物品束缚的独立女孩。Cuite背心在小髀的成长关键点发挥着作用,在时间的线上给予她重要影响,“人与物”的关系多了“共生”的特点。再如,Che是一个为了纪念拉丁美洲传奇革命英雄哲·古华拉而流行的热潮。当时有大量的Che的黑白照、T 恤等纪念品。因为阿紫和男友一同穿Che Tee,自此人们称她为Che。Che 的男友因为她死了,自此开始孤独的生活。之后,Che 画有哲·古华拉的T 恤被拿来作为游行合理性的保护伞,她新认识的大学生在庙街逛的时候被算命先生算到Che 的前世是阿根廷的英雄,只是英年早逝。由Che热潮引出来的人物故事,物件穿插合理又给人一种怪诞式的情节发展,比如男友的死亡和之后前世英雄的呼应。“Che”影响了人物的一生,同时以“Che”贯穿了多年的人物志、事物志,此物品以线性的方式给予人物命运很多改变。董启章以一件或者几件物品串人物故事的叙述手法,将冷冰的物品刻上了人物活动的印记,使得物不单单是物,而是一种有情感、有故事、有性格的人的一部分。
“人”与“物”的种种联系展现在时间的线性流动过程中,它在现了香港一代人的生活历程。
2.物品的环式影响。《梦华录》的相当一部分故事中,奇怪的近乎荒诞的物件成为时间回环、情节往复的助力点。主人公对近乎癫狂的怪异执迷,不仅是一种兴趣偏好,更是一种显示人物生活的方式。董启章以物品联动记忆,实际是很真实的港人价值观,由上文所提到的香港的断裂性可知,大部分港人在金钱、物质上找寄托。
在《贴纸相》一篇中,纪香与隆子是死党,阿平和小哲分别是她们的男朋友。在用贴纸相占卜后本以为爱情能长长久久,故事以四人二者的组合、配对的爱情为情节设计。故事情节有一明一暗的俩条爱情线,男女主人公四个人开展了双双配对的循环爱情游戏。贴纸相作为故事的助力点产生三次关键的作用,一是作为美好爱情的祝福,寄托纪香与阿平长长久的祝愿。二是纪香为破解贴纸相的祝福,对贴纸相的撕毁,推动了纪香与阿平分手,选择小哲的情节。三是纪香、阿平分手后,阿平回到隆子身边,贴纸相在结尾忽然出现,与第一次象征美满爱情的开头作为呼应相连。“贴纸相”这个物品的出现,成为四人感情发展循环的推动点,作者不以人物的情感、性格作为情节变化的必要,而是以物品带动人物和情节。类似于这样的环式结构还可见于《Windows 98》这一篇当中,用“Windows”推动人物故事发展,且层层相扣层层对指。Windows98所形成的关系环、情感环使人物命运多了可能性,成为董启章所塑造人物的重要特点,也是对他迷惘主题书写的回扣,物品尚带了人的温度和情怀,在不一样的人物身上,物呈现也出不一样的人生印记。
(二)以时带事
20世纪末,日本文化在香港被广大群众所接受。日本的流行歌曲、服饰、日常用品影响着港人生活。《梦华录》的九十九个故事中,串联了不少日本文化产品,这些物品构成了一个专属于香港的时代。我们不妨将故事放在深受日本文化影响的时代下,来解读人物的故事,董启章以物品留住了90年代的香港。
《Puffy》一篇讲述了Win 和Wen 俩个几乎在妆着、日常生活方面相同的人,Win 和Wen 所对应的原型是当时日本大火的Puffy 组合,她们的穿扮几乎完全复制Puffy 的成员由美和亚美。《日剧万岁》中沉没于日剧和日剧主题曲的少女爱琴,提到了大热的日本明星和日剧,与爱琴一样的还有一位身受日本尺八文化影响的青年奥古,他喜爱尺八,并且勇于追求自己爱的东西,孤身去日本学习。可以看出,香港的日本文化时代下,许多青年在润物般地文化浸染下,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是对香港历史的真实再现,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经济、文化水平相当先进,港人外向积极多贸易经商,充分与日韩交流,董启章把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真实的再现给读者。全文有种感伤的感情基调,犹如文中所提到的日本恐怖片的阴森萧声,奥古告别了爱琴,但爱琴却总能听到从远方传回来的空洞之音。董启章真正做到了“文”“时”结合,既有真实的文化背景,又将背景完美的嵌合到自己的人物塑造和记忆走向当中。“尺八”“日剧万岁”等消费品永恒,但相伴的人却渐渐逝去,将感情寄托在物品上才会获得的归属感,也是董对物执着爱恋的原因。对“物”的执着其实是港人的认知特点,漂浮的历史命运和有限的土地资源,几乎决定了他们“物”永恒的观念。《Colors》讲述青春型日本明星深田恭子的写真集《Colors》发行后,对一对情侣的影响。阿腿腿因吃醋自己的男友喜欢看《Colors》而失去分辨色彩的能力。虽然情节设定夸张,但这种夸大的设置更突出日本文化的巨大影响力。董启章笔下的日本文化,展示着港人点点滴滴的日常,由此虚构的“V城”更显真实。
(三)志怪式的梭子结尾
《博物志》分为五部分:异地、异人、异物、异事、私事。全书以“异”为主,是一部完完全全的志怪小说,单元组合式的小说里体现了人物共生、互为表里的怪异之事。《博物志》是董启章式的“故事新编”,人物联想来自古典《山海经》的怪物世界。怪人、怪物怪得令人惊讶,但跟着作者的思路是顺理成章的怪,《繁胜录》与《博物志》的短篇故事结尾多采取梭子式结尾,短促有力,结尾的内容往往出人意料、戛然而止,但语尽意未尽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去制造更多可能。
《博物志》有小人化的王国,在大鼠之下讨生活的市民,有体型巨大、声震如巨浪的蜻蜓,还有长在女孩发尾上与头发融为一体的蝎子。故事里的人都是半人半物,有人的特征却保持物的功能,有物的外表却是人的情绪。《霓虹灯管》描述了碰到自己喜欢的人灯管就会发亮的霓虹女子,她缺乏患得患失的矫情感,爱情总是无果而终,但她最后遇到了与自己相适应的拥有霓虹光管嘴唇的男子。把日常中的事物与人物命运结合,物决定人,人以物生,“人物”关系的共生特征令“怪”更“怪”,文本中选取的事物皆与生活息息相关,不禁让读者联想到香港混乱中的秩序、街市中的人情与躁乱中的自觉,灯红酒绿的香港旧景进入眼底。又如,《灯》中的灯之少女,一生从未放下过灯,灯却无需充电只要在她的手中就会一直发亮。她与灯融为一体、互生互存,甚至在灯发出的晕光和灯的贝母片中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前文铺陈灯与少女的共生关系,后文笔峰突转,将人物命运深化,故事情节急转又有力结尾,此篇是“梭子式”结尾的典型,荒诞、先锋、传奇迷离的结尾尽显“V城”的虚至神秘。
董启章笔下的人永远不是纯粹的主体,而物亦不可能是单纯的客体。《藻》一开头就引出了绿藻小子,一个浑身长满了绿茸茸、滑脱脱的绿藻男孩儿,他住在常年被水浸泡的屋子里。后来“我”爱上了绿藻小子,文中这样描写:我一眼就看出,绿藻底下藏着的是一个英俊的男子……绿藻小子慢慢分解,化为一滩绿水,从浴缸的去水口流走了……我把小藻丝放进口中,流了一滴有重金属味道的眼泪。“我”满怀期待,希望见到一个干净的绿藻小子,接下来会是一段甜蜜美好的爱情,接着的却是绿藻小子化成一堆绿水流走了,顺理成章的爱情故事突然转成一场悲剧,所有的美好幻想戛然而止,作者并没有给悲伤的空间,而是以“金属味的眼泪”作简短的收尾,高涨的情绪并没有文字的呼应就被遏制在结尾中,这便是董启章的梭子式结尾。
同样的结尾手法在《梦华录》中有更多的体现,《渔夫帽》里的主人公游游是个每天换不同颜色渔夫帽的酒吧女,游游跟不重复的男子出去聊笑。故事的后半段是对游游为何终日带帽的猜疑,突然出现的昆虫学研究生开始对游游执着追求:研究生说,当他扑出来抱着游游,纠缠中扯下了那顶红色渔夫帽,游游就不见了,只见帽子中飞出了一双红色的独角仙。按照读者的视角,更期待研究生和游游的爱情纠缠,但却以游游忽然不见作为卡点,“一双飞走的红色独角仙”的奇丽、魔幻的形象作为故事的结尾干净利落,同时给读者留下了大片的想象空间。同时,梭子式结尾也体现情感的大起大落,正文对于情感的反复渲染,刚把读者带入或喜或悲的情感语境,但又以人、物的突然破碎、逝去作为结尾,给人不知何方为出路的思想感受,这也是作者当时创作的心态。
董启章的结尾部分是我最乐于回看的部分,大胆、奇特、怪异的结尾总博得人会心一笑。在穿透事物表里下,面对实际客观的物品总能加以奇幻怪诞的志怪手法,比如穿着能倒着走的鞋的拔拔;能体会人间疾苦而一夜生锈的发夹;一位用海洋矿物保湿面膜膏才能存活的辉荣。在V城这个永远有着一层虚构距离[1](P5)的城市一切怪异都是正常,所有的变异都是日常。
四、结语
“V城系列”的聚焦点是V城即香港,作为城中人、见证人的董启章,以虚构我城的方式来保存他对香港的记忆和热爱。线性、循环、反复、共时的时空观不断被赋予新的故事、新的可能、新的想象,用“未来的考古学”这个对位时式的角度进行的小说创作更具有活动感、张力感,人物共生的物品观更是给志怪的偏激时空构思提供可发挥的空间。如董启章所说香港是个“多种权利和意识形态的角立场”,他以虚构的方式对香港进行书写,同时回应真实,在真实与虚构的撞击中产生另一个世界。他的最终目的,不是构建城市,而是把城市书写作为看待未来、面对过去的一种方法,为繁华美丽的香港创造更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