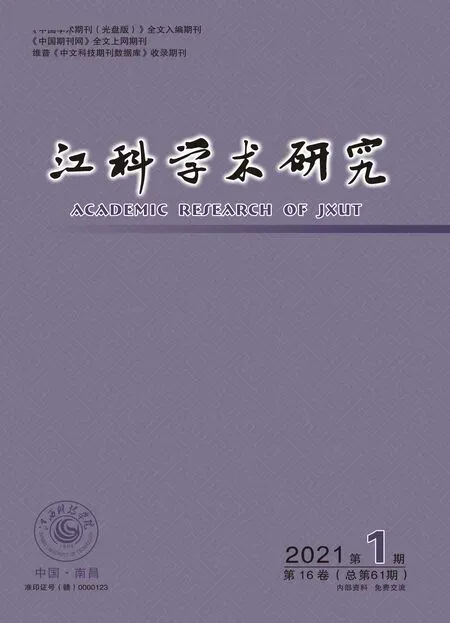从逯注《陶渊明集》看陶诗文题材的内沿与外扩
黄 丹
本文厘定的版本是逯钦立校注本《陶渊明集》,关于逯本,争议和附和赞扬之声皆有之。其中,吴云先生着墨最多,评道:“近百年来在研陶领域中,集考证、校勘、注释、评论四方面之成就最大者,仍首推逯钦立先生。”确实,先生在校注的过程中,有意识的详辩略论,从古籍中去寻找典故来源出处,细致入微,详道周备,考证功夫可见一斑;对于前人评论的观点认同的加以批注,文中多次出现汤注即为此证,略有出处便引经据典加以说明,并注明自己的观点。可谓拷备翔实,引证精微。于今读者而言,对于内容题材和思想意蕴把握功不可没。
一、陶之生死观及其存在之思——哲思之作
陶渊明的一生高洁不群,抱朴守静,他的人生经历了从“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嘉”的壮怀满志的无乐之乐之境,再到“俯仰终宇宙,不乐复如何?”的欣欣自得之乐之境,从起点到人生终点,摒弃驱驰市朝的汲汲营求之心,走向追寻“共话桑麻”的田园意趣,倾吐“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人生哲思,解锁人生价值的终极密码,不断向内探索,打破世俗的束缚,以真性自由的敞开之态迎接生命之真。在逯钦立校注版《陶集》中,选录的大量诗文作品都流露出对大均化物和生死之数的哲学思考,陶渊明直接于当下的生命体验中去领悟生命的要旨,超越现有的世间秩序,在生命的自由体验中去建立和寻求新的秩序,流露出深深的哲学思考。
“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相信和宣传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繁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他们并不可信或值得怀疑,只有人必须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充满那么多生离死别和哀伤不幸才是真的。”[2](P196)魏晋时期,社会混乱,战乱的频发使得生命和生存状态成为人们个体价值确立的聚焦点,个人意识的高涨和个性的张扬也极大地放大了对生命意识的关注,生死自然也纳入到了这个范畴,那么,既然旧有的规范和秩序已经不再使人们信服,自然随之而来的就是打破旧的秩序和新秩序的重建,由于时期士人们在心理上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巨大无力感和由此带来的巨大反差,使得大部分士人的心理走向一种委任运化的随性自然的道路,“盖陶渊明诗文‘颇示已志’之语,虽属屡见,而皆因事托心,偶尔及之求其专篇发挥其思想者,实唯此《形神影》之作也。”[3](P218)《形神影》三篇专对“形、神、影“而发,阐述自然大均之力。真正呈现了陶渊明“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1](P53)”的形神俱灭的生死观,呼吁”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的当下之乐,在陶渊明看来,人生有始就会有终,明日并非能营营贪求而能有所求的,”资大块之受气“自然化育万物,而人为灵长,却依旧只能短暂在世间寄托形体,”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又有《挽歌辞》曰“千秋百岁后,谁知荣与辱……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四)凡此种种,都肯定了“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的神随物迁,形存有尽的生命体验。
忧生之嗟和青春易逝之叹亦是陶渊明诗歌中常常出现的素材,“皎皎云间月,灼灼叶间华,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中有月华之喻,有芳颜易改,时不我待的沧桑之叹;有“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的不争朝夕,惜时系世之慨。在《自祭文》中,渊明亦慷慨悲歌,对人的生命存在和归去指明出路,他以如椽之笔书写道:
于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寒暑逾迈,亡既异存。
在《自祭文》中,陶指出哪怕寿涉百龄,生命存在必有尽时,人们不必贪求留念生命的短暂,应顺化自然,肯定形体的存在或是消亡都只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方式,这里面显然有老庄之“道”的渗透,强调生命之要旨不在于存形于世间的久长,而在于顺化,即是“委任运化”,这是生命之敞开的自由境界。这种生命之思较为具体而又形象地呈现在《影赠形》、《影答形》和《神释》三首诗歌之中,这种生命之数即是所谓“反复终穷,自然之数”。
作者探寻生命之伦常秩序,并从顺化自然中得到生命之真乃是“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本真状态。摒弃营营惜生和患得患失之心,委运知命,以自然敞开之姿态迎接生命荣枯,不汲汲于悲喜,亦不随波逐流,以凡常心态领会“此中真谛”勿向“别处”求生存之道。
二、篇篇有酒与醉酒抗争——游戏之作
酒菊盈园,可谓是陶渊明形象的标配,说陶诗文篇篇有酒丝毫不夸张,“饮、酌、壶、樽、醉、觞”等字眼弥漫全篇,数不胜数。陶渊明乐从酒中来,此有“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愁亦从酒中来,“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陶集》诗文写酒之篇不胜枚举,而其专述饮酒之作又属《饮酒》二十首独步于后世。其坎坷秉廪之怀亦在此中写尽。《饮酒》(其三)中写道“吾生梦幻中,何事绝尘羁”(其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其六)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从“仕为饥驱”到“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的价值追求的转变,陶渊明诗文中饮酒的深味是否也在发生着转变呢?难道说他的三仕三隐只是对尘世羁绊或者说是饥寒所迫的无奈之举,“时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饮酒也只是对这无赖之举的激愤回应。显然不是,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集》校注本中有按语云:庐山道人有诗每句着化字,此诗每句着“止”字,皆游戏之作也[1](P106)。
《萧统序》:有疑陶渊明诗歌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即是如此。“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十四)寥寥数语,点染酒中蕴藏之深味和诗人借酒陶情之心。其《己酉岁九月九円》云:“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陶渊明把饮酒之乐抒发到了极致,饮酒诗篇中无一处不透露出对酒的钟爱,杯盏之中流露出的是对世态的坦荡,是人性最本真的自然的流露。“亭亭复一纪,世路廓悠悠,杨朱可以止,浊酒聊可恃”和“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几句,备述人生之短暂,唯酒可以聊情,世人不睦圣贤,终日汲汲追求功名富贵,显然,诗人在醉饮的呼唤中渴求人们去追求一种返璞归真的朴素人间真理,抛却个人名利回归本真的自然天性,实际上,陶渊明正是用这种醉酒的方式与人们所热衷追求的东西做着无声的抗争,在饮酒这样自斟自酌的静默中去放任真性中难以掩盖的真性情。
大部分诗作中,陶渊明把饮酒和交游之乐很好的联系起来,是“杯尽壶自倾”的怡然自乐,是“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的邻里互动,酒成为陶渊明和邻里友人乃至精神陶冶的消遣之物和物质纽带,而这物质层面,是不需要吹嘘热捧,没有官场的尔虞我诈,是最真最纯的生产精神的物质纽带,当然,酒也成游戏取乐的精神桥梁。“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和诗仙太白一样,纵情壶酒杯盏中,人也从这个物质的平行时空跳转出来,于心灵安静无声处觅得知音,这大概是陶渊明和太白心照不宣的地方。陶渊明从酒中寻觅知音,一方面,以酒会友,另一方面又以无声的醉酒方式去揭露“非友”行止,陶渊明之饮酒,实在于以醉态嫣然之笔触,去游戏人间耳!万伟成所言“全诗二十个”止“字,诗胆可谓大矣。”[4](P254)
三、亲事农桑的田园之儒隐——田亩之作
陶渊明历来被推崇并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关于隐者,“儒隐”和“道隐”是学者分析隐逸行为的惯常的一套理论模式,阂军认为“中国古代隐士的构成及其隐居方式是多样的,这与其各自哲学思想基础有关。就此而论,又有道家之隐与儒家之隐之别。无意天下事,无意仕途,一心出世,以求超然物外,是为`道家之隐'`身处江湖,心存魏阀'、`隐居以求其志',以隐待出则为儒家之隐。”[5](P49)陶渊明的诗歌中,“生有高名士,既没传无穷,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这类的抱节守志、刺时谏今的思想要旨无处不在,无所遁形。在《咏贫士》中,“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以贫寒之士的高节和志向勉励自我,以述自己的高尚情操和安贫乐道之志,也从侧面体现做着抱朴守真,捍卫传统高志的卫道精神和热切关注现实的出世精神。显然,陶渊明的归隐田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归隐,但是,他也并不期冀一个契机而重返庙堂,而是简简单单的为了本性之真而回归乐田园生活,以自由之姿态去回归本该属于自由真性的自然山水。因而,陶渊明也不能称之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隐者,他本出于真心的回归乃是不隐之隐,这是生命最本真的状态。
仆去月谢病,还觅薜萝。……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饶竹实。山谷所资,于斯已办。仁智之乐,岂徒语哉!(吴均《与顾章书》)
吴均在《与顾章书》中描述归隐,细致勾勒隐居生活和与心境相契合的自然环境,相较吴均的“还觅薜萝”、“仁智之乐”而言,陶渊明的自然田园生活并非刻意寻求,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本我的回归,他的“隐”,在于于不隐之间,寻到生命归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怡然和惬意,没有斧凿之迹,也不用刻意求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陶渊明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诗人,在纯净的自然田园山水之间,过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自足生活。他借“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书写人生荣辱有时,莫如终日饮酒为乐,志趣田园,抛却凡尘俗念。“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爱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答庞参军》)在琴书悠扬中陶然自乐,朝为灌园,夕偃蓬廬的田园劳作场景的真实写照反应其中。“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夕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勤劳耕耘的陶渊明自得于田园之趣,把收成和结果抛之脑际,他的乐趣来自于对“民生在勤,勤则 不匮”的朴素道理的认同,那种喜欢就执着于彼的坦荡、直率、自由和真性情,在他的始终自由而任性的绽放,带着不羁和随性。游走田园的陶渊明,在其字里行间都闪现着自然的光辉。“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农人之间交杯换盏,惺惺相惜,日夕劳作,夜归相饮,极其淳朴的民风民情在诗中展露无遗,诗人完全以农民身份自居,和农人聊情欢饮,畅快无归,时耕时憩,田园的怡然自乐之情充斥笔尖。
四、交游述行诗——志道之作
陶集中有数量颇丰的记述交游志道的作品。《和郭主薄》《答庞参军》《酬丁柴桑》《岁暮和张常侍》《拟古诗十九首》《咏荆轲》《感士不遇赋》《与殷晋安别》等是等都是交游诗歌的代表,而《时运》《游斜川》这二者又是彼此交融,共同构成乐陶渊明精神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大胆批判虚伪驱名的不正之风,将自己的精神寄托于亘古贤士,放迹形骸于山野田园之间。陶渊明不慕势利,以真诚交游,所交游者均是志趣相投者,作为曾读书致仕的士子,他和乡野村民打成一片,把酒言欢,“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虽有一股读书人的桀骜之气,依旧与民亲亲,不拘小节。作为归野乡民,他不避官宦,以志趣结友,如他的五言诗歌《答庞参军》云“有客赏我趣,每每顾园林。恢谐无俗凋,所说圣人篇”。他即便幽居野外,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每每吸引志趣相投者慕名远来探访,陶渊明的人格魅力可见一斑。
陶渊明近交乡邻挚友,远交亘古贤士、名臣将相,虽志趣山野,赏田园之乐,饮酒之欢,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诗歌中窥见他脱俗的气节和远大的抱负、志向,乃至对自我情操和高洁人格和气节的坚守,可以看到他以酒为梁;以酒香酒色搭起与远古先贤沟通的桥梁。《感士不遇赋》中以极具批判性的笔触揭露了魏晋时期萎靡之风盛行,忠贤莫辨,黑白颠倒的社会现实,晋朝等级森严,《晋书·刘毅传》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是两晋时期社会现象的真实写照,即“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他把官场视为罗网和泥潭,对之不屑一顾,以大钧之力呵斥驱名逐利的“狂驰子”之徒,与当朝的腐败政治作着顽强的精神抗争;他高歌赞美士人廉洁谦让的高风亮节,“无爰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陶渊明摆脱一切俗尘遮蔽,以外露敞开之态去对话先贤哲人你,为他们的才华志趣倾倒,又惋惜他们大器晚成,郁郁难就的悲怆情怀。宁愿“拥孤襟以毕岁”辞官归故里,怀抱自己的志向度过平生,哪怕高官厚禄也不越线半步,势必“谢良价于朝市”。
萧统在《陶渊明传》载录江州刺史檀道济在宋文帝元嘉三年时曾亲自造访陶渊明,见陶渊明家徒四壁、箪瓢缕空、面黄肌瘦,浑身瘫软乏力,因说:贤者处事,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陶渊明正视到话中的拉拢之意,正色道“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这里的志一方面暗指自己心向闲人的高尚,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积极富贵、追逐名利场行为的不屑,明确表明自己志不在此的决心,这些从一个侧面展现了陶渊明大济苍生的志向和抱负。费希特认为:“只有摒弃对外在成果的指望,内向于自己本身,以求心安理得……成败利顿在所不计,才能享受陶然自得的‘至乐’生活。”[6](P144)陶渊明心向于一种古朴至真的生活体验,因此他的至乐生活是一种个性的、开放寻向自然的。因而他的交友也是不受时空局限,敞开的一种心灵相契的状态。
陶渊明的述行之作亦不在少数,《游斜川》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篇。“天和气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诗人在晴朗碧空之下,和游伴依偎傍水而坐,观湖沼平川,听空谷鸥鸣,视野无限辽阔,诗人一任诗意自由流淌,记录斜川之游的春光、山川、鸟鱼等自然风光盛景,以智慧之眼去体悟内心,发出“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的哲学感悟,将“天道无常,常与善人”的朴素道理哲学化,系统化并进一步世俗化、生活化,指出人生向往之路的终极归宿——自然之中的朴素真理。诗人以浑然天成的自然笔触记录斜川之行,实际上也透露出诗人卓尔不群、心向自然的伟大胸襟和心性追求。
陶渊明在诗文中将自己的人生体验融于现实生活中,不在轰轰烈烈中去追慕虚名高利,只是抱朴守真,于朴素中寻找并探索人生的普适价值,他以洒脱和逍遥自在的任性姿态去面对人间百态,活出自己的肆意和真淳,是充盈自在、自适自得的生命个体的存在,而这样的个性反应在诗文中,也就多了一份随意洒脱、开放自如之势,因而他的诗文题材丰富多样而又随取随用、收放自如,散发着自然人生的朴素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