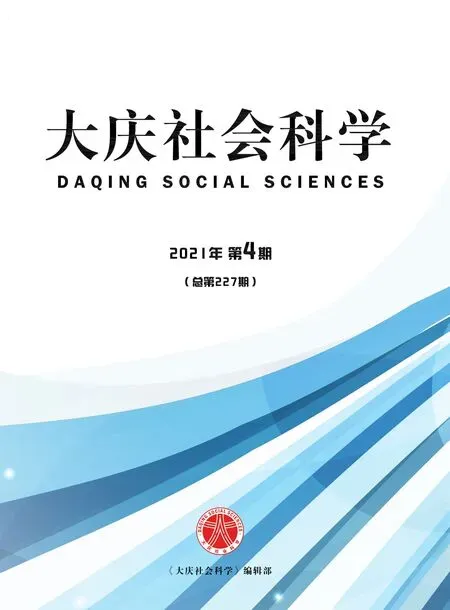当代美国“白人至上主义”探析
刘 洋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一、白人至上主义与美国的渊源
白人至上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甚至更早时期,始终与美国的社会结构与秩序存在着深刻的共生关系。通常认为,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宗教文化,即殖民时期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它在美国白人认同感和白人至上主义的形成过程中起着独特的作用。17—18世纪移民美国的欧洲人中,白人新教徒居多数,这部分新教徒由于宗教迫害、政治窘境或经济困难而迁徙北美定居,成为了现代美国的始祖,也因此在美利坚民族形成初期,新教伦理和价值观成为人们的主流文化。新教伦理中的核心价值观是“上帝选民观”,它所宣扬的是强烈的命运感、上帝选民感、特殊使命感。[1]这种“天定命运”的意识认为,美国人是被上帝选中担负重大使命的人群。[2]因“文明冲突论”而声名大噪的塞缪尔·亨廷顿曾对相关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他指出,美国的核心文化是最早来北美定居者带来的文化,即盎格鲁——新教文化,它包括从英格兰继承而来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以及习俗,最主要的内容有英语以及当时不服从英国国教的新教的理念和价值观。[3]可以说,新教文化加强了移民相互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拉近他们彼此距离的重要纽带。但与此同时产生的是美国白人新教徒对其他少数族裔的敌意和偏见。他们将基督教与种族纯洁或白人联系起来,将异教与种族不纯洁或非白人联系起来,文化中充斥着种族优越感。当这些观念受到挑战时,新教文化便为白人至上提供了神学上的理由,进而为种族主义提供了理由。
1607年登陆北美大陆的欧洲白人与当地土著争夺土地和资源的斗争开启了美国的种族压迫。事实上,不论 《五月花号公约》 还是 《独立宣言》 ,亦或是之后的 《美国宪法》 ,都是由白人 (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 所制定,有色人种长期被排除在外。从17世纪到19世纪,有几十万非洲奴隶被贩卖到美国。1776年,身为奴隶主的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美国 《独立宣言》 ,宣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4]而此时杰斐逊所言之“人人”指的是白人(尤其指男性白人),权利并非授予给全体人民,“有色的鸿沟”并没有被消除。1789年美国通过宪法,明文规定分配众议院席位时,每一黑人奴隶只按3/5个白人计算。[5]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祖先为被贩卖到美国当奴隶的黑人不能成为美国的公民。1865年南北战争后,美国虽然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度,黑人获得了人身自由,却仍没有选举权与投票权,其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依旧低于白人。同在1865年,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3K党宣告成立。3K党被定位为“美国生活方式”的捍卫者,宣称自己的主要目标是维护白人种族的至高无上地位,强调“美国主义”和“基督教文明”,反对“外来”群体和文化。3K党成员通过纵火、鞭打、酷刑和肢解等恐怖手段来达到目的,在不同时期发挥着政治影响力。1877年,美国开始了长达近百年的吉姆·克劳种族隔离制度。在所谓“隔离但平等”的精神下,美国很多州在公共场合进行种族隔离。直至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后,美国的种族隔离和歧视才被法律禁止。至此,美国步入“后种族主义时代”,白人至上主义不再像过去一样表现为直接的压迫与歧视,而是更为隐秘地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角落。
要补充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黑人皈依了基督教,异教徒不能再令人满意地为奴隶制与种族隔离辩护。于是,生物学的争论逐渐变得突出。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 《物种起源》 的问世对社会思想和科学界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种族主义者借机在其框架上建立了他们的种族概念,将种族与进化论假说联系起来,并将种族按等级排列,得出种族不可能具有同等禀赋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黑人作为一个种族可能取得一定程度的进步,但他们永远达不到白人的智力、文化、道德或身体水平,他们仍然只能在白人的压力和指导下生活;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是“自然秩序”的产物,需要努力维持这种平衡,且只有白人才能定义这种平衡。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叶日益倾向于科学思维的时期,这种立场吸引了很多人,人们普遍相信生物学因素对人的性格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它为现存的种族结构提供了“科学”支持。有学者在探讨美国种族主义的“正当性”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神学家以 《圣经》为据,创造出黑人应为白人作奴的神话;科学家以人类的起源以及不同人种体质上的差异为依据,创造出种族有优劣差等的神话。神、俗两界共同缔造了种族主义的社会与文化传统、白人至上的政治与经济原则。”[6]
二、美国白人至上主义的重新泛起
(一) 美国白人至上主义重新泛起的原因
1.把经济衰退归咎于移民伤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美国自身制度的缺陷开始显现,政治极化加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白人生活在“社会萎靡不振”的状况下。2001年、2003年, 小布什政府以反恐为名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美国深陷泥潭,巨大的伤亡和巨额的消耗蚕食着美国的经济基础。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是让美国白人的自信与骄傲消失殆尽,尽管奥巴马政府施行了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试图力挽狂澜,但未能彻底让白人走出困境,消除他们的不安。
就现阶段而言,美国白人特别是中下层白人首先面临的难题是经济上的困难,失业率的增高和贫富差距的加大令社会矛盾愈发凸显。一方面,美国的产业结构长期存在问题,过度依赖从外国进口制成品,形成严重的“去工业化”现象,大批白人工人失业;而且在全球劳动力竞争环境下,美国白人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大幅缩水。美国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2016 年联合公布的 《2015年全美收入和贫困》 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约1800万白人处于贫困线以下。[7]
对于美国经济不振、人们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美国种族主义者不是从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错误行径上找原因,而是无端迁怒于非白人群体,认为“大量基于家庭关系的移民成为低技能移民的主要来源,抑制了工资,最终伤害了脆弱的美国工人”。[8]大肆煽动种族仇恨,使种族主义的丑恶之风借尸还魂。
2.把白人社会地位下滑归咎于文化认同差异。文化多样性本质上是世界发展的正常趋势,美国种族主义者却把这种趋势看成“危机”。他们认为,移民数量的增加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结构,他们带来了更为多元的文化,占有了更多的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资源,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力日渐提升,相应的,白人的比例逐渐降低,对移民的恐惧与日俱增。从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美国总共有4500万拉美裔人口,是20年前的2倍,预计到21世纪中叶,拉美裔将是现在的3倍,达到1.3亿人。[9]这意味着按照目前的速度,不久的将来拉美裔将成为美国的绝对多数族裔,盎格鲁——新教文化极有可能不再占有支配地位,不再是美国国民特性的核心。在皮尤研究中心于2018年和2019年进行的电话调查中,65%的美国成年人在被问及自己的宗教信仰时称自己是基督徒,相较过去10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10]大多数美国白人基督徒——尤其是白人福音派新教徒对当今美国基督教的地位并不乐观,三分之二的白人福音派认为基督教在美国生活中的影响力正在下降。[11]
总的来说,当前美国白人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来自经济层面和文化认同层面,他们极度担心自身生活状况的恶化和社会地位的下降,这种担忧令白人与其他少数族裔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是促使美国白人至上主义重新泛起的重要动因。
(二)美国白人至上主义重新泛起的结果
1.美国政坛的“白人至上”倾向日益凸显。如前所述,经济的衰退和不平等的加剧成为滋生保护主义的土壤。随着白人的被剥夺感和抵触情绪的愈加增强,白人至上主义在美国逐渐复苏,直接影响着美国政坛的政策走向。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认为,大量的外来移民和本土少数族裔的壮大正在威胁白人占主导的国内秩序,他曾直呼从墨西哥入境的非法移民“大多是毒贩和强奸犯”,力主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大肆驱逐外来移民,并不时发表针对少数族裔移民的歧视言论。反对者称特朗普不是要“使美国再次伟大”,而是要“使美国再次变白”。除特朗普外,特朗普式的白人至上主义还普遍存在于美国政府中。大批身居要职的官员或是直言不讳的表达对少数族裔的偏见,鼓励白人至上主义的行为;或是闪烁其词,表面上拒绝承认白人至上主义的合法性,暗地里却支持白人至上主义的浪潮;再或是袖手旁观,用沉默替代行动,放任白人至上主义的蔓延。如:史蒂夫·班农曾被外界认为是特朗普最亲近的幕僚之一,在2016年大选时任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执行官,特朗普竞选成功后提拔他为白宫首席战略师和高级顾问。班农以极力反移民和纵容排外思想著称,特朗普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有他的身影,美国媒体甚至以“影子总统”来形容班农在白宫的权势。2017年,夏洛茨维尔市白人骚乱在美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在班农的建议下,特朗普没有及时地表达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反对,遭到广泛批评。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班农从白宫离职,卸任后仍旧活跃在美国的决策圈。除班农外,美国政坛的白人至上者不胜枚举。特朗普核心智囊团的成员蓬佩奥、纳瓦罗、莱特希泽、博尔顿等一众“鹰派”人士,无不是清一色的白人老年男性和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他们极端保守、自信、强硬甚至是狂妄和偏激,冷战思维深入骨髓。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等机构指出,美国政治人物越来越多地使用分裂性语言,试图将种族、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边缘化,煽动和助长暴力、不容忍和偏执。
有目共睹,自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甚嚣尘上。比较直观的是与白人至上主义相关的仇恨犯罪攀至高位,2017年8月,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一场白人种族主义集会演变成暴力冲突,导致至少3人死亡、34人受伤;随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郊的一所犹太教堂、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超市接连发生涉及种族仇恨的枪击案,酿成数十人死亡的惨剧。美国反诽谤联盟极端主义中心的报告显示,白人至上主义宣传活动在2020年创下历史新高。据统计,2020年有5125起通过传单、贴纸、横幅和海报等方式散播种族主义相关仇恨信息的案例,几乎是2019年记录的事件数量 (2724起) 的2倍。
2.执法司法领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歧视愈发严重。据 《信使》 杂志网报道,在路易斯维尔市,尽管非洲裔美国人仅占当地驾龄人口的20%,且在搜查中发现违禁品的比率远低于白人,但警察对于非洲裔的搜查却占搜查总次数的57%;有色人种面临更严重的失业威胁,美国劳工部2020年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非洲裔的失业率比白人高出近1倍,英国 《卫报》 网站评论称,“最后被雇佣,最先被解雇”是非洲裔美国人最无奈的现实;种族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华盛顿邮报》 网站报道称,非洲裔美国人的生活处境极为艰难,超过五分之一的非洲裔家庭面临食物匮乏,这一比例超过白人家庭3倍之多。[12]如今,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种族关系很糟糕,56%的人认为特朗普使种族关系恶化,大约三分之二的人表示自从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人们表达种族主义观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黑人对美国的种族状况尤其悲观,超过八成的黑人成年人表示奴隶制遗留下来的问题影响了今天美国黑人的地位。[13]
3.非主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的崛起不容忽视。非主流右翼作为美国保守主义的一个新兴力量,借助2016年特朗普的竞选,由一种边缘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摇身一变成为美国内外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并且透过不同媒介扩张着它的受众规模。非主流右翼的核心主张是白人的身份政治。白人至上主义智库——国家政策研究院的创始人理查德·斯宾塞是非主流右翼的代表人物,并被标榜为“白人至上主义圈子的领导人”。2010年,斯宾塞建立“非主流右翼”网站,用以宣传非主流右翼的思想,强调白人的身份认同和传统白人文化的价值。
非主流右翼没有正规的组织架构,并非严密的政治性组织,它与其他右翼的根本区别在于其追随者以年轻的白人种族主义者为主,主要依托互联网和大众媒体发表言论和组织行动,也因此具备高效的动员能力和迅速的反应能力。非主流右翼的具体主张是宣扬白人至上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反对多元文化主义、反对自由贸易和移民。在2016年的大选中,他们积极支持特朗普竞选。虽然随着特朗普的卸任,非主流右翼的发展势头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弱,但并不会因为某些人物的失势而销声匿迹,其种族主义立场仍然在美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三、余论
总之,特朗普执政的4年间,白人至上运动从之前的社会暗流逐渐涌出水面,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分裂,加深了族裔裂痕。在美国国内,少数族裔继续饱受欺凌排斥,就业和财富的种族差距更加惊人;种族极端恐怖行为密集爆发,族群关系更显紧张;特别是美国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发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全美多地大规模骚乱;而美国亚特兰大发生的连续枪击案,以及近期在美国激增的针对亚裔的无端歧视乃至袭击,则直接导致多地爆发主题为“停止仇恨亚裔”的游行和集会活动。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记者会上表示:前特朗普政府应为美国针对亚裔的犯罪浪潮负有部分责任,“我认为毫无疑问,我们在上届政府执政期间曾看到过一些破坏性言论,指责称新冠病毒为‘武汉病毒’或其他称呼,导致人们对亚裔美国人社区的不准确、不公平的看法,并激发了针对亚裔美国人日益严重的威胁”。[14]美国副总统哈里斯针对亚特兰大枪击案表示,“种族主义、仇外心理、性别歧视在美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一直如此;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身居要职的人们将亚裔群体当作替罪羊,他们利用话语权来散播这种仇恨。”[15]美国现任总统约瑟夫·拜登在其成为白宫新主人的第1天即签署了包括停止修建边境隔离墙、取消对某些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在内的17项行政命令,并在上任第1周签署了《谴责和打击美国境内针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不容忍行为备忘录》。拜登承认,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是长期困扰美国的丑陋毒药。[16]他希望能够推进美国国内所有种族、民族和族裔的包容性和归属感。但很显然,在可预见的未来,白人至上主义仍将继续影响着美国社会,白人至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将依然高悬在美国人民的头上。因为美国政府和社会缺乏的并不是诸如此类的反思,而是消除白人至上主义的切实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