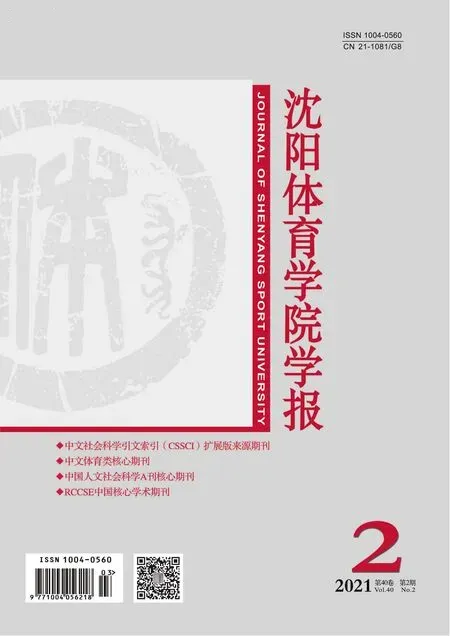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社会学实证研究
张 勇,李 凌
(1. 吉林体育学院,吉林 长春130022;2.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250061)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动各项社会事业增添新动力、开创新局面,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其中幸福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映出人们的社会适应水平及生活质量[1]。与此同时,在全民健身和幸福生活需要的政策引导与现实需求双重推动下,体育参与得以重视与发展,推动了我国社会大众的身体健康及体育社会化进程,提升了人们的生活质量[2]。体育参与和主观幸福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二者的影响关系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焦点。梳理相关文献发现,现有关于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心理机制,同伴关系、社会资本、公共体育服务在其影响关系中的中介效果,老年人体育参与者流畅和休闲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等方面[3-6]。可见,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研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在体育参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对于社会交往、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等社会学概念的探讨相对较少,缺乏对体育参与、社会学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果探析,对把握新时代体育参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仍有欠缺和不足,不能充分反映体育参与在人们获取主观幸福感中的作用路径及影响效果。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社会学实证基础,从体育参与的视角切入,探讨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路径及阶层认同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以厘清新时代背景下体育参与、社会交往、身体健康状况以及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两个社会学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关系,从而较好地指导人们通过体育参与提升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增强主观幸福感。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与社会福利的重要指标,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Diener 等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将主观幸福感定义为人们如何评价自己的生活,并认为其主要包括生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无抑郁和焦虑、积极的情绪等内容[7]。随后,Diener 对主观幸福感进行评估,将主观幸福感分为长期幸福感、愉快的情感和生活满意度3 个方面[8]。此外,主观幸福感包含的诸多因素还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人们通过各种方式提高生活质量、减少不愉快的情感,提升幸福感,因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也得到研究者的关注。Diener 等指出收入和支持性社会关系等成为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因素,且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与人们的健康、社会关系、工作表现和创造力有关[9]。由上述文献可知,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包含较多内容和影响因素的多维度概念,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充当重要的角色。当人们参与体育活动时,主观幸福感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与探析。
体育参与作为一种个体或群体性社会活动,是人们为了实现身心健康、活跃文化生活、加强社会交往等目的,采用体育锻炼、娱乐休闲或健美体育等方法而开展的有意识有计划的体育行为[10],对丰富社会生活与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包含的内容和具体实施的方式比较广泛。刘东锋指出发达国家居民的体育参与项目主要包括健身房健身、高尔夫、网球等,我国居民的体育参与项目主要包括走路、跑步、舞蹈等体育运动[11]。在体育参与方式划分方面,诸多研究将体育参与以概括的形式进行描述,将体育参与分为亲身直接实践的体育活动或体育比赛以及通过大众媒体观看体育比赛的间接参与形式[2,12],从不同的角度对体育参与的内容与形式进行研究,具有较强的应用性与适用性。鉴于此,本研究以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作为体育参与的形式,探究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
1.1 参与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
体育锻炼是以发展身体、增强体质、增进健康、调节精神和丰富文化生活为目的的身体活动[13]。参与体育锻炼作为人们进行社会体育活动的方式之一,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参与体育锻炼与未参与体育锻炼的人相比,参与体育锻炼能够带来更高的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14]。同时,参与体育锻炼能够显著增强人们的身体素质与身体健康水平。Oldervoll 等对医疗患者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参与体育锻炼能够对患者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水平以及体育锻炼能力进行有效的解释与说明[15]。还有研究指出人们的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身体健康水平是衡量主观幸福感的内容和指标[16]。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参与体育锻炼有助于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参与体育锻炼的程度越高,获得的主观幸福感越强。
1.2 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
观看体育比赛属于体育参与的一种形式,是人们通过现场、电视、网络等途径观赏体育赛事的一种行为,能够对观众的认知与行为产生较大影响[17]。观看体育比赛可增加生活趣味、缓解紧张与压力,提升主观幸福感。蒋奖等指出观看体育比赛过程中往往伴随着积极的心理认知体验,能够提升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水平[18]。乔玉成等在研究中指出,体育参与包含“玩”“休闲”“游戏”“运动”“比赛”“观赏”“教育”等许多让人幸福的元素,这些元素均对人的幸福感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19]。可见,观看体育比赛作为观赏性体育活动,能够从人们的心理体验、休闲活动、观赏性活动等诸多角度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作用。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观看体育比赛的程度越高,获得的主观幸福感越强。
1.3 社会交往的中介作用
社会交往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与人之间进行物质、精神交流的相互往来社会活动[20]。社会交往常发生在个体或群体之间,主要包括语言交流、社会网络关系等媒介和载体。在体育锻炼过程中,体育锻炼参与者通过交流体育锻炼方法、效果及经验,建立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提高社会生活质量水平和主观幸福感。Downward 等研究发现基于社会互动的体育运动给体育参与者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会更高[21]。此外,Gatab 等选择80名学生作为实验对象,经实验发现参与体育运动能够降低社交障碍,促进体育参与团队的友谊,建立良好的朋友关系,增加学生的幸福感[22]。与此同时,在观看体育比赛过程中球迷通过分享或交流体育赛事看法,促进球迷交流感情及社会网络关系建设,也能增进人们主观幸福感。Smith 在体育追随者的社会学解析中指出,体育赛事能够促进其追随者的社会交流和交往,对提升人们的社会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23]。Taks 等探讨了举办非大型体育赛事对当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分析发现居民参与或观看体育比赛,促进了居民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刺激了主观幸福感的产生[24]。基于以上理论与文献,本研究认为通过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等体育参与方式,可能通过社会交往这一中间过程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社会交往在参与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假设4:社会交往在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1.4 身体健康状况的中介作用
身体健康是人们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前提与保证,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参与体育活动是提升身体健康状况的有效方式。Huang 等研究表明参与体育锻炼能够提高身体素质,增进心理健康,且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可以有效增强人们的主观幸福感[25]。乔玉成等从生物学角度分析,发现参与体育锻炼能够刺激运动器官,给身体带来健康效应,促进人们产生幸福感体验[19]。观看体育比赛作为一种休闲活动,虽不能直接导致身体素质发生变化,但人们通过观看体育比赛能够产生积极的情绪、情感或提升心理体验,增进心理健康,人们生活方式与健康行为也会因此改变,导致身体健康状况得到改善,主观幸福感增强。Inoue 等研究表明老年人通过观看体育比赛获得情感支持增强心理健康,并促使他们更加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体育休闲活动,以保持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增强生活的主观幸福感体验[26]。此外,观看体育比赛能够引发人们积极的健康行为。Ateca -Amestoy 等研究发现个体通过参与或观看重大体育赛事,增强积极情感与观赛体验,并激发他们积极参与社区体育实践、体育文化活动等健康行为,以不断提升身体健康水平,增进个体的主观幸福感[27]。基于以上理论与文献,本研究认为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增强人们的身心健康与健康行为,进而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身体健康状况在参与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假设6:身体健康状况在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1.5 阶层认同的调节作用
阶层认同源于阶层意识,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指个体对所处社会阶层和意识形态位置的认识[28]。阶层认同是影响人们行为活动与主观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方面。Levin 等指出参加体育活动会提升彼此间的社会联系,具有低认同感的参与者会与高认同感的参与者相联系,从而产生与高认同感参与者相同的幸福感[29]。Wann 等在研究中也发现体育活动参与者的团队阶层认同感越高,参与体育活动带来的幸福感体验也越高[30]。观看体育比赛作为体育参与的另一种形式,其具有丰富的享乐体验和积极情绪效应。然而,不同类型的体育比赛代表不同阶层人群的偏好,将表现出明显的阶层区隔,人们的体验也会不同。Wilson 在社会学研究中发现,具有高阶层认同的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比较高,观赏的体育赛事类型与其他人相比有很大区别,其产生的主观幸福感会更强烈[31]。另外,人们还经常与他人进行对比或和同阶层人群相联系,触发个体主观意识与心理感受,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Jang 等研究发现体育赛事观众对球队会产生较大的阶层认同感,球队的比赛结果会影响观众的情绪及主观幸福感[32]。基于以上理论与文献,本研究认为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提升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阶层认同的调节作用,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7:阶层认同调节参与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
假设8:阶层认同调节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
1.6 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
社会经济地位是指个体在社会中的经济水平及社会地位,家庭经济收入、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家庭集体名誉成为代表社会经济地位的因素[33]。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会影响人们参与体育锻炼或观看体育比赛的质量与水平,导致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受到一定影响,如Gorely 等指出社会经济地位高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带来的幸福感体验更丰富[34]。Reyes 通过对菲律宾人的体育参与、社会人口学变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体育参与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主观幸福感与体育参与的重要关系[35]。此外,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会与社会经济地位和体育健康行为相关联,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获得主观幸福感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别。Peltzer等对来自亚洲、非洲和美洲等24 个国家的25 所大学的学生进行匿名调查,研究发现积极的健康行为和消极的健康行为都与幸福感相关,但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大部分表现为积极的健康行为和较高的主观幸福感[36]。经济状况亦是反映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Sedlarski 发现社会经济水平、相对收入以及消费水平会影响观看体育赛事和主观幸福感水平[37]。基于以上理论与文献,本研究认为通过参与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等体育参与方式提升主观幸福感时,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发挥调节作用,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9:社会经济地位调节参与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
假设10:社会经济地位调节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
综合以上对相关变量的关系论证与假设关系推导,构建出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两种体育参与方式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概念模型(图1)。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工具
为探析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社会交往和身体健康状况在其影响关系间的中介效果,以及阶层认同和社会经济地位在其影响关系中的调节效果,本研究以问卷为测量工具,对人们参与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社会交往、身体健康状况、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主观幸福感进行测量。调查问卷主要由以下7 个部分组成,具体设计情况为:

图1 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关系的概念模型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particip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参与体育锻炼问卷(Participate in Physical Exercise Scale)参考梁德清设计的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ARS-3),该量表主要包括参与体育锻炼的强度、时间、频率3 个方面,测量题项最高分为100 分,最低分为0 分[38]。从体育锻炼的强度、每次体育锻炼的时间、体育锻炼的频率、体育锻炼的时间(年限)方面,共设计4 个题项,同时为了使填答者更加直观地了解测试内容,采用李克特6 点评分的方式进行测量,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58。
观看体育比赛问卷(Watch Sports Games Scale)参考Mehus 和刘米娜对观看体育比赛的测量,主要包括观看体育比赛的频率、年限、类型3 个方面[39-40]。从观看体育比赛的频率、年限、类型以及方式共设计4 个题项,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50。
社会交往问卷(Social Interaction Scale)参考胡荣等研究的社会交往量表,目的在于测量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共包含8 个问项,采用6 点计分的方式[41]。从参与社团活动、协会活动、与朋友联系方面,共设计3 个题项,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56。
身体健康状况问卷(Physical Health Scale)参考许军对自测健康的评定量表(SRHMS V1.0),该量表共包括10 个维度和生理、心理、社会健康3 个子量表,包含46 个问项[42]。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参考3 个子量表的内容,从身体健康、身体活动功能、自我情绪、社会适应方面共设计4 个题项,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85。
阶层认同问卷(Class Identity Scale)参考闰丙金对社会阶层认同与社会阶层变化认同的测量问项,以及周葆华对主观阶层认同的测量问项[43-44]。从自我阶层判断、阶层变化、社会声望3 个方面,共设计3 个题项,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57。
社会经济地位问卷(Socioeconomic Status Scale)参考Quon 测量主观社会经济地位(SES)的问项,同时也参考陈于宁等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45-46]。从社会经济地位判断、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位置、个体在体育运动圈中的位置方面共设计3 个题项,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27。
主观幸福感问卷(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参考邢占军编制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SWBS-CC),该量表共包含57 个项目,采用6 点计分的方法[47]。从生活满意度、生活幸福度、生活质量方面共设计3 个题项,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743。
2.2 数据调查
本研究选取长春、济南、太原、北京、上海、福州、广州为调查地点,同时研究主要探究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调查的对象应具备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的经历。根据研究目的的判断,并保证调查对象具有更好的针对性和代表性,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式,共发放2 000 份问卷,收回问卷1 723 份,剔除无效问卷72 份,最终有效问卷1 651份,有效回收率达82.55%。在回收的有效问卷中,男性占比55.4%,女性占比44.6%;在年龄方面,20岁以下占5.5%,20 ~39 岁之间占23.1%,30 ~39岁占33.6%,40 ~49 岁占22.9%,50 ~59 岁占10.1%,60 岁及以上占4.8%;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占9.4%,初中占18%,高中占34.4%,大学占23.7%,研究生及以上占14.4%;在收入水平方面,低收入水平占14.8%,中等收入占51.4%,高等收入占33.8%。综合调查对象的人口特征信息可知,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20 ~59 岁高中及以上学历的中高等收入的社会大众。
2.3 信效度检验
信度检验主要采用克隆巴赫α 系数、CR 值进行衡量,以验证量表的可靠性。经检验,整体量表的克隆巴赫α 系数为0.890,且参与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社会交往、身体健康状况、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主观幸福感各部分量表的克隆巴赫α 系数均达到0.7 的标准。此外,本研究还通过组合信度CR值进行检验,经检验各变量的CR 值达到0.6 的标准,表明量表的信度较好(表1)。
效度指调查的结果反映理论上概念的程度,也是指问卷所能衡量到理论上期望的特征的程度。为检验研究整体问卷的效度,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表2 结果显示各项测量指数均在较好的范围内,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然后引用李凌等整理的拟合指标标准来源[48],将各项拟合指标以结果摘要表进行呈现。

表1 变量信度结果摘要Table 1 Summary of variable reliability results

表2 模型拟合度指标摘要Table 2 Summary table of model fit index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共同方法偏差是指使用同种测量工具会导致特质间产生虚假的共同变异,常见于自陈量表的测量数据中。被试者在填答问卷过程中或参与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社会交往、身体健康状况、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主观幸福感这7 个项目特征之间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故本研究采用Harman 单因子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在进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得到的第一个单因子解释变异为28.64%( <40%),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49]。
3.2 相关分析
本研究运用Spearman 相关性检验,验证参与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社会交往、身体健康状况、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主观幸福感两两变量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两两变量间的相关性均达到P <0.01 的显著正相关(表3),且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7,说明变量间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可进行后续的统计分析。

表3 变量间相关分析结果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among variables
3.3 参与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
为验证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出参与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社会交往、身体健康状况、主观幸福感的整体影响关系路径模型(图2),并参考模型适配度指标,对各路径关系进行验证。

图2 参与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Figure 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influence of participation in physical exercise and watching sports games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根据模型适配指标进行修正,模型的适配结果显示:RMSEA 为0.041,NFI =0.956、RFI =0.947、IFI =0.968、CFI =0.967、GFI =0.968、AGFI =0.956均满足大于0.9 的标准,且χ2/df 为3.760,各项指标基本符合要求,说明模型的适配度较好。在此基础上,进行参与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检验。由表4 可知,参与体育锻炼→社会交往、参与体育锻炼→身体健康状况、参与体育锻炼→主观幸福感的P 值均在0.001 的水平下显著,参与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表明参与体育锻炼的程度越高,获得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假设1 成立。观看体育比赛→社会交往、观看体育比赛→身体健康状况、观看体育比赛→主观幸福感的P 值均在0.001 的水平下显著,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表明观看体育比赛的程度越高,获得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假设2 成立。
3.4 社会交往和身体健康状况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将社会交往、身体健康状况在参与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以及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分别构建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设置为1、2、3、4,并对每个模型的适配度进行检验(图3)。

表4 各路径的因子载荷Table 4 Factor load of each path

图3 社会交往和身体健康状况的中介作用检验的结构方程模型Figure 3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for mediating role test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physical health
经检验,4 个模型的NFI、RFI、IFI、CFI、GFI、AGFI 均达到0.9 的标准,且RMSEA 与χ2/df 的结果较好,说明4 个模型的适配度较好(表5)。

表5 模型拟合度指标Table 5 Model fit index
在模型适配度较好的基础上,检验社会交往和身体健康状况在参与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关系间的中介效果,具体检验结果见表6。

表6 Bootstrap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Table 6 Analysis results of bootstrap intermediary effect
由表6 中模型1 与模型2 检验结果可知,在参与体育锻炼分别经社会交往与身体健康状况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直接效应的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P 值均为0.001,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的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也均不包含0,P值均为0.001,间接效应显著,社会交往和身体健康状况在参与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均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假设3 与假设5 成立。同理,由模型3 与模型4 检验结果可知,在观看体育比赛分别经社会交往与身体健康状况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直接效应的95% Bootstrap 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P 值均为0.001,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的95%Bootstrap 置信区间也均不包含0,P 值均为0.001,间接效应显著,社会交往和身体健康状况在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均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假设4 与假设6 成立。
3.5 阶层认同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
为检验阶层认同和社会经济地位在参与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及在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分别以参与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中心化后的参与体育锻炼×阶层认同、参与体育锻炼×社会经济地位、观看体育比赛×阶层认同、观看体育比赛×社会经济地位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采用回归分析进行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7。

表7 回归分析结果Table 7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根据表7 回归分析检验结果,模型5 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未产生显著的影响。模型7 检验结果显示,参与体育锻炼与阶层认同的乘积项显著(β =0.144,P <0.001),表明阶层认同在参与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假设7 成立。模型9 检验结果显示,参与体育锻炼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乘积项显著(β =0.155,P <0.001),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在参与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假设9 成立。模型11 检验结果显示,观看体育比赛与阶层认同的乘积项显著(β =0.116,P <0.001),表明阶层认同在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假设8成立。模型13 检验结果显示,观看体育比赛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乘积项显著(β =0.173,P <0.001),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在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显著,假设10 成立。
3.6 讨论
3.6.1 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的直接作用
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的程度越高,获得的主观幸福感越强,与研究假设1 和假设2 相符,表明人们通过参与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等体育参与方式增加了对生活质量的评价,获得更强的主观幸福感,这一研究结果与诸多研究相符合。Garatachea 等研究结果证明了通过参与体育锻炼进行身体活动,能够显著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50]。此外,Buecker 等采用Mate 分析的方法,对体育活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严格测试,结果也证明了参与体育锻炼活动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关系[51]。同样地,观看体育比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也得到诸多研究的证实。Kavetsos 等对欧洲12 个国家举办的3 个大型体育活动的观众进行调查,发现观看体育比赛能够增强观众的主观幸福感体验[52]。Tang 等通过研究也发现,观看体育比赛能够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53]。经以上讨论与分析,有效地证明了概念模型中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路径关系。针对这一研究结果,本研究认为在体育强国建设的背景下,可通过“全民健身”政策引导加强个体的体育锻炼意识,让更多的社会大众参与体育锻炼,推动大众体育发展;创新“体育+传媒”的体育赛事传播体系,丰富观看体育比赛的方式或渠道,激发更多人观看体育比赛的兴趣,充分发挥人们通过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作用。
3.6.2 社会交往的中介作用 社会交往分别在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与研究假设3 和假设4 相符,表明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既可以直接提升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社会交往提升主观幸福感。同时该研究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Kim等的研究发现,参与体育锻炼与幸福感正相关,社会交往与幸福感正相关,社会交往在参与体育锻炼与幸福感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54]。Wang 等的实证研究也发现,通过观看体育比赛、参与体育活动、旅游等休闲体育活动能够与个人的幸福感建立较强的影响关系,并且人们在进行休闲体育活动时,可以促进社会和人际交往,进而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55]。经以上讨论与分析,可以认为社会交往在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影响主观幸福感两条路径中的中介作用具有较好的合理性,且本研究概念模型中社会交往中介作用的两条路径关系也得到较好印证。鉴于此,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可充分利用传媒,更好地宣传与传播体育比赛,以形成较为深厚的体育赛事文化氛围,促进更多社会大众参与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等社会体育活动,增加社会交往,扩大社会网络关系,提升生活的满意度,为建立良好的主观幸福感提供前提条件。
3.6.3 身体健康状况的中介作用 身体健康状况分别在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与研究假设5 和假设6 相符,表明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既可以直接提升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身体健康状况提升主观幸福感。该结果与Ruseski 等的研究结果一致[56],即体育参与能够提升身体健康状况,同时身体健康状况又是预测幸福感的重要前提因素,三者互相关联,形成了体育参与—身体健康状况—幸福感的作用路径关系。此外,Lera-Lopez 研究发现人们通过参与体育锻炼、观看体育比赛、收听体育节目等体育参与方式,起到了放松身心以及增进身体健康的作用,对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具有显著的效果[57]。如前所述,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是提升身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条件,而身体健康状况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因子。可见,身体健康状况分别在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具有较高的合理性。与此同时,本研究概念模型中身体健康状况中介作用的两条路径关系也得到较好印证。在现实生活中可增加社会体育指导专业人才的投放,以提升社会大众体育锻炼效率,使其切身体验到体育锻炼带来的健康效益,并鼓励人们经常观看体育比赛,以缓解生活压力,保持心理健康,充分发挥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的功能,提升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从而为有效增进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做好基础性工作。
3.6.4 阶层认同的调节作用 阶层认同分别调节了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与研究假设7 和假设8 相符,该结果进一步反馈了研究概念模型中阶层认同调节作用的假设关系。这表明人们在参与体育锻炼或者观看体育比赛增强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会受到阶层认同的调节作用。就阶层认同调节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而言,国内学者并未充分涉及,如黄赞等仅探究了观众对球队的身份认同感显著调节观看体育比赛结果对情绪的影响[58]。相比较而言,国外学者Wilson 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社会阶层越高的人群,社会阶层认同感越强,越喜欢参与体育运动,随之产生的主观幸福感更强烈[31]。此外,Jang 等从观看体育比赛的角度,兼顾阶层认同的调节作用,探究了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尽管观看体育比赛对观众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的影响,但阶层认同感高的人,观看体育比赛带来的主观幸福感会更强烈[32]。可见,阶层认同在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影响主观幸福感中的调节作用具有合理性。具体到社会实践中,在不同阶层认同的情况下,人们通过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获得的主观幸福感也会不同;因而应对自己所处社会阶层进行认知,明晰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异性,以形成良好的阶层认同感,增强生活满意度,充分发挥阶层认同在通过体育参与获得主观幸福感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3.6.5 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 社会经济地位分别调节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与研究假设9 和假设10 相符,结果进一步反馈了研究概念模型中社会经济地位具有调节作用的假设关系。这表明人们在参与体育锻炼或者观看体育比赛增强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会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就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而言,国内相关学者仅对社会经济地位对体育健康不平等的关系进行探讨[59]。然而,国外相关研究则对社会经济地位调节作用有所涉及,如Inouye等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处于劣势的人们,参与体育活动后表现出较少的健康行为和较低的幸福感[60]。此外,Peltzer 等和Sedlarski 将经济水平作为体现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研究结论表明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参与体育锻炼或观看体育比赛产生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也较高[36-37]。如上所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产生的主观幸福感体验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有较大差别,社会经济地位成为调节获得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调节了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且此调节作用关系具有较好的合理性。在获取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人们应积极对待社会生活,努力提高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从而为通过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等体育参与方式获得主观幸福感提供保障与支持,以提升社会生活质量与主观幸福感。
4 结论与展望
1)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的程度越高,获得的主观幸福感越强。2)社会交往分别在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3)身体健康状况分别在参与体育锻炼和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4)阶层认同调节参与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且阶层认同也调节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5)社会经济地位调节参与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且社会经济地位也调节观看体育比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
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体育参与、社会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对指导人们通过体育参与提升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引导人们明晰阶层认同和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学因素对获得主观幸福感产生的影响,以更有效地通过体育参与增强主观幸福感具有较好的实践意义。后续研究还可从纵向研究的角度,探索随着社会时代进步与发展,社会大众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此外,基于社会学概念考虑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研究还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析体育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关系,以从更多角度发现社会大众通过体育参与获取幸福感的多种影响因素,丰富主观幸福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