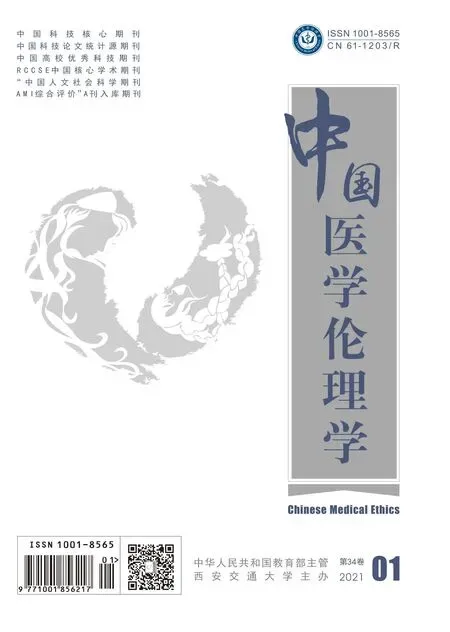年轻乳腺癌患者生育力保存的治疗与伦理思考*
王 彬,李燕姿
(1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陕西 西安 710061,february111@163.com;2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部,陕西 西安 710061)
1 中国年轻乳腺癌患者特征及困境
1.1 年轻乳腺癌患者的特征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乳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且发病率更年轻化,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患者的发病年龄比欧美国家早近十年,平均发病年龄48.7岁[1],年轻乳腺癌特指发病年龄在35岁及其以下的乳腺患者。在西方发达国家,40岁以下的乳腺癌患者在全部乳腺癌患者中所占比例低于7%[2],而在中国这个比例已经超过了10%,这其中,还有部分极年轻乳腺癌患者(≤25岁)[3]。
年轻女性乳腺癌通常具有侵袭性肿瘤生物子特征和较高复发风险,肿瘤生物学行为随人体内分泌、微环境调控而变化,年龄作为预后因素仍需论证。与老年乳腺癌相比,年轻乳腺癌在诊断时往往临床分期较晚,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HER-2)阴性的三阴性乳腺癌和HER-2阳性型乳腺癌比例更高。不仅如此,年轻乳腺癌更具有遗传倾向,涉及不同的信号通路及乳腺癌常见的易感基因,研究表明,年轻乳腺癌患者胚系图变频率达24%,极年轻乳腺癌患者突变率高达50%[4],因此,年轻乳腺癌在临床、病理和遗传方面具有特殊性。
1.2 年轻乳腺癌患者的困境
由于患者的年轻化,相当一部分患者在确诊时未婚未育或已婚未育,对于这部分患者,如果直接针对疾病本身进行标准抗肿瘤治疗,那么在日后会面临生育力受损及提前闭经等问题,这将对患者造成生理、心理、家庭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影响生育主要有三方面:抗肿瘤治疗对生殖系统的直接损害、因治疗错过生育年龄和怀孕对肿瘤复发率的影响。
化疗是降低乳腺癌复发率的基石,但是其对成熟卵泡的影响可导致可逆性停经,对原始卵泡的损伤可导致卵巢早衰及停经,从而导致不育。尤其是乳腺癌经典方案中的以环磷酰胺为代表的烷化剂对卵巢毒性最大。此外还有针对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高危患者需要通过摘除卵巢或注射戈舍瑞林达到人工绝经的目的[5]。低危年轻乳腺癌患者通常选用他莫昔芬,该药不但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动物实验也证实长期的他莫昔芬暴露可导致胎儿畸形风险[6]。不仅如此,标准的内分泌治疗至少是5年,多项实验结果提示分期较晚的高危患者还需将内分泌治疗延长至10年[7]。如果不中断抗肿瘤治疗,育龄女性势必面临高龄问题,高龄产妇所怀胎儿患21三体综合征等疾病较适龄产妇均明显增加,更不用说标准抗肿瘤治疗对卵子有致畸作用。
怀孕对肿瘤复发的影响一直是研究的热点。瑞典学者Valachis等[8]发表的meta分析,回顾了49470例绝经前患者,分析表明,在早期乳腺癌确诊10个月后妊娠不会对预后造成不利。上述数据主要来自欧美人群,2019年11月中国台湾“卫生研究院”研究比较了中国台湾地区乳腺癌患者妊娠与否的总死亡率。结果,乳腺癌确诊后妊娠患者与未妊娠对照患者相比:总死亡比例降低56%,雌激素受体阳性患者死亡比例低于77%,确诊三年后妊娠患者死亡比例低于81%[9]。因此综合目前国内外数据,从安全性来讲,乳腺癌治疗后再生育是可供选择的。
2 中国年轻乳腺癌患者再生育的方式选择及伦理问题
2.1 夫妻生育权冲突
一般情况下,出现夫妻生育权冲突问题的多为已婚未育的年轻乳腺癌患者。女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2018年修正)第五十一条规定作为法律依据:“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在罹患乳腺癌之后,女方及女方家人经常为了不中断标准抗癌治疗而拒绝生育;男方及男方家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15年修正)第十七条规定作为法律依据:“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男方认为拒绝生育剥夺了其生育的权利。拒绝生育和要求生育,都依照“生育权”,反过来说,生育权也包括生育自由和不生育自由[10]。当双方都为了保存自身利益而做出相反选择时,冲突必然会出现,甚至会破坏家庭和睦。由于生理构造的不同,女性角色本身在生育过程中必然承受更多身心上的负担,再加上罹患恶性疾病,法律会适当照顾女方。尽管如此,一旦家庭破裂,势必会对夫妻双方造成伤害。
2.2 不婚不育的伦理问题
一般出现该类问题的为未婚未育年轻乳腺癌患者。对于未婚的年轻乳腺癌患者,在诊疗过程中不但要重视“病”,更要重视“人”。尽管年轻患者保乳手术后局部复发率高于老年患者,但只要乳房条件允许,在手术方式的选择上仍然会更倾向于保乳手术。即使是实在无保乳条件,也多会建议假体植入,以保存部分形态。主要是为了帮助这些患者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能够尽早融入正常生活和回归社会。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认为自己“不完整”,丧失自信心而抗拒婚恋。当前,不婚不育作为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应得到社会的广泛接纳。尽管不婚不育不会对他人和社会构成危害,但是会带来家庭伦理方面的缺失,对于因病导致不婚不育的患者,不但要承受生理上的病痛,还需承受心理上的痛苦。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2.3 生育力保护可供选择的方案
生育力保存(fertility preservation)是指保存卵子或生殖组织的方法和手段,适用于有不孕不育风险的人群和治疗某些疾病可能会影响生育功能的患者。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年轻女性乳腺癌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患者获得了长期生存的可能,甚至走向治愈,因此“获得后代”这个需求就越来越受到重视,生育能力的保存让乳腺癌的治疗不再是单纯的治病,而是对人的综合救治。根据2019《年轻乳腺癌诊疗与生育管理专家共识》[11-12],生育力保存技术涉及药物、手术或冷冻技术等不同的助孕方法。
对于乳腺癌患者,目前在临床最为常用的方式是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GnRH-α)卵巢抑制,因为其操作简单便捷在临床上得到了推广。GnRH-α的机制是通过药物性垂体-卵巢抑制,使处于静止期的细胞对化疗药物敏感性降低,理论上降低了化疗药的毒性。目前尽管临床最常使用,但是关于GnRH-α对生育力保护的效果存在较多争议。美国临床肿瘤协会最新指南指出,只有当其他方法都不可行时再考虑使用GnRH-α。
对于已婚且婚姻关系稳定的家庭,胚胎冷冻是最成熟的生育力保护方案[13]。虽然此类患者获得的优质胚胎不多,但获取卵母细胞的数量、受精率、活产数及妊娠并发症的发生率与非肿瘤患者比较无明显差别。肿瘤患者往往需要尽早治疗,可以在自然月经周期中取出成熟卵子受精,并冻存胚胎。对于未结婚的女性恶性肿瘤患者,卵母细胞冷冻技术更加适用[14]。卵母细胞冷冻技术分为成熟卵母细胞冻存和非成熟卵母细胞冻存。成熟卵母细胞冻存为促排卵后获取的卵母细胞,避免了胚胎冷冻的伦理和道德问题,但促排卵会使用激素类药物,有促进乳腺癌进展的风险,且妊娠率相对于胚胎冷冻技术较低。而非成熟卵母细胞冻存,是在化疗或放疗前10~14天取出未成熟卵母细胞进行冷冻,在体外模拟体内成熟的微环境,将卵母细胞体外成熟培养成为成熟卵母细胞。卵巢组织冻存和移植是目前情况下保护儿童未来生育力唯一可选择的方法[15]。卵巢组织冷冻要在放化疗前至少3天进行,主要是在癌症治疗前移取富含卵母细胞的卵巢皮质进行冻存,在治疗结束后再移植回体内。虽然人类卵巢组织移植至今已经有一百多例活产数,但是移植部位血管再生缓慢导致大量卵泡的丢失是其移植失败的重要原因。
2.4 生育力保护的伦理困境
这些助孕方法已经改变或替代了人类自然生殖的一个或多个环节,让科技延伸至干预甚至创造生命,这是生殖医学领域的一场巨大的科技革命,同时,它带来的伦理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比如:谁可以处置冷冻胚胎?该如何处置未被采用的冷冻胚胎?谁有权力销毁胚胎?乳腺癌患者是有死亡概率的,那么更具伦理争议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当我们强调生育后代是其权利的同时,也不能否认养育后代是其义务。对于部分高危的乳腺癌患者来说,高复发概率意味着长期生存概率有限,那么这部分患者从自身条件是否适合再次安全生育,以及患者是否能履行养育子女义务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乳腺癌这种有家族遗传风险的疾病,是否接受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技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是否能有效甄别遗传风险的高与低?对于单性别遗传性疾病,是否能依靠生殖科技来选择胎儿性别?患者死亡后冻存的胚胎丈夫是否有权使用?冻存的胚胎是否可由患者以外的他人代孕?患者夫妇倘若离婚,该如何处理冻存的胚胎?甚至几十年后,患者夫妇均已死亡,其生前冷冻的胚胎该由谁监管和处置?这些都是当前的伦理困境。
3 中国年轻乳腺癌患者再生育伦理问题的解决方案
3.1 充分协商沟通
协商沟涌包括夫妻双方的协商沟通和医患之间的协商沟通。
对于夫妻双方,罹患乳腺癌本身是小概率事件,对于没有家族史的患者及家庭来说,无异于一个意外。因此在做出任何重大决定时,夫妻双方不仅要考虑自身利益,也要换位站在配偶的角度,考虑是否生育、何时生育等问题。夫妻应当充分听取乳腺专科医师及生殖专科医师的建议,结合疾病发展规律,避开复发高危时段,同时充分考虑患者本人意愿和配偶态度,本着对家庭及社会负责的态度,由双方协商决定。充分沟通是解决夫妻间分歧的基本原则。
对于医患之间,传统的“医者主导”的临床决策主要是以临床指南、临床实践及实验室指标为主要参考依据[16]。这样的临床决策中,缺少了人文的关怀。因为除了治疗疾病本身,医生也应该综合关注患者这个“人”,包括患者的心理需求、家庭因素和经济条件。良好的医患沟通可以针对患者所处的婚姻及经济状况,选择更为合适且个体化的综合治疗方案,尽可能照顾患者的生育要求,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因此,患者需要和医生充分沟通,充分表达诉求。
在2019年圣安东尼奥乳腺癌年会上,我国广东省中医院的一项前瞻性、横断面研究调查通过对中国2000名乳腺专科医师关于“年轻早期乳腺癌患者术后生育问题的态度”进行调查,发现医师的性别、临床实践年限不同会导致医师态度的显著差异。医师态度的差异会导致治疗方案制定的不同,这就要求主诊医师要为患者提供其做决定所必需的足够信息,让患者及家属充分知情,待其权衡利弊后,对医师所拟订的诊疗方案做出选择。这也体现了医疗行为的人文性及对患者的尊重。不仅如此,年轻乳腺癌患者对于突如其来的变故可能并没有成熟的心理去应对,而我国现状是患者父母或配偶会在决定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也需要一个机构审查委员会来审查和批准来自家人的知情同意。
此外,多学科诊疗模式(MDT)是现代医疗领域备受推崇的合作诊疗模式。MDT在打破学科之间壁垒的同时,可以综合制定出更周全、更个体化的方案。包括乳腺内科、外科、放疗科、妇产科、生殖科、肿瘤心理学科和乳腺专科护士等在内的各学科专家,也应充分协商沟通,为年轻患者制定出一个安全、实用、人性化的诊疗方案。
3.2 完善规章制度
《年轻乳腺癌诊疗与生育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推荐年轻乳腺癌患者及家庭可考虑辅助生殖技术[11- 12],但目前我国并没有一部针对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和实施以及后续权利保障等各个具体层面的法律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作为管理规范,由于缺乏对诸多细节的规定,特别是在保障这些女性患者的生育权的同时,如果其隐私权、处置权、使用权受到侵犯,应该怎样追责,也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并不能满足愈发复杂的社会需求。各种规章制度相对社会发展总有滞后性,法律的变更也非一朝一夕,但我们需要对由此带来的各种伦理问题以及此类问题的改善办法进行思考和理性反思,提高认知,及时规范化,才能降低风险。相关法律政策及管理规范应当由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相关学科专家合作,结合临床研究实践结果和中国国情,充分考虑各种已暴露的现实问题,制订出细化且人性化的政策,并进一步规范完善。只有法规达到一定层级的时候,各个部门进行合作,才能监管实施到位。
3.3 多中心临床研究的开展
尽管目前有一些研究和分析,提示罹患乳腺癌后在与肿瘤医师充分讨论肿瘤复发风险后怀孕,有可能是安全的,但是经治乳腺癌患者妊娠率仅为3%,比一般人群妊娠率低40%,并且样本量并不大[17],亚洲群里的数据更是不足。也有专家提出,被允许怀孕的这部分患者本来也是专家筛选过的低危患者,其结论有偏倚,不宜推广。不仅如此,有限的研究仍然有很多数据盲点,例如年轻患者最佳的怀孕时机无法准确预测,患者乳腺癌免疫组化分型是否影响怀孕,如何评估和预测肿瘤复发危险度,是否可进行患侧或对侧乳腺哺乳等。因此,开展国际多中心大样本临床实验或回顾性研究是为将来制定政策和指南提供参考的重要手段。
4 总结
科技的发展为年轻乳腺癌患者在完成肿瘤治疗后成功妊娠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也带来了多方面的挑战。育龄期乳腺癌患者生育咨询仍然需要多学科合作,为有生育需求的年轻乳腺癌患者提供更为个体化和更有效的治疗策略。育龄期乳腺癌患者生育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亦需要大规模临床研究予以证实。必须强调的是,针对年轻女性保存生育潜能的方案相当复杂,成功率也较低,很多方面还不成熟,或因为技术本身,或因为面对的人群。这一新的生殖医学领域产生了诸多涉及卵子收集以及卵子使用方面的伦理问题,需要在未来实践中充分发挥伦理监督作用。抗癌治疗的过程中,应当以保护患者为基本原则,充分尊重患者主观意愿,充分告知生育力保存的利弊,贯彻真实的知情同意,最大限度地保存患者生育力。相关部门及社会也应当针对生育力保存带来的伦理问题给予足够关注并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及法律,为年轻乳腺癌患者提供更多的生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