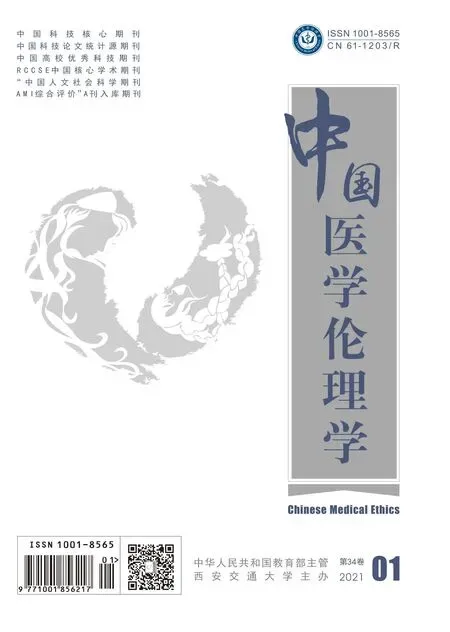论医学伦理叙事的价值诉求和伦理限度*
杨 勇
(广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1,yangyong-0720@163.com)
叙事的字面意思是讲故事,它最早是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方法用以描述真实或者虚构的事件。叙事方法所具有的独特的人文气质与医学的初心使命具有天然耦合性,正是基于叙事与医学的这种先天亲缘关系,叙事医学的发展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叙事医学”的概念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Rita Charon教授在2001年最早提出,她从学科融合视角把叙事与医学两个学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推动医学发展从技术治疗向价值关怀回归,为现代医学高质量发展开启新的维度。2015年,Rita Charon教授的著作《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中译本正式出版,表明叙事医学在我国已经朝着学科化方向发展。叙事医学越来越被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在叙事过程中体现的对主体价值的关怀与反思,在主体反思中厘定伦理关系的同时又强化了医学实践中的主体价值。医学伦理学是以临床实践中主体关系为对象,以主体价值诉求为核心的学科,它与叙事医学之间是同向而行的关系。叙事为医学伦理的教学提供有效的方法,医学伦理学又为叙事医学提供教育实践境遇。医学伦理实践中的伦理限度和价值诉求之间形成的张力又为叙事提供了言说的力量,医学伦理叙事的出现反映了现阶段医学发展亟待回归人文的诉求和趋势。
1 医学伦理教育中的叙事面向
韩启德在第二届中国医学人文大会上指出:叙事医学让医学人文走向临床,推动叙事医学的发展就要求训练医生如何见证患者的苦难[1]。可见,叙事是一种使医学回归应有温度的教育方法。医生在倾听患者故事的过程中提升医学温度,在提升医学温度的过程中塑造人文情怀。如Rita Charon所言:“医生在掌握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的同时,需要学习倾听患者,尽最大努力理解疾病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尊重患者对于疾病叙事意义的理解,并为所看到的而感动,从而在行动中能够为患者着想。”[2]叙事医学使医生的情感融入患者的生命,站在生命主体的立场与患者产生情感共鸣,使医患之间断裂的共同体关系弥合重生。因此,叙事医学作为对现代医学人文培育短板矫正的最有效的方式,它有益于医学人文突破技术思维限域的制约,推动现代医学发展回归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叙事医学既是对缺失人文关怀的医学实践的一种主体性价值的确证;同时,它又丰富了医学人文关怀的内涵,以主体在场的方式呈现医学实践的本真诉求。叙事医学的发展体现了医学价值和教育使命的终极融合,它促使理论教育和临床实践有机结合,形成最有效的教育合力,在合力中彰显医学初心的人本价值和生命意义。
近代以来,生物医学模式的发展使医学渐渐失去了应有的温度,演变成了以技术主导的临床实践活动。技术至上的医学思维模式把医生与患者原本共同体一分为二地割裂开来,成了制约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一道屏障。当下这种技术主导的思维仍存在于许多临床医生的潜意识中,如在临床诊断过程中的惯性式的“见病不见人”的思维模式。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虽然越来越多的患者对疾病信息有了更多了解,诊疗过程中患者自主权的显现也愈加明显,但是在对诊疗方案的合理性判断方面并不具有更多行之有效的决定权,医患双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使医生具有更多潜在的主动权,这就使医生更容易滋生“见病不见人”的思维情绪。“有一项调查研究表明,64%的人表示,如果自己得了癌症,他们希望可以自己选择治疗方式;但是真正得了癌症的人中只有12%希望由自己作决定”[3],事实也证明,患者对医生抱有更大的依赖性,医生在缺乏伦理情感的情况下中极易出现“家长式作风”的诊治决策。这种不对称并且显得不平等的诊治关系中因为患者主体性地位缺失为医患之间有效沟通设置了层层障碍,同时,造成医学的人本价值与工具价值本末倒置,进而造成了医学叛经离道式的异化发展。技术至上的临床思维模式是引起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内容被边缘化的现象,致使人文价值对技术的范导引领的作用尽失。牛津大学医学伦理学教授托尼·霍普教授在其著作《医学伦理学》中明确提出:“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伦理价值是医学的核心”[4],医学发展偏离了价值诉求只能进入穷途末路的 “死胡同”。所以,“医学人文价值决定了医学对象首先应该是人”“人类与疾病抗争中彰显的人本价值乃是医学的终极价值。”[5]叙事与医学的终极价值使二者有了重要交集,医学伦理就是立足在这个交集对医学主体性进行伦理分析。
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专业培养医学生道德思维和道德实践能力的课程,其目标是培养医学生成为具有审辨医学伦理关系和应对医学道德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基于道德审视的维度,要求在医学实践中体现对人健康利益和人格尊严关注的双重价值取向。孙慕义教授指出:“当代医学伦理学背负着人类的命运,并始终针对公民健康权利的维护等重大社会与时代问题,是生命科学和人文科学间的纽带,业已成为哲学与伦理学中的焦点学科。”[5]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连接人文与医学的交叉学科,与叙事医学的发展是同向关系。二者在同向发展的道路上又互为目的与手段,伦理价值以其本真之善为叙事内容提供理念的向度引导,叙事方法作为实现医学价值的手段之一,又为医学伦理分析提供主体性价值的生动勾画路径,二者结合相得益彰为医学主体性价值守驾护航。通过叙事呈现的医学伦理学,一方面使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主体间关系更加生动丰富;另一方面使临床实践中的伦理关系更加清晰。同时,叙事还是一条纽带在医学伦理教育中使理论讲授与临床实践链接起来,成为融合多学科发展的有效手段和实现途径。所以,叙事方法可以成为医学伦理学教育中最为有益的手段。叙事作为医学伦理的一种多学科视角表达,反映现阶段医学人文发展的更高层次的价值诉求。在医学伦理教育过程中,如何运用好在叙事这一法宝,这是医学伦理叙事持续发展的最为重要的面向。其中,最为关键的在于把握好叙事面向的两个向度,一是精准定位现代医学主体的价值,在医学发展时间轴线上丰富主体的价值诉求;二是立足于医学实践中的伦理限度,在主体性的空间关系中回应生命尊严。
2 医学伦理叙事的价值诉求
在全国第二届叙事医学与临床实践研讨会上,王一方提出:“叙事医学是在医学向人性回归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新的医学理念与范式,是对技术医学的矫正和补充,将医生从技术的迷宫中拖回患者的主体生活,倾听、记录患者的疾痛故事,捕捉疾病中的心灵密码与隐喻,在灵魂深处与患者相遇,真正理解患者,与患者缔结情感与道德的共同体,乃至精神和价值的共同体,使医学从技术主义的歧路上回到人的医学的轨道上来。”[6]他认为,叙事医学的出现是对现在医学发展异化的一种矫正和补充,通过叙事而使医患双方能够建立情感共同体,为医者真正进入患者的世界搭建了桥梁,通过对主体病痛的讲述使医生真正在主体性的立场上理解患者的处境感知,从而提升了医务人员的道德感知能力性,体现了医学伦理教育中真善美的道德要求。伦理叙事是医学价值的载体,是医患之间主体性价值的再现。
医学实践中的伦理叙事是通过对现实存在的建构呈现主体的价值。不管是医学实践还是医学叙事都应该围绕医学活动中主体的价值进行建构。现实中,医患主体关系间的价值颠倒混淆,或是主体颠倒,或是价值混淆,造成医学伦理关系中主体价值的遮蔽不显,这是引发医患冲突矛盾频发的根本症结所在。在医学伦理教育中运用叙事的方法是践行“医乃人学”的价值理念最契合的途径。通过叙事表达医学实践中的主体关系,通过伦理教育对医学实践中主体进行思考。“叙事医学中的伦理叙事将人性置于技术之上,跳出医患之间的契约关系(潜在的对立关系),开辟一个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关切、信任、共情关系,不是强调医患之间的分歧,而是寻找情感的纽带,去寻求融合叙事医学中的伦理叙事超越是—非、真—伪,发现(抵达)善—恶、荣—辱、高—下、清—浊、尊—卑,赋予医学生活以道德价值。”[7]医学伦理叙事作为一种方法或手段,促使医学教育从工具价值向目的价值转向,并从整体意义上理解人的生命价值,在伦理限度内把握主体间道德关系,契合了医学伦理学最高层次的教学目标,同时,为医学人文学科的高质量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医学伦理的叙事为医学教育提供了一种追求道德自觉的价值。医学实践中的主体间的价值关系以主体的道德觉悟和道德践行能力为直观表现,成为塑造实践主体道德自觉的重要评价标准。道德觉悟和道德践行力是道德精神的本质内核,代表了医学本真的使命与原本的面貌。“叙事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伦理状态的呈现。伦理叙事的内核是道德精神,通过故事表达理解,目的是促进道德自觉,关键是要产生道德实践力量。”[8]叙事中的伦理价值为医学主体实践提供的道德力量,规导医学异化回归医学应有的德性面貌。古人所谓“大医精诚”重点强调的也是医者自我散发出的德性光芒,这种光芒基源医者对医术精益追求的态度和对病患真心对待的责任。医者应有的德性光芒是助推医学向至真至善价值发展的不竭动力。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通过叙事的建构,从主体性视角强化医学发展的本真使命,对课堂上理论层面的价值预设与现实呈现的医患矛盾冲突作出有益于价值重构的有效解释。叙事为医学伦理教学提供了道德精神与支持,使医学实践中的主体性关系在终极价值导向中真正散发出人性至真至善的光辉力量。
在医学伦理教育中引入叙事方法,通过主体叙事建构人的主体性价值。一方面,叙事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成为医学人文教育与临床诊疗实践连接的桥梁;另一方面,叙事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不仅增进了医患双方的互相认同与理解,同时,使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成为价值同向的合作共同体。Rita Charon教授也指出,“叙事医学关注个体患者,为医生充电,能够生成并传递医疗实践中的知识,明了公众对医学的信任以及医学应担当的责任”[2]。叙事过程中的主体性表达,不仅对医学信任与责任担当的价值回溯与明确,而且展现了对生命生活状态的敬畏与尊重。医学伦理叙事把叙事作为传递认知生命价值及意义的方法,对医患主体和教育主体具有双重的建构作用。“讲故事与听故事都是伦理的感受,生命叙事使信息能量在个体生命之间流动、交换,它激活着、生成着、满足着说者与听者的道德需要,改变着他们的生命感觉。”[9]叙事对实践主体双重建构的作用,使讲故事与听故事的主体之间形成生命对话交流的关系,叙事作为培育道德需要的媒介手段,在生命交流对话的过程中凝练主体生命的道德自觉,从而完成对实践主体价值的建构。
3 医学叙事的伦理限度
医学伦理叙事的伦理限度在于其主体性范围的认知,这不仅是医学伦理发展的基本面向,也是叙事医学发展的基本立场。从医学发展历史看,医学发展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单一维度,而是印迹在人类文明中的具有多面向融合发展的综合文化呈现。医学并不只是实验科学的同义语,而是帮助患者解除痛苦的技术,是临床照顾,是一种如同烹调一般的生存技艺,是一种因时、因地、因民族而不同的人类文化[10]。所以,医学与文化一样,都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主体性表达。医学伦理是对临床实践中的主体性之间关系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以医者和患者这两种显性主体为对象,同样,还涵盖了与显性主体相关的隐性主体。这种主体性在医学伦理学科里面一般表述为广义的医患关系和狭义的医患关系。临床实践的主体关系是伦理描述的对象,医学叙事的表达就是要以这类主体为边界,讲述主体自我以及主体之间的故事。医学叙事作为一种双向的情感传递,患者作为故事的原型表达主体情感,医者作为倾听故事的主体,通过吸收—接纳—共鸣的情感传递过程实现一阶叙事表达的功能。
在伦理主体性限度内寻求叙事与伦理的交织点是升华医学伦理教育理念的重要路径。如何把叙事引入医学伦理过程中,从对主体价值的确认到生命价值的共鸣,实现一阶叙事向二阶叙事转化,这对强化医学伦理教育的效果起着决定作用。“教育者和医学生通过情节生动、真实情景的故事对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医疗境遇、医疗行为及其过程进行讲述与聆听,对其内在伦理价值、道德规范、核心观念进行挖掘与剖析。”[11]教育过程中运用叙事的手段,复述与疾病有关的生命故事,让医学生在生动的生命故事中深刻认识主体性的价值,进而把这种对生命的认知升华为职业价值的追求,对塑造有温情的医学职业生涯有着持久的影响力。作为一种教育方法,叙事使医学的工具价值性的疾病案例生成了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的生命故事。运用叙事这种方法,使临床的生命故事进入教育课堂,不仅丰富了教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升华了医学伦理教育的意义。医学伦理叙事从生命体认的场域中反思主体性关系的限度,正如医学不是万能的一样,医学伦理关系也有一定的限域,医患之间的主体关系的限域对叙事的内容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医学伦理在叙事的境遇下,使主体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医学的伦理限度,时刻警醒自我什么是可以做又必须做到的,什么是能够做到也绝对不能做的。医学叙事的伦理限度不仅是对主体价值的确证也是对生命价值的敬畏,更是对人的主体性独特而尊贵的价值的一种强化。
在医学伦理教育中,叙事的伦理限度又延展为其对自我表达的一种超越。医学教育中引入叙事方法,使医学实践的主体成为鲜活的生命个体,这只是医学教育的一种表象,其实质是其在哲学视域中对生命尊严和个体价值的反思。在教育过程中融入叙事的方法,使教育课堂不再是纯理论的灌输,教学成为一种具有生命气息的伦理教育。叙事加深了医学生对医学的主体认识,能够体认到不管是医者自身还是作为患者的他者都是具有生命意识的整体,疾病只是生命的表达的一个方面。“叙事元素可以帮助医学生补充生活经验的不足,提供他们体验医患关系的模拟环境,培养道德想象力和移情能力,反思当前技术至上的生物医学因漠视‘人’的价值带来的诸多问题,从而更全面地认识医学的目的和自身的使命。”[12]叙事方法有益于医学伦理教育中形成 “全人”的临床思维理念,实现以生命影响生命的理念和态度践行医者的使命。通过这种生命故事的教育模式,摒弃临床实践中“见病不见人”的弊病,推动医学人文模式回归关注生命主体利益的初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叙事的维度上实现了临床实践与课程教育的融合发展,完成了生命价值在教育过程中的升华。
4 医学叙事伦理的实践价值
医学叙事作为体现主体性价值的方法,实践层面不仅对临床实践具有矫正和范导的重要作用,对医学教育更是具有传承人文精神与尊重疾病载体的价值。临床实践中医患双方作为面对面的主体交往,双方都是叙事当事人,需要直接的情感交流,价值诉求也是直接而显现的,叙事作为一种伦理的手段对当事人产生的直接影响。医学叙事成果作为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价值追求成为医学教育的首要任务,叙事的伦理价值在教育过程中不仅被重构,教育对象而言更是一种强化和提升。
医学叙事应用于临床实践中有效方式的就是书写平行病历。医生把患者病痛书写成疾病故事,既真切感受到生命的痛苦,又对生命有了更具哲理性的认知。在书写平行病历的过程中,医生既重新认识了生命的价值,又重新认识到医学的价值。如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医师魏鹏虎在叙事医学病历中写道:“在我深深意识到,哪怕自己不会给患者很漂亮地操刀完成一例手术,哪怕能给患者解决的问题不多,哪怕能做的只有聆听,只要留意患者的疾苦,哪怕仅仅是在患者床头停留一会儿,也能让患者感动不已。”[13]医学的价值除了减轻病痛之外,比这更重要的是抚慰载有病痛的主体的心灵。医生不仅是听故事的人也是写故事的人,在写故事的过程中自己也成为主人翁之一,从而在叙事交往主体生命的场域中加深对话交流,引导着医学实践从工具性价值向伦理性价值逾越。
医学教育应该追求伦理价值第一位。追求伦理价值第一位并没有否定医学的工具价值,因为只有在伦理价值的范导下,工具价值才能更好发挥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教育特点既要见“病”,更要见“人”,而叙事使二者价值实现统一,为医学教育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教材。医学教育通过有情感故事的案例使医学生更加坚信医学的职业信念和道德理想,追求医患双方主体价值的同向统一。百岁军医牟善初老人的故事能为医学叙事提供一种价值标杆。他每次在患者表示对他崇高敬意和感谢时总是由衷地说:“医生离不开患者,就像大树离不开泥土,减轻患者痛苦,就是最高兴的一件事儿。”同时,患者们都纷纷表示让牟医生看病也是一种幸福:脚穿布鞋,巡诊查房悄然无声;听诊器在手里焐热,再轻轻放到患者胸前;碰到身体虚弱说话无力的患者,他躬下身子,把耳朵贴近患者细心倾听……[14]能够把患者的病痛转换为一种幸福体验,同时也体验到医者的幸福,这是医学主体价值的最高层面的体现。这种以德性为目标的伦理诉求是对主体价值的双重塑造,同时也为医学叙事提供了这样的目标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