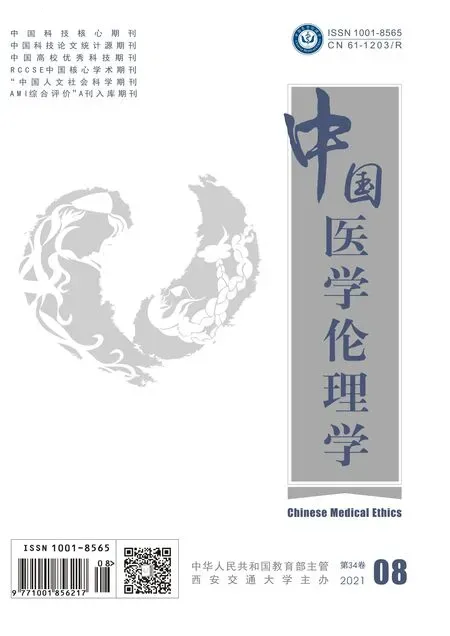病人话语权削弱的历史审视与提升对策*
——基于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
刘云章,刘于媛,赵金萍,边 林**
(1 河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17,liuyz2712@sina.com;2 云南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在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过程中,话语权是一个重要因素,包括医患平等的话语地位、充分的话语表达与共享的话语效果等,其中,需要特别关注病人话语权削弱的问题。对病人话语权削弱可以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进行审视,本文侧重于历史维度,聚焦于疾病观的历史演变、医学的科学技术化进程、医师的职业化发展以及医疗空间的转移等。病人话语权的削弱背离了医学初衷,也不利于医患沟通与医患命运共同体建设,同时,现代医疗实践发展的新特点与新要求等日益凸显出病人话语权的价值。基于此,本文提出提升病人话语权的若干对策。
1 疾病观的历史演变与病人话语权的削弱
疾病观是人们对疾病本质与价值的根本看法。早期人们认为疾病是神灵对人所犯罪恶的惩罚,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形成神灵医学疾病观。古希腊时期,人们认为疾病是机体内部的平衡紊乱,秉持疾病物质理论,形成自然哲学疾病观。中世纪以后确立了疾病与外源性病因之间的因果关系,认为疾病是人体组织的形态学变化,形成自然科学疾病观。十八世纪晚期至今,人们从生物医学角度观察疾病,认为疾病是人体偏离“正常”状态,形成生物医学疾病观。由此梳理出人们对疾病的认知进路:疾病是独立存在的“实体”、是机体内部整体平衡的紊乱、是人体组织的形态学变化、是对“正常”状态的偏离等。后一个阶段疾病观不是对前一阶段疾病观的简单代替或否定,而是“扬弃”。疾病观这一发展过程具有客观性,但是如果从病人话语权角度分析,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越来越“忽略病人的意见和感受”[1],削弱了病人话语权。
历史上,一个人是否有病主要取决于他的“主观感受”,病人拥有自己是否有病的发言权,现在主要取决于仪器检测结果[2]。也就是说病人的身体与感受不再作为疾病的见证,失去了其原来的疾病判断意义。一个人是“健康”或是“疾病”及其程度,是由现代医学技术筛查与检测出来的数据、图像等信息资料加以说明并确证。虽然这些信息来源于病人,但是对这些信息的解读与说明只能由医学专家来完成,病人失去了对自己是否罹患疾病的发言权。
此外,疾病不单是医学事件,还是社会与文化事件,如果超出医学学科范畴进入广泛的社会与文化领域,那么对疾病的认知与界定就更加复杂。疾病是社会与文化建构的结果,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文化背景与社会发展状况下,人们对疾病的认知都不完全相同。比如,在日本,人们一般不会因为“热性潮红”去找医生,但在西方就有可能;在非洲病人主诉血吸虫病引起的症状是腹痛,在欧洲往往是倦怠无力;西方人是从“霍乱”实体的角度称作霍乱病,而有的文化称作一种上吐下泻症,还有的只是描述其症状而不命名。所以疾病“既是生物学事件,同时也是一代人特有的反映医学知识史和医学建制史的语言建构物的藏品目录”,是人们“架构”的结果[3]。这种“架构”充分体现在现代各种生活方式疾病上。由此,更加削弱了病人对社会与文化领域疾病认知与界定的话语权。
但是,如果完全不考量病人对病痛的主观感受及其话语权,单纯依赖仪器检测或社会文化去认知与诊治疾病,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片面性与不合理性,毕竟,病人是疾病的最直接关联者。如何平衡病人主观感受与仪器检测结果之间的关系,考验着现代医学的智慧。
2 医学的科学技术化进程与病人话语权的削弱
早期经验医学秉持着朴素的整体观,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协调、平衡与统一,关注生活方式、饮食锻炼以及心态平和等在健康中的作用。医生诊疗主要凭借人体器官,其他诊疗手段很少,与病人有着充分的语言沟通。一方面是为了从病人述说中了解疾病信息以提高诊疗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慰与鼓励病人[4]。加之,这一时期的医疗主要在病人家中进行,医生与病人及家庭之间多保持着一种熟人关系,相互之间较为信任,病人有着比较充分的话语权。
近代以来,尤其是十六世纪以后,西方医学开始进入“科学的医学”时代。解剖学的发展使人们可以观察人体各个部位的形态学变化,能够直视患病的器官并在器官层面上分析疾病。自然科学知识与技术日益应用到医学与医疗实践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医疗器械,听诊器、血压计、X线、造影术、计算机断层扫描、核磁共振、三维立体成像等,这一切成就的取得与临床应用形成了基于身体寻找疾病的生物医学思维模式。
首先是医学重视“体征”轻视“症状”。体征是医疗器械检查的结果,症状是病人的感觉与叙述。近代医学在由临床医学模式到医院模式以及实验室模式的发展过程中,病人对自身病痛的解读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医学重视的是由医疗器械检测出的体征。其次是医学重视“疾病”轻视“病痛”。疾病是客观存在,病痛是病人的主观感受。尽管病人的主观感受是由疾病造成的,但对于医患双方来说,二者的意义不同。“医生和患者所想的并非同一件事,站在病床边和躺在床上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5]。医生关注“病”,病人感受“痛”。当生病的“人”成了“病人”,他们在诊疗过程中也就成了被隔离的、被动接受关爱和照顾的角色,而疾病越来越变得比病人重要了,甚至医学开始见病不见人。在这一过程中,病人的话语权逐渐被削弱。
事实上,医学“是一门倾听患者、诊断或预防疾病及理解病因的艺术”[6],医学由经验到科学的发展使其“科学”与“技术”特色日益浓重,淡化了或者没能充分展现其应有的“艺术”内涵,导致“考虑更多的是医学职业的发展而不是病人的利益”的弊端[7]3。实现医学的科学化与艺术化的融合是人们对医学的期望与医学发展的未来,这其中内含着病人话语权的充分表达。
3 医师的职业化发展与病人话语权的削弱
在人类历史上,作为解除或减轻人类疾病与痛苦的医疗者这一社会角色很早就出现了,包括史前时代的占卜师、巫师、萨满等,他们都具有传说与神秘的色彩。在西方,第一批世俗的医师源自于希波克拉底学派,他们不同于古代的巫师与占卜师,他们有一定的医学知识与技术,是真正的医生。在中世纪,教会神职人员独占了医疗行业。从十二世纪起,西方的医学恢复了自主生机,大学开始教授医学,医学生经过专业训练与考核,获得学位,担任医师。医学开始成为一种严格而明确的社会职业,最早出现在意大利南部的萨勒诺[8]。随着医师数量的增加出现了医师的专业组织——医师行会,标志着医师走向职业化。
梳理医师由早期的“巫医”、神灵到后来的世俗医师,再到职业化医师的过程,尤其是医师职业化前后的变化,有助于认识其中的病人话语权是如何被削弱的。早期医师的医疗与救治能力很低,其社会地位并不高。后来通过医学专业知识学习与考核,获得医师执业资格证书,得到政府和社会认可,被赋予医疗职业的专业技术和实践权利,在最大限度实现病人医疗权利的同时,也使医患关系尤其是医患双方的权利发生重大变化。医师掌握着知识、技能,在医疗中占据行业优势;病人不掌握或较少有医学知识,多是遵从医生意见,较少有自己的判断与选择空间[9]156,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病人话语权。
特别是医师权威形成以后,诊疗过程更加依赖于医学科学技术,依赖于医师的经验与能力等,原来对医疗有重要价值的病人的述说变得不再重要,医师在与病人短暂交流后就写下处方,他们“放弃了讨好患者的艺术”[9]46。对病人而言,医师“使用显微镜分析尿、痰、血以及其他体液进行辅助诊断”,使病人感受到自己被科学“关爱”着,他们会更加相信与推崇医学科技的力量,更加尊敬与信赖医师权威[7]213。在强大的医学科技、令人崇敬的权威医师面前,病人的话语权进一步弱化。
4 医疗空间的转移与病人话语权的削弱
历史上病人多是把医生请到家里来看病,家庭是医疗活动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病人是主人,医生是客人;医疗过程不仅有病人及家人在场,还会有邻居、亲属以及朋友等;病人不只请一个医生,还会请其他医生;病人也会参与到医疗之中,当对医疗不满意时还会随时更换医生等。总之,家庭医疗空间使病人有更多的主导权[10],医者的权利受到限制。家庭医疗场景中医患沟通充分,医患关系融洽。
医院出现后,医疗空间由家庭转到医院,医院不同于家庭。首先是医院空间环境。病人由家庭来到医院就进入了一个陌生环境,尤其是综合性大医院往往集医疗、保健、教学、科研于一体。这里空间大、建筑多、科室分工细密,病人需要挂号、门/急诊处就诊、交费、检查、取药、其他治疗方式等。对于初次来到医院的病人来说,一切都不熟悉,需要在不同的楼宇、楼层、科室间辗转、问询;其次是医疗人际环境。医院是陌生人空间。医疗的社会复杂性使病人面对的不仅有他们不熟悉的医护人员,还可能会有医务社会工作者、伦理学家、律师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等,这些“医学的外部人”也会参与到对病人的医疗决策之中,影响着诊疗方案的制定与实施。这些复杂的医疗人际关系削弱了病人话语权;最后是诊疗程序。现代医学分科以及医疗分工越来越细密,诊疗程序日益复杂,这些复杂的诊疗程序对于病人而言是陌生的。病人进入医疗过程必须遵循诊疗程序,听从医务人员安排,医患之间在权力、权威和知识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9]138,病人很难充分体现自己的话语权。
5 现代医疗实践的转向与病人话语权的凸显
病人话语权的削弱是历史形成的,而现代医疗实践的许多新特点、新要求都需要重新重视病人话语权。首先是疾病谱的变化与临床诊疗模式的改变凸显了病人话语权。疾病谱的变化使慢性病与生活方式疾病增多,病程延长,疾病难以治愈,医疗由快治快愈转向慢治慢愈甚至不治不愈。人们开始反思建立在循证医学基础上的临床指南存在着局限性,如忽视患者个体差异、忽视人文治疗、忽视患者参与等。临床诊疗需要重视对患者“真实世界”的把握,需要将一般选择与患者个体差异结合起来,需要患者的参与等。所有这些变化都要求病人有充分的话语权。
其次是“病人权利”“患者赋权”与“医患共同决策”等凸显病人话语权。1946年《纽伦堡法典》首次提出受试者“自愿同意”权利的必要性,后来,“知情同意”由科研受试者的权利扩展为普遍的病人权利,形成了广泛的病人权利运动,并由尊重病人权利发展到实现“患者赋权”。患者赋权的本质是提高患者在诊疗过程中的参与度,与医务人员构成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方面要求医务人员转变传统诊疗理念,让患者参与诊疗;另一方面要求患者具有参与诊疗的知识、技能与态度等。实施患者赋权的目的是加强医患沟通、弥合医患分歧、实现共同决策、共享医疗价值。
最后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触及的深层次利益调整凸显病人话语权。改革涉及社会、行业与个人等多元主体,在政策制定、体制机制设计以及路径选择时都需要体现病人意愿与利益。具体到医疗实践中存在着健康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博弈,病人既要治疗疾病恢复健康又要少花钱,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也要遵守国家规定,在协调与平衡二者关系时需要认真倾听病人的声音。此外在维护与增进病人健康权益、公正处理医疗纠纷等问题上,病人都应该具有充分的话语表达权。
6 提升病人话语权的若干对策
在医疗卫生制度、法律与体制机制建设层面,赋予病人话语权以有力保障。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基本原则,这为保障病人话语权提供了根本价值遵循,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医疗卫生制度设计与体制机制建设等,都贯穿着对病人话语权保护的基本理念与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规定:“公民接受医疗卫生服务,应当受到尊重”,公民“对病情、诊疗方案、医疗风险、医疗费用等事项依法享有知情同意的权利”,医疗卫生机构与医疗卫生人员“应当关心爱护、平等对待患者,尊重患者人格尊严,保护患者隐私”等。通过制度设计与法律保障为提升病人话语权提供坚实基础。
在医院管理层面,优化医疗空间以充分体现病人话语权。医院是落实与体现病人话语权的空间,通过加强医院硬件与软件建设,优化挂号、门诊、检查、医疗、住院、手术、康复等医疗服务流程,努力把医院科室、部门与机构打造出有利于医患沟通的医院人文空间环境。不断改进诊疗制度,通过实行分级诊疗制度“逐步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机制”。缓解医患供需矛盾、明确各级医疗职责、促进医患沟通与交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医疗空间下沉到基层[11],充分利用基层医疗机构医患更熟悉、交流更便利、沟通更有效的空间优势,满足居民健康与基本医疗需要。
在医师层面,尊重并促进病人话语权实现。首先,尊重病人话语权是医师职责。《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规定了病人享有的包括话语权在内的各种权利,帮助病人实现这些权利是医务人员的义务。当医务人员没有尽到这些义务时,如“在开展医学研究或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未按照规定履行告知义务或者违反医学伦理规范”,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其次,医师要充分认识病人话语权的医疗价值,特别是在一些复杂医疗决策过程中,病人话语权有着重要价值。医生主要遵循着医学专业思维,考量的是医学、疾病与治疗等,病人主要是基于社会生活思维,考量的因素更多,包括病痛、代价、家庭、职业、生活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病人的医疗决策。所以,医师不能仅仅满足于医学视角,还要充分重视医学之外的因素,而这恰恰需要由病人充分的话语表达才能展示出来;最后,医师严格按照“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的要求书写各种病历,以有效体现病人话语权。通过病人主诉,将病人的“发病情况”“主要症状特点及其发展变化情况”“伴随症状”“发病以来诊治经过及结果”以及“发病以来一般情况”等进行全面记录[12],使病人话语权在记述病例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病人层面,增强自觉的话语权意识与话语表达能力。医患是双主体,病人不是消极被动接受医疗,而是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医疗过程中。病人的这
一身份定位决定了其话语权的医疗价值。病人在增强话语权意识的基础上,要不断提升话语表达能力,学会充分尊重理解医师,学会准确叙述疾病感受,学会理性表达医疗诉求。总之,学会做一个聪明的病人,能够有效地与医师沟通对话。
疾病观的历史演变、医学的科学技术化进程、医师的职业化发展以及医疗空间的转移等,一方面代表了近代以来医学发展与医疗实践的成就;另一方面又会对病人话语权造成不同程度的削弱。不能因为这些成就而忽视对病人话语权的削弱,也不能因为对病人话语权的削弱而否定这些成就。基于现代医疗实践对病人话语权的要求,秉持客观、理性、辩证的态度,对每一个因素与病人话语权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度研究,并从技术的、人文的、法律的、心理的、社会的等不同角度提出可行的防范、改进或重置对策,以助力于提升病人话语权,增强医患沟通实效性,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