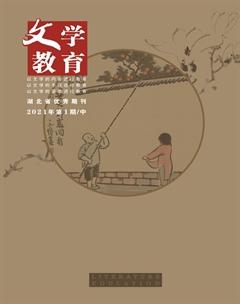从《巨流河》看齐邦媛的教育背景与人文情怀
蒋雯雯
内容摘要:作为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齐邦媛的一生经历了太多。战争时期的颠沛流离,建设台湾时期的艰难,后半生致力于教育的用心,从事文化交流的欣喜,她都在《巨流河》中一一道出,将家国史和个人史悲喜交集地放置在20世纪的舞台上。从这部回忆之作中可以管窥父母给予的教导、学校的教育和文学的滋养对齐邦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基于这种认识,本文拟从《巨流河》入手,简要分析齐邦媛的人文情怀的养成与其教育背景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齐邦媛 知识分子 教育 文化 情怀
《巨流河》繁体版的腰封上有一句话:读了这本书,你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作为20世纪在战乱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齐邦媛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越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刻,越是需要知识分子的担当,担当青年的引领者、文化的传承者与民族的守护者。通过她的书写可以看出,正是父母从小对她的言传身教,以及学校恩师的教诲和中外文学的滋养,得以让齐邦媛在面对生活中的困苦、磨难时能够平淡面对。也使得她的文学能够超越个体、种族、国家,表现出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出对知识和文化的尊重。
一.家庭教育
1.母亲的启蒙:生命底色的奠定
齐邦媛一出生,父亲便不在身边,是母亲的坚持与努力才为先天不足的她捡回了一条命。而且母亲在那些苦难日子中的挣扎和坚守,陪伴着童年时期的齐邦媛,给予她终身的观念和文化影响。
齐邦媛说:“在我的记忆中,在家乡的母亲,不是垂手站在桌边伺候祖父母吃饭,就是在牧草中哭着。”原本也是作为大户人家的明珠,十九岁嫁给父亲,婚后不久父亲就离家在外奔忙十年,母亲也就在老家庄院待了将近十年,尽心侍奉祖父母、抚养儿女,孤独地等待父亲偶尔的探望,从不表露半句怨言,就连在突然痛失幼子后悲伤哭泣也只能躲在牧草堆后面流眼泪。痛失幼子之后的母亲精神状态一日不如一日,前来看望的姥爷知道一个女人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下决心把母子三人送去南京与父亲团聚。一路上母亲的冷静和沉默是被她深刻印记的,前路未知的紧张,举目无亲的恐惧,都在那一句充满想象的“鬼哭狼嚎山”的回答中了。十年等待,终于得以和父亲团聚的母亲,此后便一直在父亲身边,帮助他料理家事、处理政事,照顾参加革命的朋友们和那些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学生。一生都在为儿女操心,为丈夫奔劳。
就是这样一位母亲,依靠着自己的坚韧和爱,与孤独作伴,与动荡相向,与苦难斗争,在最初无望守候的十年中,在那些颠沛流离的岁月里,为儿女们树立了待人处事的榜样,给了齐邦媛最初的文学启蒙。她认为:“我一生对文学的热爱和观念,其实是得自我那没有上过中学以上教育的母亲,她把那苍茫大地的自然现象、虎豹豺狼的威胁,和那无非言说的寂寞人生化作许多夏夜的故事,给我童年至终身的启发。”激发了她一生的文学情怀和想象,使得她的文字具有温润与不屈的底色。
2.父亲的教导:文学理想的确立
在齐邦媛心里,父亲齐世英一生都是位温和的君子。父亲的言传与身教为齐邦媛树立了为人为学的理想和标杆。
童年时父亲的缺席,并没有造成她与父亲之间的隔膜,反而使她对父亲更加敬重。十岁那年,患上了严重的肺病,须得去北平疗养,父亲亲自带着她坐火车北上,第一次在餐车上和爸爸面对面吃饭,爸爸贴心地为她切好牛排,这都是以前没有享受过的关怀,这一幕幕也成为了齐邦媛心中永远忘不了的深情。但父亲的教导是严厉的。孩童期间的一件小事至今让她记忆深刻,当她在泥泞不堪的小巷里遇见坐在汽车上的父亲,却被教导不可以因私事而占座公车。可以看出,这位温和的父亲,在对待人、事上有自己的原则。他以自己的言行举止为齐邦媛树立了为人的标杆,也使得她在治学方面更加严谨。
在30年代风雨飘摇的局势里,看着许多流落街头的青年,父亲力排众难在南京创立中山中学,收留那些流离失所的青少年,希望在动荡中存续知识和文化的力量。南京陷落后,学校和学生只能南迁,一路上,父亲多方设法、各处奔波,解决学生基本的吃住问题,保护每一份教学设备。他知道,越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越需要教育、知识和人才。这是父亲的理想与责任,也亦使齐邦媛第一次亲眼目睹并感受教育与国家命运的牵连。
大学期间,因为时局的原因,进步学生们组织游行、示威等活动,这对年轻的齐邦媛来说是很新鲜的,但父亲的一封来信为她在迷茫中指明了方向:“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这封信如一盏明灯,让齐邦媛发热的头脑得以冷静的思考。后来她虽然在机缘巧合下从事了一段时间的政治工作,但很快就全身而退,一方面是因为自己不适合从事政治,另一方面也是谨记着父亲的劝导,觉得救国的道路并非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父亲的关爱和安排使齐邦媛在动荡的年代接受了完整的教育,而且在父亲那一辈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济世理想和家国抱负,不仅使她深受感动,更促使她能够更深入地思考政治和文学问题,明确自己的方向,确立一生为人为文的理想与情怀。因此在以后逐渐安定的日子里,她依然坚持着父辈以教育启蒙國人的文化理想。
二.学校教育
1.国内教育:人文情怀的养成
齐邦媛的前半生处于内忧外患的民国,国家危急,教育中便处处渗透着爱国意识。这些在传统文化中浸染过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他们的教育理念、济世救国情怀、文化认同等观念深刻影响着课堂内外的学生们。作者在《巨流河》中动情地回忆起南开中学和武汉大学的恩师们。他们于硝烟炮火的一隅维护着独立自主的办学风格,倾尽所有培养学生的家国意识和人文素养。
因为战乱,小学毕业后,齐邦媛先后辗转于多个中学,其中在南开中学待的时间最为长久。当时的南开中学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任校长,倡导以教育救国,鼓励学生在国家危难之时,更要有所担当,要明确“中国不亡,有我”的意识。家国与民族开始在齐邦媛心里有了重量。
孟志荪老师的国文诗词课也让她深受启发,初中的新文学,高中的《诗经》到民国文学,孟老师用他的学识,输出优秀的文学知识,加上齐邦媛自身流亡的经历,她更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也更能理解诗词中的国仇家恨。教授世界人文地理的吴振芝老师,在遭逢大难之后依旧坚持回到学校上课,为他们讲述异国土地上的风土人情,更加激发了齐邦媛日后探索其他文化的决心。
因为父亲的原因,齐邦媛选择在武汉大学就读哲学系,一年后转入外文系。朱光潜老师的英诗课上培养了她的英文诗歌鉴赏能力和文学品位,与她在中学孟老师的课堂上所学的中国诗词相结合,中外两种诗歌或形同或相异的意象和意境引领她走进了一个全新的神奇的世界,真切地感受到了诗对人生的力量,文学对人生的力量。
在南开中学,齐邦媛受到了较好的基础教育,也使她看到了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并萌生救国救民的理想。在武汉大学,得遇名师,了解到了大千世界和中西文学,使她的文学生涯有了一个较高的起步。特别是在孟志荪老师、朱光潜老师的课堂上,她领悟到了诗歌的力量。当她得知张大飞殉国的时候,她想起惠特曼的《啊,船长!我的船长!》;当她远在异国怀念亲人时,她心中浮现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人生的大悲大恸,全都内化于诗歌和文学浸润的心灵中了。
2.国外教育:文化交流的给养
大学毕业后,思虑再三,齐邦媛最终选择去台湾工作。等到工作、家庭逐渐稳定,年纪渐大,但是追求知识、探索文化的心从未停歇。
1956年,33岁的齐邦媛考取了“美国国务院交换教员计划”奖助,开启了她的文化交流之旅,到美国进修、访问,在密西根大学进行英语教学训练,深切地了解到了美国的生活方式。这一次是齐邦媛的一个“梦”,但是却触动了她一直追求学术的心。
1967年,44岁的齐邦媛再三考虑后申请了“美国学人基金会”的进修奖助,先到印第安纳州的圣玛丽学院教授中国文学,四个月的时间里,她开始有系统地读书,也是从此时萌发了传播台湾文学的念头。之后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修比较文学,更是利用每一分从为妻为母的职责中偷来的时间学习,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最劳累也是最充实的一年。
中西文化的交涉、碰撞,不同国家之间文化的相通之处和差異之点,使得齐邦媛的文学生涯又开创了另一重境界——“声音与意象的结合,令她着迷震撼,仿佛是构筑了一种感情的乌托邦,表现出强韧的生命力,长久萦绕在她心间,化为一种生命品质和成长力量。”新质的加入,让齐邦媛对文学有了更深的领悟,激发了她致力于台湾文化与西方文学交流的拳拳之心。
三.结语
在齐邦媛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心中,战争与流亡是他们心中抹不去的记忆,但是他们的经历,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所感知的文化——“五四”新文化、启蒙精神、“人”的文学以及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等等,使他们在流亡中始终保持着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始终坚持着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为自由、平等、独立等普世价值奋斗不止,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尽心尽力。
怀抱这样的理想和情怀,齐邦媛在流离中坚持不断汲取知识和文化,在后半生致力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重建、交流与发展。她在台湾中兴大学创办外文系,引介英美文学到台湾;在国立编译馆潜心编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推动了中国文学的一大步;组织重新编写中小学国文教科书,希望孩子们能够学习到更纯粹的文学作品;在台湾大学退休后依然为台湾文学的发展尽心尽力,努力将台湾文学推介到西方等。
参考文献
[1]齐邦媛.巨流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2]王德威.“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齐邦媛与《巨流河》[J].当代作家评论,2012(01).
[3]杨小露.故国回望与使命回望——论齐邦媛《巨流河》的精神旨归[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5(06).
[4]袁玲丽.以文学之舟涉渡:《巨流河》的女性成长主题探析[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8(04).
[5]杨君宁.民国显影·台湾轨迹——跨海知识人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实践:以齐邦媛为中心[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5.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