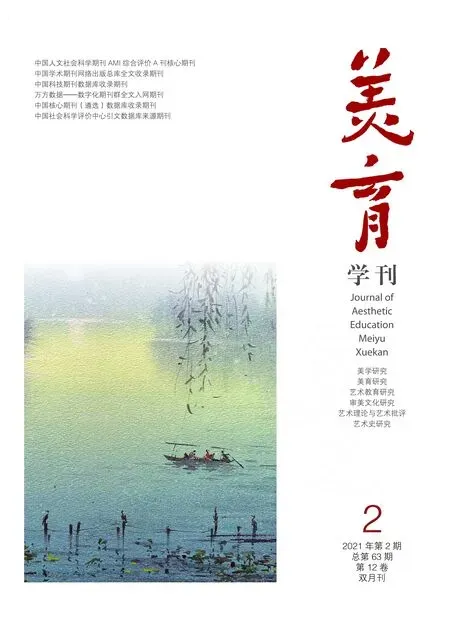郎世宁绘画之图式及风格分析
韩京雷
(杭州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西方传教士来华宣教肇始自15世纪下半叶,以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为代表。发展至康熙初年,传教士在华的势力及影响均达至巅峰。在这一过程中,虽有清廷所代表的皇家势力与罗马教皇之间在教义、礼仪、宗教观等多方面的冲突与矛盾,但整体上呈现出平稳发展的局势。康熙皇帝于1715年的朱谕中就指出:“但西洋人到中国将三百年,未见不好处,若事无大关系,从宽亦可。”[1]37显然在康熙帝看来传教士尚有可利用之处。也正是在这一年,意大利米兰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抵达中国。颇具艺术才能的郎世宁具有天主教徒的身份,其来华的目的亦以传教为首要任务。但郎世宁来华的消息经由广东巡抚杨琳上奏,奏折中云:“……因天气署热,在船日久,请假休息,并制作衣服,往北京天朝效力等语。”[1]37此内容暗示出清廷官方阶层对传教士的基本态度,即并未将传教士传教活动视为重点,而将他们视为具有实际功用的人才。确实在郎世宁来华之前,已有如雷孝思、费隐、英柱等人参与清廷舆图的制作,因此,从清廷对待传教士的态度上基本可以预见郎世宁在清廷职业画师的身份。
郎世宁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来华,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于中国去世,其在中国活动时间达五十年之久,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并凭借独特的画技在乾隆朝屡受皇帝的嘉奖。尽管如此,郎世宁并未遗忘其传教士的身份,并在凭借画艺服务于皇家的过程中,时时心系基督教的传教事务。如乾隆元年(郎世宁时年48岁),郎世宁就跪求乾隆缓和教禁一事:“五月三日,郎世宁在御前面请缓和教禁。据乾隆元年阳历十二月二十二日巴多明自北京致杜赫德书,谓五月三日郎世宁在作画之时,乘乾隆帝来如意馆观赏画之机,跪帝前面奏,哀求缓和教禁。帝谕日:‘胜未尝阻难卿等之宗教,肤唯禁旗人信奉。’十日后,又由某亲王召教士入宫,代宜帝旨:‘唯禁旗人信教,他皆不问,教士亦得自由信奉。’嗣后,官吏对信教者即持宽大态度,迫害之事几已绝迹。”[1]47郎世宁向乾隆皇帝跪求缓和教禁,受到了耶稣会的指派。在此次直谏乾隆皇帝之后,郎世宁还有过数次向乾隆皇帝的谏言,都是涉及基督教在华之传播事务,由此看来,郎世宁的主业虽然是一名宫廷画师,但却时刻未能忘记自己身为传教士的责任。但考察康熙、雍正等诸位皇帝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实际上他们并未有多大的支持,雍正皇帝甚至采取了严厉的禁教政策,这些都使得来华之传教士在传播教义上遇到的困难。相对于传教,康熙等人更倾向于将传教士视为具有实际功用的特殊人才,基于此,郎世宁的绘画技艺受到了三朝皇帝的青睐。并在服务皇家的过程中,郎世宁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中西合璧特色的绘画风格,被时人称作“海西画法”。(1)杨伯达在《郎世宁在清内廷的创作活动及其艺术成就》一文中就将郎世宁的绘画风格称为一种“新技法”“新画风”,也称作“郎世宁新体”。见杨伯达:《郎世宁在清内廷的创作活动及其艺术成就》,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2期。对于郎世宁而言,他在宫廷中的作品,大多是按照皇帝的要求进行绘制的。这些绘画的主题几乎和天主教无关。郎世宁无法通过他的画笔向皇帝或中国境内的其他人传播天主教。 虽然如此,他的西方绘画技术却在宫廷绘画的范围之内造成了强烈的影响。
郎世宁的绘画为中国的宫廷艺术带来了西方的传统写实绘画的技巧,总结起来,主要有几个方面:逼真的写实手法、光影的适当处理以及焦点透视法则。下面我们分别对此三个方面进行详述。
一、逼真的写实手法
精确的解剖关系是西方绘画发展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大成就。画家以一种科学的态度描绘人体、动物甚至是建筑、花草,逼真肖似。明末利玛窦从欧洲带到中国的绘画,给中国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逼真”。郎世宁的绘画技法之所以为清代帝王所喜爱,主要原因也就在于他对事物的描绘十分逼真,在形态方面能够描摹得栩栩如生,这种写实功夫,是当时的中国本土画家所不能达到的。
郎世宁留下的每一幅画作,都反映出他远超当时中国画家的写实功力。尤其是他笔下的清代帝王肖像,更是如此。他画有一件《平安春信图》(图1),画中描绘了乾隆和他的父亲雍正二人,对皇帝面部的描绘,表现出郎世宁的西方写实手法。从乾隆皇帝在画中的题诗可以看出皇帝对郎世宁画工的肯定和赞赏。乾隆皇帝写道:“写真世宁擅,缋我少年时。入室皤然者,不知此是谁?壬寅暮春御题。”乾隆题诗时为壬寅年,即乾隆四十七年,这时候郎世宁已经去世,因此这首诗应该是乾隆补题。
画中有两位身着汉服的男子,右侧躬身的年轻男子为乾隆皇帝,他手中拿着一枝梅花,递送给左侧的雍正皇帝。画中的雍正皇帝正值中年,乾隆则大概十几岁,当时还只是宝亲王。由于此画并无作者署款,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此作的具体创作时间。聂崇正猜测应该是在乾隆尚未登基的时候,郎世宁所画的。[2]但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郎世宁完全有可能在乾隆登基以后,由皇帝授意完成这样一幅作品。画面表现出乾隆和他的父亲其乐融融的父子之情。画中年轻的乾隆手中持有一枝梅花,似乎正在递交给他的父亲雍正皇帝。梅花显然象征着“春信”,寓意平安祥和。不过,此种构图和立意,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实属罕见,难以找到相似的作品。但在西方天主教绘画中,却常有类似的构图。如天主教绘画中常见的“圣母领报”的图式,常常由一个躬身持花的天使与圣母组合构成,这样的构图和画面情节,与《平安春信图》如出一辙。

图1 [清]郎世宁,《平安春信图》绢本设色,68.8×40.6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早在14世纪初期,锡耶纳画派中的画家马尔蒂尼就创作出《天使报喜与圣母领报》。此画是一幅镀金的祭坛画,为锡耶纳大教堂里面的圣安萨努斯礼拜堂创作,描绘了圣母领报的场景。其中,大天使加百利告诉圣母玛利亚:她已经怀上了上帝之子。来自意大利的郎世宁肯定熟知这一类构图和题材。我们可以大胆地想象,当郎世宁接到皇帝的指令,要完成一件皇帝与其过世的父亲的“合影”,此时他的脑中回忆起熟悉的构图,很自然地就借用了“圣母领报”的图式,只不过在《平安春信图》中,圣母怀孕的信息,变成了“春信”,天使手中的花朵,也变成了产自中国本土的梅花。画中的背景,也描绘成石头和竹丛。当然,郎世宁笔下的《平安春信图》中构图的灵感是否真的来源于西方的天主教绘画中“圣母领报”的题材,还是需要更多确凿证据的,笔者只是提出一种相对合理的假设。近年来有学者认为郎世宁于1741年所作的《狩猎图》的图式取材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高佐立(Benozzo Gozzoli,1421—1497)的作品《贤士的游行》(1459),其中传达了郎世宁希望乾隆皇帝最终皈依基督教的愿望。[3]笔者认为郎世宁是极有可能挪用西方天主教绘画中的图式的,但若认定其中隐含着某种晦涩宗教寓意,则显然未能考虑到作为观看者——乾隆皇帝对这种图画叙事手法的一无所知。郎世宁应当没有必要画出一件只有他懂得其中的宗教寓意,而其他中国观众茫然无知的作品。他应该只是纯粹地借鉴西方天主教题材的绘画图式,而非有宗教传播的内在寓意。
《平安春信图》的构图手法和图式,并不仅仅出现过一次。在养心殿内的贴落画《梅报新春》中,类似的构图再次出现。这幅画的内容与《平安春信图》几乎一致,作品由五块绢拼接而成,分别为天顶、地砖、左右两侧的窗户以及正中间的人物。这类绘画在二维平面上模拟出三维空间的深度,也叫作“通景画”。聂崇正认为此作描绘的人物也应当为乾隆和雍正,画中虽然没有名款,但从人物面部的描绘方法来判断,应当是由郎世宁与中国画家合作完成的。[2]
郎世宁笔下的乾隆皇帝和他的父亲雍正皇帝,面容清隽,典雅温和。画中两个人均以四分之三侧面示人,这种角度也是西方传统肖像画中常用的角度。画中的人物虽然极为写实,但却故意削弱了光影的效果,只是在面部凹陷处略略加深,这其实也是画家主动迎合清代帝王喜好的艺术处理手法。人物的服装褶皱处也略略加染,却并不做过分的明暗对比,但我们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衣褶突起处被画家用浅色颜料稍稍提亮,这是典型的西方绘画手法,在中国古代绘画中是不会出现的。此外,竹竿部分的高光处理,也显示出郎世宁调和中西画法的意图。
二、光影的适当处理
郎世宁所创造的“新体画”风格所具有的重要的特点即是将西方透视法、明暗阴影方法引入中国宫廷的院体画中,为画面增添了一种写实趣味,进而形成了一种以西法为主、参用中法的折中画风。由郎世宁之生平可知,其在来华之前即是极为成熟的西洋画家,19岁时就为教堂制作天主像、圣母像和圣迹图等大型壁画,作品或已难寻见,但可以想象郎氏壁画创作的风格特征:郎氏所采用的画法显然是重视写实、光影效果的欧洲传统绘画。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达·芬奇在《绘画论》中指出:“绘画科学的第一条原理……首先以点开始,其次是线,再次是面,最后是面规定着形体、物体的描绘。绘画第二原理是涉及物体的形状。第三原理涉及物体的阴影,阴影靠物体来表现。”(2)转引自张从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238页。对欧洲传统绘画来说,光影既关涉画面空间的表达,也与物象本身之质感表达密切相关,但前者更直观地表现于画面的透视关系中,后者则与塑造物体的光影息息相关。就郎世宁所处的清代宫廷画坛来说,他在画法上的这一创新势必会在当时的宫廷引起强烈的反映,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新技术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冲击着中国人对传统绘画的观念。由画史可知,在此之前古代中国画家对画中物象的塑造实际上多依据粉本或画谱而来,如山水画中的树法、石法,人物及花鸟画中种类繁多的画谱,他们实则起到一种绘画典范的作用,规定了塑造物象的基本程式。待画家在完全掌握这些绘画程式之后,便可通过对不同物象之间的巧妙组合来完成对画面的组织。郎世宁的“新体画”创新风格显然与传统绘画产生了极大的差异,无论郎氏笔下的鞍马、人物还是山水、花卉画,在画面氛围上均与传统绘画迥然不同。
在郎世宁存世的作品中,鞍马画应是其绘制较多,亦别具特色的一类。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百骏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郊原牧马图》、江西省博物馆藏《八骏图》等,在这些作品中,郎世宁描绘了中国传统绘画中最常描绘的一类绘画题材——鞍马。在中国传统画家中曾出现过不少以鞍马画闻名画坛的画家,如唐代韩幹,宋代李公麟,元代赵孟頫、赵雍等,但在他们的作品中,均展现了相同的绘画图式,强调线条本身对塑造形体的重要性,较少涉及鞍马质感的表达,展现出一种具有古典画风的绘画特色。在郎世宁的鞍马绘画中,传统中国画中用来塑形的线条被隐含于形体之中,画家借助焦点透视法在塑造鞍马及其活动之空间,并对鞍马不同部分展现出的差异化的质感作了处理,使其看起来具有一种真实的效果。西方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曾就西方人物画与中国人物画做出对比,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绘画属于“造型的”,而中国人物画是“有量无质的”,所谓“造型”实际上所指的就是西方绘画空间中的三维立体感;而以线条造型,空间就具有模糊的形制,趋向二维的平面性。从这一角度,也可见出中西绘画之间的差距,而郎世宁的艺术创造正是在于调和这两类截然不同的塑形方式。
显然,郎世宁在绘画中对光影效果的追求实与明暗技法有关,画面中鞍马所展现出的立体感是通过与光线之间的关系得以表现的。如果光线强烈,物体的高光会呈现白色,亮部比高光处颜色略深,紧接着是明暗交界处,之后是反光,最后是投影。这是光线下物体光影反应的整个结构。在郎世宁的鞍马绘画中运用了大量的此类光影效果,一方面要塑造物象的真实空间感,同时对物象质感的描绘,又增加了物象本身的真实效果。
有时郎世宁在绘画中表现出的明暗效果是克制的,他不得不顺应中国皇帝的审美习惯,减少阴影的使用。在他早年的一幅画作《聚瑞图》(图2)中,明暗光差相较其晚年的作品,显得更加明显一些。《聚瑞图》为郎世宁署款最早的作品,时间为雍正元年(1723)。画面正中六方委角的紫檀木雕托座上,置一天青釉宋官窑大瓶。插于瓶内的并蒂莲与双穗的稻谷遥相呼应,象征符瑞叠呈的太平景象。在《聚瑞图》中,光源在画面的右侧,因此麦穗、莲蓬、花瓶的大部分暗部都处于左侧。花瓶的明暗交界线比较明显,暗部有明显的反光,这种处理手法,显然来自西方绘画的传统。

图2 [清]郎世宁,《聚瑞图》109.3×58.7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三、焦点透视法则
清代画家邹一桂曾说:“西洋人善勾股法,故其绘画于阴阳远景,不差锱黍,所画人物、屋树,皆有日影。其所用颜色与笔,与中华绝异。布影由阔而狭,以三角量之。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学者能参用一二,亦具醒法。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4]邹一桂站在传统中国画家的立场,认为西洋绘画“笔法全无”,“故不入画品”,但同时其亦指出西洋绘画的一重要特征“画宫室于墙壁,令人几欲走进”,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真实立体空间的表达,此则依赖于焦点透视法的技术手段。
在郎世宁之前的两百多年,西方绘画中的焦点透视法则就已经传入中国。在明末的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出版中,符合焦点透视法则的建筑画并不鲜见。在郎世宁的作品中,表现较大场景的绘画,或者是涉及建筑物的绘画,都体现出西方焦点透视。乾隆时期郎世宁主持绘制了《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铜版画(图3),参与绘制者还包括王致诚、艾启蒙、安德义,全部为欧洲来华的传教士画家。此套铜版画共16张,其中的大量场景都是以严格的焦点透视法则绘制的。这套铜版画每幅纵55.4厘米、横90.8厘米,开始绘制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并于第二年完成。画稿完成后即经海路运至法国,在法兰西皇家艺术院中最终制成铜版画。《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的印数并不多,每幅只印制了200张。

图3 《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中的“平定回部献俘”
《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中的“平定回部献俘”一图中的建筑物表现出明显的焦点透视法则。此图描绘了乾隆皇帝在紫禁城午门上观看兵部官员举办的献俘礼的场景。这一事件发生于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兵部所献出的俘虏正是回部叛乱的头目。因此这件作品是一件政治意义极强的作品,它以宏阔的场景体现出皇权的威严。画面右侧的紫禁城午门呈现出明显的近大远小的特点。午门房檐上数条平行线,最终汇集于一个“灭点”,体现出严格的焦点透视法则。
此套铜版画中表现战争场景的图画较多。在描绘庞大的战争场面时,郎世宁等欧洲传教士画家也采用了西方透视法则。在这一类绘画中,有明确的地平线。画面中的人物,依照空间次序的远近位置呈现出大小上的差异。远处的山峦逐渐变得清淡,符合欧洲绘画中的“空气透视”法。中国传统绘画中也有表现大型战斗场景或皇家出行仪式的作品。如明宣宗时期宫廷画家商喜所绘制的《明宣宗行乐图》,表现出皇帝出行的恢宏场面。但其中人物大小,并无远近之别。由于画家要突出皇帝身份的重要性,画面中的明宣宗明显要略大于周围的仆从。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有时人物在画面中所占据的位置或大小就彰显了人物本身的身份,具有强烈的象征性,但西方绘画则严格恪守绘画焦点透视的绘画效果,力图展现一种实景的逼真再现。尽管在郎世宁后期的绘画中,他大量运用散点透视的绘画空间表达法,以期符合皇家之传统审美,但仍旧无法泯灭其画学源自西洋绘画焦点透视法的特征。
郎世宁整个绘画生涯均为清廷皇家成员服务,多数情况下其直接受命于皇帝本人,显然其绘画风格的形成与皇家之审美趣味密切相关。因此宏观观察郎氏一生绘画之流变,可明显看出其中之变化,如努力降低西洋绘画的因子,增加中国传统绘画的元素,但这些做法均未改变绘画整体所展现出的氛围,最终形成一种所谓“新体画”的宫廷绘画风格。当然,这一别具特色的画风并未成为当时画坛之主流,但从其制作的大量作品来看,这类画风充分满足清廷皇室成员的好奇心,此亦成为其屡受褒奖的原因。总之,这一“新体画”显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虽未获得中国传统画家的认可,但其于画坛的影响仍不容小觑,甚至这一新风格在民国时期仍在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