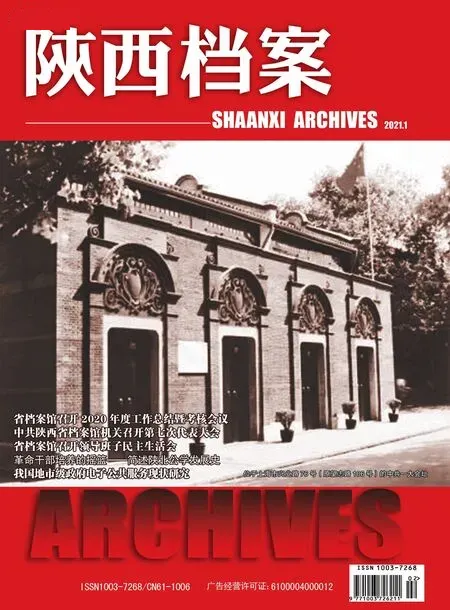从历史考释看《顺治汉中府志校注》之学术价值
——兼谈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
文/孙启祥

清顺治年间冯达道主修的《汉中府志》,是明清易代之际的一部重要地方文献。近年汉中市档案馆编辑出版的《顺治汉中府志校注》,使“隐身”300多年的这部古籍以全新面貌问世。当今历史档案和古籍文献整理质量良莠不齐,而《校注》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于历史考释征引典籍浩繁,材料取舍有度,史事辨析清晰,舛误订正有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可谓档案、古籍整理的上乘之作
顺治《汉中府志》是清初汉中府知府、常州武进(今属江苏)人冯达道主持纂修的一部志书,成书于顺治十三年(1656),记述了上起远古,下迄清顺治年间汉中的建置沿革、政治兴衰、权力更替、经济演进、社会发展和人文变迁,留下了明末清初社会变革的印记,是一卷重要的历史档案和地方文献。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汉中府知府滕天绶主修《汉南郡志》时,尽量利用了顺治《汉中府志》的刻版和素材,但隐去了王朝之初的政治纷争。嗣后,此书未见再雕版印刷。也就是说,作为改朝换代之际的一部重要志书,顺治《汉中府志》流传不过30多年,近世300多年竟难再见。2019年11月,汉中市档案馆编辑、王浩远点校的《顺治汉中府志校注》,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使这部地方文献得以完璧呈现于读者。
我们欣喜地看到,《顺治汉中府志校注》(以下简称《校注》)严格遵守古籍整理之学术规范,分段标点严谨,文字改补有据,注解说明精审;前人所谓校勘古籍训诂、考证、雠校三途,除训诂之法采用较少外,考证和雠校都做得很好,前文所述志书整理常见的问题在此书中基本没有出现;且用繁体字竖排出版印刷,典雅古朴。因此,《校注》诚可谓古籍整理的上乘之作。本文仅就其注释中地理、人物、史事的“考释”等方面之学术价值谈几点体会,以窥一斑而思全豹。
一、征引史籍浩繁
查阅、征引大量图书资料是古籍整理的基本路子和要求。对于古籍中一些人物和事件,在整理时需要做出诠释,这就需要查阅大量的历史典籍和今人研究著述。而对于一部地方志书来说,更存在许多人物其名不彰,一些事件扑朔迷离的现象,非翻检一些冷僻书籍,以致借助考古、查勘碑石而不能得其详。更有甚者,与一般古籍有多种版本流传不同,顺治《汉中府志》只有国家图书馆藏本,没有其他版本可据参考,故无法“对校”,只能以“本校”“他校”为主,因而占有资料的丰富程度在整理时就显得更为重要,征引史籍浩繁就成了《校注》的第一个特点。
《校注》考释时引用的史料,既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尚书》《周礼》《礼记》《左传》《诗经》《庄子》《孟子》《扬子法言》、明代诸帝之《实录》《清世祖实录》等基本史籍,《华阳国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雍大记》《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历代地理名著,《全唐诗》《全唐文》《全元文》《艺文类聚》等诗文总集和类书,王勃、杜甫、岑参、欧阳詹、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元稹、李商隐、罗隐、孙樵、欧阳修、赵抃、文同、司马光、苏轼、陆游、周必大、康海、杨慎等30多位唐代至明代文人之别集,明清两代之《一统志》《陕西通志》《四川总志》、汉中各府州县志及汉中之外的多种府州县志等地方志书,还有唐人陆贽《陆宣公集》,宋人邵雍《击壤集》、程颢程颐《二程集》、朱熹《近思录》,明人方孝孺《逊志斋集》、吕柟《泾野先生文集》等哲学政论著作,《道藏》《大正藏》《宋高僧传》等宗教典籍,更有唐代李肇《唐国史补》、明代刘基《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马文升《马端肃奏议》、焦竑《国朝献徵录》、张朝瑞《皇明贡举考》等稀见或不常被引述的古籍,《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里耶秦简牍校释》《秦封泥集》《名臣碑传琬琰集》《隶释》《石墨镌华》《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武侯祠元人题刻碑、张良庙明人题刻碑、汉中府明清碑石等考古研究及碑石资料,《严耕望史学论文集》《史念海全集》、陈显远《汉中碑石》、郭荣章《石门汉魏十三品合集》、朱保炯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等今人研究著述。此外,还有《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诗文评传著作,《太平广记》《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古代小说,《郡斋读书志》等书目文献,可谓涉猎广泛,琳琅满目。据不完全统计,对原文不过十多万字的《汉中府志》,校注时征引的史籍达二百多种,可见校注者用功之深。
二、材料取舍有度
注释内容的取舍是体现古籍整理学术价值的重要一环。太简,读者难得要领;太繁,容易变成“资料汇编”,影响对原著的阅读。就史实和人物考释来说,正确的做法是提供资料线索,浓缩与此书此地直接相关的内容即可,而不能简单抄录各书。前代大量古籍整理著作和当今的一些著名古籍整理著作都能恪守这些规则。但有的人点校旧志,仅靠查阅、摘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和《辞源》《辞海》等基本书籍,缺乏广泛查考和认真取舍意识,因而常常出现以下弊病,即常识性的概念和史书中有专门、明确记载的人物、事件,注释时抄写一大堆,冷僻的概念及史书、工具书中没有明确记载的人物、事件,也就不注。诚如复旦大学教授傅杰批评的:“现在很多学者所谓的注,他注出来的地方我也能很方便地查到,我查不到的地方,他也不注,因为他也查不到。”而《校注》避免了这些缺点,没有出现此类问题。
“桓温平蜀”是东晋时的重大历史事件,与汉中行政归属变化有直接关联,因而也是汉中府县志中频频提及的一个短语。桓温生平及其平蜀过程都很复杂,而《校注》的考释却很简练:“桓温,字元子,谯国龙亢人。东晋名将。永和二年(346)十一月,桓温率军伐蜀。永和三年三月,攻克成都,灭成汉李氏政权。详见《晋书》卷八《穆帝纪》、卷九八《桓温传》。”(第7页)使人一目了然。
有的历史概念产生背景复杂,所涉史事难以形成定论,如果要将相关史料完全陈述胪列,相当于写一篇学术论文,这就超出了注释的范畴。《校注》处理此类问题时注重提炼,直陈要素。《书·禹贡》中的“九州”划分是一个重大而至今难以确指的地理概念,对汉中所属之梁州,《校注》用三四十个字加以说明:“梁州,古九州之一。东界华山,南至于长江,北为雍州,西无可考。《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第1页)《诗经》中有“南有嘉鱼”说,《校注》如此表述引证:“南,指南方长江、汉水一带大川。《毛诗传笺》:‘江汉之间鱼所产也,’嘉鱼,好鱼。《郑笺》:‘言南方水中有善鱼。’”(第57页)既顾及校注本体之指向,又不悖诗文之原意。
顺治《汉中府志》各卷内有数量不等的主修者冯达道的论述,已成为原著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卷四《官守志》冯氏论及前贤循吏时,有“龚黄召杜,退处不敢与抗”语,“龚黄召杜”是古人常用的典故和循吏故事,《校注》的注释之文是:“龚黄召杜,龚遂、黄霸、召信臣、杜诗等四位循吏的合称,后世泛指循吏。龚遂、黄霸、召信臣三人事迹均见《汉书》卷八九《循吏传》。杜诗事迹见《后汉书》卷三一《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246页)线索清晰,言简意赅。此外,在考释街亭、陈仓道、真符县等地理名词,杨从仪、李师颜、胡荧、胡曾、唐卿、忠穆公严震等人物生平及校释《建置志·学校》《食货志·灾祥》中时间、年号之错误时,《校注》都做到了取舍有度,表述简明。
三、史事辨析清晰
一些地方志书囿于史料来源不广和编者认识褊狭,往往史事记述模糊甚至似是而非,需要校注者给予辨析说明。顺治《汉中府志》也存在此类问题。此著大量利用明万历《汉中府志》原文原刻,在行政建置及其沿革记述上,竟然以明代汉中府的区域和建置去反推前代汉中的行政区划,势必造成错误、混乱;有时对前代行政区划层级理解不透,乱列归属,甚至将与汉中毫无关系、距离遥远的县名列入汉中辖县。校注时如果一一论证这类问题,则耗时、繁琐。《校注》在指明“全书均以明万历时汉中府辖地统计前代郡县”(第6页)的前提下,直接援引各朝正史之《地理志》(或《郡国志》《州郡志》等)或唐宋地理著作中州县设置的史料,厘正错谬,达到了条分缕析、简洁明了之效果。
沔县之前身为西汉之沔阳县,南北朝以降,境内又有过华阳县、嶓冢县、西县、沔州、铎水县等州县设置。明初始具其名的沔县虽由沔州更改而来,但沔州徙治于沔县境内年代较晚、时间较短,实不足以体现沔县之建置沿革。顺治《汉中府志》之“沔县”沿革却大段转录《方舆胜览》等典籍中与沔县无直接关系的武都郡、沮县、武兴国、兴州的历史资料。《校注》指出,“沔州”虽由“兴州”而来,但当时沔州治所在顺政县(即今陕西略阳),“此沔州与清时汉中府所辖之沔县并无隶属关系。换言之,此沔州沿革实为略阳县沿革”(第21页),厘清了错讹之根源。
原著卷四对梁州刺史范柏年生平的记述,援引《南史·胡谐之传》附载之内容,不光语焉不详,而且给人以胡谐之因泄私愤而至范柏年殒命之印象。这当然是片面的。《校注》引证《宋书》之《后废帝纪》和《顺帝纪》的史料,说明范氏之死主要缘于政治分歧,作为宋臣的范柏年对图谋篡位的齐王萧道成原本不满,故萧道成篡宋后,“道成长孙萧长懋许范柏年为府长史,诱之襄阳,杀之”(第254页),这样就说清了范氏被杀的原委和实质。此外,卷一对“萧何追韩信处”,卷四对明代汉中知府赵玉、刘宋梁州刺史刘秀之、北魏梁州刺史傅竖眼、贾至《沔州秋兴亭记》,卷五对权皋籍贯、垣护之生平、苏轼苏辙与汉中关系,卷六对张俞生平及诗作、法照生平等史事和人物的注释,都能用简明的史料纠正原著的错讹。
四、舛误订正有据
对于旧志中的差错、谬误,整理时需要订正,但订正必须建立在证据确凿、立论严密的基础上,而不能以一己之见甚或臆想轻易否定前人。汉中属《尚书·禹贡》中九州之梁州地域,境内有山脉曰“梁山”,据《太平寰宇记》等典籍记载,梁州即因梁山而得名。[1]故汉中人每每见梁山之名,就与本地的梁山产生联想。其实天下名梁山者何其多矣,仅《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收录的就有9处。[2]汉中人容易犯的“错误”,作为顺治《汉中府志》主修者的冯达道也犯。在卷三《食货志·物产》文末,冯氏论曰:“《书》记梁州所贡首推璆铁银镂,而梁山之诗亦曰‘献其貔皮,赤豹黄羆’……”(第149页)在此,冯氏以为《诗·大雅·韩奕》中“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所咏之梁山即《尚书》中所载之汉中梁山,实则彼梁山非此梁山。《校注》在引证《毛诗传笺》及程俊英《诗经注析》的笺注后曰,《韩奕》中的梁山在今河北固安县附近,“可知此诗与汉中无关”(第150页),显示了校注者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态度。
明清时“汉中”在春秋战国时的归属是一个古籍记载有误、后世理解不一的问题。因晋人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有“六国时,楚强盛,略有其地,后为秦,恒成争地”之说,北魏《水经注·沔水》又曰:“至六国,楚人兼之(指汉中首府南郑——引者)。怀王衰弱,秦略取焉”,明清两代之《汉中府志》及相关县志,大多都有汉中之地在春秋或战国之时曾属于楚国的记载。其实,《华阳国志》和《水经注》中的记述,缘于对《史记》卷五《秦本纪》中“孝公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和卷四〇《楚世家》中“(楚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斩甲士八万……遂取汉中之郡”[3]等史料的误读。《史记》此处所谓的汉中,地望为今乾佑河流域以东至湖北房县、均县之地,与汉代以后的汉中无关。汉中府、县志因袭两晋南北朝人之旧说,致成错谬。对顺治《汉中府志》卷一《沿革》中汉中“春秋属秦楚”之疏漏,《校注》引用《水经注·沔水》说明其来历,在相关条目下明确指出“此说有误”(第5页)、“南郑属楚之说有误”(第12页)、“楚国势力不及汉水上游”(第13页),并结合《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和严耕望《楚置汉中郡地望考略》的考证,得出“春秋时,南郑当属蜀,北与秦接,与楚无涉”(第5页)结论,文约事俱,实可抵一篇考证文章。与之相呼应,对卷一《沿革》中“褒城县”“至六国,楚人兼之。怀王衰弱,秦略取焉”注曰:“以上二句录自《水经注》卷二七《沔水》南郑县。南郑属楚之说有误。详见上文汉中府沿革注释。”(第12页)既指明了原文出处,又指出了其间错误;至于错在哪里,则无赘文,以另文他见方式说明。

《校注》在史籍征引、史料取舍、史事辨析、舛误订正几方面的优点及其他方面的严谨处理,展示了其应有的学术价值。但是,作为比较仓促地出版面世的一部学术著作(据说从整理到出版只有一年多时间),也有其缺点和不足。如,对引文中历史纪年括注公元年份,尽管现在有人如此处理,但仍感欠妥。再如,秦、西汉汉中郡的治所,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尽管有人认为在南郑,但更多的史料和论证却显示在西城,《校注》既云“汉中郡尝移治西城”,又曰“秦汉中郡,治南郑。两汉时,汉中郡皆治南郑”,(第12页)既有商榷余地,也显现出矛盾,如果能采纳主流意见或吸收不同观点,可能会更恰当一些。《校注》的优点,毫无疑问有利于原著的流播和传承,其不足,则为今后整理档案资料、古籍文献者提供鉴戒。从这个意义上说,《校注》是一部值得重视的古籍整理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