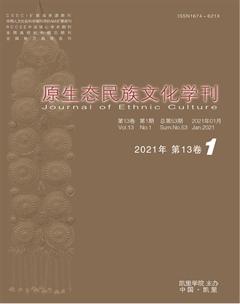伏羲文化的资源化与景观叙事
张迪
摘 要:在当代城市谋求发展的语境中,文化资源化能够为地方竞争提供经济和文化的双重资本。以伏羲文化为例,地方通过文化再生产完成对“圣地”身份的叙事与论证,通过“圣地之争”使伏羲文化由地方传统、地方性知识转化为文化资源。其中,景观叙事是伏羲文化资源化的重要实现途径,这一可视化手段促成了地方民众对“圣地”的地域认同。多地通过共享伏羲文化资源形成了地域共同体,而论争过程奠定了其在这一文化有机联合体中独特的地位和相互间的结构关系。实践证明,文化资源无法独占,只有合作互文才能深化文化资源开发,并最终促进地域共同体的多赢。
关键词:伏羲文化;资源化;景观叙事
中图分类号:C95 - 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1)06 - 0118 - 11
伴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基本的物质消费需求得到满足,民众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和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愈发急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的兴起、城市资源开发形态多样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使得文化和旅游业在地方经济发展和扩大社会影响力中扮演着逐日重要的角色。由于文化权威性与旅游资源开发的价值效益呈正相关,各地争相对重要文化要素的正统性、唯一性和独特性进行叙事和论证,通过景观生产、语言生产、符号生产等一系列文化再生产活动,争夺“故里”“圣地”的重要地位。如炎帝故里“六地之争”1、梁祝故里“六地之争”2等。论争的焦点表面上是历史真伪考辨,实质则是文化资源和文化权力之争。
本文以伏羲文化为例,探讨了在文化资源化的视角之下,地方政府如何通过景观叙事再造“圣地”的地域认同,并进一步通过景观生产促使伏羲文化资源化的过程。
一、文献综述和问题导入
近年来,受外国理论的译介和社会变迁的影响,被视为“口头传统”的神话在学术研究中由扁平式的对单一神话形态的研究,如异文比较、故事母题、信仰仪式等,逐渐转向了全形态、立体式、多向度,注重神话系统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神话与社会产业多面向的交叉研究。
叶舒宪教授提出的“四重证据法”认为,在神话研究中不仅要重视传统的文献和仪式证据,还要注重对物的叙事和图像叙事的重视[1]。与之神交的田兆元教授将民俗学的学科视角引入神话研究,提出了“神话的三种叙事形态说”,即语言文字的叙事形态、仪式行为的叙事形态和景观物象的叙事形态。他认为神话是将叙述和行为结合为一体的综合文化体系,并且是以认同性和建构性为目的的神圣性叙述。广义的神话包括完整的口头神话、传说、故事叙述形式,以及如一段不明确的表述、一个神的名称等不完整的特殊表达形式。此外,神话叙述的衍生形式,如象征符号(图案、物品、塑像、神圣的空间和遗迹等),祭祀仪式、禁忌行为、崇拜活动,甚至风俗习惯等,都是神话的组成部分[2]95 - 112。在此基础上,孙正国教授认为神话不仅是包括语言形式、神圣仪式、图腾信仰、部族制度以及行为法则的综合文化体,而且更应当是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神话的资源转化应当是神话研究的新转向[3]19 - 22。
丰富的口头传统、多样的民间仪式,以及遗留的纪念性建筑都是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通过对其中文化要素的分解、变形和再创造,可以进行相关文化产业的再开发。在现代消费社会,神话的内涵意义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和消费行为为人们所接受和获得。在文化内涵转化为消费产品的过程中,物象叙事、仪式叙事等“可视化”手段,发挥着比“不可视”的语言媒介更直观的影响,起到增强地域民众与地域文化之间的情感联结,以及促成新的地域认同的作用。景观叙事是文化资源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景观叙事是将“可视化”的对象视为文本,叙事者依据地方记忆、神话传说等原型,通过命名、序列、揭示、隐藏、聚集、开启 [4]等多种叙事策略,呈现地域文化的意义,加深地域文化认同的过程。不少学者都论述了景观叙事与文化认同感之间的相互支撑关系,如余红艳认为口头传统的故事情节通过景观的建造而加入特定的审美情感、价值观念,并经过重新的编码过程成为全新的地域文化符号[5]。张晨霞则通过研究帝尧传说的景观叙事与意义构成之间的关系,认为景观演述传说的同时,传说为景观注入特定的精神内涵和象征意义,二者融合互构促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精神凝结[6]。一方面,景观促成地域文化认同,有助于将地方建构成为风格鲜明的旅游消费对象或语境;另一方面,游客正是通过对符号化的景观叙事解码的过程完成旅游体验的。景观搭建的过程正是叙事表达的过程,最终激活了地区发展的经济活力,实现了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
综上,景观作为叙事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沟通主体与阐释对象之间的媒介,是一种解释、阐释的策略,是人们传达信息和解读世界的动态的、综合的文化发生过程。作为能够为人的视觉意识所捕捉和观赏的文化对象,景观可以是固定不动的建筑、物品,也可以是动态呈现的仪式表演和参与表演的演员,甚至游客在参与相关文化活动体验之时,也同时成为其他游客观赏的对象,成为景观的一种。
伏羲神话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创世神话之一,是关于民族血缘和文化认同的神圣叙事,几千年来传承不息,在当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依然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一方面,对伏羲文化的消费,意味着对与其直接相关的文化产品进行经济增值,有助于地方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传承伏羲文化对凝聚中华民族、弘扬民族气节具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伏羲文化的资源化困境始终是学者关心和研究的重点。周小华早在2004年就提出,对于甘肃这一文化大省而言,伏羲文化的资源化和产业开发程度是与其重要的文化价值极不相符的。伏羲文化没能像孔子文化之于山东省那样,为甘肃带来经济腾飞或者文化传播影响力的增益,甚至在省内,也没有成为与敦煌、《读者》和牛肉面并列的区域文化品牌。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之一,是地方政府缺乏将伏羲文化看成一种资源的视角和思路,从而导致了文化产业化的不足与失败。在提出解决策略时,周小华提到了可以借鉴伏羲建筑文化的精华——天水建筑的龙凤特色,以此建设民俗度假建筑,以帮助发展文化旅游[7]。无独有偶,学者杜谆也注意到了景觀生产在伏羲文化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在新密,民众和企业相继自发修建了规模不同的庙宇建筑,以形象化的呈现伏羲文化,并增强民众对伏羲文化的记忆。然而这些或简陋或精致的庙宇建筑,由于缺乏政府的相关产业配套和服务,未能较好地转化为旅游消费行为。而在市政府把伏羲文化作为宣传对象之后,某种程度上官方彰显了其在地方文化系统中的独特性和引领地位,引导民众形成了新的“圣地”认同。在此之后,原有景观生产转化为旅游消费行为的程度逐渐深入。杜谆认为,伏羲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政府权力效应的巨大作用是民间所不能比拟的,政府行为带有合法性的指向性,没有官方的认可,所有再生产行为都处于“名不正”的位置[8]。可以说,景观生产是伏羲文化资源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官方的介入决定其资源开发的深度和效率。
二、传统的发明与圣地的建构
在当代语境下,本土认同和异域想象由于具有消费价值而成为区域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占有同类文化资源的地方之间,不可避免的展开了对资源开发独占权的抢夺,通过景观生产、语言生产以及策略性叙事等方式争相论述其地方传统的正统性和权威性。
(一)天水和淮阳
历史上祭祀伏羲自秦人始,而秦人发迹于天水,并迁徙至关中发展壮大。天水也是传说中伏羲的诞生地,因此有“羲皇故里”的美誉。明朝统治者将伏羲祭祀纳入帝王祭祀制度,通过多次亲祭和颁布诏令确立了淮阳太昊陵在统治阶级祭祀秩序中的崇高地位,淮阳又是伏羲立都之所,因此有“羲皇故都”的称号。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侧重,但天水和淮阳两地始终是伏羲文化活动的最重要中心。近代社会动荡使民间伏羲崇拜活动一度中断,直到80年代,受文化复兴浪潮的影响才逐渐得到恢复。近年来,伏羲文化的呈现方式不断丰富,活动规模不断扩大,逐步成为地方标志性文化。为了更好的开发伏羲文化资源,两地分别进行了公祭大典的发明,企图将地方祭祀传统提升为国家祭祀,以谋求当代官方祭典中心的圣地地位。
另一方面,当代“圣地”的确立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话语——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是中国当代文化事业与世界接轨的重要表现,初衷是对急剧的社会变革中迅速损毁的民族文化之根进行抢救性、前瞻性的保护。具体做法是对传统文化或民间艺术依据国家行政层级进行保护主体的划分,以此来对其官方性、合法性和重要性级别进行潜在背书。尤其对视国家话语为圣典的民间来说,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意味着绝对的文化优越感,极大提升了地方民众集体的自信心。2006年5月20日,甘肃省天水市与河南省淮阳县的文化管理部门共同将“太昊伏羲祭典”成功申报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确立了两地当代伏羲祭祀的圣地地位。
张士闪将民间与正统归纳为“礼”“俗”这样一对概念,认为国家政治“地方化”与地方社会“国家化”同时发生。中国社会的“礼俗互动”包括国家的“以俗入礼”和地方的“借礼行俗”。国家通过对地方传统的甄别、遴选与调整,给予不同层级的名誉与自主,使之纳入社区公共文化系统之中,民众则自觉地将地方传统贴近国家意识形态,以获得合法性[9]。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在形式上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官方文化政策,其申报、认定、以及活动开展的全程都带有官方正统的属性特征。而非遗项目的内容本身,则多为地方代表性的民间传统文化或艺术表现形式。因此,在伏羲神话的当代传承和复兴过程中,非遗语境下的文化生产具有民间性和正统性的双向解释力,体现了国家政治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相互嵌套。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对非遗保护相关活动的优惠政策导向,在伏羲信仰的恢复过程中,借助非遗保护的名头开展相关活动更具便利性;另一方面,新的伏羲文化的相关创造,提取和借用地方非遗事项的元素进行文化生产,以此为仪式的地方性、民间性以及正统性做注。以天水为例,公祭伏羲大典充满了对民间非遗传统的转写与借用,其中表演部分常见的“西部旋鼓”“秦州夹板”“甘谷唢呐”“秦安蜡花舞”等都是天水地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只不过是将其脱离了原生态文化语境,以更适应舞台观赏为宗旨进行了表演化的再生产。
1988年时值龙年,于天水地区地方民俗知识精英所认定的“龙的生日”——农历五月十三,诞生了首届祭祀“龙祖”伏羲的典礼仪式,创造了由人民政府主祭,民众参祭,官民同庆的当代公祭格局。典礼常与文艺演唱会、书法比赛、绘画和文物展览、体育竞赛、戏剧演出、工农业产品展销、经贸洽谈签约等合办,以全方位的展示、推介地方文化,促进招商旅游等经济活动为宗旨。
公祭典礼于上午9时50分开始,取“九五至尊”之意,叙述了明代开始伏羲被视为上古第一圣王明君的重要地位。其后全体参祭人员肃立,击鼓34咚,鸣钟9响,象征全国34个省、市、自治区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中华儿女对人文始祖的至高崇拜和无限敬仰。乐舞告祭之后,参祭人员依次敬献花篮,并行三鞠躬礼代替磕头行香,陆续进入伏羲庙拜谒人祖。1这一流程基本上成为当代公祭典礼的范本,为其他城市所模仿。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设计公祭大典时,是将自己带入国家立场的高度,将重点放在弘扬伏羲文化对于全体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国家地理版图完整的象征性意义上。2000年开始,天水市政府举办每年一次的伏羲文化旅游节,结合地区旅游资源,与轩辕文化旅游节、女娲文化旅游节结成一个相互辉映的上古神话集群,此后,旅游节庆活动与公祭大典合办几乎成了惯例。由于夏季是天水最适宜进行旅游观光活动的季节,2007年,政府又将公祭大典日期改为夏至日。经过三十多年不间断的重复,公祭大典成为了新的地方文化传统。
随着天水公祭大典的规模不断提升,祭祀仪式由地方政府主办升格为省祭,最终扩展为两岸共祭,民众通过对这一景观的观赏和参与,确认了彼此间作为共同集体成员的身份认同。一衣带水的情感依恋与文化联结使得伏羲神话成为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其标志性意义逐渐从对地方历史感的认同,扩大为对国土统一和文化一致的趋向性认同。新的地方传统——公祭大典被发明的过程,即是通过景观生产强化伏羲作为上古人文始祖形象的过程,也是确立地域作为文化开发的圣地地位,以及开发出新的旅游资源的过程。
淮阳民间的近代伏羲文化活动也于20世纪80年代起逐年恢复并不断得到发展,但直到2005年,才借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东风举行了第一届公祭大典仪式。当年的举办时间为10月7日,是历时一个月的“中国周口淮阳2005姓氏文化寻根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0],其后,逐渐固定为农历二月初二举行。仪式程序和内容都与天水极为相似,上午9时5分开始,撞钟击鼓各9响,鸣礼炮34响,由官员领祭,各界代表依次拜谒伏羲圣像,通过敬献花篮、献香敬爵等方式表达对人祖的崇敬。与天水的伏羲神话利用本地非物質文化遗产进行文化再生产不同,淮阳政府不仅将非遗展演作为伏羲公祭大典期间固定的重要活动,而且其内容不局限于本地,还邀请全国多地,甚至全世界的非遗前来参会。以2018年为例,淮阳庙会的主题为“千年古庙会,万姓拜伏羲;传承民族文化,建设美丽淮阳”。可以看出,当代淮阳伏羲文化再生产是为现代城市建设服务的。由于旅游业对地方经济的重大贡献,伏羲神话成为淮阳发掘旅游资源的重要文化源泉。因此,在官方表述中,举办公祭伏羲大典以及民间庙会的目的是“扩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知名度,全面促进县域文化旅游产业又好又快发展”[11]。通过公祭仪式的展演,将伏羲神话视为一种文化资本,其目的和宗旨是促进整个区域的经济文化发展,以及扩大地域的政治文化影响力。
(二)新乐
随着社会发展,渴望地方经济开发并且拥有伏羲神话资源的城市,纷纷加入到享受圣地“红利”的队列中来,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河北省新乐市。历史上,新乐从未成为伏羲祭祀的全国中心,相对处于伏羲文化传承的弱势地位。為了与“羲皇故里”和“羲皇故都”并肩而立,地方政府采用智慧的策略对地域别称进行了语言生产,在宣传话语中使用了“羲皇圣里”的表达,从格式和意义上对天水和淮阳进行了全面模仿。此外,挖掘伏羲这一神话人物的个体生命谱系,创造出“生于天水,长于新乐,都于淮阳”的叙事方式。同时,新乐也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话语体系,完成了官方对其圣地地位的认定,并进行了公祭大典的发明。
1995年,在相关建筑景观修建的基础上,由新乐市委、市政府组织牵头恢复了公祭伏羲的活动。公祭日被设置为新乐民间祭祀伏羲的正日,农历三月十八日。典礼开始时间和祭祀仪程与天水、淮阳地区的公祭大典极为类似,上午9时50分鸣礼炮21响,击鼓34响,鸣钟9响,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整的地域版图,以及对人文始祖的至高敬意。主要内容还包括恭读祭文、乐舞告祭、供奉祭馔、敬奉高香、行祭拜礼等[12]。科大卫和刘志伟解释了对同一神灵信仰的祭祀仪式在多地呈现为相似性的原因。他们认为这是地方文化精英坦率地或有目的地,以上行下效的仪式形式掩饰地方风俗,进而把地方风俗装扮成正统,通过这种方法使其获得正当性 [13]。三地不约而同的模仿官方规格进行公祭典礼仪式的发明,正是希望通过对正统性的论述为资源开发提供合理性依据。
仪式作为一种景观,具有呈现意义的功能。涂尔干指出“仪式是社会关系的戏剧性呈现”,特纳也提到“这些事件的上演(指仪式)是公众符号化地、戏剧性地展现社会最重要的象征和价值观的时刻”[14]。公祭仪式通过举行的方式、参加的人员身份(大典主祭人一般由省长或省委书记担任,主持人为省政协主席)等塑造国家在场的象征意义。“公祭伏羲大典”的发明,是地方政府结合人民现实存在的精神需求论证地域伏羲崇拜的圣地地位以及扩大地方经济政治影响力而做出的文化创造。
随着伏羲文化资源化的不断深入,新乐伏羲祭祀祭典于2009年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于2011年进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扩展项目的形式,与之此进入名录的天水、淮阳共享同一个项目序号和项目编号,完成了对伏羲祭祀圣地的建构。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文化体系中,甘肃天水、河南淮阳,以及河北新乐都先后进行了地方化的公祭大典的发明,并努力使其成为新的传统。一方面,通过传承和恢复历史传统来证明伏羲文化与地域之间悠久的历史渊源,以论证其合法性地位;另一方面,试图将公祭大典提升为国家层面,以其重大影响力,作为论述其在当代中心地位的有力证明,也以此成为宣传旅游的重要依据。伏羲文化经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官方话语,在地方圣地资格的合法化过程中,获得了旅游开发的价值性,通过公祭大典这一景观叙事的过程,具备了资源化的前提基础。
三、景观叙事与伏羲文化的资源化
现代社会,地方文化因其独特的地域风格特征而具有了消费潜质,被视为文化资源得到多种形式的开发,转变为可供人们消费和享用的文化产品。这个过程正是通过景观叙事得以实现的。地方政府通过空间生产恢复信仰空间的建筑景观,为文化旅游活动提供场所;为了配合旅游业的发展,对民间信仰仪式进行创造和迁移,使之向表演化和娱乐性过渡,促使祭祀仪式景观化和信仰行为习俗化,对游客来说,进行信仰行为的人也成为一种叙述地域文化特色的景观呈现。
(一)物的营造与景观叙事
社会现代化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变革,不仅指文化、经济、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结构的现代化,还包括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生活空间的城市化,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最终体现为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传统社会逐渐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进程[15]。景观生产正是勾连起过去、传统以及现在的文化创造的中介。景观叙事是意义呈现的物质基础,通过对伏羲文化相关建筑景观的恢复和拓展,不可视的文化才有可能通过体验活动和旅游实践转化为文化资源。
1.旅游空间的生产
近代以来,伏羲的信仰空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民国时期军阀混战使得天水伏羲祭祀一度中断,伏羲庙建筑先后为部队、工厂、学校所占,直到1980年,才又真正意义上恢复神圣空间的属性。有关伏羲庙的一切事项由天水市博物馆接手,开启了现代政府文化机关主导神话复兴的文化保护模式,伏羲庙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恢复和扩张,民间祭祀仪式也重新得到了挖掘和保护。2005年,伏羲公祭大典升格为由甘肃省人民政府主持。为了配合典礼的隆重,为祭祀仪式提供庄严古朴、神圣宏伟的举办场所,专门修建了约一万平方米的伏羲文化广场。在广场四周配以碑亭、诗文碑廊、祭坛、祭台和牌坊等景观。通过象征符号的运用创造能够传达出伏羲文化深厚内涵的景观形象,如在祭坛四角设置了4根龙图腾柱,神道两侧布置了8根图腾八卦柱,以及为了寓意伏羲“九五之尊”的身份,在祭台周围布置了95株四季常青的松柏。在景观生产中,着力对“龙”形象进行了挖掘,将伏羲塑造为“龙祖”。如将公祭日期定为传说中龙的生日;将龙城作为城市形象的定位,命名市中心广场为龙城广场;修建以民族图腾龙为主题,并弘扬伏羲文化的城市主题公园——龙园。
与此类似,淮阳也经历了伏羲信仰空间的恢复和扩建。早在民国时期,尽管时局极端动荡,淮阳的仁人志士还是费劲心血使得太昊陵两度得到捐款修葺,当时总统黎元洪、徐世昌等,还曾制匾额以示奉祀。1新中国成立后,淮阳县成立了“伏羲陵保护委员会”,主持相关修葺工作,1966年“文革”期间,伏羲塑像被炸毁,伏羲文化的景观恢复被迫停止。20世纪80年代,当地文物保护部门开始接手保护工作,重塑了伏羲圣像,并继续修葺和扩建太昊陵的相关建筑。2004年又新建了伏羲文化广场,逐渐使之景区化 [16]410 - 417。随着信仰空间的修复和伏羲圣像的重塑,民间庙会很快得到复兴,规模一年胜似一年。
新乐的伏羲庙建筑大部分也被毁于“文革”时期,直到1987年,政府才修复了伏羲庙的后殿和大殿。到1995年,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旅游业,开始重视对伏羲庙建筑的保护和对伏羲文化的挖掘利用。在原有槐抱椿、人祖庙、八卦阵、浴儿池等景观的基础上,花費1500多万修复了庙宇主体建筑 [17]。到了2008年,伏羲台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扩建了伏羲文化广场,修葺了伏羲庙内的壁画、塑像等。不知是巧合还是借鉴天水的迎圣水仪式,新乐也新建了寓意伏羲圣水的大理石葫芦景观,以阐释葫芦、洪水与创世神话之间的关联。此外,还特意聘请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做出《新乐市伏羲文化城旅游开发规划》,以此为指导,“伏羲文化城”被纳入新乐“十一五”规划,建成了甲历馆、龙凤图腾园、伏羲雕像等,成为淮阳旅游业的支柱项目[18]74 - 75。建筑空间的营造为旅游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景观叙事是伏羲文化资源化的基石。
2.旅游对象的生产
物的营造除了为旅游文化活动提供空间之外,还提供具体的消费对象,包括以神话要素为内涵的衍生消费品,以及独具特色的文化体验活动。如天水开发的“羲皇故里”系列白酒,在当地白酒消费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并由于龙形浮雕的酒瓶设计和随酒赠送的爵型酒杯而受到游客欢迎。淮阳民间的泥泥狗,原本由于其是为伏羲守陵的神兽而具有神圣性,但在现代庙会中,已与布老虎等其他地方特产一样,变为旅游纪念品,成为日常文化消费的对象。
还有原本属于民间祭祀仪式的“迎献饭”仪式被提取出原生文化语境,以提高观赏性和审美性为原则进行了改造,由于变化的发生时空,神圣性被削减,成为景观化的表演。与信仰场所的景区化类似,传统中饱含原始图腾崇拜性质的民间艺术、禁忌和神秘感逐渐丧失,成为游客体验地方风俗民情的手段,如“灸百病”“担经挑”等。
天水伏羲庙庙会的高潮一般为农历正月十六。从零点开始,人们蜂拥而入,烧香叩首、虔诚跪拜,其中最重要也最具特色的习俗便是“灸百病”。传说伏羲庙内最初按八卦方位栽种了64颗古柏,每年有一株当值,人们会在这株特定的柏树上贴满红色纸人,并根据自身需求用香火点燃艾柱炙纸人的特定部位,以祛疾除痛。经过战乱和火灾,庙内古柏现存37株,缺少了通过卦象推演当值树神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懂得推算之法的民间专家难寻,“灸百病”的对象逐渐扩大。庙会期间,几乎所有的古柏树干上都会贴满各式各样的红色纸人,数量之大以致许多树皮被烧毁。为了保护古树,目前庙内柏树都被箍上一圈铁皮用来隔离灸烤。随着社会发展,灸病的内涵逐渐扩大到灸学业、灸福气、灸平安等。由于祭祀场所的景区化,人们容易将不可视的信仰转化为可视的旅游资源加以甄别,对游客来说,正在进行“灸百病”的人和这一文化行为过程本身也成为景观的一部分。
在淮阳,当地信众会在伏羲陵附近通过“传功”的特殊方式与天或神灵进行沟通。当作为地方传统的民间庙会举办与当代城市谋求政治、文化和经济地位提升的目标结合,伏羲信仰的灵验叙事与官方文化保护的合法性话语相遇,使得原本以纯粹的个体灵验信仰实践为特色的民间庙会活动具有了被生产成为旅游对象的可能性,地方政府以此为宣传噱头吸引游客,并将其描述为原始的、古老的、神秘的文化现象,以此使地方信众的崇拜行为具有了观赏意义,并呈现为被游客所观赏的一种景观。
(二)仪式的发明与景观叙事
物的景观生产不仅提供了旅游活动的空间和对象,还为地方政府和文化精英发明仪式提供了物质基础。仪式的创造往往是与物的空间拓展相辅相成的,如泮池的修建和迎圣水的发明,鼎的设置和祭鼎仪式的适应性创造等。随着仪式内容不断丰富,仪式形式观赏性不断提高,仪式本身与相关器物、装置成为一种表演、一种观赏对象、一种景观。
通过史料梳理发现,每当伏羲庙进行建筑风貌的扩建和建筑范围的增减,祭祀仪式都会相应地跟着不断新增或递减。据载,天水伏羲庙从明弘治三年(1490年)第一次修建,至最近的一次,先后经历过十一次大修。从2003至2007年,使伏羲庙建筑群形成了这样格局:前一楼(戏楼),迎三坊(开天明道坊、继天立极坊、开物成务坊),双进门(大门、仪们),双朝殿(先天殿、太极殿),一园(后花园),两跨院(乐善院、忠义祠),登见易,跨泮池,临后门 [19]91 - 106。泮池原本是后花园的一部分,但在历史的沧桑岁月中遗失不存。2005年,为了恢复伏羲庙的全貌,以皇家建筑建制——前有宫、次有寝、后园林的规制为标准,才重新恢复了泮池景观。随后,新的仪式——“迎圣水”被发明,并作为主要祭祀程序——“迎神”中的第一项被固定下来。仪式取名自“天河注水”的地域传说,一方面论述了水对地方文化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水又是生命之源,取水供圣也表达了对生命的礼赞之情。从泮池中取水,寓意取四海之水、天下之水,寄托着天水民众对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美好期望。
此外,根据《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泰帝兴,神鼎一”和伏羲“缓兴神鼎,制郊禅” 的记载,地方政府和知识精英商议决定以“天子祭祀礼制”为标准确立了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的当代祭祀规格,仿照文献中“九鼎十八簋”的礼仪,制作了祭器66件,编钟一套。1平时,一组由9个青铜列鼎、8个青铜簋和5张青铜俎案组成的礼仪祭器被安置在先天殿内,公祭大典仪式进行时,鼎则被搬移到祭祀广场上,并且增加了由民间仪式专家向鼎焚香化表、鞠躬致意的仪式程序。既丰富了祭典的观赏性,烘托了庄严崇高的祭祀氛围,也完成了伏羲至高统领者的形象塑造。
由于河南地区广泛流传的伏羲神话中,伏羲女娲兄妹出于善良无意之中饲喂了白龟。作为回报,白龟提前告知了洪水灾难的到来,并护佑兄妹二人藏在腹中躲避。他们靠着之前饲喂白龟的馍馍得以幸存到洪水退去,这才有了重新创造人类的故事。因此,在淮阳地区,白龟因为保护过伏羲而具有消灾免难的神圣功能。人们根据此神话内涵创造了新的建筑景观——灵佑池,并设计引导了新的旅游活动。“在白龟肚内转一转,能够消灾免难,在肚里走一走,能够增福增寿,在洗灾池内洗一洗,一切灾难全洗去,清心明目,全身放松”,2如今灵佑池变成新的祈祷圣地,游客们纷纷向池中投掷硬币。如果恰巧投掷进入白龟口内,则被视为会心想事成的吉兆。
不论在什么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会减少,景区的空间生产和仪式生产就是以此种心理结构为基础的。在长期的重复中,被发明的景观仪式进入日常生活,成为新的传统。游客正是通过对这些空间、装置、体验的观赏和参与获得对他者文化的理解与独特的个人感受的,因此通过景观生产而叙事的伏羲文化具有了吸引消费的资源性意义。
四、结 语
过去30年伏羲文化的复兴过程,也是共享伏羲文化资源的城市共同体之间争夺伏羲文化的唯一圣地的过程,城市主体通过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成了对各自权威性和合法性的论证。地方政府通过景观叙事固化或可视化这一认同,如发明和创造新的公祭伏羲的祭典仪程以重塑地方民众的集体记忆,进行景区物象建设和观赏性仪式的创造发明以丰富文化消费对象,甚至将与伏羲文化相关的文化习俗景观化为一种旅游体验活动,通过对现实景观进行创造性的符号编码,不断提升伏羲文化由资源而产品的可消费性。地方政府和文化精英共同合作促成了景观的建造和文化的生产,而地域民众与旅游者则成为景观叙事所呈现的意义的解读者,所有关于伏羲文化的发明、衍生、阐释、共享的总和构成了其资源转化的全貌。
由于重要祭祀圣地中的民众对祖庙的认同始终没能达成一致,致使各地分别对伏羲文化资源进行独立开发,形成了“一祖多圣地”的模式。再加上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人员流动频仍,地域文化赖以依存的稳定传承主体遭到挑战,现代职业作息时间制度与传统民间信仰纪念日相冲突,离开故土的人士只能通过互联网技术参与伏羲信仰活动,如网络公祭等,人们通过共享伏羲文化而获得同乡的地方亲近感和家乡认同感。随着旅游业的开发,作为地方标志性统领文化的伏羲文化,成为本地居民面对游客区分身份认同的标尺。尤其重要的是,出于复杂的原因,任何一地的公祭仪式都未能成为国家级公祭,因而伏羲文化资源化经历了地域化、去地域化,以及再地域化的过程。
在现代性语境中,当代伏羲神话的复兴与地方经济发展诉求息息相关,公祭大典的发明、景区空间的营造、庙会神秘氛围的烘托,都是以更好的服务观光旅游为宗旨的。各地纷纷以伏羲文化的名义修建景区,打造节庆活动,如新密市的伏羲山大峡谷旅游区、微山县伏羲文化旅游节、淮阳伏羲文化旅游节等,而旅游产业是一个城市推介自身的重要窗口,也能够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和不可估量的经济收益。景观生产一定程度上使伏羲文化得到了弘扬,促进了伏羲文化的资源化,并加深了其在地方文化旅游业开发中的参与度,以及在经济文化影响力中的贡献度。然而另一方面,以经济为导向的竞争模式也导致了共享伏羲文化资源的城市主体之间各自为政,相互拒斥,没有联结在一起形成合力,使文化资源形成割据之势而呈现出局限性。相对来说,在整个国家范围内,伏羲文化的资源开发规模还不是很大,整体收益还有很大的空间可挖掘,与黄帝、炎帝等上古帝王祭祀的社会影响力仍有较大的差距。
总结共享文化资源的城市共同体在既往资源开发中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由纷争走向合作及在制衡中寻求平衡,才是谋求共赢和最大效率开发文化资源的有效途径。如曾对“梁祝”故里有着相当争议的四省六地,1在2015年共同发布了《推进“梁祝传说”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创意书》,标志着从此走向合作和共同开发。湖北省武汉市的汉阳区和蔡甸区经过了对伯牙子期的“知音文化圣地”的长期竞争和互斥发展,最终发现市场竞争中的制衡关系束缚了双方的发展前景,而共建记忆和共享文化、借助经典化的记忆阐释来凝聚认同,才是促进区域共同发展的正确路径,也最终促进了知音文化的影响力扩大[20]。
在某种意义上说,伏羲文化不可能被唯一的地域独占,城市主体应当由争夺资源的竞争对手向利益共享的合作伙伴转变,寻求一条多赢的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 叶舒宪.天熊伏羲创世记——四重证据法解读天水伏羲文化[C]//伏羲文化研究论文选编.兰州:甘肃瑞通邮政印刷,2019:27 - 28.
[2] 田兆元.论神话研究的民俗学路径[J].政大中文学报,2011(15):95 - 112.
[3] 孙正国.激活认同:神话资源现代化转化的关键路径[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9 - 22.
[4] Matthew Potteiger,Jamie Purinton.Landscape Narratives:Design Practices for Telling Stories,New York[M].Chichester:John Wiley,1988.
[5] 余红艳.“白蛇传”传说的景观叙事与语言叙事[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7):97 - 102.
[6] 张晨霞.帝尧传说的景观叙事构成及意义——基于山西仙洞沟景观与帝尧传说互构的田野口述资料[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20(1):29 - 33.
[7] 周小华.伏羲文化产业化近期思考[J].甘肃社会科学,2004(3):56 - 58.
[8] 杜諄.民间文化的再生产——以新密市伏羲文化为例[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33 - 36 .
[9] 张士闪.“借礼行俗”与“以俗入礼”:胶东院夼村谷雨祭海节考察[J].开放时代,2019(11):148 - 165.
[10]张靖.河南淮阳昨日举行2005公祭伏羲大典[EB/OL].(2005 - 10 - 08)[2020 - 03 - 02].http://news.sina.com.cn/c/2005 - 10 - 08/04557110757s.shtml.
[11]刘汝,杜高峰,豆文灵.河南淮阳举行公祭人文始祖伏羲氏大典[EB/OL].(2018 - 03 - 21)[2020 - 03 - 02].http://www.rmlt.com.cn/2018/0321/514395.shtml.
[12]石家庄新乐古老伏羲祭典仪式已延续千年入围国家非遗[N].燕赵都市报,2017 - 02 - 17.
[13]科大卫,刘志伟.“标准化”还是“正统化”?——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中国文化的大一统[J].历史人类学学刊,2008(1):1 - 21.
[14]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杨丽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04.
[15]郑杭生.论“传统”的现代性变迁——一种社会学视野[J].学习与实践,2012(1):5 - 12.
[16]杨复竣.中华始祖太昊伏羲:中华远古文明探源(上册)[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410 - 417.
[17]林秀珍.新乐伏羲庙大殿复原设计[J].文物春秋,1995(4).
[18]中国·新乐第四届伏羲文化旅游节即将举行[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半月),2008(3):74 - 75.
[19]李宁民.人祖伏羲与宗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91 - 106.
[20]黄若然.故里之争与记忆重构——以汉阳、蔡甸的“知音故里”为例[J].民间文化论坛,2020(1):96 - 104.
[责任编辑:刘兴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