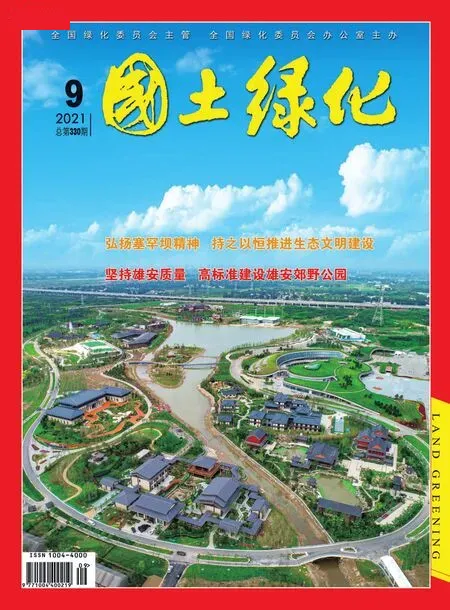不要跟一棵树过不去
◎ 寒石
一棵树,站那里,用叶子、花朵、果实和独有的气息表达,没有更多的话语。
确实,树的表达方式有限。风搔一搔树的胳肢窝,树叶忍不住簌簌;鸟儿在树枝间雀跃、聒噪,树叶也跟着簌簌;熊孩子没事摇一棵树玩,摇落一地的叶子、花朵或果实,它也至多簌簌几声……是的,簌簌是树唯一的语言和情感表达,它开心时候簌簌,生气时候簌簌,愤怒时,也还是簌簌!
说到底,树就是个哑巴,簌簌其实也不能算树的语言,那只是树受外界干扰,叶与叶、叶与枝碰擦发生的物理反应。包括花朵与果实,本身都是树成长、繁衍的一部分,说是树开心快乐的一种表情,那只是人的牵强附会。
树如果能说话,我猜第一句应该是——簌簌,别理我!第二句——簌簌簌,离我远点!树与人,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两种生物,人无法与树进行心灵的、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人面对一棵树,或赞一声,抱一抱,在树下乘乘凉、避避风、躲躲雨;或动一番歪心思,谋划这树什么材料,有什么用,如何把它砍倒,掘起,搬走。树面对人,不会欢欣鼓舞,笑语如莺;也不会捏着鼻子,叱一声“呸”后撒腿就跑。它跑不了。它能做的,是努力让自己生长得更好!
是的,树哪里也去不了,它没有脚,只有根。脚与根,最大的区别,前者擅长行走,想去哪去哪;后者用于扎根和坚守。树是为站立而生的,无论命运之神把一粒种子安生在什么地方,沙漠、峭壁、峰巅,还是旷野、平畴上,它都只想踏踏实实扎下根,踏踏实实生长,十年、百年乃至数百上千年,从一棵幼苗成长为一棵遮天蔽日的巨树。在树的语汇里,没有走与不走、想哪去哪的字眼。行走与游荡,不是一棵树的本分。
一棵树,在和煦春光里岁月静好,在酷暑烈日下风轻云淡,在暴风骤雨中傲然伫立,在冰雪严寒里萧飒成一幅水墨、一尊雕像,它不会游移半步。即便面对人类砍伐的锋利刀锯,也一样。一棵树如此,一块林子、一处丛林、一片森林,同样如此。树懂得,根即本,挪则死,它至死也不会丢弃一棵树的本分。
并且,树是公认的人类生命守护神、绿色朋友。它能吸入污浊的二氧化碳,吐出让人气象万千的生命之氧。
可是,面对这样一个没有脚、不会开口说话的朋友,人们对它的残害方式令人咋舌。当人觉得一棵树有碍自己生活和生活秩序时,会毫不犹豫地举起砍伐的屠刀。我见识过太多摧残树的方式,手段残忍,无所不用其极,令人发指。一棵树,在最靠近地面的部位,被环切剥皮;一棵树,在树干周围,燃起焦泥灰堆;有人悄悄往一棵树的树冠上,喷洒除草醚;有人偷偷往树扎根的土壤里,浇上机柴油……种种这些,根本目的,是造成树自然死亡的假象,以逃脱道义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还有人更简单粗暴,直接把一些树剃了头、折了腰。究其缘由,仅仅是这些树,影响他家采光,或蔬菜成长。
人是要有底线的。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底线,是不要冲着一个有语言障碍的人咆哮、训斥,或夸夸其谈;不要试图“鼓励”一个下肢残障人士,说:你可以的,起来走几步!这样的鼓励,无异于寻衅。再就是,不要跟一棵树过不去,轻易向一棵本本分分的树,举起砍伐的刀锯!
树所求无多,仅仅是一处,能容纳它的立锥之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