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声腔研究》序
□ 王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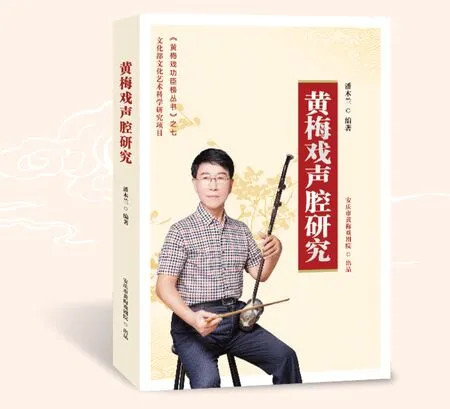
中国戏曲究其根本言,应属“听觉”艺术。这不仅从早期大量有关戏曲的论述,多被称为“‘曲’论”或“‘唱’论”可得印证;即便从表演和演出形态,也可见其一斑。早期的演员,人们习惯地说他(她)是“唱曲的”。演戏被名之“唱”戏,看戏则理所当然地被说成是“听”戏。甚至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之说。我们今天所说的戏曲是“综合艺术”、“视听艺术”或者“歌舞演故事”,其实是清代从魏长生到高朗亭再到程长庚把演员的妆扮表演提升到很高层次并最终在京剧中确定了“四功五法”才渐次形成的。即便如此,“唱”(“唱念做打”)与“歌”(“歌舞演故事”)仍是首当其冲的。由演唱一门或者主要依据演唱,派生了京剧的“新老三鼎甲”、“四大须生”、“四大名旦”、“南齐北马关外唐”以及越剧的“袁”“范”“尹”“傅”“徐”“戚”“王”等“十三派”和豫剧的“常”“陈”“崔”“马”“阎”“桑”等“六大名旦”甚至众多的地方戏曲表演或演唱派别。由此构成了中国戏曲有别于其他一切戏剧形式的独特风采,也着实形成了迄今仍风头不减的“演员时代”。“唱”之于戏曲简直就像面粉之于面包,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主材!当今戏曲艺术的式微,理由纵然有千条万条,演唱艺术的退化,当属理由中的理由。
戏曲演唱的重要,不仅在于人们一直把演戏等同于唱戏,视唱为演,无唱即无戏。更在于“唱”还是“戏”的主要载体,故事、人物、美感等主要审美信息都要靠它来传递。没有了唱,戏曲的美感功能便难得实现。很多优秀剧目之所以家喻户晓;很多消失的剧种之所以还能留住人们的一丝记忆;很多既往的演员之所以还不曾离我们远去,究其根本,正是得益于他(它)们创造的那些优秀演唱的存在。好的演唱能超越剧目、超越舞台、超越时空,纯化为一种独立存在而嵌入人们的生活中。
黄梅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演唱的成功。一说到喜爱黄梅戏的理由,人们总是把“好听”二字挂在嘴边。诚然,“好听”离不开音乐的远端设计,但人们感知的还是最终由演员口中送出的演唱。远端的一切成果,均须由终端的完美显现来了结。故此,黄梅戏的好听,演员们的演唱功不可没;黄梅戏的成功也与演员们的成功密不可分。也正缘此,人们亦有理由认为,当今黄梅戏发展的不尽如人意,或许正与具备较高演唱水平的好演员的不足有关。
潘木兰先生系由演员出身,上世纪50 年代末毕业于安庆艺校即今安徽黄梅戏艺术职业学院。先在黄梅戏舞台上“唱念做打”,之后又从事文化行政管理工作,最后又回到曾经哺育他成长、给予他最初的也是最关键的艺术认知的母校任教。这个认知就包括他对戏曲演唱价值的认定。结合它自身的艺术实践尤其是做文化行政管理和剧团团长工作而得以更深了解到的观众对于演唱的需求以及演唱对于演出成败和剧种兴衰的责任,直到退休前,他都以全部身心投入黄梅戏的唱腔教学与研究。不仅为黄梅戏培育了多位在演唱艺术上成就不凡的中青年演员,而且也在不经意间填补了黄梅戏研究和学术建设的一项空白。不仅使所在学院在黄梅戏声腔教学上独树一帜,而且也使得主要依靠该校提供表演人才的安庆市各级黄梅戏表演团体在演唱上颇显优势。其意义超出了教学、超出了表演、也超出了个体成功而惠及整个剧种。我想,这或许就是他由于热爱而对黄梅戏作出的想做而又能做的最实在最光彩因此也是最具有生命意义的事。每一个热爱黄梅戏又从事黄梅戏的黄梅戏人由潘木兰先生的实践中都应当感悟到,我们天天喊着要“唱响”的黄梅戏,我们该如何“唱好”?
潘木兰先生的这本《黄梅戏声腔研究》,与以往有关黄梅戏的其他著作不同,没有过多的理论放言,也不追求过分的学术气象,而是集中笔墨,细细推敲,反复体味,心无旁骛而又颇具视野地把黄梅戏演唱的学理、技法研深、钻透。对黄梅戏的如何“唱好”并进而实现“好听”作了大量的既定性也定量的条分缕析,有着极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其关于声腔的“唱”与“润”、“曲”与“润”辩证关系的探讨及“三功四法”,即“声”、“字”、“气”;“情”、“字”、“色”、“味”的体悟,均别开生面,义理交融。无疑将对黄梅戏声腔的学科建设和黄梅戏演唱的理论开拓有所裨益。应当被视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基础性和方法性的理论著作,一份饱含体悟与用心的成果与奉献。
当今,黄梅戏的发展遭遇了新的瓶颈,连续多年业绩平平。很多演员已多年不练功,不练唱,这里或许有待遇低,诱惑多,机会少等客观原因,但是一个演员的沉沦或者一个剧种的退化,往往就是由训练尤其是对唱腔训练的废弛开始的。一旦没有了演唱上的真功夫,竞争力就会弱化,观众就会疏离,剧种也就岌岌可危了。潘木兰先生及其著作的意义正在于它让我们读懂了他对戏曲本质与戏曲危机的认识,看到了他对黄梅戏的忠诚与挚爱。我们如果真心希望戏曲振兴,希望黄梅戏持续“唱响”,那我们就肩起我们责无旁贷“唱好”的责任,让久违的练声、练唱,揣摩唱腔重回我们的生活。
“唱响黄梅戏”必先从唱好始!这是潘木兰先生此书给我的启示,也是我欣然为序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