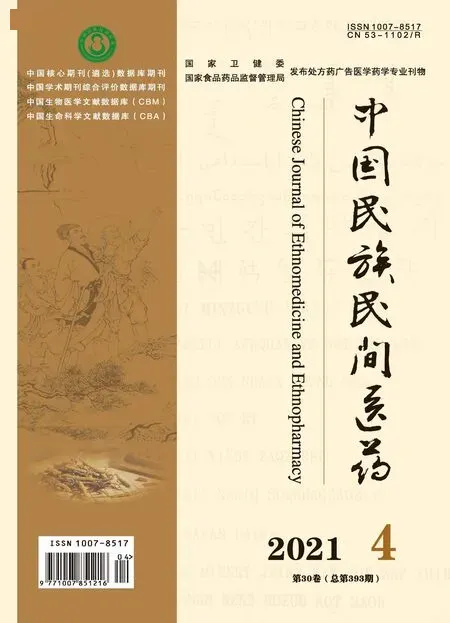傣族传统文化对傣医外治法发展之影响
谢昌松 李 媛 陈 普 李琼超
云南中医药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傣医外治法是傣医最具特色的治疗方法,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在数千年积累、沉淀的过程中,受到傣族传统文化,如宗教信仰、自然环境、生活习俗等的影响,傣族传统文化与傣医外治法交融甚广,联系密切,傣族传统文化是傣医外治法萌生、发展的土壤。
1 傣医外治法的形成与原始宗教密切相关
1.1 巫医同源 傣医学与原始宗教同一起源[1-2]。在“万物有灵,灵灵相通”观念的支配下,傣族认为神创造医药,必须听从神的旨意,求神送鬼的巫师应运而生。钱古训所著《百夷传》中记载:“病不知服药,以姜汁注鼻中,病甚,命巫祭鬼路侧,病虐者多愈,病热者多死”[3]。由此可见,在古代傣族民间已有外治疗法,但并不排斥巫术,而是采用巫医并用的方式治疗疾病,很好地佐证了巫医同源并用的史实。纹身是傣族图腾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5]。在纹身过程中意外发现针刺身体某些部位可以缓解疼痛,治疗疾病,由此产生了“沙雅”疗法(刺药疗法)[4]。此外,口功疗法的产生与原始宗教有着深厚的渊源,是“神药两解”的典型代表,是一种以念口诀为主,用口吹、手摸患处治疗疾病的外治方法。目前该方法在民间广为流传,尤其被广泛用于骨伤科疾病[6]。
1.2 天人合一整体观的形成与原始宗教密切相关 原始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影响傣医外治法天人合一整体观的形成。傣医十分注重季节气候及地理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并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与自然界的变化融为一体,遵循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运用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天人合一观诊治疾病。《档哈雅》中记载不同季节服用的防病处方和外治疗法,如冷季寒冷,多用辣味药,运用暖雅(睡药疗法)、烘雅(熏蒸疗法);热季炎热,多用苦味药物,并运用沙雅(刺药疗法)、达雅(搽药疗法);雨季潮湿,多用香涩味药物,运用阿雅(洗药疗法)、剔痧(除痧疗法)[7]。在药物的采集、使用上,也非常强调应顺应自然界对药物生长的特定影响,认为不同时令、不同季节、不同时间、不同地理、不同环境中药物作用不同,药效强弱有异。《嘎比迪沙迪巴尼》中记载:5、6月份采花、枝、叶、种子(果);清早采果(种子);正午采花;下午采树心;傍晚采树干、根茎;黄昏至凌晨药效在嫩尖;正午至下午药效在树心;正午至黄昏在树皮;下午至黄昏药效在根部[8]。顺应自然的药物采收规律为傣医外治法喜用鲜药、善用鲜药提供理论依据。
1.3 生命观的形成与原始宗教密切相关 傣族创世史诗《巴塔麻嘎捧尚罗》记载地球是英叭天神用水混合其他物质造成的,水是孕育万物之源[1]。傣族对水的崇拜影响着傣医生命观的形成。傣医认为:“没有水,万物可以枯死,人体没有水,生命就难于存续”,水是人体生命活动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物质,水可消除九十九种疾病。水被用于解释生理变化、阐释疾病、治疗疾病。《嘎牙山哈雅》中指出人体内有12种水,若发生病变可从水塔论治[1]。傣族民间传说笋塔与金掌“圣迹”故事中也描述了水可治疗瘿瘤、眼疾[3]。此外,口功疗法、睡药疗法、熏蒸疗法、洗药疗法、拖擦药物疗法等特色外治疗法的主要介质就是水,这些与水有关的外治方法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2 南传佛教促进傣医外治法发展完善
2.1 为傣医外治法提供理论构架支撑 据大量史料考证,傣医学的四塔(风、火、水、土)、五蕴(色、识、受、想、行)理论广泛记述于《巴腊麻他坦》、《维苏提玛嘎》、《嘎牙山哈雅》等文献中,与南传上座部佛教《解脱道论》、“观四大”、《大象迹喻经》等经典中所记载的“四大种”“五蕴”有相似之处[3]。傣医在积累和总结医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借鉴佛教的“四大”“五蕴”概念,吸收其合理的成分,形成自己的四塔五蕴理论。傣医将四塔五蕴理论运用于外治之中,为阐释病因病机、疾病发展变化、法立组方提供理论依据,是外治法的核心理论。如用入水塔的旱莲草外擦身体治疗火塔偏盛,水塔不足引起的发热,用睡药疗法治疗火塔不足的病症,用洗药疗法治疗水塔过盛的疾病。
2.2 充实傣医外治法内涵 随着佛教的传入,大量的医学内容也随之传入。论藏“阿皮达马”中记载人的生理、病理和医药知识,如人的皮、肉、血、骨等生理现象。并认为不同的属相,不同的出生月、日具有不一样的皮肉和血骨,月份决定皮肉,日期决定血骨[3]。傣医吸收其所长,在诊治病时要详细询问病人的属相、皮肉和血骨,以判断人的生理现象与自然界环境的关系,综合归纳各种病因,以便诊断,采取相应措施治疗疾病。此外,傣药中有不少来源于印度的传统药物,随着佛教的传入成为傣族民间药物,如儿茶、槟榔、姜黄等,丰富、充实傣医药,如姜黄被广泛运用于包药疗法、睡药疗法、熏蒸疗法、搽药疗法之中。
2.3 促进傣医外治法的传承及发展 佛教的传入,促进了傣文的创制和应用,为傣外治法的记录、学习、交流、传播提供了工具和条件,促进傣医外治法的应用与发展。有传说在八万四千册的佛经中,医学经典就有四万二千册[3]。同时,佛教传入后,几乎每个傣族村寨都建立佛寺,傣族男性青年在佛寺中接受教育,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其中包括医学理论和医药知识。佛寺成为培养傣医药人才的学校,为傣医外治法的学习、交流、普及、继承、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是承载傣医外治法的摇篮。
3 贝叶文化推动傣医外治法文献整理
贝叶文字载体的产生和发展,加速了傣医外治法知识的收集、整理、保存、应用,涌现出众多傣医著作,如《嘎牙山哈雅》、《档哈雅龙》、《桑比打嘎》等[3],书籍中记载大量医学知识及外治疗法。《嘎牙山哈雅》记载人体基本组织及脏腑功能为傣医外治法提供解剖基础及治疗机理。此外,书中论述人与气候、居处环境与疾病发生的关系,各季发病特点及预防措施、常用方药,三个不同年龄阶段生理变化、好发疾病及防治方法,这对傣医外治法临床运用具有较高的指导价值[7]。
4 雨林滋养傣医外治法
4.1 提供丰富独特的药用资源 傣族先民认为,雨林曾是他们的诺亚方舟,使傣族躲避了灭项之灾,保存了种族。因此傣族认为有雨林,才会有生命,至今都保留有树崇拜的习俗。傣族谚语说“狩猎不要进神林,撒网不要进龙潭”。傣族人民对雨林充满崇敬、敬畏、保护的情感观念及价值体系,成就了西双版纳“植物王国”“天然药物宝库”和“傣药王国”的美誉。丰富的药用资源为傣医药及其外治法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垂手而得的新鲜药物使傣族喜用鲜品,善用鲜品,无论是外洗、外包、外擦、坐药、睡药、熏蒸或是刺药,傣医推崇鲜品为佳。此外,驱避剂、烟熏剂、佩挂剂的应用,也与热带雨林丰富的药用资源息息相关。
4.2 创造富有地方特色的治疗方法及理论 在雨林这座“天然药物宝库”中,傣族先民不断探索、发现、总结和积累着医药知识,创造富有地方特色的治疗方法及理论。据《阿尼松桑顺细点》《登达格》等史料记述,傣族先民在“天然宝库中”以野生动植物充饥的过程中,获得大量外治法。如“光冒呆”(鹿不死之药)包敷患处治疗骨折,重楼外包治疗毒蛇咬伤,鸡矢藤熏蒸治疗头痛,生藤编制帽子预防感冒[10],大扬草外擦、外洗治疗牛皮藓[5],睡药疗法治疗风湿病。这些外治方法及药物的发现,都离不开热带雨林的馈赠。此外,富有地方特色的傣医药理论也源于雨林,如四塔五蕴理论、雅解理论、风病论。傣医对四塔及四塔之间的关系阐释,来源于对热带雨林的长期观察及体悟,雅解理论的起源来自于解毒药物文尚海的发现与应用,风病论来源于对自然界风的启发与感悟。
5 酒文化丰富傣医外治法
5.1 酒炙 傣族的酒文化历史悠久。在傣族传说中,酒来源于野果。明·钱古训《百夷传》记载在元、明之际,在傣族地区,“其地有树,状若棕,树之梢有如竿者八九茎,人以刀去其尖,缚瓢于上,过一霄则有酒一瓢,香而且甘,饮之辄醉。”[3]酒,傣语称“劳”。傣族人民在长期的造酒、饮酒的过程中对酒的特性有了认识并加以利用,如酒炙被广泛运用于外治疗法中,治疗风湿麻木、肢体疼痛各症时,先将傣药切碎加水煎煮或炒或蒸,再拌入酒或炒热之酒糟,患者趁热睡于药床上。接骨或治疗跌打扭伤、风湿麻木疼痛、头痛、腰腿疼痛等症时将鲜药,切碎捣烂加入酒置于火上炒热,趁热包敷于患处。《傣族传统医药方剂》载治疗肢体关节疼痛时用药粉加酒炒热外敷[9]。
5.2 药酒 傣医认为酒是良好的有机溶媒,药物的多种成分均易溶于酒中,故创制了大量的外用药酒方。如西双版纳州傣医院制剂劳雅打拢梅兰申(外用追风镇痛酒)用大剂量白酒浸泡飞龙掌血、鱼子兰、姜黄等药物,通过外擦或睡药或拖擦或熏蒸等方式治疗中风偏瘫后遗症、风湿病、痛风引起的周身肢体、肌肉、筋骨酸麻胀痛或痉挛剧痛[9]。治肢体关节、肌肉、筋骨酸麻胀痛,活动不灵,屈伸不利,取飞龙掌血、黑皮跌打、大叶钩藤(怀咪王)、树菠萝树心等药物泡酒外擦患处[9]。治小儿高热不退,取木奶果鲜叶适量,用火烘烤后放入酒中浸泡,取药酒擦患儿双上肢[9]。
5.3 以酒入方剂 傣医喜用酒,善用酒。傣医认为酒为甘辛大热之品,具有补火散寒,祛风活血,消肿止痛,通行血脉,引药势行全身之功。酒可以增强药力,改变药性,因而无论是丸剂、散剂、水浸剂、磨剂还是酊剂中,多将酒配合其它药物用于临床,具有独特的疗效与保健作用,睡药、刺药、搽药、拖擦等方剂中多用到酒。
6 小结
特定地区的特定生活、生产环境形成了特定的医药,傣医外治法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傣族特有文化的滋养,深受傣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傣族传统文化与傣医外治法交融甚广、联系密切,傣医外治法吸收、融合了傣族原始宗教、南传佛教、贝叶文化、雨林文化、酒文化的内涵,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及区域特点的治疗方式。